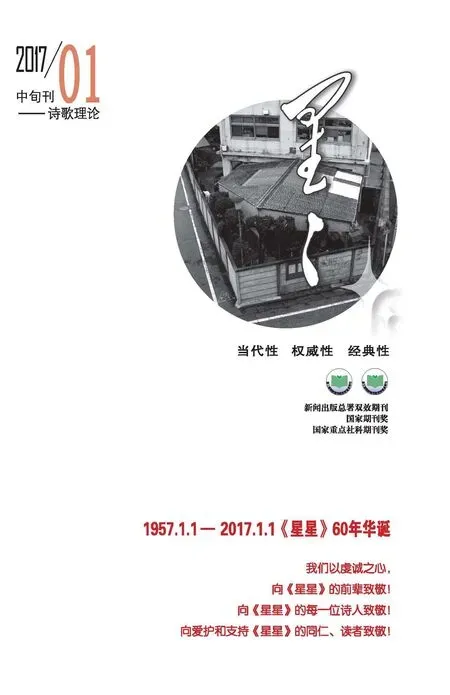论现代汉诗“词的歧义性”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2017-07-05范云晶
论现代汉诗“词的歧义性”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范云晶
范云晶(1976—),内蒙古牙克石人,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现当代诗歌的研究与批评。曾在《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文坛》、《青海社会科学》、《诗探索》、《星星·诗歌理论》等期刊发表文章数十篇。参与《2015年诗歌选粹》、《2016年诗歌选粹》以及《2016年散文诗选粹》的评点工作。有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一
现代诗人试图寻找具有这种特性的词:有力量、可增生、多样化,既能相对准确和充分表达想要表达之意,言明想要言及之物,又能超越其本身,具有不受词典意义限定的灵动性和活跃性。“只需要一个词/树木就绿了/只需要一声召唤,大地上/就会腾起美妙的光芒”。[1]同样是让树木变绿,古典汉诗似乎也有类似的文本闪现:“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泊船瓜洲》),但具有此种神奇魔力的施动者却不相同。“春风又绿江南岸”,与其说在夸赞词的能力不如说是物的力量,能使“江南岸”变绿的不是“春风”这个词,而是“春风”这个“词”所指称的“物”。假如把“春风”替换成其它词,这种力量就无法生成。而王家新诗中的施动者则是“一个词”而非“词”所指称之“物”,言说重点是“词”,“词”具有能使树木变绿的强大力量且充满变数:“一个词”只说明了数量,却没有具体所指,因此可以把它想象成无数个词和无数种可能。
“一个词”至少具备以下特质方能使树木变绿,且具有让大地腾起美妙光芒的力量:首先是有营养的,即要有效用。只有养分充足,才能在光合作用下产生丰富的叶绿素,从而使树木变绿。其次有言说权力和主动性(反抗力量),树木变绿的时间只发生在春夏两季,自动过滤掉秋冬两季的到来,阻止树木变黄和干枯,这其实是一种反抗,反抗的成功来自于一定的言说权力和自主性。再次是有力量,具有阐释力和言说效力,能化腐朽为神奇,化简为繁,化平庸为卓越,化暗淡无光为绚丽多彩。最后是多元和多样,美妙的光芒需要由多种颜色、多束光线汇聚融合而成,单靠一种颜色或一束光线,也就是词语的单一意义或字典(词典)意义,无法产生“复合性”功效。一旦找到了词语的这种特性,或者具有这种特性的词,现代汉诗就能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达到文体自身的理想状态:活跃非僵化的、自由非束缚的、细腻非粗糙的、任意非随意的、流动非限定的、变动非固定的、繁复非单一的……这个看似简单实则艰巨的任务只有靠“词的歧义性”或充满“歧义性”的词才可以完成。
“词的歧义性”被需要或必须存在的理由在于,它满足了现代汉诗文体“是其自身”的根本需求,并对现代汉诗发展大有裨益。不妨承认这样的等式:“歧义=奇异”,现代汉诗需要“歧义”这种更为有效的词语特质进入语言内部,并向外敞开,言说更复杂的人生经验,处理更棘手的现实和写作问题,从而产生“奇异”的效力。“词的歧义性”带来的“奇异”效力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丰富”(rich)。“丰富”一词至少解释如下:多与广、放大和膨胀、裂变和增生、多元与复杂等等。“丰富”被转译为动词,暂且可称之为“动态意义”,含有“能够允诺、能够提供、能够让获得和让得到”[2]之意。“动态意义”似乎比原始(字面)意义更“丰富”,也更有深意:它对“施动者”和“受动者”同时发挥作用,产生效力,即皆为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无论是“允诺”和“提供”,还是“让获得”和“让得到”,“丰富”都是针对双方的,对内和对外,向内和向外,对“词”与“物”同时有效,而不像“丰富”的原始(字面)意义只针对“单边”,即作为“受动者”的“物”有效。“词的歧义性”既对现代汉诗语言本身有益,又对现代汉诗所需要面对和阐释的物/世界有利,二者皆可变得“丰富”。“能够允诺和能够提供”是说“词的歧义性”保证了现代汉诗具有言说复杂物世界的资格和能力,这种资格和能力的获得足以说明现代汉诗语言本身首先是“丰富的”,所以才能“被允许”与日益复杂的“物”展开对话,并提供多种阐释可能;“能够让获得和让得到”意味着通过“歧义性”的增生和裂变,现代汉诗语言更加丰富和更具阐释效力的同时,“物”亦在阐释中获得更多意义,从而呈现出本应具有的复杂样态和多元样貌。“丰富”的“动态意义”所呈现出的“双向运动”线路其实是“两条”:一条是“词——物——词”,“词”作为起点和终点,“物”处于中间位置。“词”的丰富并获得言说“物”的资格,在言说过程中,使“物”变得丰富,“物”的丰富又激活了“词”;另一条是“物——词——物”,“物”作为起点和终点,“词”处于中间位置。“物”的“丰富”提供了“词”言说的多种可能,“词”的丰富反过来又促进“物”的丰富。将这两个意义链连接在一起,就是“词——物”丰富的无限循环,“词的歧义性”对“词”与“物”均产生决定性影响。
二
“词的歧义性”决定了“现代汉诗是”和“现代汉诗说”的“质”。首先从现代汉诗的文体合理性(合法性)角度来说(对内),至少在语言层面,它决定了现代汉诗是其本身,即“现代汉诗是”。“当古汉语已经充足圆满、固步不前,仅属于往昔,现代汉诗却翻转过来,不要拘束,满含可能性,用未来追认着它的此刻。由这种语言成就的现代汉诗,自由度可谓相得益彰……现代汉诗拒斥那种制服般的格式和像镣铐一样给自己带上的铁律,实在是本能和本性使然。”[3]把禁锢变为自由,把“少”变成“多”是现代汉诗彰显其自由精神品质,达到理想状态的重要衡量标准,决定着它的“诗质”。“词的歧义性”的有无可以区分和辨别出汉语诗歌的古今差异,以及与其它体裁之间的文体差异,并通过“两个独特性”的确立完成了现代汉诗“诗质”的构建:一是“现代性”,即同一文体的时代特性,主要指迥异于古典汉诗的现代诗歌语言范式。现代汉诗从肉身到骨骼,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自己专属的,不能变成内容古典的“肉身”穿上形式现代的“外衣”,汉语新诗初创时期的“旧瓶装新酒”问题就与之有关。二是“诗性”,即不同文体的语言特性,主要指不同于现代小说、散文等其它文体的现代诗歌语言范式确立,只有兼具这两个独特性才能称为现代汉语诗歌。“我们想写出的仿佛是这样的诗:既有能力改造现代,也有能力改变古典”[4],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代汉诗既与古典汉诗不同,也与宽泛使用现代汉语的其它文体不同。现代汉诗既依赖于现代汉语存活,又有着比现代汉语更多鲜活的质素。相对于其它文学体裁,诗歌语言更具多样性,这也是一直强调“词的歧义性”是现代诗歌的特性而非缺点的原因。
如果不通过对外敞开的方式,既有的有限词语难以敏锐地捕捉、精准地言说“物”。“词语,刀锋闪烁/进入事物/但它也会生锈/在一场疲惫的写作中变得迟钝……//这时就有刀锋深入,到达、抵及/在具体、确凿的时间地点/和事物中层层推断/然后,一些词语和短句出现/一道光出现”[5]。“词的歧义性”就像是一道光,闪烁着全新意义的光芒。与古典汉诗可供使用的词语相比,现代汉诗语言无疑变得更为繁复和灵活,单音节向双音节的转变,叹词的丰富,词义的扩大甚至转移等语言现象[6],都可以体现出这一变化。“词的歧义性”是由外部增生获得的,与词的本身意义的变化增生与否关系并不是很大。无论从古到今的语言如何变化,词语最基本的固定涵义不会改变——由“日”变成双音节词“太阳”指称的仍然是太阳,而不是星星和月亮,其它词语亦如此。这就需要旧词借助具体语境和上下文联系生发出新意,这样才能让词变得丰富绚丽。“陈词滥调是不够用的,于是我们会急得吐字不清,并且破坏词语,为的是使这些词能变得刺耳,使人们能看见这些词,而不是知道它们”。[7]“知道”未必是被运用(使用)的,躺在字典里的词人们同样知道,“看见”则意味着词逃离了词典,活跃于诗行之上,被运用,被灵活运用。
“词的歧义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现代汉诗的语言潜质。在词语数量和语言样态已经基本定型的前提下,再次大规模创造发明词语已经无法实现。即使能够实现,也与“词的歧义性”能够产生的“多义”不同。既有词语的“歧义性”与“新词”的差异就如同由一个点散发出的无数条射线和平行线的区别,前者有一个原始和开始的点,散射,后者则永远没有相交之处。前者可以窥到差异与不同,区别与联系,既有语义关联,又有语义差异。关联和差异共同存在,才能看到词、物以及词与物之间关系的多样性,也才会更有效。后者却只能看到差异和不同,旧词与新词、物与物之间的差异。更何况创造新词的这种假设和可能本身是难以存在和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出,“词的歧义性”所发挥的作用是唯一有效的,其它手段和方式无法取代。
卞之琳先生说中国新诗应该解决的问题是缺乏“自有的文字”[8],这里所说的“自有”不是说词语或者文字只存在于现代汉诗之中,而是强调“不模仿”、“有个性”和“有新意”的特质。“词汇借助自身的附带意义而重新成为心灵的客观对象,从而带来一种新的特性。”[9]要想保证词语的迷宫一样的特性,要想让“这些词汇能站起来,必须发明新的方法,而不是‘象带子一样陈列在纸上’”[10]。所谓“新的方法”必须是在保留词的原有意义的前提下,又借助于具体语境重新生成新的“临时意义”,这就是指“词的歧义性”。“词的歧义性”产生的过程是剥皮(原有附着意义)留核(中心意义和核心意义),重新再生的过程(新的衍生意义),就像周伦佑笔下的果核:
语言从果实中分离出肉
留下果核成为坚忍的部分
许多花朵粉碎的过程
使果核变小,但更加坚硬
一枚果核在火焰中保持原型
……
果核有时会炸裂开来
长出一些枝叶
结出更多的果实和头颅
或者一座城市[11]
(周伦佑:《果核的含义》)
“果核”是果实的最核心部分,是种子,可以结出更多新的果实。“词的歧义性”就是果实,具有丰富的增生空间和生长余地。“在诗歌里,所有的成分都在被使用的过程中经历了某种变化,获得了比它们原有的简单的抽象的字典意义更丰富的涵义”[12],这种灵活,这种变化,这种“丰富”,保证了现代汉诗是其自身。
其次,从现代汉诗(敞开)功能来说(对外),“词的歧义性”决定了现代汉诗具备言说世界/物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实现阐释的实效性,有效性和多效性,即对“现代汉诗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13],这句话可以进一步表述为:“词的歧义性”缺失处,无多样性之物可存在。词语的清晰、单纯和透明无法有效阐说复杂多变的世界,“无法”不是“不能”而是“无效”,所谓“无效”不是指浮皮潦草地触及事物的表面,而是说难以到达或者企及“物”的核心和实质——“清晰明确地表达的概念注定要消亡”[14]。只有“词的歧义性”才能更有效,至少是接近最大可能。它把现代汉诗中的词语由“一”变成“多”,意味着阐释物的效力的增强,并还原了“物”本身的复杂性。恰如当代女诗人代薇所说的“美是接近美的方式”一样,“多”是接近“多”的方式,“丰富”是接近“丰富”的方式。现代汉诗词语自身的丰富成就了“物”的丰富。“惟有词语才能把一种关系赋予给一物。惟有词语才能让一物作为它所是的物显现出来”[15],不妨说惟有“词的歧义性”才能把多种关系赋予一物,才能让一物作为它可能是的物显现出来。“月亮”是“月亮”,又不是“月亮”,是“思乡”又不单单是“思乡”,它可以有多重表述方法,也可以指涉很多物。“一物”尚且可以扩展出多种可能,展现多个侧面,按照词的数量累积和叠加,“词的歧义性”所能够呈现的,定是丰富、变换无穷的“物”世界,“你变换着钥匙,你变换着词/它可以随着雪花飞舞”[16]。这些词从固定意义(a fixed meaning)的链条脱落,重新接续出新的意义,以外部增生的方式获得意义的丰富和增殖——“宇宙万类的印象都活在里面”[17]。由“多”阐释“多”,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差异性和多样性。
“由语言说出的世界大于世界本身。”[18]用语义单纯透明之词言说物时(没有歧义性时),考虑更多的是相似性,过多相似性集中在一起,“物”就会被缩小,直至变成一个点,“世界的所有部分都会接合在一起,相互联系,而没有断裂,没有距离,类似于那些金属链因交感而被一块磁石吸住悬在空中一样”[19],无法容纳更多异质和多样性。这是古典汉诗和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现代汉诗都存在的问题。“词的歧义性”则会把“物”在显微镜下放大数倍,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更多,物的差异性和相同之处得以清晰呈现,甚至每一个纤维,每一根细小绒毛,每一个细胞。它“能将任何一个地方射来的最微弱的光芒从世界的变幻莫测的影像中析取、分离,并投射到另一个世界的白色幕布上。那另一个世界,白色的世界,就是可能性”[20]。“词的歧义性”是对“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的一种有效介入,或者说所缔造的“可能世界”比现实世界更丰富多彩。
在《诗歌语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中,朱丽亚·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认为诗歌语言有两种作用:“一种是象征的作用(Symbolic Function),一种是符示(Semiotic Function)作用。在前一种情况中,符表(Signifer)与符义(Signified)之间的关系是被限制的。在后一种情况中,符表与符义的关系并没有固定下来,而是处在不断的生发、变化之中。”[21]诗歌语言的这两种作用可以用来说明古代汉诗的“一一映射”和现代汉诗“词的歧义性”之间的差异和不同,前者类似于“象征”作用,后者则更像是“符示”作用,彰显的是语言的多样性,而非单一性。“把活生生的词语转化为固定的对象,机械的原子,必然由一种新的联合的力量(即“词的歧义性”——引者注)把它们重新卷入生活过程的漩涡之中”[22]。词语只是一个引子,由它生成意义丰富的迷宫,就像商禽的诗歌《逃亡的天空》:
死者的脸是一无人见的沼泽
荒原中的沼泽是部分天空的逃亡
遁走的天空是满溢的玫瑰
溢出的玫瑰是不会降落的雪
未降的雪是脉管中的眼泪
升起来的泪是被拨弄的琴弦
拨弄中的琴弦是燃烧着的心[23]
“诗的道德在于,诗从未背叛过迷宫”[24],而建造“迷宫”的材料无疑是词语。商禽用词语的迷宫描绘出一幅名为“逃亡”的心理变化轨迹图。近十个看似不搭界的词语,以蒙太奇的方式,断点式思维,用“逃亡”这个新的“联合力量”神奇地拼接在一起,大致沿着两种情感脉络展开:失望和希望,再将两者延伸和深化、衍生出无望和绝望,想表达了不愿逃离又必须逃离,想要逃离又难以逃离的内心纠结和两难窘境。这首诗完全是一个环形结构,意味着一种循环。按照词语出现的先后顺序,商禽的这首诗可以用以下长串等式表达:“死者的脸=荒原中的沼泽=天空的逃亡=满溢的玫瑰=未降的雪=管中的眼泪=被拨弄的琴弦=延烧的心=沼泽的荒原”,由“荒原的沼泽”和“沼泽的荒原”开始和收尾,并由“A是B”这样的句式把所有词语连接,成为等式。等式成立的前提是以“逃亡的天空”作为统筹,如果离开了这个主题的串联,A就无法是B。A是B,A又不是B,单个词语看起来透彻清明,如果脱离逃亡主题,又因难以捕捉语外意义而变得含混不明;这些词语都是逃亡的所指,仿佛又与逃亡无关。恰恰是因为这些词的运用,才使得逃亡变得如此丰富和清晰。它们可以看作由词语“逃亡的天空”歧义生出,每一个词都可以表征为“逃亡的天空”,每个词又都有其表达内心情感的细微差别,不能完全等同于“逃亡的天空”,亦不可相互替代。正是这种歧义的存在,商禽笔下的“逃亡”已经远非原有词语“逃亡”得以涵括和说清的,意义被无限放大并复杂化。原有认知中的“逃亡”场景和心境变得不再熟悉,“一个最终被我们理解的词,出现在另一首诗里,一下子又变得那样陌生”[25]。既有词语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灵魂一般,活泛地、机灵地具有了新的阐释能力,“因为是陌生与最陌生的结合,我在眼里看到了新的光亮”[26]。
三
前面论述了很多需要“词的歧义性”存在的理由,如果不存在会怎样?这种假设在现代汉诗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比如1950-70年代),或在某些作家的创作中,已经成为事实。一旦失去了“词的歧义性”,现代汉诗将会面临这样的窘境:一种可能是被“打回原形”,回到类似古典汉诗词语的固化状态。古典汉诗 “稳定性” 的获得以“词的歧义性”消除和缺失为代价,“词的歧义性”不能也不必(不需要)存在其中:“不能”是说在求稳、求安全的圆形秩序限定下,“词的歧义性”对“古典汉诗是”(文体)和“古典汉诗说”(功能)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不会建设反而会因破坏文体规范和写作规则,使得古典汉诗变得不是它自己:“歧义性”增强了词语活力,“词语”变得不可控制,“词”言说“物”时变得含混不明,意义难以琢磨,甚至还存在破坏稳定节奏和固定形式的可能。这无疑会对古典汉诗业已成熟的体式有所侵害。另外,被“词的歧义”激发的“物”的多种阐释可能,最终会反作用于“词”,使“词”变得更为活跃和复杂难缠,而这一点显然有悖于古典汉诗的文体秩序和稳定性。“不必”是说没有“歧义性”,古典汉诗仍具有原来的特质,不会产生“致命”性和根本性影响。“词的歧义性”的“反规训”特性无法在古典汉诗中找到适宜生存的土壤。即使“不小心”遗落其中,也会在“词”与“物”的对称使用过程中(类似于一一映射),被一点点缩减和扼杀,“歧义”被“削枝剪杈”,无法生根、发芽、结果,直至变为“单义”,失去原有效力。与其如此,还不如摒弃这一曲折繁琐的“修枝剪叶”过程,直接以词语的透明来面对物更经济、更有效。因此,古典汉诗从骨子里来说是禁锢歧义性、排斥歧性性甚至是反歧义性的,当然不能也不需要“词的歧义性”存在。古典汉诗必须消除“词的歧义性”和现代汉诗必须保护“词的歧义性”是一个道理。
现代汉诗缺少“词的歧义性”的另一种可能是变成“植物诗”——就像“植物人”一样,表面像现代汉诗,却不是现代汉诗,只有现代汉诗的形式和躯壳,却没有鲜活、自由、随性、繁复与灵动的精神实质和内在灵魂。“现代汉诗”须具有“两个独特性”,而“植物诗”既不现代也没诗性,也就无法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汉语诗歌”。以195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为例,这是一种掺杂着太多非文学因素的特殊诗歌体式,是权力和政治手段规训文学的典型文本,把“政治”置于首位,排在“抒情”和“诗歌”的前面极具隐喻意义。“由于‘权力’暗中压制,话语名为表意系统,往往却变成‘强加于事物的暴力’”[27],“政治抒情诗”把很多原本不该有任何限制和固定所指的词语,强行赋予既定意义,制造出一部具有绝对权威的“词语红宝书”,“青松”、“太阳”、“红旗”等等,任何悖逆于这个词典规约的意义活用都属“非法”。以词语“太阳”为例,“太阳”所具有的发光发热、普照大地的特性和东升西落的运动轨迹能够衍生出的意义,恰好契合了政治话语的需要。歌曲《东方红》进一步明确了“太阳”的特定涵义。“太阳——领袖——红色——升起——光明”,这几个本该各自独立的词语被串联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语义系统。“太阳”被规定了颜色(红色),特性(发光发热),运行轨迹(只升不落),喻指(领袖和光明),拥有至高无上的“圣词”[28]身份,成为最具“卡里斯玛”(charisma)特点的意象,也是被歪曲,被窄化得最严重的词语。这个语义系统所描画和勾勒出的“太阳”,成为再生意义的言说基点,所有意义的延伸都必须在这一核心思想统摄之下,比如:
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啊,也一样地照亮大地的清晨。(郭小川《甘蔗林——青纱帐》)
晴空的太阳更红、更娇了!(郭小川《秋歌之一》)
母亲怀中——/新一代的太阳/挥舞着云霞的红旗/上升呵/上升!(贺敬之《雷锋之歌》)
来,让我们高声歌唱呵——/“……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
太阳醒来了——/它双手支撑大地,盎然站起。(李瑛《戈壁日出》)
我为什么如此地思念北京?/那儿升起了辐射光与热力的恒星(闻捷《我思念北京》)
赞美星星,赞美月亮,赞美太阳,/冬天照样亮在天的四面八方(严阵《冬之歌》)[29]……
“太阳”仿佛被固定意义模具塑性一般,“制作”出的“产品”(只能称其为产品)永远是一种形状,且可以无限复制。这样的复制无效,或者说是空的,它驱逐了可供想象的一切可能,简化了物的多样性。在诗歌《夏》中,穆旦指出了“太阳”指涉的失效和无意义,“太阳要写一篇伟大的史诗,/富于强烈的感情,热闹的故事,/但没有思想,只有文字,文字,文字”[30]。抽空思想,只剩下躯壳的文字毫无意义。太阳未必就是万能、就是权威,它同样需要面对挑战,“我以极好的兴致观察一撮春天的泥土/看春天的泥土如何跟阳光角力”[31];更需要打破由其缔造的神话,“亿万个辉煌的太阳/显现在打碎的镜子上”[132]。消除了“歧义性”的词语“太阳”,“祸害”和“连累”的不只是它自己,与“太阳”相关的一些词语,同样被歪曲和窄化,其意义也被圈禁在一定范围内,比如“向日葵”必须是向着“太阳”,不能把光遮住,且完全依赖“太阳”生存。其实“向日葵”也可以是反叛、逆光生长的。“它的头几乎已把太阳遮住/它的头即使是在太阳被遮住的时候/也依然在闪耀着光芒。”[33]对词语类型化倾向的匡正是“朦胧诗”出现的重要意义之一。“太阳”的一切被重新规定:由红色变为黑色,由发光发热变为寒冷甚至暴力、血腥,运行轨迹由升变为落等等。当“朦胧诗人”以“觉醒者”、“启蒙者”和“反叛者”三种姿态立于诗坛,试图扭转被歪曲和颠倒的“诗歌乾坤”时,问题亦随之出现,“把诗歌与事境相连、超越事境又为了事境的做法,使诗歌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工具论中”[34]。“去蔽”和“祛魅”的目的是为了“还原”而不是新的“遮蔽”和“赋魅”,太阳不是最大最耀眼,也不一定暗淡无光。“太阳”不是红色,也不一定必须是黑色。“新瓶装旧酒”和“旧瓶装新酒”同样需要警惕。恢复词语自由,保护“歧义性”,可以避免这一弊端。柯平的诗歌《深入秋天》或许会带来某种启示:
此刻必须摒弃全部古典意象
必须有风
吹散菊篱的陶渊明气息
推倒张生的马车
在大小螃蟹横行不到的地方
深入秋天
越过长亭短亭 咸阳古道
火浇灞桥残柳
解散大观园菊花盟
任夕阳西下
把李清照送进医院隔离
扫净如泪的枫叶 让高速公路铺向远方
然后我们才能
深入秋天[35]
(柯平:《深入秋天》)
这首诗或许还可以这样续写:必须把秋天身上的片片黄叶都一一剥离,必须把存在于诗歌中的“秋天”还原为词语“秋天”,必须由“秋天”本身,而非已经被言说的“秋天”开始,必须把“秋天”只当成“秋天”,然后我们方能回到词语和意义的原初位置,才能“深入秋天”。
必须承认,古典汉诗不能也不需要“词的歧义性”存在,所以才会出现类型化倾向,类型化排斥和不允许“词的歧义性”存在。现代汉诗不是不会类型化,而是不能类型化,为了避免“类型化”,需要“词的歧义性”存在而且必须存在。无论是“词的歧义性”所能增添的特质还是所具有的功能,都保证了“现代汉诗是”的“诗质”和“现代汉诗说”的有效性。而“词的歧义性”彰显的反叛词典秩序和语言规范的精神,与现代汉诗倡导自由、叛逆的思想内核完全一致。无论是破坏还是建设,“词的歧义性”有着大得惊人的力量,它关乎词语、关乎诗质、关乎人心、关乎生存、关乎效用——“众词向心,心向无起源的歧义”[36]。
1.王家新:《诗》,《王家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96页。
2.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4页。
3.陈东东:《只言片语来自写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0页。
4.臧棣:《诗道鳟燕》,《诗刊》,2014年第17期。
5.王家新:《词语》,《王家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6.词义演变问题参见葛本仪:《汉语词汇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3-208页。
7.B·什克洛夫斯基:《词语的复活》,《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8.卞之琳:《鱼目集》(第一部分),吴思敬编:《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17页。
9.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2页。
10.T.E.休姆:《语言及风格笔记》,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79页。
11.周伦佑:《果核的含义》,《周伦佑诗选》,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12.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50页。
13.转引自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0-151页。
14.威廉.K.维姆萨特:《象征与隐喻》,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55页。
15.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8页。
16.保罗·策兰:《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保罗·策兰诗文选》,王家新 芮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17.郭沫若:《读诗三札》,吴思敬编:《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
18.陈东东:《只言片语来自写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页。
19.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33页。
20.一行:《词的伦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91页。
21.转引自叶嘉莹:《从西方文论看李商隐的几首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22.威廉.K.维姆萨特:《象征与隐喻》,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55页。
23.洪子诚编:《中国新诗总系》(1959-1969),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342页。
24.臧棣:《诗道鳟燕》,《诗刊》,2014年第17期。
25.王家新:《词语》,《王家新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26.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文选》,王家新,芮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
27.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冯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14页。
28.圣词是指诗歌写作中那些带有不容分说的道德优势、代言人幻觉、绝对知识、升华特许的核心词。圣词的出现遮蔽了生存与生命的差异性、矛盾性,降低了写作的难度,使诗歌精神类型化、整体化。参见陈超:《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1页。
29.所引诗歌均选自洪子诚编:《中国新诗总系》(1959-1969),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30.穆旦:《夏》,《穆旦诗文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337页。
31.昌耀:《凶年逸稿》,《昌耀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58页。
32.北岛:《太阳城札记》,洪子诚,程光炜:《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8页。
33.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洪子诚,程光炜:《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34.敬文东:《抒情的盆地》,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31页。
3 5.柯平:《深入秋天》,徐敬亚主编:《中国诗典》(1978-2008),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36.欧阳江河:《我们——〈乌托邦〉第一章》,《透过词语的玻璃》,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