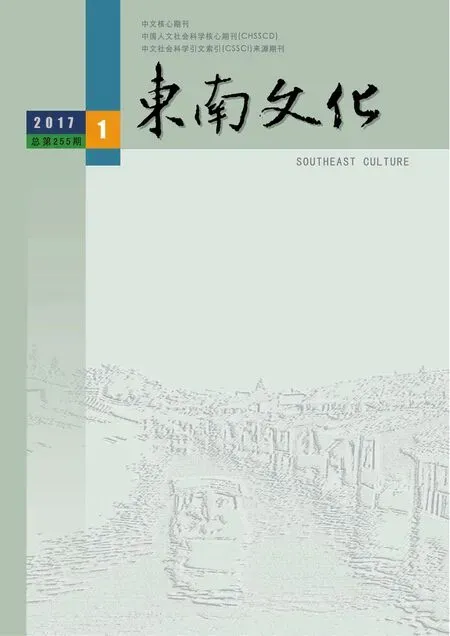论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出土的明器榻
2017-02-18周庭熙
周庭熙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 江苏南京 210023)
论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出土的明器榻
周庭熙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 江苏南京 210023)
考古发掘报告中,对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出土的明器榻的命名经常不一。通过对“榻”的概念的辨析、出土遗物的认定以及榻与墓中砖砌祭台的比较,可以发现墓中随葬的明器榻与墓主的身份等级相关,它在祭奠活动中与凭几一起象征的是墓主人的灵魂所在。作为墓主生前家居的象征,墓中榻及一系列家具的布置,使墓主生前的家居生活以及应享有的礼遇在其死后所处的墓室空间中得以延续。
南京 东晋南朝 榻 祭台 墓葬
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大型墓葬中常出土陶质或石质的坐榻模型,因其专为随葬所制,故属明器范畴。关于其命名、功能等问题,前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榻与案的异同[1];第二,汉唐家具研究中榻的地位[2];第三,榻与墓葬之间的关系[3]。但以往的发掘报告及相关研究,对榻的命名及其在墓葬中的功能等问题往往意见不一,已公布的发掘材料也未经详细梳理。因此,本文拟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葬出土的明器榻进行认定(据已公布的发掘资料,南京地区孙吴、西晋墓葬中尚未确认有明器榻的存在),进而对与之有关的墓葬等级及葬仪展开讨论。
一、明器榻的认定
东汉刘熙《释名·释床帐》说:“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体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枰,平也;以板作之,其体平正也。”[4]唐代徐坚《初学记》所引东汉服虔《通俗文》中记录了汉代榻的尺寸:“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秤(枰),八尺曰床。”[5]唐代玄应《一切经音义》引曹魏张揖《埤苍》称:“枰,榻也。谓独坐板床也。”[6]由此可见,汉晋时期的坐具与卧具可通称为“床”,据其尺寸差异又有“床”、“榻”、“独坐”与“枰”之分,仅容一人居坐的“独坐”或“枰”又可视为较小的“榻”。陈增弼先生与孙机先生曾据实物资料与上述文献材料,对汉晋时期榻的形制与尺寸进行了详细讨论。陈先生更对“独坐”一类小榻的尺寸作出了合理的推测:长75~130、宽60~100、高12~28厘米[7]。这为墓葬出土明器榻的认定和研究提供了依据。
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出土的陶质或石质的明器榻,在发现之时或简报中常被命名为“案”或“祭台”。尽管已有研究者提出将此类明器命名为“榻”,但此后的简报中依然采用以往的命名方式。因此,本文首先要对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出土的这类明器进行逐一认定。
依造型差异,墓葬出土的榻可分为无围屏榻与围屏榻两类。无围屏榻最早发现于1970年发掘的象山M 7。该墓出土一件陶榻,报告将其命名为“案几”[8]。1972年发掘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以下简称“南大北园墓”)出土的两件陶榻被称为“大型陶案”[9]。1979年陈增弼先生撰文对以上三件“案”的形制、尺寸以及汉晋间案与榻的图像与实物进行分析,明确了案与榻区分的标准,并将上述三件“案”确定为“独坐”,纠正了以往将出土案、榻混淆的错误[10]。李蔚然先生亦持相同观点[11]。近年江宁上坊孙吴墓出土的一件坐榻俑最能直观地反映当时案与榻之间的关系(图一)[12]。人物俑坐于榻上,榻前置一案,二者的长度与高度一致,但案面相对榻面较窄。在结构上,榻下曲尺形足与案下栅足亦显然有别。南大北园墓中的“大型陶案”与“中型陶案”之间的尺寸关系亦与之相同,二者分别为榻与案[13]。出土这类无围屏榻的墓葬,还包括南京农业大学东晋墓[14]、隐龙山M 1与M 3[15]、郭家山M 13[16]。
最早出土的围屏榻见于1979年发掘的尧化门老米荡南朝梁墓,榻面已不存,仅存4件应为榻足的“案足器”与10件用作围屏的“小石板”。据该墓器物分布图可知,这些“小石板”的一端均附有榫头[17]。1988年发掘的梁桂阳王萧象墓出土1件“祭台”,“台面下有5个小凹坑,另一端凹下一部分”[18]。1989年发掘的西善桥砖瓦厂南朝墓出土了形制相似的“石祭台”,发掘者注意到“在石祭台边还发现3个凸字形小石板,将小石板插入祭台的卯眼刚好吻合,说明这些凸字形小石板即祭台上的插板”[19]。1991年发掘的西善桥第二砖瓦厂南朝墓出土了形制相同的石面板,面板“可与散落在旁边的五块围屏石板榫卯相连”。简报以此为依据,将以往所发现的这类“案”或“祭台”确认为“石坐榻”[20]。邵磊先生也注意到以往部分考古简报“不乏有将此种石围屏指认为龟趺墓志残存志石或小石碑的误会”,并指出白龙山南朝墓与铁心桥马家店村南朝墓均有围屏石榻出土[21]。白龙山南朝墓出土的方形“墓志”与一端出榫的长方形“墓志”,应分别为围屏石榻的榻面与围屏[22]。铁心桥马家店村南朝墓出土的“石祭台”与“石板”同样分别为围屏石榻的榻面与围屏[23]。
从上述材料中还可看出,榻除了被误认为“案”外,也常被称作“祭台”。“祭台”一般指砌筑于棺前用以放置祭品的砖台,通常被视为墓葬建筑的一部分而非随葬物[24]。上述出土明器榻的各墓中均未发现砖砌祭台,而其他砌有砖台的东晋南朝墓葬中则不出土明器榻。从出土状况来看,东晋南朝墓葬中的榻、案及其组合,与砖台同样发挥着承置部分随葬器物的作用。这些器物常被认为用于祭奠活动,因此若从实际功能的角度来看,墓葬中的榻、案及其组合与砖台均可称作“祭台”[25]。然而,以上被称作“祭台”的陶质和石质明器榻,显然模仿实用坐榻的造型制成,有别于砖砌祭台,因此将之定名为“榻”较为合理。
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出土的13件明器榻(表一),据材质不同可分为陶榻与石榻,按造型差异可分为无围屏榻与围屏榻。陶榻均出于东晋墓葬,且均为无围屏榻;石榻均出于南朝墓葬,除隐龙山M 1与M 3两例外,其余均为围屏榻。上述各墓除象山M 7保存完整以外,均遭扰乱破坏。但较之于墓中其他遗物,榻的体积较大,不易移动,故其出土位置应与原始位置相差不远。象山M 7中的陶榻位于墓室内西南方正对甬道处,即原有木棺的前方(图二:1)。隐龙山M 1与M 3中的石榻,出土时均位于棺床之前(图二:2)。西善桥第二砖瓦厂墓的围屏石榻,出土时虽围屏已散落于榻面周围,但榻面仍位于棺床前方(图二:3)。从各发掘简报中的文字描述及遗物分布图来看,除南大北园墓外,其他墓葬中榻的原始位置均在木棺前方[26]。

图一// 江宁上坊孙吴墓坐榻俑
二、明器榻与墓葬的等级
河南省郸城县早年发掘的一座汉墓中曾出土一件石榻,榻面上铭刻“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㯓”12字[27]。“㯓”即榻。这件表明墓主身份的坐榻提示我们随葬坐榻与墓主身份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而这一点在前人研究中未能予以充分关注。
因此,有必要对上述墓葬的墓主身份以及包括榻在内的随葬明器家具的情况展开考察。如表一所示,除明器榻外,上述墓葬中还出土有陶质或石质的凭几、案、帷帐座或灯座[28]。就墓主身份而言,南大北园墓被推定为晋成帝兴平陵,出土明器家具类别最为丰富;南京农业大学东晋墓、隐龙山M 1与M 3、白龙山南朝墓、西善桥第二砖瓦厂墓与铁心桥马家店村南朝墓墓主不明,但可推知其身份较高,其余各墓墓主明确,均为宗室成员或高级官僚[29]。
如上文所述,墓葬中置于棺床前方的榻、案或砖台均有着祭台的功能。选择砖台还是以榻、案作祭台,或许与墓主人的身份有关。韦正先生将东晋墓葬分为皇帝、重臣、普通高级官员直至无官位的士族子弟、庶人四个等级,推测这一等级制度“可能只存在于帝王与重臣,而且这种差异也不一定有很强的强制性,其他社会成员的墓葬不存在明确的规定”,并指出“凭几、床榻、帐座是一组特殊的随葬品”,可视为帝王与重臣墓葬等级的表现[30]。在筑有砖砌祭台的墓葬中,墓主均非庶人,但身份高低不一。如老虎山颜氏家族墓中,M 1墓主为安成太守颜谦的夫人刘氏,M 2墓主为州西曹骑都尉颜綝,M3墓主为零陵太守颜约[31]。象山M6墓主为卫将军、左仆射王彬的继室夫人夏金虎[32],郭家山M 12墓主为散骑常侍、新建开国侯温式之[33]。墓中筑有砖台、墓主身份不明但推测有一定官位的墓葬则更多,如雨花台丹宁路M 9与M 10[34]、雨花台姚家山M 2[35]等等。所以,选择砖砌祭台的墓葬,墓主身份均在庶人之上,但等级参差不齐,而以榻、案作祭台的墓葬,等级均较高,墓主应为皇帝、宗室成员或个别重臣。
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出土的明器家具中,凭几数量最多,帷帐座或灯座次之,研究者常将二者作为推测墓主身份的依据之一[36]。通过对上述墓葬及其等级的分析可知,榻、案与凭几、帷帐座或灯座的明器家具组合可作为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葬等级判断的依据之一。但由于多数墓葬均被盗扰,墓中原有明器家具的类型、数量与位置较难确定,因而墓葬等级的确定还应结合墓葬形制与其他随葬品进行分析。

图二// 榻在墓葬中的位置示意图
三、榻与葬仪
《通典》所引贺循《议礼》的内容常被用于六朝墓葬随葬品的讨论,但其中所举的明器家具中仅谈及凭几与漆屏风[37]。凭几是六朝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的家具,漆屏风或因不易保存,在东晋南朝墓葬中未有发现。虽然榻未在其所举明器家具之列,但其他文献材料中保留了墓中设榻的记录。《晋书》提及王祥病重时对死后丧葬的安排,“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38],从其简化丧葬的要求来看,墓中保留床榻比放置其他家具更为必要。石苞在生前预作的遗令中也要求:“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唅,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39]石苞强调墓中不必放置“床帐明器”,这从另一个侧面可说明,在晋人丧葬观念中,墓中设床榻、帷帐一类器用应有特殊的意义。
榻作为明器用于随葬的缘由,可从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况加以考虑。东汉陈蕃为迎接徐稺特设一榻,“时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稺不免之,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唯稺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40]。宋文帝设榻以召僧人释慧琳而为颜延之所嫉,“时沙门释慧琳,以才学为太祖所赏爱,每召见,常升独榻,延之甚疾焉”[41]。由此可见,设榻待人是尊敬他人的礼仪表现,坐榻者对主人而言应有相当地位,此亦可解释级别较低的墓葬中未随葬坐榻的缘故。作为墓主生前家居的象征,墓中榻及一系列家具的布置,使墓主生前的家居生活以及应享有的礼遇在其死后所处的墓室空间中得以延续。
还需注意的是,在墓门封闭前对死者的祭奠环节。《通典》在叙述葬仪时引贺循《葬礼》称:“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妇人东向。先施幔屋于埏道北,南向。柩车既至,当坐而住。遂下衣几及奠祭。哭毕柩进,即圹中神位。既窆,乃下器圹中。荐棺以席,缘以绀缯。植翣于墙,左右挟棺,如在道仪。”[42]柩车到达墓地后,“遂下衣几及奠祭”,祭奠活动在墓道之北的帷帐内进行,将凭几及其他祭奠器用布置好即可开始。“哭”礼结束后,先将棺置入墓中,再放置其他随葬器物。
墓中凭几应有固定的摆放方式。象山M 7中陶凭几出土时置于榻上,弧面朝外。南大北园墓虽遭多次盗扰,但发掘者据器物出土情况仍能判断位于墓室西南角的陶榻与两件“中型陶案”上原各置一陶凭几。因此墓中凭几原应置于榻、案或砖台上,且弧面朝外——这也是凭几作为家具的使用方式,并可从魏晋时期墓葬壁画中得以印证,如北京石景山魏晋墓石龛内后壁(图三:1)[43]、甘肃酒泉丁家闸5号墓前室西壁(图三:2)[44]、朝鲜安岳三号坟西侧室西壁[45](图四)等墓主画像。帷帐座或灯座则常出土于祭台周围或墓室四隅,用于架设帷帐或照明。墓中明器家具依照墓主生前家居布置而摆放。虽然贺循在葬仪的叙述中未提到榻或案,但在地面上帷帐中祭奠时理应也按照同样的布置方式,贺循所举明器中的“凭几”与描述葬礼中的“几”应包括凭几及与之配合使用的榻、案一类家具。作为墓主灵魂所寄,墓室前部承置凭几的榻、案或砖台成为祭奠活动的中心。正如墓葬壁画中的墓主画像所示,墓主的形象以一如其生前坐榻凭几的姿态出现在生者的意识中,接受祭奠。

图三// 魏晋墓葬壁画中的墓主画像

图四// 朝鲜安岳三号坟墓主画像
四、结语
“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指导着墓主及其家属与工匠对墓室的营建与布置,同时也成为研究者将随葬器物与日用器具的使用方式相关联的前提。无疑,随葬器物可为还原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情况提供线索,但随葬器物在墓葬中的使用方式则常被忽视。
因此,将出土材料回归其原本所处的环境中展开研究非常必要。虽然榻被视为汉唐时期的一种典型坐具,但通过本文的考察可知,榻的使用还受到了使用者身份与使用场合的限制,尤其是墓葬中明器榻的使用与墓主身份紧密关联。就墓葬这一环境而言,榻与凭几的组合发挥着祭奠活
动中表现墓主形象以及墓门封闭后延续墓主家居生活与生前所享礼遇的功能。

表一// 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出土明器榻登记表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老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1]陈增弼:《汉、魏、晋独坐式小榻初论》,《文物》1979年第9期;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2]杨泓:《考古所见魏晋南北朝家具》(上、中、下),《紫禁城》2010年第10、12期,2011年第1期。
[3]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王志高:《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的讨论——兼论东晋时期的合葬墓》,《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考古学报》2015年第3期。
[4]东汉·刘熙撰:《释名》卷六《释床帐》,中华书局1985年,第93页。
[5]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二五《床》,中华书局1962年,第601页。
[6]徐时仪校注:《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7]陈增弼:《汉、魏、晋独坐式小榻初论》,《文物》1979年第9期;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20-224页。
[8][32]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9]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
[10]陈增弼先生注意到南大北园墓的陶榻“器上残留漆痕”,见其《汉、魏、晋独坐式小榻初论》,《文物》1979年第9期。
[11]李蔚然先生亦注意到器型特大的“独坐”明显区别于其他案几,见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12]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2期。
[13]南大北园墓出土“大型陶案”长125、宽100、高28厘米,“中型陶案”长126、宽35、高24厘米,二者长度与高度大致相同。
[14]简报将所出陶榻定名为“陶案”。见南京博物院《南京农业大学东晋墓》,《东南文化》1997年第1期。
[15]隐龙山M1、M2与M3各出土“石祭台”1件及“祭台足”4件,各墓所出“祭台”应均为榻。但M2所出石榻的面板已残碎,无法推知其原貌,四件榻足均严重风化,故暂不计入。见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区博物馆《南京隐龙山南朝墓》,《文物》2002年第7期。
[16]简报将所出陶榻定名为“祭台”。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
[17]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期。
[18]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阳王萧象墓》,《文物》1990年第8期。
[19]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西善桥南朝墓》,《文物》1993年第11期。
[20]发掘者将其进一步认定为“独坐”。见南京博物院《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东南文化》1997年第1期。
[21]邵磊:《南京灵山梁代萧子恪墓的发现与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灵山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1期。
[22]南京市博物馆、栖霞区文管会:《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考古》1998年第8期。
[23]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局:《南京铁心桥镇马家店村南朝墓清理简报》,南京市博物馆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南京历史文化新探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5-111页。
[24]考古报告及相关研究中常将祭台作为墓葬建筑的组成部分,与铺地砖、墓壁、封门墙、棺床、壁龛等相并列,纳入到墓葬形制的描述与讨论中。参见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馆编著《鄂城六朝墓》,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25]齐东方先生指出:“有时置石板、案几、陶榻,与祭台应该是同样功能”,“晋墓中的祭台是普遍现象,这些祭台和案几,以及与之组合的器物应是祭奠用具,强势延续到南朝时期。”参见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考古学报》2015年第3期。
[26]简报推测两件榻原分别置于主室东北角与西南角;“中型陶案”分别置于第一、二道门槽之间的甬道中与侧室的甬道口。王志高先生推测,东北角的榻原应置于棺床前而用于祭祀,其原位被附葬侧室死者时所置“中型陶案”占据,该榻“只能违例移置棺后的主室东北角”;位于西南角的榻则仍在原位。参见王志高《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的讨论——兼论东晋时期的合葬墓》,《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
[27]曹桂岑:《河南郸城发现汉代石坐榻》,《考古》1965年第5期。
[28]此类器座常作馒首形或龙虎形,中部作圆孔以插杆。学界常将其认定为“帷帐座(步障座)”或“灯座”。参见阮国林《谈南京六朝墓葬中的帷帐座》(《文物》1991年第2期),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207-209页),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6-158页)。
[29]各墓墓主身份均据发掘报告及相关研究。
[30]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2-283页。
[31]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第6期。
[33]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
[34]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丹路东晋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6期。
[35]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南京市雨花台区姚家山东晋墓》,《考古》2008年第6期。
[36]相关讨论参见阮国林《谈南京六朝墓葬中的帷帐座》(《文物》1991年第2期),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207-209页),谢明良《从阶级的角度看六朝墓葬器物》(载颜娟英主编《美术与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37-174页)。
[37]《通典》载贺循《议礼》,详见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八六《丧制四·荐车马明器及棺饰》,中华书局1988年,第2325-2326页。
[3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三三《王祥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989页。
[39]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三三《石苞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003页。
[40]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五三《徐稺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746页。
[41]南朝梁·沈约撰:《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902页。
[4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八六《丧制四·葬仪》,中华书局1988年,第2346页。
[43]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村魏晋墓》,《文物》2001年第4期。
[4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酒泉十六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
[45]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
(责任编辑:刘兴林;校对:张平凤)
A Discussion on the BurialObject Ta Unearthed from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ombs in Nanjing Area
ZHOU Ting-xi
(DepartmentofArchaeology and Heritage,Schoolof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23)
Different names have been used in excavation reports to call the ta,the burial object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dating to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discovered in Nanjing area.By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ta,examining the unearthed ta-like objects,and mak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a and the brick altar from the same tomb,it is argued that the ta has a close tie with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tomb owner and was often used together with other forms of tables in ritual activities to represent the tomb owner’s soul.The ta and other tomb furniture represent the setting that the tomb owner had enjoyed before death with thewish thatsuch setting and enjoyment could be continued in his or her afterlife.
Nanjing;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ta;altar;burials
K 871.42;K876
:A
2015-12-28
周庭熙(1992—),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唐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