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云楼不为人知的过往,都在这里了
2017-02-17陶瑾
记者 陶瑾
过云楼不为人知的过往,都在这里了
记者 陶瑾
苏州在明清两朝是文人艺术渊薮之地,其上层文人的收藏取向代表了收藏界的最高品味。论及苏州的收藏世家,“过云楼”声名显赫,以藏有宋元以来佳椠名抄、珍秘善本、书画精品著称。令人心生敬意的是,从保护文化开始收藏,到为了传承文化而捐赠,百余年来书香满堂的顾家一脉传承,从未计较所藏书画价值几何,他们始终认为这些藏品不是顾家私有财产,而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2012年,过云楼藏书以2.16亿元人民币落拍,让过云楼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13年,顾氏后人顾笃璜先生将过云楼文物六件(组)无偿捐赠给苏州市人民政府,并由过云楼陈列馆永久收藏。
然而,你真的了解过云楼吗?了解过云楼的历代主人吗?近日,记者随博物馆志愿者前去拜访了顾氏后人顾笃璜老先生,与顾老面对面,请他口述历史,说说顾家不为人知的过往。

顾氏后人顾笃璜老先生口述历史
《现代苏州》:过云楼顾家祖上是元末明初从安徽迁到苏州的,具体是安徽哪里呢?
顾笃璜(以下简称顾):我们家的家谱在太平天国时期就烧掉了,顾文彬重新续的家谱只有一份手稿,现在在江苏某个人手里,不肯拿出来。我只知道顾文彬祖上是从安徽来到苏州经商,主做外贸,有漂洋过海的大船,经营绸布生意,后来在苏州定居下来。而第一个念书做官的是顾文彬,顾文彬的父亲顾大澜从小培养儿子念书,受到父亲的熏陶,顾文彬还从小与书画结缘,诗词娴熟,三十岁考中进士,开始仕途生涯。

顾沄怡园图

过云楼第一代主任顾文彬画像
《现代苏州》:您家的顾得其老号,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主打产品有哪些?
顾:顾得其酱园,名字取自“得其所以”,主打产品是豆腐乳和糖醋萝卜。苏州顾得其总店在虎丘山正山门对面,观前街东也有个顾得其,胥门也有个顾得其,总共三家。后来公私合营就没有了,品牌也没了。
过去,不同的店打的招牌不同。我讲个小故事给大家听听,叶受和本来在稻香村隔壁,怎么回事呢?叶家的一个人去稻香村买东西,不满意提了点意见,店员说,“你要称心,不如自己去开一家。”于是他就在稻香村隔壁开出叶受和,那时候,稻香村以虾籽鲞鱼出名,而叶家是宁波人,因有着地理优势,收购的鲞鱼比稻香村好,叶受和的鲞鱼肉质硬,后来就打败了稻香村。现在叶受和与稻香村分开了。这种小故事挺有意思的,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
《现代苏州》:走在苏城街巷里,会看到一些老房子挂着像潘氏义庄的牌子,而你们家族有顾氏春荫义庄,想了解一点关于义庄的事儿。
顾:一般的大家族都有义庄,义庄归全家所有,而不属于个人,钱用于家族福利事业,有余则会投入社会福利事业。苏州就那么几大家族,不是世家就是姻亲,社会福利事业一般由各家分摊。当时我们顾家分管育婴堂,就是孤儿院,家里头的房子,如怡园、顾得其酱园的土地都是义庄产业。义庄有管理委员会,最后一任选举的管理委员会主任就是我父亲顾公硕,怡园的捐献就是他带头召集的。
我们家还办过一个学校,是女学,我到现在还没查到相关资料,学校一直是我祖母管的,里头有个教刺绣的是沈寿的学生,解放以后恢复了刺绣,就把她请来了。当然等我出生时学校都没有了。我1928年出生,1927年过云楼就不存在了,我一天都没住过怡园老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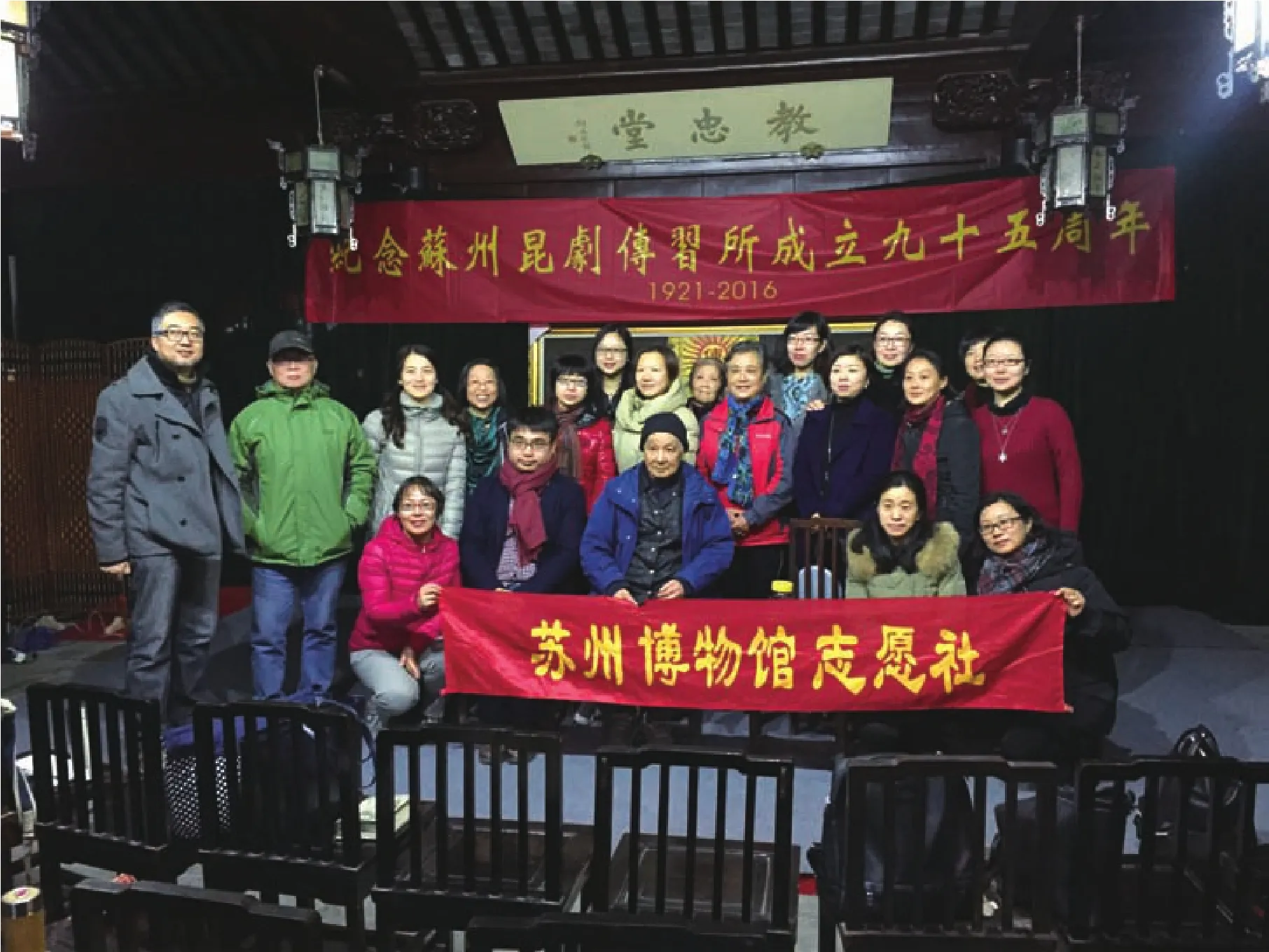
志愿者和顾笃璜老先生合影留念
《现代苏州》:书画之于你们顾家是怎样的地位?顾鹤逸老先生当初给小辈分家时,房产、书画是如何分的呢?
顾:当时祖父顾鹤逸从老宅搬出来了,一方面房子不够用,一方面祖父嫌那个地方太热闹,来访者不断,于是找了个偏僻的地方,造了西津别墅和朱家园。弟兄三人在外住,老大留在老宅,老宅里造了小洋房,西津别墅也有个小洋房,朱家园有两个小洋房。洋房楼上是摆书画的,其实我们家里最好的房子都留给了书画,人住楼下,书画“住”楼上,而且家里的箱子不放衣服,都放了书画。家里人穿的衣服都是破旧的,我祖父就穿打补丁的衣服,从小我也穿打补丁的袜子。
后来祖父将过云楼藏品分成四份,分散到四个儿子那里,我父亲拿的最少。不过书都在我父亲那里,原先没分。解放后父亲担任苏州博物馆副馆长,他将珍藏的传世珍品等文物无偿捐献。伯父顾公雄拿的画最多,他带到上海的书画珍品,后来都悉数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现代苏州》:顾家第四代在收藏保存这些书画时,恰逢战争时期,当时情况非常困苦,有没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顾:一个最主要的故事就是日本人侵占苏州以后,在伯父顾公柔所居的西津别墅闭门搜索十五天,在我父亲顾公硕和伯父顾公雄所在的朱家园闭门搜索七天,主人已经不在家。其实是接到了情报,因为我祖父有很多日本朋友,知道我们顾家有好东西,正所谓掘地三尺。等局势平静后,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家园惨遭蹂躏,放在楼上书柜中来不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寇翻箱倒柜劫掠,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画心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商周青铜器全部不知去向,损失惨重。我家里现在还保存着不少字画裱头,留作纪念。
日本这个民族很可怕,对我祖父相当尊敬,一直前来拜访,还请我祖父去日本办画展。祖父病了,日本朋友写信让我祖父去那里治病。后来岛田翰居然骗走了我们家的书,我祖父很佩服他,三十几岁对版本学精通到让人惊讶的程度,他要借书,祖父便借给了他,没想到一去就没消息了,祖父就写信向朋友打听情况,才知道岛田翰自杀了。后来被罗振玉购得,带回国内。外面有传言:顾家把东西卖给岛田翰了,绝对不可能,这么好的东西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觅来的,怎么会卖掉呢?实际是借去的,我祖父的目录上提到“被岛田翰攥取”。
《现代苏州》:过云楼这段历史非常吸引人,对于您来说,过云楼留给您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可能是一件藏品,或者一种气质,一种精神。
顾:顾家人为了这些藏品付出了太多,所幸大部分得到了保护。我不喜欢用钱来衡量过云楼的价值,一听到拍卖之类的字眼就很反感。我觉得收藏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传承的意图,并不是为了投资、增值。另外利用这些资料为社会服务,比如培养画家,把画工改为文人画等等。过云楼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精神。
《现代苏州》:过云楼为何有如此丰富的收藏?

胡芑孙、任薰吴郡真率会图
顾:过云楼所藏书画珍品,部分收录于顾文彬撰写的《过云楼书画记》以及顾麟士撰写的《过云楼续书画记》,并不是所藏全部,也不是最好的东西都上了《书画记》。过云楼为何能一下子收藏这么多东西?是因为当时画商把书画送到过云楼,家人懂书画,看好就当场拍板,而送到别家,还要请教人,可能还有不同意见。渐渐地,画商们都会先送到过云楼,过云楼不收的东西再送到别家去。这些画商大多也是文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画往往不拿在手里,而是放在布袋里,系在裤腰带上,长袍遮着,走进来时让人看不到画。

锦绣万花谷四十卷后集四十卷
记得我父亲在上海时,父亲精通书画鉴赏,很多人拿了画来请教我父亲,我也在这个时候看到并学到一些。
《现代苏州》:对于有人提到“过云楼珍藏秘不示人、阅读古籍不准抄录”等,这是事实吗?
顾:我们家里的画,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不过来看画,一定有东西给他看。对真心热爱书画并有研究的人,家人会主动拿出真品给他们欣赏。还有一套画专门应付那些不懂画的“土豪”,既不得罪,又避免对牛弹琴。
过云楼楼上有画桌,有笔墨和纸张提供,供人临画,我现在手上还有几张当时临了画没落款的画作。吴昌硕画坏的画扔在纸篓里,我祖父认为也是一种资料就收集起来,现在找不到了。傅增湘是我祖父的好朋友,祖父很钦佩他,请他来看我们家的目录,其实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带他上楼以后,让他坐在那里定心看,还让他阅览了平时秘不示人的宋元等版本珍贵藏书。
《现代苏州》:作为顾家后人,您捐献了这么多珍贵文物,您最不舍的是哪一件?
顾:没有不舍。保护文物的负担太重,要保护好真的不容易。我们家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在抗战前就运到了上海租界的四行储蓄会的保险库,其余部分仍藏匿在家中。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苏州,书画还是在上海保留着。解放后,就想着赶紧交给国家,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的。所以不存在舍得不舍得,非常非常舍得。
那时候父亲在上海,有人就对我父亲说,“你家财万贯,有那么多收藏,有钱人啊。”父亲笑着说:“这个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也不能卖,还要付保管费,我哪来的钱。”的确,我们家只是做了一段时期的文物保管员。
现在我还在继续做“捐献”这件事,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下去。
《现代苏州》:据说你们顾家收集书画,也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不知道小时候你们家有什么规矩?
顾:从我出生以后就没有了,我是听说过,家里的画绝大部分我没看过,只有人家来看画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在边上跟着看。那时候家里人反对我学习美术,要学理科,说是“科学救国”。后来我是造了反才去学了美术。
《现代苏州》:您是学美术的,您家的收藏以文人书画为主,您怎么理解文人画?
顾:谈不上。我觉得古人都很伟大,想要达到他们的水平太难了,因为现代人的心态不一样了。古代的文人画是一种精神,现在少了精神,只学表面,那还谈得上书画艺术么?!
《现代苏州》:请您谈谈《锦绣万花谷》的流转情况。
顾:《锦绣万花谷》先拍出以后转拍的,增了很多值,我是最反对拍卖的,因为不知道归属。我们家的书分成四份,三份已经给了南京图书馆,《锦绣万花谷》没有拆开过,到清初时只有八十卷了,而明朝时加过别集,变成了一百五十卷,可见它在明代十分受到大众的喜爱。
“书成锦绣万花谷,画成天龙八部图。”清代学者阮元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锦绣万花谷》的丰富内容。800多年的流传,《锦绣万花谷》起于神秘之人,藏于秘境之中,最终用一纸墨香,为我们留下一个悠长的历史背影。
《现代苏州》:顾沄画的怡园图里,有两个景,一是石听琴室,一是坡仙琴馆,而现在去怡园,两个景在一个建筑物里,原来就在一起吗?
顾:当时拓宽人民路,怡园拆掉了很多,琴馆里家藏了一把“苏东坡琴”,现在怡园展出的并不是那把琴。真的琴目前在北京,因为我一个堂姐小时候弹得最好,就给了她,现在在她的小辈手里,不想对外公开。
《现代苏州》:顾老您一直在和戏曲艺术打交道,我想您接触到的颜色有很多种,最喜欢的颜色是?
顾:我是学美术的,学戏剧是一个偶然,我觉得颜色对于我而言都是平等的。
《现代苏州》:顾老您一直致力于昆曲的保护与传承,而大多数年轻人并不喜欢昆曲,您觉得如何让年轻人慢慢接受并喜欢上传统文化?
顾:昆曲本来就是小众,我现在看昆曲本,不查字典也看不懂,我算弄了一辈子昆曲,但是古文修养还达不到。我到现在对《游园》里的一句唱词仍然困惑,请教了很多人,无人回答得出。
昆曲作为一种古典艺术,不能希望所有人都爱上昆曲,但了解昆曲是必须的。比如让孩子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高雅经典的艺术,这就够了。有一部分人喜欢,愿意学昆曲,能够将原样的昆曲保留下来,就像保存古文物一样“修旧如旧”,还有一部分人成为专家。
然而现在却有一些“转基因”昆曲和“假冒伪劣”昆曲,为了节省成本,随意删减剧本艺术,或是豪华布景、大乐队,都从本质上把戏曲的原理否定了。难道“变味”的昆曲就能让年轻人听懂么?年轻人照样不明白。传统是根,创新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动了根,就不再是昆曲,是另外的东西了。所以不能希望所有人都来拥护爱上昆曲,但了解昆曲是必须的。比如有人问我,喜欢昆曲么?我不能说我最喜欢昆曲,但昆曲的价值让我愿意为它献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