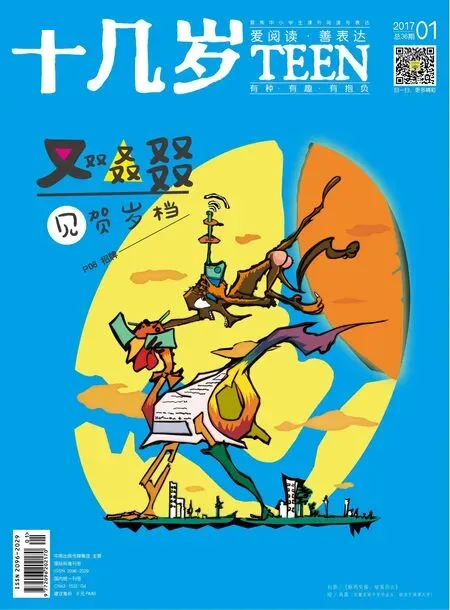银手镯
2017-02-15谭雅琪长沙市一中高1405班指导老师周玉龙
文/谭雅琪(长沙市一中高1405班) 指导老师/周玉龙
银手镯
文/谭雅琪(长沙市一中高1405班) 指导老师/周玉龙
小县里有个老人手腕上总挂着一个黑黑的银手镯。
说它是银的,只是老人的一面之词罢了。同样让众人费解的是,她总是说这是很珍贵的东西。她每次这么说,县里的人就嘀咕:“这个手镯十有八九是铜做的玩意儿,不知道她从哪个垃圾堆里翻出来的,黑不溜秋的,根本不值几个钱。”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小县城里来了几辆漂亮的小轿车,大家都说是张大婶家做官的儿子回来了。张大婶脸上也是笑开了花,口气里充满了得意之情。结果从车上下来几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看着面善,大家却都不认识。他们开口问路时,口音也与小县城格格不入。而他们要找的人也很奇怪——“一位带着银丝手镯的老人”。
县里的消息总是传得飞快,不一会儿,老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从平房里走了出来。周围的人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围观,但是每个人都像多长了一只眼睛,朝着老人那方瞥。只见为首的男人看到老人后,有点迟疑地问道:“您就是那位‘香君’吧?您还记得陆正则吗?”老人沉默了一会儿,半晌褪下自己手上黑黑的镯子,将它递给了男人,说:“往事就不用再提了。”她的嗓音嘶哑,像粗糙的砂纸一样。
那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老人还很年轻,十五六岁的花骨朵,是戏班子里的一枝花。那时候流行反串,男的唱旦,女的唱生,但她实在漂亮,班主也不愿意让小生的油污遮住了她能够带来生意的脸蛋儿,于是她成了旦角里少有的女孩子。那时,她在戏台上一亮相就有客人打赏,因唱的李香君实在是妙,又得了个“香君”的绰号。至于她那个土里土气的真实姓名,那些个喜欢附庸风雅的老爷们嫌污了耳朵,早就忘之脑后了。
还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戏馆里坐满了人。她站在台上,心中默念几遍早就烂熟于心的戏词,手上做了一个花势,朱唇微启:“妾的心中事,乱似蓬……”台下有几个军官,中间坐了个俊秀的年轻人,她扫了一眼,只道是哪家的富贵公子。
“好!”台底下是噼里啪啦的鼓掌声、喝彩声。她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唱完了。她已经很久没有完整地听完自己唱一出戏了,一切都好像是套路一样。把戏里国破家亡的人唱给戏外无家可归的人听,唱的人虚情假意地激动,听的人虚情假意地悲伤。
香君下了场,班主急吼吼地扯着她,嘴里念叨着:“你今天可算是遇到贵人啦!”她不明所以地被牵着来到一个年轻人面前,定睛一看,可不就是开始那个俊秀的男子嘛!班主脸上挂着暧昧的笑容:“香君,这位是陆长官。陆长官,我就不打扰您了。”香君脸上微微带笑,班主向来把香君的身价报得很高,现在这么恭敬地和这个年轻人讲话,说明他要么是个大官,要么是个大官的儿子。
班主退下去后,那年轻人走上前来,笑着对香君说:“我这几日听了您的《桃花扇》,才知道原来这世上真有香君!”香君心中一甜,这倒是奇怪,那么多人来听她唱戏却又看不起她,眼下这位陆长官是头一位对她用“您”字相称的。她细声细气地说道:“陆长官谬赞了,香君这名号是大家抬爱,做不得数的。”
那陆长官又是一笑,只说:“我初来吴城,身边也没有什么东西,只一个银手镯,香君如果不嫌弃便收下,也是我一点心意。”香君心里一紧,原来这陆长官也与他人没什么不同,只不过送些不一样的东西作为打赏,想来这是达官贵人的通病罢了。
面上的笑容褪去,她默不作声地就要收下镯子。也不知道陆长官是不是看出了什么,他捉住香君的手腕,香君没抽回,只得抬头看着陆长官的脸,这才发现他确是俊秀。“正式地介绍一下,在下姓陆,名正则。”他的眼睛格外明亮,像是燃烧了一团火焰一样,灼灼地让香君几乎要低下头去,“若我为朝宗,定不负有情人。”朝宗是侯方域的字。香君几乎就要说这个年轻人孟浪,但不知为何就是出不了口,她咬了下唇,突然用力拿过那手镯,只说:“我本名小桃红。”陆正则就笑了。
那几个月是她最快乐的日子。桃花扇里无法与侯方域相厮守的李香君只活在戏里,与陆正则在一起,她好像还是那个有点土气、为了任何事都可以开心的小桃红。陆正则也带她出席一些宴会。她从来不知道吴城里竟有那么多军官,这么多的晚宴。
来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了,城里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日本人。陆正则要她小心一点。小桃红隐隐约约地从陆正则紧张的神情和班主脸上的怒气中感觉到了一些东西,但又催眠自己,希望不是她想的那样。
然而这一天还是来了。小桃红那时还在台上,台下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班主说这是戏班在城里的最后一曲,然后又骂道:“把城封了的流氓!断了人生路啊!”小桃红有点心不在焉,陆正则已经很久没来听戏了,两人几次相见都是匆匆的,他说城里的气氛很紧张,顶上的人在和日本人谈话。小桃红不知道在谈什么,只知道班里的人提起日本人都是一脸气愤。
台下突然传来声音,起初只是一点点,随即越来越大,打断了小桃红唱段。她站在台上,有些茫然。班主急急地从旁边上来在她耳边说:“城破了!日本人要来听戏了!”
城破了?小桃红先是茫然,不知为何心里竟生出一点怨愤来,这是陆正则说的“顶上的人谈话”的结果吗?戏馆里突然冲进了几个大摇大摆的穿着军装的矮个的人,一堆高个的、脸上带笑的军官簇拥着他们。
中间那个矮个的说:“这个,就是‘李香君’吧?”他讲话的语调非常生硬,但小桃红依旧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意味,这就是日本人啊。“我听说,她唱得非常好?”那个日本人一字一句地咬着,旁边的中国人,脸上挂着谄媚的笑,说:“我们这里就属她唱得最好!”“哦?”那日本人突然笑了,“你们中国人,向来喜欢说大话,你让她给我唱一个,我来评价!”班主连忙让小桃红下台来,又轻声说:“你千万别得罪他们啊!”
小桃红面前站了黑压压的人群,有中国军官,有日本军官。她定了定神,右手转着左手腕上的手镯,张嘴却是:“我不给日本人唱戏。”“她说什么?”为首的日本人问旁边的军官,那军官唯唯诺诺地上前答话。日本人听完后,大笑起来:“你们中国,都属于我们了!你唱戏,是荣幸啊!”小桃红把手上的镯子转得飞快,她都能感觉到镯子磨得手都痛。她往旁边一看,正好,旁边的桌子上还放着一壶客人刚点的茶水,还冒着热气。她也不知哪来的勇气,竟笑着唱了句:“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吐不尽鹃血满胸——”然后就拿起茶壶,把那茶水往嘴里灌!
滚烫的茶水瞬间毁了她的嗓子、肚肠,她痛快地晕了过去,她知道她以后再也唱不了一句。
醒来时已是十余天后,陆正则把小桃红救了。小桃红知道自己再也唱不了戏,也不可能再被称作“香君”。一时之间,她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然而陆正则这里是绝不可能再待了。她留给了陆正则一封信,写道:“香君已死。”又把手镯留下,离开了吴城。
再次见到陆正则是十几年以后。小桃红一直住在这座偏僻的县城里。她觉得这里才是与她真正相配的地方,在吴城里唱戏,和年轻的军官在一起谈笑,被日本人挤兑喝下开水,仿佛都是上辈子的事情了。如果不是陆正则找来,她仿佛不会想起。
陆正则是在一个傍晚来到小桃红面前的。他瘦了、黑了,身上带着这个县城里的海味。小桃红见到他的时候一愣,转身只想跑开。她不再是那个漂漂亮亮、引得无数人喝彩的“香君”了,辛苦的劳作和躲避战乱的逃亡让她像脱了水的葡萄,皱巴巴的。陆正则像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拽住了她的手腕,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手镯。
那手镯已经发黑了,陆正则说了些什么“氧化”,小桃红听不懂。她的眼里全是泪水,脸上也是,想来丑得要命。但陆正则没有嫌弃,他很郑重地说道:“我要走了。”小桃红猛地抬起头来,陆正则定定地看着她,眼睛里出现了当初打动她的那团火,“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小桃红哭了,她哭得浑身都在颤抖,能够感觉得到陈年的旧伤在心肝肺肾里好像又裂开了一遍。“……”她从咬着的牙齿里挤出一句听不清楚的话,然后又尝试了一遍,最后终于停了下来。她抹去眼泪,脸上突然平静了下来。这时她仿佛又是当年的那个很多人捧场的名角儿了,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皱纹也阻挡不了那光芒。她一字一句地咬着,很慢很慢地说:“你我永结同心,纵远隔千山万水,照样可以魂来梦往!”但那声音已是粗粝的、难听而沙哑的了。小桃红很悲哀地望着黑了的军官,陆正则却仿佛早已预料到了结局,脸上竟也微微带了笑,他很温柔地执起小桃红粗糙了许多的手,将发黑的手镯给她戴上,然后轻轻地对她说:“香君。”
陆正则走了,他没有回来过。小桃红不懂得保养首饰,也没有闲钱,镯子一天比一天发黑,直到最后变成像铜做的一样。小桃红也老了,那镯子更显难看。县里的人都不知道她原来是吴城里的名人,她也顺利地在这个免于战火的地方安了家。后来家里人说要把手镯换掉,她也不回答,只是默默地转着,和很久很久以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