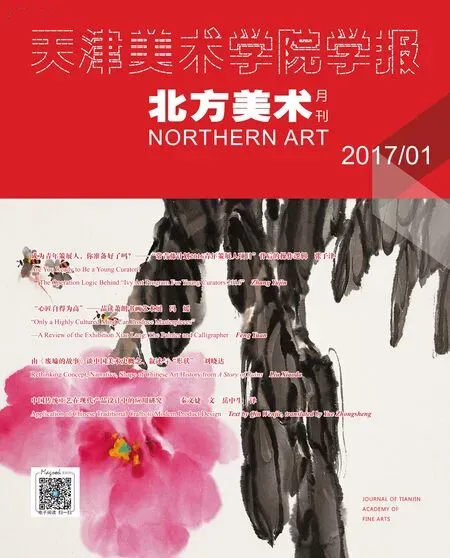“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
——“津派”绘画研究现状与展望
2017-02-14王陶峰WangTaofeng
王陶峰/Wang Taofeng
津派绘画是伴随着天津城市发展而兴起的绘画流派。它奠基于明清,发轫于近代,兴盛于当代。在近三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工细严谨、精致典雅的艺术风格。在近现代美术史上,津派绘画尤以保存、传承、发扬传统经典而闻名于艺苑。
一、津派概述
天津市位于华北平原北部,临渤海,与北京接壤,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深厚的地域文化。自17世纪起,文人墨客云集,风雅有序;近代开埠,华洋并存,一时领风气之先。
明清时期天津已成为江南文人进京的必经之地。据载,文徵明(1470—1559)、陈洪绶(1599—1652)、石涛(1642—1708)都曾驻留,与文人唱和,留下了许多诗画佳作,一时传为美谈。清初的书画大收藏家安歧(1683—1745,著有《墨缘汇观》)、乾隆年间的沈铨、嘉庆年间的陈靖,以及稍后的华琳(著有《南宗抉秘》,1843年成书)等在画史上留名。
近代,天津开埠成为通商口岸,新事物陆续引进,地位日重,“津派”应时而生。“津派”绘画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奠基期,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期,以查氏一门水西庄为代表的文人雅集与书画唱和活动为中心;第二个时期是发展期,天津开埠之后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吸引周边地区的文人——职业画家聚集、鬻画,新的市民社会逐渐形成,独特审美趣味得以产生、形成,至20世纪20年代,陈少梅将“湖社”的绘画理念引入天津,促使了“津派”绘画向传统绘画的经典之一——宋代院体诗意写实画风靠拢;第三个时期是蛰伏期与兴盛期,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后,此一时期,历经时代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和政府文艺政策的调整、画家的迁移以及历次运动,文艺思潮突变,画家主动或被动调整画风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砥砺耕耘,改革开放之后,新一代中青年画家英才辈出,在全国美展中屡获大奖,“津派”绘画逐渐影响到全国。
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文化发展形态必然受到以北京为中心的皇室宫廷审美趣味的直接影响。清代康熙、乾隆帝王审美趣味的汉化和文人化,其宫廷美术为“四王”及其传派所主导。近代天津画坛的发展状况与北京的政治变革、文化动向密切相关,1920年成立的以金城、周肇祥为会长的“中国画法研究会”(后演变为湖社),在当时大总统徐世昌(下野后寓居天津)为首的旧军阀的赞助支持下,为应对“新文化运动”而建立,以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主,成员由留日知识分子、北洋旧官僚、清遗民、文人—职业画家组成。中国画法研究会从传统绘画(宋代院体—浙派—唐寅、仇英)中汲取“现代”成分,以适应时代,尤其得力宋代院体的写实画风,倡导“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保守而不守旧,学古而不泥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社画家群体在京渐趋边缘化,部分画家到天津任教,其画风得以在天津延续,遂形成了“津派”承续宋代“院体”、兼采西画造型、工细严谨、精美典雅的审美风格。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宫廷美术的衰落,边缘文人的兴起,江南以上海为中心、以金石学为基础、具有振兴民族精神志向的海派的兴起,已预示着新的时代风向。在南方,作为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的广州,兴起了以“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以革新为目标,开启了国画“革命”。与上海、广州画坛一味求新、求变不同,天津的社会结构与分层则是在大时代中缓慢发生变革,地域新兴市民趣味与旧文化保守主义观念相混合,而呈现出“不新不旧”“不中不西”杂糅的特征。经过近三百年的发展,“津派”已形成了立足京津、辐射全国、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画派。“津派”代表画家有张兆祥、刘奎龄、陆辛农、刘子久、陈少梅、刘芷清、萧心泉、姜毅然、李昆璞、萧朗、穆仲芹、梁琦以及当代的何家英、霍春阳等。
但长期以来,相较于国内其他画派如海派、岭南画派、京派、长安画派,学界对“津派”的独特性关注不多,往往混以“京津画派”目之,忽略了津派绘画的独立性。因而,早期对“津派”整体、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论著则较少,这与“津派”在20世纪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何延喆就曾感慨:“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地方(天津)绘画史的研究专著、专论极其缺乏。书画收藏者虽多,研究者却极少。尤其缺少从学术的角度对画家的成就、价值加以研究和认定。长期以来,造成许多宝贵的史料迷失,乃至作品失传。”①近年来,学界逐渐意识到“津派”在20世纪继承、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宋代院体精工谨细一派的传承,开始尝试从整体上系统研究“津派”的起源、发展、流变,从20世纪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角度深入思考“津派”在近现代文化转型、时代变迁中的意义和价值,开启了津派绘画研究的新篇章。
二、“津派”绘画研究现状综述
由于京津文化、地缘相近,人们将“津派”视作京派的流脉和分支,“津派”似乎并不具备一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画派的条件,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观点是站在北京为主导的文化立场,却忽视了历史事实。津派早期画家多是民间文人,作品多是清赏雅玩,寄兴之作。近年,相关文献、画册、论文、专著陆续出版,如《天津文史资料选集》《〈湖社〉月刊》《京津画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天津市博物馆、民间可观的收藏,都为“津派”绘画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目前,“津派”绘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将“津派”视为一个相对独立自足的整体,对“津派绘画”风格共性的整体论述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王振德《试论“津派国画”》,何延喆《京津画派》(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天津绘画》,赵权利《京津画派研究》,崔之进《“津门画派”艺术特征初探》,徐群、杨桂华《从地域文化看津派绘画艺术》等。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何延喆的《京津画派》是较早研究“京津画派”的专著,但他对是否存在“津派”持保留态度。他写道:“近代天津画坛,从师承渊源、画家构成等方面来看,存在许多个案化的现象,既未有形成地域性的派别,也不应将刘奎龄的个人风格视为画派,更不应将天津挂在京派的名下。”②在此书中,他综述了数十余位活跃在民国时期的京津地区画家的生平、交游、师承、流派、风格,该书对明清时期天津地区画家的相关史料、画作的搜集以及津派绘画风格的整体论述,具有开创之功。
另一位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王振德在对“津派”的历史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天津地域文化,对“津派”的绘画艺术特征进行了总结,如追求传统功力、平民心性等。他说:“通过近百年六代画家不懈努力,‘津派国画’形成稳定的艺术特征……具有远离庙堂学院气息的平民心性和古今文士散淡亲民的情怀。总起来看,‘津派国画’凸现出天津现当代的文化品格,追求传统功力,讲究文化意蕴,注重生活气息,关照现实人生,抒写艺术情趣,充盈着创新活力和持续发展的潜能。……‘津派国画’朴实真诚而不矫揉造作,自然静雅而不藻饰浮躁,植根传统而不排斥西法,顺天应人而不妨碍文化品位,自强不息而不急功近利。画家们大多默默苦干,务本求实,相互理解,形成并自觉维护着适宜国画发展的地域环境和深广雄厚的人文基础。”③
赵权利在《京津画派研究》一文中对“京津画派”这一画史概念加以定义和阐释,肯定其在20世纪延续宋元传统、保存“国粹”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京津画派”是指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以北京、天津地区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以保存和发扬国粹为基本宗旨的国画流派。文章对于“京津画派”的地域、时限、画家群体、艺术主张进行了具体说明,并就“京津画派”的发生和发展中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文章阐述了“京津画派”的历史贡献和意义主要在于:延续了国画中宋元及以前的“国粹”传统,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美术革命”极端思想对国画的损害,在整个20世纪对于发扬民族文化建立了榜样。④
崔之进则在《“津门画派”艺术特征初探》中认为:“长久以来,天津的书画艺术没有在创作理念与绘画形式上形成统一的风格。就天津、就国内外美术界而言,也没有对‘津门画派’的研究予以足够重视。”⑤
对“津派”绘画独立性的认定、艺术风格标识性的辨析、地域文化对“津派”绘画风格的成因的研究是研究“津派”绘画的前提,为后来的研究者按图索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艺术家个案研究
个体画家是组成画派的重要细胞。画家个案研究对于深入研究画派风格的形成、流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个案研究是画派研究细化、深入化的必然要求。目前,对“津派”代表性画家的个案研究,以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师生为主要群体,有何延喆《刘子久》《陈少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张楠《民国时期京津两地的传统绘画支持网络——以陈少梅为个案》⑥、崔之进《论津门画派的艺术特征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艺术特质》⑦、赵宇《清末天津画家张兆祥的绘画艺术》⑧、叶春辉《颂情笔端,墨留余香——王颂余书画艺术研究》⑨等。从目前来看,个案研究往往综述画家生平和交游、师承渊源,辨析其绘画风格、风格成因,定位其在画史上的地位,但多集中于对画家生平的梳理,缺少从近现代转型的视角与文化变革意识的角度,深入探讨画家成长、画风形成与特殊的历史环境、时代精神、地域文化传统的共振的深入细节性研究。
三 “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津派”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大致而言,艺术史研究包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个思路:一是围绕具体的艺术作品、艺术家个案所做的历史个案研究,一般是指历史事实、风格分析和绘画材料学研究;二是以绘画为对象研究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群体文化倾向、时代精神、历史发展趋势的学科,即所谓的“外部艺术史”,指对社会学和相关的政治和文化史的探索。“理想”的研究形态当是内部与外部的有机结合,需掌握大量可信的史料,具有扎实的文史基础,宽广的视野,将其融会贯通,达到“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语)。但目前的“津派”研究领域总体上似乎还不能摆脱视野狭窄的弊病,缺乏“打开现象”的工具和方法,缺乏问题意识的敏感度,缺乏围绕核心立场、论点展开层层推进的辩驳论述能力等,结果是,无法在美术研究领域创造出别开生面的、具有学理和方法论意义的开创性研究,更遑论将绘画经验带入更广阔的时代思想讨论中,为当代精神生活开拓出独到的贡献。因此,笔者浅见,似乎应尝试新的开拓。
首先,审核文献的考证,确立信史理念。立足天津地域文化,放宽历史视野,以津京地方文献为主,将“津派”画家在天津的游赏、雅集、创作、交游、赞助等艺文活动,作为“津派”形成之前的文脉的考察。对画家的文献材料,进行考证、校对、审核,如画家回忆录,教学日志,师友、子侄后辈保存的信札、书画题跋、诗词文集等,作为原始资料读取、整理。
其次,树立“问题意识”,带着问题进入史实,分析形成艺术现象背后的时代因素,重点在于绘画风格形成与世变发展的关系。在形式主义者看来,艺术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形式演变风格的历史”,是艺术内部自律的历史。艺术史探讨特定地域、特定时期艺术发展阶段的代表画家、代表作品、主要艺术流派、艺术思潮以及艺术风格的演变的规律,探究其形式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在对艺术形式的审美感受中窥探时代精神在艺术中的显现。在对形式、审美的演变中窥探时代政治、文化的变迁,这就是说,艺术风格的兴衰,常常与其政治、文化环境的某些变化,产生互为因果的互动现象。如法国文化史家保罗·拉克鲁瓦就说:“在一个时代所能留给后人的一切东西中,是艺术最生动地再现着这个时代……艺术赋予其自身时代以生命,并向我们揭示这个‘过去的’时代。”我国唐代的艺术史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石守谦教授指出:“在我看来,如果想要理解文化环境变化和艺术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必须立足于风格研究之上。只有当我们清晰地描述风格变化的具体内容之后,才有可能思索它在文化脉络中的实质意义,并以之与历史上其他类似而实质不同的现象区别开来,从而得出妥适的历史解释。”⑩因此,要力图在对历史文献的发掘和整理的基础上,树立问题意识,拓展艺术研究的新领域。如台北艺术大学美术史研究所邱敏芳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课程”期末报告《民初(1921—1937)北京画坛中国画的转变》一文中,从“民初北京画坛中国画转变成因”“民初北京画坛中国画转变的艺术现象”“民初北京画坛转变的思潮与实践”等角度展开探讨,并认为“此期中国画的发展与转变是近百年来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研究此时期中国画的成就与经验,对于当代和未来中国美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⑪。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解读,探求时代政治、文化环境变迁在风格中的显现,进而窥探天人之际中艺术史发展中偶然的必然律。
再次,研究者要有“理论自觉”,即以特定理论体系切入历史,解释艺术现象背后的时代本质,在对事实抽丝剥茧的条分缕析中,概括、提炼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普遍性。尤其是在近代,中国被纳入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古代中国被迫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视野下审视“津派”绘画风格的当代意义和世界性价值就显得更有必要。在以革新为主调的20世纪美术史中,批判写意文人画,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构建中国“现代”艺术风格,是知识分子对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发展所持的文化理念在艺术中的反映。“津派”绘画的一个具有标识性的特征就是对“精能”的宋代院体画风的沿袭,“津派”的绘画理念和审美趣味源自文化观念相对较为保守的中国画法研究会,在对宋画和“四王”的复古中,寻求其现代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复古倾向和精丽典雅的画风是与当时新派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现代的民族国家的理想具有内在的矛盾和逻辑冲突的。因此,在西化派和中西融合派看来,“津派”绘画是为一种过时的、僵化的、即将死亡的艺术形式招魂,而这终究是“幻梦”。因此,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早期京津画派,其发起者、参与者常常是在夹缝和困境中寻求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突破。当然,民初宫廷收藏的艺术珍品散佚在民间,古物陈列所向民众开放,出版技术的革新,珂罗版印刷术的发展,中日之间的绘画交流等,都促成了“津派”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特殊时期的文艺政策,旧派画家迁移到天津,或开馆授徒,或参与教学培养人才,都促使画风的转移和变迁,也为“文革”之后,新一代艺术人才的储备、成长和“津派”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最后,新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9·11”恐怖袭击、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使思想界、文化界知识分子对20世纪进行了反思,他们审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力图融通传统文化精华、近代社会主义传统和当下的文化变革,构造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当代中国新型文化形态,并纳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为民众日常生活提供精神支撑和文化自信。这意味着对“津派”的阐释也转变为一个新的面向,即“津派”所折射的并不是恢复真实的古代,而是把将来折射为过去,通过对某种遗失形象的回忆、追溯和融合实现一种当代的艺术理想,也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艺术追求。
注释:
①何延喆:《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天津绘画》,《北方美术》2002年第2期,第33页。
②何延喆:《京津画派》,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③王振德:《谈“津派国画”》,《天津社会主义学报》,2009年第3期,第48页。王振德:《张兆祥与国画第一代》,《国画家》,2009年第4期,第32页。
④赵权利:《京津画派研究》,《美术研究》,2007年第4期。
⑤崔之进:《“津门画派”艺术特征初探》,《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66—171页;
⑥张楠:《民国时期京津两地的传统绘画支持网络——以陈少梅为个案》,中央美术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论文,未刊。
⑦崔之进:《论津门画派的艺术特征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艺术特质》,天津大学2006级硕士研究生论文,未刊。
⑧赵宇:《清末天津画家张兆祥的绘画艺术》,天津美术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论文,未刊。
⑨叶春辉:《颂情笔端,墨留余香——王颂余书画艺术研究》,天津美术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论文,未刊。
⑩石守谦:《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⑪薛永年、杭春晓、朱京生、赵强:《论京津画派》,《中国书画》,2006年第8期,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