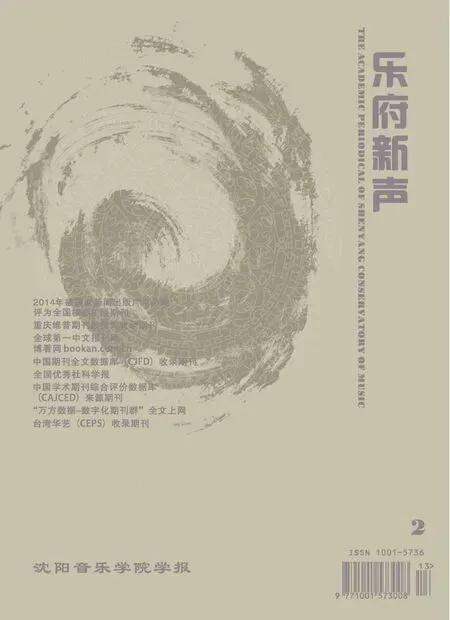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音乐剧发展创作进程与代表作品比照评述
2017-02-14屠锦英
屠锦英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音乐剧发展创作进程与代表作品比照评述
屠锦英[1]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与台湾的音乐、戏剧界,不约而同开始了对当代最有市场的音乐戏剧形式——音乐剧的探索。两岸音乐剧创作近二十年的发展进程,表现出类似的发展规律:萌发、低谷与高潮期出现在相同时期,并表现特征很相似。当然,因为政治、经济状况和人文环境不同,过程和作品风格也存在着诸多差异。作者在本文中使用比较研究方法对两岸音乐剧发展创作进程与代表作品进行对比性论述,旨在为更进一步为两岸音乐剧比较研究夯实基础。
两岸/音乐剧/描红/原创
自1927年的第一部音乐剧《演艺船》在美国“起航”,这一形式已存在了近百年时间。华语音乐剧的萌芽虽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大上海时期的黎锦晖儿童歌舞剧,但真正现代意义音乐剧的出现与繁荣,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一时期的内地与台湾的音乐、戏剧界,不约而同出现了对这种当代最有市场的音乐戏剧形式的探索。在内地,改革开放的春风将《音乐之声》、《窈窕淑女》、《西区故事》等一批好莱坞音乐剧电影吹到了渴望外来艺术已久的观众面前,虽然还没能接触到更多剧场版的音乐剧形式,但许多业内人士已经对这种充满现代意识和都市气息的艺术形式印象深刻。对岸的宝岛台湾,因为资讯相对开放,艺术创作者们有幸通过观摩、唱片、大众传媒等方式,与当时音乐剧国际化潮流中的代表性剧目《艾薇塔》、《猫》等名作接触。在这种熏陶下,两地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了音乐剧形式的尝试。纵观海峡两岸20世纪音乐剧创作历程,其萌芽时期、创作类型侧重及创作历史发展的“涨跌规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因社会意识形态和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也有许多差异,在此用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对比性论述。
一、初期——“懵懂先驱”与“用力过猛”
从1982年,中央歌剧院创作的《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起,内地先后出现了《芳草心》、《风流年华》、《台湾舞女》、《搭错车》等多部“类音乐剧”作品。之所以用这种称谓,是因为这些作品进行了“音乐剧化”的尝试,展现出音乐剧形式的基本面貌,但还不具备成熟音乐剧的全部特征。比如《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是在音乐创作和演唱风格上向当时流行的“抒情歌曲”风格靠拢;《风流年华》加入了和剧情有机联系的舞蹈场面;《搭错车》则贯穿当时最时髦的流行歌曲。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还不够开化,创作者也普遍缺乏对世界前沿音乐发展趋势的认知,因此在上演时,往往以“歌剧”、“音乐话剧”、“音乐歌舞故事剧”等名头出现。这些音乐戏剧形式具备了音乐剧音乐唱段与对白结合,关注当代都市题材,风格轻松活泼,利用舞蹈桥段参与剧情推进,音乐抒情上口等基本特征,虽然从运作模式上并无现代商业化运作,对于音乐剧最重要的音乐旋律创作也缺乏科学认识,但已基本完成了从轻歌剧向音乐剧形式的转化。只不过,创作者对于这种形式的探索,更多基于对国外流行样式的模仿,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尝试对未来中国音乐剧发展的先导性意义,还处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懵懂期。在这几部最初探索性的尝试后,80年代后期,以1986年在长沙举行的歌剧观摩演出为契机,各大文艺团体先后推出了《公寓13》、《特区回旋曲》、《雁儿在林梢》等多部作品。但这些探路之作因创作者对音乐剧创作的基本规律缺乏认识,大多存在着音乐沉滞凝重,缺乏灵动气质,音乐与舞蹈场面未能有效进入叙事框架[1]居其宏音乐剧《我为你疯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11月第1版,第231页。等问题。因此,这些作品大多还处于轻歌剧与音乐剧的过渡阶段,尚不具备音乐剧的完备品格,尽管如此,音乐剧形式毕竟在此时萌发,“准音乐剧”的时代已经到来。
反观台湾80年代的音乐剧探试步伐的迈进,显然比内地要更谨慎,目的性更明确。在通过观摩和媒介资讯接触了众多音乐剧作品后,1987,台湾音乐泰斗级人物李泰祥进行了首次音乐剧的尝试。这部汇集了国外名导、作曲大师、知名编剧(三毛),和齐秦、张艾嘉等明星的大制作《棋王》,斥资数百万台币,显示出台湾音乐人在制作本土音乐剧方面的雄心,造成了未演先轰动的效应。遗憾的是,该剧首演后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只上演了十余场便匆匆落幕。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创作团队的经验匮乏。三毛固然是优秀作家,李泰祥也是出众的作曲家,但对于音乐剧写作,他们都是十足的“新手”,都缺乏对这种形成已久的艺术形式的透彻研习与认识。音乐剧绝不能单纯理解为“半古典、半流行”[2]杨忠衡《万事俱备 东风已吹——台湾音乐剧三十年的四个发展阶段》,上海戏剧2012年6期,第7页。的音乐戏剧形式,如何能将各种元素巧妙揉合,让歌舞与戏剧张力高度统一,显然,台湾音乐人此时还没有完全领悟。台湾音乐人急于让本土音乐剧迎头赶超英美,意识明确,但未能有精彩的情节发展和感人的音乐作为填充。因此,这次仓促的制作显得火力过猛,各种元素未能化合在一起。再加上制作者对音乐剧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并不熟悉,未能形成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系统,因此单靠并不乐观的口碑和不甚可观的票房收入不足以维持商业运营成本。出品方新象艺术中心在此剧后,很长时间因资金问题没有其他动作[3]棋王词条,台湾大百科全书网.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5391。。这部《棋王》开启了台湾音乐剧的序幕,但序幕响声虽大,却让台湾艺术界意识到,本土还不具备制作“大卡司”音乐剧的能力,羽翼未丰,害怕受伤的台湾音乐剧也陷入了近十年的“冬眠期”。
二、中期——“描红”与“原创”的纠结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两岸的音乐剧进入了新一轮的探索期。作为一种舶来艺术,在其本土化进程中,到底应该先引进原版音乐剧,从中学习国外音乐剧制作的先进经验,还是直接尝试创作符合本土观众欣赏口味的原创音乐剧作品,两岸的音乐人们都在“纠结”中前行。
内地创作者们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最初探索后,逐渐意识到自身在音乐剧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匮乏,于是试图通过搬演国外音乐剧的“描红”[4]中央戏剧学院权威人士将搬演国外音乐剧的实践比喻为学毛笔字的“描红”。方式学习其先进经验。最初进行这种尝试的是1986年上海戏剧学院,采用江浙俚语搬演的百老汇音乐剧《窈窕淑女》,之后中央戏剧学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戏剧专业院校、团体在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以中文翻译的方式,翻排了《西区的故事》、《皇帝的新装》、《美女与野兽》等作品[1]居其宏音乐剧《我为你疯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11月第1版,232-236页。。这种“描红”不但让参与创作者与观众亲身感受到经典作品的巨大魅力,更在实践中为国内培养了第一批音乐剧表演人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儿艺”在1999年推出的《美女与野兽》,还创造性学习了国外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公演之初上座率颇为火爆。但因为引进音乐剧并不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在上演了近三个月后,还是匆匆卷旗收兵。翻排经典为中国音乐剧积累了最初的一批观众群。但创作者们逐渐意识到“描红”的同时,必须同时探求具有民族文化背景的原创音乐剧,才能在“描”与“创”中两条腿“并行”,形成民族化音乐剧的最初蝉变。
以1990年湖南株洲的歌剧观摩为契机,几年内先后出现了《山野里的游戏》、《请与我同行》、《征婚启事》、《人间自有真情在》、《巴黎的火炬》、《鹰》、《芦花白、木棉红》、《夜半歌声》等作品。这些作品都未能取得广泛的影响力和令人满意的票房,普遍存在着叙事冗长,缺乏张力,人物刻画缺乏个性的问题,无法让观众产生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些失败的尝试并非没有创新和亮点。《请与我同行》首次尝试将美声与民族唱法融在一剧,叠合在一起构成二重唱。《人间自有真情在》完全由通俗唱法演唱,是流行音乐剧的开端。《夜半歌声》的舞美效果与戏剧场面的对接和对音乐剧语汇的灵活运用达到了十余年来音乐剧创作的顶峰。中国音乐剧工作者在“引进”与“原创”的纠结中艰难跋涉,虽然在1997年以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符合现代商业运作模式和创作规律的音乐剧作品诞生,但许多文艺团体毕竟在前赴后继的艰难探索中进行着音乐剧形式的创作,为日后此种形式的全面崛起铺路。
和大陆体制内的文艺团体在20世纪90年代对音乐剧市场的开疆拓土不同,海峡对岸在80年代《棋王》的初试音啼后,一直未有大的动作。直到90年代中期,以“果陀”和“绿光”为代表的民间戏剧社团开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2]方钰婷《耀演》剧团音乐剧之记录与研究——以原创中文音乐剧 《DAYLIGHT》为例(硕士),台湾博硕士论文加识加值系统2010年,第42页。。台湾音乐剧的再次爆发从戏剧界开始,恐怕原因是多年来,戏剧界相对活跃,一直不断推陈出新,敢于突破自我;此外,80年代李泰祥的尝试未获得预期效果,也让音乐界人士背上了包袱,不敢轻易出手,相反戏剧界对于音乐创作方面却没有这种顾虑[3]杨忠衡《万事俱备 东风已吹——台湾音乐剧三十年的四个发展阶段》,上海戏剧2012年6期,第7页。。果陀剧场和绿光剧场这两大戏剧界的中坚力量也沿着“描红”和“原创”这两条道路前行。1994年,刚刚成立的民间戏剧社团“绿光剧团”首先做出了原创音乐剧的尝试。他们选择以台湾当代都市年轻白领的生存与情感故事为题材,用最贴近台湾民众生活状态的“艰辛与温情”的命题迅速赢得广泛共鸣,十多年来一直在复排,在纽约和内地也都获得了火爆响应。作为第一部取得商业成功的原创音乐剧作品,《领带与高跟鞋》剧的走红恐怕更多是依仗其贴近生活的题材和观众从中获得的对自身无奈处境的投射。从单纯音乐剧品格角度分析,话剧界人士为主创班底的队伍更多让音乐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其音乐平易近人又简单,歌曲更多为诉说心境般的内心独白,缺乏对剧情的有效参与和推动,称其为一部“音乐剧”倒不如叫做“音乐话剧”更为妥帖。虽然在《领带与高跟鞋》之后,“绿光”又有轻松幽默的《结婚?结昏!一桌办》和吸纳戏曲元素的《都是当兵惹的祸》等不同尝试,但始终没有摆脱“话剧加唱”的模式,当更为专业的音乐剧专业团体和作品出现后,“绿光”逐渐淡出了音乐剧舞台。
和“绿光”选择的完全本土化的原创道路不同,“果陀”所走的是一条“风格描红”之路。和内地“描红”的最大不同在于,“果陀”的“描红”不是将西方现有的音乐剧编配“中文版”剧词直接搬上舞台,而是在西方戏剧、电影作品故事基础上进行剧本改编和重新作曲,创作出有着西式风格和外壳,更符合东方人艺术欣赏习惯的作品,因此,是一种“描红”西式风格基础上的原创。从1995年“登高一呼[4]同上,第7页。”的《大鼻子情圣》,到1997年音乐才子张雨生的剧场遗作《吻我吧,娜娜》,再到1998年的蔡琴主演的《天使不夜城》,几部这种创作方式的作品无一不让专业人士、媒体和观众惊喜。后两部作品更是取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这三部作品中,《大鼻子情圣》剧因是首次发力,陈乐融的剧本和剧词改编得很出色,但舞美制作显得很潦草,音乐上存在过多模仿西方音乐剧的问题,缺乏契合东方人听觉习惯的独立主张。音乐与戏剧的整体规划中规中矩,但远未达到自然的均衡。拉丁音乐剧“《天使不夜城》”凭借明星的巨大号召力获得了不错的票房和诸多大奖,也综合调动了各种舞台手段,更多获得了创作和剧场效果上的进步,但其所特意追求的原始、野性的拉丁风格,让观众仿佛在欣赏一部南美音乐剧[1]杨任淑《果陀剧场歌舞剧之研究(硕士论文)》,成功大学,成功大学电子学位论文服务2004年,第190页。。欣赏者虽感受到了戏剧性的张力和强烈的音乐震撼,但却缺乏民族化、地域性和社会心理感受层面的亲切感。相比较而言,《吻我吧,娜娜》虽取材于西方经典著作,但剧作家将时空转换到现今台湾,反映出台湾当代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念[2]同上,第91-95页。。作曲者张雨生,能以新人姿态,不带包袱创作。音乐既不失自身的自然完整,具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但歌舞与戏剧场面的结合难以做到浑然天成,还处在各自为政的局面[3]吴棋潓《听觉的遗憾——评<吻我吧娜娜>的音乐效果》,表演艺术1997年10月,总第58期,82-83页。。从“音乐”的层面考量,此剧是几部作品中最出色的。只可惜作者在创作了此部作品后就英年早逝,未有机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三、20世纪两岸音乐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病症”
通过断代方式总结出两岸音乐剧在各时期的共性特征与本地化特点,有许多两岸音乐剧近二十年发展表现出的共同“临床表现”便凸现出来。构成音乐剧形式的主要两大要素,戏剧与音乐的结合上。音乐剧和歌剧都是音乐与戏剧结合的形式,但与歌剧主要是以音乐表现的戏剧,要求剧情和人物关系尽量简洁,预留最大空间给音乐部分不同,音乐剧因其作为商业化、娱乐化的产物的定位,要求必须有曲折动人的情节和引人入胜的故事。因此几乎所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成功音乐剧,戏剧成分永远占有第一位。即使在上世纪末音乐剧的国际化时代,安德鲁·罗伊德·韦伯创造的一系列音乐成分极重的音乐剧,如《歌剧魅影》、《贝隆夫人》等,也并非只重视音乐而削弱曲折情节或冲淡戏剧冲突,而是将音乐发展线索和剧情展开线索紧密纽结。反观华语原创音乐剧,大多存在难以消化这种“纽结”含义而陷入了“话剧加唱”或“有乐无剧”的极端,暴露出通俗艺术本土化初期的诸多弊病。
“六神无主之症”,症状是“元神患失、经络不通,缺少精气,易疲劳,难悲难喜”。两岸的原创音乐剧创作之初的许多“话剧加唱”作品,正是因为元神患失,而陷入了“六神无主”之病中。内地80年代的许多音乐剧作品,如《芳草心》、《搭错车》,以及台湾90年代戏剧界绿光剧场、果陀剧场的一系列作品,实际上就是在话剧形式中,穿插一些具有抒情性和戏剧性功能的音乐、舞蹈场面,但如果将其演唱部分的歌词改写成台词,其实和纯粹的话剧形式并无二致。这类音乐剧虽剧本设置有合理的戏剧冲突,但这种冲突的构建与发展往往并非通过演唱部分呈示而出。音乐和舞蹈的发展并非水到渠成从戏剧线索中孕育而生,而是“各自为政”,情节的发展和故事冲突成为了“串联”歌舞节目而不得不交代的背景。这种悬念的设置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未能与音乐紧密咬合的状态,造成了观众将审美注意力集中在歌舞段落,对于戏剧展开过程的关注度大大降低,本应最富魅力的部分成为了草草交代的过场。因而,故事本身虽有完整的情节,却难以带给人酣畅痛快的审美满足感。戏剧家对于人物关系网的构设和人物间性格的碰撞并未建立在歌舞力量的推动下,造成戏剧发展和音乐段落如披着“两层皮”,复杂剧情交代和音乐情感发展皆让人难以投入。音乐剧缺乏戏剧与音乐自然结合的状态,显得缺乏精气神,六神无主。
四、为20世纪两岸音乐剧 “病症”寻因“开方”
针对原创音乐剧创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因音乐与戏剧二元融合不当而引起的如“六神无主”等症状,笔者认为,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国音乐剧制作者缺乏深入到国外音乐剧环境和制作系统中认真学习的过程,是对于音乐剧的创作规则和各形式、内容要素有机结合缺乏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的表现。中国当前许多原创音乐剧的失败,大多因为剧本和音乐无法有机结合而存在的先天“乐剧相融”品格的缺失。剧作家和作曲家缺乏虚心地向西方成熟音乐剧模式“躬身”学习的精神,照猫画虎模仿或盲目追求“新奇异”的效果。但熟知西方成熟的音乐剧创作规律的人应该知道,音乐剧的商业化、娱乐化与通俗性是不可打破的根本特征,那些不将为观众讲一个险象环生、生动有趣的故事为己任,而盲目让自身追求的先锋派戏剧理念强加给受众的剧作家,结果只能“引火烧身”,从根本上“消解了作为通俗戏剧样式的音乐剧视为生命的所有基本要素”[1]居其宏音乐剧《我为你疯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11月第1版,第260页。。而两岸上世纪80到90年代音乐剧创作中,出现的将音乐剧当成话剧加“歌舞”的形式,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剧作家和作曲家在创作时缺乏剧与乐整体化的思维能力,未能将音乐段落自然嵌入情节发展的整体线索中,成为刻画人物性格和增强戏剧张力的有效推动力,说到底,仍然是对西方优秀创作典范深入学习和参与不足,自身功力不到的体现。因此,在现阶段中国音乐剧的发展过程中,引进与原创并存,“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依然不能随意丢弃。参与欧美经典音乐剧范例在中国的制作工作,能让中国音乐剧创作和表演者们静下心来,真正领略到西方音乐剧从创作、主创人员确定、演员招募、排演、宣传营销、多轮上演和衍生产品开发等一系列成熟的运作模式中。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不断“临摹”化的实践之余,必须坚持本土化音乐剧的创作,不断寻找到适合中国文化特征和符合中国观众欣赏习惯的创作方式。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音乐剧创作的发展历史,在世界性浪潮的冲击下,的确在相近或相同的时期,表现出类似的发展规律:皆经历了萌发,“原创”与“描红”类型选择上纠结的过程,本文作为抛砖引玉之作,希冀能带动更多致力于研究两岸音乐剧比较性研究文字出现。当然,比较的目的绝不是人为割裂两岸的音乐剧创作和市场,相反,两岸同宗同源,有着共同的文学、音乐和戏剧资源,应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一步资源共融,加强交流。这种共融不仅包括项目运作、创作和表演人才的资源整合,也应包括市场开发的进一步融合。相信不久的将来,用汉语演唱,能被全世界欣赏的现代华语原创音乐剧作品会越来越多地在世界音乐剧舞台绽放。
[1]居其宏.音乐剧,我为你疯狂[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
[2]杨忠衡.万事俱备 东风已吹——台湾音乐剧三十年的四个发展阶段[J].上海戏剧.2012
[3]] 棋王词条.台湾大百科全书网.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5391
[4]方钰婷.<耀演>剧团音乐剧之记录与研究——以原创中文音乐剧
[5] 杨任淑.果陀剧场歌舞剧之研究(硕士论文).成功大学[D].成功大学电子学位论文服务,2004
[6]吴棋潓.听觉的遗憾——评<吻我吧娜娜>的音乐效果[J].表演艺术,1997
(责任编辑 张宝华)
J605
A
1001-5736(2017)02-0147-5
[1]作者简介:屠锦英(1967~)女,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教授。
本文为浙江音乐学院院级课题,课题编号:2016KL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