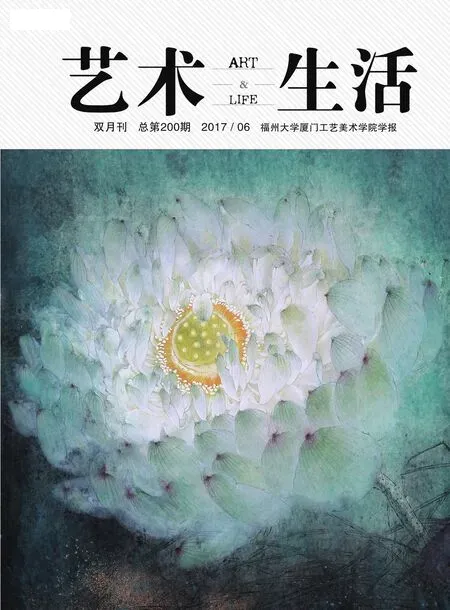庙堂的黄昏:当下博物馆问题之我见
2017-02-14程原林佳敏
程原 林佳敏
(集美大学 美术学院,福建 厦门361021)
引言
近年来,全国地市以下社区博物馆虽然在场馆硬件建设上普遍提升,但从我们的实际感受来说,其陈设内容、展示方式和运作理念,却对市民的文化生活影响甚微。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在国内省级以下地方博物馆中,其脱离社会、疏离民众、影响力弱等问题程度不同地普遍存在,而且从“知网”所见的121篇相关研究文献看,反映在对博物馆的功能、展览陈列和藏品质量等问题上,其比例分别是37%、25%和22%。对于这一现实的普遍性问题,笔者更愿意从自身的感受和体验为起点,兼以“榕博”①为例,尝试探讨造成博物馆游离现实、疏离观众的缘由、机理和看法。
一、间离感:地方博物馆在人心中的情状
地方博物馆,通常被看作是社区或区域文化发展的关键标志。近年来,包括“榕博”在内的地方馆的场馆物质建设,都呈现出良好的势态,不少地方不仅修建、扩建,甚至投入巨资重建、新建。然而客观讲,这些举措所在对观众的吸引力上,却依旧是鲜少变化。就榕博来看,馆方也在努力推进与社会互动的项目,例如“中小学生第二课堂”“海丝记忆”“道德讲堂”等活动,试图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但即便是如此,笔者在实地调研和问卷中,依然看到观众对1、2号短期陈设馆的态度,从内容到形式满意度很不乐观。地方博物馆极力想要拉近与社会、公众的距离,然而现实却是宛如隔靴搔痒、不能触及根本。
直观上讲,不能不说地方博物馆实质上仍恪守于令观众“仰望”和“壁上观”的传统规制,很容易给观众一种高高在上、不可亲近的感受。这种情况不仅导致其渐渐退出公众视线,而且使之成为一种游离于大众文化生活的盲区。就笔者切身体验,博物馆的这种失去生活亲和性的庙堂感特征,以及内外塑成人们对它的心理距离和态度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感性指标:
首先是陈列内容与社会现实的间离感。目前,国内地方博物馆藏品的来源主要有:考古发现、拍卖所得和私人捐赠。对于考古发现的藏品而言,在当地考古发掘的文物自然是最能体现当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藏品。除此之外只能采取其他的渠道去收集文物。然而,各地方博物馆的经费对于拍卖或收购文物而言却是杯水车薪,往往很难以有限的经费收集到有价值又能代表该地区的藏品。而文物藏品本身与现实生活的历史间离,本身即不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感,更不易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引发人们深入了解的欲望。此外,部分博物馆对藏品研究的不足,以及学术倾向的偏颇,忽略了博物馆作为公共教育空间和大众化知识传播的职能,这样的“学术”从而使得公众对陈列内容与现实生活无法产生联系,以至日益与社会现实形成区隔与间离。
其次是展示方式与生活效能的间离感。在全球格局下,先发国家的博物馆势力拓展,令无数博物馆模仿其范式,也使中国地方博物馆没有明确宗旨,没有明显区别,产生“同质化”现象。[1](P86-89)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乃至国内大部分地方博物馆的展示方式普遍呈现出一种单一化和简单堆积的视觉形态。就榕博来看,尽管馆内的4、5号常设展厅的展示形式(技术方面)有所与时俱进,引入了多媒体技术模拟场景再现,但由于素质、内涵不足的掣肘,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去寻找自身的重点、闪光点,只是简单地铺陈,总给人一种为形式而形式的“换汤不换药”的感觉。换句话说,地方博物馆在展示方式上,仍囿于机械地保护藏品和研究开发上的保守,无法突破陈旧的模式,无法与观众取得互动联系,无法带给观众参与感,很难唤起观众的认知快感和审美体验,以至“千馆一面”的低品质的观展感受,进一步加深了与生活现实的间离感,从而在当代鲜活的文化艺术热流中却日益边缘乃至“缺席”。
再者是空间内涵与城市社区的间离感。现代城市是一个免于世外化的文化集合体空间,公园、电影院、艺博会都是公共空间,地方博物馆也不例外。但现实是,人们在文化休闲与消费时,选择公园、电影院甚至艺博会的几率却远远高于博物馆。地方博物馆所陈之物,本就是社区历史积淀之物,就像是展示自身财产的公共大客厅一样,它理应亲和于这个地区的人民,可供所有人观赏和学习。然而,现实与之相悖,笔者就亲历过有“城市活地图”之称的的士司机不知道本地博物馆位置的情况。即便这算是一个孤例,但仍侧面反映出地方博物馆“开馆如闭馆”,脱离社区共同体,乃至让人不知在云端与地下、神圣与卑微之间选择哪个词来说明它的世外化现状更准确。这样的恶性循环,公众可能对它有敬畏,但确切没有了接近它的欲望。
对于上述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说:地方博物馆“展品有限”可能与财政经费有关(如榕博展品数量质量与省博相差很大),“布展生硬”可能与水平观念关联(如榕博出现没有文字介绍且与环境不相应的蜡像排列等),以及由此带来了“影响力低”(如百度找不到榕博官网,微信推送月均阅读量71.3人次/篇,部分场馆双休日和暑假空无一人等)等造成公众与之心理间离的三个因素,但这种“因果”关系,应该说还只是问题的表层方面。
二、“在场”的缺席:博物馆的“出走”与归因
分析起来,榕博所表现出的地方博物馆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席”或是“出走”,还有着深层的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原因。这里简要谈三个方面:
(一)神圣的幽灵
历史地看,西方博物馆的前身是为宗教宣传教义服务的神圣空间,后来成为世俗中王公贵戚珍奇陈列和对公众逐渐开放的场所。这一历史,实质上是一个造成其神圣化、精英化、中心化等三化一体、塑造传统的过程。如今,虽然在去中心、去圣化等大众文化思潮作用下,博物馆逐渐修正自身的定位,成为敞开心扉、与大众深切互动的一个公共空间,但其经典的形制,在引入我国后,与封建王公贵戚珍宝收藏把玩的历史土壤相结合,还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影响。尽管自辛亥革命到新中国建立后,博物馆被纳入国家的社会教育体系,以及学习前苏联经验开始创建地方综合性博物馆,直至成为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组成部分等等,但其传统的“三化”特征没有得到实质改变。
神圣的基因是藏在其问题表象之下的深刻根源。换句说,百余年来,尽管博物馆从圣物说教到炫耀珍奇再到惠泽百姓,走向了价值普世之路,但这一过程,却并不都是统一的和现实的。传统格局仍占据主导地位。新的形制,特别是在省级以下地方博物馆中,其理想主要还处在目标理念乃至于想象的水平上。正如“榕博”所表现出来的现实面貌一样,即使知道要加强与民众的联系,却难以真正做到“接地气”。究其本质,仍是由于其神圣化的幽灵还在。
(二)高大的冠冕
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经济基础是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等观点和观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就本土现代文博史而言,不妨作一简要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2](P10);1953 年“一五计划”开始执行,博物馆在这一时期以社会教育作为主旨,其现实教育的意义大于历史教育;1961年3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指出:“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重要工作”“切实保护文物对于我国的科学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向广大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起着重要作用”[3];至于1966年肇始的十年“文革”,则强力塑就了只能“官办”的文博事业的工具化。不难看出,作为上层建筑,博物馆历史的确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各博物馆所有的展示陈列在表面上看并无不妥,实则如笼中鹦鹉,无法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文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说教遗风渗透并长期规定和影响着博物馆所要传达的观点。19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不仅民众的精神生活开始变得多元、多层次,博物馆业也被允许“民办”和“民营”。但有意味的是,国家级博物馆、美术馆已经在日益密切的国际交流中贴近了人民,让民众乐意进入这一愈发民主的主体交互空间,但地方“官办”博物馆却依旧沿用单一守旧、脱离民众的传统范式。究其原因,除了其自主权、人才资源等客观局限外,从政府官员,到场馆管理者对博物馆高大的意识形态“冠冕”的历史保守性,以及运作眼界的局限性,不能不说是其未能实现介入生活的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身份的焦虑
从2010年全国博物馆年检公示的数据看,国有博物馆中的文物行政部门管理的国有博物馆、行业性博物馆以及非国有博物馆三类博物馆,所占比重分别为70%、17%、13%;至2015年,此三类博物馆所占比重分别为60%、16%、24%。从数据对比中,可以得出五年间各类型博物馆数量均有上升趋势,但在非国有博物馆遍地开花的同时,文物行政部门管理的国有博物馆明显活力不足,而地方博物馆正属于这个范畴之内,属于非营利性事业单位。当然,“非营利性”虽然界定了博物馆的运营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但却绝不意味着不作为、不开拓创新。目前,在国有范围内,地方博物馆存在着既无法达到国家级博物馆与公众互动的技术水平,在竞争中也缺乏开拓自身应有的特色性,又缺乏民营博物馆在资金、活力和跳出传统意识形态的能动性等三大不足。从而在这种不免悖论的现实关系作用中,也被社会现实所定义——在文化发展大潮下,画廊、艺博会、拍卖行、博物馆等营利与非营利性同构的文化生态链与产业关联中,作为价值检视与评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地方博物馆却显示出了一种类乎“出走”的“缺席”状。这种为社会提供普及性的文化教育场所,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或是脱离群众的带有精英主义的小众文化(亚文化),或是仍然处于类似前苏联意识形态传声筒状。总之,在政策体制、个性建设、运作自主等问题的多重矛盾纠缠中,地方博物馆及其管理者,明显处于一种身份无定的尴尬和焦虑中。
三、去圣化:对地方博物馆“回归”生活的两点看法
从现代文化理念看,地方博物馆对大众日常生活的归返,并不是要对别国、别地的简单模仿与复制,而是要解放思想、互学互鉴,通过引入现代视觉文化思维和互动理论的方法,来把握和彰显博物馆的精神实质。从科学体系看,这一方面要开放援借新文化社会史学等新学科的新思想新理念,将社会景观化、表象化等当代历史图景和趋势,变为鞭策自己对博物馆自身系统、机制等内部开掘和挖潜的动力,一方面又要积极借鉴和引入现代画廊、美术馆或艺术博 物 馆(gallery或 art gallery ,art museum)的活性因子和理念,通过对社会服务的具体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因地制宜地进行艺术化改造,促使各种资源和要素得到与互动社会相适应的转化和重组,从而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因为后工业化以来,各种文化早已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圣符号,而是一条在各个领域通向普罗大众的大道。而就辩证思维讲,观念的转换决定着态度,态度决定手段、媒介、陈列乃至对时空的理解和变化。应该说,从20世纪60年代瑞士伯尔尼美术馆馆长哈罗德·泽曼(Harald Szeemann)著名的《活在脑中:当态度成为形式》一展的精神开拓与变革,到当下发达国家博物馆已然成为科学认知,公众参与,主体交互等文化探索、实验的空间和场域,这也是现代地方博物馆走向当代文明的普适与亲民之路,是博物馆介入生活、民主互动、不断实现自身价值的回归之路。
(一)参与、互动、活化于日常生活
观众的参与是博物馆各项功能的基础,虽然目前地方博物馆的人流量和观众参与度尚不尽人意。但不妨从互动和活化馆藏的环节,找到博物馆“返乡”的突破口。
在互动方面,叙事结构的展厅设置可以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展感受。例如南京博物院民国馆的展厅内的多媒体技术将展示定性为“穿越式的环境”,在这里的多媒体转化为了一种“语境”。[4](P156-157)在观众的参与度上,利物浦博物馆群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一部分展陈摆脱了传统博物馆的陈列方式,真正实现了观众的参与。比如世界博物馆以自然生物为内容的“亲手触摸”环节,参观者可以亲手触摸、掂量植物种子、动物骨骼等,这一方式完全颠覆了在博物馆里什么都不可以碰的神圣原则。[5](P43-48)这便是惠于观念转换,以此增加了参与度,让博物馆不再是高高在上、只可远观的神龛庙堂,而是一个轻松、无距离休闲学习的场所。感官参与的活化案例也值得我们参考,例如在加州的沙利纳斯市,美国国立斯坦贝克博物馆把斯坦贝克小说中动人的气味景致保存下来。使用它制作了一些可供互动的永久设施,让观众闻到各部小说中的各种气息,像是《小红马》中的马厩味、《科特斯海航行日志》中的红树林气息等。这些气味储藏在隐藏的罐子里,由计时器控制而定期喷出。[6](P26-33)诸如此类,在调动除了视觉以外的感官参与的同时,不知不觉中就打破了“只可观看”的常规观念,自然就产生了强大的亲和力。与此同时,一切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是一根本原则,而决非是盲目引进一切最新的技术和设备,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否则,就不可避免的落入“同质化”的泥淖中。
(二)过去、现在、未来的现实统一
“事实上,在人类生存环境演进和城市生活变迁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往往浑然一体的,过去的遗存、当代的生活和未来的迹象,往往同时呈现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博物馆文化不应仅记录过去,还应反映现代和未来发展”。[7](P4-7)那么,如何实现“过去——未来”的创造性连接呢?我们可以参考2013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推出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8]。博物馆陈列和保护的人类丰富的遗产,与人类的创造力和活力密切相关,它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键纽带,对所继承的文化注入时代内涵和特征,让文物活起来,通过这种删去神圣感、庙堂感,融入时代感、新鲜感的过程,增大增强博物馆的亲和力,自然带动人们接近博物馆的愿望。国际博协总干事朱莉安·安弗伦斯曾说:“博物馆需要坚信自己的存在与行动可以以建设性的方式改变社会,因此,将‘保护’这一传统使命与培育创造力相结合以实现博物馆的更新和观众数量的增长,是博物馆应该追求的变化。”[8]不难看出,博物馆走入社会、贴近民众,显然需要的是现实的创造力的培养。在“保护”的传统使命下,发展多方面的创新模式、创新方法以及创新形式以实现与观众的连接,这种连接,必然也将过去和未来自然地联系起来,即通过了解传统文化,教育启发人们创造更好的当代文化。
现实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辩证与同构。一切现实都需要继往开来,都需要前瞻与开拓,从而一切历史不仅是当代史,同时也是未来史[9](P2)。当代文明要求贴近当下社会和现实生活。作为当代文明的艺术表现,当代艺术文化风起云涌。地方博物馆应该与时俱进地引入一定的本地当代艺术文化事象,打开本地区民众的眼界,提高本地区民众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水平。不仅如此,打破窠臼,培养社会“装置艺术进博物”“行为艺术进博物馆”“实验艺术进博物馆”等创新试验,也可以让地方博物馆焕发出新的魅力。博物馆之于中国正处于“青春期”,青春意味着敢于尝试、充满活力,不应该害怕尝试。正如法国巴黎卢浮宫相对于奥赛博物馆和蓬皮杜,古代、现代、当代并立,才是对历史文明的完整诠释。反观各地方博物馆,其莫如将陶瓷、青铜、钱币、玉器、字画等古器物,有现实意指地与当代艺术链接,古今砥砺、相互激活,为博物馆注入时代气息,让公众对文化艺术的认知与时俱进,管窥世界。
巫鸿先生曾表示:在中国的艺术博物馆馆,你看不清世界。如果这算是一种对国家层面的期待的话,那么我则认为,在福州市等博物馆也未必就能看清本地——我们好像既没有“世界性”的博物馆,也没有真有个性的“本地性”博物馆。在我眼中的现实是:地方博物馆不如从开掘自身社区的内涵做起,从而更符合自下而上、百花齐放的历史趋势。此外,正如巫鸿先生在诠释本土美术馆特点和不足时所言:“我们的美术馆缺这些东西(中国近现代艺术),这也说明研究者对19、20世纪的研究不够,结果呈现给大众的印象是,那好像是个很荒凉的时代,但其实不然,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②作为地方博物馆,因地制宜,引入本地近、现代艺术作品自然不是随意的。这便需要地方馆的研究部通过正面研究近、现代文明,以带动对传统文化发展的梳理和价值再认,从而将既符合历史趋势、又反映本地生活的文化理想和发展观。由之策之以展,在引导、提升公众三观和审美品位的同时,也能彰显出自身的功能和对时代的回应。
结语
麦克卢汉曾说过:我们创造了工具,工具反过来也塑造了我们。[10](P4)在现代视野中,地方博物馆当下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要融入时代生活,实现现实的“在场”。博物馆远不是一个被动的工具或中介平台,而是一系列关乎价值取向的文化理念;它不只是资源集合的贮存地,同时更是意义发现、扬帆未来的精神港湾。即便从传统美学观看,其内容的目的是形式,而其形式的目的也是内容。正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那样[11](P9),把握好这一点,观念与态度很重要。因为观念决定态度,态度成就形式。为此,无论从接受美学还是互动理论看,对地方博物馆这一培养社会、塑造社会、彰显和开拓现代文明的文化空间,从其“存在方式”到“价值实现”,必须尽快有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反思批判和深入实践的探索过程。
注释
①福州市简称“榕”,“榕博”即福州市博物馆(后同)。该馆包括七个附属馆:辛亥革命纪念馆、邓拓故居、福州文庙、闽王祠、华林寺、海上丝绸之路展示馆、陈绍宽故居。
②《巫鸿:在中国的美术馆,你看不清楚世界》一文是记者石剑锋对巫鸿先生的访谈,原文发表于2015年2月6日的《东方早报》,由于该报停刊并被“知网”移出,其内容通过百度或通过“宋庄美术馆”手机公众号可查阅[EB/OL]:http://mp.weixin.qq.com/s/g6KmuVLOYfNn48YHfUKpfQ,2015-02-06/2017-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