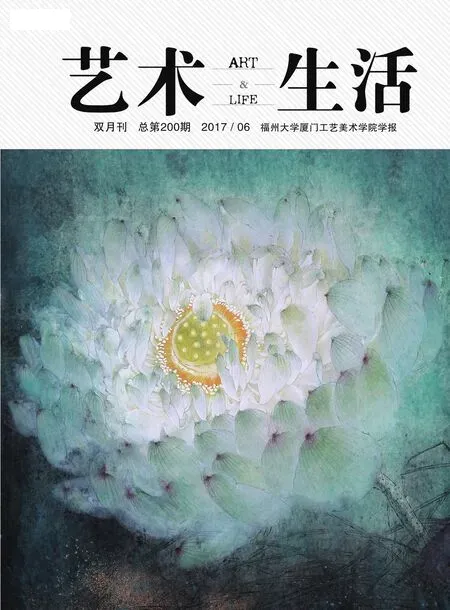重估传统批判
2017-02-14赵成清
赵成清
(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610065 )
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浪潮席卷中国,本土文化受到灾难性地冲击。此时,如何创新成为一个时代的焦点话题。历史的巧合抑或是冥冥中的定律,在今天,创新再度成为亟待挖掘的多义词。
当传统领域一度面临被湮没的时候,胡适提出“整理国故”[1],这是一个与时代极不相符的号召,显得孱弱无力。在百年的历史沉浮中,中国的儒学就曾连番遭遇批判否定的命运。无独有偶,在艺术层面,传统式微,国画也命运多舛,新生的油画逐渐取代了中国画的地位,一切价值都面临着重估。相比之下,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全盘西化论点尤其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界的广泛关注。文学革命和美术革命接踵而至,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肇始似乎同样表明了一种观念:西化即创新。
从文学到艺术,从科学到民主,从思想到革命,20世纪的中国呈现出“西化”一边倒的倾向。在各个先锋领域,倡导者无不视西学为改造或创始新学说的催化剂,然而,历史的积淀却遗留下了诸多问题,曾指导中国人前进方向的“科学”旗帜,却间接催生了两次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欧游归来的梁启超一度高呼“业已破产的西方文明亟待中国文化来拯救”;曾促使中国人孜孜以求的“自由”理念却导致了中国古典审美标准坍塌,传统文化亦在当代缺席。
无可否认,对于任何一种文明的涅槃而言,外来文化的刺激和引入是极为重要的。可是,其中更重要的仍要归结于主体内在性。在几种古老的文明形态中,唯独华夏文明延续了一以贯之的道路,这个问题一直未受到重视。难道否定历史就是创新?孔子的“述而不作”是否可以被看作一种创新?如果该命题成立,那么对传统的掇英何尝不是创新。《左传》倡言“三不朽”①:立德、立功、立言,对于学者,此三者不容忽视,中国人追求的不应该是西方意义的线型社会“进化论”,而一度引领时代革命的进化思想,其消极后果在本世纪也引起了深刻的反思。用西方的学科知识诚然可以丰富中国固有研究的建构方式,却尤其不应该忽略中国的文化本体,即坚持民族传统的求实精神。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儒家的一种人生态度,古之学者为己不为人,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首先根于“修身”,正可谓“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自知”。而古希腊最聪明的智者苏格拉底之所以被神认定为最聪明的人,恰恰在于其“我知道‘我不知道’”这样的真理。如何安身立命?黄土文明的儒家世界观中,“正心诚意”②是根本要旨。在现实中,孔颜乐处代表了一种理想,若理想破灭,仍可乘桴浮于海。或许这成为一种中庸的心态,却绝不消极后退,儒家思想从来不是遁世的哲学,可却有一种心理的自我调适能力。很显然,鲁迅在批评阿Q式的劣根性时从儒家中庸观中找到了其不足之处。“中国人过得是一种精神的生活”[2]。在我看来,辜鸿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从颜回到曾点到刘禹锡,安贫乐道,其乐在自足;从孔子到杜甫到康有为,其推行天下大治的主张超越了个人得失,这些无不展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人本主义情怀。
宋元以降,儒道释逐渐合流,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必然走向。庄禅美学都强调亲近自然,适时而退,故可以万物静观皆自得。而在儒学的天命观中,直到当代,人们的视域更多集中于剖析封建王权专制的人格神控制论。至于儒家中更广泛、更深刻的可以为华夏文明发扬的心性之学,其受重视程度显然不够。在中国传统中,道家以“道”为世界万物创生的逻辑元点,儒家亦曰“道不远人”“人能弘道”,禅宗则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③,为什么华夏文明能够生生不息地延续,正在于中国人对平常之“道”的体证和坚守。虽则迥异于西方之方法论和世界观,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倒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正是中国美学对自然和人生的追求,有别于西方文明中科学主义滥觞后的激进思想。中国近代美学家朱光潜曾著文道:“慢慢走啊,慢慢欣赏”。人生的道路固然通畅坎坷皆有之,但人生态度却至关重要,岂不闻“朝闻道,夕死可矣”,当一个人确立了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其人穷志坚,不应过度苛责。
王阳明曰:“不离日用常行外,直到先天未画前”④,此语标明了日常实践的重要性。学术研究固然不应该是空洞的理论,否则将意义全失,纯粹的人生观照,却可以在学习中得到体会,宗教、艺术、哲学等人文学科增强了学习自身的乐趣,这种乐趣有别于生理上的悦耳目口鼻之乐,而是悦心情意志的一种快乐。同样,在理论维度转向实践维度时,意志和行为融为一体,偶尔也会陷于方向选择的两难境地。这个时候,过程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是杨慎所做《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从历史学的角度,是一种循环论观点。同时,该词也灌注了一种人生关怀,一种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在没有宗教神学可以托付的前提下,中国人面临着个人的“小我”和历史的“大我”矛盾,面临着有限的存在和无限的世界这样的困惑。那么,从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角度看,“文王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这些个例都证明了目的和结果的差异性,过程则为成就的关键。因而,“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虽成也项羽败也项羽,他的行为却对“英雄”形象有了深刻地诠释,失败并非后世对他唯一的盖棺论定。
在现象世界中,词语成为建构世界的有效方式,话语权的掌握凸显了弱势群体的卑弱心态。从尼采的叙述中,奴隶道德显示了主人的威权,“酒神”精神是一种个体的解放。尼采的哲学反对权威和理性,要求重估一切价值。同时,他又是尊重传统的,他原初也是一名优秀的古典文化传承者,他写道:“谁可曾向一个希腊人学习写作!谁又可曾撇开罗马人而学习写作!”[3]这种对传统的思索本可以为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性”做一范本,孰知国人不吸取其批判精神,却只强调对西学的全盘西化,甘做他者的中国当代学者,认为中国已全面落后,将西方人言必称希腊的传统发扬光大,言必称西学,批判的落脚点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却罔顾西方的现代文化是基于对传统价值的扬弃而非抛弃。
追求西学者固然有最好的辩护理由,抛开融合中西的宏大叙事不谈,西学作为一种对中国固有文化的补充的确大有裨益。症结在于,如何将西学的核心理念有效引入中国文化中,中国为什么要引入西学理念?当亨廷顿、汤因比、斯宾格勒、泰戈尔等西方学者纷纷将文明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时,中国却在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证明着二律背反的命题。正如在现代艺术思潮抛弃了写实主义而追求个体化、表现性的自由创作方式时,中国艺术却将发展的动因追溯到在西方已经没落和抛弃的准则上。这种吊诡反映了中国现代民族文化在道路选择上的困境。
笔者悲凉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竟然不是由于西学的冲击而遭到摧垮,而由于自我的否定。须知,任何一座大厦的倾倒多由于内部结构的原因。中国文化的承传需要坚定的拥护者,需要虽九死而不悔的勇气,需要王国维“五十余年,只欠一死”的决心。在传统和现代交锋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经受了百年的冲击,余波尚在延续,部分学者既缺乏学贯中西的根底,又丧失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锐气,在保守心态下强以为知,缺乏研究却滥加批评,成为学术发展和文艺复兴的阻碍。
在当代,学者多空发议论,其批评多无创见。其中,弊病有三:一,但未见之事实或未闻之言论,则不足信。则其人何尝见过远祖,岂可谓远祖之不存?二,随波逐流的言行方式。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古人言:“修学好古,实事求是”⑤。当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以“专家”自居,常常扮演着全知全能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这种强以为知的骄傲心态往往引领着大众的盲目跟随。西方哲学的自由思潮方兴未艾,国内的国学复兴却已粉墨登场,文化艺术固然是随时代不断变动的,可是这其中需要深刻的理性反思和自我批判。掌握话语权的学者何时能意识到自己对知识权利权利的滥用?三,畅言现代化即西化,西化即创新。须知,无中学之积淀,立足稳乎?冯友兰引公元5世纪的鸠摩罗什语曰他人翻译之语言如嚼饭喂人,食之无味。本国之文字尚且难以琢磨,无他国之社会环境和历史文明熏陶,语言只触及他人文化之皮毛,取西人文明史中纤细之毫末,蔽国人眼目,以为泰山之大,发论作新成就与新创举,有识之士,以为然乎?
20世纪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⑥的治学理念,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让后学钦佩不已。他的思想对于中国近代化发展,包含文化艺术教育、思想革命事业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斯人已逝,对其思想真正了解者正如对中国文化真正了解一样,何其之少,倘若国内学者有蔡元培的包容思想,中国当代文化之进步指日可待。近代国学大师黄侃言:“五十岁前不著述”。这句警言诚然对现在的博士论文洋洋洒洒数十万字有批判价值,对著作满天飞的专家也是一种有力的嘲讽。学之不深,积之不厚,德之不修,其悾悾然之言辞能发幽微之立论乎?妄言传统的人经常忽略的事实是,中国古人追求的是一种天地境界和人生境界的融汇,实践性的和日常性的生活实则是生活的至理,故曰立德为先,此处“德”的内涵是内在的修养外化为一种行动,并非空洞的理论论述。同样,对于那些肆意空谈西学而不深晓其文化语言及历史精神的学者,“惜墨如金”更是一剂苦口良药。须知,中国文化的脊梁要倚靠他们承负,他们不仅应担负慎终追远的传统,更应该将传统文化中个人修身和大同社会的宏大理想光大,而不是神话异国文化,这一点,他们任重而道远。
当个人的认知能力与日俱增,对文化核心理念的纯熟掌握,就会产生一种由内生发的气质,孟子曰:“吾善养我浩然之气”⑦,这是中国独有的生命体悟,儒家倡入世精神而摈弃杂说,道家求自由而言“道”不可“说”,禅宗曰开口即俗。吾生也有涯,而学也无涯。人生有很多阶段,需以平常心辅弘毅之志,对待学术,固然需要“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⑧否则,将是学术之殇。
当中国学者批评自己本土的的文化传统,批评他者不懂传统时,自己可曾意识到传统这口井的深度,若知之,必不会作如是批评。
批评传统与批评现实是一对双胞胎,辨别的界限相当模糊。对于只求皮毛的西学崇拜者,启蒙现代性的光芒遮蔽了它的阴影。盲从者尚未意识到,在缺乏具体语境的时候,西方的话语和方法在中国本土是失效的,他们用西方文化艺术的逻辑推演中国传统艺术的未来之路,难免走入死胡同。由学术创作上的步步亦趋到艺术批评上的陈词滥调、捕风捉影,中国当代文化艺术批评陷入的困境是本土批评标准的缺失。
传统和现代的桥梁经常让缺乏独立批评精神的学者一如“封丹的驴子”⑨那般彷徨。管窥传统艺术,传统变革中是否存在着现代性?通过中国现代绘画史可见一斑。潘天寿无疑是20世纪中国画坛最杰出的代表,他意识到不能囿于传统的窠臼,而立志于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内部革新,从长期浸淫的中国画审美内涵中深入研究,高度关注画面形式,追求形象真实和视觉效果。因而,潘天寿的画面中,诗书画印的功能拓展出形式美的视觉效果;他特别讲究画面经营,将画面的块状几何分割辅以一种装饰色彩,画面从而生发出一种形式意味浓厚的现代美。现代形式绘画大师吴冠中在回忆潘天寿时说到:“他作画时说‘我落墨处黑,我着眼处却在白’。从潘师这多年,我认为这是他课徒中最重要的一把钥匙,也正是形式法则中矛盾双方性命攸关的斗争焦点。”在西方现代绘画中,黑白灰的整体组织非常重要,潘天寿在整合了传统国画中黑白的虚实之妙用后,以笔墨的黑白创造出抽象的点线面结合的审美形式,在这一点,不但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可以窥斑知豹,而且在吴冠中的画面中多能看出其深受潘天寿影响。克莱夫·贝尔曾宣称“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4],潘天寿的艺术创作很好地将东方的审美意识通过绘画形式传达出来,他的绘画充满了现代视觉张力。他对于形式美的创造赋予了新国画以极大的启迪,在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上,潘天寿都充当了时代的先行者。当江丰提出“中国画不能做大画,没有前途”的时候,潘天寿创作了很多气势撼人的大型绘画作品,他以一种“入世”的态度说明,中国艺术并不囿于传统的象牙塔,也没有沦落到“中国近世之画颓败之极”[5]的地步。中国传统绘画向现代绘画的转变,以潘天寿的艺术作品为例,可与西方优秀的现代抽象绘画交相辉映。直至今日仍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潘天寿在中国画广受批判,西画被视作现代和进步的标志时,他仍然在捍卫中国的传统审美价值,提出了“东西方艺术是世界两座高峰”的“双峰论”,并执著地在中国的内部寻找创新的源泉。回顾艺术史,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一味追求西化而片面忽视传统为中国近代的文化艺术带来了巨大的劫难。直至今天,重估传统仍是时代课题,如何在中国传统中找到西学可以生长的嫁接点,其任重而道远。批评家否定传统文化艺术的时候首先需要深入传统,其次必须提供对未来的具体实践方案而不是空洞的语词指摘。鲁迅先生临终遗言告诫后代“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此言足可成为当代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警世钟。
陈寅恪先生言学术亟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西方学术界有自己独立的批评体系,西学之佳者固然可以采纳融入,但西学当代的发展则有其身后的文化、历史、宗教、艺术、语言等背景依托,而批评家在对待中国传统时却真如一盆洗澡水,其中之污垢与婴儿被一齐倒掉,不禁让人作疑。
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的冲突”这一著名观点。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根据宗教主题,中国近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梁漱溟曾指出,中国人的生活是现世的,是反求诸己的,而西方人和印度人则时刻寄望于超越性的“神”的莅临。因此,梁漱溟概括了中国、西方、印度对待生活的三种路向:一,向前面要求,此处指的是西方人的科技、征服意欲;二,对于自己的意欲变换、调和、持中,这恰恰是中国儒家传统追求的中庸之道;三,转身向后去要求,这里可以看做是印度哲学的自我否定态度。在梁漱溟看来,西方文化的态度需要更正,更重要的是,要“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6],在中国近代,对传统的重视应不仅理解为一种国故的整理,中华民族的传统是基于内部挖掘和个人主体性的前提下坚持文化道统,以治学为本,超越民族、宗教、道德和科学等领域的沟壑,寻求社会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的整一融合。
从现代国画家潘天寿的创作和思想中可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对撞交融,它反映了出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重要主题即:文化中心和中西融合。潘天寿的思想和实践体现出美学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整一,从对民族文化自身、个人的主体性和道德性挖掘,其内在性不仅是哲学命题,也是文化理念的展现。
以史为鉴,对传统的批判,应立足于深厚的传统积淀。在21世纪,随着精英艺术的消解和大众文化的滥觞,中国当代批评标准需应时而生,建构完整的本土批评体系,其中,传统和现代的二元转换的话题将继续下去,当务之急,在于摆脱功利主义的目的论,认真做好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梳理工作,并重估文化艺术传统,从而让一切历史都成为当代史的有益参照。时至今日,一直在仰望西方的中国文化需要自我确认,让世界更多观看和体验中国,其中尤不可忽视古典的规范和传统的价值。
注释:
①《左传·襄公二十年》
②《礼记·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③《传灯录》卷八
④ 王阳明:《别诸生》
⑤《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
⑥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1919年3月18日),原文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1919年3月21日出版),《新潮》杂志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出版),《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及4月1日。
⑦《孟子·公孙丑上》
⑧《胡适讲演集》一,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第5页。
⑨法国作家布·丹封在寓言中讲了一个驴子的故事: 一头驴子在两垛青草之间徘徊,欲吃这一垛青草时,却发现另一垛青草更嫩更有营养,于是,驴子来回奔波,没吃上一根青草,最后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