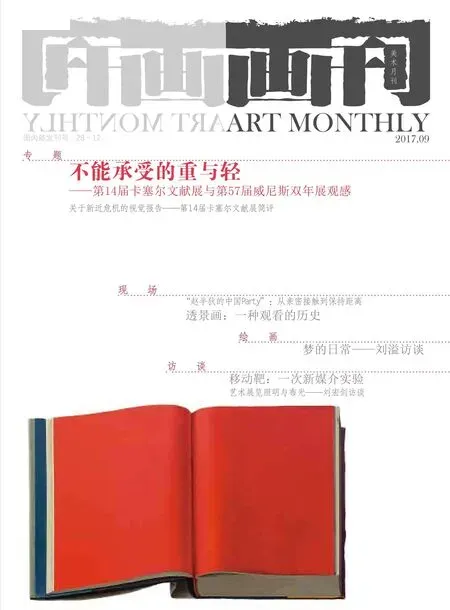托多罗夫的反神话
——《日常生活颂歌》读后
2017-02-13张颖
张 颖
托多罗夫的反神话
——《日常生活颂歌》读后
张 颖
托多罗夫1939年出生,早期从事结构主义诗学研究,精通俄国形式主义。1993年《日常生活颂歌——论十七世纪荷兰绘画》问世时,他54岁。此书行文相当放松,画面分析张弛有致,展现出作家成熟期的魅力。在阅读过程中,我产生了两点体会,经过推敲、反思,越发察觉到托氏思想的绵绵不断的启发力。
第一点体会关乎托多罗夫的艺术史观。
该书给我的第一个强烈印象是:作为艺术史随笔,它对艺术史研究成果的参考是有所拣选的。全书征引最多的是黑格尔的《美学》,而不是对荷兰风俗画有直接研究的诸多西方艺术史著作。众所周知,在主流的艺术通史著作中,荷兰17世纪绘画往往有一席之地(比如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专章讨论过这段历史,并题名为“自然的镜子”)。然而,就该书所列参考文献而言,尽管数量和种类可谓丰富,但其中艺术通史类著作明显缺席。这是由于托多罗夫缺少艺术通史的阅读经验吗?但他良好的艺术史修养,仅就这部小书而言也足以令人叹服。所以,托多罗夫应是有意忽略艺术史通史著作,有意排斥其中的某些观点。
现代学术建制起步于18世纪,在19世纪充分展开。张坚在最近的一篇文章[1]中提到美国艺术史家沃德、奈格尔等人提倡反思既有的研究框架的僵化之处,恢复历史记忆的碎片化和个体性,打破18世纪以来贡布里希、潘诺夫斯基等人刻意划分的过于清晰的历史界限,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的清晰分界。
对照此文来看托氏这部书,会发现托多罗夫也站在这一重估艺术史的行列里。例如,他将17世纪的维米尔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象派打通,认为前者预言般地实践了200年后被大声地、正式地说出来的观念:作为根本价值的绘画本身(马尔罗)。可见,托多罗夫的艺术史观不囿于通常的历史分期,而其实是穿越式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折叠式的。对于线性史观、对于进化论、对于严整的分期、对于广义上的任何艺术史建构,他都抱有相当的警惕和审慎。
由此也可以解释他对阿尔珀斯的看重(该书参考文献里列出了阿尔珀斯的作品)。这位出色的荷兰绘画研究者提出:伦勃朗的神话是19世纪的人们通过对他的生平和作品进行选择性解读而塑造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话呢?——伦勃朗几乎是凭一己之力,为画家们建立了一套自画像的基本模式,并使之成为西方绘画的一个主要门类[2]。类似地,托多罗夫也指出:荷兰绘画的历史地位及贡献是由19世纪的学者们建构,并被沿用至今的。二人所抵制的是同一套“神话学”。
托多罗夫不仅反对僵化的通史观,而且反对僵化的治史方式,比如任何形式的决定论。他鲜明地指出19世纪的决定论在两个方面固化了对荷兰绘画的解释:一方面是不加反思地将因果论用在绘画上,使作品成为政治和社会背景的结果,比如丹纳;另一方面是给荷兰绘画重新定性,给它贴上“现实主义”甚至“自然主义”的标签。
他不仅抵制决定论,甚至抵制反-决定论。因为后者实际上与决定论同属一套思维的正反两面。托多罗夫选择站在决定论与反-决定论之外,给艺术的影响因素赋予一种充满弹性的参考价值。于是,他一方面说“社会意识形态并不是像苹果树结苹果那样分娩出其代表人物的”,以此否定决定论;而紧接着又表示“作品不能简化为这一意识形态,但如果对此毫不在意,则意味着在一场对话中,执拗地忽略来自对方的驳斥”[3],以此否定决定论的反面。
第二点体会关乎荷兰绘画与照片的关系。
在第一次翻阅此书时,我一再想起罗兰·巴特的《明室——论摄影》,尽管书中对他这位老师未提只字。《明室》也是晚期作品,在那里,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之弦也松弛了下来,就像54岁的托多罗夫在《日常生活颂歌》里所流露的状态那样。
读毕,我开始反思这种联想是否合理:很有可能,这是先入之见所导致的阅读印象,也就是从“结构主义”这一标签去识别人、识别书,就像通过超市货架上的标签去挑选商品。这种先入之见很可能带来刻板印象,从而掩盖托多罗夫本人的独特性。
带着这种警惕,我进行了第二次阅读。而这一次,我更加感到该书与《明室》之间内在的亲缘关系。若说有一点蛛丝马迹的证据的话,那就是书中所引米开朗基罗的断言:荷兰绘画的特征有两点,即“现实主义”和“原样照搬”。对于这个断言,托多罗夫表示既不完全赞同,也不完全反对。而“现实主义”和“原样照搬”,不正是通常所认为的照片的基本属性吗?
那么不妨一问:这些17世纪的荷兰风俗画,可否被当成照片来看呢?这个设想很不成熟,也不严谨,甚至有些穿越的味道。但既然托多罗夫的史观可以是折叠式的,既然他颇有见地地将17世纪荷兰画勾连于20世纪初的印象派,那我们也不妨同样大胆地设想一下,17世纪的荷兰画法是否可以同样地勾连于20世纪的摄影术。
《日常生活颂歌》中共计45幅插图,皆为该画种的代表作。就我个人的视觉经验而言,它们很像照片,或者说,至少比20世纪初期那些照相主义绘画更接近照片。据我所知,照相主义绘画较多在“原样照搬”上下工夫,企图与照片争胜,反而被照片的这一天然优势给拘束住了,难以充分发挥画家真正的创造力和洞察力。而真正有资格跻身“艺术”层级的照片,其优势恰恰在于把握“生活的一瞬”(这是我在巴黎玛黑区那座摄影艺术博物馆获得的感受),而这也正是荷兰风俗画的强项。
我还发现,巴特和托多罗夫都更愿意使用“直接的直觉”来接触这些视觉艺术作品,与此同时将外部因素暂时性地悬搁起来。也就是说,不单单在画面的形式分析方面,而且在欣赏状态中的主客关系上,二人也颇有相通之处。那么,不妨更加大胆地设想:荷兰风俗画上有没有照片意义上的那种“刺点”?有没有可能把托多罗夫施展在荷兰风俗画上的分析方法应用在巴特书中的照片上?对于这些问题,进一步的落实尽管繁难,但这个角度的启发确实令人兴奋、令人脑洞大开。
通观全书,托多罗夫对于治史方法及史观有着相当敏锐的反思自觉,对于现有的艺术史叙述框架也怀着极其谨慎的审视态度。托多罗夫身上的那种反神话特质,是20世纪下半叶成长起来的西方人文学者所特有的。这一类学者反对僵化的学术建制,提倡个体的历史直觉。这种解放性的反思态度,一直在为西方学术激发新的活力。就此而言,托多罗夫的前沿性是永恒的。
注释:
[1] 参见张坚:《多重时间:从风格到“图像研究”——“重置的文艺复兴”及其争议》,载《文艺研究》2017年第7期。
[2] 参见阿尔珀斯:《伦勃朗的企业——工作室与艺术市场》,冯白帆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3] 托多罗夫:《日常生活颂歌——论十七世纪荷兰绘画》,曹丹红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