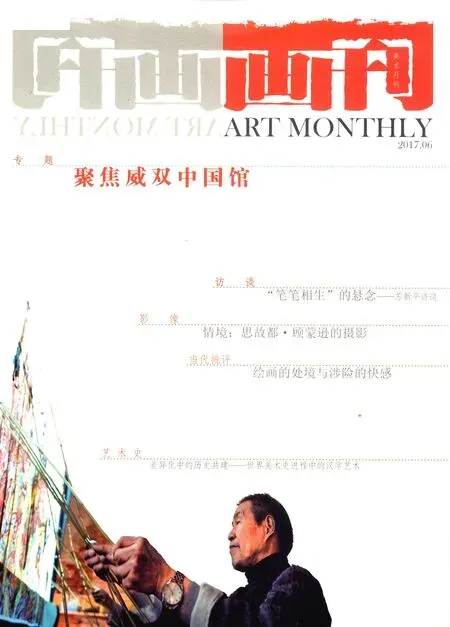差异化中的历史共建
——世界美术史进程中的汉字艺术
2017-02-12高天民
高天民
差异化中的历史共建
——世界美术史进程中的汉字艺术
高天民
按: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第九组分会主题为“独立”与“超脱”,该主题是对艺术史研究、成果和既定规范的“挑战”。本组尽可能地采取淡化针对艺术史学科问题讨论的方式,尝试性地避免把会议引向对某一课题或一结论进行的讨论。通过本次大会,我们试图进行的是一种“篡改”规则与规范的尝试,试图去探讨一个关于如何集合来自不同个体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史研究。这个尝试不完全体现在发言者的发言内容中,它更多的是融入我们的工作中。“独立”与“超脱”,简单地看是在讨论艺术史的一个比较抽象的“真伪”定位问题,实则上我们希望这个主题能被理解成关于艺术史研究起点和终点的原始猜想。世界艺术史大会不仅仅是一个展示成果和交流的平台,也应该是一个尝试的舞台。如何把我们自己(组织者或主导者)、发言者、听众和参与者从固有的和必须顺从的规范与规则中释放开来,以本体模式去咀嚼史料、史学观点,展现个体对艺术史学(或史学成果)的“误读”、“误解”和“误用”,以及让这些“误”有机会对话的尝试是我组重要的期待。(宁卓涛)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美术史界日益关注一个新的问题:世界或全球美术史的重建。这个问题被英国美术史家约翰·奥尼恩斯(John Onians)称之为未来“艺术研究的趋势”。实际上,对“世界艺术史”问题的思考自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1986年华盛顿世界艺术史大会就以“世界艺术:整体与多样化的主题”为题出版了大会文集。尽管那时人们对所谓“世界艺术”的认识与研究还存在着本质上的分歧与“差异”,但已经力图站在更为“中性”的立场来看待世界各地所出现的艺术现象与历史。可以说,这较以往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的动力就是80年代之后开始出现的“全球化”现实。
实际上,关于“世界”或“全球”的概念早在16世纪就随着所谓“世界地理大发现”而开始形成了。但那时的所谓“世界”所带来的是伴随着西方武力强权而至的西方文化的扩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非西方文化的遮蔽乃至摧毁。因此,这样的“世界”或“世界美术史”是不完整的,不过是西方价值观的呈现,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泛滥。但是,20世纪(尤其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整个世界在一个平面上彼此互动,由此带动了各种文化的共同参与,并依托建基于现代化进程而展开的现代艺术形成了一个世界美术“统一的美术史”。在此基础上,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的个体经验对于推进这种世界美术史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近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汉字艺术”以其全新的概念参与到这种历史共建之中,这无论对于中国美术还是世界美术都将产生划时代的影响。
一、全球化与世界主义
面对历史我们看到,全球化是将世界重新勾连为一个整体并推动“世界主义”这一概念再次抬头的一个主要因素。然而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全球化还是世界主义,其概念一直在随着历史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说16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那么第二次全球化的趋向早在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现代主义时期就已经开始,但由于低技术和信息传播的阻塞,尤其意识形态的对立,这种全球化便以“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的面目出现了。从客观上说,“全球化”既是西方跨国资本试图建立“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的一种尝试,也是由于通信技术、信息高速公路、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当这种全球化发展到了文化层面,其“世界主义”或“普世主义”的面目就演化为一种新的文化侵略。因此,在这个时期,作为这种“世界主义”或“普世主义”之变种的“全球主义”的实质则延续了“世界主义”的内涵,即以进化论为宗旨来推行新的意识形态,以消除差异。但是面对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环境,那种单极化的冷战思维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世界已向多元差异化发展。正是面对这样的新的历史情境,进入80年代之后,一种新的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主义观再次出现,其意图是在文化上重新建构“世界新秩序”。表现在美术史研究中,就是意在从“世界中心”出发去建构一种全球战略和全球眼光[1]。
可以明显感到的是:西方艺术史家自20世纪以来就对一种“不偏不倚”的世界艺术史写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从20世纪初开始,在《加德纳艺术史》《詹森艺术史》、弗莱明《世界艺术史》等几部经典世界艺术通史中,构建一种具有包容性和“普世主义”价值观的世界艺术史的趋向就已经显露,只不过在那个时候,世界美术的发展在客观上还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其一体化进程才刚刚起步,许多问题还没有出现。因此,他们的观点使之在处理“世界美术史”时还不免多少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余蓄。
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化推动下而再次兴起的“世界美术史”建构提出了新的理想:重建一种可以面对全球艺术史,并解释全球艺术发展的概念系统和阐释体系,这样的系统和体系能够容纳多学科并较以往具有更强的普遍阐释力。显然,这种学术理想在今天更具有客观的价值,也因而日益受到美术史学界的重视。在这方面,西方学者不仅再次走在了前面,而且做出了不懈努力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这个领域中,英国美术史家约翰·奥尼恩斯(John Onians)是一位积极的推动者。他不仅出版有《世界艺术地图》(2004年)和《简括与表现:世界艺术的组成与解释》(2006年)等重要著作,而且于1992年在英国东安吉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创办了世界艺术研究院,首次提出了“世界艺术研究”的概念,宣称这一新领域不仅在导向上是全球性的,在方法上也是跨学科的。此外,1986年华盛顿世界艺术史大会的文集《世界艺术:整体与多样化的主题》、美国学者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的《世界艺术史及其对象》(2008年)、吉提·齐尔曼斯(Kitty Zijlmans)和维尔夫里德·凡·丹米(Wilfried van Damme)的《世界艺术研究:观念与方法》(2008年)、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的《世界当代艺术——晚期现代至今》(2011年)等,也都是重要的研究成果和文献。与此同时,构建世界艺术史和开展世界艺术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2007年9月在英国诺里奇的塞恩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召开的题为“世界艺术:艺术研究的趋势”会议、2008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世界艺术史大会(会后出版了文集《跨文化——冲突、迁移与融合》)、2008年在东京大学举办的关于“世界艺术史”的研讨会——这些都广泛传播了美术史研究领域中的世界主义观念。不仅如此,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还于2009年筹划了以“世界艺术研究:为什么?何时?何地?何种方式?”为主题的研究生课程。这表明学界已经开始向青年一代研究人员传播这种观念。
有意思的是,在贡布里希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艺术的故事》成为畅销的经典艺术史著作之后,芝加哥艺术学院的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教授受到启发,从而认为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过去那种单一的艺术史已经发展成为一系列艺术的故事。为了回应贡布里希仍具有浓厚欧洲中心主义意味的《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埃尔金斯编写了表明自己观点的《艺术的故事集》(Stories of Art)[2]。他力图在一个客观的框架下来重新表述世界各地美术的发展。
世界美术史研究已然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如何就人类的艺术写出不带偏见又解释合理的世界美术史?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工程;就像约翰·奥尼恩斯所言,它是多元学科的或跨学科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它将对今天的美术史家构成新的考验。
我们注意到,这种在新的世界主义观念下的“世界美术史”建构仍然是在西方主流美术史家的主导下开始的。无疑,这种状况还将延续。但我们也注意到,在那之后,美术史研究的世界概念开始向非西方学界扩散。2012年底,中国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也成立了世界艺术史研究所。这意味着这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思想已开始受到更多美术史家的注意,只是其含义和意义正在悄然变化。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在中国举办,标志着世界美术史及其研究将进入一个“差异化中的历史共建”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的美术不仅将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而且还将进入一个新的一体化共建的新阶段——无论是美术史研究还是美术史本身。我们从世界美术史的历史趋向上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二、“世界美术史”的进程
尽管西方美术史学界对“世界艺术史”或“全球艺术史”的研究已经显示出了方法与学科等方面的不俗的成绩,但一个基本的问题却没有改变,即美术史本身。如果撇开史学或史学史概念而单纯从美术史本身考察,我们或许能从另一个侧面来验证“世界美术史”的一个不断世界化或全球化的特质。
如果就地域美术的扩展来说,“世界”的概念很早就在各地形成了:纪元初,印度美术随佛教文化的北传而构筑了一个地域广阔的佛教美术的世界;公元前2000年,古代埃及美术向地中海沿岸的扩散形成了一个连接欧非的埃及美术的世界;自汉唐时期开始,中国美术开始向周边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中华文明圈的东方美术世界;如此等等。从“世界美术史”的角度说,这些“世界”的形成从地域化的范畴上第一次向人们展现出“世界美术史”的可能。
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知识状况而言,“世界”的概念却是与西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第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世界艺术史”的形成发生在西方古典艺术向世界传播的时候。西方美术以古典主义的方式开始,文艺复兴标志着西方美术的成熟。这种具有体系性的成熟的艺术之所以在意大利发展起来是因为在新的世界观和科学技术的支持下,意大利的哲学和视觉传统为艺术上的突破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按照传统的“世界”概念,西方美术的第一次世界性传播仍然是区域性的——它只是西方文化圈内部的自我递进关系,即一个不断科学化和系统化的过程。这一点与之前其他地域美术的表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西方美术传播的第一次世界化具有两个方面的全球意义:一方面,西方学者和美术史家由此最早在美术史的概念上提出了世界化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在理论上为西方美术在19世纪中期以后向全球大规模扩散并真正实现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西方美术的全球扩散早在16世纪就已经伴随着耶稣会的成立而开始了,但直到19世纪才形成燎原之势。这种扩散当然是在西方强大的科技力量的支持下展开的,这种力量之强大使得整个世界都被卷入其中,并开启了一个科技美术的世界化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西方古典艺术为依托,呈现出从西方向非西方的单向推进趋势。而在第二阶段,随后兴起的西方现代艺术尽管在势头上更为强劲,所传播的理念也更具煽动性,但却逐渐失去了其方向——西方现代艺术的世界化进程是一个与世界各地文化与艺术不断融合与非西方化的过程。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现代艺术日趋东方化(这被丰子恺称之为“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3]),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中得以完全汇合。这一方面显示出其巨大的包容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其力量的衰竭。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美术史家宣布了西方艺术的死亡。
“世界美术史”在这里就具有了两层含义:属于世界的美术史和世界化的美术史。前者相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属于地域化的美术史,而后者则具有了世界一体化的性质。就目前状况而言,“世界美术史”的一体化进程越来越明显,即地域化的世界已经彻底让位于一个统一的全球化的世界。这就向未来的世界美术发展提出了一个紧要的问题:在一个以西方现代艺术为基础,而西方现代艺术却宣布自身已经死亡的统一的世界美术史中,世界美术将走向何方?
从美术的历史来看,19世纪末以来的世界一体化进程是以西方美术的现代化为基础的一个全球共建的过程,这个过程突出了差异化的理念,而差异化就使得全球各地的各种文化都具备了参与世界美术史建设的可能(至少理论上如此)。因此,这种共建在艺术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带来了世界各地艺术现代化的共同趋向。但我们在此要注意的是:艺术全球一体化使得世界各地艺术的现代化形成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共同的知识学基础”,而另一方面,在促使各地文化参与共建的同时,这种一体化又在改造着“共同的知识学基础”,并逐渐耗尽了推动这种一体化的源发动能,因而使西方从艺术到理论皆相继宣布“死亡”。这也就意味着,西方自16世纪起开始主导的世界美术一体化进程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世界美术的未来进程将进入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个阶段将由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接力,并在一个全新的文化观念下进行全面的资源整合,从而推动世界美术走向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未来。
三、汉字艺术及其全球价值
也就是在此时,汉字艺术在中国的兴起为这种酝酿中的趋势提供了契机。
所谓汉字艺术是以中国的汉字为基础进行艺术创作的一个全新的艺术概念,最初来自于现代书法的探索。经历了30多年的风雨历程,现代书法已发展成为今天的汉字艺术,从水墨书写延伸到当代艺术的各个领域——除了在水墨、油画和雕塑中逐步深入展开外,甚至包括了平面与立体设计、服装、陶艺、营造(建筑、装置)、实验戏剧、电影(影像)、行为等,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看,汉字艺术包括了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
1.中国的汉字及其一切文字资源都是汉字艺术进行创作的基础,其中包括汉字、传统书法、现代书法。因此,汉字艺术的创作离不开对中国汉字、中国传统书法和现代书法的学习与研究。
2.汉字艺术是一种形象的艺术。尽管它是以中国的汉字、传统书法以及现代书法为基础进行创作,但汉字艺术既不是艺术汉字,也不是书法,甚至不是现代书法,即它不再是一种汉字平面书写的艺术,而是一种包括了以上资源和平面书写的艺术形象的创造。因而它是一种建基于人的视觉感受的精神和观念表达的艺术。
3.作为一种精神和观念表达的艺术,汉字艺术将人类一切视觉艺术资源皆纳入自己的视野,因而其艺术语言和艺术表达方式同样是开放的。艺术的表达是人的表达,必然与创作者的当下感受和思考相关。因此,汉字艺术是当代艺术的一部分,并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而不断开拓出新的艺术语言和艺术表达方式。
4.中国的汉字、传统书法和现代书法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方式。作为汉字艺术创作的基础,它们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以各种方式在汉字艺术中体现出来。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将成为一切从事汉字艺术的艺术家(包括世界上任何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创作的基础,也是评价其艺术成就和艺术高度的价值基础。
简单地说,汉字艺术不是艺术汉字,也不是书法,甚至不是现代书法。它是一种当代艺术方式,以中国汉字、中国传统书法为基础资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价值依托,并向一切人类文化艺术成果全面开放,建基于人的视觉感受的精神和观念表达。
汉字艺术并不是一种新的艺术形态,而是一种新的艺术观念。作为形态,它不仅植根于中国的汉字和传统书法,而且已经在具有世界影响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中得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阐释。而这种阐释又反转回来,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艺术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启发,并在其后的实践中得以系统化和理念化,从而使汉字艺术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如今,汉字艺术已然以全新的姿态向当代艺术的各个领域扩展,显示出其巨大的包容力与适应力,而这种包容力与适应力恰恰来自中国文化的基本性质。中国文化中所强调的和谐的理念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当今世界美术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因此,作为一种新的艺术观念,汉字艺术依据中国传统文化而强调和突出了和谐的艺术理念,这种理念不仅以其包容性和容纳力将世界各民族文化置于一个平等互动的平台之上,而且还将使世界美术重新构建成一个互为依托的整体。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艺术理念之下,世界美术将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共建新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共同的知识学基础”——这是汉字艺术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内核。
在形态与理念之间,汉字艺术可以说是一个艺术价值系统,而不是一种艺术形式和语言;在这个系统中,形式和语言只是它借以进行表达的媒介和手段。但这并不是说汉字艺术就只能依赖于其他艺术所提供的形式和语言,恰恰相反,正因为汉字艺术是一个独立的艺术价值系统,它才更具有形式和语言创新的能力与空间。而这种创新一旦出现就将是全新的,并将在根本上改变世界艺术的形式语言系统,使之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进一步展开。因此,汉字艺术(无论其形态还是理念)是一种具有全球普世价值的艺术方式。其本身在形态上就具有天然的普世性——汉字是一种来自自然并直接诉诸人的视觉的形象化的语言形态。其文化亦是一种具有全球普世价值的文化。汉字艺术不仅将改变世界,而且将引领世界。
注释:
[1]陈岸瑛:《世界美术史何以可能?》,《中国国家美术》2014年第6期。
[2]James Elkins, Stories of Art,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2003.
[3]“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美术史上忽然发生了奇怪的现象,即现代西洋美术显著地蒙受了东洋美术的影响,而千余年来偏安于亚东的中国美术忽一跃而雄飞于欧洲的新时代的艺术界,为现代艺术的导师了。这有确凿的证据,即印象派与后期印象派绘画的中国化。欧洲近代美学与中国上代画论的相通,俄罗斯美术家康定斯基的艺术论与中国画论的一致。”婴行:《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一号,193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