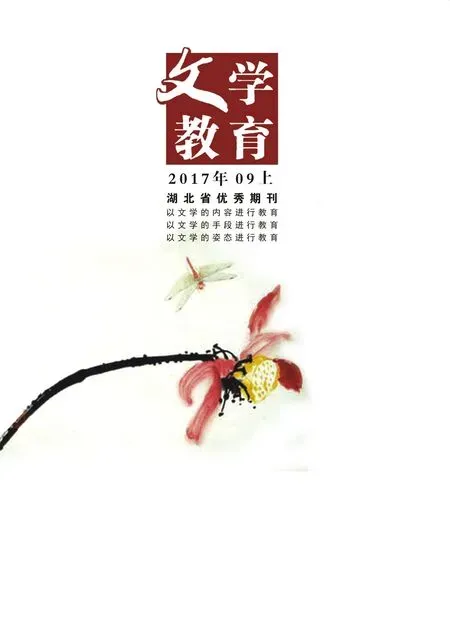晓苏《父亲的相好》叙事主体的选择
2017-02-12何永生
何永生
晓苏《父亲的相好》叙事主体的选择
何永生
父亲节这天,我在《钟山》2017年第3期上读到了晓苏短篇小说新作《父亲的相好》。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叫吕爽的男子,青年时代曾经一段不伦之恋,一波三折,却不中缀,不仅藏于心,而且施于行;不仅我行我素,而且还得到了女儿的理解与尊重,甚至连外孙也可以当面拿来说笑的故事。这样一个婚外情,不同的叙事主体一定会讲出不一样的故事。叙事主体不同,叙事立场、叙事视角、叙事腔调必然不一样。不同的叙事主体不仅会使故事形态不一样,而且会使故事的味道也不一样。《父亲的相好》选择以女儿来讲述父亲的婚外情,读者看到的父亲的相好,其实是父亲女儿眼中的相好。这个叙事主体的选择别有讲究,值得一说。
一.女儿作为父亲婚外情事情史讲述人的合法性和合适性。
小说作者选择故事讲述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一定会考虑讲述者身份的合法性和合适性。这关系到故事的可靠性、可信性、合理性及可读性。《父亲的相好》的故事讲述人“我”是父亲的女儿。作为女儿的“我”,并非讲述父亲婚外情事情史天然的合法者和合适者。按照“为尊长者讳”、“子为父隐”和“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恰恰相反。但正是这样逆情悖理的设计,不仅满足了小说阅读陌生化效果的诉求和期待,增强了故事的可靠性、可信性和可读性,而且通过讲述人讲述的话语方式和叙事腔调,让读者可以收获到更多除被讲述人以外诸如讲述者对故事中人、事的价值判断、情感倾向以及这些判断与倾向与日常生活规则和伦理产生的冲突,从而为读者在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重新审视这些规则,重新定义某种生活提供一个机缘。
为了让“我”取得讲述人合法性和合适性,与读者的前见达成某种妥协,小说以概述的方式作了极简短而又必要的铺垫。“我”也曾本能地意识到“不该这么口无遮拦地谈论自己父亲的风流韵事,而且多少也有点难以启齿。”由“本不该”、“难以启齿”到娓娓道来,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大略看来,至少经过了不让人讲,不听人讲,到“心情十分淡然”地面对,“还常常一个人回忆他们往事”亦生些许感慨的三个阶段。“小时候,每当有人提起父亲和他的相好,我当场就要发怒,又是哭又是骂,还扑上去抓人家的脸。青年时代,听见有人说他们,我马上会无地自容,什么话也不说,只顾着赶紧走开”,而“人过中年……再遇上有人讲起父亲和李采”,“我”不仅能够“十分淡然”地面对,还会“从中生出许多的人生感慨”。正是因为从懵懂少年到人过中年,不断遭遇关于父亲和他相好的传说和议论,“我”对父亲和他相好的事是了解的,有些事甚至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和亲自体察过的。加之“我”与此事关系特别,所以也特别敏感,接受的信息也特别丰富。所以,“我”的讲述是比较具有可靠性和可信度的。这样多种渠道断断续续虚虚实实的有关父亲和他相好的情事和情史的获得,加上自己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不仅拓展了“我”叙事选择的可能性空间,丰富了透视事件的视角,而且突显了故事讲述人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趣向。
“人过中年”“看多了、看穿了、看淡了”“人间的事”,是理解、宽容和接受父亲和他的“相好”;理解、宽容和接受那些对他们情事情史猜测、议论和传播的基础;也是“我”能够讲述父亲婚外情事情史之合理性的交待。读者看到的故事就是在这样“淡然”的心境下讲起来的。讲的很从容,且略带抒情性,甚至不乏美好的韵致。也正是在这样的讲述姿态和叙事腔调下,父亲和他的相好本来带有道德污点的情事和情史慢慢变成了一段罗蔓蒂克的传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了美谈;本来不无感伤和无奈的家庭生活变得有了波澜,生动丰富起来;本来一桩家丑也慢慢演变成了一件世代交好的佳事。就这样,父亲和他相好的婚外情在女儿的娓娓讲述中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读者很可能读着读着就放下了法律、道德和伦常的棒棰,在不知不觉中欲辩已忘言了,进入了叙事主体预设的价值逻辑磁场。仿佛不如此,男女主人的情感世界在不睦的婚姻生活中难得有一抹光亮,日子简直没法过下去。当然,不如此,故事也没办法讲起来和讲下去。因为不如此男女主人早年的冲动就会成为不堪回首的荒唐,中年的执着就会变成逆情悖理的执迷不悟,老来的坚持也会变成老不正经教坏年轻人的坏榜样。这自然是现实生活的逻辑和价值评判,如果小说的情感逻辑和价值标的与生活中的高度同一的话,小说作为心灵世界的真实与现世生活没有了任何的差别,小说作为人之精神世界某种特殊空间的存在就失去了应有的合法性。充斥生活的道德说教可谓多矣,未必缺少这一课。小说既要关照生活,也要与生活保持应有的距离,方才让读者有审视生活和自我的可能。当小说与生活同轨同辙,小说就成了生活的婢女,小说家也就成了街边地推上拿着主顾提供的照片为死者放大肖像的手艺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女儿讲述父亲婚外情事和情史的这一特定故事讲述人的设计,通过她的价值尺度和情感向度重新定义事件的性质,方才能够实现作者对婚外情在具体情境中消解法律正义性和道德绑架的可能,进而张扬爱情价更高的人道情怀。
二.女儿作为父亲婚外情事情史讲述者的比较视角和综合视角。
从伦常和情理上讲,女儿是父亲婚外情的直接受害者,是父亲婚外情最坚决的反对者,是母亲权益和自身权利最坚决的捍卫者,是父亲相好天然的敌对者。在《父亲的相好》中,尽管“我”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对别人讲传父亲和他相好的事表现过激烈的行为和隐忍的态度,但那都是不懂事的表现。在“我”人过中年,“看多了、看穿了、看淡了”“人间的事情”之后,也就是说在“我”懂事之后,对待父亲既往的情史和一直未曾中断的婚外情事的态度就几乎完全发生了变化。作为女儿,“我”虽然与父亲婚外情中的每一个相关者都存在高利害的关系,但读者不难发现,作为故事讲述者,“我”却显得相当的超然。在超然中又不乏情感倾斜,但并不是倾向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母亲,而是对父亲婚外情的好奇和对父亲相好掩饰不住的好感。这种情感倾斜有悖人伦与常理,它肯定是违拗本能的。但在没有受到外在压力下的情感转移或者说变异的驱动力来自哪里呢?社会学可能提供的价值驱动这一答案当然是切中肯綮的。小说文本没有提供直接可供分析的支持,却并不缺少间接的分析素材。那就是来自“我”对母亲和父亲相好的比较,来自对各个方面关于父亲相好的传闻和“我”亲眼所见、现场体察李采与父亲的生活情境以及李采对“我”友善的综合。是在反复比较,综合种种之后的合理反应和理性对待。这种比较在故事中仿佛不存在,因为它并不是显性的,但又无处不在,因为它浸润在故事的话里话外,产生了极高的溢出率。
在“我”讲述的故事中,凡涉及到关于父亲这位相好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不美、不雅、不善、不得体、不亲近、不可爱的地方。她的长相、才华、气质和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综合起来,就是典型的古典美与现代美的完美结合。在“我”的故事中,唯一对李采不利的传言,是父亲受处分回乡下地种田以后,社员中“有人”关于父亲和李采究竟谁主动猜测时候的议论:“肯定是那个相好主动找的吕爽,听说她已经结婚了,丈夫隔着几百里,远水解不了近渴呢。”即使对这样一种近乎“合理性”推测,“我”也并不认可,先是用其他人对父亲天生就是找相好的议论来加以平衡,后来干脆说“我至今没弄清楚,父亲和李采究竟谁是主动的”加以否定。在“我”讲的故事中,对父亲的相好虽有简历般的客观情况介绍,但更多的是主观感受式描述。李采是读了两年师范后分配到油菜坡小学的音乐教师,“她长一个小嘴,小得像个鹌鹑蛋,两个眼睛却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她“能歌善舞”。如果说这只是一般古典美人的标准画像,过于概念化平面化的话,那么,当“我”因一个偶尔的机会在一个平常家居的场合第一次亲眼见到她的时候,简直就“呆住了”,“她实在是漂亮,嘴和眼睛都像是画到脸上去的。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李采不光漂亮,而且还是极具现代气质的女性。她勇于担当:在校长别有用心地处分父亲的批斗会上她挺身而出,希望通过主动担责以减轻校长对父亲的惩罚;她在父亲备受孤立,踽踽离开学校的时候,拿着赶织的毛衣和月饼泪眼相送;她知道母亲因父亲与她的婚外情史和情事后犯病,主动自取其辱,以疗治母亲的癔病。她自尊:宁可被发配到荒僻的鸡公谷小学,也决不让垂涎她美貌的校长讨到哪怕是一个“谢”字的便宜。她善良心细:在“我”翻山越岭到鸡公谷寻父找到她那里的时候,她一眼就看出了“我”是吕爽的女儿,“弯下腰笑着问我,还伸手在我头上摸了摸”,她宁可委屈自己的亲生女儿,在为“我”准备的面条碗里埋下两个鸡蛋,晚餐的时候不仅为我们父女准备了很丰盛的饭菜,还专门为“我”做了青椒炒肉丝;看到“我”衣衫破旧,就把为女儿准备的花布料请裁缝师傅连夜为“我”赶做连衣裙。她懂得男女风情:在她家门前,“我”亲眼目睹了她和正在劈柴的父亲之间的互动。“她出来时双手不空,左手拿着一条毛巾,右手端着一个茶杯。她径直走到父亲跟前,温柔地说,吕爽,歇会儿再劈吧!父亲立即停下来,转身面向李采。李采先给父亲抛了个媚眼说,来,我给你把汗擦擦。父亲像个听话孩子,马上把脸伸到了李采面前。擦完汗,李采又给父亲抛了个媚眼说,出了这么多汗,也该喝口茶了!说着她就把茶杯递到了父亲嘴边。”李采对“我”的关心,自然是爱屋及乌,对父亲的柔情蜜意,世间哪个男子能够拒绝呢?这样的事情,好多年以后,在“我”儿子和父亲身上还有继续,那时父亲已经变成一个乡下老头,李采也已经是城里人了,就像当年山山水水不能阻隔她和父亲的爱情一样,时间、城乡差别、物质和容颜也没有阻止她对父亲的感情。她照样是那样的热情,一样是问寒嘘暖,打点前后,添衣备物,体贴有加,无微不致,还打发她的女儿照料我的儿子。
在这些关于李采大大小小点点滴滴的讲述中,其实总是有一个潜在的比较对象,那就是我的母亲,无论她在场还是不在场,她都隐隐存在。在“我”的眼里,母亲说不上是一个好女人,还是一个不好的女人,但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叫尚贤,喜欢循名责实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母亲不贤。她虽然没有李采那样风流的缺陷,但是也的确乏可陈,作为媳妇她没有尽到对公公婆婆义务,作为妻子也没有尽到对丈夫的责任,作为母亲我没有感受到她的温情与呵护;作为祖母孙子更愿意拿爷爷的相好来和爷爷逗趣。作为女人,她的光彩夺目仅在“很热闹,很喜庆”的新婚那个晚上有瞬间的绽放。在那个满足爷爷面子的婚礼仪式上,“母亲心情也特别好”,但“一层一层堆在脸上”“仿佛伸手就能抓一把”的“笑容”,在灯火阑珊之时,因为李采差人送来的一床毛毯,弄得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往下掉”。新婚之夜她和父亲“各睡一头,和衣而卧,连手都没有挨一下。”本来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促成的一桩婚姻,母亲在新之夜就遭遇了感情的滑铁卢。她的婚姻生活还未展开,就合上了页。36岁那年她就患上了一种类似臆病的疾病,每遇刺激即口吐白沫,如土委地。多年后在获得李采写给父亲的一封信后随即发作,又好多年后,“有一天”“在清理箱子和柜子,无意中发现了李采十几年前为父亲织的毛衣”,也会“不禁一阵心慌,两眼直冒火,身子一歪就倒在了地上”。母亲一辈子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却没有一天走进父亲的心里,也从来没有走出过李采的阴影。
在“我”的故事里,李采遭遇的危机是外在的,她作为父亲的相好是不合法的,是不道德的,但她总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去抗争,去坚持,去平衡,去拓展,去维护,去经营;母亲遭遇到的危机是来自内在的,她是父亲明媒正娶的妻子,是合法的,是道德的,但却只能依靠外在的力量勉强维系一个形式的婚姻,她没有化解危机的智慧,她自身所拥有的武器除了以泪洗面,就是自虐成疾,以至于“动不动就生气”,最后还是靠李采提供的所谓治疗秘籍以保全不再犯病,但对于感情这回事却渐至于麻木。
三.女儿作为父亲情事情史讲述者的女性视角和理性立场。
在这里强调女性视角是不是有将母亲性别虚无化的嫌疑呢?没有。不错,母亲是女性,也有女性情嫉情妒的表现,甚至还相当的激烈,但在某种意义,基本上出于本能。鲁迅先生曾经讲过,母性是天然的,妻性是后天形成的。意思是两性相悦是需要后天学习的,是需要有意而为之的。而女性视角也非凡女性则必然具备的天性,女性视角是超越女性本能,获得自觉性别意识和社会意识之后所形成的女性的自我认识、自我确证、自我肯定、自我调适和自我救赎的心理倾向和行为能力。如果这一理论假设成立,则故事中的母亲是不具有女性视角的。而“我”作为父亲婚外情的受害者,之所以能平和、从容讲述父亲的相好,作为母亲的女儿,正是因为“我”具备女性视角,摆脱本能的干扰,超越血缘和利害关系,才能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深陷于这桩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情感纠葛中的人(包括父亲、李采、母亲和我自己)和事。女性视角和理性立场是这个故事能够走出家庭,走到读者面前形成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小说提供新的价值判断的基础,能够向读者发出讨论邀请的特殊魅力所在。
在女性视角下,父亲这一辈子遇到的两位女性,一位是恨不相逢未嫁时的红颜知己;一个是于穷途末路在父母媒妁掺和下的合法妻子。一个是两情人,一世相好,爱而不得,却互相支撑,岁月有增爱而弥笃。这样有始有终的婚外情,看似平常却难得。一个是虽是明媒正娶,正大光明的妻子,也终致相濡以沫,但实际上是别人感情上的第三者,在别人的同情、自责和怜悯中讨生活的“多余人”。在“我”讲的故事中,对父亲的相好和自己母亲的情感投入是绝然不同的。这也是女性视角下超超血缘和超功利下的理性表现。
对父亲的相好,这位明显存在道德缺陷的女性,采取的是客观叙述加情理辩护的策略。父亲和他的相好,在他们情窦初开的时候,都曾犯过错误。年纪比父亲大三岁的李采,在媒人“能调到城里”的诱惑下,轻易就嫁给一个自己不相识,后来证明也是不合适的电焊工。实事求是地说,这多少带有骗婚的嫌疑的撮合,导致了李采婚姻生活的不幸,但既合国情,也无违乡俗,属于既合法,又合理。骗婚的媒人和丈夫都没有错,因为法律不追究,组织不过问,世人不理睬。这为她后来成为父亲的“相好”埋下了伏笔。李采如果不和小她三岁且未婚的男同事——我的父亲吕爽因相互爱慕而在“岩洞”屡行男女之事,也没有错。错就错在她无法压抑女性的觉醒,要奋不顾身地追求一段永生不缀的爱情。李采成为父亲的相好,开始也不过缘于孤男寡女青春荷尔蒙的作用,由心生爱慕而致发肤之亲,如果说有感情,也就是因爱美之心而致肌肤之亲产生的情愫。天下至爱,哪一个又不是始于斯,终于斯的呢?没有肌肤亲,哪得夫妇情呢。圣教之大禁男妇授受,其奥也在于此。李采与丈夫的不睦,“除了寒暑假”“基本守活寡”也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更哪堪基本上是一场骗婚。普天之下,“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男子不多情”。何况是“身高一米八五”,“皮肤光洁、四肢灵敏、动作矫健”,“打篮球不用跳就能把球投进篮筐”“帅呆了”的小伙子和“小嘴”“小得像个鹌鹑蛋”,“两个眼睛却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能歌善舞”的少妇呢?但假如父亲和他的“相好”之情仅止于此,也就和其他男女的逢场作戏,甚或奸夫淫妇,或者现在的什么“办公室恋情”和“网约炮战”之类没有什么两样了。父亲和他“相好”的故事虽说尚未达到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的程度,但也是现实生活中有此类经历的人们所望尘莫及的。他们在情感和人生面临考验时候的态度和行为都是让身边人有讲头的,有传播价值的,能够满足人们内心向往而又难以付诸行动的,是有些出格的。人们常将真、善、美并置,其实这里面并不存在天然的合理匹配,反倒是相左的时候多,真的不一定美、善,比如故事中的父亲和母亲的婚姻;而美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善的(合道德),比如父亲和李采的关系;但他们的相爱是真的。
但爱和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超功利和非实用性。如果夹杂着利害考量和功利计算就是对爱和美的不尊重。所以,小说故事所传递的不是艳色和香情,更不是宣淫诲盗,替婚外情张本,而是帮助洗涤现实生活中饱浸利害和功利之毒的心灵,让沉重的肉身变得轻灵起来,让人生还有些意义以自慰。在“我”的故事中,父亲的相好之所以美,也不仅止在于外表的美,而是在于其美的外表下所拥有的不屈的灵魂、善良的内心世界与平衡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智慧、能力与勇气。而父亲对相好永不中缀的迷恋,也绝非仅限于李采的美貌和肉身,而是对理想女性的恋慕和真正感情生活的追求。而“我”对母亲的“淡漠”和对李采的良好印象,是超越血缘之亲,向往美好女性和反思什么是幸福爱情生活的结果。
作者让“我”在故事的涉母叙述中采取了零度情感策略。正是因为这种零度情感策略,使母亲在女儿和读者这里获得了不同的情感反应。母亲作为生活的失败者,本身就惹人同情,女儿的冷漠反而会使母亲收获读者更多的同情。此所谓小说创作中之情感逆反原则,即同情一个人物就越让她受罪。这与母女之间关系的好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是作者的一种叙事策略,是小说作者处理情感的技术手段。但技术手段并非冷冰冰的工具要素,也不乏饱含温度的人文情怀。通过这种叙事策略,不难看出作者对处于感情生活失利女性的同情,同时对她们不自知、不觉悟的无奈和悲悯。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女性启蒙的问题深藏其间,相信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是不是还有如何建立婚姻的容错机制与文化,改良国人在男女关系问题上走极端的习惯思维,建立理解、宽容、友爱的两性文化的问题。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人在处理男女关系问题上,向来存在走极端的倾向,要么把她做成贞洁碑,要么做成性解放。什么样的男女之情才算是真正的爱情?法律专家、道德家及芸芸众生自然各有各的说法,作为小说家自然也有他的价值判断。不过,他并不直接评判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调动各种各样的叙事策略,创造一个个艺术的生活世界,呈现事件的“原貌”和“真相”,让读者来领略和领会。感谢《父亲的相好》在让读者收获不同审美愉悦的同时,也开启我们认真对待生活与爱情的片刻之思。
(何永生,博士,学者,现供职于湖北省武汉市教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