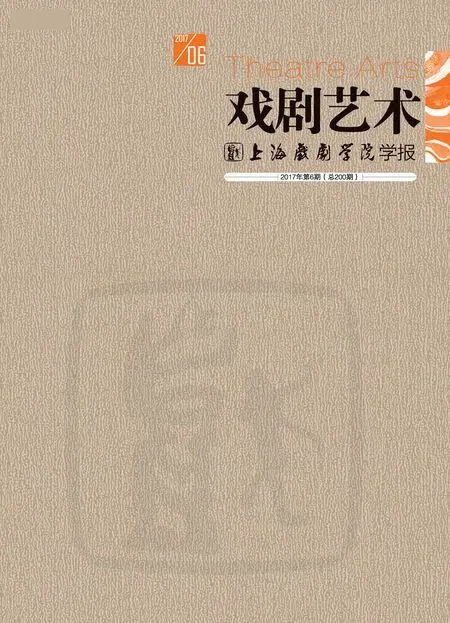梨园戏“表演科范”艺术特征探微
2017-02-12
泉腔梨园戏素有“宋元南戏活文物”之称,历经八百多年的朝代更替与时代变迁,奇迹般地在东南一隅福建泉州存活了下来,且完整地保存着大量弥足珍贵的宋元南戏剧目、成熟系统的科范程式和古乐雅韵的泉腔南音。侧重“四功”中的“做”和“念”是梨园戏有别于其他剧种的一大特色,因而,“上路”“下南”“小梨园”三流派的“做功”涵盖了“科”“介”“科母”“科步”“科范”和“特定科步组合”等一系列的科范范畴,汇集融合了隋、唐、宋、元、明、清等历代乐舞表演艺术之精要,形成了一脉相承、自成体系且兼具地域特色的“表演科范系统”,故而,其历史地位、艺术成就、文化价值与当代意义显然不言而喻。
在梨园戏的相关研究中,“表演科范”的研究仍属极为薄弱的环节,中国知网上从1954年至2017年这63年之间,有关梨园戏研究的期刊论文共计383篇,而针对科范研究的仅有7篇,且自2005年才陆续发表。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导演苏彦硕先生,堪称梨园戏表演科范研究的集大成者,然而,其研究成果笔者所见也仅有一本资料整理性质的专著《梨园戏·表演科范图解》(汇集九百一十多张科范图)和两篇论文《梨园戏基本表演程式——十八步科母分解》《梨园戏表演艺术中的“科”》。“表演科范”艺术特征这一基础性问题的探讨,苏先生曾有两处触碰但皆不尽然。他所归纳的科范表演的“三种特性”,即“灵活性”“重复表演”与“创作手法的多样性”,这些概念的表述既缺乏梨园戏自身剧种的个性特征,也缺乏学理性、逻辑性与体系性的理论界定和论证。
重要的是,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既是破解南戏之谜的突破口,也是开启“梨园戏表演科范体系”乃至“中国戏曲舞蹈体系”研究的一个奠基性问题。统而观之,梨园戏“表演科范”艺术特征的界定可从多个维度重新审视:一、从子集与母集的从属关系来考察,由“梨园戏表演科范艺术特征”推及“戏曲舞蹈艺术特征”乃至“戏曲艺术特征”三级关系进行纵深考量;二、从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进行辨析考察;三、从形式与本质、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思维逻辑进行系统考察。是故,我们将在多维审视、辩证统一中展开系列探究,并以“里三层外三层”的逻辑结构,诠释和论证梨园戏“表演科范”形式上显著的五大外部特征和本质上深层的五大内部特征。
一、梨园戏“表演科范”显著的外部艺术特征
梨园戏“表演科范”艺术特征的确立与其悠远的历史渊源、特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舞台场域、婉约的古乐南音和各色人物行当等诸因素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故而我们先来讨论其直观的、形式上的、形而下的、显著的五大外部艺术特征。
1.端方四正,妙手为势
梨园戏“表演科范”兼备了戏曲形神兼备、情景交融、悲喜交加、美丑相间、且歌且舞的艺术精髓,整体上颇有宋元古南戏之传统法度,古朴、规范、细腻而典雅。梨园戏属宫廷或贵族家养的戏班,是南宋大批宗室迁居泉州所带来的家班,因而,其表演科范已臻至极为成熟的艺术水平,形成一整套代代相承、高度规范化的科范系统和训练方法。
“端方四正”,意在演员训练时,手势有手法、科步有步法、身段有身法、传神有眼法,掌握了这些基本法度方能在具体科范表演中灵活运用。梨园戏的科范训练极为严格规范,一招一式都有特定的法度,我们从传诵至今的“戏谚”可见一斑:如“举手到目眉,分手到肚脐,拱手到下颏,毒错到腹脐”(苏彦硕等校订 8)、“指手对鼻,偏触对耳,提手对乳”(苏彦硕等校订 8),严格规定了各种手势在高、中、底三度空间中特定的位置和分寸,以达举止端正、身姿威仪。又如“眼随手动”,“白完科也完”,将动作的线条和动作之间的连接规范化,每科做完须放手还原再接下一科,科与科之间脉络相连,构成难以分割的流畅的线条。再如旦站立须“糕人身”,生走场要“墓牌身”,手要“三节手”,眼要“四顾眼”等,从体态眼神上规范化,无论静态或动态皆须符合角色的规范,站立时旦角须保持S型的曲线美,而生角须保持T型的阳刚美。因此,在严格规范的法度中,立规矩以成方圆,有限制以守风格,从而“正”其形以练其心,故能八百年一脉相承而不改其风。
“妙手为势”,既说明其手姿表演之神妙,也体现其“以手为势”的舞动方式。梨园戏的手姿之丰富堪称“神妙之手”。表演科范中生、旦、净的手姿共有四十式,占手姿、眼姿、身姿与步姿比重之最。在“十八步科母”中有九项属手姿动作,总计六十三式中手姿就有三十九式,足见其手姿数量与形态之多。由于梨园戏生、旦上装的袖口都极短,只有盈尺的水袖,故将双手自然袒露,从而在表演上创造了各种奇妙的手姿,如“尊佛手”“玄坛手”“上帝公手”“贝壳手”“姜母手”等,这些手姿又配合身段表演,构成千姿百态的舞蹈形态。所谓“步宜稳,手为势”,梨园戏身段表演遵循“以手为势”的舞动原则,由手起舞,上下随合,步态从容,配以眼神,指顾相应,五法谐和。
2.娘形娴体,七色行当
“娘形娴体”是指梨园戏科范表演中人物形象的高度典型化,演员在舞台上每个科介动作都要求“到角”“到位”,皆须符合人物的身份、年龄、性格和情绪的特点,以细致入微地刻画众生百态。“娘”出场须用“按心行科”,娴静端庄,文雅含蓄;“娴”(即丫鬟)出场则用“垂手行科”,活泼灵巧,轻盈跳跃。这些人物形象大多为类型化的行当,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都有各自独特的科范程式。各类的表演程式、表现手法和技巧运用无不带有角色行当的色彩,由此决定了梨园戏身韵“舞姿动作服从于人物形象”的基本形态特征。
梨园戏的角色行当,沿袭早期南戏《张协状元》角色分工的体制,由“生、旦、净、末、丑、贴、外”七色组成,戏班也因此得名“七子班”(小梨园)、“七角围”(大梨园)。这种传统南戏的角色建制,也是人物身份及其性格特征的典型分类,它运用造型艺术高度概括的手法,雕塑七种层次分明、个性鲜活的人间相。梨园戏科范中生、旦称为“幼角”,其余统称“粗角”,其表演体制以生、旦为主,脚本还有生、旦行专用的剧本《生首簿》《旦簿》。表演科范在完成“十八步科母”的基础训练之后,便按行当分类继续深造。师傅严格遵循“以戏教戏”的方式,依据古剧本和乐曲曲谱,各角色行当亦步亦趋、口传心授,将整套表演程式一丝不苟地传承下来,在严谨的师承中原汁原味地保存古南戏原始的演出风貌。
3.南鼓主帅,一曲一科
南鼓主帅,科曲相依,雅韵缭绕,张弛有度,展现了梨园戏身段表演高度的韵律化特征。梨园戏的鼓,即南鼓,又称“压脚鼓”,被誉为“万军主帅”。司鼓者须掌握全剧的科、白、唱,运用鼓点的轻重疾徐、音色的千变万化,来指挥乐队的起止、强弱与快慢,来配合演员的各种科范表演,以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形象、推动剧情发展。各行当的科范表演须配于不同的“锣鼓经”“鼓关”,譬如特殊表演动作,以“鸡啄栗”配合老公行、跛足行、上楼、过桥、落山、七步颠;以“假煞鼓”配合跑马、磨墨、加冠跳、忐忑;以“满山闹”配合加令跳等。再如各行当方面,旦角常用“小邦鼓”“假煞鼓”“满山闹”;生角常用“大邦鼓”“鸡啄栗”“擂鼓”;丑角则常用“马锣鼓”配合。(王爱群 373)各种锣鼓关再与具体剧情相结合,有机地糅合、裁接、创造和伸缩变化。
梨园戏唱腔基本节奏型有两种,即“切分音多坐拍多”与“切分音多坐拍少”。“坐拍”即上小节最后一拍的音连接到下一小节第一拍。切分音多坐拍多就会形成强弱拍倒置,本是四拍子节奏却有种三拍子的感觉,节奏速度缓慢、圆润流畅且从容典雅。梨园戏唱腔的音程起伏不大,四度以上的跳进不多,旋律进行一般都是大小三度或四度的回旋。(王爱群 370)这种声腔特点与动作配合时,自然给人以婉转、纡徐、圆润、典雅、优美而恬静的感觉。演员要把握此特点,须将物理节奏转化为内在的心理节奏,用心理节奏控制身体节奏,产生一种气韵生动“心灵律动”的感觉。故而,运用节奏韵律这一纽带,将“手、眼、身、步”各要素串缀、组织起来,形成善于表达喜、怒、哀、乐、爱、恨、欲等各种感情的动态语言。
4.砌末行头,尚文轻武
在舞台表演技艺上,梨园戏科范善于将剧中人物自身的服饰道具转化为传情达意的艺术语言,在特殊的小戏棚上形成高度特技化和尚文轻武的独特舞风。中国传统舞蹈素来善用道具,常以衣帽服饰点缀舞容,在《礼记·文王世子》中早有“不舞不授器”的记载。梨园戏科范表演秉承这一传统风习,艺人们从剧中人物角色出发,将身上穿的、手里拿的、腰里系的以及背上扎的,周遭一切砌末、行头和大小道具,经潜心揣摩变化为传神的舞具,为科范程式积累了珍贵丰厚的艺术资源。
梨园戏用于表演的“砌末”(即“随身道具”)有五类,包括兵器刑具类、请神供用类、生活用具类以及书信类和旗帜类。(吴捷秋 387)依据这些随身道具,艺人们创造了“扇科”三十三式、“伞科”四十二式、“马鞭科”三十一式、“棍棒科”八式、“舞旗科”九式等种类繁多、姿态万千、巧技超群的表演程式。梨园戏服饰称为“行头”,它对身体动作形式有决定性影响。梨园戏三个流派的行头都极为精简,服饰以红、黑二色为多,幞头、纱帽、盔头皆属于宋制,一直保持其古朴、简易、传统的舞台造型。梨园戏赋予“行头”以年龄、身份、权力、性格和人格的象征,它在辅助身段表演、烘托人物情绪和暗示典型环境等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
“尚文轻武”“武戏文唱”之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梨园戏小戏棚的演出形式息息相关。梨园戏的演出舞台称为“棚”(草台),是一种大小基本固定、临时搭起的小戏台。一般由城乡请戏的主人提供,卸下三、五块门板,平架在两块高脚凳上(泉州俗称“大水椅”,亦名“登椅”),成为一个高约一米二,面积宽二米深三米的戏棚。这种演出形式可追溯至南宋绍熙嘉定年间(公元1190—1218年),“过戏搭棚,无戏搬收”这种临时搭棚演戏的风俗在漳泉一带延续了七八百年之久。(林庆熙、郑清水、刘湘如编注 21)在这狭窄而简陋的演出空间里,严重制约了科步动作的大小幅度、舞台调度和技术技巧的发挥,自然形成了细腻温婉的舞风和“文戏”为主的戏风。譬如“返头轧角科”即典型源自小戏棚演出形式的一种台角转身的程式,在一丈见方的戏棚上,凡下场、过场或在大角、小角、三弦角、踏口等表演区的表演都得用此程式。
5.兼收并蓄,多元融合
梨园戏地处千年古城泉州,泉州被誉为“中世纪世界第一大港”“世界宗教博物馆”和“东亚文化之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悠久的对外文化交流史、奇特的多元文化大观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故而,在多元文化交融中自然广泛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梨园戏表演科范的体系。宋朝的泉州已是一个繁荣开放的港口,教坊与民间戏班沿袭唐时“梨园乐”之称,通称为“梨园”,活跃于“刺桐城”。在八百多年历代文化孕育发展的过程中,梨园戏“表演科范”汇集、吸收了东晋士族歌舞、汉代“相和歌”、晋代“清商乐”、隋代“康衢戏”、唐代“参军戏”、五代歌舞与宋代百戏杂剧等历代乐舞表演艺术,(吴捷秋 74)还从地方民间舞蹈、武艺拳术、壁画雕塑、佛舞道乐乃至广泛的生活素材中吸收融合了有益的滋养,从而积累了丰富多姿的舞蹈语汇,形成了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经典舞蹈体系。是故,“兼收并蓄,多元融合”成为梨园戏科范表演突出的艺术特征。
从梨园戏科步的来源及其命名来看,这一艺术特征显而易见。如旦角的基本手姿“螃蟹手”“姜母手”“尊佛手”等皆源自敦煌壁画的手姿形态;如生角的坐姿“脚踏金狮”“十八罗汉科”等皆来自佛教塑像;又如“科母”中的“垂手行科”以及“大垂手”“小垂手”其源甚古,自六朝以至宋元皆广兴垂手舞;又如“相公摩”“嘉礼落线”“三节手”等皆从提线傀儡的表演转化而来;再如“牛车水”“鹤展翼”“猴照镜”“虎仔探井”“金鸡独立”等皆源自对生物情状的模拟;而“拱手”“毒错”“偏触”等则是由日常生活动作转化而来。(苏彦硕等校订 5)梨园戏科范熔历代乐舞元素、姊妹艺术、民俗民情乃至宗教哲学为一炉而自成体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戏曲从历代古典舞、民间舞中吸取滋养,使得不少古代传统舞蹈在戏曲中被保存了下来,而后艺术家又从戏曲中吸收、恢复、创新成当代的中国新古典舞,于是,它们在互滋互润中交错发展、春晖再现、常演常新。
二、梨园戏“表演科范”深层的内在艺术特征
梨园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秉持固守传统与传承经典的原则,在历代永续“不变”的传承中保存了宋元南戏的历史基因,让我们有机会破解南戏之谜,故而,我们继续探讨其深层的、本质上的、形而上的五大内在艺术特征。
1.象形取意,仿生超越
从发生学的视角考察,象形取意、自我完善的创造力和仿生机制下超越自我的精神自由之追求,是梨园戏科范深层的本质特征,而其渊源在于中国自六千年前就自成体系的“天人合一”之哲学观和由此派生且影响深远的“师法造化”之美学观。武术名家刘峻骧先生曾提出,“本能机制、仿生机制、超越机制”是武术、舞蹈、杂技、生命科学气功等东方人体文化的三大发生机制。(刘峻骧119)“天人合一,师法造化”的哲思,使得先民们自古就有一种超脱肉体凡胎、与宇宙相通的追求。他们仰观天宇,体悟永恒不息的日精月华;他们俯视大地上的鸟兽虫迹,启迪心智,汲取无穷的灵感;他们面对神秘莫测的海洋,对至善和真美有着深沉的向往和憧憬,在模拟万物、象形取意的方法中不断积累创造。
“象形”即以人体动作模拟客观事物的各种形象,贵在模拟其形,摄取其神;“取意”指象形动作中所含蕴的意味,以探寻自然物象的深层底蕴。梨园戏科范中举凡各种手姿,如生角的玄坛手、三香手、刀手、遮阳手,旦角的观音手、鹰爪手、螃蟹手、凤尾手、香芋手,净角的许远手、康王手、铁沙手、末指手等;再如各种身姿,生角的脚踏金狮、哪吒踏轮,旦角的半月沉江等;乃至各种表演程式,如猴照镜科、猴担水科、鹤展翅科、虎仔探井科、十八罗汉科等。这些皆是历代艺人观察日月星辰、鸟兽鱼虫、高山流水与松柏菊兰时,赋山水以性情,给万物以品格,或宛若沙洲之惊鸿,或犹如迎风之杨柳,以象形取意之法移植于人体而形成的。
东方“仿生机制”下的象形取意与“超越机制”密切关联,是一种物我相通、道技并重、蕴涵深刻哲理的民族特征。梨园戏“十八步科母”中的“拱手科”乃是“仿生超越观”最逼真的体现。拱手如启天,高度与额齐,表示对上辈的尊敬或基本的礼仪。“拱手科”右手为“鹰爪手”,左手为“螃蟹手”,暗喻上天如“雄鹰”,在无垠的穹窿中自由翱翔;下水如“螃蟹”,在神秘的海洋里自在神游,在二者之间的“转化”中,人超越了陆行动物之限,入水乘云以达闲云野鹤之逍遥境界。正如《庄子·内篇》的“鲲鹏之喻”,它以超越时空的鲲鹏变化顺应天地阴阳的反复转化,自得其乐顺应自然之道,故能忘却大小高下之异,齐物去累而安闲自在。
2.圆润古雅,提神明理
梨园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圆润舒畅,细腻典雅”是其科范表演一条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也是对几千年来中华传统乐舞“子午阴阳,求圆占中”审美追求的继承与发扬。这种“划圆的艺术”十分讲究身体舞动中的阴阳和谐与对立统一,手臂的阴与阳、脚步的虚与实、力度的刚与柔、速度的快与慢、动作的开与合、线条的断与连、气息的提与沉,整个过程皆在对立中求统一;再加上运动时“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欲进先退,欲扬先抑,欲冲先避”的反向动势,使得舞蹈动作如行云流水般浑圆自然。梨园戏科范亦将此种珠圆玉润的“圆韵”贯穿于身体的造型姿态、科步连接、队形变化以及场面调度等每一个细微环节之中,使之丝丝入扣、曼妙婉转、流畅和谐。
“提神明理”是小梨园名师陈家荐先生对梨园戏表演艺术特征的高度概括。“提神”即演员在戏棚上应清晰而警惕,将一曲一科表演得圆润精道、形神兼备;“明理”即明了“戏中之理”,入情入理地把戏演好演活、演出个性。如是既要准确把握人物的外部动态特征,更要深入体察不同角色之间心理和神韵的微妙变化,方能塑造出一个个性格迥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譬如“二度梅”得主曾静萍在演绎梨园戏《大闷》时,舞台上除了一条凳一方桌、一面镜一支烛以外,全靠身段科步和唱腔来完成。在微弱烛光下,五娘纤秀的小脚迈出懒散的风情,透出失眠后性感的憔悴;十指微弱地拨动在参差音律间辗转,分明是小心肝儿碎成一片片;缓急有序抖动的纤指,重复着蚊帐的垂落又撩起、合拢又掀开,勾勒出闺床之轮廓。三进三出的跪床、卧床、脱鞋、穿鞋,折射出女人一夜辗转反侧的思怨。在五十分钟之久的旦角独角戏中,人物的内心和外形被完美地统一起来,既呈现了规整的体态又能看到体态中的脉络,每一个得体的细节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位思念中的女人在一个不寻常的夜晚,亦相思亦怀春、亦希望亦担忧、亦幽怨亦憧憬的万般风情。
3.科科表意,亦舞亦戏
梨园戏科范的程式动作大量源自对现实生活动作的模拟、升华与美的再现,俗话说“老戏旦跌倒都是科”,真可谓“处处可舞,无动不舞”。生活动作舞蹈化之后所形成的这些科范程式,又蕴涵着原初生活动作的含义,一连串富有表现力、感染力、表意性的科范程式推动着剧情的发展,使观赏者觉得它们是“戏”又是“舞”,故而,“科科表意,亦舞亦戏”成为其根本的艺术特征。
举凡梨园戏的整冠科、整袖科、提靴科、招手科、挥手科、虚坐科、夜行科、三跪九叩科、发怒科、盘须科、窃听科、开弓科、磨刀科、跳门科等等,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它们的“原型”,并且每一科又各表其意。梨园戏艺人们正是通过将生活动作“四化”(即舞蹈化、规范化、程式化和戏剧化)和“三法”(即夸张、变形与虚拟的表现手法),从而创造了一整套表意性的舞戏相依的科范程式系统。科范动作的“表意性”特征实际上蕴涵着两层含义:一则“情动于中而行于外”,演员须为角色内心的思想情感找到相应的外部动作来表达,将看不见的内心世界转化为看得见的肢体语汇;二则“形似而意真以通心”,演员的身体表达须赋予外部动作一定的意味,通过肢体语言准确生动的表达方能与观众产生共鸣。戏曲舞台上对空间、时间的处理,全靠演员的科范表演来完成,而那一整套的程式和动作技巧,皆为塑造特定环境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梨园戏科范表演大量运用了表意性动作,它们既能交代故事情节、推进剧情发展,又能刻画人物内心活动、抒发思想感情,因而往往是叙事与抒情浑然一体,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叙事,相辅相成,难于界分。例如梨园戏《陈三·留伞》中陈三与益春的经典双人舞,陈三在对姻缘极度绝望之后坚决要离去,而益春深知难言之情,故苦苦挽留,剧情凭借着一把代表差旅的“伞”,在“急去”与“苦留”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持,把戏剧冲突推向一个大转折的高潮。双人舞在一系列的踢伞、挽伞、握伞、拾伞、踩伞、挟伞、夺伞中,配以急促多变、顿挫有力的鼓点,渲染紧张热烈的气氛,一环紧扣一环地将“急去”与“苦留”的对比情绪层层皴染。(吴捷秋 379)这段历时三分钟的精彩舞段,既是角色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又能推动戏剧情节向前发展,叙事与抒情并行,以舞带戏、舞戏相依。不过,梨园戏中专事抒情性的舞段其实并不多,更多的是叙事性的舞段,因为作为“唱、念、做、打”高度综合的传统艺术,感情的抒发还有赖于大段唱腔来完成,以舞抒情仅作为辅助性的表现手段,故而往往是叙事为主,抒情为辅。显然,这与中国传统古典舞和民间舞“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特点不同。
4.三合重复,绛树两歌
“三合”一词源自古南戏,在梨园戏与傀儡戏的旧抄簿中随处可见,如“三合泼”“三合看”“三合末净”“三合拔佐科”等。“三”在古语中含有“重复”的意思,在梨园戏《生首簿》《旦簿》中,“三合”是一种古老的舞台表演提示,即提示此处需重复表演,亦即同一动作或台词反复三次,譬如“三合看”,即重复三次举手看的表演。(苏彦硕等校订 3)戏曲理论家刘念兹先生曾表示,“三合”一词的解释也解开了南戏的一个谜,岂知此谜恰是梨园戏表演科范的一个典型特征——“三合重复”。
“重复”这一概念范畴实际上蕴含着多层深意,是传统戏曲艺术不容忽视的民族特色。其一,重复是科范表演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即通过程式动作或舞段的重复运用来刻画人物、描述情节、深化主题以及增强艺术感染力。譬如“下南”宋元古戏《郑元和》一剧中的“来兴,安排笼杠马匹,随公子上京赴试。三合看枰下”,即采用重复三次看枰动作紧随下场的手法,来展露此时此刻郑元和急迫的心情。再如“上路”宋元古戏《尹行义》一剧的第八出《投井》,抄本中注着“三合拔佐科”,这里就有大段“拔佐科”舞段的重复表演,以渲染惊险紧张的气氛。
其二,重复也是科范表演中常见的一种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的基本法则,即重复中有变化、规范中有创新。重复不变的是高度规范化和规律性的科范程式,而其具体运用时又是千变万化,十分自由。不同人物角色重复表演相同的程式动作,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和情感变化的迥异,将会产生各种微妙差异的别致风格。最典型的是“十八步科母”(行内称为“父母步”),它们是各行当共同的基本科步,也是演员的基本功,在不计其数的重复运用中,根据剧目和人物的不同,还有一个再创造的问题。譬如其中的“相公摩科”,重复同一程式可以表现高中状元、功名成就等极度欢快的情绪,也可表达恨杀奸臣、冤家、仇敌等极端愤慨的心情;又如“七步颠科”重复相同的四慢三快、七步一颠脚的动作,可表现神情恍惚、萎靡不振,亦可表现遭遇不幸、脚酸手软,还可表现跋山涉水、千辛万苦等情状。
其三,重复在科范表演中还代表着在“重复中洞见共性,重复中生长个性”的哲理奥妙以及“个性—共性—个性”周而复始的艺术规律。戏曲演员对科范程式日复一日的重复训练表演,如同习武者对太极拳招式的千锤百炼、书法家对汉字结构的日日书写,在长期不间断的重复训练和研习中常习常新。在重复中洞见科范表演的共性,在重复中生长科范表演的个性,还在重复中逐渐体悟从个性到共性、从共性再到个性的循环往复的艺术规律,遂而深深着迷于此取之不尽的曲山戏海。譬如小梨园特有的“按心行科”,由泉州傀儡戏提线木偶的身姿,经过某些艺术家的借鉴和转化,成为梨园戏生、旦出场时通用的舞姿,此即由个别到一般、从个性到共性的艺术规律。进而,人们为表现不同人物的身份、性格和威仪,同为旦角的“按心行科”,《高文举》中孤身跋涉千里寻夫的王玉真、《孟姜女》中坚韧前行为夫送寒衣的孟姜女,以及《陈三五娘》中娴静端庄的名门闺秀黄五娘,各自的身姿表演则各具风格,此为由一般到个别、从共性再到个性的艺术规律。于是,在这样循环往复的艺术发展过程中,既尊重传统程式的共性,又善于运用程式塑造个性鲜明的形象。
“绛树两歌”的典故出自唐人冯贽《记事珠》,记述了魏武时能歌善舞、容貌娇美的宫女绛树,歌唱时能一声两曲且一字不乱、神乎技矣。这里借此暗喻梨园戏科范表演一笔多用、一字多意、一科多表和多层深意的玄妙技法;同时,它也暗合了科范表演中身段之态与唱腔之情相依相衬而达情态相生、象外有象之艺术妙境,是故,以此来形容科范表演的那种微妙玄奥难以言表的艺术特征。
5.伦常善美,性灵净化
中华民族千古重孝,五伦五常是国学的根本,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戏曲行将唐明皇奉为“祖师爷”,唐明皇除设立梨园、亲操鼓板、能歌善舞之外,更重要的功业乃是注释《孝经》,倡导“以孝治天下”。是故,伦常孝道、向善崇美与高台教化成为传统戏曲艺术特有的国学价值。戏曲成为中华国学原典“六经”(或曰“六艺”)大众阐释的文化载体,它通过历代龙争虎斗的故事展现并培育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性德,在唱、做、念、打中为博大精深、奥义难表的国学做了形象生动的诠释,呼唤着社会民众求真、向善、崇美的信仰,这正是华夏民族精魂永续之根本。
在各艺术门类中,戏曲与社会人事的关系最为密切。绘画、音乐通过颜色线条和声音高低缓急的变化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而戏曲的产生源于人类的文化、历史的高度发达,它与社会人事和世人感情息息相关。关注社会人事,塑造各类人的品貌,书写众生百态,以美善人生感人而化人,成为戏曲之核。因而,这种以“人”为核的传统艺术,自然关乎人的性灵之净化与道德之进化。鲜明典型的形象无疑可以在观众心里产生善恶的道德评价和内省自励的机能,剧中之人善者从之、恶者弃之、智者向之、贪者避之而痴者笑之。戏曲微世界,体验大人生,品味戏中百态人生,与之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对生活有了判断、认识和深刻的理解,从中深受启发和教育。
如果说艺术中戏曲与人事关系最密切,那么戏曲中身段科范则与人体身心关系最密切、最直接。人的外貌形象、心理描写和品格的塑造皆免不了有动作行为,所以戏剧的名称“Drama”在希腊的原意即“动作”的意思。剧中人物经过一连串内外交互、精雕细刻的科范动作表演,情感的表达越发真切感人,品格的塑造渐渐鲜明生动。这个过程也是演员和观众道德熏陶与性灵净化的过程:一者演员在长期真善美的艺术陶冶中,为人做艺皆经历了一个勤习内省的自励过程;二者观众在剧中所塑造的各种忠孝节义的人物的影响下不断吸取教训而深受教育,这正是科范表演又一深层的艺术特征。人向善尚美之本性,犹如“葵之向日”“石针之朝南”一般,在艺术这面镜子里,人类对自身的写真愕然而起敬,经历一番宣泄、自省、净化与觉悟的陶炼,在灵魂栖息处源源不绝地滋生着人类温润的美德。
结 语
梨园戏“表演科范”从孕育、滋长到成熟经历了八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艺术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多姿的舞蹈语汇,汇集了古往今来诸多东方人体文化的精髓,形成了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舞蹈体系,也形成了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艺术特征,成为中国乐舞发展史上珍贵的“活态传承”的奇葩。其艺术特征的探微是一个永续性的问题,并非一蹴而就。上列论证的外部和内部的这十大艺术特征,环环相扣,相互制约,维系着梨园戏艺术特色和剧种风格的延续性,也为“梨园戏表演科范体系”以及“中国戏曲舞蹈体系”研究奠定了夯实的理论基础,还为中国戏曲艺术特征的再认识提供了一些新的启发。数个世纪以来中国戏曲理论界关于戏曲艺术基本特征的讨论,提出了“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三性说的理论,以及“歌舞说”“写意说”“意象说”“剧诗说”“自由时空说”等不同的论说。这些特性范畴的提出诚然有其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但对于博大精深的民族戏曲艺术的诠释却未尽然,其内在深层的本质上的艺术特征仍尤为引人深思。
苏彦硕等校订,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梨园戏·表演科范图解: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第八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
[Su,Yanshuo,et al.,ed.“Pictures of Performing Forms of Liyuan Opera.” Traditional Quanzhou Xiqu Series,vol.8.Ed.Quzhou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Local Xiqu.Beijing:China Theatre Press,2000.]
王爱群:《南戏论集:泉腔论》,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Wang,Aiqun.Collected Criticism of Nanxi:On Quan Qiang.Beijing:China Theatre Press,1988.]
吴捷秋:《梨园戏艺术史论: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年。
[Wu,Jieqiu.On the Artistic History of Liyuan Opera.Ed.Quanzhou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Local Xiqu.Beijing:China Theatre Press,2000.]
林庆熙、郑清水、刘湘如编注:《福建戏史录: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Lin Qingxi,Zheng Qingshui,and Liu Xiangru,ed.Theatre History of Fujian Province.Ed.Fujian Provincial Research Office of Xiqu.Fuzhou: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3.]
刘峻骧:《东方人体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Liu,Junxiang.Oriental Physical Culture.Shanghai: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1996.]
曾静萍:《关于梨园戏〈大闷〉》,载《福建艺术》,2017年第1期。
[Zeng,Jingping.“About Liyuan Opera Da Men.” Fujian Arts 1(2017):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