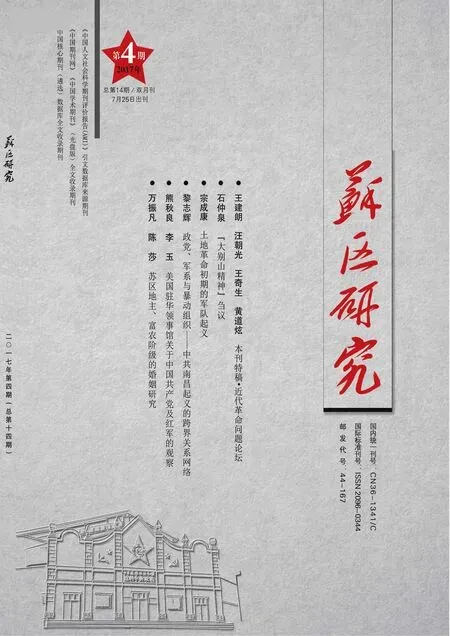政党、军系与暴动组织
——中共南昌起义的跨界关系网络
2017-01-29黎志辉
黎志辉
政党、军系与暴动组织
——中共南昌起义的跨界关系网络
黎志辉
国民革命军北伐引发南方各省,尤其是两广、云贵、四川等省的地方军系跨出原先的防区或地盘,汇聚和交错于湘鄂赣等省区域。借助党部、学校等机构以及军中党代表、政工制度等路径,国共两党在加强对地方和军队进行渗透与控制的过程中,迅速扩散了两党在北伐过境区域的党政军关系网络。与此同时,军人们的地域观念、部队情感以及军校认同感等因素充斥其间,成为其相互联络或结成团体的重要关系纽带。1927年武汉国民党中央即将“分共”之际,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以“东征讨蒋”为名驻守江西九江、南昌沿线地带,中共精英人物也随之聚拢于此。后者正是在上述复杂的关系网络背景下,通过调遣和运用渗透其中的关系资源,以此推动“党”“军”之间结成南昌暴动的组织架构,并获得暴动前期的某种政治掩护。但另一方面,对现有关系资源、尤其是军系力量的过度依赖,也使中共难以完全贯彻其政治纲领。南昌暴动的失败经验,启示中共此后确立并贯彻工农革命的路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共与军队的关系由此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型态。
中国共产党;南昌暴动;军系;关系网络
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策动的武装暴动,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八一起义”——一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和独立创建人民军队历史开端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共党内对这次暴动的各种言说,重点在于叙述和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于军队的组织领导,超出此视野之外、与此不大吻合的史实则极易被忽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内部骤然面临权力调整和中枢更替的艰难过程,正处于旧的权威顿失而新的权威尚待树立的危机状态。在此情势之下,中共对国民政府治下军队的联络和动员颇具个人色彩,而不宜单纯用中共日后总结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来加以理解和阐释。中共党内的领导人,一面凭借党内的权威和制度调遣自己可能支配或影响的军队力量,一面自然而然地借助各种非制度化的关系网络和因势利导的利益许诺,对超出其组织控制之外的军队力量进行说服与整合,由此促成组织安排、非组织行为和军队倾向或惯习之间的多元耦合。而中共南昌暴动之所以能够达成的关键原因,即是在北伐军过境后的湖北武汉、江西九江与南昌等沿线区域,存在着中共有可能广泛加以运用的关系网络和军队资源。
放宽视野来看,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之间以及它们和各式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远比国共对抗这种历史叙事框架表现得更为错综复杂。一方面,国共两党的关系处于正在断裂却又并未断绝的状态,不但中共在国民党内仍有为数不少的党员潜伏其中,甚或公开活动,而且中共对国民党也还抱有政治上的幻想和倚赖,这种态度实则反映当时莫斯科方面不愿舍弃昔日国共合作成果的忍让立场对中共的影响,并与国民党内少数“左派”对“清党”“反共”所持的保留态度有所呼应。另一方面,在国共两党均对国民政府治下多数军队缺乏有效的组织性或制度性控制能力的局势下,各支主要军队的首领实际上延续民初以来军队坐大的历史惯势,存在着相当强固的自主行动能力、政治雄心和扩张冲动。在其眼中毫不惊奇地,政党也经常能够成为被利用和控制的对象,由此使国共两党和军队的关系展现出合纵连横、相互为谋的复杂面相。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京蒋介石、武汉唐生智两大军系竞逐格局中,那些可能受到排挤或打击,同时又与共产党存在某些或强或弱的关系的军系势力,在危机面前具备与中共联合暴动的极大可能性,这就为中共策划和举行南昌暴动提供了各种若隐若现的政治机会。
本文主要从国共两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层面,论述南昌起义的领导群体是如何在军系竞逐和党军联盟的政局演变中被组织起来的,以及这种政党——军系的组合关系对于中共南昌暴动前后过程的影响,以期更为真实或准确地揭示南昌暴动的组织过程与机制。
一、政党和军系的关系演化
从概念上来说,在近代中国以国家权力势微为典型特征的军事变迁中,军系比军队更准确地反映了军人组织的时代特征。“系”既表示“源流”,又表示由联属关系所结成的“派别”。地域认同是在近代中国军队中形成“源流”和树立“派别”最重要的因素。早期的湘军、淮军,民初的滇军、桂军以及后起的粤军,均以地域而得名。不容忽视的是,清末以降,特殊类型的学校——新式军校,对军系的形成和组合产生过很大影响,并由此而使文武之间和区域之间的跨界关系流动变得平常。除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中国北方的保定军校、南方的云南讲武堂这两所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军校外,各省还有许多地方性军校,助长着各地军系的成长与更替。近代新兴的国共两党,最初主要是依托军校而对军队产生影响,进而干预军队内部的分化组合。军校生成为那个时代相对稀缺的人才资源——既能获军队重用,又能受政党重视。民国肇建后,南方各省军界中遍布受到国民党(或其前身同盟会)影响的军校生,只是由于民国肇建后十年间国民党在全国政权角逐中处于失势地位,这些由军校生成长起来的军人们与国民党的关系亲疏不一,并且时有变化。他们在南方各省崛起为军系首领或中级军官的过程,仍多具有扎根地方的浓厚特征,军校背景通常只有与地缘因素交相配合,或在横向联络和跨界流动的时候,才能发挥更大作用。比军校、地域这两大因素更能影响他们今后政治命运的因素,是南北之间的政治与军事冲突。大体而言,由于他们中一些人的政治命运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关联性,双方对国家变革的政治理念也更为接近,因而在“反袁”“护法”和孙中山数次“北伐”等军事活动中,通常能够发现他们的名字或身影。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上述带有攻伐“北方”的政治意味的军事行动,为他们中的一些军人的崛起持续创造了政治机会。
1924年黄埔军校在广东的创设,确具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国民党不再只是通过联络亲国民党的各派军系首领来达致军事目标,而是试图通过大规模地培养军官,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对于中共而言,则意味着她可以继承国民党的传统,在军校中发展组织并进而影响和控制军队。黄埔军校为1926年后的北伐军培养了许多中下级军官,不过与之相比,那些在“反袁”“护法”或孙中山北伐时期就已崭露头角的南方军系首领和部分中级军官,在北伐中的崛起势头更为突出。换言之,北伐不仅是国共两党越出广东、突破危局的战略安排,同时也为那些居于失利地位或偏远区域的南方军系首领带来挺进中心地带的发展良机。在北伐战争的核心战区——两湖地区,唐生智的新湘军、李宗仁的新桂军以及粤滇川黔等军风云际会,汇聚一时。除蒋介石直属“党军”以外的各地方性军队的穿插流动,其上固有接受国民政府或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调遣的一面,另一方面,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联络也变得频繁和密切。值此之际,军校背景在北伐将官——他们多数是地方性部队的重要将领——跨出所属部队的界限进行交往和联络时变得更为重要,以致成为某种集体认同的精神来源。
在以军校为载体的关系网络和集体认同中,保定军校显得最为重要。早在北伐前,李宗黄等人就在孙中山的推动下,于上海、广州等地成立了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陆军四校同学会”,并从中招募了许多人员到黄埔军校担任教官。*参见李宗黄:《返滇指导集》,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33页;王哲学等编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史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在粤军中,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的佼佼者最多,这期毕业的粤军名将李汉魂在其日记中写道:“北伐及抗日战争时的著名将领如顾祝同、张发奎、薛岳、邓演达、余汉谋、黄琪翔、缪培南、吴奇伟、叶挺、叶肇、朱晖日、李扬敬、邓龙光、黄镇球、陈克华、陈公侠、上官云相等人,都是这期同学。”*朱振声编:《李汉魂将军日记(上)》第1册,香港联艺印刷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10页。不仅是广州,南方各省其实到处散布着“陆军四校”毕业生,他们在湖南、四川两省还形成了所谓的“保定系”或“保定派”,代表着新生代军系势力在本省的崛起。*参见龚浩口述、汪仲弘笔记:《我所知道的唐生智》,《传记文学》(台北)1986年第295期,第17页;张仲雷:《四川的军事学堂与川军派系的形成和演变》,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等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79年,第16-18页。尤其是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青睐的得意门生——保定一期毕业生唐生智,在蒋百里的支持下,由其同学、部下龚浩居间联络,借着父亲生日的名义宴请军校同学,“一致奉蒋百里先生为精神领袖,奉唐生智为实际领导人”,形成“保定大团结”“隐形结成力量”。*龚浩口述、汪仲弘笔记:《我所知道的唐生智》,《传记文学》(台北)1986年第295期,第17页。1927年唐生智所部团长以上的军官共64人,其中出身保定军校者就达50多人,可见其“保定派”之名不虚。*叶惠芬:《唐生智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建立》,载简笙簧主编:《国史馆学术集刊》(台北)第2期,台北“国史馆”2002年版,第4页。北伐时期“无疑是四校联谊会最辉煌的时代”,“在这段时期,保定校友掌控了南北双方的军事权力,他们至少是校官,升级迅速。不少人上过广东陆军小学或武昌军官预校”,而与之相比,“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地位日渐下降”,“黄埔毕业生犹如雏鸡,同保定毕业生简直不能比”。*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
北伐军围攻武昌孤城时,唐生智部下龚浩正是借助同学关系,“设法与因病住在城内休养的保定同学聂世声与守军团长保定一期同学贺对廷联络”,并由唐生智、邓演达与其见面谈判,约定保障贺对廷生命安全、不缴械、升混成旅旅长等条件,最后才在其内应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攻进武昌城。*龚浩口述、汪仲弘笔记:《我所知道的唐生智》,《传记文学》(台北)1986年第295期,第18页。唐生智俨然以保定系领袖自居,并从保定同学的关系经营中受益良多,然而一旦同学关系妨碍其军事扩张或政治施展,仍会暴露其不留情面、行事操切的面相。他在湖南驱除赵恒惕后,为谋改编其他各师力量,就不顾与叶开鑫部下刘重威、张雄舆两人的保定同学之谊,利用召开军事会议之机将其扣押并加以杀害。北伐军攻下武昌后,唐生智又命人以设宴为名,伏兵枪杀另一保定同学——黔军首领、北伐军左翼总指挥袁祖铭及其属下第九军军长彭汉章,并收编其队伍,再次显示他对保定同学关系网的两面性运用。这种两面性虽然未必会威胁唐生智在所属湘军中的威望和地位,但至少不利于他对所属部队之外的保定军校出身的军系首领的充分整合。更值得注意的是,粤军陈铭枢、桂系白崇禧等保定军校前三期的毕业生,与唐生智尚多往来,然而保定军校后期毕业的学生及其外围的地方军校毕业的学生,例如张发奎和李宗仁,则明显对唐生智所主导的“保定派”活动不甚积极,由此显现保定军校或“四校同学会”在整合军系力量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换言之,对军系首领而言,在军校同学和政治立场或军系利益的关系序列中,后者通常高于前者,只有在两者未发生明显冲突或具有相互借力作用的情况下,军校同学的身份才易发生联络、包容乃至整合的关系功能。
国民党组织依托国民政府对其治下的军队进行制度化控制,初期远比以军校同学为弹性纽带的军系整合显得更为正式、有效和强大。通过向各军派遣党代表和政工人员,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制度上或名义上实现着对军队的统一领导,而中共则在实际上对多数军中党代表和政工人员具有支配力。这种制度在北伐过程中甚至成为其他军队是否归顺国民政府的标志。在总政治部任职的郭沫若发现:“凡是有来归附的军队,他们最先所请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员。所谓政治工作在当时的旧军阀们看来,就好像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样,是成为了革命军的必要的徽章。他们并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军和北军在组织上的重要的不同处便是在这种工作的有无。有了这种组织的南军打了胜仗,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使军队强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个时代的宠儿。”*郭沫若:《革命春秋》,海燕书店(上海)1949年版,第393页。
军队政工制度背后的革命理论、“党治”制度及其配套的话语和仪式,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并在广东省首先获得既隆重又日常的演练。蒋介石在当时广东的中年军人中,即属于成功的学习者之一。但对于北伐后两广地区之外的“旧军阀”而言,对这套制度、话语和仪式的学习和运用,短期内无疑会面临相当的考验性。在湖北较早归附北伐军的原北洋师长刘佐龙,当时年已五十多岁,在举行师代表大会这种仪式性的场合,就“颇以致开会词为难”,即使政工人员已代拟讲稿并授其记诵,他自己也事先悉心模拟演习,但临到发布演说时,仍只讲一句即“尽忘其词,窘立良久无续说”,显见尴尬至极。*黄宝实:《北伐时期的经历与见闻》,《传记文学》(台北)1968年第75期,第33页。保定军校高材生唐生智对新话语、新仪式的领会和表演,明显容易得多,也正因如此,他才有可能被苏俄顾问视为替代蒋介石的优先人选,苏俄顾问甚至一度想“利用保定派来反对蒋介石”。*《鲍罗廷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27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比唐更年轻、具有随营军校学历的贺龙,虽然不像唐那样在话语和仪式方面善于表现“左倾化”,但适应这种新的政治环境似乎并不费劲,他“开会讲话时也讲三民主义”,部队受训时还“每人发有一本书,书上有孙中山、陈独秀的讲话”。*张应祥口述:《我跟随贺龙的历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桑植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桑植文史资料》第1辑,1989年,第10页。
郭沫若所说的政治工作成为时代宠儿的日子很快就结束。到1927年6-7月间,随着国共合作破裂,多数军系以“反共”为名,驱除甚至杀戮政工人员。前述那位刘佐龙对其军中政工人员的捕杀,自然不在话下。就连一度“左倾化”的唐生智,也不再愿意支持共产党。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军中推行的“党治”制度,顿以军队中“反共”并清除政工人员而宣告失败。从其过程的演变来看,各军系对“党治”制度的反弹,先以反对工农运动而获得某种共鸣,继而则以“反共”而取得普遍性的成功。此时粤军张发奎部和由湘西发迹的贺龙部队,依然优容政工人员,这无疑使中共看到了潜在的机会。
二、军系与中共的合作
张发奎和贺龙同年(1896年生),其部队在孙中山时期,均参加过“反袁”“护法”“北伐”等战争。张发奎原隶属于邓铿率领的粤军第一师,系孙中山麾下的正统革命军,粤军名将大多出自该师。18岁时即由桑植高等小学的留日学生陈图南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贺龙,大致也可算是辛亥革命余脉,另一与其关系密切的重要人物——常澧镇守使王正雅,辛亥年间曾以领兵攻打荆州而轰动一时。*分别参见《贺龙生平大事年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页;苏姗:《关于贺龙出身及其他》,《传记文学》(台北)1995年第392期,第56-58页。贺龙在地方政争中失利后,追随石青阳入川,转为熊克武辖下,被大元帅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3)、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1925)*分别参见《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3年11月30日,第8页;《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5年3月31日,第11页。。北伐之前,张发奎由中级军官升任高级军官未久,在省外尚无多大名气,贺龙所部则托庇于黔军首领袁祖铭,在湘黔边境艰难求生,总之两人都还处于孜孜不倦的奋斗阶段。然而北伐后不过数月,张发奎作为“铁军”领袖的名头就已轰动大江南北,尤其自到武汉后,他开始跻身政治名流行列,与陈公博、宋子文、谭平山、徐谦等人结识和交往,加上他与邓演达原本深厚的袍泽情谊,其人生发展显有突破一名军人界限的无限前景。*参见《张发奎口述自传》,第77页。贺龙率部则摆脱生存窘境,特别是在进军宜昌时,不顾原北洋十八师卢金山部已被黔军王天培部收编,强行缴获卢部大量枪支弹药,由此奠定其作为北伐独立师的实力基础。*贺龙部属形容当时缴获的武器数不清,第二天起来发现走错路都碰到枪。参见张应祥口述:《我跟随贺龙的历程》,《桑植文史资料》第1辑,第10页。
张、贺两人在大踏步发展过程中,均得益于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支持,并越来越被中共寄予厚望。官兵的补充,是政党和军系得以密切合作的重要基础。北伐期间张发奎所部的连续作战和主攻担当,使其对干部产生迫切需要,但他不像蒋介石那样可以从黄埔军校中补充干部来源。实际上北伐时跨地连续作战的部队都会面临如何招募干部的难题。如果既难从当地获得干部来源,又无军校可以依托,那么在当时的情势下,这种难题的解决过程就很有可能为国共两党、尤其是中共在军队的渗透提供各种条件或契机。当张发奎告诉郭沫若“我需要干部”时,郭就将四川同乡朱德介绍给他,由张派朱去四川“邀聘了许多干部”,后又委任朱德为“待命军官团团长”训练这批干部,这就是其“部下有四川干部的缘由”。*《张发奎口述自传》,第74页。罗永扬可能是证明朱德这段特殊经历的关键人物,此人出身于四川自流井观音滩罗氏大族,不仅其家族与入川作战的朱德有过交集,其本人也曾加入过当地的国民党左派,北伐时才入张发奎军中任职,此后逐渐声名显赫。中共在北伐期间尽其所能,安排受其影响的军事人员或工农骨干加入北伐军队。在陈嘉祐所部第十三军中也有类似情况。李济琛“清党”后广东形势恶化,龚楚率广东工农军离开广东,后来就在中共的安排下投奔到曾经驻军韶关的陈嘉祐部队。这支工农军的全部官兵“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大部份是中小学生,革命情绪很高,战斗力很强,比当时的一般军队质素强得多”,因此于公于私都格外受到陈嘉祐的重视和优待,以致龚楚接到中共命令要求迅速脱离十三军后,陈很不愿意其离去,亲自到工农军驻地——武昌跑马场“召集全体官兵训话两次”,训话时“真个声泪俱下,言词恳切”。*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上卷,明报月刊社(香港)1978年版,第67页。北伐军在这一时期招降纳叛式的扩张有其合理之处,当时也势属必然。张发奎就坦率地认为,吸纳刘佐龙、叶开鑫、贺耀祖和其他投诚部队是正确的,否则“这些人将成为北伐的障碍”。*《张发奎口述自传》,第72页。对投诚部队的吸纳,固然能够迅速扫清北伐障碍,并有助于扩张势力,但另一方面,这些部队通常具有地方色彩,私人关系网络交织其间,改编起来通常并非易事。相比整团整师甚至整军式的吸纳方式,具有中共色彩或由中共遴选的人员加入军队的方式更多时候是分散式的、原子式的,不易使军系首领感受到威胁。从当时的政治格局来看,军系首领越能超出地方军系的视野广泛吸纳力量,就越有可能在北伐战场上赢得优势。张发奎率部出粤后,显然经历了这种巨大的转变,他承认其部队“在北伐初期,粤籍人士占了北伐军的大多数。但当我们从其他省份招募更多新兵时,粤籍人士所占比率便下降了,我们在湖南征兵尤多,并将俘虏兵安插到各部队”,因此他“在广东讲粤语,到了湖南则改说国语”。*《张发奎口述自传》,第72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党员当时在张发奎军中所表现出的朝气和勇敢,也确实有助于提高其部队的战斗力。
贺龙的部队也陆续从中共方面获得人员补充,尤其在武汉“分共”期间这种现象更趋明显。由中共派至贺龙部队工作、后任警卫团连长的黄霖回忆,“就在7月6日左右,有好多工农武装编到二十军来。他们的到来,第一是因为他们在本地不能立足了;第二是党内那些坚持革命、反对右倾投降的负责干部,为了壮大贺龙同志的部队而决定的。所以,这些队伍的到来是完全秘密的”,“还有一个午夜,我连又遵照命令到一个地方去取过好几百条枪。这些枪,当然是工人同志藏起来的”,他还描述当时贺龙同志高兴极了,对好多人说:“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但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队伍和武器;现在不同了,共产党给我们补充,工农同志愿意编到我们这里来。”*黄霖:《南昌起义亲历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中共对贺龙最大的帮助,还在于助其解决在北伐中的“身份危机”。贺龙在湘西虽有根基,且不乏革命资历,但在与各方势力十余年的反复角逐中,其部队既与谭延闿、赵恒惕所属湘军屡有对峙,亦曾背离熊克武所部川军,后名列黔军却又并非正宗,可谓非湘、非川、非黔,更算不上正统的革命军。易言之,贺龙的部队在各大军系中就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凡事均须自己设法努力,当然这也造就其悍勇善战、不拘常规的性格。1926年随黔军借道湖南北伐后,即有传言说贺龙“面见唐生智,陈述本人原系湘军,现愿归湘,受第八军指挥,以谋湘军之团结,不愿隶黔军旗下”。*《袁祖铭部下破裂》,《申报》1926年12月30日,第2版。宜昌缴械事件,激起黔军王天培和湘军何键部对贺龙部队的强烈抗议,当时幸亏国民政府派吴玉章前去调解,才免除各方部队正面冲突的危机,但这一事件基本断绝了其重新归属湘军的可能性。*此前中共党员周逸群已在贺龙军中任政治部主任。宜昌缴械事件经过,参见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另可参见《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记录》(1927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2页。此后在吴玉章等中共党人的建议和运作下,贺龙所部因祸得福,由荆州调到武汉并被编为独立第十五师,后又冲锋至河南前线,得以成就其“钢军”荣誉,这在袁祖铭名下的各路黔军旧部中,可算难能可贵。
1927年7月间武汉“分共”对张发奎、贺龙所部冲击最大。在此之前,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在苏俄(共产国际)顾问的帮助下,合力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决策权,故对这两支较显“亲共”的部队一般会有相当适宜的安排,使其只要履行军队职责,在前线冲锋陷阵,而不必过于担忧其他事务。然而“分共”之后,这两支客居异乡的部队缺乏后勤补给、无地盘依托的致命弱点顿时暴露。尤其在手握重兵、掌控两湖的唐生智逐渐对武汉国民政府形成操纵之势,并进而以“东征讨蒋”为名驱使张发奎部离开两湖地区之后,张发奎担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不禁处于险境当中。另外,此前中共遴选党员、军校生和工农分子以较为分散的方式加入军队,他们在战场上又大都勇往直前,这使张、贺所部受益极大,并由此而对其有所倚重,然而一旦“分共”,势必损及军心与战力,这是军队长官无论如何不愿正视,而且事实上短期内也不易做到的。
在武汉决定“分共”之前,张发奎很可能与邓演达、汪精卫和苏俄(共产国际)顾问进行过多方沟通和密商,以图摆脱所面临的困局。而对张发奎与汪精卫、邓演达最具可行性的方案,几乎可以确定是回兵广东,再谋发展。在武汉国民政府后期,张发奎已被苏俄(共产国际)顾问视为继蒋介石、唐生智之后可能加以扶持的另一个人选,这些顾问中甚至有人强调“每一个清醒的中国将领现在都清楚,蒋介石是由俄国共产党人提拔起来的”,以此来激励张发奎作出与武汉国民政府决裂的“亲共”选择。然而张发奎毕竟不像蒋介石、唐生智那样具备强烈的政治野心,尽管苏俄顾问到1927年6月20日已查清其部“共三个军,约四万士兵集中在九江——南昌一带,不是东进而转向南方,准备占领广东”,但他却声称“没有汪精卫他不去”,显示他与汪精卫在政治上的某种特殊关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记录》(1927年9月1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37页。转回广东发展,应当是张发奎与汪精卫、邓演达的共同想法。依据6月27日汪精卫与罗易的谈话记录以及翌日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汪精卫认为“我们在武汉这个地方犹如在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小岛上。我们在这里什么事情也不能干”,因而明确表示目前“唯一的出路是同第4军和第11军一起去广东”,既然要同南京这个“最坏的敌人”作斗争,那么就“应当进行战斗并推翻李济深”,再在广东对国民党进行彻底改组。*《罗易同汪精卫的谈话记录》(1927年6月27日)、《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年6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369页、371页。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决定实施“分共”后,张发奎的好友邓演达曾劝他必须把“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带到后方——广东,重建革命基地,一切从头开始”,张相信邓的主要目标是鼓励他“同共产党合作,以便建立一支既反蒋又反汪的部队”。*《张发奎口述自传》,第92页。张发奎与苏俄顾问和邓演达的意见分歧,并不影响其将部队集结于九江一带的战略布局。在南京蒋介石和武汉唐生智两大军系的夹缝中,张发奎部以“东征讨蒋”为名驻守九江及南浔沿线地带,无疑形成了进可攻伐江浙、退可转兵广东的机动态势。正如《南昌起义研究》的著者张侠所言,九江地区既是“东征讨蒋”的进攻出发地和战略要冲,又是南下广东的转折点和战略要冲,在东有蒋介石、西有唐生智的挤压态势下,只有九江及南浔线可以不必打硬仗而直下广东,最适合作为南下的前进出发地。*参见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与此同时,中共主要的精英人物或随军行动,或受党派遣,或闻风而动,聚拢于九江——南昌一线,显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贺龙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后来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十一军四师师长叶挺,系CP军事中心,奉命集中南昌后,所有知名CP如谭平山、恽代英、林祖涵、吴玉章等,均相继来集。”*《陈浴新报告赣变经过》,《申报》1927年8月23日,第3版。
在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锋地带,这一时期江西政局原就杌陧不安,此时更添变数。滇军首领、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被武汉国民政府发表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后,南昌仍有蒋介石早前任命的省府主席李烈钧留守,并由其兼理总司令部行营事务。辛亥元勋李烈钧虽为赣人,却有滇系背景。朱培德与其有多年师生及部属关系,不便公然出面驱李,然而事涉军系生存,驱李又势不可免。同为滇系出身、时任第三军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的朱德无此顾忌,他不但将李保送教导团的十余名赣籍学员“一律开除”,抑且放任工会纠察队等民众团体冲击并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其时南昌城内“满街张贴‘打倒李烈钧’、‘捉拿段锡朋’之标语”。*雷啸岑:《十六年南昌政变杂记》,《社会新闻》1933年第4卷第14期,第212页。李烈钧及行营部队卒被驱离后,朱培德以客军身份统管江西,缺乏地方根基,只能重用滇人,是以滇系军人在江西有特殊地位。早已加入中共的朱德此前在四川、湖北均曾活动,但却难成大事,唯有在江西——昔日云南讲武堂同学和滇军袍泽的聚集地——高朋遍地,左右逢源,大可呼风唤雨。*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曾在汉口召集四川革命人士举行秘密会议,征询到会者对发展革命军事力量的意见,针对会上有人提出回四川再干的主张,朱德和刘伯承认为,现在四川形势险恶,再谋发展很困难,武汉也日趋紧张,朱德根据他在江西工作半年所了解的情况,提出可以在江西发展革命力量,并号召大家到江西去。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即使朱德等中共党人后被朱培德“礼送”出南昌,然而驱李时期他与江西中共人士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及其鼓动起来的“左倾”势力,并未遽然消散,只待有人振臂高呼,即有重燃可能。
三、关系编织的暴动组织
经历北伐后,中共透过国民党的省县党部机构和国民政府的军中政工制度,以及占有优势的各类学校和工农运动,再加上有意识地不断向政府和军队输送中共干部,在北伐过境省份形成了横跨政界、军界、学界等的庞大关系网络。尤其在张发奎的军队中,中共既通过党代表和政工人员对军、师、团等各级部队有所联络,又拥有许多公开或隐藏中共党员身份的中下级军官作为潜在的实力基础。政治部主任郭沫若、秘书长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等,均系第二方面军中的中共党员。中共在张发奎部队极为广泛的渗透和影响,使苏俄军事顾问认为“在那里的部队中,特别是在三个师的广州部队中,至少有60%是赞成我们的”,贺龙的部队也招募了“成百上千名共产党员”,至少“能有1000名共产党,而一个军里有1000名共产党员,这是很大的数目了”。*《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记录》(1927年9月1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1-42页。
与中共的关系网络同时变动的是,两广、云贵、四川等省早先参与过“反袁”“护法”等战争或追随过孙中山的诸多军系首领及其部队,还有像谭延闿、程潜这样流寓广东的客籍军系首领,均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大量地从相对偏远的驻防所在地汇聚到南方相对中心的省份或区域,北伐主战场——两湖地区、尤其是湖南省的军人和青年则有数不清的参军机会,并由此而跟随各式各样的部队四处流动。军人之间基于血缘、家乡、军校和战场情感等因素所维系和发展的关系纽带,不但在北伐军中弥散和扩张,有时还在其异乡的防区或地盘继续扎根生长。这些或大圈或小圈、或紧密或松散的关系网,与中共透过党组织、政工制度和军队所编织的庞大关系网络,经常交错共生,互为倚助。前者的优势在于个体关系的网结,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宏观层面的联络。
中共策划南昌暴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调遣各种关系资源的过程。当时负责中共前敌军委日常工作的聂荣臻、贺昌等人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联络和接待各方面的关系人员。他们不仅需要向张发奎部驻九江的叶挺二十四师、李汉魂二十五师等部队中或公开、或秘密的中共党员分别传递起义消息,还负责通知在庐山、九江的党内负责干部接应从武汉等地赶赴九江的党员干部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包括前来参加南昌暴动的军队。参与南昌起义的胡公冕后来回忆:“聂总当时经常在九江的江边上,迎接来的部队和领导同志,把要准备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一个一个地通知他们。”*转见《南昌起义中的中共前敌军委》,载王健英:《红军统帅部考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341页。返回南昌组织暴动的朱德,当时在中共党内虽无重要地位,但从关系网络的角度来说,却是中共极为稀缺的人才。朱德不但具有军校生、军人、中共党员等多种跨界身份,而且先后在滇军、川军、粤军或长或短地任职。更特殊的是,他还具备多年就学或任职于各类军校的复杂经历,尤其是在南昌担任过朱培德部的军官教导团团长——相当于高级随营军校的校长,因而培养了众多军事学员。以上这种跨业界、跨军系、跨地域的经历使朱德拥有极为丰富的关系资源。当这种关系资源汇集于江西一地时,就更能助长朱德的活动能量。由这种视角来看,朱德在延安时期曾说“我帮助组织这个暴动,她是在我的保护下计划的”,与史实大体上是符合的。*[美]斯诺:《西行漫记》,复社(上海)1938年版,第433页。
不过,军事暴动如果只靠调动关系网络,显然难以成事。这时最好要有胆大敢为、一呼百应的军人挑头,才更有成功的把握。作战勇敢但行事谨慎、注重情感的叶挺师长,并非最合适的人选,且其军队数量也较有限。另外,据张国焘回忆:讨论南昌起义回师广东这一问题时,“叶挺是唯一表示不同看法的,他大致认为南昌暴动不易获得成功,如果能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较为合算;中共同志们隐藏在第四军中,也不会遭到暗算”。*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5页。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的性格与行事风格与叶挺迥然不同,他敢于对抗任何势力,之前且有数次改换部队隶属关系的经历,当时甚至有媒体评论其为“反复无常之军人”。*《赣变之前因后果》,《申报》1927年8月13日,第3版。苏俄军事顾问则分析他“由于性情暴躁,他的情绪很容易表现在行动上”,“按其社会出身来说,经过改造以后他是跟我们一起走得很远的将领之一,至少要比所有其他人、要比叶挺走得更远”。*《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记录》(1927年9月1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9页。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尽管隶属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但贺龙很显然不愿屈居于张发奎之下,再加上贺龙对中共及其政治主张向来具有好感,甚至一度向中共组织主动靠拢,这充分提供了中共对其游说的空间。武汉“分共”之际在政治上极度失意的中共高层领袖谭平山,来到江西后与贺龙接触,很快就获得他支持南昌暴动的肯定答复,这对于中共策划南昌暴动来说无疑是个惊喜。换言之,原本不在策划南昌暴动的中共领导层之列的谭平山,能在此过程中主动地成为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其原因不仅在于他在聚集南昌的各种军政人物的关系网中,仍然具有很高的声望和较广的人脉,而更重要的则在于他对贺龙的策动,使中共在南昌组织暴动具备了关键条件。
贺龙答应支持中共南昌暴动后,不论其自身想法如何,在中共当时对其缺乏了解和信任的情况下,他本人已然成为中共与潜在或预计的暴动军队捆绑在一起的重要因素。当张国焘从武汉赶到南昌,试图以共产国际的指示阻拦南昌暴动仓促爆发时,在南昌的中共领导人纷纷以贺龙为由表示暴动不可停止。李立三警告说“贺龙不得志,疑忌甚多;他不满张发奎,也自觉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无出头之日,迟早要被缴械的,现在如果我们改变计划,联络张发奎,那他可能认为是被出卖了;也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张发奎告密,洗脱自己,反过头咬我们一口”;周恩来补充说“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才有出头之日;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最先运动贺龙参加暴动的谭平山也向张国焘说明,“贺龙内心有恐惧也有野心,企图取张发奎的地位而代之,我们正要利用他的这种野心,捧他做总指挥,而且任何联络张发奎的做法都易引起他的疑忌”。*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96-297页。此前中共通过周逸群的关系对贺龙部队已有所渗透,还曾将鄂城、大治等地的工人纠察队编入其教导团,然而即便如此,仍无把握掌控这支部队,更多时候仍需依靠贺龙的个人权威开展工作。周逸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所幸其部下封建思想极浓厚,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氏为神人,故当时唯有利用贺之主张及言论以为宣传之资料。”*《周逸群报告——关于南昌起义问题》,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由此可见,李立三等人的担忧,尽管未必符合贺龙的真实意图,但就当时的情形来说,似也合乎常情。
由于暴动主要依靠第二方面军,中共对军队的动员口号以“回广东去”最具实际效用。张国焘认为,张发奎部队“这班将领大多是广东籍,参加革命较早,深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影响。他们在两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战力最大”,“返回广东的想法,除了思乡和消极情绪外,还有脱离污浊气氛,先将广东情况改善,再图发展之意。这也就是当时南伐之说的根源”。*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72页。“回广东去”的说法估计在张发奎军中流传已久,不仅张发奎与汪精卫、邓演达探讨过这类问题,镇守广东的李济琛也曾“暗地里派人至武昌和九江,劝张向华带兵回广东休养”。*李锷、汪瑞烱、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137页。中共广东特委致信给中央常委信也反映了李济琛与张发奎就张部回粤存在联络的可能性,信中指出“四月十五事变后之李济琛已非以前之李济琛,自不甘事事受蒋牵制”,张发奎“转战千里,无一地盘”,如果李济琛以“团结四军”为口号,“纳张灭钱,排斥外军,实行四军治粤”,“则张未始不可妥协”。参见《中共广东特委致中央常委信——李济琛与蒋介石的关系,我们对粤局政策》(1927年7月16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甲),1982年,第20页。南昌暴动酝酿之际,暴动的组织者一直就未放弃以张发奎的名号发布命令,这恐怕也使一般的士兵以为部队移动系张发奎授意所致,故而较容易接受“回广东去”的口号。在北伐已近乎结束、然而政局却暧昧不清的情势之下,“回广东去”可能对所有在外的广东部队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如果中共再从中加以鼓动,这一口号很有可能变成实际行动。在武汉的龚楚接到开赴南昌集中的命令后,就在其率领的广东工农军中“暗中以‘回广东去’的口号去煽动士兵的思乡情绪,以士兵不服水土,农民家庭观念重等理由和十三军军长陈嘉祐公开谈,要求准许工农军官兵离汉回粤”,由于全体官兵中已经“掀起了一个坚决要求回粤的高潮”,结果任军长陈嘉祐“说尽千语万言,都无动于衷”,最后仍是离汉赴赣,参加了南昌暴动。*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上卷,第66-67页。对以湖南人占多数的贺龙部队来说,则解决后勤补给问题更为迫切,如果能够先在南昌缴获现金和补充枪弹,“到广东后或械或弹或饷,无不所求如意”,那么显然具有极大的诱惑,况且“于汉宁两政府外,重新建设一革命的政府”、“不致再受制于人”,这些都有可能打动人心。*《陈浴新报告赣变经过》,《申报》1927年8月23日,第3版。从一定程度来说,“广东”作为革命策源地,伴随着孙中山的崇高声望和国民党势力的屡仆屡起,在中国革命史上就像一个创世神话的起源地,无论对于国共两党还是对于一些军系首领而言,“到广东去”似乎具有不可言状的某种魔力。
四、余论
中共在组织和实施南昌暴动的过程中,事实上不能完全支配贺龙等军系首领,更谈不上在短时间内对参与暴动的军队进行全面改造,因此南昌暴动以及此后暴动队伍撤往广东的行动,在很多方面反映军系的行为或心理倾向。比如,有的暴动军队自命为正义之师,而极少贯彻中共关于暴动的激烈政策。他们总体上较为注意约束军纪,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大体上制止了工农武装组织对城市和富户的抢夺或破坏,其前期筹款也符合北伐军的通行做法;有的暴动军队则军纪涣散,未能严格约束军队的行动,当然这也反映那个时代军队的通常面貌。“党”与“军”所构成的暴动组合关系,对中共和暴动所产生的更为明显的影响是,由于中共对军系力量依赖很大,迁就很多,因此暴动军队的松散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但导致暴动后未能防止蔡廷锴在进贤率兵出走,而且在此后出现了许多士兵丢弃子弹、甚至临阵脱逃的现象。暴动后这些明显背离中共组织意图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军系内部的结构缺陷或组织特征。从军队构成来说,蔡廷锴原本就属于陈铭枢的部队,张发奎虽将高级干部安插其中,但重组力度显然不够,因此这个师才有可能乘暴动之机脱离张发奎的掌控。另外,粤军北伐过程中招募了大量非粤籍士兵,这在北伐作战时当然有合理之处,但让这些非粤籍士兵参加暴动并“回广东去”,必定面临方方面面的困难,许多士兵临阵脱逃与此不无关系。南昌暴动最终以失败为结局,这使中共在苏俄(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下,更加坚定地贯彻依靠工农力量组建军队进而取得胜利的革命政策,而不是依靠所谓的“将变”——通过策反军事将领而发动的政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昌暴动对中共而言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中共认识到单纯依靠与现有军系或旧军队的结合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昌暴动才有可能从政治理念上成为中共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以工农力量为发展根基的同时,中共并未放弃对旧军队或敌方军队力量的渗透和转化,而是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对其进行争取、改造或重组,并依照这一原则建设红军,使其此后大体摆脱了过去需要依靠军系或旧军队的力量推行革命的不利状态。
责任编辑:魏烈刚
Political Parties, Army Departments and Insurgent Organizations ——The Cross-border Network of the Nanchang Uprising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i Zhihui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caused local army departments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especially Guangdong and Guangxi,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provinces, to step out of their original defense domain, and to convergence and stagger in the area of Hunan Hubei and Jiangxi provinces. Through parties, school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nd meanwhile, with the help of Party representatives and political work system,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pread rapidly the two partie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network in the transit areas of Northern Expe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strengthening the infiltr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local and military forces. Meanwhile, it was full of the military's regional concept, army emotion and identity of the military academy,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link to contact or form a community. In 1927, during the time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Kuomintang in Wuhan was soon be divided, Zhang Fakui's 2nd front army garrisoned Jiujiang, Nanchang and other surrounding areas in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name of "Crusades Chiang". Thereupon, the elit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gan to converge there. The latter, through dispatching and using these resource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network, promoted the party and the army to form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uprising in Nanchang, and gained some political cover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upris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cessive reliance on existing relations resources, especially the military forces of army departments,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CCP to fully implement its political program. The failure experience of the Nanchang uprising enlighten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have established and implemented the principles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volu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party directing guns" since then. Th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rmed forces began to form a new patter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anchang Uprising; army departments; relational network
10.16623/j.cnki.36-1341/c.2017.04.007
黎志辉,男,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副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