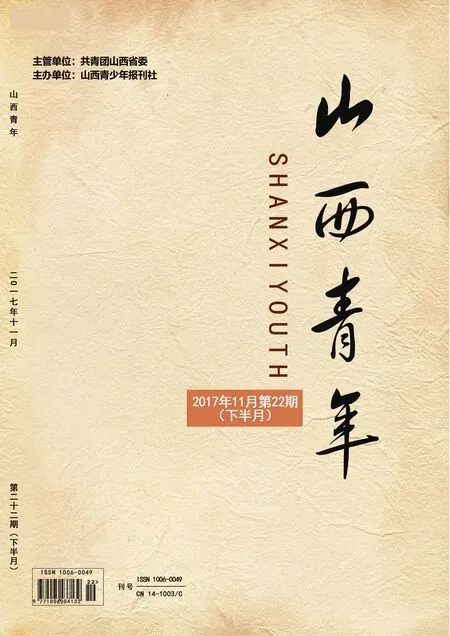对清朝时期天山南路汉回信仰需求的思考
2017-01-29柯榕
柯 榕
对清朝时期天山南路汉回信仰需求的思考
柯 榕*
新疆医科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清朝平准叛乱之后,大量的汉回进入新疆且行走于不同的路线,天山北路的汉回主要以屯民和士兵为主,天山南路则多是商人群体与绿营士兵,不同的身份使得天山南北汉回在信教需求上各有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那彦成奏折提到回民(汉回)“充当阿浑”一事分析天山南路汉回信仰需求,以及清朝管理者可能存在的问题。
阿訇;汉回;天山南路
一、移民天山南北的汉回不同身份特征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之后,在新疆实行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行政、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管理机制,这些制度的建立为稳定当时的新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试图研究的人群汉回在当时的新疆人口比例中所占很少,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将这一人群称为回民[1]。平准事件之后有大量的内地移民迁入新疆,其中占重要人口的是回民,也就是清朝官员口中的汉回(本文涉及的回民仅指汉回)。虽然汉回与新疆回子同样信仰伊斯兰教,但地域差异使其各俱特色,“在全世界的伊斯兰社会中,将礼拜寺的最高宗教者称为阿訇的,(除了喀什噶利亚有若干例子之外)只有中国回民伊斯兰。”[2]由于移民天山北路和南路的汉回来源不一,身份不同,进入新疆为了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和人文习俗,信仰习惯也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新疆回族群体并没有完全进入原有少数民族伊斯兰教的体系,而是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信仰习惯,这些现象可以从清朝初期汉回的大规模移民找到历史根源。
(一)天山北路汉回主要由屯民和士兵构成
元朝以来,汉回以其活跃的商业活动为依托,定居或流走于中国的各个地区。“居住在关内各地的回民族,其历史大约有一千三百五十多年,回民进入新疆地区的时间最晚.....到今天为止不过是三百多年,”[3]虽然没有史料明确记载回民进入新疆的具体时间,但根据学者的推断,“天山北路的回民,可能是在18世纪30年代清朝将准噶尔势力驱逐到吐鲁番盆地以西之后,自1760年开始逐渐从内地移居过来的。”[4]早期的移民者主要来自陕西、甘肃这两处毗邻新疆的区域。甘肃肃州回民较多,乾隆年间为了分散该地区人口压力,迁肃州回民往新疆地区,“《甘肃通志稿》说‘(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移肃州回民分驻哈密’。”[5]“乾隆三十五年从甘肃等省迁往吉木萨尔,阜康的回族屯户就有1150户。三十六年,清政府又以‘屯垦实边’为名,将陕、甘、青回民集体迁徙新疆。据当时户口统计,仅由甘肃迁居迪化的便有2万人以上,在达坂城居住的也有500户。”[6]有学者认为:“新疆回族史始于元朝,而于清朝有较为明显的变化。”[7]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天山以北一些重要的地区已经有相当规模的汉回迁徙入住,以屯垦戍边为主要职责。
(二)天山南路商人群体已有一定规模
在天山南路,回子居住较为密集,清政府采取汉、回隔离政策,限制内地的汉人随意进入回疆地区。所以行走于天山南路的回民可能主要是个人或三五成群的商人团体,并且前往南路经商的汉回人数不断扩大。《回疆则例》规定:“内地汉民,前往回疆各城觅食佣工者,如无原籍、年貌、职业、印票及人票不符,即行递解回籍,”此处史料主要是针对内地汉人经商人员,在经济上严格控制入疆商人来源。而在1829年,钦差大臣那彦成在限制汉回移居新疆的对策中提到:“嗣后内地汉回赴回疆贸易、佣工者,均令在原籍请票出关,注明年、貌、执业、照验,”[8]从那彦成特别强调汉回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赴天山南路经商的汉回人数较多,可能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从而引起管理者的特别重视。
除了经商的汉回群体外,士兵也是天山南路汉回人口的主要来源。天山南路一些重要的城市实行换防兵制,从换防时间上由最初的二、三年改为后来的五年更换,并且不能携带家眷。这些处于天山南路的汉回群体,就不像多数居于北路的汉回一样,有较为固定的生活地点和生活方式,天山南路汉回部分是士兵,在军队编制管理下活动,另一部分是商人,人数分散流动性强。清政府在宗教管理上是否对这个群体给予足够的注意和关照。佐口透学者在其著作《新疆民族史》新疆的回民一节中提到“关于19世纪50年代喀什利亚的回民,瓦里汗诺夫曾做过考察。他说东干,汉语称回回,是来自陕西、甘肃、四川的中国回教徒,他们自称东干。他们有哈乃斐派和沙斐仪派。东干人着汉服,有汉人的相貌,说汉语,在自己的礼拜寺中念着阿拉伯语的祈祷文。”从瓦里汗诺夫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东干人也就是清初的汉回,在喀什利亚有一定的人口,他们拥有自己的礼拜寺,并不是在当地人的清真寺中进行宗教活动,并且念阿拉伯语的祈祷文。
二、汉回“充当阿浑”行为的另一种思考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那彦成在道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一份奏折中称:“汉回盘踞各城,诓骗回子财务,教诱犯法,久为回疆之害,......张逆滋事以前,竟有汉回剃去发辫,充当阿浑之事。”从那彦成奏折的这段说明中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其一,1828年天山南路主要的城市汉回商人已有一定数量,汉回在当地经商,取回妇为妻由来已久。其二,有部分汉回剃去发辫,充当阿浑。
阿訇(阿浑),伊斯兰教中职业宗教者的通称。据《西域图志》记载:“回子通经典者曰阿浑。为人诵经,以禳灾迎福。每遇大年、小年(两大节日),阿浑诵阿伊特玛纳斯经,为众祈佑。”阿訇作为职业宗教者,致力于经典研究和教学,通过经文学校向学生教授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以解经诵读为目的培养后继的职业宗教者。诸多学者对清朝时期清政府对新疆阿訇及伊斯兰教的管理政策做过研究,普遍认为清政府对伊斯兰教采用“恩威并用”[8]、剿抚并存的方式。
清政府官员很早就意识到阿訇在信教群众中的影响力。“回俗阿浑为掌教之人,凡回子家务及口角争讼事件,全凭阿浑一言剖断,回子无不尊依。”[9]所以,“慎选充当回子阿浑”[10]是清政府对下级管理官员反复传达的信息,什么样的人员能够充当阿訇,选取阿訇的具体过程如何,史料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在《钦定回疆则例》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回教阿浑为掌教之人,回子素所信奉,遇有阿浑缺出,由各庄伯克回子查明通达经典、诚实公正之人,公保具缮,准阿奇木伯克禀明,该管大臣点充”。“如有不知经典,化导无方,或人不可靠及剥削回户者,即行惩革”,并对“原保之阿奇木伯克一并参办”。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清政府要求阿訇的任用必须通过各庄伯克推举贤能人士,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阿訇地位高于伯克的状况,伯克掌握任命阿訇的实际权力,但是为了防止阿訇和伯克互相勾结,欺骗地方官员,清政府的行政官员亦可作为监督者,对不可靠的阿訇严格查办,甚至连推举伯克也一并参办。
分析那彦成奏折的这段内容,在“充当阿浑”这件事上显然有疑问。既然明知清朝政府对遴选阿訇如此重视和严格,那么当地汉回为什么要冒险犯法去充当,毕竟以经商为主体的南路汉回看似在政治生活上并无太多诉求,希望通过“充当阿浑”来获得世俗地位的目的显然不可能实现。笔者认为这一事件背后显示出来的问题在于清朝管理者不是真的了解汉回和当地回子在伊斯兰教信仰上的差异,不了解引发的管理真空可能不仅体现在宗教方面,也许已经辐射到汉回生存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得这一群体直接或间接的被反叛分子利用,与清政府的离心力日益明显。
三、对天山南路汉回的宗教环境思考
(一)清政府对待天山南路汉回态度的转变
清朝统治者对待移民南路或者经商的汉回态度有明显的变化,从接受到控制再到防范。随着南路汉回人数的不断增多,汉回势力日渐强大,且天山南路多是商人或者士兵,还有因受内地新教起义事件牵连的逃犯和无业游民,清朝官员认为这些人不务正业,诱骗回子犯法,成为社会治安不稳定因素,于是开始建议朝廷控制人口的流动,加强管理,包括不能和回妇通婚等诸多限制。19世纪中期张格尔叛乱,叛军利用或者蛊惑这些在新疆四方贸易的汉回,由于商人群体大分散小聚居,没有能力抵抗叛乱,便任其俘虏割辫,剃去发辫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是逆反行为,剃发即站在了清朝政府的对立面,也很可能作为勾结外部势力或者叛逆分子造反的证据。于是清朝从控制汉回人数开始转为防范和抓捕逆反人员,即使是被迫剃去发辫者也被发配给官兵为奴或者到云贵地区充军。这一态度的转变过程,反映了清朝政府对南路汉回群体认识的缺失和管理的真空。
(二)充当阿訇是部分南路汉回的信教需求
清朝官员认为汉回“充当阿浑”是对当地回子起到了不好的作用,是对回子盘剥诓骗的另一种形式,管理者对阿訇这个宗教职业者的敏感度和影响力认识深刻,认为汉回是希望通过阿浑这个宗教职业者的地位获取世俗权力。笔者认为“充当阿浑”的行为是汉回进行宗教生活的需求,回民有自己的清真寺,就不得已需要自己的阿訇,个别汉回“充当阿浑”不排除其为投机谋生的手段。佐口透学者在其《新疆民族史研究》一书中写到新疆的回民一节,举例陕西渭南县的回族商人赵均瑞,在阿克苏和叶尔羌地区经商多年,“据说他(赵均瑞)在叶尔羌、阿克苏还担任了乡约,这说明他被公认为当地寓居回民集团的长老和管理者。”这里的乡约应该就是回族教胞的代表者乡老,回民商人赵均瑞在这一地区经商多年,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当地有较为稳固的人脉资源,是回民集团的代表人和管理者。从上述的材料可以看出,随着汉回人数的不断扩大,这个群体的生活处境较为矛盾,虽同样信仰伊斯兰,但南路汉回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和阿訇及其教坊管理者,并非和当地回子的信仰习俗完全相同,由于语言的限制,回民未必能真正融入当地的宗教生活中,生活在天山南路的汉回,在选取阿訇等职业的宗教人士方面没有合理合法的渠道,只能通过民间选取的方式。所以在清朝官吏口中的“充当阿浑”一事,笔者认为可能是部分汉回在天山南路寻求的生存之道,而并非完全出于诓骗和谋逆的心理。
(三)天山南路汉回的教派发展难成系统,易受忽视
天山南路和北路的汉回在伊斯兰教派发展程度上不尽相同,南路回民难以形成受人瞩目的规模,则自身的宗教需求更容易受到忽视。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在天山北路设置了17个垦区,屯垦的士兵将当地的教派门宦制度带入新疆,“时妥明所传虎夫耶在乌鲁木齐一带影响较大,该门宦中有一些回族官吏,如迪化绿营参将索焕章就是妥明的弟子,索焕章加入后,虎夫耶在新疆发展很快。”[11]在一些官吏或者有威望的人的推动下,后期虎夫耶和哲合林耶门派在新疆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天山北路回民多为兵屯和农民,生活环境较为稳定,在教派发展上沿袭内地的门宦制度,发展基本没有受到阻力。而天山南路多是流动贸易的商人群体,多数不具有稳定的生活环境,再加上清朝政府的控制和防范,人数较少,没有明显门宦制度发展的痕迹,虽未见有史料反应真实状况,但是由于大部分商人也是陕甘一带迁徙而来,本身带有不同教派门宦的区别,组织形式如一盘散沙,管理的真空使得这一群体的宗教生活需求不能得到保障。
总的来讲,由于内地汉回移民新疆的身份和路线不同,导致了天山南北的汉回在伊斯兰教宗教习俗和宗教生活上有很大不同,由于清朝统治者的严格管理,南路汉回身份复杂多样,没有稳定的生存环境等因素,使其生存条件和信仰需求都较北路更加艰难,“充当阿浑”现象所体现的是汉回寻求宗教自由和信教空间的本质,而当时清朝政府对这一本质的忽视,认识不足以及管理的真空为后来回民起义迅速在新疆引起回响,以及新疆汉回群体努力寻求生存空间和伊斯兰话语权的行为埋下伏笔。
[1][日]佐口透.1760—1860年新疆回民简况”.回族研究,1992(2):50.
[2][日]佐口透.新疆穆斯林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210.
[3]马良骏.考证回教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85.
[4][日]佐口透,著,章莹,译.新疆民族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69.
[5]穆德全.清代回族的分布.宁夏社会科学,1986,10:60.
[6]马伟.多元融通的新疆回族宗教文化特征研究.新疆师范大学,2012.
[7]盖金伟.近二十年新疆回族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西域研究,2007(2).
[8]《那文毅公奏议》卷77,道光九年三月五日奏.
[9]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264.
[10]《钦定回疆则例》卷八.
[11]马岳勇.新疆回族伊斯兰教的宗教人类学考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6):48.
柯榕(1987-),女,新疆人,初级职称,新疆医科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史新疆近现代民族史。
G
A
1006-0049-(2017)22-007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