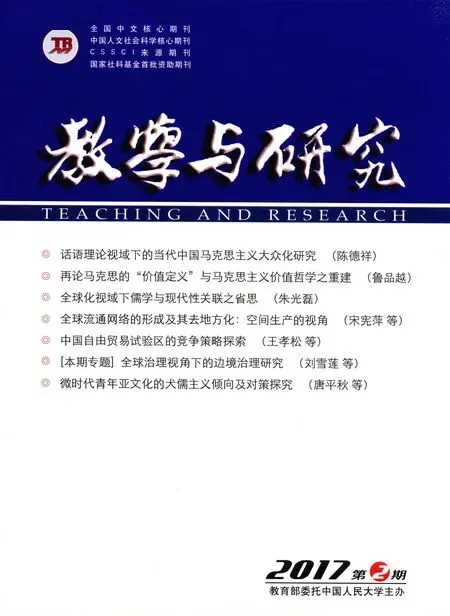全球化时代边疆政治思维困境及应对之道*
2017-01-29曹亚斌
曹亚斌
全球化时代边疆政治思维困境及应对之道*
曹亚斌
边疆;现代国家;边境;全球化
在现代性政治语境中,边疆一词蕴含着单一性、被克服以及封闭性这样三方面思维特征。这种思维既是对现代政治的反映,同时也能很好地分析和解决现代政治中的诸种边疆问题。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边疆一词既不能对新时代所出现的诸种政治状况作出合理概括;也无法通过其所蕴含的特定思维逻辑推导出全球化时代与边疆相关的诸种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基于此,我们需要引入边境这样一个新概念来分析全球化时代在国界线周围日渐兴起的各种新政治现象。边境意指国界线穿过的互动性区域。一方面,边境是一块以国界线作为最明显标识的地理区域;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块以多种多样的跨界互动为特征的社会性异质区域。
目前,边疆政治、边疆治理等研究已成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总体来看,边疆研究在政治学领域的兴起主要与三方面背景紧密相连:一是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日渐深入,边疆地区已成为推进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二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也更为频繁,边疆地区的地缘属性使其自然地成为处理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的中心场所;三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提出,使得边疆地区的多元性、公共性等特征开始凸显,边疆已成为推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主阵地。
正是作为对上述现实的回应,近年来边疆研究开始兴起并迅速升温。[1]然而与研究热潮相对的是,在实际研究中却存在着诸多思维误区,这使得一些研究命题往往成为伪命题,而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具有现实指导性。在诸多思维误区中,对于“边疆”这一概念的认知首当其冲。事实上,正是由于对边疆概念的使用不当,导致研究者的视野受到限制,进而使得出的研究结论无法有效分析和解决当今时代所出现的大量新问题。本文意在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以时代变迁为分析背景,考量和分析边疆概念中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及其在当今时代所遭遇的思维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索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概念体系和思维模式。
一、现代性政治语境中的边疆
作为一种制度形式,现代国家①现代国家是相较传统国家而言的,在当今时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表现形式,可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18-24页,三联书店,1998年。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它是在经历了绝对主义国家形式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家制度②法国大革命一般被认为是现代国家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可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82页,中信出版社,2014年。。借助于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现代国家制度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并于20世纪中期最终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导性国家制度。[2](P4-6)全球范围内现代国家体系的形成,对于非西方世界造成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在这些地区造就了新的政治组织及其运行模式,而且还形成了新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思维方式。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民族—国家虽说是历史的产物,但发展至今,它已彻底重塑人们的政治想象,仿佛不受时间限制地永恒定格了。”[3]可以说,现代国家制度的推广和发展导致人们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以现代国家为标尺思考诸种政治问题。具体而言,这种现代性的政治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通常以如下几种视角展开或体现。
一是国家中心视角。由于“作为政治秩序和哲学教义,主权是政治现代性开始的标志”,[4](P253)主权的独享性和排他性特征使得在现代国家体系下国家中心视角开始凸显。这主要包含两重意思:一方面,在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中,国家处于主导性地位,其他行为体的存在应以国家为基础。“一种特殊版本的国家,即民族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社会;所以,从一种晚期现代观点来看,国家就显得至为重要,而社会则处于应当受国家控制的地位。”[5](P69)另一方面,本国与他国以及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冲突性或竞争性的。“‘国家中心主义’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在国家层面上的扩大化,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下,‘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被视为冲突式的或是竞争式的,进而认为‘我者’的存在具有优先性和独立性。”[6]
二是现代化视角。由于现代国家是一种从传统国家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新型国家形式,现代国家的出现是一个传统国家的裂变性特征被消除,进而获得有效政治整合、资本主义生产、工业化经济以及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等现代性特征的历史过程。因此,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现代化视角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现代化视角下,人们以“现代性”为标尺看待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认为国家的现代化即是将自身所具有“传统性”逐渐消除的过程,通过“传统性”的彻底剔除,从而为“现代性”的获得铺平道路。[7](P30-32)而在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上,则认同一种“同质化”的目标,即认为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就是向已实现转型的现代国家靠拢,将实现国家的政治同质化看作现代化的最终目标。[8](P30-31、72-74)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代国家最早产生于西欧,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往往将政治现代化与“西方化”相等同。[9](P27)
三是集装箱视角。现代国家是通过其他国家对其边界的认可而最终得以出现的,“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2](P147)“民族—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是现时代最为杰出的权力集装器。”[2](P145)这种状况使得人们将现代国家视为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箱,并以集装箱的视角看待相关政治问题。在集装箱视角下,国家的政治边界与社会文化等边界是重合的。国家的政治边界线既是划分不同国家政治权力范围的标识,也是划分不同社会文化范围的标识。边界线两边的社会、文化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随着本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分离,本国货币的主体性凸显,关税及出口定额的改变,以及本土资本与劳动力的大量供应。所有这些使得如下观念产生,即社会与民族国家是一体的。”[10](P185-213)
在汉语政治语境中,“边疆”一词的含义曾几经变迁。若以时间为序列进行考量,我们会发现,这种变化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由于现代国家制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所导致的。19世纪中期以前,边疆是一个帝国语境下的概念,它主要指中华帝国的边缘地带:在文化上来看这是一块文明与野蛮的过渡带,在政治地理上来看这是一条维护帝国中心安全的藩篱。“‘边疆’兼具地理和文化意义,古已有之,只是地理上没有明确边界,文化上以‘智识低下’为特点”。[11](P24)自19世纪末期以来,随着东西方政治关系的变化,以及现代国家观念的引入,[12]边疆一词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边疆不再被看作一块地理上模糊的区域,清晰的国界线开始注入边疆内涵之中。例如民国时期兴起的边疆政治学研究,实质上是以现代国家建设为研究的最终目标。此时学者们思考最多的问题,即是如何将那些历史上称为边疆的地区有效地纳入现代国家的版图之内。[11](P30-39)然而由于传统帝国观念依然存在,使得此时的边疆概念具有多意性特征:它同时汇集了古代帝国和现代国家语境下的双重意义。例如吴文藻认为:“国人之谈边疆者,主要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区上的边疆,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13]而《边疆研究季刊》编者则明确宣称:“所谓边疆,依词义释之,当为中国与外国毗邻之地区。惟吾人本于文化观点,以为边疆之涵义,当为‘中华民族文化之边缘’”。[11](P35)
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国家建构任务的完成①此处主要指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可参见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边疆一词的含义又再次发生转变:古代帝国意义上的含义基本消除,边疆开始成为现代国家语境下的一个概念。[14]
在当今中国政治学界,学者们可能由于自己的研究偏好不同而赋予边疆不同的定义。但若以国家的政治边界为参照系,我们事实上可以将这些纷繁复杂的边疆定义划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可以称为领土性边疆,即以一国的国家领土来定义边疆。在这种定义下,边疆主要指国家领土中的边缘性部分。“边疆通常指一个主权国家边界内侧一定范围,这个范围必须达到一定面积才能称边疆。”[15]“民族国家的边疆,仍然是国家的边缘性区域,但强调边疆是中华民族生活家园内的一个特定区域,是主权国家领土中的一个边缘性的部分,是邻近国家边界的区域。”[14]第二类可以称为利益性边疆,即以一国的国家利益来定义边疆。在这种定义下,边疆不仅指一国领土的边缘部分,那些关涉国家利益的边界外区域也属于一国的边疆。“利益边疆主要是指,在历史过程中产生并在全球化时代凸显出来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判定主权国家之间或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利益划分的界限和范围。”“利益边疆是领土边疆概念的放大和转化。”[16]第三类可以称为社会文化性边疆,在这种认识下,边疆不仅与国家的政治边界相关,而且还和区域内社会发展状况、宗教文化特征等因素相关。“(陆地边疆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硬条件,就是这个地区它具有跟邻国相交界的边界线;二是软条件,那就是这个地区的发展中具有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特点。”[17](P177)
分析上述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看似多种多样的定义其实都是在现代国家语境下产生的,都是边疆的现代性含义:第一种定义是以现代国家制度的核心特征领土为思维起点而形成的,第二种定义是以现代国家所强调的排他性国家利益为思维起点而形成的,第三种定义则是以现代国家所蕴含的现代性政治文化为思维起点而形成的。显然,由于边疆是在现代国家语境下所使用的概念,其内涵中便蕴含了现代性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思维方式。具体而言,在边疆概念中是通过如下三个方面来体现这些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
首先,作为单一性概念,边疆体现了国家中心视角。这种单一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确切地说就是中央政府)在边疆含义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而其他行为体(例如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社会力量、公民个人等)则往往处于次要地位。领土性边疆中国家领土占据了中心地位;利益性边疆中国家利益占据了中心地位;社会文化性边疆中国家的主流社会文化占据了中心地位。二是在边疆含义中边疆只指涉对其具有所有权/利益关切的某一个国家,对于该国边疆之外的所有区域则用“外部环境”等词语总体概括,且这些外部环境在许多时候被看作该国边疆安全和发展的阻碍因素,进而倾向于以“隔离”、“对抗”等方式处理边疆与外部环境间的关系。
其次,作为被克服的概念,边疆体现了现代化视角。由于边疆地区与中心地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存在着不同,从而使得需要用中心属性来克服边疆的异质性。例如领土边疆就需要用中心的安全属性来指导边疆,使其变得和中心地区一样安全;利益性边疆则需要用领土内的国家利益为指导,使其变成与领土内国家利益相同的场所①虽然有人讲利益边疆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来看待,但这种特殊性只是表示获取国家利益的方式不同,而要获得国家利益这一点上与领土内国家利益的获取目的则是相同的。;社会文化性边疆则需要用发展指标为指导,使其最终达到与中心发展一致。“许多曾经被视为边疆的城市。如昆明、桂林、南宁、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现在已经不被作为边疆看待了。甚至一些曾经被视为边疆的地区(或地级市)和自治州,其边疆的角色也在逐渐淡化。在现代化的侵蚀下,边疆的范围缩小了,而且随着现代化的深入。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并不断加强。这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14]
再次,作为封闭性概念,边疆体现了“集装箱”视角。边疆就像细胞的细胞壁一样,其作用在于将国内与国外相隔离。“在20世纪的亚洲,边疆被认为是‘国家认同的细胞壁’,任何对边疆的威胁都会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8](P3)例如在领土性边疆和社会文化性边疆中,边疆便是将本国与其他国家的领土或社会文化予以隔离的区域,而利益边疆虽处于边界之外,但其往往被认作是以国家边界为基础而形成的延伸空间。在这一空间里,利益是独享的。“利益边疆从个体国家角度分析其利益的地域指向,具有单元性的特点”[16]“利益边疆的拓展和争夺已经成为激烈竞争中的相关国家心照不宣的秘密。拓展本国的利益边疆,侵蚀、压缩甚至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边疆,正在成为大国关系中愈演愈烈的‘暗战’。”[19]
二、全球化与边疆政治思维的困境
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全球化的发展已导致人类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等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在诸多行为体中,受全球化冲击最大的当属现代国家,甚至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是与现代国家的行动能力受到限制或削弱相同步的。“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20](P4)“许多国家的权力已经更加严重的衰落了,以至于它们对其人民的权威和它们的疆界之内的行动已经弱化。与此同时,非国家权威却已越来越多地影响其人民,并越来越深地渗入到他们的活动中。”[21]当然,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并不认同各种各样的“国家终结论”,[22](P87-92)而只是想指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现代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从国家权力结构、合法性来源到国家治理模式和目标等方面的整体性变革。
与现实状况相一致的是,以现代国家为标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全球化时代也正在面临着多重危机:一是国家中心视角正受到多元行为体凸显、国际合作的需求和实践激增等现实的挑战。“在全球化开始之际,社会科学家便认识到将民族国家作为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个实体已经日渐过时,因此他们认为需要新的研究视角。”“如果想要理解21世纪的世界,我们就需要打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23](P115)“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思考方式,除了导致物化之外,还会导致民族国家与国家和与社会的混同。”[23](P118)二是现代化视角正受到发展的多样性、世界的碎片化等趋势的冲击。全球化正在催生着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特殊性的普遍化指的是对特殊的东西,对表面上越来越精致的认同展示方式的寻求具有全球普遍性。”[24](P225)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的发展就需要在实现发展统一性的同时,在所有地方保持、维护和扩大发展的多样性。[25](P163-164)三是集装箱视角正受到频繁的跨界活动、跨国性公共问题大量产生等状况的冲击。“民族国家‘集装箱’的观念一直被社会学,以及相应的政治和政治学视为理所当然的出发点,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在这个‘集装箱’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26](P201)
在这种状况下,蕴含了现代性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思维方式的边疆概念也开始面临诸种思维困境:一方面,边疆概念不能对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诸种状况作出合理的概括;另一方面,则由于边疆概念所蕴含的思维模式,使其无法通过该逻辑推导出全球化时代与边疆相关的诸种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具体来说,边疆概念正面临着这样几点思维困境。
第一,全球化时代的跨界公共性开始凸显,从而使得边疆概念中的单一性思维受到挑战。长期以来,公共性与现代国家紧密相连,但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关系已发生变化:除现代国家内部的公共性之外,国家之间的公共性、跨越国家界限的个体之间的公共性开始日益为人们所重视。[27]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边疆地区的公共性成为一种多元的公共性,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社会力量、公民个人等行为体在边疆公共性构建中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边疆地区的公共性也成为一种互动的公共性,它的实现需要与邻国特别是这些国家的边疆区域进行紧密的互动和协调。可以说,在全球化时代,跨界公共性使得国家中心视角下的边疆概念出现困境,而在单一式、独白式的思维下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片面、冲突性的。例如一位学者就曾指出,“研究‘边疆’、‘边界’的概念问题只有不断扩展我们头脑中的文化背景的边界线,尽可能突破‘地方性知识’的局限,……理解他人的见解,叙说对象的言说。”“只有同情的理解,才能避免欧洲普遍主义支配下东方学将异域空间转变成殖民空间的旧辙。”[28]而另一位国外学者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把‘我们’同‘他们’分隔开,……隔离造成更加盲目无知,对于恐惧和猜疑感的盲目无知,而对于其邻居的这种感觉变成和解和真正长期解决冲突的重大障碍。”[29]
第二,全球化时代各个领域边界的不重合性日益明显,从而使得边疆概念中的被克服性思维受到挑战。虽然各个领域边界的不重合状况一直存在,但由于现代国家对经济社会等领域所具有的强大控制力,从而使得长期以来这种不重合性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30](P53-80)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国家控制能力的减弱,这种不重合性开始变得十分明显。上述状况加之多领域互动的不断深入,使得边疆地区“我者”与“他者”间的关系已开始发生变化:“我者”与“他者”不能再用政治边界为唯一标准进行划分,一个人可以具有多重身份,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具有多重关系;政治上的我者可能是经济上的他者,而经济上的我者则有可能是文化上的他者。例如一项实证研究显示:在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南浪村,同一民族(哈尼族)之间文化互动较多,而经济交往较少;不同民族(哈尼族与傣族)之间经济交往较多,而文化互动较少。[31]面对这种状况,边疆概念中的现代化视角便出现问题:在现代化视角下,人们的身份应是单一的(或应趋向单一的),边疆发展意味着不重合性的消除,并最终达到国家的一体化。[32]但这种目标如今已变得不大可能。在全球化时代,边疆地区我者与他者间多重关系将会持续存在并可能不断多样化,协调而非同质化已成为应对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例如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如果继续沿用克服性思维,那么边疆地区跨国族群、跨界活动者①即以跨界活动作为自己生活样态的群体,这些群体不一定都是跨国族群。例如,那些在边疆地区从事跨界贸易的商人、跨国劳工、跨国求学者、跨国传教人员等。的国家认同将变得极其难以解决。“边界居民在认同上出现了模糊化的状况,这主要是因为经济、文化、语言等因素的‘张力’所导致的。这种认同的模糊性导致边界社会在国际合作与冲突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33](P11)
第三,全球化时代国家对边界的控制方式显著变化,从而使得边疆概念中的集装箱思维受到挑战。正如吉登斯所言:“边界是在地图上画出的精确界限,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损害。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又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与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34](P134)在这种状况下,冷战时期那种密不透风的“铁幕”开始大幅度减少②以巴、朝韩地区或许是现存的少数几个“铁幕”。,许多国家的边界正变成“多孔的藩篱”:一方面,国家对边界依然具有控制力,许多跨界活动受到限制;但另一方面,经济贸易、网络信息、疾病传染、环境变迁等则可以较为轻易地穿越国家边界,进而将边界两边的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
国家对边界控制方式的变化使得作为封闭意义的边疆概念出现困境,而若继续以此思维看待相关问题,就有可能得出拒绝、隔离式的结论。例如在发展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边疆的发展应略高于周边国家,略低于内地,呈现一个坡型,从而将跨界活动以“倾倒”的方式拒绝于国门之外。[17](P182)而在面临跨国恐怖主义、贩毒、移民等问题时,封闭式思维则表现得更为明显,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边疆地区军民联防机制建设,构筑维护国防安全的‘铜墙铁壁’”。[35]很显然,在国家开展全方位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时代背景下,上述方案不仅无效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三、边境: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新概念
面对上述困境,我们需要在两种破解路径间进行选择:一种是对边疆概念进行再定义,赋予其新内涵。另一种则是重新引入一个概念来指代上述新状况。笔者的观点是选择后者,这是因为:一方面,边疆一词的含义已在历史上几经变迁,若再赋予其新内涵,将会导致词语意义的混乱,中国近代时期的边疆概念即是一例。另一方面,从概念的精细化方面来讲,我们需要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对某一概念赋予其较为固定的含义,既然如今边疆概念已与现代国家制度紧密相连,那么也就不应再使其内涵变化。例如在美语中,由于自特纳以来“frontier”特指文明的前线,表示文明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拓展区,从而使得在美语学界人们便放弃了用该词指代主权意义上的边疆,转而使用“borderlands”或“border region”等词来指代。相应地,frontier的内涵也便固定化了。[36](P633-649)
在已有的汉语词汇中“边境”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备选词。因为它既指一块与国界相关的区域,同时又是一个较为客观化的词,不像边地、边陲等词具有强烈的价值取向。对于边境,人们有时将其与边疆交互使用。例如《词源》中就这样定义,“边疆,边境之地”。[37](P1683)而在学术界,一些学者也将其等同,“边疆是所有国境线的边境县的总和。”[38]但若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边境与边疆事实上包含着不同的意义。“边境,靠近边界的地方;边疆,靠近国界的疆土。”[39](P91)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边境与边疆概念进行区分,并赋予边境一词新的内涵。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将边境定义为:国界线穿过的互动性区域。该定义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边境是一块空间性区域,该区域以国界线作为最明显的标识,它表示一块以国界线为中心的地理区域;二是边境是一块社会性区域,该区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跨界互动,这些跨界互动使得在该区域内形成了某种独特的规则和互动模式。可以说,在边境概念下国界两边的区域不再被看作两个或多个独立的系统,而被认为是一个整体性的异质区域。
与边疆概念所蕴含的现代性政治思维不同,边境概念则体现了一种全球性政治思维。这种思维主张用多元的、整体性的视角看待相关问题。具体来说,在边境概念中全球性政治思维主要体现为这样两点。
首先,边境概念中体现了一种主体间思维。所谓主体间思维,一方面指言说者并不偏袒我者而贬损他者,而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来看待两者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指言说者并不将我者与他者固定化,而是以一种动态的眼光看待两者间的互动与转化。[40](P139-143)在这种思维下,边境概念中的主体内涵发生变化:除中央政府外,边境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社会力量、公民个人等同样是重要的主体;而在边境地区公共性的确认和实现上,则仰赖于各种行为体的互动与协调。例如在安全问题上,边境安全便是一种综合性的安全①关于综合安全问题,一些学者已提出许多富有创建性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存在的问题是其依然以边疆安全这种独白式的概念为思维基础,而没有使用边境安全这样一个主体间的概念。关于边疆安全的论述可参见余潇枫、徐黎丽:《边安学刍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它不仅指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安全,而且从主体上来看还包括边境地区安全、团体安全、公民安全等,从领域上来看则还应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内容;而在实现和维护每一种安全的过程中,则需要重视诸种行为体间的博弈和协调;同时还应重视诸种安全间的互动与转化。
其次,边境概念中体现了一种系统性思维。所谓系统性思维,是指将思维对象看作“处于一定相互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相互关系的各组成成分的整体”。[41](P36)在这种思维下,边境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互动系统,而它的特征则主要由边境区域内的诸种因素所决定。其中,国界线是边境系统得以出现的核心因素。全球化时代的多孔国界使得它会对其穿过的周边地区产生互动性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又随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最终导致国界周边地区形成某些与相邻各国的内地社会都不相同的特征。也就是说,“边界不再被认作一个被动的因素,只能被描述、绘制或归类,而是一个主动的力量和过程,其对于国际国内各种事务都会造成广泛的影响。”[42](P1196-1216)当然,除国界线外,其他边境区域内的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因素既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社会力量、公民个人等行为主体,也包括边境区域内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因素。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边境形成了与周边地区不同的特征,从而使其成为一块可以辨识的异质性区域。已有的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这种设想的合理性,例如马丁内斯从美墨边境的实证研究出发,提出了一种“边境类型学”,即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边界都有着某些功能性的共同点。继而他认为边境区(borderlands)是被国界线所分割的一块区域。用比较的观点来看,这块区域被认为是一块具有独特性的区域,这种独特性通过多种认同、社会网络、正式与非正式、合法与非法的关系网络把临近边界线两边的人们联系在一起。[43](P6-10)
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边境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首先,作为国家领土的一部分,边境以国界线为标识可以划归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其次,由于国界线的显著影响以及地理位置的边缘性,边境地区与其所归属的国家的其他地区又存在着显著区别。再次,属于不同国家的相邻边境地区间存在着大量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既可以表现为国界线两边地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具有诸多相似性;还可以表现为尽管存在明显的不同,但这种不同主要是由于国界线以及边境区域内的互动所造成时,我们依然可以将这两个(或以上)不同的地区划归为一个边境区域之内。
作为一个空间性概念,边境应有自己的地理范围;而作为一个社会性概念,边境的地理范围则并非固定不变。在一些情况下,随着跨界互动范围的扩大,边境的范围就会随之扩大;而当跨界互动范围缩小时,边境的范围就会缩小。若无跨界互动,社会性意义上的边境就会消失,这时我们就可以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边疆概念来指代这些相互分离的区域。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边界线基本上是静态的,而边界线周围的跨界区则往往是动态的”。[44](P165-201)
在确定边疆地理范围时学者们经常使用一国领土的面积、与中心地区的异质性程度、国家的影响力等单一性的外部标准来衡量。与边疆不同,笔者认为确定边境地理范围时应充分重视边境的多主体性、整体性特征,因而需要用多元的标准进行综合衡量。具体而言,我们至少需要用如下三方面的标准进行综合判断。
一是周边国家的国界政策及其对国界的控制能力。作为正式的制度性规范,周边国家的国界政策会直接影响国界周边的互动状况。一般认为,当国家的国界政策趋于缓和时,跨界互动将会增强,互动影响的区域也将会扩大,这时边境的范围将会增大。反之亦然。国家对国界的控制能力同样会影响边境的范围,当国家对国界的控制能力较强时,这时国家的国界政策就会对周边很大一部分地区造成实质性、直接性的影响。而当国家是一个弱国家时,其影响力的范围就会大打折扣。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对国界控制能力的增强并不表示国界的隔离性变强,而只表示国家政策影响力的增强。例如较之于非洲国家,美国对其国界的控制能力很强,但这并不表示美墨边境互动就弱于非洲国家间的边境互动。“边界两边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平等,促使跨界活动的激增,人们为了需求更好的工资、医疗和教育,就开始大量的跨界活动。这种现象在美墨边境很明显。”[33](P559-560)。
二是国界穿过区域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对边境范围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边境范围受到自然环境静态属性的影响。各种国界线所穿过区域的静态属性不尽相同,一些地方的国界线以河流、山川等阻隔性的自然环境为界,另一些地方的国界线则以文化、历史状况为界从而使得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不具有阻隔性,例如国界两边都是平坦的土地。[45](P7-8)我们可以认为在阻隔性的自然环境下的跨界互动要低于非阻隔性自然环境下的跨界互动,从而使得后者的边境范围要大于前者①如果自然环境的阻隔性极强使跨界互动难以开展时,边境就会被完全分割开来,从而使得边境互动系统消失。。另一方面,边境范围受到自然环境的动态属性的影响。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这种变化除了从阻隔性变为非阻隔性或与此相反之外,还体现在对于跨界公共性的激发或抑制。[46](P182-205)若由于自然环境变化导致跨界公共性问题大量出现且影响范围较大时,边境的范围就有可能较大,反之亦然。
三是国界穿过区域的社会属性。在国界线附近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群,他们所具有的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宗教等因素也会对边境的大小造成影响。例如从历史因素来讲,若国界线两端是有着长期历史冲突的不同群体,那么他们相互间的互动就会相对较少,从而使得边境的范围较小,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边境的消失;如果国界线两端是有着长期交流或协作的不同群体,那么他们相互间的互动就会相对较多,从而使得边境的范围较大;而如果存在许多跨界群体,那么跨界互动则会更为深入,从而有利于边境范围的扩大。当然,除历史因素外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状况也会以其独有的方式影响边境的地理范围。
结 语
全球化使得跨界互动日益频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边界的消亡,国界在全球化时代将会一直存在并将持续产生影响;全球化使得远距离的交流与互动不断加速,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球村”的到来,大多数人依然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并主要与周边的人群进行交流和互动。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既存在超越又存在继承的时代,是一个既在摆脱诸种羁绊又被不断限制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边疆概念正遭遇到诸种思维困境但又并非完全无用,边境概念的新含义正在彰显但又并非放之四海皆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边疆概念指涉的是一种在全球化时代逐渐消退的政治状况,而边境概念指涉的是一种在全球化时代日渐兴起的政治状况。但正因为是一种政治状况,所以边疆与边境都是社会性建构的产物,因而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1] 周平.论中国的边疆政治及边疆政治研究[J].思想战线,2014,(1).
[2]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
[3] 张凤阳.西方民族—国家成长的历史与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5,(6).
[4] [英]安娜贝拉·穆尼,[美]贝琪·埃文斯编.全球化关键词[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 [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 赵汀阳.从国家、国际到世界:三种政治的问题变化[J].哲学研究,2009,(1).
[7]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8] 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09.
[9] 文军.承传与创新: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的变革[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 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nisms and Results[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4,(XXV).
[11] 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2] 俞祖华.晚清知识分子现代国家观念的生成[J].河北学刊,2013,(1).
[13] 段金生.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政治及边疆认识的演变[J].社会科学战线,2012,(9).
[14] 周平.我国边疆概念的历史演变[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4).
[15] 吴楚克.边疆政治: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J].中国图书评论,2012,(5).
[16] 杨成.利益边疆:国家主权的发展性内涵[J].现代国际关系,2003,(11).
[17] 马大正.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J].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18] Malcolm Anderson.Frontiers:Territor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6.
[19] 周平.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利益边疆[J].探索与争鸣,2014,(5).
[20] [德]乌尔里希·贝克,[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21] [英]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2] [英]戴维·赫尔德,[英]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3] [美]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9.
[24]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5] [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祖国[M].北京:三联书店,1997.
[26] [德]贝克,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7] 沈湘平.论公共性的四个典型层面[J].教学与研究,2007,(4).
[28] 张世明,龚胜泉.“边疆”一词在世界主要法系中的镜像:一个语源学角度的考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2).
[29] 弗拉基米尔·科洛索夫.边界研究:后现代进路[J].第欧根尼,2007,(1).
[30] John Agnew.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No.1,Spring 1994.
[31] 滕传婉,金炳镐.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互动与民族关系发展:以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南浪村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32] 袁明旭.从精英吸纳到公民政治参与:云南边疆治理中政治吸纳模式的转型[J].思想战线,2014,(3).
[33] Thomas M.Wilson,Hastings Donnan(ed.).A Companion to Border Studies[M].Hoboken:Wiley-Blackwell,2012.
[34]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5] 栗献忠.跨境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刍议[J].学术论坛,2009,(3).
[36] Emmanuel Brunet-Jailly.Theorizing Borders: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J].Geopolitics,Vol.10,No.4,2005.
[37] 辞源[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8] 李治亭.架构中国边疆学的科学实践[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3).
[39] 饶杰腾,王问渔主编.新编同义反义词典[Z].北京:金盾出版社,1994.
[40] 任平.广义认识论原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41] 那日苏主编.科学技术哲学概论[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42] Alexander C.Diener,Joshua Hagen.Theorizing Borders in a“Borderless World”:Globalization,Territory and Identity[J].Geography Compass,Vol.3,No.3,2009.
[43] Oscar J.Martinez.Border People:Life and Society in the U.S.-Mexico Borderlands[M].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4.
[44] Alberto Gasparini.Belonging and Identity in the European Border Towns,[J].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Vol.29,No.2,2014.
[45] Alexander C.Diener,Joshua Hagen.Borderlines and Borderlands:Political Oddities at the Edge of the Nation-State[M].Lanham: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0.
[46] Joren Jacobs,Kristof Van Assche.Understanding Empirical Boundaries:A Systems-Theoretical Avenue in Border Studies[J].Geopolitics,Vol.19,No.1,2014.
The Dilemma of the Political Thinking of Frontier Governanc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ao Yabi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Gansu 730070)
frontier;modern state;border;globalization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modernity,the term“borderland”contains three aspects:singleness,being overcome and closeness.This kind of thinking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modern politics,but also a good way to analyze and solve various frontier problems in modern politics.However,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the term“frontier”can neither reasonably sum up all kinds of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the new era,nor can it deduce the effectiv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borderland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Based on this we need to introduce a new concept of border to analyze the new political phenomena emerging around the boundaries of our countr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On the one hand,the border is a national boundary as the most obvious geographical region,on the other hand,it is a social heterogeneous region characterized by a variety of cross-border interactions.
[责任编辑 刘蔚然]
曹亚斌,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甘肃兰州730070)。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地缘战略研究”(项目号:16JZD02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