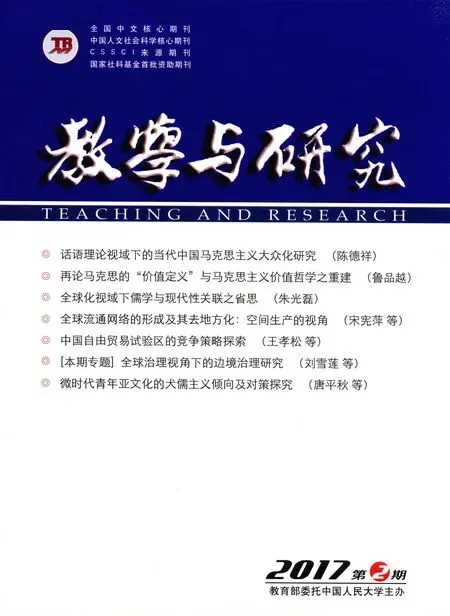国家主权与国际干涉
——一种以规范为基础的解读
2017-01-29赵洋
赵洋
国家主权与国际干涉
——一种以规范为基础的解读
赵洋
国际规范;国家主权;国际干涉;合法性
国际规范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建构主义主要关注规范的传播、内化和本土化等过程,认为规范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可以将国家主权和国际干涉看成是一对共生规范,因为它们相互依赖,并互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而对于主权理解的变化也推动了干涉行为的发展,特别是“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在当代的发展。同时,规范的存在是以合法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这种规范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接受。本文从规范变化的角度对主权和干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干涉行为仍然需要在主权的框架下进行这一事实。
一、引言
国际规范在当代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就主权和干涉规范的演变来看,当代的主权国家的概念起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它承认当时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诸多邦国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从而用主权国家的观念替代了罗马帝国的“世界国家”的观念,并确认了主权平等和领土主权等原则。[1](P36)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不干涉原则便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无论是否得到有效的遵守,各国之间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地位,并且各国都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这一原则后来被联合国宪章所采纳,提出了联合国是建立在成员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的组织。但是在当代随着人道主义干涉规范的发展,传统的主权概念和不干涉原则越来越受到争议和挑战,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开始寻求进行对外干涉行为,并且特别注意诠释其干涉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所有这些都表明,主权和干涉原则作为一种共生的国际规范,其本身也同其他国际规范一样,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其变化也具有国际规范演变的一般特征。
基于此,本文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国际关系理论对于规范的演变和发展的现有研究,其中特别强调了阿查亚(Amitav Acharya)的规范“本土化”模型对于理解主权和干涉规范的演变的重要意义。随后,本文提出了当前推动主权和干涉规范变化的两个因素,即人的安全的概念的发展和作为责任的主权的概念的出现。第四部分本文将对干涉合法性的判断和来源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结论。
二、国际规范的形成、传播与本土化
建构主义对规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解,规范不仅仅具有限制行为体的行动的作用,而且具有构成性作用,即作为一种对于行为体适当行为的集体理解,规范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而不是仅仅限制行为。[2](P327)从这种观点出发,建构主义将注意力集中在研究规范本身的传播、扩散以及发展变化等方面,并强调这种传播和变化对于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的影响。
在这方面,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通过借鉴社会化理论,提出了规范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理论,用以解释规范的传播、扩散以及内化的过程,并且将规范的传播看作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趋势。[3](P888)但是在她们看来,规范的传播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即由少数规范倡导者将规范逐渐传播给其他国家,而大部分国家只能出于增强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性等原因而被动地接受规范。[3](P895)但是在事实上,正如主权概念的变化所显示的那样,规范的传播往往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总是会对规范的内容提出质疑,任何国家都会对一种特定的规范提出自身的理解。为此,托马斯·瑞斯(Thomas Risse)借助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动理论,提出了争论逻辑(logic of arguing)的概念。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以争论理性为基础的逻辑,它试图挑战一个因果性或规范性陈述中内在的有效性论断(validity claim),并且寻求建立一种交往性共识(communicative consensus),这种共识则涉及到行为体对于它们所处的情形的理解以及指导它们行动的规范的合法性。[4](P7)
但是争论逻辑也具有自身的问题,即在当代国际社会中基于综合国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等方面的差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地位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因此无法满足达成交往性共识的先决条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国际关系中实际上存在着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的“层化”(stratification)现象,即不平等性是内在于国际体系当中而存在的,大国占据了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且支配和塑造了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而小国则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5](P156)因此在主权和干涉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并不能形成哈贝马斯式的建立在共同的生活世界基础之上的争论和对话过程,而是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力的过程。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发展中国家处于规范接受者或承担者的地位,但是同时也会对这一规范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质疑,并努力使这种由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外来规范适应自身的社会文化环境。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将这一现象称为规范的“本土化”(localization)的过程,即“本地行为体对于外来观念的积极建构,它使外来观念发展出与本地信念和实践的有意义的一致”。[6](P245)本土化的结果是本地先前存在的一些规范的关键性特性得以保存下来,而不是完全被新规范所取代。当然,新规范也有可能完全取代旧规范,正如奴隶制度被完全消灭一样,这种情况被阿查亚称作“规范取代”(norm displacement),它发生在本地规范的功能有效性或道德正当性已经从内部受到了质疑的情况下。但是当本地规范涉及行为体强烈的身份感时,规范取代就不会发生。如果行为体相信现存的本地规范并没有坏处,仅仅是不完善或不充分,需要通过吸收外来观念来加以修正和完善,那么规范本土化现象就会发生。[6](P247)
就对于主权和干涉问题的研究而言,本土化是一个最具有借鉴意义的概念。有些学者从西方国家的视角出发,认为美国对于预防大规模屠杀等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因为其国内对于“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这一规范的适应,也就是说美国将这一规范本土化了。[7](P30)同时,“保护的责任”规范同时具有限制性和构成性的效果。它的限制性效果体现在它阻止了诸如大屠杀、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犯罪等特定的行为,它的构成性效果则体现在它在国际社会内部为不同的行为体赋予了特定的角色和责任,并且将国际社会的成员假定为是“负责任”的主权国家。[7](P31)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当代国家对于主权的理解往往是同其自身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主要由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主权有限”的思想并不会被其他国家所全盘接受。仍旧以西方国家所提倡的“保护的责任”为例,这是一种同主权与干涉规范的变化所紧密联系的倡议,但是其以责任为借口对于国家主权的侵蚀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受到了一定的抵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结合自身的国情对其进行了重新阐释。例如,俄罗斯就强调“保护的责任”不应当仅仅局限于防止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还应当包括应对诸如环境恶化、危险疾病扩散和饥荒等对于公民造成的伤害。[8]印度则对这一倡议抱有较深的疑虑,强调在解决问题时和平手段的优先性以及当事国政府参与的重要性,并且对使用武力所可能产生的效果表示怀疑,主张国际反应必须是适度的,要避免武力的滥用。[8]在巴西,则有人主张用“保护中的责任”来取代“保护的责任”,主张应当关注“过程中的责任”、“适当终结”和“事后问责”等原则。[9]中国学者则针对这一倡议提出了“负责任的保护”的思想,强调保护应当对目标国的人民以及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负责,而且被保护的对象必须是平民,而不能是特定的武装派别或者政治力量。同时,保护一个国家的公民首先是其本国政府的责任,此外联合国也是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合法的行为体,而除此之外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干涉别国事务。[10]从“保护的责任”所经历的争论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乃至自身的利益对这一规范进行了本土化,从而形成了对于这一规范的具有国别特色的解读。这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各国对于“保护的责任”这一规范的接受是受到其具体的国内环境的影响的,并且同各国自身的历史文化紧密相关。具体来说,就是同一个国家的历史经验、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取向以及对于国家主权的同具体的文化相联系的解读结合在一起的。[11](P76)这正是主权和干涉规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所经历的演变历程,即不同的国家都根据自身的国情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发展。
三、主权和干涉规范的发展
作为一对共生的国际规范,国家主权和国际干涉的观念也是在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当代国际社会中,相互尊重和互不侵犯主权已经成为各国共享的观念,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当前这一观念也日益受到侵蚀,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人道主义干涉现象日益增多。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尽管不同的国家对于“保护的责任”有不同的解读,西方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对这一倡议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是大部分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倡议。事实上,本土化过程就是国家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理解来接受外部规范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也认可“保护的责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大部分国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保护的责任”倡议这一现实表明,主权和干涉规范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某些变化。本文认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两种规范性变化推动了主权和干涉这一对共生规范之间的张力的扩展,即人的安全的观念的出现和作为责任的主权的概念的发展。
(一)“人的安全”的观念的出现
传统上在国际关系中所说的安全是指国家的安全,主要涉及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国家的内政不受干涉等内容。但是当代安全观念的一个重要变化,就在于用人的安全取代了国家安全,将个人的安全视为安全领域中的核心问题。巴里·布赞(Barry Busan)认为,相对于个人而言,国家即是威胁的主要来源,也是安全的主要提供者。[12](P36)从这一点出发,就不能简单地将主权和人权看成是对立的,而是需要在保留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来谈论人的安全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观点。国际关系学者并不认为主权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而是寻求结合当前的现实问题重新阐释主权。在这方面,布赞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应当从三个角度来看待国家和个人安全的关系:第一,尽管个人安全非常重要,但是它从属于国家安全;第二,国家对个人安全的影响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第三,个人对安全的追求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多种影响。[12](P57)
阿查亚则注意到了东方国家对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的不同的解读,而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规范的“本土化”现象。在阿查亚看来,亚洲作为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更加关注解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即实现“免于匮乏的自由”;而西方国家则更强调对人的基本政治权利的保障,即实现“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时,阿查亚指出,强调人的经济权利和发展权利,并不排斥对人的政治权利的追求,事实上它是包含在亚洲国家先前提出的综合安全的范围之内的。阿查亚认为,这种源自西方的人的安全的概念在亚洲地区的制度化程度取决于它同该地区现存的社会规范和文化进行共鸣的方式,如果它能很好地融入亚洲国家的综合安全的观念之中,那么就可以在这一地区得到普遍接受。[13](P23)
(二)作为责任的国家主权的概念的发展
就国家主权这一规范本身而言,当前它正在经历着从“作为权威的主权”向“作为责任的主权”的转变。前者将国家主权看作是一种对于有限的领土和人口的绝对的控制,而后者则强调主权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国家表现出对于最低的人权标准的尊重的时候主权才是有效的。[14](P511)对于“作为权威的主权”,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指出其所具有的历史特征,即它是一种绝对的和无条件的权威,并且推动了绝对王权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在法律上,对外主权同独立具有相同的含义,而坚持主权则表明了一种敌视国际法但是却符合国际惯例的哲学,即国家保留了解释主权的义务以及通过援引主权来确保自卫的自由。[15](P704-707)
至于“作为责任的主权”,则是伴随着人道主义干涉行为而发展起来的新概念,它旨在揭示干涉所具有的正当和合法的一面。沃尔泽(Michael Walzer)对此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支配性力量正在从事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么援引自决原则而反对对于该国进行干涉的立场就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正在野蛮地侵犯它自己的人民的时候,人们就应当怀疑自决原则的适用条件是否具有可行性。[16](P101)从“作为责任的主权”的角度来看,国家有保护其国内人民的安全不受侵犯的责任,如果国家没有做到这一点,或者一个国家本身就侵犯了它的公民的生命和财产权利,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再具有主权,而对它进行国际干涉也就是正当的。阿琼·乔杜里(Arjun Chowdhury)引用干涉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ICISS)的观点,认为主权不是一种国家的权利,而是一种责任,特别是一个国家保护它的人民的权利的责任。当一个国家拒绝或者没有能力这样做的时候,国际社会就有权通过废除该国内政不受干涉的权利来保护它脆弱的人民并约束该国的不当行为。但是这种干涉行为的目标仍然是重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国家,这就意味着责任化的国家主权仍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原则,同时负责任的国家政府也仍然是其边界内人民的权利的最有效的和合法的保护者。[17](P40)
乔杜里所理解的主权就是“作为责任的主权”,它是证明当代国际干涉行为的合理性的主要依据。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看,国家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最终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要最小化对人的侵害。主权保证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一套国内政治体系来维护和推动其公民的利益,这是国家主权的正当性所在。但是国家也可能运用其权力来伤害本来它应该保护的那些人,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国家进行干涉就是合法的,在这里干涉实际上承担的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体系所应当承担的保护其公民的职责。[18](P23)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保护、或者说伤害了其公民,那么国际社会就有责任对它进行干涉以保护该国的公民。从总体上看,作为责任的主权的思想的发展为干涉行为提供了正当性理由,也明确了国际社会采取干涉行为的先决条件。
当前很多西方学者同意的一个观点在于,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并且捍卫国家主权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对其公民恣意妄为的借口。主权除了包含国家的权利,还包含国家的责任或义务,即为其公民至少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的责任。从这个观点出发,一些学者认为主权并不是国家的本质属性,而是给予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成员国资格的一种地位。[18](P23)这种地位不是国家固有的,也不能无条件地给予国家这种地位。如果国家侵犯了其成员的安全,那么国际社会就可以剥夺这种地位。当然,这种非绝对的主权观点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一种主要的声音认为,这种观点会形成一种新干涉主义,借此西方国家可以将自己标榜为国际社会的代言人来对他国进行干涉,而实际上代表的则是西方国家自身的利益。[18](P24)这种批评反映了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利用新干涉主义侵犯他国主权的担忧,也表明在关于主权和干涉的规范问题上各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
四、干涉行为合法性的判断和来源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人的安全的概念的出现和作为责任的国家主权的概念的发展推动了主权和干涉规范的关系的变化。但如果一个国家要进行干涉,就必须为其行为寻找合法性的来源,也就是说国家需要证明其干涉行为的正当性。因此对干涉行为的合法性的研究仍然是同主权与干涉规范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的,因为这对共生规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决定了国际行为体仍然需要为其干涉行为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①当前,对于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重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参见:Friedrich Kratochwil,“The Force of Prescrip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8,No.4,1984,pp.685-708;Thomas Franck,“Legiti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2,No.4,1988,pp.705-759;Ian Hurd,“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3,No.2,1999,pp.379-408;Ian Hurd,“Legitimacy,Power,and the Symbolic Life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Global Governance,Vol.8,No.1,2002,pp.35-51;Martha Finnemore,“Legitimacy,Hypocrisy,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Unipolarity”,World Politics,Vol.61,No.1,2009,pp.58-85;Ian Clark,“Legitimacy in a Global Orde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9,Supplement S1,2003,pp.75-97;Ian Clark,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Christian Reus-Smit,“The Crisis of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4,No.2,2007,pp.157-174;Oliver P.Richmond,Stefanie Kappler and Annika Bjorkdahl,“The ‘Field’in the Age of Intervention:Power,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Versus the‘Local’”,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4,No.1,2015,pp.23-44;Andrew Hurrell,On Global Order:Power,Values,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国家对于干涉行为的合法化来源的追求也表明主权规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规范,尽管其内涵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通常,可以从外部和内部来分析干涉行为的合法性来源,前者主要涉及国际社会中活跃的各种行为主体(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判断,后者则涉及干涉规范本身所具有的特性。
(一)干涉行为合法性的外部来源——他者的判断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合法性是行为体关于一个规则或制度应当被遵守的规范性信念。[19](P7)国际合法性的来源不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偏好,而是取决于国际社会中其他成员的判断。也就是说,一个行动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因为它维护了这些国际社会的成员所共同接受的规则,而共同规则则构成了合法性的基础。
就干涉行动而言,他者的判断对于决定行动是否正当尤为重要。凯瑟琳娜·科尔曼(Katharina.P.Coleman)认为,有四种社会群体可以判断一个行动的合法性,即干涉国本身的国内公共舆论、被干涉国的公共舆论、同干涉国直接接壤的邻国以及国际共同体。[20](P24-25)在这四种观众当中,一个国家最关注的就是国际共同体,通常将其看成是国际层次上最直接的合法性来源。除来源之外,合法性还需要有恰当的判断标准,这种标准就是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科尔曼认为,国家对规则的关注源于这一事实,即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有意识的行为体,它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同其他国家进行互动,而且这些互动是受到特定的“游戏规则”的支配的。[20](P27)这就导致了无论国家无论是否情愿,都需要遵守——至少是在口头上遵守——这些规则。一个国家可能会违反这些规则,但是绝不会公开承认这样做,它们或者直接否认,或者通过话语将其行动建构为没有违反这些规则。据此,科尔曼提出了她的“社会行动的逻辑”(logic of social action)的概念,即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需要关注其行为的合法性。[20](P37)
相比于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对于合法性的判断更具有权威性。就干涉行动而言,国际组织的作用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可以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发起各种干涉行动。作为干涉发起者的最主要国际组织是联合国,但也包括其他一些地区性组织,例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对民主刚果和莱索托的干涉。二是国际组织可以为主权国家所发起的干涉行动提供合法性。事实上,国际组织在干涉行动中具有个体国家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首先,国际组织具有个体国家所不具有的各种权威。这些权威包括理性——合法权威(由于非人格化和中立而产生的权威)、授予性权威(由国家所授予的权威)、道义性权威(以体现、服务和保护某种广泛共享的原则为基础的权威)以及专家权威(因国际组织所具有的专业知识而产生的权威)。[21](P30-34)这些不同类型的权威体现了国际组织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三个作用:第一,国际组织可以对世界加以分类,把问题、行为体和行动分成不同的范畴。第二,国际组织可以确定社会性世界中的意义。第三,国际组织可以表述和传播新的规范和规则。[21](P43)根据这些作用,国际组织就可以为干涉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
其次,在使用国际规则来评估局势方面,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回应。不仅是干涉国和被干涉国,而且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也会出于自身的利益对同一个现象做出不同的判断。正如克拉托奇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所指出的,不仅仅行为体在做出选择时需要诉诸规则和规范,观察者也必须理解支撑行动的规范性结构以便解读和评价这些选择。[22](P11)因此,由于判断标准的不同,不同的国家很可能对同一起干涉行为做出不同的判断,因而就需要国际组织作为一个权威机构来为各国建立一种共同的判断标准。最后,在国际干涉中,需要在具体的环境中对规范进行解释。当代很多国际规范并不是像国际法那样得到了明确的表述,而是取决于各国的赞成或默许。因此,规范的内容也会不断地改变,以便可以得到更多国家的接受。例如,“保护的责任”就是属于这样一类规范,自从它在2001年被ICISS提出之后,就经历了一种从“硬性”规范到“软性”规范的转变,并且将任何关于人道主义干预的具有精确性的约束标准从该规范中去除掉,而只是强调对于预防人道主义危机的规范性承诺。[23](P209)“保护的责任”规范做出如此调整的目的,则在于使更多的国家可以接受它,而不至于使该规范受到直接的质疑和挑战。但是这也意味着这种规范很容易随各国态度的变化而改变,所以对合法性的判断也应当相应地改变。作为个体的国家对规范会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它们无从了解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该规范的判断。[20](P47)只有一个相对中立的第三方来代表国际社会对合法性进行判断,才能得到所有的国家的认可,而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只有国际组织才能具有这样的特性。国际组织的多边主义特性使得它可以成为国际社会的代言人,并且比个体国家更具可信性。它对合法性的判断反映的不是某个国家的态度,而是国际共同体的整体态度,或至少是其中一部分成员的态度。[20](P48-49)因此国际组织对一个特定行动的支持最能证明该行动具有合法性,也可以表明该行动是符合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规范的。
(二)干涉行为合法性的内部来源——干涉规范自身的特性
除了从他者的判断的角度探究干涉行为的合法性之外,一些学者也从干涉规范本身的角度来分析其合法性所在。对于研究规范的理论家而言,国际体系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存在,而且是由历史性产生的,不断进化的共同理解、规则、规范和相互预期所构成的结构。因此,国家主权、国际法或战争的概念也不仅仅是权力政治的产物。通过共享的和以历史为基础的对于战争或主权的理解,人们可以决定国际关系中的游戏规则,以及这些规则变化或进化的方式。[24](P193)尼古拉斯·惠勒(Nicholas Wheeler)指出,人们所建构的主权国家边界在道德上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道德的界限本身就是一种由历史和社会所建构的产物,人道主义干涉则是由人们所造就的。[25](P10)这也就意味着,国家主权本身并不能在道德上证明不干涉原则的合理性,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解读和建构来证明干涉行为的正当性。惠勒引用沃尔泽的道德最小主义(moral minimalism)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一系列所有人都应当共享的核心道德原则,而这些原则则是通过历史经验、文化规范以及多种社会生活形式之间的互动来塑造的。对于沃尔泽而言,存在着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是所有作为人类的个人所共享的。这种普遍性的道德原则意味着,他者的痛苦可以同我们自身特有的历史、价值和经验产生出共鸣,而这种共鸣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所有人都是全人类的一分子[25](P12)很明显的一点在于,人道主义干涉就属于这种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如果侵犯人权的暴行存在并且仅凭本地的力量无法终结这种暴行,那么干涉行为就具有道德上的必要性。
同时,就如同干涉规范自身的发展演变一样,对于干涉的合法性问题的判断也处在不断演变之中。惠勒指出,合法性的判断取决于他者,也就是说合法性不在个体施动者的控制范围之内。[26](P6)但是,规范性观念的变化会推动新的行为的出现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合法性的认知的变化,也就是说先前曾经被认为不具有合法性的行为也会在后来变得具有合法性,而这则是规范自身的演变所导致的结果。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人道主义干涉并不能构成使用武力的合法基础,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联合国所授权的新的人道主义干涉规范出现了,从而推动了干涉行为的合法化。[26](P8)另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在于,关于规范合法性的认知的变化可以为行动提供正当的理由,但是并不能决定国家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正如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时国际社会的反应一样,在屠杀的早期阶段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愿意通过牺牲本国军人的生命来解救大屠杀的受害者,而这就导致了屠杀的延续。[26](P9-10)
另一方面,正如许多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干涉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有学者指出,干涉不应当是一个具体的行动,如果要使干涉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合法化,就必须同时关注具体的冲突预防和冲突后重建等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干涉的合法性就是同预防人道主义灾难的真实意图以及对于灾难后重建的承诺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就意味着干涉仅仅是一系列问题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27](P331)对此,针对干涉的合法性问题,艾利克斯·贝拉米(Alex J.Bellamy)提出了关于干涉的“扩展的本体论”(broaden ontology of intervention),并据此提出了干涉合法性的三项原则:第一,决定干涉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主体应当是需要干涉的人民,而不是其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第二,国家,特别是大国应当积极进行干涉,以便阻止人道主义灾难和在当地进行社会重建,而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大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引发人道主义问题的原因,因此它们有责任缓解其他国家人民所承担的由它们所造成的痛苦。第三,除军事干预之外,国家应当使用非军事手段来增进当地人民的福祉,而这可以使人们关注人道主义灾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27](P331-332)惠勒则指出,要使人道主义干涉具有合法性就必须满足四个要求:第一,必须存在着正当的干涉理由,即存在着所谓的“最高人道主义紧急情况”(supreme humanitarian emergency),它证明了需要干涉的事件是一种例外情况。第二,武力的使用必须是最后的手段。第三,武力的使用必须满足成比例的要求,不可以过度使用武力。第四,必须存在着武力的使用将会导致积极的人道主义结果的高度可能性。[26](P33-34)很明显,惠勒在这里借用了沃尔泽的“最高紧急情况”(supreme emergency)的概念,它意味着危险是即将到来的,并且将会带来严重的危害。[16](P252)
五、结论
从当代国际关系中干涉实践的发展来看,国家主权和国际干涉的规范是在不断变化的,干涉行为也越来越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显著的现象。但是正如国家需要对其干涉行为进行话语建构以及为这种行为寻找合法性来源这一事实所显示的,干涉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主权原则的式微。一方面,国家会通过各种话语建构的方式来证明其行为是符合主权规范的;另一方面,国家要经常在国际组织当中寻找对其干涉行为的支持。对于主权和干涉规范的这种变化,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时也具有西方国家通过其话语霸权来推动这种变化从而谋求自身利益的一面。正如现实所显示的那样,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对国际事件的话语解释,因此可以依其所好来决定是否进行干涉。对于这一点,也有研究指出正是由于美国选择性地使用“保护的责任”规范来为其行为进行辩护,才导致这一规范的道德权威受到了削弱,从而使得非西方国家对于这一规范的抵制更加强烈。[11](P92)从总体上看,本文通过对于国家主权同国际干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初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尽管在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以来干涉规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这种规范所固有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例如,有学者指出,在当代国际社会当中“保护的责任”正面临着一种“是否要进行干涉”的困境:一方面,如果国际社会不进行干涉,那么就有可能会产生人道主义灾难;另一方面,即使国际社会进行了干涉,其所采取的行动也可能会违背最初的人道主义逻辑,从而导致人道主义问题的发生。[28](P434)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则注意到,“保护的责任”为干涉行为所设定的门槛过低,从而导致几乎所有的国内动荡都为国际共同体提供了侵犯该国国家主权的机会。同时,保护的责任对重建目标国国内政治秩序的要求也会导致干涉国承担无限度的责任,从而导致对干涉国行为的帝国主义动机的怀疑。[29](P43)针对这种情况,佩普提出了他自己的干涉标准:第一,目标国内部存在着大规模杀戮的行为;第二,干涉的成本比较低;第三,可以预期目标国的国内和平会持续下去。[29](P74)佩普将他的干涉标准称为“实用性人道主义干涉”(pragmatic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认为它为干涉行动提供了一个道义上可行并且可以比其他的替代性方案拯救更多人的框架。
其次,当代主权和干涉规范之间的张力的扩展体现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主权的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有条件的,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义。例如,“作为责任的主权”的概念的出现就体现了这种变化。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这种转变在英国学派的发展中鲜明地体现出来,这一学派从多元主义(pluralism)到连带主义(solidarism)的转变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主权和干涉规范的演变。传统的多元主义理论以主权国家为核心,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社会,强调国家主权在这一社会当中的支柱作用。例如在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看来,国际关系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国家的存在,而国家则是在特定的区域内拥有主权的独立的政治共同体。一方面,一个国家对其领土和国民享有对内主权,也就是说它在其领土内和国民当中享有最高的权威。另一方面,国家也享有外部主权,也就是说任何国家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而是对外独立于其他国家。[30](P6)然而同布尔等人的观点不同,连带主义则强调个人权利的重要性,认为不干涉原则导致了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侵犯其本国公民的人权而又不受到惩罚。在连带主义的理论家们看来,主权不是一个可以保护人权破坏者的屏障,相反国家应当具有保护其公民的安全和生命的功能,而这就意味着侵犯人权的极端事件就构成了对于不干涉原则的合法的例外,也就是说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干涉就是具有合法性的。[27](P325)连带主义者强调,将个体同人类共同体联系起来的纽带比将他们分离开的多元主义的规则和制度(如国家主权)更加强大。因此,个体在连带主义理论中被赋予了基本的权利,而这就意味着主权规范需要得到修正,以及国际社会的成员有责任通过干涉来保护这些基本的权利。[31](P275)为此,连带主义指出,国家主权是建立在对于国际人权规范的遵守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国家拥有责任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保护人权。[32](P244)这种理论上的变化表明,主权规范在当代正在受到人权规范的不断侵蚀,而主权和干涉之间的张力也因此而越来越突显出来。
最后,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往往对这两个规范的变化更加敏感。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接受这些规范的合理方面,从而使自身更加紧密地融入国际体系,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借口来干涉他国内政。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指出,非西方国家对于“保护的责任”这一规范抱有警惕的原因并不在于该规范保护一个国家的公民的目标,而在于它同国家主权的原则相冲突,而在国际关系中几乎没有国家会在主权的问题上做出让步。[11](P76)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于主权问题往往更为敏感,对于任何有可能侵犯其主权的行为和规范也往往更加警惕。因此,“保护的责任”在非西方国家当中的推行往往会遇到障碍。在这里阿查亚的规范本土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启示,发展中国家需要将国际干涉规范同自身对于主权的理解结合在一起,形成自身关于国家主权和干涉规范的本土理论。从主权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当中仍然将是国际关系中最为核心的规范这一点来看,发展中国家防止西方国家干涉和支配的最主要武器就是国家主权。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自身对主权规范的阐释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从而实现维护自身的独立自主。
[1] 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 Jeffrey T.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J].World Politics,Vol.50,No.2,1998.
[3] MarthaFinnemore,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
[4] Thomas Risse.“Let's Argue!”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1,2000.
[5] Jack Donnelly.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ies:An Approach to Structural International Theory[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8,No.1,2011.
[6] Amitav Acharya.How Ideas Spread:Whose Norms Matter?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58,No.2,2004.
[7] Jocelyn Vaughn,Tim Dunne.Leading from the Front:America,Libya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R2P[J].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50,No.1,2015.
[8] 陈拯.金砖国家与“保护的责任”[J].外交评论,2015,(1).
[9] 海泽龙.“保护的责任”:法治良心与严峻现实——以利比亚冲突为案例[J].国际政治研究,2014,(3).
[10] 阮宗泽.负责任的保护:建立更安全的世界[J].国际问题研究,2012,(2).
[11] Charles E.Ziegler.Contes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J].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Vol.17,No.1,2015.
[12] 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M].闫健,李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13] 阿米塔·阿查亚.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M].李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4] Jennifer M.Welsh.From Right to Responsibility: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J].Global Governance,Vol.8,No.4,2002.
[15] 雷蒙·阿隆.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理论[M].朱孔彦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16] 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M].New York:BasicBook,1992.
[17] Arjun Chowdhury.The Giver or the Recipient?:The Peculiar Ownership of Human Rights [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Vol.5,No.1,2011.
[18] Cristina Gabriela Badescu.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M].New York:Taylor &Francis Group,2011.
[19] Ian Hurd.After Anarchy:Legitimacy &Power in the United Nation Security Council [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20] Katharina.P.Colema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Peace Enforcemen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21] 迈克尔·巴迈特,玛莎·芬尼莫尔.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M].薄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2] Friedrich Kratochwil.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23] Jochen Prantl,Ryoko Nakano.Global Norm Diffusion in East Asia:How China and Japan Implement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J].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5,No.2,2012.
[24] Andrew Hurrell.Norms and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2.
[25] Nicholas J.Wheeler.Agency,Humanitarian and Intervention[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8,No.1,1997.
[26] Nicholas J.Wheeler.Saving Strangers: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7] Alex J.Bellamy.Humanitarian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ventionist Claim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9,No.3,2003.
[28] Christopher Hobson.Responding to Failure: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fter Libya[J].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4,No.3,2016.
[29] Robert A.Pape.When Duty Calls[J].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1,2012.
[30]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M].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1] Tim Dunne.The English School[A].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32] Andrew Linklater,Hidemi Suganami.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State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A Study Based on Norms
Zhao Y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
International norms;state sovereignty;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legitimacy
Norm is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of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nstructivism mai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of norm spread,inter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nd considers that norms have shaped the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of actors.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ate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 pair of symbiotic norms,because they exist interdependently.The changing understanding of state sovereignty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especially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Meanwhile,the existence of norms is based on legitimacy,which means that they must be accepted universally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his paper thus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and argues that interv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in the framework of sovereignty.
[责任编辑 刘蔚然]
赵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北京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