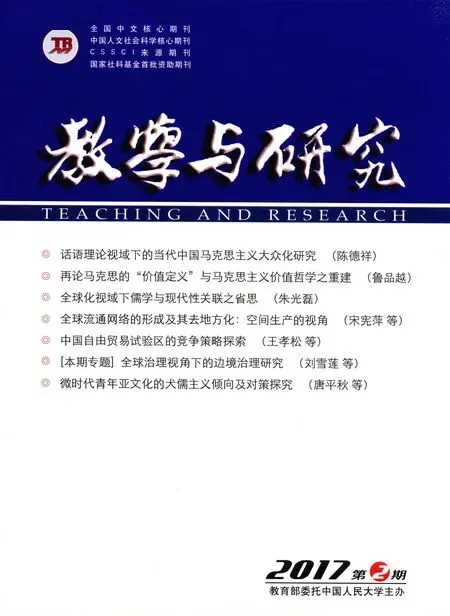边境对“一带一路”战略支点性作用探析*
2017-01-29欧阳皓玥
姚 璐,欧阳皓玥
边境对“一带一路”战略支点性作用探析*
姚 璐,欧阳皓玥
边境;“一带一路”;战略支点
长期处于国家发展战略末端的边境,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产生了从封闭到开放、从静态到动态、从内敛到延展的嬗变。边境作为领先触点、整合力量、联通透达、战略认同开端的独特作用,使它得以成为撬动“一带一路”宏大战略的战略支点。但是,边境的自身缺陷、国家战略的考量缺失和安全的固有障碍仍是边境发挥支点性作用的主要制约。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也将反作用于边境的重塑,并对边境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边境”,依托于边界的延伸区域,是远离国家中心的边缘地带。作为权力重心,对边境的守护等同于保卫国家“疆域”的安全与和平。我国边境发展情况复杂特殊,例如我国陆上边境线绵长,相邻的国家和民族众多,每一个边境地区涉及的问题不尽相同;边境地区涉及的人口结构变动较大,人口流动和流失严重;边境的整体经济发展迟缓。如此种种复杂的问题造成边境研究涉及的学科众多,使得在国际政治学科视角下,对边境始终难以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
“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以来,得到各方的响应与支持,尤其是将我国九个边境省份与沿线国家联通,使边境地区的存在意义拓展,不仅是为了国家安全、政权稳定,同时在国际整体和平的大环境下,边境成为国家经济对外发展新的突破口。面对边境所在省份的企业结构单一,产业转型迟迟不能推进的情况,传统的以戍守边境、看重安全功能的陈旧边境观将予以打破,边境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毗邻多国的地缘禀赋,成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将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放以及西南大湄公河三角洲等地方发展战略与国外链接的新的战略支点。
一、“一带一路”战略视阈下边境特性的嬗变
边境(border)一般指彼此相邻两国或两地区的分界处,即分界线附近的边缘部分。边境的实体范围在法律上始终没有形成统一标准,在新华词典中,边境是“靠近边界的地方”。本文将边境定义为临近边界线的本国国内领土的一定区域。将边境作为研究对象,因其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从整体空间结构看,由于边境地区依托两国间的边界形成,边界具有与生俱来的中介效应和屏蔽效应共存的矛盾性。[1]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边境作为接壤国的最前沿,由其区位优势所带来的跨境沟通的便利性,“将边境区由一个国家内部的‘边缘区’转化为具有发展潜力的‘核心区’,增进其空间可达性与辐射力,达到双方或多方共赢的目标。”[2]造就了边境特性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内敛走向延展。
其一,边境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开放性和封闭性是边境的最根本属性。这种属性与边界的中介效应和屏蔽效应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由于国际边界的独特地理位置,边境的开放性解释为毗邻国边境地区的商品、人员、技术、信息等要素源源不断地进行自由交换与流通,从而推动毗邻国之间乃至区域合作的增强。长期以来,边境地区被认为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最末端,主要肩负着安全屏障和民族稳定的首要任务。一方面,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邻近,深受复杂的地缘政治影响,地缘安全成为边境地区发展的主要职责;另一方面,在边境治理中“族际主义”一直是治理的核心。“把边疆等同于或直接界定为‘边疆民族地区’”,“围绕族际关系问题来开展陆地边疆治理。”[3]因此,边境地区作为敏感地带,一直以封闭性为主导。“边境社会远离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处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能量及信息传导的末梢。”[4]并非处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序列的优先安排。“一带一路”战略,“跨国经济走廊”设计,凸显了边境地区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桥头堡作用。“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使曾经封闭式的边境转型为开放性边境。例如,作为中国最大的陆地口岸——瑞丽,通过“一带一路”重大战略部署,尤其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设想的提出,瑞丽所在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从对外开放的末梢变成了中国对东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铁路项目的设计使其从交通末端变成了新的交通枢纽。
其二,边境从静态性走向动态性。边境的静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客观层面上,边境地区在地理范围上的静止。在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开疆拓土、争取生存空间的大规模战争几乎不会爆发,虽然边界争议依然存在,但边境线基本是稳定的;另一方面,主观层面上,长期以来边境地区地缘安全具有优先性。加之长久以来,在中国传统的地缘安全观念中,国家安全是通过屏蔽外部影响,封闭边境而实现的。因此,存在于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边境是入侵和渗透的静态防线。“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大战略,同时也是区域整合的地缘战略。正如美国地缘政治安排中的“利益边疆”、“战略边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完善将延伸中国的战略边界,通过软化边界,增加其动态性,使其成为区域地缘整合新的增长点。
其三,边境从内敛性走向延展性。边境具有先天的内敛性,无论是天然边界还是人为边界,形成之时便对边界两侧的国家形成了隐形约束,这种约束包括天然边界的约束和人为边境的约束。具有一定政治敏感性或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边境地区,往往出于对边境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的考量,被视为屏蔽邻国影响和渗透的屏障,内敛性成为一种不可扭转和无法避免的必然。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中,边境的逐步开放将推动边境的延展性特征。首先,在自然状态下,当边境地区与其他国家临近,这种地缘方面带来的便利对政治沟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领域有很强的扩展性,即潜移默化的将本国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溢入邻国,对邻国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产生影响。这种行为可以是一种自发、自觉地双向行为,也可以是单方向的一方施加,一方承接。其次,地缘空间作用理论认为,区域作用的强度在空间距离上具有规律性。伴随着空间距离的扩大,相互作用强度递减。边境地区的区位优势,决定了跨境次区域合作更容易达成。[2]尤其作为边界两侧的邻国,如果经济合作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那么合作更容易达成。特别是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当毗邻国家间经济要素传递时,经济活动带来的优势或劣势效应延伸,从而提高市场的近似与对接,并根据供给与需求使得毗邻国之间经济活动频繁往来。
二、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支点的边境
“战略支点”主要指在战略推行过程中,具有决定战略走向的关键性节点。
其独特意义就在于它利用地缘上的优势在整体战略的演进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5]由此,在政策制定、实施、反馈等整体过程中,推动双方的沟通与协调,促进被实施者的理解以及双方的合作。
选取“战略支点”主要归因于以下两个要素:首先,地理位置是战略支点选择中最主要和最先考虑的因素。这种优势可以是单纯地理位置的接近,也可以是在战略意义上、在政策传达和实施中的便利与直接。其次,“战略支点”还扮演着“后备力量”的角色。政策的实施不是一蹴而就的,“战略支点”集沟通、中介、动力作用于一体,作为政策的“轴承”,是整体战略发展中无法忽视的存在,其存在的必要性恰恰是缘于当政策缺失时需要一个补充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战略支点”是战略实施中支撑、协调、带动实施的保证。
“一带一路”战略是统筹国内国外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之所以需要战略支点,主要归因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作为统筹国内国外,横跨海缘陆缘两个方向的宏大战略,战略的推行需要找到“支点”以撬动整个“一带一路”战略。其次,战略支点是“节奏”的“调节者”和“带动者”,负责整个政策推进过程的把控,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提供便利和帮助。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石油资源、公共基础设施等产能输出项目庞大,谈判与协调周期长,而边境地区由于地缘上的优势,对邻近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有着更为详细的了解,在信息的交换上可以为大型项目提供支援和帮助。在此基础上,边境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性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其一,边境是“一带一路”向外拓展的领先触点。对边境的优势探讨首先集中于其地理位置。自身地理实际距离的临近使边境成为“支点”的不二首选。中国幅员辽阔,有着漫长的陆上和海上边界,陆上接壤国家达14个,并且陆上边界多以河流、湖泊、山脉等自然划界。因此,从地理位置角度看,边境是与邻国对外沟通最直接的地区。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6]“一带一路”战略侧重于东北亚经济、东南亚经济整合,“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青海、宁夏、甘肃、山西、新疆、重庆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共1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一带一路”与以往国家发展战略不同,它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实质是一种跨境次区域合作,即边境两侧的国家或地区将双方边境地区视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场所,实现本地区的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参与者的经济福利。[2][1]
其二,边境的地理优势带来的整合力量不容小觑。这种整合力量是边境的自然条件和后天发展择选的结果。首先,我国幅员辽阔,陆上边境多以河流、湖泊、山川等作为天然疆界,除了存在极端气候人迹罕至的边境地区,边境的自然资源丰富,同时,人力、资金、资源、优势产业在边境地区均有所发展,自然会在边境地区形成群聚效应。另外,边境地区与邻国毗邻,在国家的对外交往中,边境是必经之路。国家推行对外开放政策,重视边境地区的力量,在双方开展运输、资源互补、商品沟通时,通常会给予边境特殊的关注。“我国倡导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7]在保证边境安全的前提下,能够充分利用边境的区位优势,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补充和能量。虽然边境地区存在着经济欠发达,产业链条不完善等发展劣势,但是未来发展前景和空间较广,它为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输出,以及配套设施的运用提供了良好的资源保障。
其三,从地缘角度上看,边境作为一个具有先天优势和后天发展的地域,是与国外沟通最临近和透达的地区。“边境地区通常是各国经济联系的重要渠道,跨国合作往往需要借助边境地区的地理优势。”[2]如果说地缘优势是先天产生,“透达”则是在国际环境平和的状态下,沿边地区在与邻国发生跨境贸易往来合作中带来的实际反应。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为了双方沟通的顺畅与直接,边境可以作为政策的“沟通者”。在边境地区形成新的中心区,作为“沟通者”,为所在省份及周边地区的资源、人员、商品提供新的交换途径的同时,也为国外的商品在边境省份的发展拓展空间。同时,为毗邻国家与中国在能源、基础设施的互通提供便利,比如在边境地区形成大宗商品集散地等形式都是边境地区发展的新方向。将边境打开,不仅是增加对外开放程度,而且对边境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产业转型、拉动省内经济也起到带动作用。
其四,边境是构筑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认同的“开端”。由于边境是一国通向另一个国家的地理“起”点,在边境两侧的国家之间通过进行经贸往来以及民间交流等,增强与周边国家的认知与互信是有必要的。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在赢得周边国家支持的同时也引发了质疑,“中国威胁论”再次尘嚣而上。“一带一路”战略在边境地区的落实和发展状况以及政府对此支持力度的呈现,可以增强邻国对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信心,增强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而且中国的陆上边境整体趋于和平,在边境的发展重心由政治安全转向经济领域,这种导向变化对边境地区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特别是利用边境的区位优势构建物流枢纽。在我国主要边境省份的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包括图们江流域次区域合作和大湄公河流域次区域合作,边境的区位优势明显,使其可以作为大宗商品交易的物流存储地区。由于大宗商品的生产地零散于国内的各省份,大宗商品协议从签订到落实的时间跨度较长,但如果在边境地区建立大宗商品的“物流储存仓”,在边境地区就能完成销售过程,将交易过程化繁为简,从而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在边境贸易区发展阶段,随着物流运输成本下降,边境地区生产与消费水平提高,自身吸引力也随之提升,增强生产、资本等各要素的流动,提高集聚效应,缓解沿边省份存在的经营管理、布局不合理、现代化水平低等种种问题。[8]从2015年开始,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开始与黑河市政府合作,参与黑河市的跨境电子商务基地的建设,“参与黑河和俄罗斯之间物流通道建设,在黑河及俄布市设立边境仓和海外仓”,推动黑河市“传统外贸企业转型”。[9]边境地区经济合作方式的多元化探索,有助于推进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度和响应度。
此外,虽有边界将两国分隔,由于一些边境地区的边界意识薄弱,跨境商贸、民族、文化等往来频繁,从低层次的边民交流互市到高层次的政府间合作,足以加深彼此理解。由此,边境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新窗口。
三、“一带一路”战略在边境的实施困境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至今,边境作为战略支点发挥作用的成效仍不明显。一方面,自然条件的约束和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地缘劣势,限制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边境发展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并非处于优先地位,边境的保卫功能是首要,发展功能则是其次。由此,制约边境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支点性作用的因素主要归结为边境的自身缺陷、国家战略考虑的缺失以及国家安全问题。
其一,从边境自身缺陷层面来讲,中国边境地区的缓慢发展,边境地区的基底薄弱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同的边境存在不同的情况。一些边境地区的自然与气候条件恶劣,造成边境本身不适宜在经济上有所突破,甚至是少有人居住;还有一些边境在演化过程中旧有特质的留存,比如边境的封闭性特征带来的隐形阻碍,边境安全的顽疾造就了人们心理对边境动荡的不安以及政治敏感性的过分强调,却忽视了对边境经济发展需求的关注,这些缺陷造成边境难以充分得到发展。
其二,从国家战略考虑的缺失层面来讲,国家对边境的整体规划直接而且简单,最初且最主要的就是保证其安全性,维护国家领土安全。而且,探讨边境问题是边界两侧国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边境涉及的治理问题虽立足于本国,但又涉及国际关系的问题。因此,国家对边境的战略考量存在偏差,以中国古代为代表的封闭式边境,将边界视为隔离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天然屏障。自古以来,由边境向内发展的封闭边境观深深融于中国的帝王统治思想。因此,在中国的历史精神深处,边境地区追寻的是地区安全而非经济发展,这种潜意识仍延续至今。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开放型边界逐渐增多,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日益发展,成为区域经济集团化的一种表现形式。[10]边境在跨境次区域合作中的承接作用不言而喻,边境不再只是扮演国家安全的“前沿哨所”,其经济发展的优势和诉求逐渐凸显。但是国家战略的长期忽视,边境自身承载力不足,基础设施无法跟进,整体投资环境基底薄弱,使得跨境次区域合作出现诸多问题与阻碍。而且,中方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对邻国依赖性过强。以黑龙江省黑河市为例,黑河市作为国家首批沿边开放城市,与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仅一江之隔,近年来主张发展与俄罗斯对外贸易,但由于俄罗斯经济下滑,汇率贬值,黑河市出口贸易量明显下降。同时黑河市对俄罗斯主要是农贸产品出口,虽然存在大宗商品的进出口,但与俄罗斯的传统工艺、技术成熟、完整的产业链等相比,黑河市缺少自身优势,因此黑河市在对俄的出口导向型贸易中很难占据主动权。
此外,由于我国与毗邻国家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宗教等差异,在双方进行跨境合作中出现不同程度的中国单方面主动实施,另一方抵触的问题。大湄公河流域次区域合作计划中,中国与沿线流域国家便存在着矛盾。东南亚国家将中国视为东亚的“庞然大物”,“中国威胁论”的反复提及以及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抵触情绪增加了次区域合作的实施难度。不仅我国与邻国之间存在矛盾,次区域内的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问题,如越南、老挝之间就存在着历史积怨。[11]
其三,安全始终是困扰边境发展的固有障碍。地区发展离不开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边境存在着天生的“不安定”,因此探讨边境未来发展问题,自然需要对安全问题给予关注。特别是当前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传统安全的冲突依然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上存在,大量非传统安全领域导致的冲突也纷纷涌现。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冲突与传统安全领域的冲突交织在一起”。[12]近年来,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人口流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中国边境地方政府治理的主要难点。这些与内地城市相比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阻碍了边境贸易的发展和生产、资本等要素的充分流动。边境地区距离国家发展中心较远,核心发达地区的发展溢出难以辐射到边境地区。边境安全仍是众多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即使在全球化状况下,传统安全风险有所缓解,但国家对边境安全的关注度要远高于其经济发展。例如,每次朝鲜核试验都在挑拨东北亚安全形势脆弱的神经,与朝鲜邻近的中国东北边境的整体氛围变得异常敏感。朝鲜半岛的极不稳定,随时爆发核试验以及官方层面的摩擦等都造成中朝在经济合作等领域的停滞。[13]
四、“一带一路”战略对边境的重塑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扩大了边境发展空间,同时这种发展外溢到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将对边境地区的社会结构、产业转型、人口变动等提供新的解释和努力方向。它将边境地区的各种生产要素、资源糅合再分配、再利用。这个“重塑”是多个方面的。
其一,“一带一路”对边境经济的重新布局。“一带一路”战略将为边境经贸发展重新布局,注入活力。首先,“一带一路”战略为改变边境地区的经济结构单一、资源配置不合理、交通基础设施陈旧之面貌带来机遇。国家针对边境地区的政策多有优惠,无论是在推进跨境次区域合作乃至区域合作层面,政策支撑下边境地区的盘活都将起到积极作用。“一带一路”对边境的重塑不仅需要国家层次的战略部署,同时需要当地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引领与促进。东北边境地区注重将自然资源与传统工业相结合,为传统产业转型找寻出路,同时加强与俄罗斯、朝鲜等的合作。作为国家批准实施的沿边开发开放区,长吉图先导区的发展不可忽视,在长吉图先导区引领下,吉林省2016年上半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为48.14亿美元,同比增长10.0%。[14]但由于东北传统工业急需转型,体制僵化,以及人口流失严重等问题,亟需重新开辟新的发展领域为东北经济发展引入新思路。此外,边境所在的地方政府会运用区位优势及本地发展的优势产业,完善跨境地区的开放程度,促进沿边地区依附于本区域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形成经济集聚效应,提高沿边地区整体的城市辐射能力和带动力。[15]
其二,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边境地区跨境交流的日趋频繁同时引发了毗邻两国间边境社会的新问题。例如,美加边境是加拿大人口的主要密集区,传统的美—加边境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整合下相对平稳,但不少“加拿大人民表示出对美国枪支文化的厌恶”,认为他们深受美国“枪支自由化”的威胁,并且这已经威胁到了加拿大本身的安全。[16]“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不仅是“走出去”也是“引进来”。边境地区作为“互联互通”的枢纽地带,其对外开放程度在进一步提高的同时,其面临的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中国边境地区自然环境复杂,边境各要素的活跃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例如我国云南边境地区,地形复杂,与邻国缅甸没有山脉或河流的天然阻隔,虽然在边界线上设有武警部队的边防检查,但一直以来,两国边界线上的上百条“便道”使完全意义上的边境管控无法实现。随着云南成为“一带一路”上通往东亚、东南亚的桥头堡,其面临的“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跨国犯罪、毒品网络、恐怖主义等安全威胁有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因此更需要国家和地方予以重视和管控。
边境地区的人口结构变化形势严峻,使边境安全面对新问题。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出量增加,人才流失速度加快。受到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的限制,实际人口下降快,男女比例失调,甚至在去年人口呈现负增长,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人口渐进式和递增型的内迁和外逃,使边防问题出现隐患。因此,维护边境安全,护边、治边是边境未来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三,“一带一路”对边境金融领域提出更高要求。随着边境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边境贸易发展呈现迅猛态势。边境地区贸易往来的顺畅,为货币结算便利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在国家注重货币外交,开展人民币国家化的同时,为边境地区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机会,减少投资过程中双方因资金问题造成的各种摩擦。2016年10月人民币作为除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外的第五种货币正式加入了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结算将会为边境地区不断增加的国际使用和结算起到支持作用。另外,中国开始逐步在边境地区开展试点,“位于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已正式被国务院批复为中国首个卢布使用试点城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允许一种外币在中国某个特定领域行使与主权货币同等功能。”[17]
中国边境拥有地理环境、政治因素、经贸往来、宗教信仰、人员流动等纷杂的自变量,造成边境未来发展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比如南北方的边境状况就天差地别。可拥有复杂因素的自变量的边境,将承接其地缘禀赋,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在资源的互换过程中,在文化交流中,发挥协调和引领的作用。这个过去在国家战略构想中曾经忽视的部分,将在“一带一路”战略贯通国内与国外的过程中,逐步作为“战略支点”发挥其独特的杠杆作用。
[1] 李铁立,姜怀宇.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研究:一个边界效应的分析框架[J].东北亚论坛,2005,(3).
[2] 柳思思.“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新进路[J].南亚研究,2014,(2).
[3] 周平.陆疆治理: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6).
[4] 周平.国家治理视阈中的边疆治理[J].行政管理改革,2016,(4).
[5] 徐进,高程,李巍.打造中国周边安全的战略支点国家[J].世界知识,2014,(15).
[6]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7] 张玉新,李天籽.跨境次区域合作进程中我国沿边地方政府行为分析[J].东北亚论坛,2012,(4).
[8] 史进,刘养洁.论跨边界区域物流运输一体化的构建[J].经济地理,2012,(7).
[9] 黑河市与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等平台和企业开展对俄跨境电商合作对接[EB/OL].黑河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eihe.gov.cn/html/2015-09/10-39-81405.html.
[10] 汤建中,张兵,陈瑛.边界效应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地域模式——以东亚为例[J].人文地理,2002,(1).
[11] 张庆霖.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演化:边境区域经济合作——GMS框架下以我国西南边境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14,(14).
[12] 方长平.国际冲突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3] 禹颖子.近期中朝边境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趋势剖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2,(1).
[14] 上半年吉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48.14亿美元[EB/OL].中国吉林网,http://www.cjtzlss.com/index/news/id/9884.html.
[15] 李天籽.中国沿边的跨境经济合作的边界效应[J].经济地理,2015,(10).
[16] 美加边境修筑高墙?两国民众都说“好”![N].羊城晚报,2015-10-12.
[17] 绥芬河成首个卢布使用城市卢布可当人民币用[EB/OL].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20131210/070617583929.shtml.
On the Strategic Fulcrum Role of the Frontier for the“One Belt,One Road”Initiative
Yao Lu,Ouyang Haoyue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
borderland;“One Belt,One Road”;strategic fulcrum
The border has long been at the end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In the push of“One Belt,One Road”strategy,the border has witnessed the changes from closed to opening up,from static to dynamic,from the inside to the extension.Border has played a unique role in the fields of leading contacts,the integration of strength,connection of all ways and strategic identity.It has become a strategic fulcrum leveraging the grand strategy of“One Belt,One Road”.However,the border's own defects,lack of national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and inherent barriers to security,are still the main constraints for the border to play a fulcrum role.At the same time the advance of“One Belt,One Road”strategy will react to the border remodeling and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责任编辑 刘蔚然]
姚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欧阳皓玥,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地缘战略研究”(项目号:16JZD027)、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的转型与中国的战略应对研究”(项目号:2015QY03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