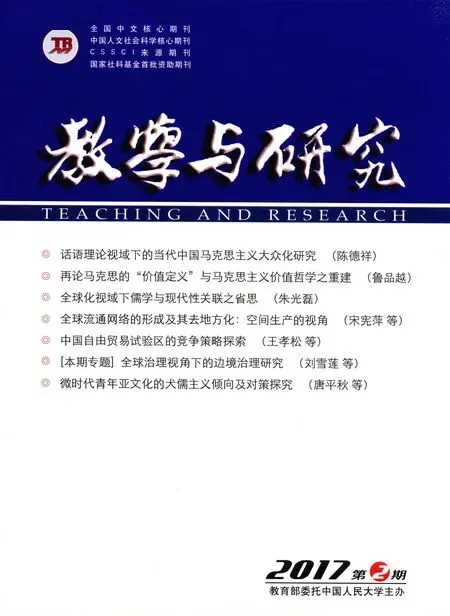再论马克思的“价值定义”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之重建*
2017-01-29鲁品越
鲁品越
再论马克思的“价值定义”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之重建*
鲁品越
使用价值;自然价值;社会价值
我国现行价值哲学中的价值概念,以马克思著作中出现的“外部客观世界的事物(客体)对于人(主体)的需要满足与否(意义)的关系”为其理论依据,将价值理解为物对人的关系,并且将《资本论》中的“价值”排除在“价值哲学”之外。这是对马克思的著作的曲解,我们可以严格地证明:这句话的确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价值概念,而决非马克思本人的价值概念。物对人的使用价值是“自然价值”,其为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对象。哲学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价值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它负载于物质之中而使物质社会化,由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价值纽带。而《资本论》的劳动价值概念是整个价值世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作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人伦价值(含伦理价值、法律价值、政治价值)、美学价值,社会历史实践过程就是价值世界的生产过程。
人类不但生活在由实践生成的事实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由人类主体赋予客体以意义而生成的价值世界之中。因此价值哲学理应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而“价值”正是活生生地体现唯物史观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的核心概念,因此《资本论》的价值概念与价值理论,理应作为唯物史观重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基础。
然而,事实情况与此相反。在当今中国流行的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恰恰以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概念为基础,与马克思的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相对立。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是这样定义“价值”概念的:“哲学上的‘价值’是解释外部客观世界对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即外部客观世界的事物(客体)对于人(主体)的需要满足与否(意义)的关系。当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时,客体对于主体就有价值,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越高,价值就越大。”[1](P81)按照这种观点,作为客体的“物”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关系(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哲学上讲的“价值”,而这正是西方经济学中物品对人的效用价值。于是,自称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为基础,必须声明其要与《资本论》中的“价值”概念划清界限。有人干脆说得非常彻底:“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的价值,不同于作为人类劳动凝结的商品的‘价值’,但却可以相当于商品的或物的‘使用价值’”。[2]这种既自称“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却要把《资本论》的价值概念完全排除在“哲学上的价值”之外的现象,不能不说是一个怪现象。这种怪现象表明:现在流行的“价值哲学”中的“价值”概念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不能冠以“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必须正本清源,以《资本论》的价值概念为基础,由此衍生出真正的“价值”概念。
一、所谓的“马克思的价值定义”的真相
将《资本论》中的“价值”排除在“哲学上的价值”之外,而将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作为“哲学上的价值”,并且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这种奇谈怪论根据何在呢?原来是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句话:“‘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P406)这句话被理解为马克思对“价值”一词的“定义”。因为“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的“‘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必然是“使用价值”,由此推导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就是使用价值”,进而混同的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现行的全部价值哲学都建立在这个所谓的“马克思的价值定义”基础之上。
但是,这句话是马克思给出的价值定义吗?非也!郝晓光先生早在1986年就敏锐而深刻地指出,这句话所表述的并非马克思本人的价值概念,而是马克思所总结的瓦格纳的价值定义,因而正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对象。[4]这一见解是对中国价值哲学界的重要贡献。李德顺先生对郝晓光的见解十分大度,称尽管对其观点未尽认同,“但不能不承认,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不懈钻研的执著精神和学术积累,已使他开辟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理论天地。”[5](P序言)但是问题并未就此了结。对马克思这句话的性质至今仍然具有不同理解:有人仍然坚持认为这句话就是马克思自己所持的价值定义。[6]其最突出的表现是现行的哲学教科书的价值哲学,将上面这句话理解为马克思关于“一般价值”的经典定义,将哲学上的“价值”理解为“外部客观世界对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这就导致了前面所述的奇怪现象。现在的确到了应当了结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所谓“公案”,而给予确定性判断的时候了。从郝晓光的文章发表至今已有近30年,为什么仍然存在着对马克思的这句话的不同理解?说到底是我们没有彻底弄清楚马克思这篇文章,特别是这段话的真正含义。对此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围绕这句话的争论过程及其细节,而最需要做的工作是原原本本地、实事求是地搞清楚马克思的这句话的原意到底是什么——是马克思本人的价值定义,还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瓦格纳的价值概念。我们将从几方面来进行考察:第一是马克思这篇文章的总体主旨;第二是从马克思对这句话的逻辑推导,梳理出马克思给这句话所加的预设前提条件;第三是对马克思本人这句话的评论。任何遵循理性的人们将会发现,这句话千真万确地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瓦格纳的“一般价值”概念,而决非马克思本人所主张的价值概念。
1.马克思此文的主旨:批判将“价值”与“使用价值”相混淆的“一般价值理论”。
1879年出版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评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其劳动价值论。他的批评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无视马克思与李嘉图之间的本质区别,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降格为纯粹经济学上的“生产费用理论”,认为“这个理论(马克思的)与其说是一般价值理论,不如说是来自李嘉图的费用理论。”[3](P400)第二步是站在“一般价值理论”这个哲学的“制高点”上来否定《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他的办法是断言这种价值理论(指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引者注)不是‘一般的’,因为它不符合瓦格纳先生关于‘一般价值理论’的观点。”[3](P400)由此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剔除出“一般价值理论”之外而加以否定。
马克思对于瓦格纳的上述“批评”是如何回应的呢?他首先鲜明地指出自己的价值理论与李嘉图的本质区别:“瓦格纳先生从‘资本论’和季别尔的著作(如果他懂俄文的话)中应该看到我和李嘉图之间的差别。李嘉图实际上把劳动只是当做价值量的尺度来考察,因而他看不见自己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的本质之间的任何联系。”[3](P400)这就是说,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只是商品的成本,因而与哲学上的“一般价值”没有关系。于是瓦格纳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贬低为李嘉图的“费用理论”之后,再用他的“一般价值”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他的“一般价值”指的是“像德国教授们那样传统地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在一起”而得到的抽象概念。马克思对此做了下述回应:“如果瓦格纳先生说,这‘不是一般价值理论’,那末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他是完全对的,因为他所说的一般价值理论,是指在‘价值’这个词上卖弄聪明,这就使他同样有可能像德国教授们那样传统地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在一起,因为他们两者都有‘价值’这一共同的词。”[3](P400)
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一旦按照瓦格纳等“德国教授们”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在一起”来得到“价值一般”的概念,那么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把《资本论》的价值概念从“一般价值理论”领域剔除,从而贬低为与价值无关的李嘉图式的“生产费用”理论,这正是瓦格纳贬低与反对《资本论》的价值理论的办法。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瓦格纳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在一起”所得到的“价值一般”概念,也就承认了瓦格纳对马克思的批评是“完全对的”。由此可见,马克思绝无可能承认这种“价值一般”的概念,因为这等于承认瓦格纳对自己的批评完全正确,自己的价值理论完全错误。
因此,从这篇文章的总体逻辑上看,这种将“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的“一般价值”概念,本来正是瓦格纳反对马克思而秉持的“一般价值定义”,决无可能是马克思的“一般价值”的定义。如果把它理解为马克思的“一般价值理论”,意味着马克思专门写此文,用自己的“一般价值理论”来反对自己的《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这岂非咄咄怪事!
2.所谓“价值一般定义”的前提条件:两个“如果”。
正因为瓦格纳要用他所说的“一般价值”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所以马克思考察了瓦格纳的“一般价值”概念是如何形成的,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段话,其中包含那句被许多人奉为“马克思对价值的定义”的话。让我们原原本本看这段话是怎么说的:“如果说,人们不仅在实践中把这类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且在观念上和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满足’自己需要的物,从而也是‘满足’自己本身的物……如果说,‘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P406)
必须注意:这段话是假设条件复句,即要得到这个“一般价值”的定义,需要两条假设的前提条件:这就是文中的“两个如果”。一旦文中的“两个如果”都满足,于是就会得到这种“普遍的价值”的概念。而那些将这句话理解为马克思本人的价值定义的文章,[6]其根本缺陷正在于没有看到:作为这个“普遍的价值”概念的前提条件的“两个如果”本身根本不能成立,它们正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下面让我们对此作实事求是的仔细分析。
第一个“如果”是:“如果说,人们不仅在实践中把这类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且在观念上和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满足’自己需要的物,从而也是‘满足’自己本身的物”。这实质上就是把物质资料对人的社会性的“实践关系”曲解为单纯认识论上的“理论关系”。马克思在此文中指出,“但是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这种理论关系,正是“人的自然愿望,是要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内部和外部的财物对他的需要的关系。”[3](P405)也就是“抽象的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单纯的直观的认识论关系,也即把客体作为直观对象的认识论关系:在观念上和在语言上认识到客体是满足自己需要的物。然而事实是:人与对象并非仅仅是这种“理论的关系”,更是社会性的“实践的关系”。马克思在此文中清楚地指出,“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3](P405)而是处在“实践的关系”中。因此人不仅是对自然物具有需要的人,而且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作为客体的“外界物”也不是单纯地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纽带。马克思在此文中强调这种“实践的关系”是由物质生产实践所生成的关系:“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3](P405)因此这种“实践的关系”就是通过劳动形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统一体。如果阉割这种真实的“实践的关系”,将其片面地曲解为直观认识论的“理论的关系”(孤立的人对客体的生理心理需要),就撇开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进而撇开了在这个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赋予劳动产品之中的社会联系。由此可见,要得到这里的“价值一般”的概念,其前提条件是对现实的“实践的关系”的阉割,仅仅将其理解为人与对象的“理论的关系”。由这个前提条件所得到的结论——价值一般的定义,当然是马克思一贯反对的错误观念。
第二个“如果”是:“如果说,‘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这就是说,如果把这种观念和语言上的“满足”,“按照德语的用法”叫做“赋予价值”,于是将“使用价值”与“价值”相混淆,那就证明了上述“普遍的价值”概念。这是“按照德语的用法”所产生的对“价值”一词的曲解,而不是普遍的价值本身。
什么是“按照德语的用法”?原来在德语中,“使用价值”用“Gebrauchswert”表述,由Gebrauchs(使用)和Wert(价值)两个词合成。而“交换价值”用“Tauschwert”表述,由Tausch(交换)和Wert(价值)两个词合成,这两个词都含有共同的Wert(价值)一词。这种用法与中文正好相应。马克思认为这种构词方式非常容易产生将“使用价值”与“价值”相混淆:似乎在这两种价值背后有一种“价值一般”(Wert),因而至少使用价值是“价值一般”的特殊形式。为了消除“按照德语的用法”容易产生的这种混淆与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开头,就在“使用价值”条目下特别提出了一个注释:“在17世纪,我们还常常看到英国著作家用‘worth’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表示交换价值;这完全符合英语的精神,英语喜欢用日尔曼语源的词表示直接的东西,用罗曼语源的词表示被反映的东西”。[7](P48)由此可以消除这种语言上容易产生的混淆与误解。因此,马克思认为应当不受德语构词上的这种影响,通过人与外部世界的“实践的(劳动的)关系”,将“使用价值”与“价值”(其在交换中表现为“交换价值”)区别开来,作为同一商品的二重性来理解。
而瓦格纳则在利用“德语的用法”的同时,加上自己的一套语言游戏,从而将上述“‘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直接等于“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瓦格纳把通常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叫做‘价值一般’或‘价值概念’”。[3](P411)“他采取的办法是,把政治经济学中俗语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按照德语的用法’改称为‘价值’。而一经用这种办法找到‘价值’一般后,又利用它从‘价值一般’中得出‘使用价值’。做到这一点,只要在‘价值’这个词的前面重新加上原先被省略的‘使用’这个词就行了。”[3](P406-407)这就是:先将使用价值(Gebrauchswert)中“使用”(Gebrauchs)这个词头去掉以得到Wret这个“价值一般”概念,然后再把这个词头(Gebrauchs)加上。于是“使用价值”(Gebrauchswert)和“价值”(Wert)合并为一个概念,最后导致“‘只有一种价值’,即使用价值。”[3](P411)
而瓦格纳进行这种语言游戏的关键,是通过“财物”这个环节:即“给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财物’的印记同样可以叫做:‘赋予’这些物以‘价值’;瓦格纳正是用这种办法得出‘价值概念一般’的”。[3](P409)这样得到‘价值概念一般’必然与使用价值和“财物”相混淆。由此形成的当然是瓦格纳的“价值概念一般”,而绝无可能是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一般”。马克思所主张的真正的给财物“赋予价值”的过程,绝对不是把外界物认定为“财物”的“理论的关系”的过程,而是物质生产实践过程:即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劳动)把人的生命凝结在产品中,从而赋予劳动产品以价值,其成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纽带。
因此,以上述两个“如果”作为假设前提下,“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而一旦满足了这两个前提条件,我们就坠入到瓦格纳等人的陷阱中了,将“使用价值”被理解为“一般价值”的定义,由此证明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错误的概念。马克思对此写道:“这个蠢汉在耍了这些把戏以后还洋洋得意地继续说道:……从人的需要和经济本性出发,去了解财物概念,并把价值概念合并到财物概念中,争论得那么多的、而且为许多往往不过是虚假的深刻研究弄模糊了的价值概念,就很容易[indeed(的确)]弄明白(不如说)弄糊涂”。[3](P410-411)
所以,我们由此清清楚楚地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出的“价值定义”,是马克思根据瓦格纳的理论立场所导出的“价值定义”,与瓦格纳的思想完全一致。瓦格纳得到这种“价值一般”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它怎么可能是“马克思的价值定义”呢?我们的一些哲学家把这句话视为马克思关于普遍价值的定义,其错在忽视了这个定义的前提条件,忽视了这种前提条件本身的错误。
二、“一般价值定义”的社会心理根源与哲学根源
在假设两个“如果”的前提条件下,得到了瓦格纳用以反对劳动价值论的“普遍价值定义”之后,马克思立刻对该定义的价值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进而揭示了产生这种错误定义的社会心理根源与哲学根源。
其一是社会心理方面的的根源。马克思说:“这个德国人的全部蠢话的唯一的明显根据是,价值[Wert]或值[Würde]这两个词最初用于有用物本身,这种有用物在它们成为商品以前早就存在,甚至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但是这同商品‘价值’的科学定义毫无共同之点。”“这一情况之所以模糊起来,是由于现代高地德意志语中,Wert这个词的没有限制的(错误的)的词尾变化方式成了通常现象;……但是,所有这一切同‘价值’这个经济范畴毫无共同之点”。[3](P416、417)瓦格纳将在日常生活德语的“价值”一词与严格的科学的用语的“价值”相混淆,由此反对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其错误观念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文化基础。我们中文语境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些把马克思所批判的瓦格纳的价值概念当作马克思本人的价值概念的严重错误观念,长期难以得到纠正,也是由于这种语言上的基础。这种语言习惯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解与传播的严重障碍。
正是在这种语言习惯的基础上,瓦格纳将对外界物品标记为“财物”的行为当做“把它改称为‘赋予价值’”的行为,于是导致二者的混淆。而马克思则指出,这并不能把“财物”变成“价值”①参见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马克思原话是:“如果人把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来对待,那末他就把它们当做‘财物’来对待,——瓦格纳这样证明。他赋予物以‘财物’的属性,但是这一行为的内容并不因为瓦格纳先生把它改称为‘赋予价值’而有丝毫的改变。”。而人们之所以把会产生如此概念混淆,源于人们把“财物”当作“价值”来估价的“自然愿望”。他说:“‘人’具有把财物当做‘价值’来‘估价’的‘自然愿望’,这样也就使瓦格纳先生有可能履行诺言,得出‘价值概念一般’”。[3](P407)正是人们的这种对财物进行估价的“自然愿望”,导致瓦格纳“给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财物’的印记同样可以叫做:‘赋予’这些物以‘价值’;瓦格纳正是用这种办法得出‘价值概念一般’的。”[3](P409)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他赋予物以‘财物’的属性,但是这一行为的内容并不因为瓦格纳先生把它改称为‘赋予价值’而有丝毫的改变。”[3](P407)马克思由此道出了那种将“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观念,能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心理基础:语言习惯上的基础,根据使用价值进行估价的“自然愿望”,以及基于直观唯物主义影响而形成的只看到事物表面的“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相符合的观念。应当指出,这些分析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正是对劳动价值论理解与传播的巨大障碍。
其二是直观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影响,这导致瓦格纳用所谓“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推论出“价值一般”。马克思引用瓦格纳的话说:“主观价值或广义的财物价值=财物因……其有用性……而被赋予的意义……这不是物本身的属性,虽然也以物的有用性作为客观前提”,由此论证“主观价值”就是根据物的有用性赋予物以价值。另一方面,“在客观的意义上,‘价值’、‘各种价值’指的也是具有价值的财物”。[3](P411)因此,客观价值指的是物的有用性。瓦格纳由此似乎从“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的一致性“论证了”价值与使用价值(有用性)是同一概念,导致二者的混淆。马克思对这种“推论”造成的混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斥之为“胡说”。马克思是这样讲的:“瓦格纳在把通常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叫做‘价值一般’或‘价值概念’以后,当然不会忘记,‘用这种办法(这样!这样!)推论出来的(!)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他起先把‘使用价值’叫做‘价值概念’一般或‘价值一般’,接着发现他只是就‘使用价值’胡说了一通,从而‘推论出了’使用价值,因为对他说来胡说与推论‘实质上’是同一的思维作用”。马克思最后总结式地指出,瓦格纳的“这一切都是胡说”。[3](P411、412)而这种“胡说”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人们潜移默化地受到直观唯物主义思维习惯影响,只看到物本身对人的作用,只看到物对人的客观有用性(客观价值),以及人对物的客观有用性的认识(主观价值),因而看不到它所负载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力量。只有唯物史观才有可能透过物对人的有用性,看到这个有用性背后所掩藏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一般人是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这种深刻的认识的。这正是瓦格纳的“一般价值概念”的哲学根源之所在。
从上述对《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实事求是、逻辑严密的分析与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到下述确切无疑的结论:把作为物对人的关系的使用价值作为价值哲学的“一般价值”,是马克思所反对和批判的瓦格纳的“一般价值定义”、瓦格纳们所奉行的价值哲学。这种价值哲学将作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价值(例如《资本论》中的价值)排除在“哲学上的价值”概念之外。这种价值哲学的根本错误在于:虽然使用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只是一种“自然价值”。如果将其作为普遍的“一般价值”,那就抹煞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将社会关系理解为物对人的自然关系,违背了社会关系存在的基本现实。用这种违背现实的价值哲学分析人类社会,就会把社会理解为原子式个人的集合体,陷入到以个人主义的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唯心史观。其在经济学上则陷入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庸俗经济学,而在历史观上则会陷入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
三、以“实践二重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
列宁深刻地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8](P312)这句话说出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说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如果说,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哲学以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物对人的有用性)为基础,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地要以马克思本人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的“劳动二重性”思想为基础,因为正是“劳动二重性”使马克思看到了物对人的价值、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将经济领域的“劳动二重性”思想推广到整个社会,可以很自然地得到“实践二重性”思想:人们进行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实践活动,生产出现实的各个层面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意识形态关系、文化关系等等;另一方面,这些各个层面的社会关系的实现又必须通过具体的自然物质过程来进行,从而又是一种自然物质过程,并将生产出自然物质结果——政治实践、军事实践、意识形态上的实践活动(宣传等等),莫不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哲学正是建立在“实践二重性”基础上。
现在,我们简单地概述一下这种以“实践二重性”为基础的价值哲学有哪些最主要的概念与思想。
1.价值的二重性: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
由于实践的二重性,导致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的二重性,即任何现实的事物对人而言都具有双重价值:一是作为物对人的关系的“自然价值”,也即物质本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效用价值乃是这种使用价值的心理表现;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社会价值”,其负载于物上,使物成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纽带,从而形成物质化的社会关系。这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然而在社会实践中的相互统一,构成现实的整体。这才是真正的“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因为它包容、涵盖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价值。现行教科书的价值概念并没有完全错误,只是需要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加以扩大,使之成为由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对立统一过程构成的实体。这种以实践二重性为基础的普遍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可以权且作如下定义:价值是以物对人的自然价值为载体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具有正向意义的社会关系是正价值,具有负向意义的社会关系是负价值。在这里,作为物对人的意义的自然价值是价值的外在形式,而作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社会价值”是价值的内在本质。
以实践的二重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正是上述价值的哲学,它是作为人和人的关系的“社会价值”与作为物对人的关系的“自然价值”的辩证统一;社会价值是价值本体,它以物的使用价值为载体,从而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通过物对人的自然物质过程来实现,由此社会关系过程受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制约,进而产生了人们在社会关系上的主体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统一,产生了历史的规律。这种价值哲学以《资本论》中所确立的劳动价值概念为基础,将其推广到人与人之间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而形成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价值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多层面的,这些多层面的社会关系体现在物中,以物质为载体,从而形成了多层面的价值体系。
2.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层面结构。
由于人类实践是多层面的,因此由实践二重性所产生的价值,也通过多层次的实践展示出来,从而形成了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层面结构。从社会组织层次来分,可以分为个人层次、社会层次和国家层次,乃至国际层次的价值。对此我们需要专门的讨论,在此从略。而从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层面来分,可分为经济关系、人伦关系、美学和文化关系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经济关系及其价值。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价值是社会经济层面的劳动价值,这是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每个人在为他人创造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劳动中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化的生命,它用抽象劳动时间来量度,结成了市场经济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马克思称其为客观存在的“价值实体”(substance of value),简称为“价值”。“价值实体”的概念出现在《资本论》第1卷的第1章第1节的标题中,可见此概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性概念。马克思说:“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7](P65)而这种物化的劳动即是“价值实体”。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7](P61)但并不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存在物,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社会关系力量。“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么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作为客观的社会关系力量,只是以该商品本身的有形构造为载体,通过这一载体而活生生地存在于商品所处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中,并且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客观力量支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生成了形形色色的社会经济现象。价值的客观性“纯粹是社会的”,“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原译文中“价值的对象性”,我认为应当译为“价值的客观性”。此段的英文译文是:“……human labour,that their objestive character as value is therefore purely social.From this it follows self-evideant that it can only appear in the social relation between commodity and commodity.”(Karl Marx,Capital,Translated by Ben Fowkes,Penguin Books,1990.pp.138-139)这里的“objestive character”是“客观性”。。
以劳动价值为基础构成的市场经济关系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在它之上,产生了人们之间其他层面的各种社会关系。各个层面的人与人的关系负载于物质之中,形成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以下各个层面的价值世界。
第二层面是人伦关系价值。这是关于人的社会地位与交往行为的价值。它又可以分为伦理(宗教)、法律和政治三个方面的关系及其价值。所有这些关系及其价值都建立在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之上。
伦理关系是人伦关系的观念基础。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而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产生了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每个人与他人、社会、国家的关系等等。由此决定了他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了对他的行为的要求与期待。于是产生了各种社会地位及其交往行为的价值观念,即道德伦理价值。例如,中国古代的忠孝悌义,古代与中世纪的等级制观念,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革命时期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等。
伦理关系是围绕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责任和义务等所产生的基本价值观念,它要求每个人自觉地按照这种基本价值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强制性关系,即法律关系与政治关系。习近平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9]这种法律关系产生了人们对行为的合法性等相关的价值判断,由此产生了关于法律关系的价值。而社会组织中一旦出现了通过政令实现的权力,便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即围绕政治权力的产生、运行、监督等等产生的关系,于是也就产生了人们对政治交往行为的价值观念。
从总体上说,伦理关系、法律关系与政治关系可以概括为人伦关系,这是直接建立在经济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人们在这些关系上所追求的存在价值,对这些关系中人的行为的是非曲直的评判标准,构成“人伦关系价值”,这是以人的社会地位及其交往行为方式的评价为中心的价值。
第三层面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关系及其审美价值。审美与“美学”(Aesthetics,也可译为“审美学”)是个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我们这里不作深究,仅仅讨论它所关涉的社会关系。对社会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人与人除了物质生活上的经济关系、人伦关系,还有情感交流关系,即每个人总想通过某种感性符号(声音、图像、动作等等)来表达自己的复杂情感,以此引起他人的共鸣;同样,每个人都在接受他人发出的感性符号时,总会发生内心的某种情感冲动。由此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关系,通过感性符号来勾通人与人的精神情感世界。这种情感交流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交往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人们对美感的追求,产生了通过对美感的共鸣而实现情感交流的追求,由此产生审美价值。
上述三个层面的价值——经济关系价值、人伦关系价值、情感关系价值(审美价值)构成了作为社会关系价值的主要内容。而这些价值既然是社会关系价值,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媒介物来实现,这个媒介物,正是社会化的物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物质世界。各种社会关系价值,通过物质载体及其遵循的客观规律,从而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活生生的社会关系体系。
[1]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原理概论(2013年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 陈依元.关于价值、价值认识和价值真理的哲学探讨[J].哲学动态,1984,(6).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 郝晓光.对所谓“马克思主义普遍价值概念定义”的否证——“使用价值概念等于哲学价值”批判[J].江汉论坛,1986,(12).
[5] 郝晓光.从否证到创新——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初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 高飞乐.一桩未了结的学术公案——关于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一段话的解读[J]].东南学术,2000,(5).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列宁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J].求是,2015,(1).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rx's“Definition of Value”and Philosophy of Value
Lu Pinyue
(School of Humanitie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
use value;natural value;social value
The value concept in the current value philosophy of our country regards Marx's work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which regards value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and people.It excludes the“value”in Das Capital out of the“philosophy of value”.This is a misinterpretation of Marx's works.We can rigorously prove that this is indeed the value concept criticized by Marx rather than the value concept of Marx himself.The value of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s the value of social relations,it is carried by the material and make the material socialized,which forms the value lin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The labor value concept in Das Capital is the basis of the value world as a whole and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ethical value(including ethical value,legal value,political value),aesthetic value are formed.The proces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is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of the value world.
[责任编辑 孔 伟]
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互联网背景下的财富革命研究”(项目号:13CZX0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