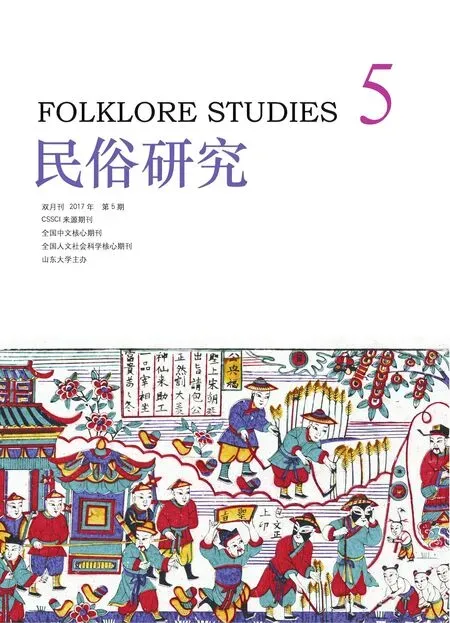历史记忆与“刘三姐”多重文化意象的建构
2017-01-28覃德清
覃德清
历史记忆与“刘三姐”多重文化意象的建构
覃德清
壮族“刘三姐”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主体”与想象空间的社会记忆相交融的文化符号。“刘三姐”被不同的记忆主体记录和想象,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中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扮演不同的文化角色。不同记忆主体的不同历史心性保留或舍弃不同的文化元素,建构了“刘三姐”的不同文化意象。而想象主体隐含的人类审美感知、审美体验与审美记忆的复活,是壮族诗性传统得以延续的文化根基。
历史记忆;刘三姐;文化意象;诗性传统
一、引 论
在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贝茨·洛德(Albert B Lord)关于南斯拉夫史诗歌手的研究成果问世之前,“荷马是谁?”一直是困扰西方学术界的谜团。其实,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拥有各自的或真实存在、或想象甚是虚构的诗性传统的传承主体。现在,帕里和洛德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早期希腊的诗歌都是口头创作,像南斯拉夫杰出歌手阿夫多,能够唱15000行到16000行的长歌,被称为“南斯拉夫的荷马”*[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38页。。回观壮族诗歌的发展历程,壮族历史上同样造就了不计其数的有名无名的歌者,也不乏杰出的歌手,只是他们更多地被不同的记忆主体“记录”和“想象”,被不同的记忆载体“承载”并“延传”,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呈现不同的“文化意象”,而更多的现实生活中诗性传统的“真实主体”是“名不见经传”的歌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历史遗忘了,业已成为匆匆过客而化为历史烟云。因为历史往往是书写一种“胜者为王”的历史和“被支配族群”。
屈服的历史,“普通大众虽然确实是历史过程的牺牲品和沉默的证人,但他们同样也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因此,我们必须发掘‘没有历史的人民’的历史——‘原始人’、农民、劳工、移民以及被征服的少数族群的鲜活历史”。*[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面对21世纪全球一体化时代,针对壮族诗性传统的延续而言,我们需要省思的是壮族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作为诗性传统传承主体的歌者是如何被人的历史记忆所建构的?以“刘三姐”为文化符号的诗性传统缘何呈现多重的文化意象?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如何对诗性传统的延续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
二、关于“刘三女太”“刘三姐”的历史记忆
在众说纷纭的与刘三姐相关的研究领域,与其争论“刘三姐是谁?”“刘三姐出生何地?”“是何族人?”不如超越科学考据的研究范式,将研究的重心由历史记忆的对象转向历史记忆的主体,从历史想象和记忆的视角,分析“刘三姐”的不同文化意象,探寻“刘三姐”是“被谁记忆?”在何种时代语境中形成的历史记忆?记忆主体以何种历史心性建构“刘三姐”的文化意象?因为“历史”是“人们经由口述、文字与图像来表达的对过去之选择与建构。”*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刘三姐”被当做“杰出歌手”,是大多数文人和民众的共同记忆;被当做“神仙”顶礼膜拜,是壮族民间歌者的文化想象;被当做“黄色歌手”,是左倾极权时代“文化暴力”操控的结果。
在壮语中,称“刘三姐”为“刘三女太”,壮族称年轻女性为“女太”(古壮字,音“达”,意为“姑娘”,作为词头冠于未婚女性的名字之前)。清道光年间编纂的《庆远府志》记载:
刘三女太,相传唐朝时下枧村壮女。性爱唱歌,其兄恶之,与登近河悬崖砍柴,三女太身在崖外,手攀一藤,其兄将藤砍断,三女太落水,流至梧州。州民捞起,立庙祀之,号为龙母,甚灵验。今其落水高数百尺,上有木扁挑斜插崖外,木匣悬于崖旁,人不能到,亦数百年不朽。
广东、广西以及周边地区广泛流传着关于“刘三姐”“刘三妹”“刘三姑”“刘三娘”的传说,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王士祯的《池北偶谈》、陆次云的《峒(删洞)溪纤志》都有关于“刘三姐”“刘三妹”的相关记载,民俗学界的许多学者皆撰文探讨过刘三姐传说问题。钟敬文先生认为“刘三姐是歌圩的女儿”。*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11页。农学冠先生指出,刘三姐在封建时代,被封建卫道士当做“风流放荡的女人”,被民众奉为“歌仙”“神巫”,“传说中刘三姐善于作巫,是为了挣脱邪恶势力对她的禁锢和迫害,维护女性做人的尊严;巫觋宣传刘三姐作巫,目的在于扩布自己巫术巫法的影响,无意中也扩布了刘三姐文化的影响;人民群众崇敬、追慕刘三姐,是因为刘三姐具有‘超人’的本领,祈求得到她的帮助,是因为自己的美好愿望,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和幸福。”*农学冠:《岭南神话解读》,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58-259页。在这里,农先生注意到了不同的主体对于刘三姐意象的不同塑造模式。黄桂秋先生认为:“所谓的歌仙刘三姐,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实有其人,而是歌海之乡的各族民众寄托自己愿望的虚拟性人物,是歌唱民族的象征性符号。”*黄桂秋:《桂海越裔文化钩沉》,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第77页。因而,自然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刘三姐歌书文本传世。黄先生还认为,壮族民众对刘三姐的敬仰之情促使刘三姐的神格不断升级,由掌握巫术和魔法的女巫,变成超脱尘世、长生不老的歌仙;由传唱情歌为主的爱神,逐渐演化成保佑航运平安的水神,还有一些地方将刘三姐当作多功能的保护神,人们祭祀刘三姐,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刘三姐是“东方狂欢文化的一种标志性符号。”*黄桂秋:《桂海越裔文化钩沉》,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第77页。过伟先生则将刘三姐定位为“民间文化女神”。*过伟:《民间文化女神刘三姐“六维立体思维”的文化人类学探索》,潘琦主编:《刘三姐文化品牌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覃桂清在《刘三姐纵横》中,论述刘三姐是“广西贵县人”,因为王士祯、孙芳桂、张尔翮等人在各自的著述中都认同刘三姐是“贵县西山人”的说法,覃先生在广东阳春等地调查发现,《肇庆府志》《阳春县志》记载来当地传歌的刘三妹,“来自广西贵县”。广西贵县民众也认为:刘三姐年轻时离开贵县,四处传歌。*覃桂清:《刘三姐纵横》,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43-44页。在“刘三姐”是“虚构的歌仙”还是“真实人物”的问题上,覃先生还倾向于认为“历史上刘三姐是真有其人。”是壮族的“歌圩风俗涌现出一大批‘女儿’,刘三姐是其中佼佼者。”*覃桂清:《刘三姐纵横》,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42-245页。
关于刘三姐的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许多记述者和民间故事讲述者通常将“刘三姐”当作“真人真事”来述说,笔者在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兰靛乡调查期间,当地民众指认“刘三姐”的住处、在家族中的排行、她搓衣服的石板。很显然,此“刘三姐”非彼“刘三姐”,或者说只是当地民众认可的众多“刘三姐”文化原型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实,关于广东、广西以及周边各地民众讲述的“歌仙刘三姐”一系列传说,无疑包含虚拟和想象的因素,覃桂清先生搜集了47条有关刘三姐的传说和歌谣*覃桂清:《刘三姐纵横》,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59-260页。,既说明了刘三姐传说传播的广泛性和漫长的历史跨度,也说明“刘三姐传说”从总体上说是一种虚构的文化想象。因为,现实中真实的生命体尽管长大后可以云游四方,但是,只有一次性的唯一的出生地。另外,人活一世,不过百年,现实中不可能有人跨越时空地“长生不老”。因此,与其从历史考据学的角度论证“刘三姐”其人其事的“真或假”,不如从“文化想象”“历史记忆”的角度,分析“刘三姐文化”体系中,有哪些情节和现象是刘三姐传说讲述者的主观想象?哪些文化元素、文化基因是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可信的历史记忆?由此省思“刘三姐”如何成为集体记忆的主体?如何被想象?被谁想象?始于唐宋时期,延至21世纪以至遥远未来的“刘三姐”文化基因和文化想象,缘何拥有如此漫长而强劲的生命力?
三、被想象和虚构的“刘三姐”文化意象
如果说“可信的历史记忆”是在现实性、真实性基础上合乎文化逻辑的想象,那么,“虚拟的文化想象”纯粹是现实中不可能真实存在的“文化幻想”和“审美幻象”。是因为“历史被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分离出去,成为某种象征和幻象,事实上,这是文化投影的结果,是意识形态对人们与过去的关系进行想象性畸变的结果。”*王杰:《审美幻想问题与心理学解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笔者并不认同黄桂秋先生认为刘三姐“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实有其人”的说法,而更倾向于将“刘三姐”当作是广大民众在歌圩文化背景下想象而成的“典型形象”,“刘三姐”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客观存在的,岭南地区无数女性歌手是“刘三姐传说”的真实原型。关于这些原型的历史记忆是可信的,而超越原型之上的述说是想象和虚构的文化产物。这些虚构和幻象在人们的口述传承中“越传越玄”“越传越真”,但这种“真”只是审美幻想世界的“真”。
譬如,“刘三姐”被奉为“始造歌之人”,显然是“相传”而已,是民众的想象,因为真正的民歌“始造者”,绝不是在唐代。“七日夜歌声不绝”,显得有点夸张;刘三姐的兄长反对刘三姐唱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将刘三姐推下山崖,砍断藤条的情节是想象的。刘三姐与白鹤少年、张伟望、陶、李、罗、石等秀才对歌,有真实的现实基础,而与对歌者“俱化为石”,显然是民间众多“化石”传说母体的套用。
因此,“刘三姐”文化基因和文化现象的孕育、萌芽、生成、传播,经历了千百年的漫长历史演化,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民众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刘三姐文化序列”的创造与传承,都将自己的文化认知、历史记忆、文化想象、审美体验和情感寄托渗入其中,刘三姐成为一种“箭垛式”的人物,凝聚了无数虚拟的情节和想象的元素。刘三姐文化形象的可塑性、变异性、复杂性、多元性,一方面给人们带来认知其文化本质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为后人的重新阐释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譬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中国笼罩在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时代语境中,国民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强化了《刘三姐》的阶级意识。传说中与刘三姐对歌的秀才,本是平等、友好的歌友,甚至一同化石成仙,在电影《刘三姐》中被改编成不同阵营的相互对立关系,在对歌中相互挖苦、嘲讽,秀才们丑态百出,落荒而逃。而观众们觉得这是影片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这种文学创作切合时代的潮流,尽管是虚拟的想象,却得到人们的认可。
在“文革”期间,“刘三姐”又被想象成“毒草”,能用山歌唱倒“地主阶级”,将《刘三姐》当作是“反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蒙上许许多多莫须有的罪名,电影《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受尽人生的折磨。这种现象基于极左思潮的干扰,是社会变态的表征。
历史进入21世纪,“印象·刘三姐”从2004年3月20日正式公演,至今已有10多年的历史,有道是一个创意“十年十个亿”,作为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比起电影《刘三姐》,离真实历史记忆中的“刘三姐”更加遥远。“印象·刘三姐”的核心策划人梅帅元、张艺谋虽然声称“向自然致敬、向传统致敬、向人性致敬”,但是,只是借用了传统电影《刘三姐》的一些对歌作为母题和素材,增加了制作者更多的文化想象的成分,壮族、侗族、苗族的文化元素也被融合到演出过程当中,为了吸引游客,还增加了“浴女婚俗”等作为吸引游客的噱头,试演时月亮船上的“脱衣舞女”表演,更是引起大量的争议,有记者撰写《刘三姐·歌仙·脱衣舞女》的短文,认为有女子“披着一缕轻纱,由远而近,飘然出现在梦幻般的江面上……是对刘三姐的不敬,是对赞美劳动、歌唱爱情的淳朴民歌的亵渎。”*缪新华:《刘三姐·歌仙·脱衣舞女》,《光明网》2003年12月10日。后来,编创者在实际演出中作了改进,但是,这种虚拟和想象显然迎合了消费时代的文化趣味。
“刘三姐”反复被当作“文化符号”原型而被重新想象,这种文化再生(regeneration),既显示了“刘三姐”文化基因的强大生命力,也意味着“刘三姐”拥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提供给后人巨大的想象空间。因而,诗性传统的承载主体虽然离不开历史上真实生活中的民间歌手和虚拟世界的“刘三姐”,但是,更重要的是承载“刘三姐”历史记忆的广大民众。社会大众关于“刘三姐”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是梅帅元、张艺谋等人编创“印象·刘三姐”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印象·刘三姐”持续十多年演出成功的根本保证。
四、可信的历史记忆中的“刘三姐”文化意象
刘三姐原本是在岭南地区的民众中流传的民间传说和民间信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刘三姐》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经作家的改编,以彩调剧和电影的形式,登上大雅之堂,得到官方的广泛认可,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赞赏。文革期间,“刘三姐”被打入冷宫,受到严厉批判。改革开放之后,“刘三姐”成为文化品牌,虽然有人高喊走出“刘三姐怪圈”“刘三姐圆圈”*常弼宇执笔:《别了,刘三姐》,《南宁晚报》1989年1月5日。,但是,并不能抹去世人对刘三姐的深刻记忆,不能扭转对刘三姐多元化的改编趋势,特别是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连续十多年演出成功,取得令国人震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展现区域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而历史记忆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记忆本是心理学的概念,是人类大脑对过往发生的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造成的心理印痕的回顾、编码、存储和重新叙述。大脑活动是个体行为,是个体性的现象,而人是社会的人,除了少数远离群体的隐居者,人们通常聚集而居,由此生成基于家庭、宗族以及其他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为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特定成员所分享,是立足于现在而对历史往事的一种回忆、重述和建构。
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与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密切相关。历史记忆源于历史事实,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人的大脑中的投映。王明珂先生认为:
“历史记忆”或“根基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此“历史”的起始部分,也就是群体的共同“起源历史”。“起源”的历史记忆,模仿或强化成员同出于一母体的同胞手足之情;这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它们以神话、传说或被视为学术的“历史”与“考古”论述等形式流传。*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在壮族民间,刘三姐传说是作为解释歌圩起源的原因而存在,显然这不是歌圩起源的历史真实,而是满足人们解除疑惑的心理需求。这种心理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答案是想象的产物。正像许多民族中流传的关于太阳、月亮和星星的故事,这种故事本身是虚构的,而太阳、月亮和星星是客观存在的。包括壮族在内的南方民族的现实生活中无可置疑地有许许多多擅长歌咏的女性,她们是民歌文化的创造和传承的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歌圩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壮族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杰出女性歌手从壮族先民走出蛮荒岁月开始,就同特定群体中的男性歌手一起开掘了壮族民歌文化发源的先河,她们在壮族历史记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关于她们的生平事迹的传闻也是屡见不鲜的。南方各地关于“刘三姐”“刘三妹”的传说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事实基础上诞生了。
所以,不同时期与不同地区都有杰出的女性歌手,各个地区的民众传承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以女性歌手为主角的传说,刘三姐传说的讲述者因为生活背景的差异和讲述重点的不同,加之听众的不同,往往塑造了人物形象基本统一的情况下的不同细节。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历史真实(historical reality)的同时,也难免会出现想象和虚构成分。因为:“在对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关系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注意到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亲历者本身也是有主体性的,历史事件亲历者对已经逝去的历史事件的回忆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来环境因素的影响,难免不带有片面性。”*张荣明:《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何况壮族杰出女歌手不计其数,她们的事迹进入成千上万人的记忆之中,而这种记忆的复活以及再生,有意无意间掺杂了主观想象的因素。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原本的真实,但是,并不能够由此质疑原本人物及其事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历史记忆通常是对历史碎片的拼合与复原,其拼合结果呈现的口述序列构成的整体往往是真真假假元素的混合体,因需要借助“慧眼”,辨清历史记忆中,哪些是记忆主体所展现的虚拟表象?哪些是隐含其中的历史真相?
对于刘三姐传说而言,历史的久远性、地缘的广阔性以及传承主体的多样性,导致其中包含着数不清的变化因素,每一次口头讲述和每一篇文献记载资料,都有不尽相同的故事情节,不变的可信的母题是“能歌善唱”“聪颖可爱”“秀外慧中”“情深而刚毅”。
譬如,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载:
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年间。年二十,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酬和而去。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尝往来两粤溪峒间,诸蛮种族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言语,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倡和,某种人奉之为式。*屈大均撰,李育中等注:《广东新语注》卷八,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5页。
以上记载,可以推知的地名、姓名、生年、“善为歌”、“解音律”、“往来两粤间”、和歌者众多、懂得多种语言,等等,这些内容大体是可信的,至少是合乎岭南民俗中隐含的文化逻辑。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记载:刘三妹“居贵县之水南村,善歌,与邕州白鹤秀才登西山高台,为三日歌”*王士祯:《池北偶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259页。。张尔翮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中记载:刘三妹“生于唐中宗之神龙元年。甫七岁,即好笔墨,慵事针指,聪明敏达,时人呼为女神童。年十二,能通经传而善讴歌,父老奇之,偶指一物所歌,顷刻立就,不失音律”*(清)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四四卷,第074册,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7年。。这是壮乡歌海人们“以歌代言”“出口成诗”之文化智慧的折射,现实中不乏其人。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中将“刘三妹”与白鹤秀才对歌的地点确定为“粤西七星岩绝顶”,可理解为是民间传说的异文。这些记载通常可信,只是更可能是另一个“刘三妹”,是构成“刘三姐”形象的原型之一。
刘三姐传说更多的是在民间以口述的方式传承,这些作品经当地文人收集整理而保存下来,同样展示了民间记忆中刘三姐的风采。广西宜州民间传说认为,刘三姐生于唐朝末年,原住罗城,后受人逼迫,移居宜州中枧存,喜欢唱歌,其兄以为对歌惹事误工,强力反对,但也改变不了刘三姐嗜歌的天性。广西扶绥、贵县(贵港)、桂平、恭城、马山等地的刘三姐传说,其情节单元大体上包括:三姐酷爱唱歌、遭家兄反对;遭坏人逼婚,三姐抗婚、逃婚;与外地歌手对歌,三姐获胜,外地歌手将歌书遗弃;或对歌不止,升天成歌仙。这是岭南民间对刘三姐具有共性的历史记忆,也是相对稳定的刘三姐文化基因,构成刘三姐传说文化谱系的核心主轴。
因为民间口述传统自身具有变异性和文本的多样性,由此产生的逼婚者、对歌者、对歌场域的不同,不能因此而质疑这些故事情节的文学想象的真实性和历史记忆的可信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排演的彩调剧《刘三姐》和拍摄的电影《刘三姐》,增加了更多阶级对立的情节以及其他基于当时社会语境的文学创作因素,使得“刘三姐”的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形象更加丰满,影响范围更加广泛,总体上也并不违背千百年来形成的关于刘三姐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逻辑。譬如,“山歌只有心中出,哪有船载水运来”“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弯又多”“黄蜂歇在乌龟背,你敢伸头我敢锥”“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绣球当捡你不捡,两手空空捡忧愁”等等诗句,以绝妙的诗性语言展现了壮族社会文化中隐含的能歌善唱的诗性智慧、不畏强权的顽强意志、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热切渴望。
因此,一千多年来,从“刘三女太”到“印象·刘三姐”,讲述的情景和展演的语境发生了跨越时空的转移,但是,其内在的审美意蕴和以对歌为核心的主题思想均未发生实质变化,内在的稳定性因为得到民众审美心理的认可而不断换发新生活力。
五、审美记忆重构与“刘三姐”文化意象的延续
壮族民众对“刘三女太”的历史记忆,底蕴深厚,流传久远,世人对“刘三姐”始终怀着充溢审美意蕴的文化想象,其内在的文化动因在于壮族以及其他民族对于“女性”“女神”“歌仙”的深刻历史记忆,对于人类美好文化意象的普遍性的尊崇与敬仰,而现代理性思维对诗性思维的渗透与消解,更激起世人对诗性传统的珍惜。
“刘三女太”“刘三姐”作为女性的杰出代表,在男性与女性构成的二元世界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从性别角度审视,男女婚配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前提。壮族的诗性习俗与男女婚恋始终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异性之间的情歌对唱对婚姻的缔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壮族歌圩起源于对偶婚时代的异性之间的对唱,女性歌者和男性歌者构成二元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女性或没有男性参与,就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歌圩。女性歌手需要同性歌师的指点,而男性歌手对于女性歌师则是怀着追慕之心。“刘三姐”由此获得男女歌手的共同尊重,进入男性和女性的心脑记忆之中,“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的。就像上帝需要我们一样,记忆也需要他人。”*[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0页。南方民族较少受到“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将杰出女性奉为神灵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刘三姐”实际上是壮族真实生活中的女性歌师和文化虚拟空间想象性的诗性传承主体的融合体。真实的或虚拟的“刘三姐”对于诗性传统的生成与延续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现实世界无数的壮族歌者是实实在在的壮族诗性文化的承载者,正是不计其数而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歌手、歌师、歌王,构成了壮族审美记忆和历史记忆的文化主体。
壮族民间素有“天上刘三姐,人间黄三弟”的说法,黄三弟*黄三弟(1907-1971)原名黄河清,因在家中排行第三而称“黄三弟”,祖籍广西宜州,其先辈迫于生存压力,历经辗转而定居柳城县凤山乡赶羊屯。这里地处柳江河畔,壮汉杂居,壮族歌圩文化底蕴深厚,村边鲤鱼冲是歌者集会对歌之处,是举办歌圩的场所。黄三弟从小就深受歌圩文化习俗的熏陶,看惯了人间的酸甜苦辣。黄三弟因为家境贫困,没有上学机会,因而不识汉字。他七岁给财主打短工,到十五六岁,开始外出打长工,增加了社会阅历,增长了见识,也有更多的机会向其他歌手学习唱歌,磨炼自己的歌唱本领,在歌师张天恩的开导下,黄三弟的歌艺不断长进,歌咏天赋得到深度激发。到20岁左右,黄三弟已经养成“以歌代言”的心灵习性,能够遇事唱事,见物唱物,即景抒怀,歌随口出,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高。1932年,时任广西省府建设厅厅长的伍廷飏因其“天资敏慧”而称之为“平民文学天才”。是壮族历史上唯一与“歌仙刘三姐”相提并论的著名歌王。刘三姐实际上是在大量原型基础上被“想象”歌者的化身,黄三弟则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但是,黄三弟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也被想象成不同的社会角色,尤其是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操弄使之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境遇。
黄三弟一生乐于服务乡里,用超群绝伦的歌才传播着喜庆和欢乐,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用心传授歌唱技艺,培养民歌传承人;用山歌调解家庭矛盾、劝人向善,使社会和睦融洽;将山歌作为武器,与恶人斗智斗勇,惩恶扬善,救人于危难之间,在桂中壮族地区备受民众的拥戴。但是,在文革期间,在人性颠倒、是非混淆、社会变态的残酷岁月中,黄三弟被别有用心者被污蔑为“广西最有名的黄色歌手”,受尽折磨,身心俱疲。从“想象主体”和“真实主体”互动的角度审视,“刘三姐”的原型是大量的女性歌手,是人们借助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塑造的杰出歌者;而黄三弟是真实的生命个体,被人们奉为“人间歌王”。如同壮族许多地方的民众将刘三姐延请进庙宇中立神像予以供奉,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主体”黄三弟也以“想象的主体”刘三姐作为顶礼膜拜的偶像和心灵的寄托。文革期间,监视他的人强行闯入家中,并将刘三姐雕像丢入火中,黄三弟的心灵支柱轰然坍塌,悲愤至极,含冤辞世。
因此,无论诗性传统的“想象主体”,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主体”,都寄寓在特定的时空语境中,每个人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表达都同特定的社会历史相关联。他们的人生际遇摆脱不了他们寄寓其间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更摆脱不了国家力量和政治势力的操弄。
从审美记忆的生成和重构的角度审视,刘三姐因其超群绝伦、无人能比的歌唱本领而成为文化想象世界“美的化身”,体现了美的本质而超越了历史时空与民族边界,“刘三女太”无疑是壮族的,而作为文化符号的“刘三姐”既属于壮族,又超越了壮族,成为汉族乃至人类共同接受、共同欣赏的“美的象征”“美的隐喻”“美的符号”,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审美文化基因的凝聚。从四面八方、从世界各地来观看“印象·刘三姐”的游客,实际上映现了人们喜爱山歌、崇拜歌艺超群者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所有人类成员都或多或少携带着诗性基因的文化密码,也都具有对诗性世界的文化想象和文化体验,因而也成为诗性历史记忆的承载体。换言之,具有人类普同性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都以不同的显现方式参与诗性传统的延续,都对以“刘三姐”作为象征符号的诗性基因之久传不衰,发挥各自的助推作用。
在21世纪初叶,“刘三姐”的历史记忆借助“印象·刘三姐”山水实景演出而得以复活,还不只是由于梅帅元、张艺谋等人的成功策划,更重要的是在人类诗性传统趋于崩解的时代语境中,重新唤起人们的诗性情怀。现代社会以物为主体的理性思维占据人类的精神世界至少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都市化、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都市人生活在钢筋水泥构成的栖居空间。远离了山水田园,告别了诗情画意,但是,人类的诗性想象和诗性精神饱经风霜却未曾歇绝,虽然萎缩却还余绪犹存,诗境消失与诗情枯竭,更令诗心和诗意变得珍贵,诗人边缘化与诗作平庸,更让世人期待有诗性杰作问世。“印象·刘三姐”顺应了这样的文化语境,因而实现文化的逆袭,在喧嚣中展示静谧的诗性意境,在诗性文化边缘化中唤醒人的诗性情怀和诗性历史记忆。
农学冠先生指出:
这些歌,以优美的旋律、优美的音韵、优美的歌词,唤起了一切善良的人的美好心灵!古代人依恋刘三姐,是她的潇洒多情的感染,是美好理想的寄托,是智慧力量的激发。当代人依恋刘三姐,是她自由发挥的个性的召唤,是她无穷创造力的显现。刘三姐,是我国岭南的山茶花,是广西人民审美的结晶。维纳斯、祝英台、朱丽叶……都无法取代她的位置。刘三姐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优秀遗产。*农学冠:《刘三姐文化初论》,潘琦主编:《刘三姐文化品牌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壮族诗性传统得以延续的文化根基是人类审美记忆的复活与重构。历代壮族歌师的敏锐审美感知、审美体验和审美表达能力,促进了民歌的传承、发展。而在民族文化式微的时代语境中,唤醒年轻一代的审美文化记忆,重塑年轻人的心灵世界,将对壮族诗性传统的延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六、结 论
历史记忆与文化延续存在密切的关联,文化延续需要历史记忆作为人文根基,而文化延续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历史记忆的重生。至为关键的是要了解历史记忆的主体、历史记忆生成的方法与路径。与历史记忆相对应的是忘却,记忆主体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选择不同的记忆对象,被选中进入记忆过程的文化事象往往获得了延续和传承的机会,而没有被选中的历史事实必然就被遗忘而化为云烟。历史记忆具有历时性与选择性,记忆借助口传心授、音影图文诸多载体而代代相传。每一位有记忆能力的正常人都是历史记忆的主体,壮族诗性传统的延续确实有赖于历史记忆的有效支撑以及审美文化的现代重构。
[责任编辑 龙 圣]
覃德清,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桂林 54100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诗性传统与文化建设的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4BZW170)的阶段性成果;壮族诗性传统研究系列论文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