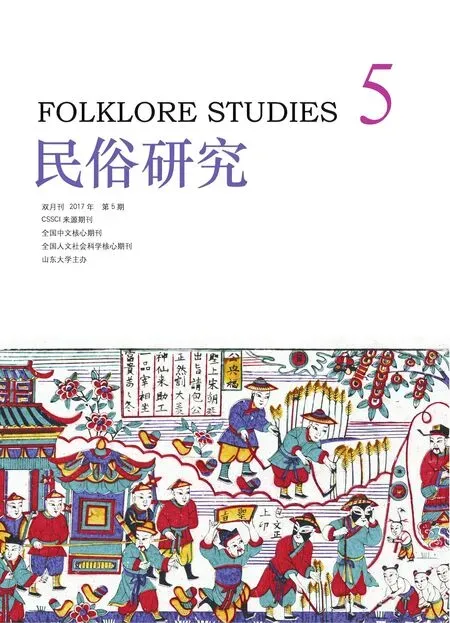观念与思想:汉代虎形肖形印的解读
2017-01-28赵洋
赵 洋
观念与思想:汉代虎形肖形印的解读
赵 洋
汉代虎形肖形印的图形内容具有较强的重复性,这些图形来源于汉代人的历史记忆,是汉代人观念、思想的承载物。在汉代普遍的观念与思想影响下,出现了多类以虎为题材的肖形印,具体有“人搏虎”题材、“突出虎纹”、“白虎”题材等,这些虎形肖形印体现出汉代人的尚武精神、辟恶御凶观念、祥瑞思想等,同时,汉代虎形肖形印的寓意与功能也与汉代人普遍的观念和思想密不可分。思想史视阈下的肖形印解读与研究是拓宽肖形印研究途径的一种努力。
汉代;虎形肖形印;图形;观念思想;寓意功能
肖形印是古代印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单纯从肖形印的图形内容来看,其包含的内容繁多,既有禽兽、虫鸟、草木等自然之属,又有角抵、农桑、宴饮、歌舞、轺车出行等人事之属,除此之外,另有神人、神话等异类幻化之属。在汉代肖形印中,以虎为题材的肖形印众多,这一题材之下又有多个不同的小题材,如人搏虎、人御虎、单一虎形、子母虎、四神印中的虎形等等,在这些具体的题材中,印章的图形趋近重复,具有规律可循,且印章存世较多,成为我们窥探肖形印相关问题的范例。
一、思想史视阈下的虎形印解读
在汉代肖形印中的,虎形肖形印占有的比重很大,图形的重复性也很强,为何在汉代会出现此种现象?虎形肖形印该如何解读?虎形肖形印是否能够体现出汉代人的一般思想?这些是我所关注的重点。我将试图从以下三个类型的虎形肖形印入手,解读其所蕴含的寓意,一是“人搏虎图形”肖形印、二是突出虎纹的虎形肖形印、三是白虎图形的虎形肖形印。
1、除虎患、大校猎与尚武精神:人搏虎图形肖形印
人搏虎类型的肖形印印面虽有方圆之别,然其图形颇为类似,圆者多取人物与虎形左右对称,依印面圆转而体势变化。方者亦与圆者相类似,人物与虎形左右各占一半空间。在以上两种模式中,内容又有两种,一是人物作赤手空拳搏虎貌,二是人物手持某种兵器或器具,刺向对面之虎,作刺虎貌者多见之于方形印面中。在“人搏虎”类型的肖形印中,几乎每一方印章之内容、布局、样式都能找到与之相类似的另一方印章,如果将一些细微的细节之处忽略不计,如人物躯体的弯曲度、老虎四肢的长短等,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印章的内容反复出现,图形具有重复性。以上这些印章虽然很难断定全部为汉代之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考察,从虎患的发生,到社会中搏虎、杀虎,再到角抵、校猎之风的盛行,是战国至汉代都面临的问题,并且至两汉时期,上述各种事件与活动都更为普遍,尤其是在角抵、校猎中人与虎的较量达到顶峰。基于此点,我们将上述印章放置在汉代人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中来考察,至少不会脱离这些印章的本意过远。
除在肖形印中存在众多人搏虎、刺虎的图像模式外,在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中亦存在大量人搏虎、刺虎的图像,这些图像与人搏虎图形的肖形印共同构成了两汉人对虎的态度。
人搏虎的图形模式与先秦至汉代社会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古时虎行于山林草泽,多为人患,古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免受其害。至两汉时期,虎患仍然有增无减,虎为人患时常见诸文献。《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载九江郡之虎患,“郡多虎豹,数为民患,常设槛阱而犹多伤害。”*(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412页。同时在汉代,虎之出没于道路,以至行旅不通,《后汉书》卷七十九《刘昆传》载“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刘昆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550页。更有甚者,虎径行于皇陵,危害卫兵,《后汉书》《五行志》刘昭注引《袁山松书》云:“光和三年正月,虎见平乐观,又见宪陵上,啮卫士。”*(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65年,第3286页。有虎患,就有搏虎、杀虎之事,早在先秦时期,古人搏杀恶虎而求安宁已多为常见,如《孟子》中所载“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清)焦循撰:《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988页。在汉代,搏虎、杀虎除以力搏之外,尚有以方术制虎,《后汉书》卷八十二《徐登传》记载:“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方。”“越方”即禁咒之术,唐李贤等引《抱朴子》注曰:“道士赵炳以气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不伏地低头闭目,便可执缚……越方,善禁咒也。”*(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徐登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742页。
古人一方面深受虎患,故有搏虎、杀虎之举,另一方面,在搏虎、杀虎的过程中,人的尚武勇猛之精神得以流露体现。在汉代,武士搏虎、杀虎或方士以方术制虎,具有普遍的社会认同,尤其是在虎患与尚武的背景下,人们对于武士搏虎,多有歌颂,这在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中都有表现。汉代人对于搏虎之事,除了最朴素的除虎患的原因外,在基于游戏心态的校猎活动中,搏虎也成为风行之事。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古人在搏虎过程中即已经带有校猎游戏的性质,《诗经·大叔于田》云:“叔在薮,火烈具举,袒裼暴虎,献于公所。”*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只不过这一心理到两汉时期变得更为普遍而已。汉代上至帝王诸侯,下至民间百姓,一面因迫于虎患而搏虎,一面基于游戏心态而斗虎。《汉书》卷十《成帝纪第十》载元延二年冬(公元前11),汉成帝刘骜行幸长杨宫与胡客大校猎,颜师古注曰:“校猎者,大为阑校以遮禽兽而猎取也。”*(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十《成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327页。又,司马相如《上林赋》:“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汉)司马相如著,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5页。《子虚赋》又云:“有白虎玄豹,蟃蜓躯犴,于是乎乃使剸诸之伦,手格此兽。”*(汉)司马相如著,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页。由此可知汉代帝王在搏杀猛兽中的游戏态度。西汉初期,帝王即已建造“虎圈”以豢养猛虎,《汉书》卷五十《张冯汲郑传》载:
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人也,与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者。文帝称善,拜释之为谒者仆射。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张冯汲郑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307-2308页。
由此可知西汉初期不仅设立虎圈,还有专人管理。《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载武帝亦建造“虎圈”以为乐:
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245页。
汉武帝“虎圈”规模宏大,这个大“数十里”的“虎圈”当作豢养猛虎之用,《太平御览》卷第一百九十七引《汉宫殿疏》曰:
有彘园,有狮子园,武帝造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长二十步,西去长安十五里。*(宋)李昉等纂:《太平御览》第一百九十五卷《居处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840页。
《汉书》卷六十八载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时“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0页。《汉书》卷八十九《龚遂传》亦载刘贺“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十九《龚遂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638页。虽然在龚遂看来,刘贺此种奢靡放荡的生活是“所为悖道”,但从此处也能体会到汉代帝王追逐“弄彘斗虎”的刺激。在汉代不仅帝王以建造“虎圈”、“弄彘斗虎”为乐事,民间百姓亦效仿之,恒宽《盐铁论·散不足》载:
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玩好无用之器,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六“散不足”第二十九,中华书局,1992年,第349页。
汉代从帝王到庶民的搏虎体现了汉代人对虎的复杂态度,一方面是虎患对人们日常生活造成诸多不便与伤害,另一方面,人们在与虎搏斗的过程中逐渐由现实利益考量转变成基于游戏心理的游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汉代人“尚武”之风的盛行。除此之外,汉代人在搏虎中,带有一定的主体意识,人定胜虎是这一过程中突出要表现的主体。“人搏虎”题材的肖形印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2、辟恶御凶:突出虎纹的虎形肖形印
虎最大的生物性特征莫过于纹饰相错的虎皮,古人对虎皮、虎纹的认识是经过了一个神化过程的。汉代虎形肖形印中有一类虎形印的图形着重突出虎皮的纹饰,虎爪亦较为突出,而虎首作简化处理,由此可以看出,这一类虎形肖形印所要突出的重点是在虎纹上。古人对这类虎形肖形印作如此处理,和其他类型的虎形肖形印有所区别是有其原因的。
虎作为百兽之君,以其勇猛辟恶著称,从先秦时期开始,行道多以虎皮为装饰,取其勇猛有威仪之意,《礼记·曲礼上》载先秦行军之时:
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页。
“前有士师,则载虎皮”成为了汉代人历史记忆中的一部分,司马相如《上林赋》云:“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汉)司马相如著,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5页。汉代帝王出行时的前驱“皮轩车”即是以虎纹为标志,《宋史·舆服志》云:
皮轩车,汉前驱车也。冒以虎皮为轩,取《曲礼》前有士师,则载虎皮之义,赤质,曲壁,上有柱,贯五轮相重,画虎文。
在汉代,虎皮与虎纹已经具备了某种政治性功能,虎的威仪与统治者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可知汉代肖像印突出刻画虎的虎纹,也是有其大的社会背景。从风俗角度来看,在汉代虎皮与虎纹也完全具备了趋吉避凶的功能与寓意。虎能够除恶鬼,辟不祥,其最主要的“法力”即是来源于虎皮与虎纹,王充《论衡·订鬼》: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黄晖:《论衡校注》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90年,第939页。
在汉代人看来,在门上画神荼、郁垒二神以及虎可以起到御凶的作用,作为民俗,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后代,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载:“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聻字,谓阴刀鬼名,可以息疠也。”*(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代《赤雅》云:“肉翅虎,出石抱山,晨伏宵出……身虎文,饰其皮以辟百鬼。”*(明)邝露《赤雅》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汉代的人们不仅认为虎能“嗜食鬼魅”,还认为烧虎皮和水饮下能够辟恶,应劭《风俗通义》卷八云:
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执抟挫锐,嗜食鬼魅。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卷八“祀典”“画虎”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368页。
我们认为,汉代突出虎纹的虎形肖形印的产生与辟恶御凶密不可分,辟恶御凶也成为这一类虎形肖形印的主要功能之一。
3、至信之德与天瑞之徵:祥瑞观念下的汉代白虎图形肖形印
在汉代虎形肖形印中,有一类虎形印章存世较多,此类虎形肖形印的图案也具有固定的模式,图案趋于重复,具体是虎形体积硕大,其一般样式为方形,虎形依印面亦作方形盘曲,尾部较长,呈方折状,尾部在整个虎形图形中较为突出;虎身所占空间较大,口部张开,眼部着重刻画,部分虎形身体中有虎纹,温廷宽先生将其称为“白虎”是有一定道理的。*温廷宽:《中国肖形印大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1页。
在汉代之前,古人已经相信白虎为仁兽之一,《诗经·召南·驺虞》即有“于嗟乎驺虞”*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3页。之句,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三云:
今按,驺虞,白虎黑文,亦通名白虎,以为玉饰,字作琥。《周官》以玉作六器,云以白琥礼西方。*(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三“驺虞”,中华书局,1989年,第105页。
由此可知,在古代,白虎即为驺虞,是虎的一种。驺虞又被古人称作“酋耳”,此外别名另有多种,《困学纪闻》卷三“诗”条云:
驺虞,驺吾,驺牙一物也,声相近而字异。*(宋)王应麟撰,(清)翁元圻注:《翁注困学纪闻》卷三“驺虞”条,世界书局,1996年,第157页。驺虞,驺吾,驺牙为一物又可从古代读音证之,宋代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清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七“驺虞”三云:“虞者,吾声之转,吾有牙音。”由此可知,驺虞,驺吾,驺牙虽名异而实为一物。
那么白虎驺虞具体有何特征?据《山海经》卷一二“海内北经”载:
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彩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虞,乘之日行千里。*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2年,第368页。
许慎《说文解字》卷五:
虞,驺虞也。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食自死之肉。*(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03页。
驺虞因食自死之物,不食生物,不履生草而被看作仁兽,又因其此种秉性,而被加以延伸,成为人的德行之一。古人认为,驺虞为天降祥瑞,人有至信,则驺虞为祥瑞而至,故《毛诗正义》卷一“于嗟乎驺虞”下有孔颖达“驺虞之为瑞应,至信之德也”*《十三经注释·毛诗正义》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之言。
汉代,受谶纬思想的影响,祥瑞观念深入人心,作为祥瑞之一的驺虞“有道则见,非时不出”,不免在此时被人借题发挥,在汉代一些著述中,驺虞作为“天瑞之徵”而出现,如司马相如《封禅文》云:
般般之兽,乐我君圃。白质黑章,其仪可喜。文文穆穆,君子之态。盖闻其声,今视其来。厥涂靡从,天瑞之徵。兹尔於舜,虞氏以兴。*(汉)司马相如著,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5页。
《汉书》中多次记载白虎驺虞这一祥瑞的出现,《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
时(元康元年,公元前65),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牙、爪,上为立祠。*(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249页。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八: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259页。
白虎的出现一方面是帝王为宣扬其德行、德政而作的政治性措施,另一方面,白虎驺虞本身“外猛而威,内仁而信”的秉性深入到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之中,在此两个前提下,白虎肖形印的出现即是自然之事。白虎驺虞作为“仁兽”之一,在后世更是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六《酋耳兽》载:
唐天后中,涪州武龙界多虎暴。有一兽似虎而绝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杀之,亦不食。由是县界不复有虎矣。录奏,检瑞图,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则杀之也。*(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二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白虎肖形印的出现及其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祥瑞观念的影响下,白虎的“仁之至”的德行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二是白虎“有虎暴则杀之”的能力又成为古人心中安全的“保护神”。
二、汉代虎形肖形印的寓意与功能
对于肖形印的功能言人人殊,难以有确凿的解释,诸如图腾说、封泥说等,笔者不太赞成非得对肖形印的功能作出明确解释的做法。如要将肖形印作为图腾标志,那么要讲出是谁的图腾,这在目前显然是难以做到的;封泥说则显得模棱两可,在汉代,印章作为封泥之用的观点是无可动摇的,既然任何印章都是作为封泥之用,肖形印自然也不例外,封泥说只不过是指出了肖形印的使用方式,而非功能。在不可证实肖形印确切功能的前提下,笔者更希望从肖形印的寓意与功能两者之间讨论这个问题。肖形印的寓意与功能密不可分,又很难分清二者的界限,对于此二者的讨论更不能脱离汉代人的一般思想观念。从大的方面来看,虎形肖形印的主要寓意与功能不外乎两类,一是趋吉避凶之用,二是升天长生之用。
虎形肖形印趋吉避凶的寓意与功能的形成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从殷商时期人们对虎的敬畏到汉代虎患的蔓延,再由除虎患到基于游戏的心理而搏虎、斗虎,趋吉避凶始终贯穿于古人的思想中。汉代两面印中,一面作“出入大幸”,另一面作人搏虎肖形印,可以看出,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虎形肖形印在人们的出行中,扮演着“趋吉避凶”的寓意与功能。佩印以避凶是汉代印章的一个常见的功能,在汉代或者更早一点的秦代,道教教团形成的前期,方士即已经使用“天帝使者”、“天帝神师”、“天帝杀鬼之印”、“黄神越章之印”等印作为除凶辟恶的手段,《抱朴子》卷十七《登陟篇》有一段广为人知的记载:“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祸福者,以印印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313页。我们认为汉代虎形肖形印的功能与“黄神越章”等宗教印类似,也是汉代人谋求趋吉避凶的一个重要方式。《十钟山房印举》“举之十四”收录二方两面印,其中一方一面作单一虎形肖形印,一面为“出入吉利”文字;另一方一面作人搏虎肖形印,另一面为“出入大幸”文字。“出入吉利”与“出入大幸”皆为古人在行道时所使用的文字,显而易见,肖形印另一面的虎形图形与人搏虎图形带有在行道中趋吉避凶的功能,这正是肖形印趋吉避凶作用的表现。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本文所论述的几类虎形肖形印的寓意与功能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在这几类肖形印中,其寓意与功能是相互渗透,彼此联系,只不过在思想与观念的视角下,其图形的寓意有各自强调的范围。同样,汉代其他题材的肖形印其寓意和功能与虎形肖形印也有着彼此重合之处,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不同题材的肖形印都是在汉代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同时又都是汉代思想观念的承载物。
三、谁在观看?——图形寓意与观看者的身份
关于汉代虎形肖形印中的“虎”,我们很难明确将其归为是现实的写照,还是虚幻的神化传说,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汉代人的思想中,虎所代表的寓意具有多重性,虎的身份也具有多样化。从自然界中的虎到附加汉代人思想与观念的虎,虎形图案从现实性的题材逐渐扩大至虚幻的图像。由此也提示我们,在观看与虎有关的肖形印时以什么为视觉中心,采取怎样的观看方式,我们的重点是在虎上,还是在人上?单一虎形肖形印的图像意义是否依赖于观看者的一般思想状况?
在汉代,虎形肖形印的图像叙事内容要远远比图形本身重要。上文谈及的每一类虎形肖形印都有其所叙述的内容和要表达的思想观念。图形并非是肖形印的最终表现目的,叙事内容和其所蕴含的思想观念才是肖形印的表现目的和重点。如在“西王母御虎”这一题材的肖形印中,西王母所能带来的升天长生是这类肖形印的主要叙事内容与寓意,西王母御虎的明确寓意是这类肖形印要表现的最终目的。
面对汉代的肖形印,是谁在观看尤为重要。今天我们在面对虎形肖形印的时候,能感受到“印外之意”与汉代佩印者存在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从两汉时期到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观看者远离了肖形印使用者时期的一般思想,而以纯粹的艺术眼光来看待这些肖形印,其观看的视觉中心会不自觉地落在肖形印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整体和艺术美感,面对虎形肖形印时,观看重点均匀的放在画面的全部图形之上,人与虎无差别的被作为审美的对象。而在这批肖形印的持有者看来,其观看的中心与方式未必如此。上文已经分析,肖形印是在汉代人一般思想的前提下产生、使用的,当时人在观看这些肖形印时应当以当时的一般思想与观念为前提,重点应当在人上,而不应在虎上,即便是在没有人的虎形肖形印中,其重点也应当在肖形印图形的象征意义以及能够给人心理上的精神安慰。思想与观念的影响决定着汉代肖形印的图形内容,图形反过来又是思想与观念的承载者,在一个长时段中,人们的思想与观念趋于稳定,承载人们思想与观念的肖形印图形也逐渐变得稳定,从而使图形变得带有一定的重复性。
笔者认为,对汉代肖像印的解读与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鉴赏层面,还原肖形印产生、使用时期的历史、观念、思想等是准确认识肖形印的前提。随着时代变迁,虽然我们不能,也无法完全还原当时完整的历史,但是还原的越多,我们对于肖形印的认识也就越深刻,离肖形印本来的寓意与功能也就越近。我相信,在本文的讨论中,研究视角变换或许会比研究结论更有意义。
[责任编辑 李 浩]
赵洋,华侨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福建泉州 36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