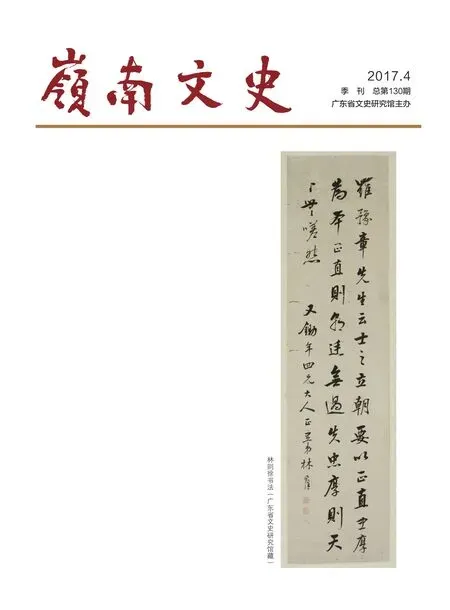张九龄“丁父忧”准确时间考辨
——兼及初唐授官泛滥问题
2017-01-28张效民
张效民
拙文《张九龄进士中举时间考辨》、[1]《张九龄进士及第“重试”问题正误》[2]曾考证张九龄于唐长安二年(702)进士得第,但未参加吏部主持的“释褐试”,而参加了由中宗主持的“材勘经邦科”制举考试,得中乙第,授职为校书郎。但是,进士得第后理应授官,为何张九龄又未曾得官?反倒是于五年后才应参加“材勘经邦科”制举,得第后方才授官?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唐代官员选授是十分困难的。傅璇琮先生曾说:“进士科及第后,还需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才能授予官职。称‘释褐’试,意思是从此脱去麻衣,步入仕途。如韩愈进士登第后,三试于吏部皆不成,十年还是布衣,而制举则一经登第,即可授以官职。”[3]傅先生所说韩愈这种情况比较极端,而且是唐玄宗之后的事情。而在唐初自开科举考试以后,因为建政伊始,中央政府与地方治理均需要大量人才,凡是进士中举,均立即授职,而仅靠科举考试也不能满足需要。因此还有诸多赤牒授官的情况出现。在黔中、岭南等地,还开设了所谓“南选”,以满足地方治理人才缺乏的急需。至高宗年间、武则天时期一直到中宗、睿宗时期,授官就因为制度的不严密而发展到极其泛滥的程度,主其事者利用制度漏洞上下其手,卖官鬻爵也十分普遍。如《新唐书·选举志·下》记载:
“初,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而其务收人心,士无贤不肖,多所进奖。长安二年(702),举人授拾遗、补阙、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评事、卫佐凡百余人。明年,引见风俗使,举人悉授试官,高者至凤阁舍人、给事中,次员外郎、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之起,至此始”。[4]
《旧唐书》卷五十一《中宗韦庶人》记载:
“上官氏及宫人贵幸者,皆立外宅,出入不节,朝官邪佞者候之,恣为狎游,祈其赏秩,以至要官”。“(韦)后方优宠,亲属内外封拜,遍列清要。……安乐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请帝书焉,帝笑而从之,竟不省视。又请自立为皇太女,帝虽不从,亦不加谴。所署府僚,皆猥滥非才。又广营第宅,侈靡过甚。长宁及诸公主迭相仿效,天下咸嗟怨之。”[5]
“(李)峤在吏部时,阴欲藉时望复宰相,乃奏置员外官数千。既吏众猥,府库虚耗。”[6]《旧唐书.睿宗纪》:“先是,中宗时官爵渝滥,因依妃、主墨敕而授官者,谓之斜封,至是并令罢免。”[7]
但很快睿宗又下令让这些斜封官官复原职。
对于这种授官泛滥、卖官鬻爵的现象,当时就有人不断提出反对意见。当时一些官员屡屡上书,反对乱置官位、乱授官爵。《旧唐书》卷八十二载刘祥道上书云:
“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经明行修之士,犹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岂能皆有德行?即知共厘务者,善人少而恶人多。有国以来,已四十载,尚未刑措,岂不由此乎?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付选;趋走几案之间者,不简便加禄秩。稽古之业,虽则难知,斗筲之材,何其易进?其杂色应入流人,望令曹司试判讫,简为四等奏闻。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次付主爵,次付司勋。其行署等私犯公坐情状可责者,虽经赦降,亦量配三司;不经赦降者,放还本贯。冀入流不滥,官无冗杂,且令胥徒之辈,渐知劝勉。”又说“古之选者,为官择人,不闻取人多而官员少。今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遂令九流繁总,人随岁积。谨约准所须人,量支年别入流者。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壮室而仕,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此便有余,不虑其少。今年常入流者,遂逾一千四百,计应须数外,其余两倍。又常选放还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复年别新加,实非处置之法。”[8]
至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1),时任左拾遗的辛替否就针对“时置公主府官属,而安乐府补授尤滥”事上书云:
“古之建官不必备,九卿有位而阙其选。故赏不僭,官不滥;士有完行,家有廉节;朝廷余奉,百姓余食;下忠於上,上礼於下;委责无仓卒之危,垂拱无颠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动心虑,事不师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赏,倍十增官,金银不供於印,束帛不充於锡,何所愧於无用之臣、无力之士哉?”[9]
这些史料都证明了唐玄宗之前授官泛滥的情况。
按照《新唐书·选举志》所记:不仅长安二年,还有长安三年,举人不仅授官,而且授官职务还较高。同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科举考试及第者也较之沈佺期“知贡举”随录取的人数大大增加。当时不仅举人授官,还授有大量非科举出身者的官职,史称“斜封官”、“墨敕官”。这种情况在睿宗时得到一定的抑制。[10]
总之,在唐初至玄宗近百年内,授官途径较多,士人得官比较容易;而能够坚持原则、清廉奉职的礼部官员是不多的。太宗开科举后,考中进士即授官是一种常态。
二
张九龄考进士之时考中进士即可授官。长安二年(702)张九龄中举后授官是正常的,未授官即为不正常。但张九龄确实未得官职,反而是返回韶州家中,一直等到五年后才再次赴京参加制科考试,及第后才授予校书郎,进入仕途。
对此,史书失载。徐浩《张九龄神道碑》亦无记载。本应参加“释褐试”授官而未参加,因而未得授官,那因何缘故未参加“释褐试”呢?既然已经排除了考试结果作废的原因,那唯一可能的原因就只能是张九龄自身家庭的原因。考张九龄前后的行踪,可以认定,唯一原因就是张九龄在长安二年参加进士考试后未能参加吏部授官的“释褐试”。为何未参加“释褐试”放弃授官?唯一的理由就是“丁父忧”——就是父亲去世,作为人子者,必须在家守制三年,做官的必须立即解任,回乡守制。当然也有所谓夺情的现象,但那是极少数人,因为身膺重任,朝廷事务繁忙,经皇帝挽留,不回乡守制,或者守制期未满被召回朝廷办事,这就是所谓的“移孝为忠”,夺情任事。但如无“夺情”的情况,在守制期间,不得从事其他任何公务事由,私事也有明确限制。如不得举乐、不得婚娶、不得参见宴会等。张九龄在其母亲去世后曾经被唐玄宗强制“起复”,也就是在守制期间,重新履行公务。但在张九龄参加进士考试期间,还不具备被皇帝强制起复的基本条件。“居家守制”是封建社会时期的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现象。如无皇帝的特别要求,任何人也不能违背。
“丁忧”的前提是张九龄父母去世。张九龄母亲卢氏夫人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离世。那么,张九龄长安二年(702)未参加吏部“释褐试”的原因就只能是父亲张弘愈的去世而“丁父忧”了。这就涉及到张九龄之父张弘愈去世的准确时间。对此,史书并无明确记载。后人根据徐浩《张九龄神道碑》、《张九皋神道碑》、《新唐书》的一些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提出一些分歧较大的推测性意见。
张九龄在作于唐开元五年(717)的《与李让侍御书》中说:“而慈亲在堂,如日将暮;遂甘心附丽,乘便归宁。”[11]大概是李侍御出使岭南,张九龄曾表达过愿为随从,乘便返乡宁亲之意,为其拒绝,所以张九龄再次作文予以申述。但文中的“慈亲在堂,如日将暮”一语,则表明当时张九龄的父亲已然离世,唯母亲尚存。考张九龄于神龙三年(707)春参加“材勘经邦科”制举后被授予校书郎。入仕后至此时,均无为其父“丁忧”的记载,则表明张九龄之父去世是在神龙三年(707)之前;而长安二年(702)张九龄参加沈佺期“知贡举”的进士科考试,则说明张九龄“丁父忧”必在参加进士科考试之后这五年时间之内。而“丁父忧”时间为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则张九龄父亲张弘愈去世的时间应该在长安二年(702)至长安三年之间。
再考徐浩《张九龄神道碑》:“列考讳弘愈,新州索卢县丞,赠太常卿,广州都督。皆蕴德葆光,力行未举。地积高而成岳,云久蓄而作霖。是生我公,蔚为人杰。弱不好弄,七岁能文。居太常府君忧,柴毁骨立。家庭甘树,数株连理。王公方庆,出牧广州。时年十三,上书路左。”[12]此处将张弘愈去世时间排在张九龄七岁之后,但未明确具体时间。从行文分析,约在张九龄七岁至十三岁的时候。
萧昕《张九皋神道碑》说张九龄二弟张九皋“特秉中和,诞生淳懿。恭推色养,孝自因心。幼岁丁太常府君忧,孺慕衔哀,欒棘无恬,毁能达理,□□成人,及日月□除,而顾复就养。”[13]这里说张弘愈去世的时间是在张九皋的“幼岁”时期。在成人之前,均可称“幼岁,”这是一个宽泛的时间概念,据此很难准确确定张弘愈的去世时间。
关于“幼岁”一说,《文苑英华》本的《张九皋神道碑》则有异文:“孝自因辛卯岁,丁太长府君忧”,“孝自因辛卯岁”。此语实难成文,定有遗漏或者误写,但“辛卯”二字很重要。辛卯岁,即是武则天即位改国号为周的第二年,武周天授二年(691)。据《张九皋神道碑》,张九皋生年66岁,逝于“天宝十四载(755)”,按此推知,张九皋当生于武周天授元年(690),至天授二年尚不足两岁。碑文中说他“丁太常府君忧,孺慕衔哀,欒棘无怙,毁能达理”。这实在不近情理,太过夸张,难以凭信。
对此,《学海堂》第二集卷十四侯康即指出:
“《文苑英华》云:‘辛卯岁丁太长府君忧’,石刻作‘幼岁’。按碑称公薨于‘天宝十四载,’‘春秋六十有六’,则当生于武后天授元年庚寅,次年即辛卯,九皋年甫二岁耳。九皋尚有两弟,即未必同母,何以三人者同生于一二年间?且碑称:‘孺慕衔哀,栾棘无恬。毁能达理,志若成人。’,虽瘐墓之词,不无润色,然施之甫晬小儿,亦太不伦。自当泛言‘幼岁’为是。”[14]
这里说张九皋尚有两弟,指的是张九章、张九宾。张九章行实大致可考,入仕居官时间不会比张九皋晚多少,年龄也不会小太多。而张九宾只见名字,难以考定行实,亦未见其他事迹记载。或者较之张九龄要小得多。这里侯康的辨析具有说服力,但仍然难于确定张弘愈去世的具体时间。侯康还指出:
“《新唐书》叙曲江居父丧在张说贬岭南之后(原注:曲江公碑则叙在前,并在十三岁上书王方庆之前,是时九皋尚未生,其谬不待辨)。考(张)说在岭南当武后长安三年,时九皋生十四年矣。而居忧又在其后,故碑文云:‘及日月外除,而顾复就养,思致逮亲之禄,方求筮仕之阶……未几遂登科,始鸿渐也。’是除服后即有志禄养,未几遂登科。细玩碑文,当日情事如是,必非辛卯岁也。”[15]
温汝适所作《张曲江年谱》也认为:“疑石刻是。既云‘幼岁’,或即在辛卯也。”[16]温汝适因《张九皋神道碑》中有“幼岁”二字,即将此认定为“幼儿”,所以说“疑即在辛卯也”。温汝适是把“幼岁”理解为“幼儿”,实属误读。近人何格恩著《张九龄年谱》则另持一说:“余颇疑‘辛卯’乃‘癸卯’之误。”[17]癸卯即武周长安三年(703),此说似有些道理,但是何以撰碑文者竟将“癸卯”误作“辛卯”,其家人竟未曾发现,或者是《文苑英华》过录者之误?使张九皋年岁竟出现12岁之差,实不可解。何格恩亦未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只是因为年岁巧合而做出的推测。看似有理,实则难信。
台湾学者杨承祖《唐张子寿先生九龄年谱》试图做出解释:
“且就九皋碑文读之,宜‘孝自因心’为句,‘幼岁’下读;‘辛’盖‘心’之音误,‘幼’‘卯’形近,又因上‘辛’字联想而误耳。石刻盖是。综比诸文,新传较安,故从之。”[18]
杨承祖所谓致误之由是由于“辛”“心”音近;“幼”“卯”形近而致误,亦缺乏说服力,未免牵强。但是他确定“新传较安”,倒是较为接近张弘愈去世的时间节点。
以上诸说对于确定张九龄“丁忧”,亦即其父张弘愈的去世时间具有重要启迪。但是我对温汝适、何格恩、杨承祖推测的依据和思路有些不同意见。《张九皋神道碑》现存最早版本有二:一是清代翁方纲《粤东金石略》卷四所载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夏五月《重刻张九皋神道碑》;一是明隆庆元年(1567)刊本《文苑英华》卷八九九《张九皋碑》。翁方纲是清代著名学者,所编《粤东金石略》裒辑文献经过严谨考证,对于阙文难识文字,均已标出,应该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可证,在明嘉靖年间,碑文尚未出现差谬。出现差谬的是《文苑英华》文本。
《新唐书》本传说张九龄“七岁知属文,十三以书于广州刺史王方庆,方庆叹曰:‘是必致远。’会张说谪岭南,一见厚遇之。居父丧,哀毁,庭中木连理。”将张九龄居父丧的时间放在张说贬岭南之后。按新旧唐书均记张说远贬岭南在长安三年(703)九月之后。则《新唐书》记张九龄居丧在长安三年拜见张说之后不久。顾建国据此在《张九龄年谱》中推测说:“疑于是年丁父忧”。[19]他分析说:张说此次坐忤旨,由长安出发,到韶州,大约需要月余才能到达。而张九龄“丁父忧”又在其后,他依据魏元忠被贬和召回的行程时间为三个月计算,则张九龄“丁父忧”的时间可能在长安三年十一月中或十二月。[20]顾建国分析的论据有启发。
查《唐律》卷十《职志》中规定:“冒哀求仕者,徒一年”,亦即处流放一年的徒刑。《唐律疏议》中解释说:“冒哀求仕者,谓父母之丧,二十五月大祥后,未满二十七月,而预选求仕。”注中又说:“谓父母丧,禫制未除。但父母之丧,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内是正丧,若释服求仕,即当不孝,合徒三年。其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内是禫服未除,此中求仕,名为冒哀,合徒一年。”[21]唐代是依据汉代郑玄的解释。郑玄的解释是以二十五个月为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乐。[22]因此《唐律疏议》按这样规定。如此,就可以理解张九龄即使进士及第,也必须立即回乡守丧,而不能参加吏部的“释褐试”而得授官职。既有礼制的规定,又有朝廷制度的强制性安排,张九龄中举后回乡“丁忧”,未参加“释褐试”而未得授官就顺理成章了。
这些材料还证明,古人所谓守丧三年,实际上只是守丧二十七个月,即是以九个月代替一年。由此看来,顾建国定张九龄丁忧在长安三年(703)张说过岭后的十一月中或者十二月,在时间上就有了可能。按照张九龄实际守制时间计算,张九龄结束守丧当在神龙二年(706)三月间或四月间。这样他就有了赴试的时间了。所以,顾建国的说法可信可从。但是,顾建国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宗即位后科举考试内容、规则的变化问题。
徐松《登科记考》神龙元年(705)载:“二月甲寅,复国号曰唐。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通鉴》、《册府元龟》又作此令时间为“神龙二年。”不管是神龙元年还是二年,对于在守制中的张九龄来说,要适应这一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即使是天资高卓,也还是需要聚精会神去应对的。何况本年还规定“进士科三场试。”[23]这也需要参加科举考试者精心准备的。但是在守制中以纯孝著称的张九龄是没有这个心情、精力去考虑这些问题的。
三
因此,张九龄“丁父忧”的准确时间还需重新考定。我认为,张九龄“丁父忧”的准确时间应该是在长安二年(702)春初或二月初,也就是张九龄参加进士考试及第前后。大约张九龄参加进士科考试时其父张弘愈还健在,或者虽已去世,但消息并不为张九龄所知。按照唐时制度,进士及第者还需要参加由吏部主持的“释褐试”,是在科举考试之后,也是在春天正月或者二月。“释褐试”考完拟官至春末结束。可能张九龄在等待参加吏部“释褐试”期间,才得到家中告丧人的报告或者是报丧的书信,得知父亲张弘愈于长安二年正月中去世的消息。因为家中人赴京告丧者取赴长安最近的郴州路也是3685里,按照《唐六典》规定的水陆行程速度,[24]报丧人水陆兼程也最快需要约一个月多月时间。当然如果是通过官府的邮驿来报信,也可能快一些。得到父丧消息的张九龄自然还需要将此消息报告有司,得到批准才能返乡奔丧。按照当时礼制,这一批准的时间应该是很快的。这样张九龄回到曲江的时间应该是在夏初了。他无缘参加吏部授官的“释褐试”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来解释张九龄中举未能授官,在家中未再赴举的原因就很有说服力。
四
然则确定张九龄“丁父忧”的时间起点即张弘愈去世准确的时间为长安二年(702)正月,也还有一个疑问需要解答。即是张九龄于长安二年二月开始守制三年,那么他的守制期当在神龙元年(705)二月结束。按照一般情况,张九龄在守制结束后的神龙元年八九月间即可赴京,参加神龙二年(706)春的吏部“释褐试”。但是张九龄因为神龙三年吏部“释褐试”与制科考试时间冲突,或者是因专注于参加制科考试,实际上并未参加“释褐试”,而是参加神龙三年(707)的“才堪经邦科”的制举。这中间又有何原因呢?
要说明这一原因,还需要从当时朝廷的情况说起。人们可以排列一下长安二年至神龙二年这几年朝廷所发生的大事件和张九龄此期的一些行实,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长安二年(702)二月:张九龄参加进士科考试,因父亲张弘愈病逝回家守制,未参加“释褐试”。
本年进士科进士21人。[25]
长安三年(703)九月:张说、魏元忠、高戬等因张易之、张昌宗诬陷而被贬岭南。南贬途中或神龙元年张说返京途中经韶州,或与张九龄见面。一见则“视为族子。”
长安四年(704)春:张九龄的恩师沈佺期以“考功收赇”,“被弹”入狱。
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暐、袁恕己等五人发动政变,杀张易之、张昌宗,迫使武则天退位,传位与太子李显,改国号为唐。大赦天下,惟张易之党不原。贬韦承庆、房融、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阎朝隐、王无竞、李峤、苏味道、崔融、韦元旦、刘允济、刘宪、郑愔等。其中,沈佺期长流州;宋之问贬泷州参军。
五月: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暐、袁恕己以诛张易之封王,被剥夺朝廷实权。实为韦后与武三思暗通,夺取五王实权之举。自此,朝廷实权尽归武三思。
十一月:武则天死。
秋冬间:李峤召为吏部侍郎。对于被张柬之等人重贬的李峤再次入朝担任要职。傅璇琮、陶敏等疑“次当与武三思再次当权有关”。[26]其实不仅李峤的复出如此,即如之后回朝的宋之问、沈佺期等大批神龙元年前后张柬之执政时期被贬的武氏集团成员也在武三思当权后纷纷回朝担任要职。这当然与武三思的死灰复燃和韦后勾结组建政治势力、巩固政治版图紧密相关。
神龙二年(706)五月:武三思使郑愔告朗州刺史敬晖、亳州刺史桓彦范、襄州刺史张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与王同皎通谋。六月,戊寅,贬敬晖崖州司马,桓彦范泷州司马,张柬之新州司马,袁恕己窦州司马,崔玄暐白州司马。子孙流放,参与政变之人悉数被杀、被贬。
七月,乃长流敬晖于琼州,桓彦范于瀼州,张柬之于泷州,袁恕己于环洲,崔玄暐于古州。武三思指使中书舍人崔湜定计遣使杀桓彦范等于岭外,政治报复,极其惨烈。
从以上的局面,可以看出当时的朝局是何等的混乱,政治斗争又是何等地惊心动魄、惨烈异常!如果说身处岭南边远地区的张九龄对于高层那种斗争尚无直接切身感受的话,那么,分属两个相互斗争、陷害残杀政治派别的与他有着十分特殊关系的人物,一个是张九龄的座主、恩师,一个是对张九龄视为族子,赞赏有加,然而他们都相继被贬出朝廷到岭南,不可能不对他这位后生晚辈有所说教的。而且张说途经韶州还与张九龄见面,沈佺期也极可能与张九龄在韶州见面,从中张九龄也必然能够感受到政坛的风云变幻。
长安二年张九龄是一位25岁的青年人,且参加了科举考试,对于朝廷事务已经有所认识。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丰富、对于朝廷事务尤其是朝廷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斗争的了解加深,对于政局也必然具有较强的判断力了。同时,尽管沈佺期和张说虽然分属两个阵营,但由于对张九龄均十分赞赏,也必然会对于他的政坛出身和未来的选择提出建议。这些建议也许会因为沈张二人所属政治势力不同、政治判断力有异,提出的意见也可能相互矛盾,但无疑都必然会对张九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张九龄对于何时出仕也必然要做出时机的选择。
综合分析,朝廷政局的急剧变化、惨烈的政治斗争,沈佺期、张说的建议,张九龄对于政局变化的迷惑,都必然影响张九龄再次入京赴吏部“释褐试”授官的时间选择。同时,如前所述,中宗时期考试内容和规则的变化也需要张九龄以一定的时间去准备。他一定会在自以为看清了政局变化的方向、同时对于应对考试有了较大把握后才决定参加“释褐试”而出仕。在看到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武则天逊位、唐中宗李显继位后又贬斥五王,到张柬之等五王政治势力被韦武政治联盟消解之后,张九龄或许会认为朝廷政局已经完全稳定,而对于《老子》的修习也有了较大的进展。何况他的座主沈佺期尤其是对他及其欣赏、视他为族子的张说均已回京,可以为张九龄入仕助一臂之力。作为一个待价而沽的青年俊才,确实应该出山了,因而才决定于神龙二年秋入京,参加神龙三年(707)的吏部“释褐试”授官出仕。但因为中宗于神龙三年“二月,令举天下宏儒博学之士”,也就是开设“制科”,张九龄实际上未参加“释褐试”,而是参加了制科“才堪经邦科”的考试,获得“乙第”,得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进入烟波浩渺的官场仕途。
以上对于张九龄长安二年(702)之后一直到神龙三年(707)这五年的情况作了细致的研究和考辨。可以确认,张九龄长安二年参加进士考试及第后未能参加吏部举办的“释褐试”,因而未能授官的原因是由于其父的遽然辞世,张九龄必然返乡“丁忧”守制。换言之,张九龄之父张弘愈去世之年应该为长安二年(702),具体时间应为正月或二月初,张九龄“丁忧”守制也必然是在这一时间。
注释:
[1]《张九龄进士中举时间考辨》,见《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2]《张九龄进士及第“重试”问题正误》,见《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3]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14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4]《新唐书》卷三十五《选举志》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二十五史》版(下同),《新唐书》卷四十五,第128页,总4254页。1986年12月,第1版。
[5][6]《中宗韦庶人》,见《旧唐书》卷五十一,260页,总第3736页。
[7][10]《旧唐书·睿宗纪》,见《旧唐书》卷七,25页,总第3501页。
[8]《刘祥道传》,见《旧唐书》卷八十一,列传第三十一,330页,总第3806页。
[9]《辛替否传》,见《旧唐书》卷一百一,列传第五十二380页,总第3856页。
[11]见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下册,第867-868页。中华书局,2008年11月,第1版。此文写作时间,并从熊飞注中所考。
[12][13]《宋重刻张九龄神道碑》,萧昕《张九皋神道碑》,翁方纲著,欧广勇、伍庆禄补注《粤东金石略补注》第166页、17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
[14][15]侯康所云,转自顾建国《张九龄年谱》第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16]温汝适著《张曲江年谱》,附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刊本《曲江集》。转引自顾建国《张九龄年谱》第31页。
[17]何格恩著《张九龄年谱》,《岭南学报》,民国24年(1935),第四卷第一期。转自顾建国《张九龄年谱》第31页。
[18]杨承祖《唐张子寿先生九龄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转引自顾建国《张九龄年谱》第31-32页。
[19][20]见顾建国《张九龄年谱》第29-31页。
[21]见《唐律疏议》第170-1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22]参见《辞源》3024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第22次印刷本。
[23]见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第161-16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24]《唐六典》卷第二第80页。中华书局,1992年1月,第1版。
[25]长安二年进士科人数据,清徐松《登科记考》,见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上册各年所载。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26]傅璇琮主编,陶敏、傅璇琮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第419页,辽海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作者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