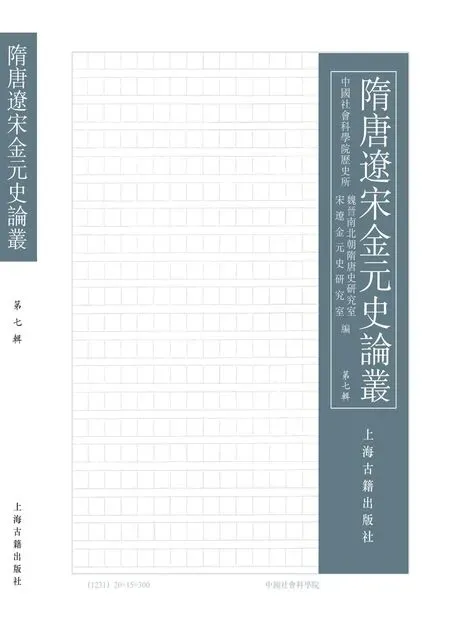言詞内外: 碑的社會史研究試筆
2017-01-28仇鹿鳴
仇鹿鳴
近二十年來,出土墓誌成爲推動中古史研究進展的重要動力,特别是隨著基礎建設的展開及盜墓活動的猖獗,每年通過各種渠道刊佈的新出墓誌數量頗爲可觀。僅以唐代而論,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及《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兩書共輯録墓誌5164方,資料收集的下限是1996年。據氣賀澤保規《新版唐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録(增訂版)》統計,截至2008年前已達8368方(不含誌蓋)。目前已刊佈的數量雖難以確切掌握,但估計已在11000方以上。平岡武夫《唐代的散文作品》曾統計《全唐文》及《拾遺》《續拾》共輯録唐人文章22896篇,則出土墓誌已佔存世唐人文章的三分之一以上。北朝墓誌整理刊佈的情況與唐代類似,其中可以一提的是近年來鄴城一帶大量出土東魏北齊墓誌,流散民間者已輯成《文化安豐》《北朝藝術研究院藏品圖録·墓誌》《墨香閣藏北朝墓誌》等書出版。正是有了這些新資料的推動,出土墓誌研究近年來頗有成爲顯學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自20世紀初延續至今的墓誌發現潮流,在某種程度上已悄然改變了一千年來金石學研究的傳統。由於新出石刻中,墓誌佔了絶大多數,使得石刻研究有被簡約爲墓誌研究的傾向。墓誌本身是一種格式性較強的文體,内容以記載誌主一生的經歷及世系、婚姻情況爲主。因此圍繞著墓誌展開的研究,儘管數目龐大,但大體可以歸爲三種模式: 圍繞人物、家族及婚姻、交遊網絡展開的傳記式或群體傳記式研究;利用墓誌中涉及重要政治事件的文字,補充或糾訂傳統政治史因文獻不足造成的疏失;利用墓誌進行較大樣本的統計,對年壽、婚齡等普遍性的社會狀況進行描述、歸納。其中又以前兩種佔據了主導地位,這使得目前的墓誌研究具有明顯的政治史取向,即在資料上視之爲補充、糾訂傳世文獻的手段,研究内容上則以重要的政治人物、事件爲中心。這一研究理路承續金石學的傳統,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毋需筆者贅言,但總括其基本方法,大體是選取石刻中姓氏、爵里、世系、民族、仕宦、婚姻等有效信息與傳世文獻互證,披沙瀝金,或可目之爲“萃取式”的研究。值得反思的是,在這一學術傳統中,各種出土文獻,無論是甲骨、青銅器,還是簡帛、碑誌、文書,學者多不過視之爲文字的不同載體,其價值的高下,在於能否訂補傳世文獻的不足。在此背景下,石刻文獻難免成爲傳世文獻的附庸,其受學者重視的程度,往往取決於能否在傳世文獻中找到對應的記載。
另一方面,儘管對新出墓誌的收集與考釋在方法上承續了傳統金石學,但處理資料的廣度與深度較之於既往皆有所不如。僅從廣度而論,翻檢自《集古録》《金石録》以降的傳統金石學著作,不難注意到傳統金石學關注的範圍大體以立於地面的碑碣、摩崖、造像爲主,埋於地下的墓誌由於多是零散發現,僅是其中一端。現在學者則多受新資料帶來新問題的驅策,聚焦於新出墓誌一隅,宋至清歷代著録的地面石刻以及隨各種文集傳世的碑銘,早屬明日黄花,關注者稀,視野較之於前人,反而趨窄。某種意義上而言,當下的墓誌研究,是用舊方法研治新材料,因此雖忝居“預流”的學問,但反而感受不到新史學的衝擊,學者大都對於石刻這一文字載體的社會功能及在古人世界中的意義缺乏自覺。
衆所周知,中國古代紀念性石刻傳統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至秦始皇巡幸各地時的刻石,直到當今社會,每逢重大的事件、工程,仍不乏刻石紀念、記述前後因果之舉。如果將簡帛、紙張及電子儲存介質視爲普遍通用的書寫材料,那麽在過去的兩千餘年中,通用書寫材料已經歷了兩次重大革命,但紀念性石刻的傳統穿越其中,至今依然保有生命力,這無疑與石刻這一介質所具有的永恒性與公共性密切相關。而且這一傳統並非中國獨有,在世界各個文明中普遍存在,或可説是人類共通社會觀念的産物。如果説通用書寫載體的變革在於追求記録及傳播的便利,那麽金石這類介質則恰恰相反,甚至是借助鏤刻的不易而爲人所寶重,成爲超越於通用書寫載體之上,承擔特定社會功能的紀念物。循此思路,不難注意到墓誌雖佔據了已知中古石刻文獻的大宗,但因其鐫刻後便被埋於地下,僅具有永恒性而缺乏公共性,所承擔的社會功能也較爲單一。若以古人的觀念揆之,並非是最重要的紀念物,而現代學者關注較少的地面石刻,特别是各類紀功碑、德政碑等公共性的碑碣纔承載了古人“鏤之金石,以志不朽”觀念的核心。
因此,如果説當下以墓誌爲主體的石刻研究,採用的是“萃取式”的方法,具有政治史研究的取向,強調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互證,那麽我們若能更多地把注意力轉向探討碑這一公開的紀念物在古人世界中的功能與意義,開拓碑的社會史研究,至少在四個面向上,較之以往或將呈現出新的觀察角度。
碑作爲景觀的象徵意義。由於中國學術的傳統素來注重文字記載,對於研究者而言往往本能地關注碑銘上的文字,但如果回到古人的情境之中,作爲公共性的紀念物,碑在很多情況下是通過形制與空間的規劃來呈現其景觀效應,進而傳遞刻石背後的政治訊息,特别是對於文化層次不高的普通庶民而言,更多的是碑的“觀衆”而非“讀者”。因此,我們可以注意到唐代一些巨碑,如《何進滔德政碑》高達12.55米,寬3.04米,厚1.04米;玄宗《華岳廟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比也”*《開天傳信記》,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説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24頁。,皆遠遠超過實用的需要,有意借助碑本身的宏大規制,造成強烈的視覺衝擊,進而塑造政治權威。除此之外,也可以通過對石材的選擇、刻寫方式的變化等手段來傳遞政治訊息。例如張嘉貞於恒岳廟中立頌,“其碑用白石爲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舊唐書》卷九九《張嘉貞傳》,中華書局,1975年,3092頁。;玄宗表彰楊國忠改良銓選制度,爲立頌德碑,“敕京兆尹鮮於仲通撰文,玄宗親改定數字。鐫畢,以金填改字處”*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卷五,中華書局,2005年,40—41頁。。可以想見,以金所填各字,在陽光的照射下呈現出别致的視覺效果,而玄宗對於楊國忠的恩寵便不待文辭而爲衆周知。正因如此,想到這一方法者並非玄宗一人,富有藝術家氣質的宋徽宗於崇寧四年(1105)十月二十三日詔,“中書省檢會應頒降天下御筆手詔摹本已刊石迄,詔並用金填,不得摹打,違者以違制論”*《宋會要輯稿·崇儒》,河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334頁。,與玄宗的做法不謀而合。當然,更常見的方法是在碑文中保留詔書的原有格式,早在東漢乙瑛碑中“制曰可”一行便高出一格刻寫,宋代以降石刻公文中大量保留了原有格式,這種形式或是有意將官文書的權威借助永恒性的碑石展現給公衆。
筆者之前曾討論過古人對於立碑的地點往往做精心的選擇,立碑於大市通衢或對碑主具有紀念意義的地點,以便更多的往來吏民能注意到這一景觀,達成廣泛的傳播的效用是其中重要的考量。因此,在普通城市中,官署府衙兩側作爲城市的視覺中心往往成爲首選*仇鹿鳴《權力與觀衆: 德政碑所見唐代的中央與地方》,《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84—85頁。。這一考訂,目前也能得到考古發現的支持,徐州蘇寧廣場工地出土的五代王晏德政碑,據考古現場情況可推斷原立於武寧軍節度使衙東南側,該處直到明代仍是徐州府衙所在,至明天啓四年(1624)爲洪水所淹没,因此此碑出土於距地表深5米的地層中。判斷其爲道東,緣於天啓大水自徐州城東南方向破奎河大堤而入,王晏德政碑倒向西側,碑首飛走不知去向,碑身倒塌時撞上龜趺首,故碑身上部及趺首缺失,出土時殘斷碑身叠壓在龜趺之上,這也與文獻記載和各地點考古所見房屋的倒塌方向一致*這一信息蒙張學鋒先生賜告,特此致謝。另該碑録文與考釋,見孫愛芹、于康唯、鄭洪全《讀徐州新出土“太原王公德政碑”》,《東南文化》2014年第1期,84—92頁。。如能進一步結合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將會進一步深化對立碑地點選擇與都市空間關係的認識。
碑作爲信息與知識傳播媒介的社會功能。作爲一種永恒性的景觀,碑當然不像紙張這樣的通用書寫材料具有携帶上的便利性,但碑依然具有重要的信息與知識傳播功能。碑的刻立、廢弃、重鐫本身就傳遞出不同的政治訊息,唐憲宗平定淮西,特别選擇利用吴少誠德政碑的舊石改刻平淮西碑,通過對碑銘這一永久性景觀的重新定義,重塑唐廷在當地的政治權威。另據宋人龐元英《文昌雜録》記載:“余昔年隨侍至定武,見總管廳有唐段文昌撰平淮西碑石。”*龐元英《文昌雜録》卷三,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4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138頁。則唐廷似曾於多地立平淮西碑,其所欲傳遞的政治訊號則不言而喻,定武軍即唐代定州,義武節度使恰是河北藩鎮中對唐廷較爲恭順者。類似的例子亦見於後世,清乾隆平定準噶爾、回部後,不但將告成碑立於太學,更下詔於省、府、州、縣各級文廟中復製此碑,以達成向一般吏民宣揚宏業的目的*朱玉麒《從告於廟社到告成太學: 清代西北邊疆平定的禮儀重建》,《高田時雄教授退休紀念東方學研究論集》,臨川書店,2014年,403—410頁。。另一方面,碑文可以通過拓本、抄寫等手段化身爲通用的書寫材料,擴大自己的傳播範圍與效力。如玄宗曾將華岳廟碑的拓本張架立於洛陽應天門,供文武百官觀覽。太宗親自撰書的魏徵神道碑,“刻畢,停於將作北門,公卿士庶競以模寫,車馬填噎,日有數千”*《册府元龜》卷四〇,中華書局,1960年,451頁。,於是碑從“固定的景觀”變成“流動的文本”。敦煌文獻中《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淮深)德政之碑》鈔本則於正文之中多用雙行小字箋釋典故與史事,這一詳注古典與今典的鈔本或是向歸義軍中文化程度不高的節將士卒宣講碑文所用,而敦煌兒童習字也有以《張淮深德政碑》《史大奈碑》爲素材者,可見這類文本傳播於各個階層。如果説碑的興廢及碑文的流佈在當時是窺測政治氣候移易的風向標,那麽對於後世而言,長存於地面的碑碣則成爲重要的知識資源。如中唐張建章爲人好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苞麥屑置於水中,摸而讀之,不失一字,其篤學也如此”*《册府元龜》卷七九八,9486頁。。宋以降金石學興起後,圍繞著訪碑、拓碑産生的各種故事及作爲禮物流動的拓本等都構成了中國古代知識社會史上的重要一頁。
石刻生産過程中的社會網絡。碑誌製作的過程中往往透露出誌主生前及家族的人際網絡。北朝唐初墓誌多不題撰書者姓名,至盛唐後方漸普及,這或與墓誌這一文體漸爲人所重有關,中唐後重金禮聘名家撰書墓誌已蔚然成風。既往學者對碑誌作者與誌主間的關係不乏關注,但這僅是石刻生産中社會網絡中的一端,如墓誌製作至少包含撰寫、書丹、鐫刻三道程序,撰者、書家、刻工三者間的分工與網絡,便注意不多。如柳公權書寫的《玄秘塔碑》《迴元觀鐘樓銘》《符璘碑》《金剛經》皆由刻工邵建和、邵建初兄弟鐫刻,兩者間有密切的合作關係。俄藏敦煌文書中的鄭虔手劄則透露了以詩、書、畫三絶名世的鄭虔與刻工陳博士如何商議合作製碑。這種固定的合作關係並不局限於著名的書家與刻工之間,會昌三年(843)、四年(844)分别落葬的神策軍將李遂晏及妻田氏這兩方墓誌皆署何賞撰、劉文貞書、李從慶刻字,考慮到誌主的身份及誌文中未提及撰書者與誌主生前的交誼,大約是倩人作文,而這三人顯然也是一固定的組合。朝廷製作的一些巨碑,往往差專使勒碑,如規制巨大的華岳廟碑,玄宗以吕向爲鐫勒使,孫逖、徐安貞分别有《春初送吕補闕往西岳勒碑得雲字》《送吕向補闕西岳勒碑》詩紀其事。除了社會網絡,刻石過程中涉及的經濟活動也值得注意,如石材的獲取、刻石所需的時間與費用等問題,儘管相關史料寥寥,仍頗具探討價值。如從目前所見唐墓誌的物質形態而言,高規格墓誌文的長度與誌石大小嚴絲合縫,事先當有設計,誌石亦爲定制。而一些中下層人物的墓誌,如宫女墓誌(著名的井真成墓誌亦如此),由於誌文簡略,誌石左側往往留有大端空白,似可推測這類預先畫好罫綫的標準格式誌石能從市場上購得或預先批量製作,滿足官府及一般階層需求。
作爲政治、社會事件的立碑活動。古人素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説,立碑頌德、流芳後世是立功最直觀的體現,故爲人所重。因此圍繞著德政、紀功之類紀念性碑刻興立背後往往充斥著種種政治的角力,是確認君臣關係、塑造政治秩序的重要一環。既往的研究儘管重視將傳世文獻與石刻文獻相比勘,但受制於“萃取法”的取向,多將碑文割裂開來,尋找有無糾訂傳世文獻記載之處,但對於如何從整體上理解碑文的表達與當時政治角逐間的關係,立碑的過程中碑主與朝廷的互動等則措意無多,所重者仍是碑文的内容,而對碑文言詞内外的藴意及與立碑相關的政治運作則缺乏關注。筆者以爲可以嘗試用“代入法”展開碑的社會史研究,由於古人對立碑一事的崇重,立碑本身就是當時重要的政治、社會事件,圍繞從立碑的許可、碑文的撰寫到碑落成前後的宣傳等皆可引申出進一步探究的綫索。重要的頌德碑、紀功碑,除碑文外,往往在史籍中也保留了不少相關記載,若能綜合地加以運用,激發周邊史料的活性,足以勾勒出更加豐富的細節,復原一個完整的政治事件。
由於碑與墓誌不同的功能,相對而言,碑具有更加豐富的内涵,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生活中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20世紀以來的石刻研究以墓誌爲主體,以新史料的發現爲驅動,但從現代學術的要求而言,更需要提升方法上的自覺,在文獻考訂的基礎上,思考石刻的社會功能,復原立碑前後的政治場景,由物見人,借助文本通向歷史現場,構成我們進入古人世界的重要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