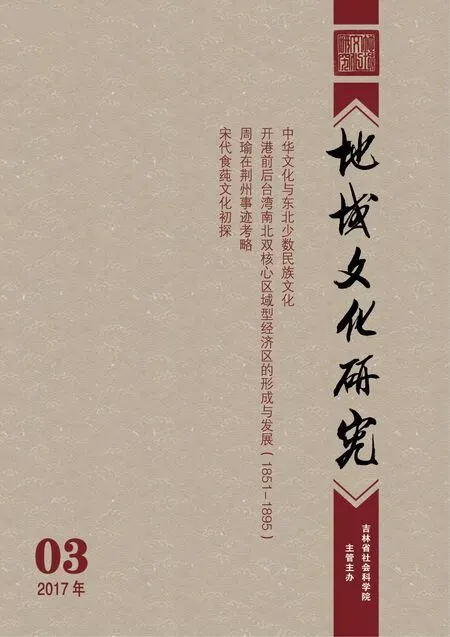中华文化与东北少数民族文化
2017-01-28陈志贵
陈志贵 关 捷
中华文化与东北少数民族文化
陈志贵 关 捷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自秦始皇建立中央封建集权国家以来,出现过多次大的统一局面。秦汉时期开创了全国统一的先河,隋唐王朝疆域的开拓,扩大了中原传统政治、经济及文化与边疆地区的联系。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开创了我国少数民族统一全国的先例,中原和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本身,发生了长达近百年的富有特色的大融合,改变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传统结构和固有观念。及至明清,特别是满族开创的清王朝,在元明两代的基础上实现了大一统,基本形成了现今的中国疆域范围。近代以来共同的遭遇和命运促进了东北各民族间及与中华民族间的相互理解、支持和团结,更加珍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及中华民族文化,表现为民族认同意识、维护国家统一的中华民族心理素质得到巩固与加强,从而鲜明地显现出东北少数民族的地域文化在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和地位。
中华文化 东北 少数民族 东北疆域 文化贡献
美丽富饶、历史悠久、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东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迄今学界对东北许多问题的见解仍未取得一致,因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早在五千年前,今辽宁西部出现的“红山文化”被学者称为“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①《红山文化——“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新华网,2016年10月17日。。李治亭在《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较全面地论述了那时的东北地区已走到各地区文明的前列。认为商周之际,延至春秋之后,生活在松花江中下游的肃慎族已与中原王朝建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②李治亭:《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2期。其后,东北地区与历代王朝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各王朝之兴亡与安危无不与东北地区发生密切的关系。
东北地区的地理环境既特殊又优越,如其西南连接中原,辽南隔海与中原腹地山东相对,出入中原十分便捷;北与西连接游牧民族地区。在东北区域内,多个民族共同繁衍生息,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从东北地区崛起的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先后逐鹿中原,并建立北魏、辽、金、元、清等政权。元、清两代王朝统一全国,对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从上古至中世纪,中华民族对古代东北亚区域文明的创造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创了有独特魅力的地域文化。这一区域虽然有时未被中原中央政权或地方政权管辖,但确属众多的中华古族所开发、建设的地域。只是到16世纪后半叶,沙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侵略扩张,部分区域才最终落入沙俄侵略者手中。此后,东北各民族斗争生活的途径,大抵由分而合,自内及外,到国内统一不再纷争之后,外患却又日趋紧张起来(主要是抗俄、抗日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共御外侮的斗争中,共同的遭遇和命运促进了东北各民族人民间的相互理解、支持和团结,更加珍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及中华民族文化,表现为民族认同意识、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得到巩固和加强,从而鲜明地显现出东北民族的地域文化在中华民族大文化缔造、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
一、东北地区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中华文化格局形成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华民族观、中华疆域观、中华文化观三位一体,互相渗透与交融,不能分割,不能孤立,不能片面强调某一点。
(一)从历史地理环境看东北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格局中的地位
“研究东北民族文化离不开地理环境,历史地理的生态环境制约着甚至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决定性地影响着民族文化格局。由于中华大地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单元,这既决定了中华文化起源的本土性,又形成了极其不同的多种生态环境,构筑了多种不同的人文发展机遇与文化区域,从而形成了中华大地上的多元文化区系。根据考察与对资料的分析论证,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已初步形成了四个大的文化区域(或称文化区系),这就是阴山山脉以北的北方文化区域(后来发展为草原游牧渔猎文化)、阴山山脉以南和秦岭山脉以北黄河流域旱作农业文化区域、秦岭山脉以南和南岭山脉以北的长江流域稻作农业文化区域以及南岭山脉以南的亚热带块茎种植文化区域。”①关捷:《东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作为包括“三河流域”②即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斡难河(今鄂嫩河)和土拉河。、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燕山山脉和东北大平原的广袤地区,东北地区不仅是阴山山脉以北的北方文化区域的主体部分,而且以阴山山脉为接触地带,与阴山山脉以南、秦岭山脉以北的黄河流域旱作农业文化区域形成密切联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及文化统一体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东北地区民族文化的作用,费孝通教授曾指出:“考古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起已陆续在长城外的内蒙古赤峰(昭乌达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该地区的先民已过着以定居农业为主,兼有畜牧渔猎的经济生活。近年又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的祭坛和‘女神庙’,出土的玉器与殷商玉器同出一系。铜器的发现更使我们感到对东北地区早期文化的认识不足,而且正是这个东北平原和大兴安岭及燕山山脉接触地带,在中国历史上孕育了许多后来入主中原的民族。”③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包括东北地区民族文化在内的地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虽然看似相隔而实际是相连的,同时存在、同时发展,彼此之间相互关联、交互作用,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而构成一个整体单位,也就是形成一个多元统一体。事实表明,文化的多元性反映出中华文化发展中的横向联系,而多元文化发展为“一体”文化,诸地区、诸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与传承,又反映出中华文化发展中的纵向联系,这种文化上横向与纵向的交叉发展正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历史轨迹。中华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接触文化(或称连续性文化),它是由内陆平原高原文化与东北森林草原文化、沿海海洋文化交感激荡、碰撞、交流、融合而形成的。这种多元文化之交感激荡,多元文化之叠合——冲击、碰撞、交流、融合,产生了强大的内聚力。
(二)东北地区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交融的中原华夏文化,由于它处于中华大地的中心地带,必然与周围各种文化相互接触、相互激荡、相互吸收及相互融合,从而促进了中原华夏文化的发展,且使其在各文化区系中脱颖而出,最先具备文明条件,率先迈入文明大门。不同源的夏、商、周三代,使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族群与渭水流域的族群统一为一个整体,其文化碰撞、交流、交往、交融、汇集与融合,形成华夏文化的主体,为中华疆域内部诸多民族的联合——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奠定,起了重要作用。
“多元文化统一体一经形成,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诸多民族的努力,构筑成多元统一的中华文化传统,这种文化的构成、连续性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见的。”①关捷:《东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39页。正如美国学者伯恩斯(Burns.Edward)所说:“当这个远东文化一旦出现,它就延续——并非没有变化和间断,但其主要特征不变——到现代20世纪。”②[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73页。
“三代华夏文化形成后,中华文化史上形成了第一次文化高峰——诗经时代,经过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又演变为诸子时代与楚辞时代。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各民族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活动在东北西部地区的为东胡族,东胡系统诸族因最初有东胡族而自成一系”。③关捷:《东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39页。“秦汉文化的发展经历了由西而东、由南而北的整合过程,由多元走向一元。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多属于游牧文化或狩猎文化,最早在游牧区出现了匈奴人统治下的大一统局面。中原与匈奴的战争,又使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从而构成秦汉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特点。”④关捷:《东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39页。两个统一体的汇合促成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这一时期东北地区有鲜卑、北夫余、挹娄、北沃沮以及黑龙江以北的“玄丘之民”“赤胫之民”和库页岛一带的“玄股国”“毛民国”及“劳民”,还有堪察加半岛上的“黑齿国”。黑龙江流域的广阔山河及原野成为这些古代民族驰骋雄飞的场地,展开了这一时期祖国东北极边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东北西部的鲜卑族是东胡的一支,中部的北夫余、夫余和滨海地区的北沃沮属秽貊族一支,东部的挹娄是肃慎族的后裔。“玄丘民”“赤胫民”或“玄股民”“劳民”属通古斯族系,而“毛民”则属古亚洲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急遽交融时期,即民族的大移动和大交融的时期。北魏登国元年(386),鲜卑拓跋珪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北魏登国十一年(396),“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①(北齐)魏收:《魏书》卷2《帝纪第二·太祖道武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页。,鲜卑族相率离故土而南迁,走向与中原汉族相融合之路。东北西北部地区的室韦族继之兴起。中部地区北夫余之裔北迁,称豆莫娄。东部地区挹娄在晋时又称肃慎,至北魏时又称勿吉。勿吉七部形成,吸收了夫余和北沃沮人后裔,而后又出现粟末靺鞨和号室靺鞨等。挹娄曾受夫余阻隔不能自通中原,而晋时肃慎和北魏时期的勿吉却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直接联系。东北各族此时出现了新的组合。在此以前的东北历史已发展到较高的社会阶段,即鲜卑已是大部落联盟,夫余进入奴隶社会阶段,鲜卑入主中原后而逐渐融入主体民族,夫余失国,室韦、勿吉见于史传,室韦、勿吉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氏族社会。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的对峙、碰撞与交流,文化在多元辩证中发展,继匈奴族之后,鲜卑、氐、羯等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幕雄壮的历史活剧。这为多元文化走向“一体”——隋唐文化的全面高涨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约3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建立起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唐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自唐朝开始,中原王朝在东北地区和黑龙江流域陆续设置了一系列行政机构。这一时期,东北西北部有室韦族,西部、西南部有奚(库莫奚)、契丹族,东部有以粟末靺鞨为主建立起的渤海国,东南原为高句丽后其故土的很大一部分为渤海统属,黑龙江口和库页岛一带有黑水靺鞨的窟说部以及莫曳皆部。
唐代的文化,在当时最具有中华文化多元辩证发展的特点,唐代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一元化的统一,其开放性与世界性的品格特征,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典范,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典范。②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东北地区各民族文化对唐文化形成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鲜卑族的作用最为突出。由东北森林、草原南迁到阴山之下的拓跋鲜卑及其建立的北魏王朝,在政治、文化、民族交融等各方面,对唐代均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③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44页。这里既指出李唐统治者有鲜卑族的血统,也确认了鲜卑及北方森林草原文化的影响。对此,费孝通更具体地指出:“经过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更扩大了的中原地区重又在隋唐两代统一了起来。唐代的统治阶级中就有不少是各族的混血。建国时,汉化鲜卑贵族的支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之他们在统治集团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有人统计,唐朝宰相369人中,胡人出身的有36人,占十分之一……唐代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它的特色也许就是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开拓性。这和民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是密切相关的。”④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辽、宋、金、西夏、元是多元文化大发展时期,其发展的前提之一,便是南北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这期间,东北民族文化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907-1125)①辽建国为公元907年,国号契丹,无年号,直到公元916年始建年号,公元938年(另说为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公元983年复国号契丹,公元1066年道宗时再次称辽。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1115-1234),均统治过当时北中国的广大地区,在中国民族融合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在长期征战和社会变化过程中,大量汉族北迁,与当地民族共同劳动,互相交流,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蒙古乞颜部的孛儿只斤·铁木真于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12世纪末,以呼伦贝尔草原和“三河”流域为摇篮的蒙古诸部完成统一。忽必烈继汗位后,定国号为大元,元朝(1271-1368)统一了中国。此后在中国历史上已基本上不复出现长期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辽、金、元对东北政区持续行使有效管辖并不断加强。
明代是继辽、宋、金、西夏、元开放之后转为封闭的时代,当然已不可能是原来旧式的封闭。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提到当时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情况:“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惜乎当日之君子徒诵‘用夏变夷’之言,而无类族辨物之道”,“当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②(明)顾炎武著,黄汝成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25页、第1723页。。明代文化虽由多元走向“一体”,但融合各种文化开放的势头如滚滚洪流不可阻挡,其文化新质不断涌现。
清代,北方统一南方,东北少数民族再次统一中国,尽管它“没有轶出过去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的老路”③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但这时期的文化仍遵循多元辩证发展的规律,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阶段的文化高峰。而到了清中叶之后,中国固有文化开放性逐渐减弱,封闭性逐渐加强,走上了完全封闭的道路,伴随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对中国原有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内外矛盾交织中,清王朝走向覆亡,中国封建社会也走完了最后的道路,中华文化史由此而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④张碧波:《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上),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页。
中华文化史是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的历史,每一次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都带来中华文化的跃进,出现新质文化,推动社会的前进,并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多元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民族文化传统。地域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织结构,没有各地域文化也就没有中华文化。东北地区民族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
中国东北民族创造的地域文化包括东北西北部的草原游牧文化,兴安岭地区的森林狩猎文化,黑龙江、松花江、嫩江和乌苏里江的水边渔猎文化和黄海、渤海、今日本海沿岸及近海岛屿的海洋文化以及东北平原的农业文化,其中以草原文化渔猎文化和农业文化为基本形态。草原文化“一个突出特质是开放性与流动性,这恰恰与中原一带稳定的、保守的农业文化构成鲜明的对比”。⑤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页。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使蒙古族等民族充满生气,充满活力,不拘一格,慷慨豪放,善于吸收异质文化。一旦与中原接触,就很容易与具有很强凝聚力、同化力的农业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史”⑥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与满族的兴起,加速了中华民族多元统一体的最后完成,加速了中华文化从内陆封闭型向沿海开放型的转化。
关于东北诸族森林文化、草原文化对中原农业文化的影响作用,费孝通先生曾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在系统地总结、介绍了东北的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的发展、迁徙历史进程之后,明确而肯定地指出:“北方诸非汉民族在历史长河里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农业地区而不断地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使汉族壮大起来,同时又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这些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①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上述规律也同样作用于汉族,即汉族也同样融合并充实了其他各少数民族。正是各民族间的双向交流,给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不断注入新的血液、新的因素,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生机勃勃的活力,在各个时期不断展现出新的文化高涨与文化跃进。东北草原民族、渔猎民族、兼营渔猎农业的民族不断地与高度发达的汉族农业文化相融合,既改造与促进了东北各民族的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使之迅速发展并出现质的飞跃,也给中华文化注入新的因子,使中华文化更为多彩多姿。②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页。
二、东北少数民族对开发祖国边疆作出的贡献
东北少数民族长期居住在白山黑水的广袤地区,对开发建设这块神圣而富饶的土地作出很大贡献。
(一)达斡尔族对开发祖国边疆的贡献
达斡尔族迁到嫩江流域时,当地还是一片荒原。雍正十二年(1734),开始兴建墨尔根(今嫩江县城)、布特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所在地)等城时,达斡尔人八旗兵和壮丁,或上山砍伐树木编成木排顺流送到工地作为建筑木材之用,或在建城工地上担负各种劳动。除了参加筑城以外,达斡尔人还参加了建筑驿站和卡伦的劳动。顺治九年(1652),自黑龙江北岸迁到嫩江流域之达斡尔族,为龙江县“最初之耕作者”③中东铁路局商业部编:《黑龙江》,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598页。。《清世宗实录》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打虎儿兵五百人,先赴额苏里耕种”。康熙二十五年(1686),“墨尔根达虎尔索伦官兵耕种公田一千六百六十垧”。④(清)阿桂等修:《盛京通志》卷24,沈阳:辽海出版社,1955年,第25页。1垧,约合15亩。农业生产的任务主要落在达斡尔人身上。
晚清的达斡尔族既从事农业生产并有显著成效,亦发展畜牧业,饲养牛马,少的数头,多者数十头。⑤《达斡尔族简史》编写组、《达斡尔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编:《达斡尔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59页。海拉尔地区达斡尔族主要从事畜牧业,而且有的屯落建有共用的大型畜圈。达斡尔族还从事多种形式的猎业生产,为市场提供皮衣、肉食等。达斡尔族利用大小兴安岭的茂密森林,发展林业,伐木供给城市建设之用。伴之而行的是捕鱼,并使用树皮制桶、盆等器皿,制造大轱辘车等,这些生产活动对达斡尔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锡伯族对开发祖国边疆的贡献
锡伯族在东北嫩江、松花江流域居住时,除了从事畜牧狩猎业外,还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康熙二十一年(1682),锡伯族能以约“一万二千石”①《吉林通志》卷1。转引自《锡伯族百科全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5页。军粮支援清朝调派黑龙江的军队。翌年由吉林伊屯口(今伊通口)地区种植的“席北米”(锡伯米)约2500石运往黑龙江②(清)长顺修,李桂林纂,李澍田等点校:《吉林通志》卷56《武备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表明锡伯族在东北边疆的农业生产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康熙三十一年(1692),锡伯族被清政府从蒙古旗中“赎出”,编为74牛录,移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城,除驻防城池、驻卡巡边、保护台站、防范盗贼外,其附丁则自备耕牛籽种,开垦种田。所收粮食一半供养披甲人,一半缴纳官粮。
乾隆二十九年(1764),锡伯族开始西迁伊犁,后定居伊犁河流域,促进了当地的开发。锡伯营总管图伯特决定在绰霍尔渠基础上再修条大渠。嘉庆七年(1802)农历十月,锡伯族军民正式动工修建。嘉庆十三年(1808),长200余里,渠深1米,宽1.2米的“锡伯渠”胜利竣工。③徐松:《西域水道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31页。锡伯营驻地的近10万亩荒地成为沃壤,进一步稳定了迁居西北边疆军民们的生活。东北、西北两地锡伯族种植的主要作物有小麦、高粱、玉米、大豆等,均为一年熟。起初耕作方法简单,产量低,后来随着农具改造,使用犁、车、耙、铣、镰刀等深耕细作,不仅自给自足,尚有余粮交予国家。
(三)赫哲族对开发祖国边疆的贡献
赫哲族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活动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满洲八旗的组成部分,参加驻防八旗在东北的农业屯垦开发;其二是留居于三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族,在当地从事经济开发。如在清前期编设新满洲的过程中,大批赫哲等民族的成丁被编入新满洲,仅康熙年间编为新满洲的赫哲等民族成丁就有万人之多。编为新满洲的赫哲族被派遣到东北各地驻防,在承担各种军事任务的同时,也参加当地的屯垦开发活动。赫哲族一直以农业生产为副业,但大力放荒垦殖,使东北边疆地区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出现拥有几十垧乃至几百垧屯垦开发地占有者。留居于三江流域未被编为新满洲的赫哲族,继续从事着他们传统的渔猎经济。赫哲族捕捞的大马哈鱼进入交易市场,渔产品的商品化,促进了渔业生产的发展。赫哲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对当地的经济开发作出了贡献。④韩效文等:《各民族共创中华·东北内蒙古卷》(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随着社会的发展,赫哲族的手工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起来。男子既从事渔猎、采集人参,又自己用铁、木造船,加工器具;女子以桦树皮、皮革、鱼皮、兽皮制作日用品。传统以物易物方式向商品经济方向发展,其中渔猎产品大量商品化,木劈柴与手工业品也进入交易市场。赫哲族人的生活随商品经济的到来而变化较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四)鄂温克族对开发祖国边疆的贡献
居住在黑龙江支流精奇里江及石勒喀河一带鄂温克各部以狩猎为主,兼事相当规模的畜牧业经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已使氏族社会成员失去财产的共有性,氏族公社逐渐解体。交换的产生,使军事首领和酋长等利用权势发财致富,成为氏族上层,出现了氏族贵族,但还保留着浓厚的猎物平均分配习惯。他们与清统治势力接触初期,正处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状态。康熙十年(1671)清政府开始对鄂温克的“图勒图”“阿布纳”“索嫩扎本根”“额和内”等部众陆续编佐,总称为“布特哈打牲部落”。在布特哈地区,鄂温克族共分5个“阿巴”(围猎场),以围猎场为单位,进行兵丁测量、纳貂等事宜。
清朝驻兵边疆,为解决军粮的供应,在鄂温克士兵驻防地设立了屯田制度,这使鄂温克族开始熟悉了农业。农业的引入使部分人逐渐放弃了原始的狩猎生产。特别是清统治者于雍正十年(1732)从布特哈调派1636名鄂温克士兵到呼伦贝尔时,发给了他们牲畜,这对鄂温克后来发展规模较大的畜牧业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对当地的开发。
清廷为了征收布特哈八旗所属鄂温克等族每年缴纳的貂皮,在齐齐哈尔开设一种定期的交易市场。到市场交易的有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他们用猎品和桦树皮工艺品,换回所需要的铁质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这种早期的交易,不仅促进了鄂温克等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加强了各兄弟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五)鄂伦春族对开发祖国边疆的贡献
鄂伦春族是一个以狩猎为主的民族,人口比较少,在定居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往往以三四家或七八家为单位组成一个“乌力楞”。在兴安岭2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地区里,和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满等兄弟民族长期共同生活。
17世纪,鄂伦春族狩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当时,铁器逐步进入鄂伦春族的经济生活领域,特别是火枪的传入逐步取代弓箭成为主要的狩猎生产工具,对促进鄂伦春族社会经济的变化产生了巨大作用。后金及清朝统治之前,鄂伦春族“无釜甑罄瓿之属,熟物刳木贮水,灼小石淬水中数十次,瀹而食之”。①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5,清光绪七年石印本。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化。铁器的传入,使鄂伦春族的狩猎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加上商品交换的催化作用,鄂伦春族的父系大家族结构开始分解,个体家庭逐步成为一个消费单位乃至生产单位,私有制开始出现,传统古老的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制度开始受到破坏。
鄂伦春族的社会经济一直是以渔猎、采集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产生内部的社会分工。这种经济结构顽强地存在着,交换关系在它的内部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后金及清朝的统治,使鄂伦春族与周围民族的联系日益增多,交换关系也随之发展起来。鄂伦春族与周边民族的交换关系,首先是由清朝统治时期的“贡貂”制度与“谙达”制度引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②《鄂伦春族简史》编写组编写:《鄂伦春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54-55页。。鄂伦春族向清朝“贡貂”是在每年五月举行的“楚勒罕”(盟会)大会上进行的,在齐齐哈尔的“楚勒罕”又叫“纳貂互市”,即含有物资交流意义的经济活动。
随着鄂伦春族与外界的交换关系日益发展,商品货币经济逐步深入到氏族公社的内部。商品货币经济的渗入,打破了鄂伦春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加速了鄂伦春族私有制的发展。通过商品交换而传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从而促进了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③《鄂伦春族简史》编写组编写:《鄂伦春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59-60页。
三、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
实事求是地论述历史上东北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东北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关系,是正确评价东北少数民族历史地位的基本出发点。
汉民族是一个人口规模庞大、发展历史悠久、文化积淀雄厚和内部发展差异极大的民族群体。历史上,这一民族在群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以封建政治制度的完善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性和农业文化的发达深刻地影响了周边民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产生了凝聚核心的作用。正是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和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基础。“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同属一个层次,他们互相结合而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高一层次认同的民族实体。”①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这种密切的历史文化关系,奠定了今日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历史基础。
今辽宁省境即古之辽东,是汉族世代生息之地,而今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东部与辽、吉、黑接壤处,为少数民族即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在阐述东北三省历史进程时,应突出各民族的历史主导地位。在哪个时期哪个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就应当给予该民族以主导地位。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②牟本理:《民族问题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如实地展现这一充满斑斓色彩的历史画卷,是历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当今中国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同时,正确评价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双向交流关系,是认识和解决两者关系的关键。
历来的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不存在“单向”的问题。不可否认,东北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反之,东北各民族也对中原文化及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鲜卑建立北魏、契丹建立辽朝、女真建立金朝,都曾占有黄河流域,得中国之半壁江山。他们将本民族的文化带进中原,对中原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元朝统治全国近百年,焉能无蒙古文化之影响?而满族建立的清朝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影响更为深远。同样,中华文化也影响了东北各少数民族。清朝是以满族为主体联合蒙古、汉等民族建立的王朝,不仅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大一统,而且在统治方式、统治理念等诸多方面都有了发展。开始了以“中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使“中国”和“天下”的含义基本实现了重合。彻底放弃了修筑长城进行防御的思想,代之以对边疆民族的积极管辖,对于边疆地区和内地融为一体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就东北地区而言,充分地体现在满族和东北较小的少数民族为奠定东北疆域,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巩固、捍卫祖国边疆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证明,摆正东北地区各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包括中华文化的关系,体现各民族间的交往和文化的交流交融,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对当代民族学的发展亦十分重要。
四、东北地区民族文化研究的意义
自远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东北地区,自古迄今生活着许多游牧、渔猎以及农牧结合、渔猎兼农业的民族。他们虽然族属不同,语言、文化、风俗也有差别,但是,与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各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据此,可以认定东北地区各民族古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所谓中华文化实际上应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总和,而东北各民族共创的地域文化的贡献则占据显著的位置。
中国古代东北各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文化可以说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全部复杂关系种种表现形式的总和。
“东北古文化不是中原古文化的衍生或地方变种。东北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产生了众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科技医术专家、教育家等等,在他们的游牧、渔猎、农牧相兼等特定的生产、生活中,在与自然斗争和社会生活中,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了东北各民族独特的哲学观念、宗教文化、伦理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创造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字与文学艺术、科技与教育、哲学与史学、军事文化与体育文化。对这些创造性的民族文化进行综合的比较与分析,探讨其特点、形态、发展轨迹、成就,探讨其及在中华文化史上的贡献与地位等问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学术课题”①关捷:《东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44页。。
东北地区各民族在各种文化形态上的创造,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文化对象以及中华文化发生互动、双向以至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产生都起着推进作用。在中华文化形成、发展中,各民族文化互相影响,而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影响不断加深、加强。东北民族文化中经常闪现着汉文化的烙印,反过来东北各民族文化又给汉文化以影响,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东北各民族的哲学思想是中华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伦理、习俗、文学、艺术、军事、体育等等,均是中华伦理史、习俗史、文学艺术史、军事史、体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创造的各类文化均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这些文化或文化史的特点、成就,与汉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途径、方式种种问题是东北民族文化史也是中华文化史研究中极具重要意义的课题。
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复杂历程,经历长期的自在的民族实体阶段,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交融,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②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与之相对应,中华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文化史是一个多元辩证发展的历史,它是在中华大地上多元的民族单位的世代的无穷的连续发展中形成的,是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一体中包含着多元),从一体又走向多元的对立统一过程,最终形成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据此,古代东北民族可以从地域、人种、语言上给予界定,有其独特文化史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从而体现了作为文化区系的科学性。
中国古代东北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东北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塑造新文化的历史实践,是基于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反思。它有利于加强今天的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民族的和睦团结,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是最根本的条件。考察东北地方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对东北地区各民族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判断与分析,揭示东北各民族文化在构筑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与中原农业文化碰撞接触、交流融合的发展规律,认识中华文化构成的复杂历史过程与传统特征,对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总之,东北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在于塑造新的文化,在于指向未来,在于反省文化传统中已有的东西,以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独立性,同时吸纳世界文化的合理内核,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对既定的文化现象进行考察与形态描述,更主要的是在于进行文化哲学的评价,“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①董德刚:《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新时期党的基本理论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
综观东北地区五千年文明史,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它与中国其他边疆地区不同之处,就在于东北民族参与中原地区及中原王朝(亦可为中央王朝)事务的机会最多,参与中国历史进程,左右其变化,主导其发展方向。更有东北历史上的五个民族即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都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并在一定历史时期成为主导中国的统治力量。
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具个性的多元一体”②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在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更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③参见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9月29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G127
A
2096-434X(2017)03-0001-11
陈志贵,齐齐哈尔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东北地方史;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6。关 捷,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民族史;辽宁,大连,116600。
责任编辑:刘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