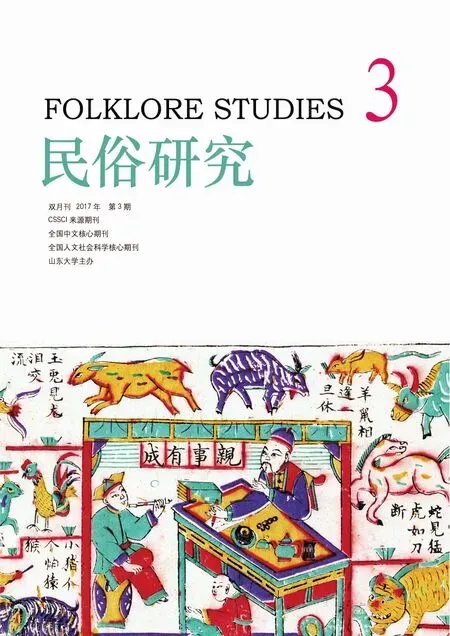从主妇到厨娘
——传统宗祠祭礼中女性角色的历史变迁
2017-01-28邵凤丽
邵凤丽 萧 放
从主妇到厨娘
——传统宗祠祭礼中女性角色的历史变迁
邵凤丽 萧 放
宗祠祭礼是传统宗族深化血缘认同、维护生活秩序的重要仪式。从先秦《仪礼》的士人祭礼模式初创,到宋明宗族对《家礼》祭礼的继承、变革实践,女性在宗祠祭礼中的角色由居于核心地位的主妇逐步被边缘化为专司祭品的厨娘。女性祭祀角色的历史变迁表明岁时祠祭的举行是对宗族生活中性别秩序与伦常关系的维护与强化。
女性;宗祠祭礼;角色变迁
宗祠祭礼是在宗族祠堂中举行的,用以深化血缘认同、维护生活秩序的岁时祭祖仪式。①宗族祠堂是分等级的,一般宗族祠堂分为宗祠、支祠、家祠。宗祠指的是宗族全体族人祭祀始迁祖的祠堂。支祠指的是因宗族人口繁衍,主要祭祀从宗族分出来的本支族人先祖的祠堂。家祠主要祭祀家族先祖的祠堂。参见王鹤鸣、王澄:《中国祠堂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5-209页。本文中使用的宗祠概念是以上三者的统称。宋以后民间祭祖活动除了以祠堂为中心的祠祭之外,还有包括以祖厝为中心的家祭和以祖墓为中心的墓祭。②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较之家祭和墓祭,祠祭作为士大夫的行为特色,基本上接受了朱熹《家礼》的提倡,发展成为明中期以后关乎宗族组织未来发展的重要仪式而存在。③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作为血缘共同体的重大仪式,祠祭在对行动者人格、品性进行内在模塑的同时,也是对社会角色、社会分工与社会地位的仪式性确认。不同性别群体在祠祭中扮演的角色、活动的空间与掌控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生活的仪式化展演。祠祭中的角色通常由男、女两个性别群体组成,既包括被祭祀的对象——祖先,也包括祖先的后裔们。后一类身份群体的构成较为复杂,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仪式所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自身属性、价值功能等多种要素的影响与制约。
关于祭礼与女性地位的关系,朱凤瀚进行了经典论述,“能用来说明女性在家族内地位高低的标志之一,就是女性在家族祭祀活动中所处的位置。因为祭祀祖先等神灵无疑是宗法制度下家族成员显示其身份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也正因此,女性参与祭祀的程度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族内部宗法形态的差异与父权的强弱。”④朱凤瀚:《论商周女性祭祀》,《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9-135页。
一、主妇:《仪礼》《家礼》中的女性角色
中国传统祭礼以《仪礼》《家礼》两部经典礼仪文献为蓝本。《仪礼》记述的是先秦时期贵族阶层的祭礼模式,后被汉唐贵族社会长期传承实践。直至经历了唐末五代之乱,世家大族瓦解、庶族社会兴起之后,宋代文人知识分子急需重新评估礼仪的社会文化价值,并重建满足庶族社会需要的祭礼模式,在司马光《书仪》之后,朱熹“援俗入礼”,编订《家礼》,为正处于形成期的新型庶民家族组织提供了祭礼规范与行动指南。
(一)《仪礼》中的女性角色
中国传统祭礼模式始建于《仪礼》,其中《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与《有司彻》三篇分别记述了士与大夫阶层的祭礼。内容虽略有差异,其建构的祭礼模式却基本相同。*文中所使用《仪礼》资料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彭林:《仪礼》,岳麓书社,2002年。
从女性出现的空间看,女性出现在房与室。先秦祭祀场所的建筑格局是室、堂、房。室地位最尊,是整个建筑的核心。祭祀时,主人位与尸位都在室中,主人在室中接神、事尸,“祝筵几于室中”,即将供神的席铺设在室中,尸入室后,“使即席坐”,然后主人拜尸。房与堂并置于室左右,西堂东房,均陈设祭器。祭礼准备时“盛两敦,陈于西堂”,分别盛有黍稷的两个敦,陈设在西堂。同时,“几席设于西堂”,主人在西堂与众宾及诸兄弟行礼。而“实豆、笾、铏,陈于房中”。主妇位在东房,“主人纚笄,宵衣,立于房中”。行礼时由房入室,礼毕立即由室返回房,“主妇出,返于房”。房也是主妇酬女宾的地方,“主妇及内宾、宗妇亦旅,西面”。
从女性参与的具体仪节方面看,女性只参与祭祀当天的部分仪式。先秦时期,正式祭祀之前要举行“筮日”仪式,选择祭祀日期。祭祀前三日要“筮尸”,通过占卜确定尸的人选。接着“宿尸”,邀请尸,再“宿宾”,直至祭祀前一日陈设器皿、洗涤祭器,这些仪式均不需要女性参与。
祭祀当天,主妇先要参与部分祭品的制作、摆放等准备工作,“主妇视饎爨于西堂下”。之后,主妇穿戴齐整,在房中等待陈设祭品,“主妇盥于房中,荐两豆:葵菹、蠃醢,醢在北”,“主妇设两敦黍稷于俎南,西上”。祭礼中主妇参与制作、陈设的祭品主要是谷物类“粢盛”,区别于主人、男子执事负责宰杀、清洁、进献的“牺牲”。除了在仪式中多次敬奉祭品之外,主妇在整个祭祀仪式中的重要角色体现在主人初献之后行亚献礼,“主妇洗爵于房,酌,亚献尸。尸拜受,主妇北面拜送”。
从《仪礼》的记载看,女性不仅参与了祭祀活动,还是以主妇的角色出现,那是否能够说明先秦时期女性拥有较高的宗族地位呢?关于先秦时期祭祀与女性地位问题,朱凤瀚通过对周代青铜器铭文资料分析认为自西周晚期贵族家族内妇女已有权参与家族内重要祭祀,介入了男性贵族的世袭领地。*朱凤瀚:《论商周女性祭祀》,《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9-135页。但陈昭容通过对周代大量青铜器铭文的比较分析予以了指正,认为周代是以男性或父权为中心的时代。祭器的制作和整体祭祀活动,掌握在男性手中;去世后享祀,男性祖先的地位亦高于女性祖先,女性并没有突出的家族权力。*陈昭容:《周代妇女在祭祀中的地位》,《妇女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1-40页。青铜器铭文的记载已经充分表明女性在祭器制作、受祀权、祭祀祖先主导权方面都没有独立的权力,为何《仪礼》中记载女性在祭祀中可以作为主妇参与行礼呢?
按照礼书的记载,先秦时期“祭必子妇俱”,即祭礼必须有女性的参与。《祭统》云:国君取夫人之辞曰: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庙、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所以备外内之官也。*(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礼器》云:君亲制祭,夫人荐盎,君亲割牲,夫人荐酒。卿大夫从君,命妇从夫人。洞洞乎其敌也,属属乎其忠也。*(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第663页。《召南·采蘋》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21页。上述礼书中的祭祀思想,受宗法制度的直接支配,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后世儒家的构拟成分。在宗法制度下,祭祀祖先首先是血脉传延、子嗣繁衍的象征,主人、主妇共同祭祀是其直接体现。其次,祭礼的岁时举行可以用来维护、强化固有的性别秩序与文化观念。“整个祭祀过程都是主人行礼开其端,主妇从之续其后,妇女的价值在主从关系的框架下在家庭中进一步实现。”*王小健:《中国古代性别结构的文化学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仪式过程中时刻反映出作为男性代表的主人与作为女性代表的主妇是“主从”“尊卑”的关系。女性在仪式中“陪同”主人献礼,主要源于女性承担生育任务使宗族得以延续,故从本质上看,其宗族地位不可能与男性平等,而是依赖于男性,并将自身融化于男性意识之中。
(二)《家礼》中的女性角色
无论《仪礼》的祭礼模式是否在当时社会被真正推行,但是作为文化传统,《仪礼》所创制的祭礼模式在汉唐社会,长期被主流社会奉为圭臬。直至唐末五代社会动荡,庶族社会成长,先秦以来的传统礼制不合时宜,宋代文人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探索适合时代需求的新型礼仪模式。在祭礼的传承方面,既受到当时社会传统礼仪重建时势的影响,也是新型庶民宗族形成过程中的现实需要。前后有张载、二程、司马光等人的祭礼探索,最终朱熹集大成者编著了《家礼》。从祭礼的应用对象和属性上看,《仪礼》是贵族阶层的礼仪行为,而朱子《家礼》关注的是作为庶民日常生活的礼仪,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为新型庶民宗族设计的祭礼模式。*邵凤丽:《朱子〈家礼〉与宋明以来家祭礼仪模式建构》,《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
在祭礼的仪节方面,《家礼》基本沿袭了《仪礼》的祭礼模式,但将具体内容大量精简。*文中所使用《家礼》资料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四库全书》第1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家礼》中规定祭祀之前要“卜日”,“时祭用仲月,前旬卜日”。“卜日”的具体做法是“孟春下旬之首,择仲月三旬各一日,或丁或亥,主人盛服,立于祠堂中门外”。“卜日”之后,直到祭祀前三天全体参祭人员要斋戒,“前期三日,主人帅众丈夫致斋于外;主妇帅众妇女致斋于内。沐浴,更衣。饮酒,不得至乱;食肉,不得茹荤。不吊丧。不听乐。凡凶秽之事,皆不得预”。到了祭祀前一天,进行准备工作,“前一日,设位陈器,省牲,涤器,具馔”。
在准备工作中,祭馔本应由主妇亲自负责,这是传统祭礼的要求。但是到了宋代,传统祭礼早已消亡,主妇也未必亲自入庖造馔。对此司马光在《书仪》专门提到这种现象,“往岁,士大夫家妇女皆亲造祭馔。近日,妇女骄倨,鲜肯入庖。凡事父母舅姑,虽有使令之人,必身亲之,所以致其孝恭之心。今纵不能亲执刀匕,亦须监视庖厨,务令精洁。”*(宋)司马光:《书仪》,《四库全书》第1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祭礼当天,主妇全程参与祭礼,从“请主”开始,直至最后的“馂”。主妇的工作有三种,一是洗涤祭器、准备祭品。如在“蔬果酒馔”的准备中,“主妇背子炊暖祭馔,皆令极热,以合盛出置东阶下大床上”。仪式结束后,“主妇监涤祭器而藏之”。在宋代,各阶层妇女都要参与洗涤祭器、准备祭品的工作。如魏侯夫人是太宗皇帝的曾孙,身份高贵,嫁给左屯卫大将军魏侯,在魏氏祭祖时,她“必斋明洁齐,岁时祭享供陈之物,手自执授”*(宋)苏畋:《宋故赠左屯卫大将军魏侯夫人玉城县主墓志铭》,《全宋文》卷一○二七,巴蜀书社,1992年,第341页。。吴夫人“每春秋祭祀,躬修仪物,秩其几筵,蠲其盏斚,祓其户牖,酒醴在樽,葅醢在皿,牲牷在盘,磬折而立,濯手而执事。”*(宋)谢逸:《溪堂集》卷九《吴夫人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43页。由于祖先祭祀活动的神圣性,有的女性会终生亲自操办,无论是生病还是年迈,都不让他人代理。张氏“岁时佐寺簿羞馈,祀必躬以严,必丰以洁,如是者二十有四年。姑殁,独春秋之事勤劳怵惕如初,他皆付幼子。”*(宋)杨简:《慈湖遗书》卷五《叶元吉请志妣张氏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59页。
二是进献各种食物。如“降神”之后、主妇陪同主人一起“进馔”,“主人升,主妇从之,执事者一人以盘奉鱼肉,一人以盘奉米面食,一人以盘奉羮饭,从升。至高祖位前,主人搢笏奉肉,奠于盘盏之南;主妇奉面食,奠于肉西。主人奉鱼,奠于醋碟之南;主妇奉米食,奠于鱼东。主人奉羮,奠于醋碟之东;主妇奉饭,奠于盘盏之西”。
三是参与馂食。“诸妇女献女尊长于内,如众男之仪,但不跪。……诸妇女诣堂前,献男尊长寿,男尊长酢之如仪。众男诣中堂,献女尊长寿,女尊长酢之如仪。”
四是主持“亚献”之礼,这是整个仪式中凸显主妇身份的关键仪节。朱熹指出亚献由“主妇为之,诸妇女奉炙肉及分献,如初献之仪,但不读祝。”*(明)邱濬:《文公家礼仪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84页。朱熹沿袭了古礼传统,让主妇进行亚献,而在宋代,很多文人知识分子都倡导由男性行亚献之礼,吕东莱云:主人为初献,亚献终献以诸弟为之*(清)王复礼:《家礼辨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5册,齐鲁书社,1997年。。
如果将《家礼》与《仪礼》进行对比会发现,《家礼》中女性对祭礼的参与度明显高于《仪礼》,女性一直与男性并存在于仪式现场,并未离开。究其原因,“宋代的礼家既想以传统礼教维系、加强伦常纲纪,又不能不正视和顺应现实环境的巨大变化,因而大都处在崇古和维新两种情绪的交织之中。”*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朱熹在《家礼·序》中指出:“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他主张对古礼“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从《家礼》的写作背景和目的上看,《家礼》是朱熹在社会失序之后为了解决礼俗矛盾的理论诉求和文化实践,他试图从理论高度为祭礼的推行提供保障,引导祭礼的发展方向,从而最终推动尊卑有序的新型宗族生活秩序的形成。延续宗族血脉、重建生活秩序是祭礼承载的重要功能,这必然要求象征宗族绵延的主人、主妇共同执礼。此时的祭礼中虽男女有别,但是不过多强调男尊女卑,而是主人主妇分工合作、相辅相成。
同时,女性在祭礼中的角色也与当时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关。有学者认为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古代中国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宋代亦如此。理学家们尽管有歧视妇女的倾向,但其思想未必就及时贯彻到社会之中,当时的社会舆论并不受理学的支配,两性地位虽不平等,但妇女仍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某种权力。*张邦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8-115页。这在一定程度为女性延续主妇角色提供了依据。
从《仪礼》到《家礼》,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古代祭礼文化模式。在该模式中,女性一直保持着主妇的角色,在家庙、祠堂中获权行亚献之礼。但《仪礼》、《家礼》中所记祭礼之女性只能代表儒家思想中理想的礼仪模式中的女性,并不能等同于它所影响、塑造的真实社会中的女性,文化传统、礼仪模式对性别的规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相应的调整。
二、从主妇到厨娘:明清时期守礼与从俗的矛盾
关于中国宋代以后的宗族组织,很多学者们的研究常常关注祠堂、族谱和族田三大要素,认为这是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新型宗族组织的普遍模式。*“所有的家族,都由祠堂、家谱和族田三件东西联接起来。”徐扬杰:《宋明以来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第20页。对此,郑振满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宋以后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而且始终起作用的因素,并不是以上三大‘要素’,而是各种形式的祭祖活动。”*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03页。他的证据是,有不少宗族直至清代仍未修谱,甚至也未建祠堂,但却不失为严密的宗族组织,这就进一步证明宗族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并不取决于修谱、建祠之类的形态特征,而是取决于祭祖活动的规模及祭祖方式的变化。
明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宗族祠堂的大量建造,岁时祭祖活动逐步在社会各阶层间推广开来。常建华提出“议大礼”的推恩令允许庶民祭祀始祖,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常建华:《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陈柯云、赵华富也指出明代中后期徽州宗族祠堂开始普及。*陈柯云:《明清徽州的修谱建祠活动》,《徽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赵华富:《徽州宗族祠堂的几个问题》,周绍泉、赵华富:《’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在宗祠祭礼的实践中,人们首先遵循《明集礼》、《明会典》等国家礼制的规定。《明集礼》第一次将《家礼》内容纳入国家礼典。*本文若无特殊版本说明,使用的《明集礼》品官、庶人祭祖礼仪文献材料均出自(明)徐一夔等:《明集礼》,《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卷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5-179页。但是从祭礼的社会传播和推广角度看,《明集礼》对明代社会礼仪发展的实际影响范围有限,“虽然《大明集礼》的品官家庙礼言明权仿《家礼》的规定,但由于《集礼》修成而未刊布,影响并不大,《家礼》主要仍是流传于信奉程朱之学的学者之间,而且流传的广度显然不可过高估计。至于《家礼》由特定的学术流派之书,转变为实际上具备国家礼典的性质,则与永乐年间纳入《性理大全》中颁示天下有关”*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稻香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永乐年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集中体现的《性理大全》将《家礼》纳入其中,继承了明朝政府对《家礼》的一贯推崇态度,并进一步将《家礼》原文直接抄录到礼典中,从形式上再次肯定了《家礼》的国家礼典地位,这样就彻底改变了私家著述的性质。之后,随着《性理大全》刊布天下,《家礼》也被在明代社会各个阶层间广泛推广和普及。“就算是利用官方力量刊布的官书,倘若只藏于官府却无人阅读,也无从发挥其影响力,与科举挂钩的《性理大全》显然并非如此”,“在当时,尤其是明代中叶之前,不仅举子读之以应试,由于其包罗甚广,也被学者认为是一部有用的学术集成”,“有些士人甚至手抄《性理大全》而深有所得”。*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稻香出版社,2009年,第171-172页。对此,杨志刚做出评价,“自《明集礼》肯定《家礼》的地位,又特别是《性理大全》收录《家礼》,《家礼》遂被官方礼制所吸纳,其性质也由私人编撰的著作,变成为官方认可、体现官方意志的礼典。有明一代,城乡读书人都把《家礼》奉为金科玉律”*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9页。。通过国家赋权,《家礼》改变了文人礼书的属性,上升为国家礼典,具有了官方话语权威。清朝《大清通礼》同样肯定了《家礼》的礼典地位,继续将其作为国家礼典在地方社会推行。但国家礼典不等同于礼仪实践,在具体的祭礼实践中是否延续《家礼》传统,让女性行亚献之礼,不同身份群体做出了不同的回应。
(一)秉持传统:主妇行亚献礼
明清时期,女性社会地位较前代明显下降。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之中,人们对于女性是否应该参与祭礼的意见并不统一,甚至有人坚持延续《仪礼》《家礼》创制的祭礼传统,让女性行亚献之礼,凸显主妇在祭礼中的重要位置。
明景泰元年(1450)汤铎刊印《家礼汇通》,完全沿袭《家礼》传统,由主妇执行亚献之礼,“主妇为之,唱行亚献礼,引主妇盥帨,由西阶上,其礼如初献仪,四龛献毕,四拜,复位,不读祝”。不仅主妇亚献,且赞礼也是女性,“用女赞”,这是《仪礼》、《家礼》中并未有过的事。汤铎还特别强调,男女拜礼不同,在“男妇拜礼”中写到女性行四拜礼,“凡拜男子再拜为礼;女子四拜为礼。若主人主妇同行礼,女子先下一拜,男子随后一拜,同下则男子一拜,女子再拜,后拜亦然。是男子再拜,女人四拜,此谓之侠拜,家常男女相拜亦如之”。*(明)汤铎:《家礼汇通》,景泰元年刻本。与《仪礼》、《家礼》的记载相比,汤铎在女性行礼方面花费了更多的笔墨。汤铎之所以编写一部《家礼汇通》,是因为有感于当时佛道盛行,习俗不正,“痛释道之昧正学,或俗流之谕奢僭”*(明)汤铎:《家礼汇通》,景泰元年刻本。,他要通过《家礼汇通》的编写坚守儒家礼仪正统,排斥佛道、习俗的干扰、破坏,重新确立儒家礼仪秩序,“俾人皆由于正礼而学,不惑于他技,家孔孟而户朱程,谨名分而崇爱敬,修身齐家之道勃然而兴,慎终追远之心犹可复见,矢心无二,勉助而成,然于国家化民之意或亦不无小补云”*(明)汤铎:《家礼汇通》,景泰元年刻本。。
与汤铎坚守《家礼》传统不同,明代著名学者邱濬(1421-1495)主张在传承传统的同时,应该根据时代变迁进行适当的礼仪变革,以适应日益世俗化的日常生活需要,也正是他因俗而变的礼仪创造,使他被誉为“继承朱熹《家礼》而使之世俗化之第一功臣”*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邱濬乃明代中期大儒,怀抱“以礼经世”的宏伟抱负,有感于佛道盛行,礼教不倡,于是在丁忧居乡时期编写《文公家礼仪节》一书,此书成书于成化十年(1474)。他在序言中说:“窃以为《家礼》一书,诚辟邪说,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诵此书,家行此礼,慎终有道,追远有仪,则彼自息矣,儒道岂有不振也哉!”*本文若无特殊版本说明,使用(明)丘濬《文公家礼仪节》,均出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31页。为了重振儒道,必须推进礼仪进入日常生活,“是以不揆愚陋,窃取文公《家礼》本注,约为《仪节》,而易以浅近之言,使人易晓而可行,将以均诸穷乡浅学之士”。为了达到“易晓而可行”的目标,主妇亚献的传统不一定必须遵从。在邱濬看来,主妇必须参加祭礼,按照《家礼》传统,从前三日斋戒,一直到祭祀当天,全程参加。如进馔时,“主人升,主妇从,执事者一人以盘盛鱼肉,一人以盘盛米面食,一人以盘奉羹饭。主人、主妇逐位自进,子弟进祔位,毕。”邱濬与《家礼》的不同之处在于将亚献设定为三种情况,一是主人行亚献,二是主妇行亚献,三是主人之兄弟长者行亚献。“主妇亚献,则诸妇之长者逐位进炙肉。若主人或其兄弟之长者行,则次长者进之。”
虽然从主观意愿上看,邱濬本意坚守祭礼文化传统,但是生活现实与礼仪传统的疏离是不可忽视的,现实生活中极度被压抑的女性的不可能在神圣的祭礼中获得存在空间,她们虽然承担着传宗接代、延续后嗣的重任,但是“男女有别”“闺门整肃”的律条早已把她们排除出祠堂亚献之礼的多种选择就是这种守礼与从俗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
从根本上看,无论是汤铎,还是邱濬,秉持的都是汉代以来形成的政教礼俗观,在他们看来,礼是对个人行为、社会秩序进行有序规整的重要工具,礼的象征性意义必须给予保留。也正是为了延续祭礼文化传统、展现祭礼的双重内涵,他们才不顾世俗生活变迁的现实,继续给予女性主妇的角色。但社会生活的发展不是文化传统所能禁锢和掌控的,生活的变迁不断对传统礼仪模式提出挑战,迫使人们在守礼与从俗的矛盾中进行抉择。
(二)发明传统:女性角色的多样化
在守礼与从俗的矛盾抉择中,一部分人发明了传统。所谓发明传统是指沿用《仪礼》《家礼》创制的祭礼模式,允许女性参与祭礼,但不行亚献之礼。
第一,保留女性的主妇角色,主张“夫妇并献”。毛奇龄(1623-1716)说“凡祭子妇俱”,“主祭者与主妇俱,诸子助祭,与诸妇俱”。*本文若无特殊版本说明,使用(清)毛奇龄《辨定祭礼通俗谱》,均出自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主妇即主人之妻,主人之母不能担任主妇的角色,“父死而母尚在,则母不主祭,但统诸妇助祭者,而先其列,父妾则稍后,所谓子无嫡庶,而母有嫡庶,仅与诸妇之在先列者差立而已”。
在准备阶段,主人省牲,杀牲,瘗毛血。主妇则“授内饔(即内妇婢)簠簋(十二)、清钟(十八)、笾(四十八,上祭加十六),豆(四十八,上祭加十六)”,还要“帅诸妇(弟子侄妇)办簠簋、笾豆所需实者。”
祭祀当天,主妇“各易盛服,诣家堂”。站立的位置次序是“主人、主妇居中,弟以次东,弟妇以次西为一列,子侄以次由中至东,妇以次由中至西为一列。有母列西上一位,有庶母列西稍上一位,女弟与妇列,女与子侄列。若有次嫡并贵不主祭者,则与妇侧主人主妇后为第二列,而降子侄为第三列,如子侄贵者则但与妇侧主者后,仍第二列”。仪式开始后主妇要不断配合主人行礼。安主时,“主人奉安考主,妇奉安妣主”,荐腥时,“主人奉盘,主妇奉副”,初献时“主人奉清盏,主妇奉醴盏”,再献时“主人奉清爵,主妇奉醴爵”。对此,毛奇龄说:“古献祗一爵,不知考妣分合何等。今合主人主妇为并献,而以二爵进考妣,较为近礼。”之后进粢饮,“主人奉簠簋,主妇奉清钟”,进笾豆,“主人奉笾,主妇奉豆”,饮福受胙时“主人主妇诣香案前”,神赐饮食时“主人啐酒,主妇哜脯”。
毛奇龄主张主妇应该参与祭礼,这是对《仪礼》《家礼》传统的遵循,但是按照他的礼仪设定,主妇不仅参与了祭礼,且要陪同主人向祖先进献各种祭品,并一起接受祖先的赐福。从仪式的参与度方面看,毛奇龄一方面扩展了主妇对祭礼的参与度,同时他又通过剥夺主妇的亚献权,消解了主妇在整个祭礼中角色的特殊性。“夫妇并献”现象的出现表明,在毛奇龄的宗族礼仪观念中,“凡祭子妇俱”的古礼传统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仪式中的主妇已然丧失了独立的性别身份,完全成为男性的附属品。
第二,“存礼意”,缩减女性参与仪节。清代林伯桐(1778-1847)特别关注祭礼的施行问题,撰写了《品官家仪考》《士人家仪考》《人家冠婚丧祭考》。在《品官家仪考》中他详细描述了女性参与祭礼的情况。他指出虽然按照祭礼传统,女性必须参加祭祀,“按祭祀之礼,必夫妇亲之,故男女皆入庙”,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世家大族亦罕闻有行此者”,世家大族之所以不让女性参与祭礼,主要原因是宗族祭祀,参与人数众多,且“亲疏咸在”,这时候“妇女出入不侵”。*本文若无特殊版本说明,使用(清)林伯桐《冠婚丧祭仪考》,均出自《丛书集成三编》二十五,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431-442页。
受“男女有别”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女性不能同男性一起参与公共活动,那么应如何处理礼与俗之间的矛盾呢?林伯桐坚持“但其仪如此,礼意所存固当考也。”为了“存礼意”,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主妇在相应仪节中进祠堂进献祭品,但不能停留在祠堂中参与仪式,进献之后应退回房。在初献时,“主妇率诸妇出于房,荐匕箸醢酱于几前案北(谓分荐于四世各几之前,各案之北),跪,一叩,兴,遍及袝位(谓分荐于东西两袝位),退,皆入于房。”亚献时,“主妇率诸妇和羹以实于鉶,又实饭于敦(按鉶敦皆早在房中者),出荐于案(分荐于四室前之各案),荐腊肉炙胾(此实于笾与豆者),皆遍跪,叩,兴,退入于房。”终献时也是如此,“主妇率诸妇出于房,荐饼饵与果蔬,叩,退入于房。”三献之时,主妇都要从房中出来,进入祠堂,进献食物,然后返回房中。主妇不能在祠堂中与男性一起参与其他仪节,这样做是为了“存礼意”,实现女性作为主妇的象征性。林伯桐允许女性在祭礼中保留部分权力,但此种特权仅限于品官之家,对于士庶人家,祭礼无需女性参与。虽然林伯桐没有解释这其中的原因,联系到“礼不下庶人”的古礼传统,很容易理解林伯桐的用意,品官之家应保留礼仪的象征性,但是士庶之家便可从俗,女性不必参加祭礼。
元代郑氏祭礼遵行《家礼》,“今遵《家礼》,而略有损益者,盖时或有所禁,而礼乐之器之文不得不异,吾求其质而已矣。”*(元)郑泳:《郑氏家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11-414页。整个祭祀仪式中女性都没有出现,只有到了最后的馂食仪节中,“家长中坐,男女东西相向而坐”。在郑氏宗族,女性不可以参加祠堂中的祭礼,仅可以参加最后的馂食,与男性一同接受祖先的福佑。另外,在宗族日常礼仪活动中,女性可以参加朔望两日的参拜礼仪,“家长率众子妇诣祠堂前”,参拜之后,所有人来到有序堂,“家长出,坐有序堂,男女左右坐定”,听子弟宣读家训。郑氏宗族中并未将女性完全排斥在宗族礼仪活动之外,女性可以参与日常性的参拜礼,但是祭祀祖先时只能在最后出现。
在这些发明传统的人看来,祠堂早已是被男性主导的神圣空间,性别身体决定了女性要远离祠堂,自然也不必参与祭礼,亚献权力的丧失是必然结果,但是“夫妇共之”的古礼传统依然强固。人们不能完全脱离祭礼传统,祭礼传统作为惯习力量一直在束缚着人们的行为与选择。如果祭礼作为香火传承、延续后嗣的象征性意义必须保留,女性不能在祭礼中完全缺失,其性别身份的象征性必须在特定仪节中予以保留。
第三,增加、扩充女性参与仪节,认为女性不仅可以参加祭礼,甚至可以主持祭祀。明清时期,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也是《家礼》实践的重要场域。按照徽州习俗,祖先祭祀通常是男性成员参与的活动,女性不必参与,或是只能参与最后的馂食环节。但是特殊情况下,则允许宗族中德高望重的女性主持祭礼。如程母汪孺人,归长公后,长公长期在浙江经营商业,家里内外家政“大者蒸尝,次者庋阁,次宾客燕享”,“一切倚办孺人”。*(明)汪道昆:《太函集》,黄山书社,2004年,第895页。程母潭渡许氏,归封公,“躬摄家秉,事无巨细,无恩封公”,作为家中长媳,宜人“内奉宗枋,外应闾里,无所失”。*(明)汪道昆:《太函集》,黄山书社,2004年,第897页。汪道昆之母去世时,诸母回忆:“……祭礼燕享,夫人能也……为吾党祭酒”。*(明)汪道昆:《太函集》,黄山书社,2004年,第930页。在徽州,不仅有正妻,还存在继室担当主祭的角色。元君安人余氏为继室,对丈夫前妻所生四子视为己出,主管一切家务,操办祭祀大事,“家事悉委之夫人,自朝夕饗餐,以致祭祀宾客燕享,诸子必禀命夫人”。且受到家人好评曰:“女正位乎内,男位乎外。……富家之吉,夫人殆庶几为焉。”后来遵循丈夫的遗命,“建祠修谱,凡鸩工庀材以次兴作,夫人论诸子某经理某事,某督率某工,某出某处,届期毕效日落成”。*(清)乾隆《王充东源洪氏宗谱》卷10。
徽州女性可以参与祭礼,甚至主持祭礼,成为仪式的核心人物,承担了超越传统礼制赋予女性的权力。这种现象的存在,既与《家礼》设定的祭礼文化模式不同,又与明清时期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不符。那么,应如何解释徽州女性参与祭祀、主持祭祀的这一特殊现象呢?在徽州地区,一些宗族有女性主持祭礼的文献记载,但女性主持祭祀活动在徽州地区并不具有普遍性。徽州地区长期恪守礼教传统,女性日常行动受到宗族的严格约束。黟县环山余氏宗族提出“闺门内外之防,最宜严谨”。余氏宗族认为“古者,妇人昼不游庭,见兄弟不逾阈,皆所以避嫌而远别也。”他们也要按照古礼传统,“凡族中妇女,见灯毋许出门,及仿效世俗往外观会、看戏、游山、谒庙等项,违者议罚”。*(清)《环山余氏宗谱》卷一《余氏家规》,咸丰年间,安徽黟县。徽州宗族对族内女性日常行动的严格约束和限制并非余氏宗族特有,而是明清时期徽州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此,唐力行认为徽商的发展得力于商人妇的大力支持,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商人在实际经营中的需要促使宗族制度强化,封建纲常对妇女的束缚比以往更甚。*唐力行:《论商人妇与明清徽州社会》,《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4期。
徽州女性一方面被封建纲常所束缚,一方面由于男性长期外出经商,不得不由女性操持家中事务,有时还要主持祭祀。这些可以参与祭祀、主持祭祀的女性背后通常是男性主祭不在家中,自己是以母代子、以妇代夫主持祭祀,仪式中的身份具有双重性,既有女性自身的身份,也有他所替代的男性身份在场。可以说,正是这种身份的双重性才赋予了女性特殊的仪式权力,女性主祭的出现是徽州特定地域文化中礼俗调和的产物。
(三)摒弃传统:女性被逐进厨房
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是中国传统宗族制度发展的典型区域之一。伴随着宗族制度的发展,祠祭也获得了实践场域。在祠祭发展过程中,徽州人凭借朱熹桑梓之乡的地域性特点,产生了强烈的地域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在这种浓重的地域文化情感的推动下,徽州人不但熟知《家礼》内容,且一切家族礼仪都严格遵照《家礼》的设定进行,“古人重礼教,冠婚丧祭之仪载在文公《家礼》甚详,吾族中家长宜于每月朔望令子弟通儒业者集众人而讲明之,遇事则细陈条款,一一依之而行”*(清)《霞川汪氏重修族谱》,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在祭礼的操作过程中,徽州家族按照《家礼》祭礼模式设定仪节程序,“祭祀每年以春秋仲月所首辛为期,头首先期洒扫以俟拜献,其祭仪悉遵文公《家礼》”。*(清)《霞川汪氏重修族谱》,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徽州家族选择了与《家礼》不同的操作方式,即由男性主祭或陪祭进行亚献,主妇不进行亚献。献祭者的更换是对《家礼》祭礼模式的重大调整。《家礼》规定主妇及家族女性均应参加祭礼。在祭礼中,主妇与主人对立而站,由主妇亚献、献茶,其他妇女参与行礼。到了丘濬时,他提出妇女应参加准备工作和正式祭礼。前一日“涤器,主妇帅众妇女濯祭器,洁釜鼎”。具馔,“主妇帅众妇女具祭馔”。在三献礼中,由主妇及诸妇女献馔。但在明清时期徽州家祭仪式中,女性没有出现在仪式现场。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文献,尤其是在家谱的祭祀条目中,很少提及女性与祭祀的关系问题。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资料出现在明万历年间《林塘范氏宗规》中。范氏家族规定“今祠惟焚黄者,同主妇入祭点茶外,清明等祭,俱惟男子。”*(明)《新安林塘范氏宗规》,万历年间,刻本。
在明清社会生活中,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女性的活动空间被严格限制。在家庭生活中,女子必须服从“四德三从之训”,且男子有责任管教女性,“若以姑息为爱,稍听妇言,则非但唇舌渐多,伤残一家和气,而昏惑日深,酿祸不小矣,务相禁戒”,“违者罚及夫男”。在“四德三从”的束缚之下,“各妇女非本宗嫁娶吊丧,毋得轻出”。*(明)《新安林塘范氏宗规·宗祠条约》,万历年间,刻本。
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管控之外,一些宗族也说出了具体困难。这些宗族称“按礼主人、主妇例应致祭,众子众妇从之,古之制也”。但是现实生活中困难重重,致使他们无法沿袭古礼。困难一是祭祀时人数众多,祠堂空间有限,没有地方留给女性。宗族分布“星罗棋布”,人数众多,祭祀时“祠屋虽广”,“尤惧其跪立无地也”。二是远地祭祖,来回行路不便。“且礼妇女无百里奔丧之文,况祠祭乎?则子孙告享而诸妇似不必与焉,亦权之正矣。”*(清)《太平曾氏彤公房谱·祭礼论》,湖南邵阳,清末刻本。在明清族谱中,像曾氏宗族一样较为详细地阐明女性不能参祭原因的极少,人们更倾向于直接将女性驱逐出祭祀现场,族谱中不做任何记载。因而,无论是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考虑,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女性都不必参与祭礼,或者说在男性话语权力下女性被彻底剥夺了祭祀权。
作为宗族共同体的标志性建筑,传统宗族中的“祠堂是成年男性的世界,女性一般不准进入祠堂”。*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83页。葛学溥在20世纪初对中国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发现,凤凰村共有三个宗祠,人们在里面举行祭祀活动。仪式上出场的是男性家长和宗族的男性后代。他们向祖先进献祭品,给祖先鞠躬,最后一起参加丰盛的宴会,还要平等的分享祭祀食品。整个仪式上没有女性的身影。*(美)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周大鸣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
林耀华同样指出直至20世纪三十年代,福建乡村中的女性依然不能参与祠祭活动。在义序,“祠堂祭祀可以分两部:一是族房长绅衿代祭,一是族人合祭。所谓族人合祭,因地点的限制,亦分各支分祭,族人只包括已成年的男子,妇人和子女不在此例。”*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第51页。因为在义序地方文化传统中,女性一直是男性的附属品,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女性出头露面。“家庙十规”中明确规定“禁妇人投祠”,“投祠原非美事,况妇人乎?妇人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有夫有子,而妇人出头,成何体统?今后若非夫亡子幼,并夫与男出外者,藉泼闯投,无论理之是非,其夫与男必加重罚。”*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第201页。
按照以上论说,女性不用亲自到祠堂参祭,但并不意味着女性不用参与祭礼的相关事务。实际上,祭礼所需要的祭品通常都是由女性负责烹制的,厨娘是女性的重要角色。从《仪礼》到《家礼》,再到明清祭礼实践,祭品的烹制一直都是女性的重要工作。一旦女性不烹制祭品,就会被批判失礼,清代颜元说:“想见宋时妇女骄踞之态,观《家礼》中妇人衣衰絰带不为制,祭礼中妇人不亲厨办祭,先儒屡言之,可见彼时内庭不足为礼。”*(清)颜元:《颜元集·礼文手抄》,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年,第387页。清代张文嘉也说:“凡祭祀专在诚敬,须主妇亲入庖厨监视,务令精洁,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犹防猫犬虫鼠及童稚侵汙。”*(清)张文嘉:《重定齐家宝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5册,齐鲁书社,1997年。虽然在大宗族中,主妇未必亲自烹制祭品,但是古礼传统还是被人们高度赞扬的。在百姓之家,祭品的烹制自然是女性的工作,鲁迅在《祝福》中这样记载:“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地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地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5页。将女性与祭品联系起来并非偶然。这与女性的社会分工有关,长期以来,女性主内,负责烹饪,到了祭祀时人们自然将祭品准备工作分配给了女性。同时,女性负责准备祭品,还具有另外一重意义。祭品自古以来就带有神圣性,是沟通神人的重要媒介,后人以祭品敬献祖先,以示孝道,祖先以祭品回馈后人,以示福泽。因而,女性烹制祭品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参与祭礼的一种特殊方式。
三、结 论
宋明以来,随着宗族组织的扩大发展,岁时祭祖成为民众生活的大事。从女性的参与方面看,常建华指出明代时“不论是家祭还是墓祭,都有女性参加,说明女性在家中和社会上还是有相当地位的”*常建华:《观念、史料与视野:中国社会史研究再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3页。,但是祠祭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明清时期,伴随祠堂的大量修建,加之士大夫的提倡和推动,祠祭成为宗族组织最为重视的仪式活动。在祠祭中,女性的角色由居于核心地位的主妇逐步被边缘化为专司祭品的厨娘,女性几乎不会出现在祠祭现场。女性在家祭、墓祭和祠祭中不同的角色表明三种祭祀活动的性质与功能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弗里德曼指出在中国东南宗族中,“祠堂举行的仪式由男人主持,由男人参加;他们的女儿和妻子不直接参与仪式的过程”,“相反的是,在祖先崇拜方面,无论是理论上女性的地位如何低下,她们在家里表演的仪式中则占中心的地位。她们照料家里的神龛,而且可能完成每天的燃香仪式。……正是女性主要负责家庭的祖先祭祀仪式,纪念祖先的忌日”。*(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究其原因,“宗族不是扩大的家庭,宗族较高裂变单位举行的祖先崇拜与家庭内举行的祖先崇拜也有点区别。在家祭中,人们与他们在生活中熟知的逝者联系在一起,而且能够向他们贡献,使其在另一个世界中快乐。另一方面,祠堂中举行的祖先崇拜仪式基本上是集体行为的方式,社区的权力和地位之结构以仪式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宗族的所有层面,亲属体系所要求的裂变单位……在仪式过程中得以表达和强化。这是一致的仪式。但是在祠堂表演的仪式中,人们是不平等的,这种一致是和不平等连在一起产生的。”*(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4页。家祭是在家中进行,墓祭也是以家庭、家支为单位,几乎没有“外人”在场,整个仪式要表达的是子孙的孝思之情。祠祭是在作为宗法制度核心和象征的祠堂进行,在“报本反始,以伸孝思”的祭礼核心精神之上,更是“为了收族、治人,巩固封建统治”*赵华富:《徽州宗族祠堂的几个问题》,周绍泉、赵华富:《’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2页。,进而迫使女性完全退出了祠祭空间,祠祭彻底转变为展示男性话语权力、强化固有性别秩序和血缘伦理的工具性仪式。
[责任编辑 刁统菊]
邵凤丽,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辽宁沈阳 110036);萧放,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本文是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生仪礼传统的当代重建与传承研究”(项目批准号:14AZD12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