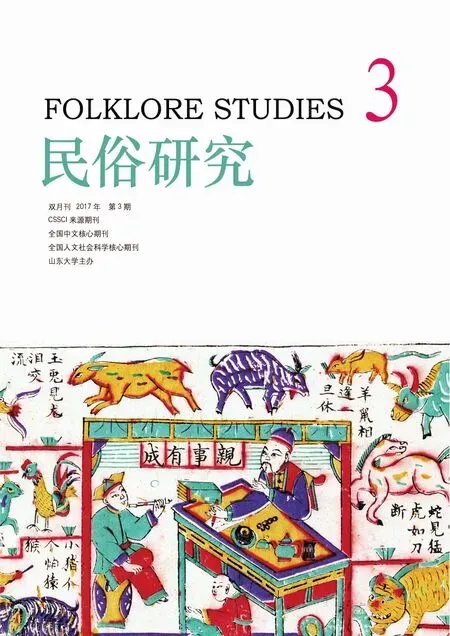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
——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2017-01-28陆薇薇
陆薇薇
引 言
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
——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陆薇薇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协同合作;介入式日常实践;民众幸福
引 言
迄今为止,日本民俗学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以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及其弟子为首的创立期;二,由宫田登、福田亚细男等引领的学科体系建设期;以及目前所处的多样化探索期。研究方法、目的、对象的不统一及扩散性是第三代的特征。①[日]菅豊:《民俗学の悲劇―アカデミック民俗学の世界史的展望から―》,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化》2012年第93号,第34页。
日本民俗学界中,由第二代学院派民俗学者确立的历史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占据着主流地位。然而从80年代末开始,也陆续有学者挑战固化的学科体系,试图跳脱历史中心主义的束缚。尤其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部分学者在了解到美国、欧洲、中国等地的民俗学发展现状后,深感日本民俗学在某些方面的滞后,他们积极探索学科的走向,力求打开学科的生存困境。如岩本通弥借鉴德国民俗学的经验,试图将民俗学转向生活学、经验主义文化学,完成德国民俗学范式在日本的本土化建构。再如菅丰,熟知美国学院派民俗学(academic folklore)与公共部门民俗学(public sector folklore)之间半个多世纪的纠葛,试图跨越学院派与公共派之间的鸿沟,立足日本国情开拓一条崭新的民俗学之路,即新在野之学②“新在野之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泛指当今在世界各地开展的一种强调普通民众的参与、以民众为主体进行协同合作的学问,是以这一形式存在于各领域的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的总称。狭义则专指其在民俗学领域的表现。本文中采用狭义的含义。,亦称新公共民俗学。
菅丰《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讨论了非遗时代文化保护政策实施过程中民俗学者的立场问题。一方面,他对不假思索便轻率参与文化保护政策的学者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他认为那些因反感文化政策的过度政治性而拒绝参与文化保护的学者有些曲高和寡,脱离实际。民俗学者选择以上这两条路而形成的二元对立局面,正如学院派民俗学与公共部门民俗学在历史上的对立如出一辙,而问题的解决在菅丰看来都有赖于第三条路——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的创成。该文可以说是菅丰的新在野之学理论在民俗学者如何应对文化保护政策这一领域的运用,然而由于篇幅所限,其理论核心及缘由并没有得以充分阐释,在被转引和评述时存在被误解之处。
菅丰的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并不同于狭义的公共民俗学,即公共部门民俗学。*[日]菅丰《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提到:“笔者所主张的公共民俗学虽然也包括上面所提到的公共部门的公众民俗学,但并不仅限于此,而是进一步注重学院派民俗学者从事社会实践的一种民俗学方法。”1980年代开始,美国民俗学界也开始积极探索学院派与公共派的融合之路*[美]罗仪德、游自荧、丁玲:《美国公共民俗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美国民俗学会理事长Timotby Lloyd(罗仪德)访谈录》,《民俗研究》2013年第6期;[美]芭芭拉 克什布拉特-吉布利特:《误分为二:民俗学的学院派与应用派》,宋颖译,《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3期。,为公共民俗学注入了新的内容,虽然菅丰受到美国公共民俗学思想的影响,但其试图建立的新公共民俗学植根于日本本土,与美国的新公共民俗学有本质区别,旨在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的“在野之学”进行回归和再构建。菅丰指出:“在日本能够让具有‘在野之学’特征的民俗学重生,形成与美国公共民俗学不同的‘新公共民俗学’=‘新在野之学’*将日本“新在野之学”等同于“新公共民俗学”是菅丰的初衷,然而由于“新公共民俗学”这一名词来源于公共民俗学,容易让人误将其等同于公共民俗学,产生概念的混淆。与先生商定认为“新在野之学”一词更为恰当,故本文在论述时,除引用原文外,对其理论以“新在野之学”的形式加以表述。,这应该成为今后日本民俗学前进的方向之一。”*[日]菅豊:《民俗学の喜劇―「新しい野の学問」世界に向けて―》,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化》2012年第93号,第224页。针对部分民俗学者对于“第三条路”的误解,菅丰解释说:“公共民俗学不是民俗学的一个门类。它超越了专业细分、能让所有民俗学研究者都参与进来,代表了民俗学的发展‘方向’。它不是一种基于特定立场的民俗学,而是超越了被隐蔽和割裂的立场,使知晓、学习、理解民俗的人们均能够介入其中的民俗学。”*[日]岩本通弥、菅豊、中村淳:《民俗学の可能性を拓く―「野の学問」とアカデミズム》,青弓社,2012年,第111页。可见,菅丰并非将公共民俗学列为民俗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而是视作现代民俗学的一个新方向,试图构建日本民俗学的新理论。
一、新在野之学的提出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主页上载有菅丰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大约从2006年开始,菅丰陆续发表了与公共民俗学相关的论文并合作编写了一些理论著作。2013年菅丰独著的《走向“新在野之学”的时代——为了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联接》一书由岩波书店*岩波书店创立于1913年,是日本最具权威的出版社之一。出版发行,该书是其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岩波书店创业百年纪念书籍之一。
(一)日本民俗学的在野特质
菅丰“新在野之学”的提出首先源于对日本民俗学原点的思考。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推行富国强兵之策,并为此积极引进西学,形成了所谓的“官学”学术体系。与此同时,地方上兴起“民间学”的热潮,大有对抗官学之势。“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就是民间学的代表。”*[日]鹿野政直:《近代日本の民間学》,岩波書店,1983年,第7页。
20世纪初,被称作第一代的柳田国男及其弟子创立了民俗学,严格说当时尚无民俗学一说,而是叫乡土研究或民间传承论。1935年,民间传承之会(日本民俗学会前身)成立,但与官学体系中的所谓学会有本质的区别,“它的实质是对地方‘在野之学’的鼓舞并将地方成果进行全国性统合”*[日]菅豊:《「新しい野の学問」の時代へ―知識生産と社会実践をつなぐために》,岩波書店,2013年,第116页。。其实早在民间传承之会成立以前,日本各地民众就对本土文化进行过积极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这为民俗学的创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冈正雄甚至称柳田国男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提醒世人关注普通民众的贡献。
可见,日本民俗学在草创期体现出有别于其他学问的“在野”特质,它是相对于官学而出现的民间学;是有别于中央的地方学;是由非专业人士结集而成的杂家之学;是脱离了学术机构的草根式的学术探索。故被后世称作“在野之学”。
然而之后,日本民俗学迈向了学科建设之路。拥有民俗学专业素养的第二代学院派学者活跃在第一线,他们编写了民俗学概况等教科书,按照学科建设规范将民俗学这门学问“体系化、组织化以及制度化”*[日]福田アジオ、菅豊、塚原伸治:《「20世紀民俗学」を乗り越える》,岩田書院,2012年,第12页。。“学院派民俗学将原本支撑着日本民俗学发展的非专业研究者默默地驱逐出了学术舞台,从而失去了日本民俗学作为‘在野之学’的这一实践性特征。(中略)学院化路线实施之后,学会中虽然还能够看到非专业的民间研究者的身影,但民俗学研究及讨论的空间还是被分隔了开来。”*[日]菅豊:《民俗学の喜劇―「新しい野の学問」世界に向けて―》,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化》2012年第93号,第223页。
在野之学的日文原文为“野の学問”,“野”在日语中有两个读音,分别是“ya”和“no”。“no有民间之意,将学习者引向田野;ya有野党、下野的语感,强调对抗性”*[日]佐藤健二:《方法としての民俗学/運動としての民俗学/構造力としての民俗学》,小池淳一編:《民俗学的想象力》,せりか書房,2009年,第281页。,菅丰指出:“在野之学的含义包括学问的民间性*民间性一词的日文原文是“在野性”,因为直译会造成与在野之学中“在野”一词的混淆,所以意译为民间性。、田野现场的重要性、利民的实践性及与权力、权威、学院派的对抗性。”*[日]菅豊:《「新しい野の学問」の時代へ―知識生産と社会実践をつなぐために》,岩波書店,2013年,第5-6页。这些含义在其倡导新在野之学中均有所体现,可以看出他对日本民俗学发展过程中丢失在野特质的痛心,对回归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渴望。然而菅丰新在野之学的提出并不单单意味着对在野之学的回归,还意味着在当代学术格局及社会潮流中的民俗学再建。
(二)学问公共性的时代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学问公共性(应用性)*90年代多使用“应用性”一词,相当于当下所说的“公共性”。菅丰认为两个词基本同义,公共性的说法相对更能体现出与社会、与公众的关联性,更具社会影响力。的讨论愈演愈烈。学问不应被束之高阁,而应向社会敞开,与社会接轨,为社会服务,这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动向。同一时期,中国民俗学也曾有此趋势,1988年张紫晨提出“发展应用民俗学”,1995年陶思炎发表了《论民俗学体系的重构与应用民俗学的建设》,2001年出版《应用民俗学》,提倡发挥民俗学的潜能为社会服务。而日本民俗学“虽然在柳田国男创始之初有过经世济民、贡献社会的倾向,但之后除了宫本常一等少数民俗学者外,这种倾向被淡化了”*[日]岩本通弥、菅豊、中村淳:《民俗学の可能性を拓く―「野の学問」とアカデミズム》,青弓社,2012年,第83-85页。。
菅丰在哈佛大学访学时期,即已充分接触和了解了美国的公共民俗学、公共历史学、公共考古学、公共社会学、公共人类学等。美国这些冠以“公共”二字的学科,例如公共民俗学,最初是由公共部门引领的,这与学问的公共性不是一回事,但至少打破了学院派一统天下的格局。菅丰指出:“当(我们)思考‘学术的公共性’或‘研究的公共性’这一问题时,恐怕不能不将‘知识的支配权(governance)’现状考虑在内。”*[日]菅豊:《「新しい野の学問」の時代へ―知識生産と社会実践をつなぐために》,岩波書店,2013年,第155页。governance一词与government相对,government指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而governance则指与组织、社会相关的所有成员自觉参与,自由表达意志并形成合意的协同统治体系。在governance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的今天,菅丰认为“在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应该打破专家学者自上而下的引领方式,形成多方平等参与、协同合作的模式”*引自菅丰2016年8月在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集中授课时的PPT讲稿。。
这里再提一下菅丰早年使用的一个理论“共有资源管理论(Commons)”,探讨多个主体共同使用和管理资源时的协作制度。该理论被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学等多个领域。尤其在环境学领域,为了应对自然资源的枯竭,学者们在“共有资源管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地域共同体内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菅丰使用该理论的著作出版于2006年,书名为《河川属于谁?——人和环境的民俗学》。该书基于对新泻县大川乡20多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当地传承了300多年的传统捕鱼法,揭示传承背后“共有资源管理”制度的形成和变迁。人们看似摒弃私欲、自觉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实际是“共有资源管理”这一共同使用、共同管理制度作用的结果。
学问的公共性问题实质也是学问归属的问题。从“河川属于谁”到“学问属于谁”,我们可以看到菅丰思想的内在一贯性,河川是属于大众共有的,学问也是如此,不仅属于学者,也属于普通民众。共有的河川需要共同管理,共有的学问需要共同创造,这是新在野之学提出的基础。
(三)新一轮民间研究热
此外,日本社会的新一轮民间研究热为菅丰新在野之学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19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出现了又一轮民间学的热潮,如吉本哲朗和结城登美雄的本地学、宇根丰的百姓学、赤坂宪雄的东北学等等,还有一些没有冠以学问之名,如宫内泰介的市民调查等,这些各地方的民众自主进行的调查研究如火如荼,而且已颇具专业水准。
菅丰特别介绍了一个实例,即NPO法人“宍塚的自然和历史之会”。该会为保护茨城县土浦市以宍塚大池为中心的里山区域而组建,有会员600名。1989年正式成立后,每月进行一次自然观察活动,从1990年开始进行宍塚大池的历史和环境的采访调查。1999年出版发行《所听所写 里山*一般指靠近村落的山,后山。的生活》一书,2005年出版发行其续集。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地域居民自己成为主体来计划、调查、研究、编写、出版的“民俗志”,但无论是内容的精细程度还是社会影响力,比民俗学者及行政机构主导编撰的民俗志有过之而无不及。*归纳自[日]菅豊:《「新しい野の学問」の時代へ―知識生産と社会実践をつなぐために》,岩波書店,2013年,第210-217页。
“与民俗学作为‘在野之学’被创立的年代相比,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发现身边的问题,收集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发布、实践,建立组织、获取资金支持的能力及热情要高得多得多。由此,专业知识得以普及化、大众化,作为专家的学院派学者的地位则被相对化、去特权化。”*[日]菅豊:《「新しい野の学問」の時代へ―知識生産と社会実践をつなぐために》,岩波書店,2013年,第206-207页。可见,当前日本社会的民间研究热与民俗学草创期相比,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大幅提升。正是在这样“高水平”的民间研究热潮,即广义上的新在野之学不断涌现的背景下,菅丰的民俗学新在野之学理论应运而生了。
二、新在野之学的内涵
菅丰为新在野之学给出了一个“暂定”的定义(因为他觉得随着公共民俗学进一步的发展,定义也将不断被检验和完善):“所谓(新)公共民俗学*为了区别于过去的公共民俗学,笔者在翻译时加上了“新”这个字。是民俗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它要求在理解性质相异的立场的同时,跨越这种差异,使多样化的行为体得以协同合作;要求各行为体一方面认识到文化的所有权及其表征行为的权威性这一难题,另一方面努力获得对其进行表现的正当性,积极介入到对象人群的社会文化中去,为了他们的幸福,将该地域及其人群、文化加以客体化并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进而对与这一整体相关的自我与他者的实践及研究以一种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重新把握。”*[日]岩本通弥、菅豊、中村淳:《民俗学の可能性を拓く―「野の学問」とアカデミズム》,青弓社,2012年,第119-120页。
(一)协同合作与正当性(legitimacy)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在野之学,此处引用一下美国公共民俗学的定义。这是1990年代的定义,已不同于最初的公共部门民俗学,包含了更广阔的内容:“民俗传承人通过与民俗学者或其他专家的共同努力,推动了新形势和新语境下民俗传统在其原生社群内外的表现与实践。”*Baron. Robert and Nicholas R. Spitzer (eds.), Public Folklore.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92.
与之类似,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的第一重含义也在于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美国公共民俗学是从公共部门引领下的民俗学向融合各种参与者的方向发展,打破公共部门的主导地位是其需要突破的问题。而新在野之学旨在对“20世纪后半期的日本民俗学”*该说法源于福田亚细男2010年3月28日参加日本女性民俗学研究会第600次纪念会议上所作的演讲《20世纪民俗学的从今以后》。他将20世纪前半期的民俗学归为在野之学,后半期归为学院派民俗学。进行反思,从学院派掌控的民俗学向包含非学院派的诸多参与者在内的民俗学这一目标前进,挑战学院派学者的固有观念是其关键。
依据上文所述,基于日本民俗学与生俱来的在野特质以及当下对学问公共性的时代需求,加上日本民间研究的蓬勃兴起,菅丰提出了新在野之学。菅丰希望借此打破日本民俗学界专业与非专业人士间的界限,学院派民俗学者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只是作为行为体之一,与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民俗传承人等共同探究民俗的表现与应用。多样化的行为体拥有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意愿、不同的价值,需要尊重彼此、跨越差异来形成合意。
菅丰所谓“(新在野之学)要求各行为体认识到文化的所有权及其表征行为的权威性这一难题”,实际上是多样化行为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菅丰认为:“美国的公共民俗学多少还是存在自上而下,行为体间不平等的意味。新在野之学虽然主张各行为体平等参与,各司其职,但其中存在比重的问题,能言能做能介入多少因行为体而异。毫无疑问,众多行为体中以民俗文化传承人为核心的当地民众具有最强的正当性,占最高比重,这点其他行为体,尤其是学院派民俗学者应铭记于心。另由于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长期以来处于较高的地位,所以在与普通民众对话过程中将自己放在比对方略低的位置上才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平等。”*整理自2016年9月笔者与菅丰的对话记录。
在任何一个国度想要实现多样化行为体的平等合作都非易事,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比起美国、日本来说还需先解决把民众作为公民,实现公民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学界热议的话题。在日本建构新在野之学同样充满艰辛,长期以来的惯性使得很多学者不愿改变现状,所幸日本民俗学与生俱来的在野基因增加了其实现的可能性。
(二)介入式的日常实践
新在野之学的第二重含义重点在于探讨民俗学者的实践问题。严格说来,新在野之学中的所有行为体都是实践的参与者,然而包含于其中的学院派民俗学者应首先对实践有清晰的认识。菅丰在《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中指出:“作为我们必须摸索的一个方向,可以提倡以民俗学的知识和见解为基础的在现实社会中的直接的实践——公共民俗学……笔者所主张的公共民俗学是进一步注重学院派民俗学者从事社会实践的一种民俗学方法。”*[日]菅丰:《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陈志勤译,《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第66页。
回到新在野之学的定义,“努力获得对其进行表现的正当性,积极介入到对象人群的社会文化中去”,菅丰所倡导的这种直接的社会实践是一种“介入式实践”,因为只有融入地域内部,才能逐渐拥有对文化加以表现和应用的正当性,成为当事人。这比起我们通常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运用的参与观察来说更加深入,菅丰称之为“参与共感”。“共感”是科胡特empathy一词的日译,empathy指一个人在保持客观的观察者立场的同时试图体验另一个人的人生,而“参与共感”则意味着“与面对的人就所处的环境、所拥有的感情和知觉进行部分共享,从而获得与他们一道理解、思考、发言乃至行动的资格(正当性)”*引自菅丰2016年8月在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集中授课时的PPT讲稿。。
以菅丰本人的实践经历来说,他与田野调查对象新泻县小千古市东山地区已有17年的交往。由于2004年的新泻中越地震,他从一个田野调查的局外人,变成了参与复建、恢复“斗牛”*斗牛的日文原文为“角突き”。小千古斗牛的文献记载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泷泽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比赛“不分胜负”是其最大特色。文化的圈内人。通过深入交流、参与共感,他获得的正当性不断增加,甚至作为“势子”*势子指的是在斗牛过程中守护在牛的身旁,负责引导牛进行比赛的人。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斗牛中,成为文化承载者之一。于是斗牛不再是单纯的研究客体,而是需要和其他承载者共同传承的对象。
然而另一方面,作为研究者,菅丰也明白自己始终是外人,无法与当地人站在完全一致的立场去思考问题。所以提出了“渐进式地接近”这一方法,他说:“然而,我认为,即使只能如渐进线一般,接近目标人群对所有田野调查者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所谓渐进式的接近指的是这样一种方法:在认识到不论多么靠近对象人群,哪怕在他们身上植入自己,最终仍无法与他们实现同一化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地不断靠近他们,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日]菅豊:《「新しい野の学問」の時代へ―知識生産と社会実践をつなぐために》,岩波書店,2013年,第54-55页
“置身于这样一种既接近又存在差异的两难境地,研究者不得不对自己日常的言谈举止进行慎重选择。尽管如此,从好的方面来说,要注意到被调查的地区不仅是田野,更是我们生活的日常领域,我们的选择也由此成为日常选择的一种。总之,在区域范围内所进行的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是基于日常场合下的价值观和平凡感受通过交换意见所实现的。实际上,这里所呈现的只不过是作为普通人的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日]菅豊:《「新しい野の学問」の時代へ―知識生産と社会実践をつなぐために》,岩波書店,2013年,第55页。
可见,介入式实践是一种试图跨越自他差异的实践,逐渐地将这种实践将融入研究者的日常生活,与被研究者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理解和对话,我们不妨称之为介入式的日常实践。而这种介入式的日常实践使得研究者可以与当地人一起共同感受共同创造当地文化,并在其过程中发现和思考诸多问题,实现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
(三)当地民众的幸福
实践的目的在于当地民众的幸福,这是新在野之学的第三重含义,也是最核心的内容。民俗学者在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是否采用介入式实践的方式,是由实践能否使当地人幸福这一点决定的。若为实践而实践,则有可能造成过度介入。“民俗学者在地方进行实践活动之际,首先必须奠定根植于地方规范的思想。当然,这样的实践不是为了我们学者而进行的,也不是为了行政组织等公共部门而进行的,它应该是为了生活在地方上的、长期以来承担这个文化的人们而实行的。也就是说,这种实践活动,应当是在以重视地方为目的的地方主义以及以重视生活者为目的的生活者主义这些实践思想的基础上而展开。”*[日]菅丰:《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陈志勤译,《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第67页。
为了当地民众的幸福,“将该地域及其人群、文化加以客体化”,定义中的这一内容可以看出德国民俗主义和美国公共民俗学对菅丰的影响。民俗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可以被构建的,可以在新语境中焕发新的价值。随着研究者的介入式日常实践的展开,文化的客体化现象不可避免。文化的客体化指的是“将文化作为可操作的对象来加以重新创造的现象”*[日]太田好信:《文化の客体化:観光をとおした文化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創造》,《民族學研究》1993年第57卷第4号,第391页。。“(美国)公共民俗学中研究者不仅把调查地区的文化作为客体,还将文化传承人也作为客体,这么做是为了当地人的幸福,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日]菅豊:《「新しい野の学問」の時代へ―知識生産と社会実践をつなぐために》,岩波書店,2013年,第188-189页。新在野之学也有类似之处,将目光从民俗文化本身转向了民俗文化的传承人、生活者,以人为本。
除了客体化以外,菅丰的定义中还提到“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也是以当地民众幸福为出发点的思想。所谓“一定程度”是指只有当地人觉得需要时,研究者才发挥专业性,给予帮助。菅丰在新泻小千古的实践过程中就是如此,他不是强行植入自己的理念,而是在当地人需要自己的专业知识或技术去解决一些问题时,雪中送炭地给予支持。
那么民俗学者具体能给予怎样的支持呢?菅丰重点归纳了两个方面:“其一,通过与个别地区的深入交流,可以提取出该地域内重要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这三种价值的具体案例分析请参照《文化遗产》2009年第2期《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一文。,并将其展现至地域之外。而这些价值往往会被其他学科忽略或无视。其二,将地域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动向通俗易懂地传达到地域内部,共同创造、维护以当地人为主体的文化活动。”*引自菅丰2016年8月在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集中授课时的PPT讲稿。
菅丰所提倡的新在野之学的实践是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变的学术实践:“(这是一种)在永无终结的关系中展开,无法被定型化、规范化、标准化、通用化、手段化,甚至不以(实践)行为本身作为先验目的的实践。”*[日]菅豊:《民俗学の喜劇―「新しい野の学問」世界に向けて―》,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化》2012年第93号,第235页;[日]菅豊:《「新しい野の学問」の時代へ―知識生産と社会実践をつなぐために》,岩波書店,2013年,第236页,第247页;[日]岩本通弥、菅豊、中村淳:《民俗学の可能性を拓く―「野の学問」とアカデミズム》,青弓社,2012年,第116页。它不是站在研究者视角展开的,而是需要依据当地人的需求适时调整的。研究者需要积极进行介入当地,将该地域及其人群、文化加以客体化,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实践本身不是目的,当地民众的幸福才是目标。
(四)自反性、适应性地把握
新在野之学定义的最后提到“进而对与这一整体相关的自我与他者的实践及研究以一种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重新把握”,这是为了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自省与修正,达到更好的效果。
自反性原指原因和结果间的循环论证关系。自反关系是一种双向关系,因果间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自反性一词在诸多学科中被使用,但各学科对它的解释不尽相同。在社会学中,它指一种“自我指涉”行为,在这种行为中,调查或行动“折回到”、涉及并影响激发该调查或行动的主体。在实际应用中要求专家系统的自我监控,要求研究者根据自己设下的假定来盘问自己。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中,自反性一词除了上述的折回之意外,还有“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融入到研究对象里,自身也成为研究的一部分,从而产生了主客体的融合”*Myerhoff.Barbara and Jan Ruby “Introduction”, in Jan Ruby (ed.),A Crack in the Mirror: Reflexive Perspectives in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35,1982.之意,提醒学者不断自我检验。
在上述含义的基础上,菅丰提出新在野之学中“一直注视着当地居民的研究者和专家们开始重新检视自身的研究姿态和行为;一直被研究者和专家注视着的当地居民(研究对象)开始觉醒,反过来注视其研究姿态和研究行为。二者不再扮演固定的注视和被注视的角色,而是互换身份,相互协作”*[日]菅豊:《「新しい野の学問」の時代へ―知識生産と社会実践をつなぐために》,岩波書店,2013年,第3-4页。。
可见,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是自反的双向关系,研究者的介入会给被研究者带来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会反作用于自己。同时,随着介入的程度变深,自他的界限变得模糊,成为无法分割、协同合作的有机整体。定义中“对自他实践及研究进行自反性地把握”意味着研究者需要不断自省,将自身客体化,重视自身行为对自身的反作用。
菅丰借鉴了生态学中针对未来可变的不确定资源进行的适应性管理。所谓适应性管理主要包括三个步骤,即:“第一阶段为目标设定。明确目标并向利害关系者明示资源情况,以求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合意。这里的利害关系者,并不仅仅指政策制定者,当然还包括持有资源的当地居民。第二阶段为监控。在相关政策实施过程中,必须随时检查它与第一阶段所定的目标是否一致。监控的结果要及时公开,作为利害关系者的共同信息来处理。第三阶段为反馈。如果背离了设定的目标,那么这样的手法就存在问题,必须尽快进行改善和修正。”*[日]菅豊:《「新しい野の学問」の時代へ―知識生産と社会実践をつなぐために》,岩波書店,2013年,第221-222页。
适应性管理方式强调对当地居民意见的充分重视,认为他们具有超越学者的环境保护智慧。菅丰将这一思想拓展到了民俗学领域,把自然资源的管理理念延伸到对文化资源的管理中。新在野之学对自他实践的适应性管理是以尊重当地居民的地域文化认知,寻求他们的理解,及时向他们公开信息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设定民俗传承和应用的目标,随时监控并完善。
不论是自反性还是适应性地把握,都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必须时刻关注被研究者是怎样看待自己介入实践的,并对介入实践的影响进行监控,不断自省与修正,并应用于接下来的实践中。
新在野之学不是只属于民俗学专业人士的学问,多样化的行为体协同合作进行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是其主要特征。其中当地民众的正当性最强,其他行为体尤其是民俗学者需通过介入式日常实践以获得正当性,成为当事人。介入实践的目的在于当地民众的福祉,在此目的之上,将该地区的人与文化加以客体化,努力理解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同时对自身行为带来的影响进行自省和修正,切实以实现当地民众的幸福为己任。
三、新在野之学践行过程中的难点
在现实中践行新在野之学并非易事。为了防止理论中的概念被偷换,菅丰对新在野之学践行过程中的难点作了预判,从而使得整个理论体系更加严密,并对广义上的新在野之学具有警示意义。五个难点分别如下*以下五点内容归纳整理自[日]菅丰:《「新しい野の学問」の時代へ―知識生産と社会実践をつなぐために》,岩波書店,2013年,第229-239页。:
第一个难点在于价值判断。由于新在野之学践行时存在多样化的行为体,所以会出现多样的价值观,使得价值的选择变得困难。研究者自认为“有益”的行为,未必能得到各地方民众的认可。因此,对于社会上普遍认为的“善”,民俗学者不该不加批判地接受并将其标准化,要防止独善的行为,这样才能关注到更多的人群。
第二个难点在于研究手法。新在野之学必须切实将地方居民、市民等纳入主体,尊重其意见。然而目前日本社会在文化保护、环境保护、地域振兴、灾后重建等活动中,存在着打着市民参与的幌子,将主办方意图植入普通民众脑海里的“伪民主”做法。民俗学者需要看穿这一点,探寻真正的协同合作的手法。
第三个难点在于消除隐藏的霸权。实现新在野之学所追求的多样化行为体的平等性、合作性、民主性并不容易。现实中有可能出现表面上是governance(共同协作)体系实际上却为政治所用,回到government(自上而下)体系的情况,从而使在野之学失去在野之性。要谨防公共部门和学院派学者故意赋予市民以特权,再对这一特权加以利用的危险。应避免多样化行为体中某一行为体的优越性,例如市民过度的优越感会造成其与地域居民等其他行为体的矛盾。所以,在新在野之学的践行过程中,民俗学者应充分重视当地民俗传承人的正当性,但也不能赋予其优越性,一味迁就他们的主张。
第四个难点在于坚定新在野之学的目的。当下有不少学科别有用心地向民间渗透,它们以实践为志向,高举实践是为了民众幸福的大旗,实则将该地区作为研究活动的实验田,为了自己的研究消费当地的资源。它们还试图归纳出实践的固定范式并推广,将本属于在野的学问纳入自身的学术体系,为己所用。新在野之学必须与之抗衡,不将实践定型化、规范化、标准化、通用化、手段化,不以实践为目的。民俗学者要提取该地区被其他学科忽略的,当地人没有注意到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向原生社群内外展示。而这些价值是不可触及、不可计数、不可替代的。
第五个难点在于学术观点和实践当地观点的磨合。当外部人士介入到地域内部,改变当地文化,赋予其新的价值并获取到某种利益时,我们可以从政治性的角度对其加以批判。然而当地域内部人士自行将文化客体化,大幅更改其原貌并从中获利时,则很难从学术角度评价这一行为,因为这与追求真实性的学术观点相违背。应该阻止该行为或是不闻不问,抑或是抛开学术观点去迎合当地的观点?根据新在野之学的理念,民俗学者应首先深入实践,融入地域内部,参与共感,之后再作判断。
菅丰的《被置换了的森林》(《文化遗产》2010年第2期)以明治神宫的森林为对象,揭露了如今自然价值、环保价值被高度认可的这片森林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数十年前由于政治的需要,它被偷换了概念,从民间信仰的空间变成了国家信仰、民族认同的空间,且为了建造这片国家森林,政府不惜破坏地方上的森林来获取树种。菅丰以此警示我们,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接受的某种价值,有可能是为政治所用、人为构建出来的。2016年8月菅丰在东南大学集中授课时除“被偷换了概念的森林”外,还增加了“被偷换了概念的河川”“被偷换了概念的鱼”两讲内容,体现出一位民俗学者在日常生活中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质疑所谓“理所当然”的批判精神。对践行新在野之学理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难点的预测是菅丰这种不为表象所迷惑,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的展现。
四、结 语
菅丰对自身的定位始终是一位民俗学者。虽然Commons论、建构主义、民俗主义、生活环境主义、自我民族志等理论和方法都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出于对民俗学的热爱以及发展日本民俗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立志创成日本民俗学的新理论,新在野之学便是菅丰为此交出的一份答卷。
新在野之学借鉴了美国公共民俗学的经验,却又有本质区别。它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以及在当下学问公共性的需求和日本民间研究热潮的有力支撑下的再构建。理论包含了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民俗学者的介入式日常实践,对实践的影响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等内容,以人们的幸福为最终目标。
虽然践行新在野之学民俗学将会面临种种艰难险阻,但菅丰认为民俗学者应知难而上,不忘“在野”的初心,回归民间,深入地域,与当地人一同实践和研究。这样,日本民俗学才能在贡献社会和服务民众的过程中绽放新生。他说:“日本民俗学或许本就是田野间不可采撷的紫云英*“田野间不可采撷的紫云英”是日语中的一句谚语,紫云英之花只有绽放在田野间才充满生机,若采之,置入花瓶,摆放家中,则会失去魅力。暗指所有事物均有其适合的位置。,然既已采之不妨将其种子重新撒向田间,让花再开,这也并非不可能。为了告诉世人学术圈就像被围起来的庭院那般狭小,为了向世人展示学术圈外那孕育着各类知识的广阔沃野,我们就不能让民俗学成为脱离实际的无果之花。”*[日]菅豊:《民俗学の喜劇―「新しい野の学問」世界に向けて―》,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化》2012年第93号,第241页。
美国著名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曾感叹民俗学缺乏“宏大的理论”。为此,2005年,美国召开了题为“为何民俗学中不存在宏大的理论”的民俗学年会,展开热议。其中,多萝西·诺伊斯批判了那些艳羡哲学、文学研究的高蹈派理论,试图将民俗学理论高级化的学者,提出应立足民俗学自身特色,在高端理论和现实社会的中间地带找寻“谦恭的理论”*Baron. Robert and Nicholas R. Spitzer (eds.), Public Folklore.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92。
菅丰赞同诺伊斯的观点,所以他所构建的新在野之学不是令人敬而远之的哲学思辨,而是接地气的理论表述。同时,菅丰虽努力改变日本民俗学的现有格局,开创日本民俗学的新时代,却怀有谦恭之心,不希望新时代中仅有自己的一家之言。菅丰希望围绕民俗学的定义、理论及方法出现百家争鸣的格局,而“从中选择哪一个则交由每个民俗学研究者决定”*[日]福田アジオ、菅豊、塚原伸治:《「20世紀民俗学」を乗り越える》,岩田書院,2012年,第155页。。
另一方面,作为新在野之学的民俗学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菅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其在小千古的斗牛实践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然而更重要的,是必须明确实践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目的而展开的。新在野之学中为了当地民众的幸福这一核心理念体现出对柳田国男“令人幸福的学问”的血脉相乘,它对民俗学者的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值得中国民俗学者在探索实践回归的道路上加以借鉴。
[责任编辑 赵彦民]
陆薇薇,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 210096)。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项目“国际视域下大运河江苏段自然再生的环境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15ZXC006)的阶段性成果;并获东南大学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资助计划(项目编号:2242015R30018)及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