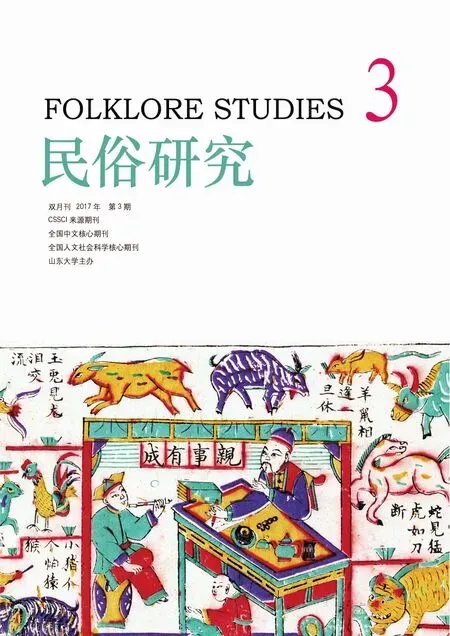公共民俗学与新在野之学及日本民俗学者的中国研究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菅丰教授访谈录
2017-01-28菅丰张帅邢光大
[日]菅丰 张帅 邢光大
编者按
公共民俗学与新在野之学及日本民俗学者的中国研究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菅丰教授访谈录
[日]菅丰 张帅 邢光大
一、传统斗牛活动的危机
张帅(以下简称张):非常感谢菅丰老师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刚从中国回来,还要准备斗牛会的一些事情。在正式展开访谈之前,能否请菅丰老师简单介绍一下您最近从事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活动?
菅丰教授(以下简称菅丰):我近十年来在日本主要从事关于公共民俗学的研究与推广这方面的工作。众所周知,公共民俗学是从美国开始的,而我所做的就是把美国公共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介绍到日本,同时也在做一些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接下来还会做一些公共历史学方面的研究。从公共民俗学到公共历史学不仅仅是改变名字这么简单,在专业学术领域我们通常会很严格地将科学分门别类,学者也因此拥有了不同的称呼,如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等等;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所有的学科都是不可分割的,他们心中没有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这样的分类,只有一以贯之的“人文学科”这个概念,这个观念是他们从生活的感受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我的想法是能否把从事公共民俗学、公共历史学甚至公共宗教学等实践性学科的学者们结成一种关系,在社会上进行共同的研究。
张:这是一个从民众的角度出发,非常有益于地域社会文化建设的想法,这个想法开始付诸实施了吗?
菅丰:这个计划从今年四月份就已经开始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计划也在进行。2016年由日本三得利文化财团提供经费,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所以说它非常有趣也非常特殊是因为这个课题不仅仅是学者的单独参与,而是学者和当地的居民结成了共同合作的关系,这正与我十年来研究的公共民俗学相契合。在你们来之前,我刚刚跟那边的人通了电话,我们正打算要召开一个由学者和当地百姓共同参加的研究会。你们应该都知道我参与的斗牛活动,这个研究会就是跟新泻县小千谷市斗牛会的成员一起组织的。另外,我们还会把他们聚集到一起,有些学者和专门人士会针对他们做一些演讲,当地的老百姓也都会参加。
张:您参与的斗牛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特别关心的话题。
菅丰:我正在参与的斗牛现在已经是国家级的无形文化财,相当于中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斗牛与国家文化财发生关系的时候会涉及非常多的问题。斗牛虽然是无形文化财,但是并没有得到国家实际上的资助,因为在日本像表演、祭典,或者传统文化类的文化财是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到国家资助的,但斗牛就不太容易,因为斗牛作为一种与生物相关的活动对于很多人来说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关于动物保护的问题。顺便问一下,您认为斗牛是很残酷的事情吗?
张:我认为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这种以动物争斗的形式参加竞赛的活动应该在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性,我的老家虽然没有斗牛,但是有斗羊、斗鸡、斗蟋蟀等同样激烈的活动。从参与其中的民众的角度来说,这只是一个传承已久的传统活动。在参与者的意识中,牛是自己饲养的,它作为我的财产也好,甚至是我的朋友或家庭成员也好,我带它参加一些竞赛和我养一头猪过年吃掉所起到的意义是一样的。关于动物保护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斗牛并不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介入或破坏,而且动物之间的争斗在非人为的情况下也是存在的,所以不应该过于苛责这样一项古老的活动。动物争斗是这项活动的核心,如果因为保护动物而禁止动物争斗,那么只能让这种活动完全停止。
菅丰:我赞成您的说法,但是很多人是反对这种说法的,比如在中国过年杀猪的时候有些人也认为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日本的捕鲸,韩国吃狗肉,包括中国广西玉林狗肉节,这些活动虽然也是古老的活动,但仍然会有很多人不赞成。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传统的正当性正在不断地遭受大众的质疑。民俗学者非常重视传统,非常在乎传统的意义,但是对于有些民众或动物保护者来说,传统在他们这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三得利财团此前也举办了一些关于动物保护的会议,这些会议源自于2013年日本环境省拟对《动物爱护管理保护法》作出修订。日本环境省组织的委员会针对“动物打架的活动是否应该继续进行”举行了一个非常大的讨论,这个委员会包括大学老师、兽医、动物爱护团体等不同的身份。其中有一个委员向环境省报告了有关斗牛残酷性的讨论,实际上他并没有多少专业知识,也不太了解当地的文化传统,如果让这些人去主导一个法条的修正和执行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中有一个议员曾去现场观看斗牛,他发现有只牛的一个角旁边流了一点点血,他便问牛的主人:“等会儿要把这个牛带去医院吗?”牛的主人说:“不去呀。”后来他就提出斗牛会缺乏必要的医疗措施,是有很大问题的。虽然您没有参加过类似活动,但我想问你,在中国的话牛受伤了会拉去医院吗?
张:不会。
菅丰:一般会怎么做?
张:中国的类似活动都是发生在农村,农村是没有专门的动物医院,但是村里会有兽医,有这些活动的时候,我相信兽医会在现场的,他们会及时做出救治。
菅丰:你说对了,日本也是一样,但他问的是“你会带它去医院吗?”正常的回答肯定是不去医院,但如果他继续追问的话,就会得到“会有兽医进行处理”的回答。同时,这些斗牛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牛的情况,自己也会做出一些处理措施。这些关于救治的经验是存在于斗牛者脑子里的,但这个委员并不了解这种情况,看到牛受伤了就直接问他去不去医院,这是非常错误的理解。
张:所以这个社会才特别需要民俗学者通过观察和参与来感知和理解民众的生活,如果用精英的知识来看待民间知识,就会难免带有偏见。
菅丰:对于这个议员来说,他本身的专业是跟狗、猫等小型动物相关的,他根本没有理解当地的价值观,只是用自己的价值观来理解问题。所以说让这些不懂当地人知识的专家去改变针对当地文化的法律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
张:那我想知道的是,最后法律真的改变了吗?
菅丰:幸运的是当时的委员长正好是我的朋友,他曾经跟我一起去观看过斗牛,而且他本身是兽医,对斗牛的知识是非常理解的,他向大家解释了这是一种误解,所以法律最终并没有被改动,斗牛也没有被禁止。这个问题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委员会的人在讨论,但是作为最大利益相关方的斗牛会却完全不知道,然而这种讨论却是非常重要的。通常这样的讨论是秘密的,一般的老百姓当然不会知道,所以我的目的和作用就是在老百姓与委员会之间做一个沟通的桥梁。
张:这也就是您一直所提倡的公共民俗学的学科要义吧。
菅丰:对于公共民俗学者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民间的大众跟官方专门的机构这两方连接起来,在官方的层面对官方政策进行一些引导,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要把国家目前正在做什么传送给他们。
二、日本公共民俗学的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
张:那么下面就请菅丰教授从学术脉络上谈一谈公共民俗学吧。
菅丰:我提倡的公共民俗学虽然来自于美国,但和美国的还是有差别的。其中一样的部分是,主张学者将民众、官方等不同的机构组织联络起来,作为一种沟通的桥梁而存在。不一样的是我更加注重学者进入当地成为当地一员这样的公共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虽然美国也有一些公共民俗学者会进入到民间的一些团体中,但他们同时也存在非常多的问题,而且也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倡。
张:美国公共民俗学者通常采取的是什么方法呢?
菅丰:美国的公共民俗学是非常多样化的,但从整体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纯净、单一的学问,之所以说纯净是他们一直在进行一种具体的说明书化的工作,比如他们会整理出来遇到A问题的话怎么办,遇到B问题的话怎么办,都有各自的条条框框。
张:是用以指导民众生活的具体的方法指南吗?
菅丰:虽然并不存在一本真正的说明书一样的东西,但是有些指导方法还是真实存在的,问题是按照这种方式,如果完完全全照搬说明书的东西来指导地方的文化建设会造成非常多的困扰和麻烦,因为这是一种很公式化的硬性东西,没有太大张力,不同的地方环境、人和文化特性都不一样,如果仅仅依靠一本说明书一样的指导方针在公共民俗学界进行普及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
美国公共民俗学的调查最初是在多个地方同时进行的,在美国有包括多点调查型及单点调查型等多样化的公共民俗学者。而我所倡导的,不是多点而是在深入到一点中,在成为当地的一员后,对地方知识进行理解和总结,以更好地从当地人的角度提出和解决一些问题。当然,这并不代表多点型的说明书化的公共民俗学的做法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方法也是应该存在的。成为当地一员的做法虽然对于理解地方的价值观、文化和传统来说更加具有优势,但它同样也具有局限性,这种方法不能在多个地点同时进行,而且为了理解当地的文化必须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想要被当地人认可的话也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在我看来以上这两种方法应该是互补的。就如同民俗学这个学科需要多样的学者一样,既需要学院派的民俗学者,同时也需要一些对社会更加关心的学者,即公共民俗学派。从这个角度来说,学院派与公共民俗学并不是完全分离的两派,两者之间也应该相互包容。
张:但是美国的学院派与公共民俗学派在历史上曾有长期的对立。
菅丰: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对立的历史,美国著名的公共民俗学者芭芭拉·基尔森布拉特-基姆布拉特(Kirshenblatt-Gimblett Barbara)曾在一篇名为“误分为二”的文章中讨论过学院派与公共派的分离。在以前美国民俗学史里面是没有公共民俗学,原因是自1950年代开始的公共民俗学派与学院派的对立最后以公共民俗学派的失败而告终。学院派的代表是印第安纳的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M. Dorson),公共民俗学派的代表是本杰明·波多金(Benjamin A. Botkin),他们俩都是犹太人,都是哈佛大学毕业,他们原本关系非常好,后来却因为学术意见不同而导致多尔逊对波多金展开攻击。多尔逊实际上非常在乎纯粹学术作为独立学科的权利;波多金则更加关心人民群众,主张学者要离开办公室去为民众发出声音。在这场斗争中多尔逊胜利了,然后在历史上关于公共民俗学的事项就被否定了。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整体的社会反而对公共民俗学有所期待,1960年代,美国从国家层面为民俗生活(folk-life,而不是民俗学folklore)相关的保护提供了政策支持,因此公共民俗学开始正式发扬起来。在学术领域内是学院派胜利了,但是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和需求的恰恰是公共民俗学派。
张:美国政府具体做了哪些扶持工作?
菅丰:对于公共民俗学的学者来说,从20世纪60至70年代到现在美国政府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机构或活动来保障公共民俗学的开展,第一个是美国全国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简称NEA),这个组织是美国公共民俗学顺利开展的资金源,它解决了钱的问题;第二个是史密森博物馆开办的“史密森民俗节”(Smithsonian Folk-life Festival),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这是美国公共民俗学的实验场,它解决了活动的问题;第三个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办的“美国民俗中心”(The American Folklife Center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这个机构保存了大量的有关民俗生活的资料,并致力于公共民俗学的普及工作。多年来,很多学院派的学者和毕业生也同时参与其中,这使得公共民俗学派的学者逐渐变得多了。到20世纪80、90年代,公共民俗学派在美国的民俗学者中已经占据了接近一半的人。我们都熟知的比尔·艾威(Bill Ivey)原本就是艺术基金会的会长,后来成为以学院派为主的美国民俗学会的会长,还有很多公共民俗学的学者也都成为了美国民俗学会的会长,这说明公共民俗学派已经在美国民俗学界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张: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日本的公共民俗学,菅丰老师非常强调融入到地方,那么您认为民俗学者在进入地方社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
菅丰:实际上在日本和中国展开多点调查的民俗学家是非常多的,美国也一样,但是做单点调查的民俗学者却非常少。我所提倡的这种做法,调查者不单纯是一个民俗学者,他成为当地一员之后会与当地人形成一种协同合作(collaboration)的关系,重新去构建一种民俗事象的发展。我从事的民俗学强调和当地人共同进行工作,即通过交流互动与当地共同进行传统的再生产与再创造活动。
张:菅丰老师是如何成为当地一员的呢?您是如何认识当地民众和文化的?又具体做了一些什么?
菅丰:之前所说的斗牛就是我进入地方的社会实践,在2013年春天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当地的百姓与政府之间进行一些沟通方面的工作了。作为斗牛会的成员,我在跟大家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把是否取消动物打架类活动的讨论情况向大家传播出去,他们非常震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外界是这样被否定的,反而迁怒于我,对我说:“我们明明把牛像家人一样对待,为什么你们会把我们说成那么残酷?”我赶紧摆手说不是我的问题。他们这时候突然意识到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他们以往只局限于自己的内部,并没有理会外部的关系,现在才明白外部看法对于他们自身文化的重要性。
除了动物爱护的问题,还有观光化的问题,他们也在很认真地在思考传统是什么,这其实是民俗学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但他们把它当做自己的问题来考虑,当地民众非常疑惑究竟在多大程度内发生变化才算是保持了传统,他们非常认真地讨论和考虑跨越传统的基准线是什么。其中有一点是关于传统服装的,斗牛的时候有很多人是穿着传统服装过去的,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穿着普通的T恤就进场了,民众认为披着“法被(手艺人、工匠等所穿,在领上或后背印有字号的日本式短外衣)”去斗牛就是传统的,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披上法被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稍微有点偏题,八月十五日是有斗牛的比赛的,我的牛——天神和外来的牛比赛,我的牛非常厉害,有外面的牛慕名前来挑战,对方就是穿着红色的polo衫进场的。斗牛会的民众对他的着装非常生气,大声地喊着让他滚出去,呼喊着喝倒彩。他们认为他穿着红色衣服进场去挑战一个非常强的、非常值得尊敬的牛,这样的行为就像把当地人当成了笨蛋一样,是对他们的不尊重,于是就非常生气。
张:这样一来,菅丰老师和您的牛会不会在比赛中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因为挑战者已经在围观者眼中变成了无视传统的反面形象,菅丰老师作为正面的形象必须要战胜他。
菅丰:每次失败的时候,我都会遭受很多指责,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受尊重的感觉,那个时候你只是一个非常弱的弱者,他们会围着你对你说:“你干脆别干了!”
张:这也充分说明,菅丰老师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当地以斗牛会为核心的社群中,在那时候您已经不是一个研究者,也不是大学教授,而是他们中普通的一员。
菅丰:是这样的,经过这些事情确实能够反映出,虽然不可能跟当地人百分之百完全一样,完全同化,但是一定程度上已经非常接近于一般的群众了。像这样的身份是非常有利的,他是一个连接国家与老百姓之间的通道与桥梁,他可以把两方的意见所综合,而且可以代替底层民众发出声音,把传统的正当性正式的提出来。之前说到老百姓与国家之间是有断层的,我的身份刚好可以把这个断层弥补起来,将一个比较正确的信息传达给两方。我的东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对一般人来说会觉得非常了不起,但这样的身份也会使我和当地人产生隔阂,如果不亲自去进入当地与当地人共同生活的话,你的意见是不会被当地人所认可的,你也不会真正的了解当地人,只有真正地成为了当地人的一员后,你才能真正地说出一些话并被当地人所接受。
张:实际上这并不简单。
菅丰:非常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刚才所说的并不代表着要跟当地人完全一样,因为完全一样的话本身是无法做到的,这种关系就像数学中渐近线的概念一样,它无限的接近一个轴但永远不会跟这个轴重合,作为民俗学者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张:在中国,有许多学者,比如吕微、户晓辉、高丙中等几位老师近几年所提倡的“实践民俗学”与作为实践语境的“公民社会”实质上与公共民俗学有很大关联,他们从哲学背景和学术理论上做了很多思考和探讨。
菅丰:中国大多数学者实际上始终是跟公共民俗学有些关系的,不过也有反对的声音,比如学院派的施爱东就持有批判的态度。我开始做公共民俗学研究的最初六年,爱知大学的周星老师也参与其中,周星老师虽然是团队一员,但是他对于公共民俗学采取了非常谨慎和慎重的态度。我也大概明白他为什么会慎重,公共民俗学要展开的话,很重要的是公共的部分,就像刚才我说的,我实际上是在地方团体和政府国家层面之间进行一种互动,所以与他们的交流是非常紧密的。
张:在中国有一种意见是学者一旦跟政府发生联系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府的干预,在这种干预的情况下,民俗学会不会有失去他的学科批判性的危险?
菅丰:对于这个问题,施爱东老师也有同样的看法。因为公共民俗学确实是与国家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说想要把这门与国家相关的学问非常大型的并不局限于地方本身的学问向全世界展开的话,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对于我来说,我的立场始终是站在老百姓的那一边,国家的权力和老百姓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关联,对于民俗学者来说站在中间从老百姓的立场去跟政府进行一种交流的话是比较合适的。公共民俗学者卡在一个中间位置的时候,他们非常需要考虑的是“为了谁?”“为了什么?”这两个问题,我的立场当然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地方文化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会尽量避免被政府所干预。
张:那么美国公共民俗学者呢?他们作为一些公共机构的专业人员,听起来似乎要偏向政府一些?
菅丰:这一点是不能误解的,美国许多公共民俗学者反而是跟我一样的,更加贴近于地方而不是政府。不过非常有趣的一点是美国认为民俗学跟政府扯上关系并不是一件有问题的事情,他们称公共为public,日本和美国对于公共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另外,对于公共民俗学持有否定意见的国家也是存在的,比如德国,在纳粹时期德国民俗学实际上是完全为政府服务的一门学问。这样的历史导致战争结束以后德国强烈反对民俗学者与政府产生关系,对于他们来说,公共的概念与国家权力的概念是相距非常远的,所以公共民俗学的实施在不同的国家是有不同的难度的,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也需要有不同的考量。
张:也就是说公共民俗学的展开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的。
菅丰:是的。
张:以日本为例,开展公共民俗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菅丰:对于现在的日本来说,将公共民俗学的概念介绍出去,得到的反响是非常有限的。非常直接的说,原因在于日本的民俗学者相较于中国的民俗学者更加缺少一种全球性、国际性的思维,并不擅长借鉴外来成果。虽然中国也更加偏向本土文化的研究,但是中国的学者很多都拥有海外留学经历,他们会把国外先进的理论带到中国,所以更具全球性的思维,但是日本的民俗学者少有去海外求学的经历,因此对于海外的一些民俗理论相对来说感觉比较迟钝。公共民俗学也是舶来品,所以在日本的民俗学圈子里,好像并不太容易被接纳。对此民俗学者需要建立一个清晰的认知,那就是日本现今在做的公共民俗学绝对不是单纯地把美国公共民俗学移植过来。日本最早的民俗学是在野之学,其性质与美国公共民俗学中有一些部分是很相近的。我在做的是实际上是在野之学与公共民俗学的一种融合,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研究主体是谁,最初的日本民俗学就是老百姓和民俗学家,还有专门从事民俗工作的人一起参与活动和研究,而不是专门把他们分开的,与美国公共民俗学让一些有关组织和当地人“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研究主体是相似的,像这样的研究方式在很多的领域中是不断产生的。
我现在在做的公共历史学一样涉及到学者与当地民众的紧密结合。以往研究历史学的都只是历史学家,他们作出相关研究然后将这些事情向大众传达。但实际上当地民众自己也会讲述历史,然而有些历史学家却认为地方民众讲的历史有一部分是假的不真实的东西。现在的历史学在反思这种观念的基础上提倡历史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仅由历史学者讲述历史,更尤其注意地方民众的一些思考和话语。这说明这种类似跟公共民俗学一样的方法在别的学科领域也正在展开。
三、走向“新在野之学”的时代
张:我们了解到您最近几年提倡“新在野之学”的说法,并于2013年出版专著《走向“新在野之学“的时代——为了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联接》,刚刚您还提到了“在野之学”。
菅丰:一般来说,比如像美国,他们的民俗学是一个由学院派逐渐向公共派过度的学问,在日本却刚好相反,日本最开始是在野之学后来逐渐发展为学院派,日本过去的在野之学对于现在来说反而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研究方法。
张:福田亚细男老师在2009年出版的《日本的民俗学——“在野”之学二百年》中,把日本最初被置于国家学科体系之外的民俗学定义为在野之学,并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院派出现并占据主流的历史过程。福田老师在多个场合主张今后的民俗学要回归在野之学。
菅丰:是的,福田老师虽然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福田老师本身也是很纯粹的学院派学者。福田老师其实有两本书,一本是《日本的民俗学——“在野”之学二百年》(吉川弘文馆,2009年),介绍1960年代以前的民俗学史;一本是《日本的现代民俗学——柳田国男之后的五十年》(吉川弘文馆,2013年)介绍的是1960年代以后的民俗学史,他在这本书的最后提出回到在野之学。虽然他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在野之学这种东西,但却没有真正去做,由此也能看出来福田老师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学院派代表。但是作为学院派代表的他又提到了在野之学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大概是因为福田老师已经认识到了日本民俗学的一些窘况,就主动思考了日本民俗学的出路,于是想到了在野的民俗学,但问题是他自己是有很多事情也是无法做到的,于是就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人。
张:福田老师有没有具体描述在野之学是什么,学者应该如何去做?
菅丰:福田老师关注的是在野之学的研究主体是什么,同时,在野之学重视的是在社会中的一种实践。按照福田老师的观点,在野之学并不依存于政治体系,也不被政治体系所束缚,学者可以用自己的意识去研究地方文化,然后将研究成果回归于野,在当地进行一种带有公共性质的民俗实践。福田老师的想法与柳田国男“经世济民”的目标具有相似性,但是福田老师过多的将官方与地方隔离开来,这种想法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太合理的,也不好去提倡。
张:那么您提出的“新在野之学”是不是对“在野之学”的修正?
菅丰:福田老师是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接受的教育,他的学生时代在世界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中国有文革,日本则有学生运动等等。福田老师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当时的学生普遍认为,国家与权力是我们的敌人,这种想法让他们对于官僚系统非常敏感。因此他对于新在野之学这种做法是持有比较慎重思考的,就像他在书中所说的那样,他还是较站在批判官方的立场,对学者与官方合谋的共同行为持有批判意见。这本书(《日本的现代民俗学——柳田国男之后的五十年》)里面并没有涉及到我所主张的“一方面与当地进行互动,另一方面与政府进行沟通”这种具有公共性质的新在野之学,我的书(《走向“新在野之学”的时代——为了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联接》)大概是福田老师的书出版半年前就已经发行的。当然像福田老师这种对官方比较敏感的态度也是学术界非常需要的,但是现在时代已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当今社会完全不依赖于官方去开展一些民俗实践的活动非常的不现实。
就像我在新在野之学中所说的,官方已经与学者和民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充分互动基础上的协同合作关系。以前是官方在上边,老百姓在下边,上边对下边随意发号施令,下边只有遵从,1970年代福田老师的学生时代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政府可以不经过讨论就直接命令民众进行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今社会政府处在一种权力的高姿态虽然是始终存在的,但是底层民众的权力也不断的提升,政府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不考虑老百姓的意见就擅作主张,制造出各种政策和法律。尤其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官方开始处在一种被民众监视的状态。所以说官方和民众共同组成了一个协同合作的关系,而不再是单方向的上传下达。
今天关于政府协同合作管理方式的话题不会讲很多,但是总的来说,在现在的时代面对政府和地方已经处在一种合作关系的社会现实,福田老师所主张的不依存于官方束缚的研究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将官方和地方完全切割会处于一种绝对理想的,不现实的状态,比如说斗牛,斗牛开始的时候斗牛会也会去邀请一些政府的人,政府的人前来参观斗牛之后,政府与民间会展开一些协作,民间总是希望能从政府那里争取一些扶持资金,所以有的时候政府官员反倒非常害怕地方民众。以前是政治家单方向的驱动老百姓去做一些事情,现在反而是老百姓可以驱动政治家去做一些事情。所以福田老师所说的在野之学是一个老式的,已经不适应现在社会现实的理论,这不仅是福田老师的想法,日本的很多民俗学家也是抱着同样的态度。甚至很多公共机关的民俗学者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说的新在野之学就是希望学者能够正确认识官民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的发展趋势,将百姓和官方之间的墙壁推开,这也是公共xx学的意义所在。
四、日本民俗学会与日本现代民俗学会
张:我注意到2005年在东京大学召开的日本民俗学学会,学会主题就是“在野的学问与学院学问:审视民俗学的实践性”,也就是说在那时对于民俗学的实践性,以及在野的学问与学院学问之间的对立与反思,就已经存在一个比较广泛的讨论了。
菅丰:对,那次会议我是主要的组织者,也参与了讨论。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官方和民众中间的墙壁推掉。那时候我从美国访学回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就组织了这场会议。会议还强调了一个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难以理解的问题,在日本民俗学界有一个固有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日本民俗学会的会员有1800多人,民俗学者只有100人左右,加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后将近两百人,来自官方、博物馆等机构的会员有两三百人,学生会员有两三百人,还有一些是老师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另外还有近五百人的身份是未知的,这一部分人属于非专业人士,他们与专业人士一起参与活动,非常符合福田老师所说的野的学问的想法。对于2005年的会议,有些非专业人士误以为会议目的是公开创造一种金字塔一样的结构,民俗学者和一些专业人士在金字塔最顶端而普通的爱好者则处在最底层。事实上在民俗学会中这种特殊的金字塔结构本来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偷偷地把他隐藏起来是日本民俗学会一贯的做法。比如有一个只有日本民俗学会才有的习惯,中国民俗学会和美国民俗学会都没有,开会的时候,假如我是报告人,你对我提问时你会说什么?
张:我会说菅丰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精彩的发言,对于您的报告,我有一些疑问希望您能解答。
菅丰:不不,这个是正式开始提问,我说的是在提问之前。
张:那应该是对自己身份的简单介绍吧,我会说我是一名民俗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菅丰:对,但是在日本的话我们经常会说我是东京的菅丰,大家都会说住的地方而不是身份,目的就是要将这个金字塔结构悄悄地隐藏起来,以避免普通爱好者的劣等感。但对于民俗学来说,民俗本来就是具有多样性的,将不同身份的差别隐藏起来对民俗学来说是不应该的,不如主动去说出来,大家在理解的基础上相互知道可能会更好。因为普通爱好者和学院派的学者们的目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大家既然组成一个学会就应该很主动的认识到爱好者和学者之间的差别。我自己并不反对因为爱好而投身于民俗学的人,民俗学本来就诞生于一些人的爱好。承认这种差别之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打破那种劣等感,因此将这个东西拿出来然后破坏掉才是那次会议的真正目的,所以在会议上我们非常敏感地提出了学院派、公共民俗学派和一般的人的区别,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承认这种身份上的差别并消除歧视,从而真正地实现学者、官员、民众共同进行民俗研究和实践的目标。
张:提到民俗学会的事情,我们知道日本还有一个现代民俗学会,现代民俗学会成立的初衷是什么?学会的学术研究和探讨有没有特定的领域或者旨趣?
菅丰:日本民俗学会现在有1800多人,这导致学会的研究方向非常的分散,同时它本身缺少一种理论研究的核心动力,如果在理论上阐述太多,很多上了年纪的民俗爱好者会认为这不是他们理解的民俗学,但如果每次都向他们做出解释,又特别浪费时间和效率。所以我们成立现代民俗学会,以更加偏向于一种精细化、专业化的研讨,当然这并不是排除一些爱好者和非专业人士,他们也可以随意加入,现代民俗学会的成立只不过是想从日本民俗学会这个广的范围中找到一个比较精细的部分来进行一些相关研究。日本民俗学会大概一年会召开五次大型公共会议,现代民俗学会的会议会更多一些,同时还会涉及到与一些海外研究者和研究组织的一些沟通和关联。现代民俗学会大概有两百个人,对于人数比较多的民俗学会来说操作起来相对比较容易和简单。
张:也就是说现代民俗学会比较偏向于纯学术的讨论。
菅丰:是这样的,现代民俗学会的会议一般五十几个人参加,有的时候能达到一百人,福田老师也经常会出席这样的会议,他在一些著作中也会提到他在参加研究会时候的一些见解和发现,关于“超越福田亚细男”的那个会议就是我组织和福田老师展开讨论的。
张:这个会议我曾在中国民俗学官网上看到您通过网站向大家征集向福田老师提问的问题。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样的会议在中国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菅丰:在日本其实也很少见,首先是从大家那边收集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网上公开的,所以尽管福田老师原本并不想来,但是既然已经公开了,就不得不出席了。
张:这说明您跟福田老师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菅丰:关于我跟福田老师的关系,我不是福田老师的弟子,福田老师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后来因为政策上的原因,这个学校变成了筑波大学,结果福田老师对于筑波大学不是太喜欢。我最开始工作的地方是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正好福田老师是那里的教授,我是他的助手,在关于我入职的欢迎会上,福田老师直接跟我说,你不是我的后辈(这里指学弟、学妹),我也立马跟他说我确实不是你的后辈,不过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福田老师组织去浙江省的中日联合调查的时候,我也参与其中。这个项目持续了二十多年,有很多成员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退出了这个团队,但是我一直坚持了下来。在中国做调查的时候我与福田老师有着非常多的讨论,我们彼此十分了解对方的学术思想。所以真的是因为我跟福田老师之间有这样的良好的关系才促成了这次会议。我们两个人相互承认彼此的观点相左,即使意见不同,也一样可以进行讨论,而且这样的交情还能一直持续下去。在那次会议上,我们与福田老师像两方对打一般,先是我们把福田老师推到了墙角,然后福田老师又推回来了,最后还是势均力敌。我送给你们的书(福田亚西男、菅丰、塚原伸治编:《跨越20世纪民俗学》,岩田书院,2012年)就是对这次会议讨论的整理与总结。
张:像这样的不带偏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学术讨论,或者说是学术争论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对于学术向前的发展非常重要。
菅丰:也正因为是福田老师,所以对方也能接受这样的方式,并且也会比较平和的进行,如果换成是别的老师的话就可能会是一种拒绝的态度,两边的关系甚至会恶化。所以会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福田老师本身的性格所促成的,另外福田老师在日本民俗学界对日本民俗学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与他对谈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五、日本民俗学者的中国研究
张:在日本有许多从事中国研究的民俗学者,菅丰老师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与研究也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菅丰:我想知道你们对日本民俗学家的中国研究有哪些直观印象?
张: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从地域上看,日本学者与欧美地区的海外汉学家一样,大部分把调查点都选择在了南方,从台湾、香港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到福建、广东等大陆边缘,再到浙江、湖南、江苏、上海等地,比如田仲一成老师,渡边欣雄老师,菅丰老师,以及福田老师组织的在浙江省的联合调查,最近的则有一些做客家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比较民俗学的学者,都选择在南方。
菅丰:确实如此,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政治的原因,做中国研究还是要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入手,香港、台湾、新加坡确实比较容易进入。因为政治的因素,与其说是民俗学者更不如说是人类学者,他们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很难在中国大陆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所以会选择东南亚或者台湾进行华人研究。至于中国境内,渡边老师为什么选择福建调查呢?因为渡边老师最初的田野点是在日本冲绳,而冲绳受到了福建移民文化的影响。关于为什么日本在中国的研究更加偏向于南方呢,我个人的想法首先可能是北方更接近于以北京为主导的政治中心,虽然从原则上来说南北方是一样的,但从具体的执行力和自由度来说,南方更加适合国外研究者的进入。
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作为民俗学者去研究中国民俗学的时候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许多在中国做研究的日本学者很大程度上在用日本本土的东西去研究中国。这种做法的代表者就是比较民俗学会的学者,不仅是我这么说,福田老师也批判比较民俗学。我和福田老师反对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都在用中国的眼光去看日本,而不是用中国的眼光去研究中国。到中国去做研究的话会发现中国和日本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当然只是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研究。比较民俗学的研究总会意识到两个现象:一个是相似,一个是不相同;针对中日文化相似的部分就归结为文化的传播,不相同的地方就可以认为是本土化。实际上比较民俗学作为比较的部分是理所当然的方法论的比较,但是同时也是非常简单的,并没有涉及到一种深层次的探讨。柳田国男的一国民俗学做的就是日本地方与地方的比较,这是被福田老师所批判的,而比较民俗学则是对这种比较的延伸,所以福田老师反对比较民俗学也是理所当然的。从这一点出发,为什么大家选南方作为调查地,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南方跟日本更像,都属于稻作文化,这跟以前很流行的“照叶树林文化论”很相似,所以因为上述这些理由导致日本民俗学者在中国南方做调查相对比较普遍。
张:我作为一个出生在北方,生活在北方,又在北方学习的学生,对这种现象感觉非常的遗憾,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差异还是很大的,这些在南方田野调查基础之上形成的研究范式有些时候并不适用于北方,比如北方村落宗族的特征并不明显等等。
菅丰:中国是非常大的,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之前做中国的宗族系统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体系,想要一个人去调查全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中国涉及到多种环境圈的国家,比如说西方有沙漠,南方有照叶树林带,北方却是针叶林带,同时还有东方和东南的沿海地区,所以说中国整体相当于世界的一个缩影,如果中国能研究好,那么证明他可以去研究这个世界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依照自己的田野经验站出来说中国如何如何,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可以用什么观点概括,这样的说法一定是非常片面的。北方没有被深入调查,虽然确实有些遗憾,但是换句话说北方也是一座拥有丰富矿藏的矿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宝库。
张:那我们非常欢迎菅丰老师能够来北方跟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宝库。
菅丰:我虽然非常乐意,但是比起面条,我还是更喜欢吃米饭。
张:那么菅丰老师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菅丰:直到现在为止从跟随福田老师进行联合调查的时候我就开始对中国的动物文化非常感兴趣,一直持续至今。中国与日本不同,有着非常丰富的动物文化,做动物研究的话世界上最有趣的地方大概就是中国,比如我之前一直关注的斗蛐蛐之类的文化现象。动物本是自然的产物,但是人们却将动物转变成与人类文化息息相关的成分,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手段是最厉害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猪、羊、鸡、鸭、鹅,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牛,淡水鱼包括观赏性的锦鲤也是中国最多。因此,与家养动物相关的文化最厉害当然也是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江南一带,虽然与日本的文化比较相近,但是日本关于动物的文化是很少的,到明治时代为止,经常吃畜肉的日本人仍旧不太普遍。中日在动物文化方面的差别为什么那么大呢?这与社会构成和动物利用的发展历程有关系,日本更加偏向于对自然动物的利用,自然动物是不能被控制产出量的,所以只能通过控制捕获量来避免动物在该区域的消失。那么如何来控制捕获量呢,这就与社会的规则有关了,为了控制就必须要在共同体之中创造一种普适的规则,这种规则对于日本村落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也是日本村落共同体的自我认同观念如此强大的原因。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的共同体意识比日本要弱很多,因为中国更加倾向于开发自然。为什么中国会采取开发的意识,而不是保守的意识呢?因为中国在开发的同时也在创造一种新的人为环境,比如我在太湖南部的桐乡进行过调查,这个地方养蚕、鱼、鸭子和湖羊,蚕吃桑叶,动物粪便和鱼塘里的淤泥成为桑树的肥料,蚕粪喂鱼,这样的循环在中国是很常见的,中国会人为的创造一种跟自然调和的环境,这种环境虽然开始于破坏自然,但是却最终又跟自然相调和,扩大了生产力。但这种环境在日本是完全不发达的,所以日本人对环境的依赖性更大,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日本讲求与环境共生的文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日本当初没有掌握这样的技术导致的,所以我认为日本人绝非对待自然更加温柔。将类似这种事情解密后传达给大家是民俗学者应该做的事情,这个东西也是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在中国一直在关注的文化。
与这个相关联的是中国的民间技艺,民间技艺是中国民俗学重点关注的对象,在日本却不太受重视,比如今年学会的发表,关于技术研究的能有一两篇就不错了,因为日本没有,所以我对中国的民间技艺非常感兴趣。
另外,福田老师退休以后,想把他从中日联合调查时期一以贯之的后续工作交给我,但是我拒绝了。福田老师二十年以前的做法对现在来说并不具有特别大的意义,福田老师的做法就是将日本的方法直接带到了中国。当年,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大概15人左右到达一个地方一起研究,每个研究者都会分到一个专门的调查事象,比如年中行事、村落信仰等等。这是福田老师毕业的东京教育大学的做法,曾经对日本民俗学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这项工作的初期,因为还未曾对中国文化展开广泛调查,所以这种方法对于资料的收集和文化的研究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现在中国有很多文化已经被实际调查过了,再采用原本那种将互相之间有关联的文化事象分成若干部分的分离式的方法就是不明智的,所以我并没有延续福田老师的方法。另外还有语言的问题,很多参与调查的日本学者并不懂中文,而近年来中国学者所做的本土研究发展的更快,也更加有深度。因此为了克服刚才所说的问题,我选择了跟中国的民俗学者合作,通过一些中国民俗学者还没有意识到的方式比如多点民俗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去重新研究中国的民俗事象。
如果问我为什么必须要研究中国的文化的话,我的回答是因为中国文化很有趣而且中国菜很好吃。
张:谢谢菅丰老师,我们非常欢迎您以后继续来中国品尝中国料理,研究中国文化。
[责任编辑 赵彦民]
菅丰,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东京153-8902);张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 250100);邢光大,日本神奈川大学历史与民俗资料学研究科硕士研究生(日本神奈川221-8686)。
菅丰(Suga Yutaka),1963年出生,1998年获日本筑波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日本民俗学会理事、日本现代民俗学会运营委员等职。菅丰教授长期以中国和日本为主要田野调查点,主要研究领域为自然与文化资源利用及管理、共同(Commons)资源论、无形文化遗产管理、无国界(Transnationalism)的传统文化等方面,同时致力于日本公共民俗学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主要成果有《走向“新在野之学”的时代——为了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联接》(岩波书店,2013年)、《河川属于谁?——人和环境的民俗学》(吉川弘文馆,2006年)、《修验道创出的民俗史——围绕鲑的仪礼与信仰》(吉川弘文馆,2000年)等专著,并发表中、日、英文学术论文近百篇。2016年9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帅与日本神奈川大学历史与民俗资料学研究科硕士邢光大就公共民俗学、新在野之学以及日本民俗学者的中国研究等问题对菅丰教授进行了访谈。本刊对访谈内容进行了编排整理,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