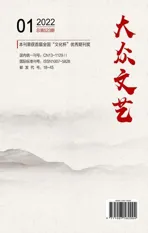《蓝风筝》的三种电影“操作”解读
2017-01-28牛媛媛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215006
牛媛媛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215006)
《蓝风筝》的三种电影“操作”解读
牛媛媛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215006)
罗杰•奥丹是法国当代电影理论家,他将电影分为八种风格(mode),每一种风格又可以由多种操作(operation)来表现。然而,国内对奥丹的相关理论研究甚少。本文在此理论框架下,重新解读影片《蓝风筝》,并认为影片主要通过“赋形化”“剧情化”和“信念”三种操作呈献给观众一个基于历史而又不乏掺杂着作者理念的小人物的世界,在平淡的叙事中触及历史、生活和小人物的悲剧。
《蓝风筝》;电影;认知;符号
一、关于电影《蓝风筝》
电影《蓝风筝》由中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指导,讲述了文革开始前的十七年里,孩童铁头和母亲树娟寻常却又不断被政治活动所影响的生活故事。整部电影平淡,没有大起大幅,甚至画外音(成年后的铁头)都异常平静,似乎在诉说着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但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身不由自却清晰地被一幕幕生活化的情景放大,显得格外沉重而深刻,有力地冲击了观影者的心理,为影片蒙上了一层灰败、悲凉的色彩。
导演田壮壮按照主人公铁头的人物关系,以“爸爸”“叔叔”和“继父”作为电影的三个章节,展开空间叙事,三段男人,三段人生,却以同样的悲剧结束。在第一部分“爸爸”中,铁头的父亲少龙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在改造期间被倒下的大树砸倒去世;第二部分“叔叔”中,少龙的好友李国栋因为自己告发少龙,心存愧疚,开始进入铁头母子的生活,并扮演照顾二人的角色。他在大跃进后期的三年饥荒中,对铁头母子关爱有加,自己却省吃俭用,最终积劳成疾,死于营养不良;第三部分“继父”中,吴需生是一位老干部,平日里不苟言笑,铁头对他充满敌视,就在二人关系破冰之时,这位老干部被红卫兵批斗时突发心脏病死亡,母亲也被划为反革命分子。影片最后一幕是铁头为了救母亲,拿着砖头拍向红卫兵,却被痛揍,浑身血污地躺在地上,面无表情地看着挂在树上的风筝。
国内对电影《蓝风筝》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文革情结、叙述模式、家的空间意象和风筝的象征含义,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第一类是对文革的反思,认为作品呈现多角度、多人物、非全知全能式的叙事特征,人物性格及其命运都是在政治的漩涡中无一幸免,从而表达了对文革期间极端行为的批判;第二类是聚焦在影片的叙事模式上;第三类则解析了家的空间意向,认为电影将四合院作为家族寓言符号,表现了文革时期普通家庭的兴衰,通过不同空间造型的展现讲述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灰暗的社会环境下一个普通家庭的遭遇和每一个人所经历的坎坷命运,通过宅院空间营造的视觉影像所传达的观念和寓意引发出对民族历史和社会形态的反思;第四类研究最多,研究广度和深度也最大,即对“风筝”以及其他玩具的符号象征意义的解读,其中“风筝”作为影片中最重要的象征意义的载体,不仅仅是孩童的玩具,而是自由和理想的承载物,是自由的生存处境和自由的政治环境的象征,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对于脱离束缚和禁锢的向往;第五类不局限于《蓝风筝》一部影片,而是将其与其他类似影片进行对比。
这些研究都深刻剖析了影片背后的含义,但所用理论较为重复,从而得出的结论也相对比较单一。笔者尝试采用法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奥丹(1994)的分析体系,将《蓝风筝》归入“家庭电影”风格,探讨影片运用了怎样的“操作”(operation)去展现电影的特征。
二、 罗杰•奥丹的电影认知语用学
罗杰•奥丹对于电影研究有着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他认为电影包括多种风格(mode),即电影文本种类。奥丹定义了八种不同的“风格”:1.奇观风格;2.虚构风格;3.动力风格;4.家庭电影;5.记录风格;6.教化风格;7.艺术风格;8.美学风格。奥丹在勾勒了电影制作的主要风格之后,随即结合“操作”(operation),赋予每种风格以具体的特征。初期,奥丹罗列了七种操作:1.赋形化(figurativization),即定型,符号学意义上形象的建立和肖像化,修饰形象,以便制造能转化为真实世界影像的指示性幻觉;2.剧情化(diegetization),即构建一个人物栖息的想象世界;3.叙事化(narrativization),即时间的呈现和剧本的叙事;4.信念(belief),即观众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电影虚构幻觉的否定;5.演示(monstration),即空间呈现和剧场;6.定相(miseenphase),即电影和观众的关系同电影陈述世界所呈现的关系之间达到了共振;7.虚构化(fictivization),与其他操作不同,虚构化仅对应单一的风格——虚构电影,这种操作的功能赋予电影的陈述者和接受者以虚构的地位。后期,奥丹又修改为三种操作类型,第一类是与画面和声音的表达相关的操作,第二类是话语操作,即剧情化、叙事化、话语化。第三类是陈述操作,即虚构化。对奥丹电影理论的介绍和相关研究在国内并不多见,本文借助该理论框架重新解读《蓝风筝》,希望借助影片的分析引发国内研究者对奥丹理论的关注。
三、 解读《蓝风筝》的三种“操作”
根据罗杰•奥丹对电影风格的分类,笔者认为《蓝风筝》属于家庭电影。所谓家庭电影风格,即电影是以家庭中一个成员的角度,去记录或者叙说过去的生活经历。影片《蓝风筝》这一点特征鲜明,不论从电影的画外音(即讲述者)、影片的主要角色,还是故事的成长主线,都表明铁头是整个动荡时期的亲历者。导演用铁头的视角,去表现在文革前后成长起来的人如何看待那段历史。
从前文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每一种电影风格不可能局限于一种操作,而是包括多种操作。笔者认为,影片《蓝风筝》的操作主要为赋形化(figurativization)、剧情化(diegetization)和信念(belief)。
赋形化是非常常见的电影操作,也是不可缺少的塑造电影的元素。通俗来说,即影片要塑造人物,塑造人物背后的寓意,使得故事中的人物能够成为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还要塑造相应的背景,大到整个时代背景,小到可以贯穿影片的象征物,两者结合才能创建电影世界,传递创作者想要表达的内涵。《蓝风筝》无论对人还是对物的塑造都十分鲜活。就人物而言,影片依次出现的铁头、铁头母亲、父亲、叔叔、继父,以及一些次要角色,如铁头母亲的哥哥树生、弟弟树岩、树生的女朋友朱瑛、房东兰太太,都非常生动贴切,每一个角色都充满独特的魅力。本文主要讨论对主人公铁头的人物塑造。铁头可以看作是创作者塑造的一个符号。铁头作为画外音叙事者,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影片行为的主体,另外一个是见证和记录事态发展的观察者。他观察记录叙述的过程也是自身由孩童到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从这个层面上来看,铁头可以被看作是经历过文革前夕混乱年代的孩童记忆的象征。主流的叙事倾向于把文革塑造成为狂风暴雨的历史时期,仿佛那个年代只有灾难,《蓝风筝》则是从孩子的视角去展示五、六十年代的历史。铁头和一群孩子无忧无虑地玩耍、闲逛,在他们的视角里文革前后的时期并没有那么晦涩,反而由于父母的缺席(忙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活动)自己更加得轻松自在。《蓝风筝》对物的符号塑造可以说非常鲜明,贯穿整个影片出现的蓝风筝便是典型的代表。对蓝风筝这一符号的解读已经十分丰富和全面,此处不再赘述。一般认为开头飘扬的新风筝象征着铁头内心深处欢乐的记忆,第二幕出现时铁头成了安抚妹妹的角色,铁头不再懵懂无知,风筝此时也不再是无忧无虑快乐的代表,而最后残破的风筝挂在枝头,象征着理想和自由的破灭。赋形化是创作一部电影关键的一步操作,总体来说,《蓝风筝》对人物、宏观环境(文革前夕)、微观视角(风筝)的塑造,都赋予了深厚的意义,构成了整个影片的骨架。
剧情化是构建人物栖息的想象世界。《蓝风筝》构造的世界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想象的世界,而是基于对已有历史记忆的再创作,既是对已有历史的还原,也同时加入了创作者的认知。《蓝风筝》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正面讲述从解放后一直到“文革”这一段留给中国人民深刻印记的17年,讲述17年间中国的政治制度对普通人一生命运的影响。导演田壮壮认为尽管中国在这17年里社会局面动乱,但在他的记忆里,更多的是去打麻雀、大炼钢、在人民公社吃饭,这些都是开心的记忆,所以他希望以孩童的视角和记忆去呈现整个影片。影片的三个小标题分别表明了三个历史阶段。整风运动时,铁头的爸爸因为在开会时去了洗手间回来便被打为右派,发配到北方劳动改造,随后在改造期间被据倒的大树砸中头部死去;大跃进时期,也是全家最困难的时期,叔叔李国栋成为妈妈的第二任丈夫,对铁头百般疼爱,但是死于营养不良;最后文革爆发,继父在被批斗时死于心脏病突发,妈妈也被划为反革命。剧情化是对影片整个时代背景的设定,这个时代背景便是塑造的角色生活的世界。在《蓝风筝》中,这个世界既是我们所熟悉的基于历史的年代,也是我们所陌生的不了解的世界,我们不了解普通的小人物是如何生活,他们的生活又是如何被影响;与此同时,导演试图用孩子的视角塑造一个快乐与茫然、自在与痛苦并存的世界。尽管影片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并不是如主流电影对文革充满批判,但仅存的美好总是被政治运动所摧毁,孩子心目中对家、对父爱、对生活的渴望和憧憬也一再被肢解。
信念这一概念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意思,奥丹提出这一概念是指观众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电影虚构幻觉的否定。影片《蓝风筝》出现孩子们一起出去玩耍、铁头和父亲放风筝等本该是让人欢乐的情景时,我们却无法畅快,因为我们对那个年代有着特定的解读,不管这个解读正确与否,我们总是把那个年代等同于混乱、动荡、迫害、残酷,所以尽管影片中的孩子显得并不那么痛苦悲哀,我们也会归结为孩子的不谙世事,并不会认同这样的“无忧无虑”。整个电影用一种平和甚至平淡的声音来叙事,没有夹杂批判、悲伤的情绪,只是安静地讲述一个孩子眼中家庭的变迁。然而,影片的一幕幕悲剧重重地敲击着我们的心灵,三个扮演着父亲角色的人物相继由于政治运动而死去,如同高低起伏的波浪,把观影者的感受推向高潮。每当父亲角色出现时,我们总是会舒一口气,盼望着能带给铁头和他母亲一丝安定和幸福,然而这三个父亲角色依次死去,甚至最后连母亲也被划分为反革命。身为孩童的铁头并不明白这些动荡对他将会产生怎样深远甚至悲剧的影响,但观影者深切地明白这一切将会给一个孩子带来怎样的灾难。所以我们无法认同孩子眼中的无忧无虑和欢乐,而会认为影片始终令人压抑;所以,当成年后的铁头以画外音的叙事者出现,用平静、没有一丝悲哀的声音说话时,我们觉得分外刺耳。综上,《蓝风筝》的“信念”操作体现得尤为明显,观众总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用既定的看法(如文革前后社会动荡不安)否定影片试图表现的含义(如文革期间孩子们的自由欢乐)并认为后者是虚幻的、不存在的。
四、结语
本文借助当代法国奥丹电影轮框架,重点分析了电影《蓝风筝》中的三种“操作”,认为赋形化、剧情化和信念是影片运用的最主要的操作。赋形化塑造人物,《蓝风筝》中塑造的角色贴近时代,力图还原当时的人物,其中主人公铁头更是可以视作一个符号,一方面是影片的记录者和叙述者,另一方面又是孩童对文革记忆的象征;剧情化构建人物栖息的想象世界,《蓝风筝》构建了一个文革前后既混乱无序却又不乏童真的世界,但温馨的世界最后还是随着悲剧分崩离析;信念则为观众对电影虚构幻觉的否定,是观者感受与影片画面所产生的矛盾,一方面创作者试图以孩童的视角去还原记忆中的文革,但观影者很难改变既定看法,仍会质疑影片中孩子式的短暂快乐,并且会认为这种无知的欢乐越发让人感到痛心和压抑。此外,分析显示奥丹的电影“操作”理论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解释力。
[1]BucklandWarren.TheCognitiveSemioticsofFilm[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82-108.
[2]沃伦•巴克兰德,雍青译.《电影认知符号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77-108.
[3]郜杏.政治运动狂潮中的集体无意识——浅析电影《蓝风筝》[J].视听,2015(7):77-78.
[4]韩琛.记忆的政治——论1990年代的第五代电影[J].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8(2):41-45.
[5]贾宏.“以物象为骨,以意格为髓”——电影《蓝风筝》的语言意象风格[J].影视话语,2006(10):85-87.
[6]李典.文革题材电影的思考:《蓝风筝》——折翼的翅膀[J].电影文学,2008(18):58-59.
[7]李沐泽.“家”•叙事•寓言——对“第五代”导演作品中“家”的空间意象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8]刘珉僖.90年代电影中的文革记忆——以《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和《蓝风筝》为主[D].北京:北京大学,2011.
[9]刘亚兵.《蓝风筝》的“四个”世界[J].电影评介,2007(16):42-43.
[10]孟君.历史空间:当代城市电影中的多重“文革”叙事[J].淮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6):769-775.
[11]王永江.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完美结合——评影片《蓝风筝》[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9(1):81-82.
[12]张祖群.“后文革”时代的死亡哲学:《蓝风筝》探析[J].电影评介,2004(11):1-5.
[13]赵冬梅.自然与人性:田壮壮的电影世界[D].信阳:信阳师范学院,2012.
牛媛媛(1991-),女,山西晋城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