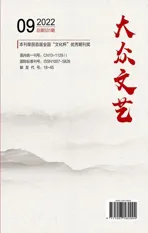张爱玲小说的现代主义特征
2017-01-28曹妮娜陕西师范大学710119
曹妮娜 (陕西师范大学 710119)
张爱玲小说的现代主义特征
曹妮娜 (陕西师范大学 710119)
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与传播,很多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就有意无意地运用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本文着重探讨在新旧的交替、中西的融合里,张爱玲的小说都有哪些西方现代主义的特征。
张爱玲;小说;现代主义
西方现代主义萌发于19世纪欧洲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逐渐被城市破坏乃至取代,新的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稳定的农业型社会结构,并因此动摇了社会的上层建筑。发展到二十世纪,一战和十月革命的发生促使工业文明带来的不安转变为对传统的质疑和叛逆,反映在文学中,就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是相对于后现代主义而言,现代主义文学在传统文学中发展而来,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文学的印记,如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唯美主义与自然主义就是分别从西方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发展而来的,与其说现代主义是对传统的反抗,更不如说是精英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改良。
作为“孤岛”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张爱玲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以及自身的广泛涉猎使她深受中西文化的共同熏陶,因此她的作品中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笔法又有西方文学思潮的痕迹,正如当时新旧交替的时代。
一、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彼时欧洲知识分子在写作中用一些意象的组合来隐晦地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而在体裁方面,诗歌是能最大程度上堆砌意象的,所以当时的代表作家有庞德、叶芝、艾略特等都是诗人。著名的诗作如庞德的《地铁车站》:
在地铁站
人潮中这些面容的忽现
湿巴巴的黑树丫上的花瓣
我们可以看出这首小诗运用了意象叠加的手法,而这些叠加的意象具有象征性,因而暗示读者凭借意象之间内在的情感逻辑而获得一种全新的感受和自由的解读空间。
张爱玲是擅用意象来达成象征的效果的。基于“苍凉”的生命体验,张爱玲所用意象也多与苍凉有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月亮。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人体就是由很多个传感器组成的,而光学传感是最容易带来情绪和感觉的。中国人有绵延至今月亮情结,风月本无情,是文人墨客赋予其象征意义。月亮多出现在静谧冷清的黑夜,月光又不同于日光的灼热,是阴柔、清冷且便于直视的,因此很容易让人思绪万千,被敏感的作家用以表情达意。
例如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开头对月亮的这一段描述:“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象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一一完不了。”这里的月亮代表意义不同于我们通所说的“团圆”,而是重在通过对年轻人和老年人记忆中的月亮进行对比,象征一种时代的变迁,暗示着小说人物的命运,并首尾呼应。此外,在文中亦有其他对月亮的描述如:“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月光亮而皎洁本应令人心旷神怡的,而文中的芝寿在曹七巧的变态压迫下看到月光只觉得害怕和仓皇,这正是用月亮这一意象来烘托出文中疯狂的、反常的世界。在《金锁记》中月亮一共出现了,每一次出现都象征了不同的生命体验。
主人公曹七巧被自己的欲望扭曲了情智,虽脱离了姜家但仍用自己精神上的枷锁“劈杀”了几个人,可恨又可悲,这样的悲剧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对此并不是憎恶和冷眼旁观的,而是恰似那一轮总是笼罩在文中的明月,灼灼地映照在文中凄凉的世界里,却让我们在黑暗里看的清楚,沉默而悲悯。正如作者一语道破“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一一完不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是没有尽头的,月亮就像小说的线索一样,启发读者思绪。
又如小说《留情》中这一段描述:“他们家十一月里就生了火。小小的一个火盆,雪白的灰里窝着红炭。炭起初是树木,后来死了,现在,身子里通红隐隐的火,又活过来,然而,活着,就快成灰了。它第一个生命是青绿色,第二个生命是暗红色”,用炭的生死象征了郭凤坎坷的婚姻,从而揭示了她的悲剧人生。
二、表现主义
作为一种思潮,表现论早在西方18世纪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已经蔚为大观了。如华兹华斯所言:“诗是强烈情感的自发流露。它起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然而作为一种艺术原理,表现论形成于20世纪初,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克罗齐,英国的科林伍德和卡里特,俄罗斯的托尔斯泰等。表现论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情感的表现,具体到把文学作品中就是侧重从作者角度,从心理角度解释文学现象,它是针对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发迹而来的“再现论”提出的,传统的再现论轻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仅仅把艺术看做生活的复制品,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认为现实生活高于艺术,艺术的目的和本质就在于再现生活,而表现论正是弥补了再现论的这个缺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表现主义的风潮。
张爱玲是传达情感体验的大师,从行文来说,首先,她能唤起自己曾体验过的情感,激发读者内在的想象,其次,她能通过一些独特的外在标志来传达自己的情感体验,这就体现出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主人公葛薇龙“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盘里一棵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叶子,四下里探着头,象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通过反差强烈的色彩组合和诡异的比喻表达出了主人公葛薇龙有求于人却遭受冷言冷语的凄凉与无奈。类似的还有《金锁记》中:“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这样怪诞离奇的比喻的作用已经不是再现生活,而是作为媒介来表达作者想要传达的内涵。
表现主义的又一特色就是放大社会对人的异化。如卡夫卡的《变形记》,直接写外在形态、行为上的异化,用荒诞来表现真实。而张爱玲对人物的异化的描写是覆盖在日常琐碎之下的。如《心经》便是讲诉了一段畸恋,女儿小寒对父亲怀有深深的执念,以至于从小便离间父母的感情,视母亲为情敌,而父亲许峰仪竟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最后只好选择与女儿长得相似的凌卿来结束这不伦之恋。《半生缘》中的曼璐为了留住丈夫不惜牺牲亲妹妹的清白。《金锁记》中守活寡的曹七巧硬是把自己的精神枷锁强加于儿女而致其不幸。诸如此类,“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的畸形家庭关系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不在少数,且都是以旁观者平淡的口吻讲述的,即张爱玲一贯的“冷眼旁观”。
在当时新旧交替的时代,殖民地受资本主义影响最大,生活方式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封建思想依然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女性还是活在男权社会活在男权社会的阴影里,因此张爱玲笔下一系列被社会、家庭、历史因素异化的形象正体现了张爱玲对小人物的关照、对社会弊病的揭露。不同于一些宏大叙事的作品,张爱玲把新旧社会的冲突与融合缩小到作品人物的精神世界里,表现为变态扭曲的心理,其本质就是一种异化。相比较于《变形记》,张爱玲笔下的表现主义没有那么张扬,而是隐藏在情节的角落里,不经意间点缀着文章,正是这样的“别有用心”才值得我们去挖掘去思考。
三、意识流
意识流小说是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的,然而并没有形成一个文学流派,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一般来说,意识流技巧多表现为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由正在进行的事情而引发,展开自由联想,重视主观的心理现实。代表作有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夫的《到灯塔去》。然而纯粹意识流的小说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作为手法融入小说中却能够展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从而推动小说的叙事。
夏志清曾在《论张爱玲》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有些西洋小说家专写意识流,即为她所不取;因为在意识流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道德问题,需要小说家来处理。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张爱玲认为“人心的真相”,应当放入“社会风俗”的框架中,她在作品中也做到了这一点,把小人物的悲喜放在动荡的“乱世”中,并对他们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刻的剖析,站在作品中人物的角度展现意识的流动。
如《金锁记》中:“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枯槁的曹七巧通过胳膊想到自己“出了嫁”之后的几年,思绪又追溯到自己十八九岁的时候,尚且对爱情和婚姻有朦胧的憧憬,如果不是迫于生计,如果还有其他选择……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都是由手臂引发的意识流动,并最终引向了空虚。而文中另有一处用了典型的蒙太奇手法“风从窗子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蒙太奇不仅是一种电影的拍摄技巧,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对人类意识的某种模仿。张爱玲运用了电影中的蒙太奇的手法来调动读者意识的流动,产生如梦如幻的错觉,从而弱化了时间跨度的突兀,形成自然而然的过渡。
又如《心经》中对许峰仪意识流动的描写:“隔着玻璃,峰仪的手按在小寒的胳膊上----象牙黄的圆圆的手臂,袍子是幻丽的花洋纱,朱漆似的红底子,上面印着青头白脸的孩子……”寥寥数语就足以刻画出一位深陷畸恋的父亲,他在行为上克制着自己,但他的欲望在意识里却袒露无遗,又是由手臂而来的意识流,张爱玲似乎很喜欢由手臂、手、展开心理描写,在《金锁记》中出现过两次“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这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张爱玲的小说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典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的融合,它不能仅仅局限于写作技巧,这种融合的背后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一个时代的表达,其价值还需后人深入探究。
[1]张爱玲全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2]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7.
[3]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A].土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
曹妮娜,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