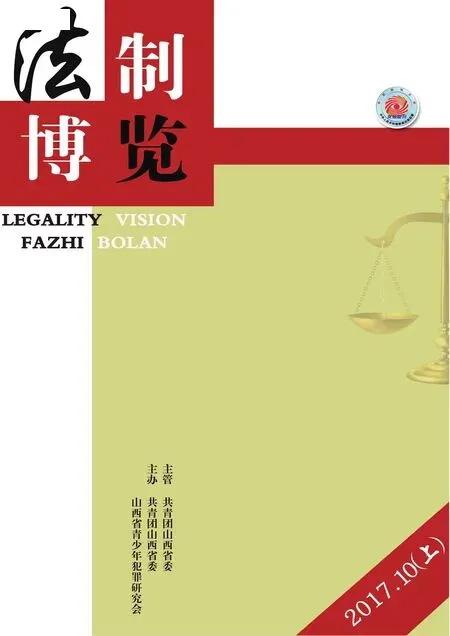“先行调解”制度再探讨:时间适用范围及调解主体
2017-01-27谢米隆
谢米隆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先行调解”制度再探讨:时间适用范围及调解主体
谢米隆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先行调解”制度入法至今已有数年时间,在这期间学界对“先行调解”制度的理论研究硕果丰富,司法实践中也积累了大量有益经验。通过对二者的结合,就“先行调解”制度的时间适用范围及调解主体进行再探讨,对“先行调解”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从现有的民事诉讼程序的功能及程序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先行调解”制度的时间适用范围应当是当事人起诉后至审前准备前。其次,在明晰“先行调解”应当是非诉讼调解的前提下,通过梳理我国调解制度的相关发展历程以及对实务操作的有益借鉴,“先行调解”的调解主体应当是除法院审判人员之外的所有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和人员。“先行调解”工作展开的具体形式则是以法院为主导,通过法院委托、委派等途径将非诉讼化解纠纷力量进行整合建立的链接平台,其具体形式依各地方资源不同而表现形式不一。
先行调解;时间适用范围;调解主体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程序的诸多方面做了修改,其中增设的“先行调解”制度受到了学界的重点关注及热议。①“先行调解”制度指的是《民事诉讼法》新增的第122条:“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先行调解”制度的设立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自2012年该制度设立以来,学界对“先行调解”制度讨论较多的就是该制度的时间适用范围以及主持“先行调解”的人员即调解主体问题,因为《民事诉讼法》对“先行调解”制度的实施未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如果不对“先行调解”制度的时间适用范围及调解主体进行预设,势必导致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运行不畅。针对这两个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的见解,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方式的应用,所以目前该制度运行的显著问题就是对“先行调解”制度的认识不统一,缺乏具体的标准的实施细则。鉴此,本文拟从“先行调解”制度的时间适用范围和调解主体两个方面,结合学界的理论研究和司法部门的实践操作进行再次探讨,以期为“先行调解”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一、“先行调解”制度的时间适用范围
(一)“先行调解”制度的时间适用范围的两种理解
学界目前对“先行调解”的时间适用范围的理解可以归纳为两类:
1.起诉后至立案受理前
这一类观点认为“先行调解”即是在纠纷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至法院立案受理期间,由特定的主体进行的调解工作。[1]这一观点可以从法条的逻辑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得到支持。[2]从《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的具体位置来看,“先行调解”处于第二编“审判程序“中的“第一审普通程序”这一章的第一节“起诉和受理”之中,而该节总共有6个条文,其中前3条是关于起诉条件和起诉状的规定,即第119条是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第120条系关于提交起诉状或口头起诉的规定、第121条是有关起诉状之内容的规定,后3条则是关于法院如何处理起诉的规定,包括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第123条关于审查起诉和立案的规定以及第124条关于不属于立案范围的诸情形之处理。第133条又单独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可以调解的,采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这种调解指的就是立案之后、开庭审理之前的调解,它体现了法院立案受理后、开庭审理前这一诉讼阶段上“调解优先、调判结合”之政策导向的具体要求。在立案受理之后、移送业务庭审理之前或开庭审理之前,法院都可以进行调解,但须明确的是,“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的调解,在名称上已经不再是“先行调解”了,此时的调解,应称之为是“庭前调解”或“审前调解”,与“先行调解”是并列关系,而不是被包容的关系。如果“案件分流处理”机制中的调解也是属于“先行调解”的话,那么《民事诉讼法》第133条中对调解的规定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从条文安排上的逻辑关系和法律解释理论中的体系化解释来看,对于第122条所规定的“先行调解”指的是在起诉后至立案前这一期间进行的调解。此外,赵刚教授还认为从《民事诉讼法》第122条中使用的概念来看,在《民事诉讼司法》122条中使用的是“民事纠纷”而不是“民事案件”。纯粹自然状态的“民事纠纷”还不是进入“司法状态”的“民事案件”。因此,“先行调解”的时间适用范围只是在立案受理前。[3]
2.起诉后至审前准备前
另一部分学者对“先行调解”时间适用范围的界定可以归纳为在纠纷当事人起诉后至案件的审前准备前,但是在具体表述中略有不同。如在一些官方出版的法条释义类书中指出“先行调解”是指法院立案前或者立案后不久的调解。[4]这里将“先行调解”的时间适用范围界定的更加广泛,也更为不明确。此外,还有学者主张将“先行调解”分为两种来理解,一种是提起诉讼至立案前,即当事人起诉后至法院受理前进行的调解。另一种是立案后至审前准备前进行的调解。之所以要将“先行调解”分为两种,是因为这两种“先行调解”在其调解主体和调解效力上都有所不同。[5]还有类似观点的学者,如王亚新教授认为先行调解包括当事人提起诉讼至法院立案前以及立案后较“早期”的调解。大致为立案后至送达程序期间进行的调解。如在实务中,通过电话等便捷的手段联系被告时,告诉被告原告的起诉信息并可以询问被告是否接受调解,如果被告不拒绝调解,并来到法院,则即完成了送达,也可以进行先行调解程序。[6]
(二)“先行调解”时间适用范围之我见
通过对上述理论的归纳及对法条的理解,笔者认为我国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的时间适用范围,应当是在当事人提起诉讼至审前准备程序前。对上述的观点,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1.有利于程序之间功能上的衔接
将“先行调解”的时间适用范围理解为是在当事人提起诉讼至审前准备前,有利于诉讼程序之间功能上的衔接。2012年《民事诉讼法》正式设立“先行调解”制度的同时,也对“审前程序”做了重大修改,建立了实质意义上的“审前程序”。
在西方国家审前准备程序发展早期,通过在审前程序,由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归纳争点以便后面的庭审阶段能够有效、快速的对案件进行判决。随着审前程序的发展,出于加强审判效率的考虑,法官对审前程序的管理逐渐加强,形成了一种法官管理下的审前准备程序。在审前程序中,双方当事人互相了解证据,为辩论做材料准备,随着对案情的进一步了解,在这一阶段就出现了解决纠纷的机会。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日本出现的“辩论兼和解”的审理方式,法官在律师的配合下,对案件的证据和争点进行讨论,法官伺机进行调解。[7]我国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加的第133条,其内容和西方国家的审前准备程序相似,功能上也更接近,而且在功能上还有在诉讼终结和审前调解方面的扩张。2015年的民诉法解释中,第225条是对庭前会议的规定,其中规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庭前会议可以包括下列内容:……(六)进行调解”。而庭前会议是民诉法解释中第224条争对《民事诉讼法》第133条审理前准备方式所做的规定。从这一角度来说,严格意义上的审前调解应当是在第133条规定的审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其并不等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十二章第二节“审理前准备”阶段的调解。而案件尚在立案庭时进行的调解不属于“审前调解”的范围。因此,将立案后至庭前准备程序之前进行的调解纳入“先行调解”,并不会和“审前调解”相冲突,相反,更有利于程序之间功能上的衔接。
2.“先行调解”是对建立诉调对接机制的立法确认
随着我国民事案件的逐年增长,法院“案多人少”的问题十分严重。为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法院审判效率,另一方面也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利用多种纠纷解决途径,实现又快又好的化解纠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将社会中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种多功能程序体系,体系内部多种纠纷解决方式能够相互配合、共同存在,其中的关键一环就是要处理好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问题。因此,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就成为了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在《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将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相衔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的改革思路。[8]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就对人民法院在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后、正式立案之前以及立案后的民事案件进行调解的相关规定。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对立案前后进行的调解做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尽管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设置“先行调解”制度,但在法院工作和实务中已经形成“先行调解”制度的设计。2012年通过《民事诉讼法》将“先行调解”制度进行确认,其实质是对诉调对接这一阶段开展的调解工作的一种立法确认。通过这样一种立法上的确认,为法院在引主导这一阶段的调解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二、“先行调解”的主体
(一)“先行调解”的主体选择困境之缘由
1.对“先行调解”的性质认识模糊
对“先行调解”的性质认识模糊是导致司法实践中主体选择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调解类型及调解主体类型相当丰富,又不同主体主持的不同类型的调解工作其效力也不相同。因此,只有在对“先行调解”的性质予以明确的前提下,才能合理的选择“先行调解”的主体。目前对“先行调解”的性质异议较大是“先行调解”到底是属于诉讼调解还是非诉讼调解,亦或是诉讼和非诉讼相交织的调解。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将立案受理作为节点来区分诉讼调解和非诉讼调解。非诉讼调解包括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和仲裁调解。诉讼调解包括立案调解、庭前调解和庭审调解。该法院在实务中进行“先行调解”的人员包括法院法官、司法辅助人员以及法院外的其他组织。所以从“先行调解”的主体构成来看,认为“先行调解”是诉讼和非诉讼调解相互交错,链接的产物。[9]相对而言,在我国的一些民事诉讼法教材中则认为,诉讼调解和法院调解是同一事物,只有诉讼程序当中才有法院主持的调解。法院调解就是指在组成法庭的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而不是指在法院其他部门人员的主持下进行的调解。[10]从这一角度来看,仅仅只有审判人员主持的调解才叫法院调解或诉讼调解,也就意味着只有案件进入审判庭之后进行的调解才叫做诉讼调解或法院调解,在此之前的调解都属于非诉讼调解机制。且在先行调解中排除主审法官作为调解员,可以实现调审适度分离,减少法官给当事人的压力,充分年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11]因此,对“先行调解”性质认识上的不统一,导致对“先行调解”主体的选择的认识有所区别。
2.缺乏明确的主体范围界定
通过观察司法实践中的情况与对现有的相关文件的梳理,导致“先行调解”主体选择困境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司法实践中缺少明确的主体范围界定。
从司法实践中的观察来看,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法院在“先行调解”主体的安排上存在诸多不同的设计,如:设立在法院的人民调解室负责,由选任的退休法官、检察官或其他具有调解经验和专业知识的非法院在职人员担任调解员;由本院法官独自主持,如由立案庭的法官主持,将立案与后面的审判主体分离,达到调判分离;还有则由被委托的调解组织的人员担任调解员;由本院法官和受委托的调解组织共同组织成调解庭;此外。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裁判文书中,还有通过审判员进行先行调解的现象。②
从相关文件的规定来看,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强调进一步强化了诉前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目标,且对围绕立案前后的调解方式进行了更细致的规划,如在立案前建立诉前调解工作室或者“人民调解窗口”,在立案后、移交审判业务庭之前利用立案窗口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在调解主体上,委托调解不限于和审判人员共同进行调解,可以通过制作调解移交函,由被委托的调解人进行调解。在调解机制上要求建立以调解类型分类划、调解法官专业化、调解方法特定化为内容的类型化调解机制。由于对“先行调解”主体的规定零散的出现在有关调解的文件之中,且常常规定的较为粗糙,所以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先行调解”主体安排的较为混乱。
(二)“先行调解”主体选择解困之我见
1.明确“先行调解”的性质
对“先行调解”性质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民事诉讼程序之间功能的正确理解之上。从与国外的类似调解程序与设计来看,国外的法院调解除了法院在诉讼中所主持的调解之外,还包括在诉讼程序之外由法院所主持的调解形式,如日本的民事调停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诉前调解以及美国的附设在法院的调解,此类调解称为“法院附设调解”。法院附设调解虽然与我国的法院调解名称相似但性质不同。虽然都有法院的参与,但前者是诉讼外的调解,调解作为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程序独立地运行于审判之外,属于非诉讼程序。从这一角度来认识,先行调解应当是非诉讼调解,其性质与前述的“法院附设调解”更为相似。法院附设调解是基于优化司法资源,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同时保持诉讼程序本身的运作规律和基本原则,使调解和诉讼在对立的前提下进行衔接而设立的,与诉讼程序联系最为紧密,具有简单易操作等优势。我国目前的“先行调解”制度在部分功能和形式上是和国外法院的附设调解是类似的。此外,从前文中提到的“先行调解”在调解功能上与现有的“审前程序”中的调解的功能是相互衔接的关系来看,将“先行调解”理解成非诉讼调解是合理的。
2.统一“先行调解”主体范围
通过对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这一阶段调解工作的历史回溯以及对当前司法实践中的有益借鉴,笔者认为“先行调解”的主体应当是除审判人员进行的法院调解之外的所有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和人员。
我国成立初期,在诉讼与非诉讼相接阶段承担调解职能的主要是法院调解制度,而法院邀请调解、委托调解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时期法院调解的两种具体工作模式。后来委托调解被弃之不用,法院邀请调解得以保留,并且被我国1982年、1991年《民事诉讼法》肯定,但在法院调解冷落期间法院邀请调解也很少被运用。[12]随着国家倡导的诉调对接机制的构建,法院邀请调解、委托调解被视为调解与诉讼业务衔接的重要方式。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对于能够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该规定依据的是《民事诉讼法》第87条。尽管在前文中,将人民法院调解和先行调解区分为截然不同的性质,但这也表示邀请调解、委托调解等调解方式的新发展。在2009年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法院在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可以委托诸多非诉讼调解机构进行调解,以及在立案后可以将民事案件委托给诸多非诉讼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尽管在用词上,对立案前和立案后分别用了“委托”和“委派”,但其意义都是相同的,即是对“先行调解”主体初步认定。而对邀请调解依然限定在人民法院调解的阶段,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有关规定邀请符合条件的组织或者人员与审判组织共同进行调解。2010年通过的《人民调解法》第十八条就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该法规也明确表示,人民调解委员会也能作为“先行调解”的主体。
从2012年《民事诉讼法》对“先行调解”制度予以确定之后,各地法院对“先行调解”的有益尝试及带来的社会效应,上述对“先行调解”范围的定义也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及可行性。如重庆市渝中区建立的“1+8+77”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针对纠纷类型建立联合调处机制,其性质更像是一种以法院为主导,通过整合非诉讼调解资源形成的纠纷化解平台。在调解主体上包括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员以及法院工作人员。如厦门法院2015年发布的《厦门经济特区多元化纠纷促进条列》实施的在立案前由人民法院进行风险评估,提供程序选择的建议。还可以通过社会购买购买社会力量进行纠纷调解。其次,还通过提前将纠纷分类成涉军纠纷、保险纠纷、证券期货纠纷、传统民事纠纷等23类纠纷,分别争对这些纠纷类型预先登记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单。还有如山东省2016年发布的《山东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列》,其中表示在人民法院在登记立案前应当进行诉讼风险告知,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宜的纠纷化解途径;并在通过预先登记的人民调解组织名册和调解员名册中的组织或者个人进行先行调解;不难看出,各地法院在先行调解中或者即使没有明确为先行调解而在实际却是先行调解的情形中,普遍实行的由社会组织、行政机关、人民调解员通过法院委托、邀请、建立联动机制或社会购买的形式参与先行调解。
此外,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指示了健全特邀调解制度,“人民法院可以吸纳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作为特邀调解组织,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专家学者、律师、仲裁员、退休法律工作者等具备条件的个人担任特邀调解员”,明确提出可以适用特邀调解的方式进行先行调解。同期还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第一次在司法解释的层面认定法院可以通过立案前委托、立案后委派特邀调解组织或特邀调解员进行先行调解。而特邀调解组织或特邀调解员则来自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和行业调解的组织或个人。由此可知,在实务工作中和法院工作安排中,先行调解的主体愈加明确,即是除法院审判人员之外的所有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和人员。“先行调解”工作展开的具体形式则是以法院为主导,通过法院委托、委派等途径将非诉讼化解纠纷力量进行整合建立的链接平台,其具体形式依各地方资源而表现形式并不统一。
三、结语
事实证明,一项制度的完善必然要经过反复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先行调解”制度被《民事诉讼法》确认至今已有数年时间,期间,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该制度的运行都进行了不同程序的探索。本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尝试从分析诉讼程序之间的联系以及观察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入手,对“先行调解”的时间适用范围与主体两个问题进行了再探讨,以期为“先行调解”发展中遇到的困境提供有益参考。
[注释]
①在知网上篇名中直接带“先行调解”字眼的文献,从2012年到2016年就有74篇,其中包括期刊、报纸和硕士论文.
②中国裁判文书网((2016)鄂606民初199号).
[1]许少波.先行调解的三重含义[J].海峡法学,2013(1):12.
[2]李德恩.先行调解制度重述:时间限定与适用扩张[J].法学论坛,2015(2):48.
[3]赵刚.关于“先行调解”的几个问题[J].法学评论,2013(3):33.
[4]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9.
[5]李浩.先行调解制度研究[J].江海学刊,2013(3):139.
[6]王亚新.新民事诉讼法关于庭前准备之若干程序规定的解释适用[J].当代法学,2013(6):16.
[7][日]田中成明.现代社会与审判:民事诉讼的地位和作用[M].郝振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9.
[8]许少波.论先行调解协议的效力[J].江苏社会科学,2014(6):79.
[9]李喜莲,裴义芳.先行调解法制化运行的困境和出路——以H县人民法院为分析样本[J].怀化学院学报,2014(10):58.
[10]江伟.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13:215.
[11]蔡泳曦.民事案件“调解优先”政策再思考——以新<民事诉讼法>先行调解制度为视角[J].现代法学,2013(5):135.
[12]常怡.中国调解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6.
D925.1
:A
:2095-4379-(2017)28-0014-04
谢米隆(1992-),男,汉族,湖南邵东人,湘潭大学法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