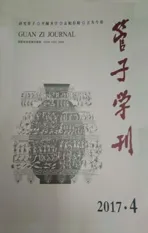日本《管子》四篇研究概述
2017-01-27杨纪荣夏晓辉
杨纪荣,夏晓辉
(1.山东理工大学 齐文化研究院,山东 淄博 255000;2.山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日本《管子》四篇研究概述
杨纪荣1,夏晓辉2
(1.山东理工大学 齐文化研究院,山东 淄博 255000;2.山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管子》四篇是先秦诸子学的重要文献,指的是《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内业》《白心》四篇。《管子》四篇的形成并非一时一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在《管子》的海外研究中,以日本的研究成就最为突出,《管子》四篇也是日本学者重点关注的课题之一。文章梳理了日本学者在《管子》四篇研究的几个方向,其内容涉及到《管子》四篇与老庄思想的关系、“气”论思想、养生学说及心学和政治思想等,总体说来,日本学者是从《管子》四篇的内在线索来考察其思想内容,他们的研究视角可给国内的《管子》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日本;管子四篇;道家思想;气论;养生
《管子》一书思想内容驳杂,兼有道家、法家、儒家、阴阳家、名家等诸家特征,其中关于《心术上》《心术下》《内业》《白心》四篇,刘节与郭沫若首先展开了《管子》四篇的系统研究,他们认为“《管子》四篇”应为战国时期的宋鈃、尹文之作,而近年来不少研究者认为它们是出自稷下黄老学派或者稷下道法家之手。关于《管子》四篇的研究,也成为日本学者重点关注的《管子》研究内容之一,当然他们所关注的兴趣点也许与国内的管子学者有所不同。在日本学界,比较早谈及《管子》四篇的学者是贝塚茂树,他在《诸子百家》中加以著述,并认可刘节和郭沫若关于《管子》四篇是宋鈃、尹文遗著的说法。但是总的来说,日本学者对于刘节、郭沫若的宋尹遗著说多持批判意见,多数日本学者会依照内在线索来考察《管子》四篇自身的思想内容,并进而开展相关研究[1]9。日本学者关于《管子》四篇的研究较多,本文不可能一一详述所有的研究成果,只能选择比较重要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来加以介绍与归纳,使读者可以窥见日本学者关于《管子》四篇的研究概貌。
一、《管子》四篇与老庄思想的关系
武义内雄是比较早从《管子》四篇所蕴含的道家思想来研究管子的学者之一,武义内雄(1886-1966),号述庵,三重县人,日本哲学家,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专家[2]227。他于1941年在《支那学》刊发了《管子的心术与内业》,后又载于《武义内雄全集》第六卷,文章的内容主要分析《管子》中的《心术下》《内业》这两篇文章中的道家思想,并将《心术上》和《心术下》《内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但他却没有展开更深的后续研究。
(一)《管子》四篇蕴含道家思想的原始形态及对《老子》的影响
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且取得一定成就的学者是赤塚忠。赤塚忠(1913—1987),文学博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楚辞研究专家。赤塚忠对《管子》四篇中的道家思想尤为关注,且自成一家,影响很大。1963年,他发表了《虚静说在老子中的发展》,探讨了《老子》思想中的神与虚静的问题,认为道家的虚静说从《管子》到《老子》,已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接下来,他在1967年发表了《道家思想的原始形态》①《东京大学文学部研究报告》第三,又载于《赤塚忠著作集》第四卷。转引自谷中信一编《日本·中国:〈管子〉研究论文、文献总目索引》,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1页。,1968年又发表了《〈庄子〉中的〈管子〉心术篇系统学说》②《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0集,又载于《赤塚忠著作集》第四卷,研文社刊,1988。转引同上,第92页。。在这两篇文章中,赤塚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他在《道家思想的原始形态》中认为“《管子》四篇”中保存了道家思想的最初形态,并且这种思想来源于古代的信仰体验,为此他考证了四篇的成书时代及各篇的特点。在《〈庄子〉中的〈管子〉心术篇系统学说》这篇文章中,赤塚则从《庄子》的序言、外篇、杂篇的思想系统来探讨和《管子·心术》篇的关系。赤塚的研究自成一种风格,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也多与他人不同,而且他认为《管子》中的道家思想比《老子》还古老,并且寻其源于中国古代的信仰体验,这都是他的新说,值得参考,这与很多学者认为《管子》四篇在《老子》之后并接受了《老子》的影响不同。
在《道家思想的原始形态》一文中,赤塚首先总结了武义内雄和津田左右吉博士对于道家思想的分析和各自的不足,然后提出要考察道家思想的原始形态就应该排除道家传承者的论述而只以公认的原始文献为依据。他认为,原始文献中虽然没有直接表明道家思想的资料脉络,但总会有显示这一系统思想的起点资料,而以这一思想的原始形态为基础,就会更进一步地以实在的证据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赤塚对《管子》四篇的基本特征所做的进一步的探究,是为了考察它们在道家思想史上的特有地位。
赤塚首先分析了《心术上》篇,上篇前半部分是“经”,后半部分为“解”。他以“心之在体”到“与人并处而难得也”这一段韵文为例指出,解文与经文有着某种程度的差异是客观事实,解文以经文为根本,导入了新的命题和概念,尤其是强调了“心术之虚”,并力图展开论述,说明解文和经文并不是同时产生的。结合先秦典籍的常规情况,赤塚分析《管子》是把有韵之文作为经文的,而他所引述的《心术上》篇中经文的有韵之文,则是先于整个经文而成的、固有的、被传承下来的“原经”,我们所看到的该篇经文则是对“原经”的解说。基于他的推断,赤塚将《心术上》篇分为三个部分:即“原经”“经文”“解文”。三个部分代表“心术”系统发展的三个阶段,而“原经”则体现了这种思辨的原始形态。他指出,“原经”是《心术上》篇和《心术下》篇的古经,先于《老子》和《庄子》的出现,是现存最古老的道家文献,道家思想即由此展开。
在对《心术下》的考察中,赤塚指出,下篇中的“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与上篇之经文、解文中的“物固有形,形故有名,名当,谓之圣人”所揭示的意旨是同一的,下篇承继了“原经”的系统,而且,对“原经”有所否定,从而提出了“专意一心”而达至“精气”的主张。赤塚认为,《心术下》是以新概念的提出来展开的,文中首先提出了“气”的概念。“气”这一概念的产生来自于对人的外形与内心的分析,它是人的精神的一种形态。下篇提出的第二个概念就是“心”的能动作用。如“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民”[3]12。上篇也谈到“心”,但主要是对否定自我意识的一种反省,而下篇中的“心”,更强调由心而生成的先验的意志。下篇提出的“心”这一概念,是与“气”合为一体而发挥作用,其实是在强调身心的调和统一。第三,下篇中还提出了“养生”的观念。如“人能正静者,筋肕而骨强”“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3]13。
在分析《内业》篇时,赤塚指出本篇提出了独立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强调“道”,明确了道、心、气三者的关系。其二,是对“心”的认识尤为显著。《心术下》篇对“心”的认识也有论述,但把“心”置于“气”之后,指出由专意一心、内省以达至精气。而《内业》篇不管修道也好,获得精气也好,都依赖于心。“正心在中,万物得度”[3]78,这种主张与儒家所倡导的统率万物者是心的观点是一致的,恐怕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三,强调了“和”的作用。《内业》篇主张抑制自我,便可达至一种和谐状态。心之和谐与养生说,在《心术下》中都显露端倪,《内业》篇又将其加以光大,而且把个人的身心安静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论述,正好显示了道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态。
最后,赤塚忠对《白心》篇进行了考察。他认为,《白心》篇所承接的是《心术上》篇,并试图将这一系统进一步展开。当然,《白心》篇也提出了新的主张,并与《心术上》篇有诸多不同。其一是倡导“以时为宝”,从而赋予“道”以“时”的成分。其二是主张“以政为仪”,主要的着眼点是“应物”。《白心》篇中的“应物”说有两个方面特征:一是与重视“时”相适应,二是倡导“和则能久”“人不倡不和”,主张君主之和。
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中,赤塚忠把《管子》四篇各自的内容和构成归纳为脱离了道家思辨的原始形态,与时共进,逐次展开,从中可以看出道家思想形态的发展过程。日本学者原宗子在她的《〈管子〉研究的现状和课题》中说:“《管子》书中为何、又是如何保存了这些各类的论说?或许这是稷下横议的遗说,但却又未能找到任何确认这一点的证据。从战国末期到秦代,存在《管子》之类的文献,这是确定无疑的,就是法家的著作。西汉末期,经过刘向的编订,大致成为现在的形式,但究竟是如何传承下来的还不清楚。《管子》的成书之事及在学术史上的性质仍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这点上来讲,以上各种论说是否妥当还要画上一个问号。但是即便如此,通过探讨心术系统之说在《老子》《庄子》等其他文献中如何展开,可以提升这种假设的可信度”[1]15。文章也使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理论也发生了相应地变化,也就是说《管子》四篇体现了道家思想有原始形态逐步发展的一个过程。
(二)《庄子》对《心术》篇道家思想的传承
在上篇论文的基础上,赤塚又发表了《〈庄子〉中的〈管子〉心术篇系统学说》。在这篇文章中,赤塚将《庄子》与《心术》篇展开了比较研究,来探讨两者的关系。文章首先比较了《庄子》内篇中《人间世》里的“心斋寓言”和《养生主》里的“庖丁解牛”寓言与《心术》的关系,认为这些寓言显然是继承了《心术》系统之类型相异的寓言。比如在《内篇》中的《人间世》的“心斋寓言”,结尾说:“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其中“鬼神将来舍”与《心术上》“原经”所作“虚其欲,神将入舍”几乎无异,由此可以知道“心斋寓言”和《心术》关系之密切。在逐句逐字解释了彼此的对应关系后,赤塚指出:“心斋寓言”的主要问题在于心的状况,在于“万物之化”,这与《心术上》所说的对象完全相同,所以它是属于《心术》系列的论述。而“心斋寓言”中提及的“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也暗承了《心术下》中的“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饰德,万物毕得”,修“内德”是《心术下》的主张,而“心斋寓言”里提倡“德”,并且也提倡“人气”“人心”,这些都是受《心术下》的影响。其次,“心斋寓言”也有与《白心》篇的主张应和之处,赤塚在举例详细阐述后,指出:从系谱上来说,《心术上》“经”的“虚无无形,谓之道”,及其“解”中的“唯圣人得虚道”、“虚者,万物之识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舍矣者,言复于以虚也”等等,都是强调“虚道”乃至得道,因此,“心斋寓言”的“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结合了《心术上》的“虚”“道”与《心术下》的“气”。其后,赤塚又分析了《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寓言,《德充符》中的王骀、哀骀它等寓言,认为它们均与“心斋寓言”相关,而“心斋寓言”是基于“原经”,以及对《心术下》《白心》主张的批判之上来展开其论点论述的。
接下来,赤塚又分析了《大宗师》的“坐忘寓言”“见独寓言”及《寓言》的“大妙寓言”等,作者认为这都是根据“心斋寓言”乃至《心术上》《心术下》,或至少是以此观点为基础来展开的;在他看来,这些寓言的主旨在于得道的境界,显示出道家思想成熟的极点,这些寓言大抵与《内业》同时存在。至于《庄子·外篇》的《在宥》《天地》《天道》等,是主张虚静无为的帝王之道的类型,此类型晚于“见独寓言”,呈现出道家思想的衰落现象,较《内业》晚,由此可知,《管子》四篇学说的传承过程经历了很长时间。总之,《庄子》书中不仅有传承《管子》四篇《心术上》系统的学说,也受到《心术下》思想的影响,而将此传承作为发展其思想的重要一环。
对于赤塚忠的学术研究,原宗子做出了以下评价:“为了研究《老子》《庄子》或者道家思想,作为使用《管子》言辞的研究者,我们看到了最具良心的辩证法之一。赤塚的这些论说,并不只限于道家思想研究,也大致概括了利用《管子》解析事情的大部分日本研究者的态度。不管怎么讲,赤塚的目的在于探索道家思想的展开,而非对于《管子》的解析说明。他以“道家思想的原始形态”中的结论作为基础,按实际顺序使用《管子》四篇,对于《老子》《庄子》的各个篇目,也展开了扎实地分析论证。”[1]15在赤塚发表的这四篇文章中,他对于道家思想体系的源起、发展、传承的脉络给出了他较为透彻的论证和思考,在日本学界也备受关注。
二、《管子》四篇中的“气”论研究
在对《管子》四篇的研究中,小野泽精一从“气”这一观念的思辨发展过程入手来加以分析,其观点也很有见地。小野泽精一(1919—1981),出生于东京都淹野川区,1943年9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他在其《齐鲁之学中的气的概念——〈孟子〉与〈管子〉》①《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小野泽精一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一文中阐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探讨齐鲁之学中“气”的思想史,二是比较《孟子》的“气”与《管子》的“气”的不同——《孟子》中看到的“心”对“气”的制约,《管子》中看到的“气”向“心”的扩张。
小野泽精一首先分析了日本学者对《管子》四篇里“气”的观念的认识以及这一观点提出的过程,他说:武内义雄在《老子和庄子》(1930)、《中国思想史》(1936)的《管子的心术和内业》中,注意到是稷下之学中的道家之言,特地把《心术上》的内容分析和《心术下》《内业》进行了比较,但未能提出“气”的观念。而对“气”加以注意的,是栗田直躬《中国上古思想之研究》(1949)中的《古代支那典籍中所见的“气”观念》一文,它以追究用语意义为资料,考查了从呼吸的原意开始到生命原理为止的发展,在抽象出具有跨越肉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冲动性质的同时,还对“气”“心”“魂魄”等文字出现以前的阶段加以关注。但是,对《管子》的注意很少,对为什么“气”会出现这个问题,也未能加以关注。小野指出:黑田源次的《气的研究》,从对“气”字的小学考察出发,以“氣”字的构成要素“米”和与“气”字通用的“既”字的构成要素“皂”都是谷物为根据,提出了“气”是以饮食为基础的生气这样的假定,另一方面,把人的血气向自然之“气”的发展,也理解为从《诗经》到《淮南子》的古文献中阴阳五行思想的东西。《管子》《吕氏春秋》的资料之多也引人注目,但就齐学的考察而言,却没有被作为对象。根据小野的观点,赤塚忠的《道家思想的原初形态》在内容上探讨了《管子》这四篇作品,也谈到了“心”“气”“道”,但作者主要是在假定了道家思想原始形态的同时,从其发展过程中来考察四篇作品的成立关系。综上,小野泽精一对之前的日本学者对齐学和《管子》四篇里的“气”的研究做了一个梳理,然后他重点来分析《管子》中的气的思想,而主要素材就取自《管子》四篇。
小野认为,《管子》中的“气”,在受“心”和“气”这两个范畴制约的理论立场上来说,未见有与《孟子》特别不同之处。甚至,就连在重视“气”本体的《心术下》《内业》中,“心”也受到比气更多的重视。小野指出,即使同样使用的“心”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四篇中的内容上是有变化的,在《心术上》中,“心”用“宫”来表达,但在其解说中,则有作“智之舍”的意思。到了《心术下》《内业》,“心”虽然多次被提到,但有与“外”相对的“内”(或曰“中”),作为替代“心”之物,也有被多次使用的情况,关于生存方式,在《心术上》中,要求的是人去欲去智,讲求虚静,因顺的、被动的生存方式,而到了《心术下》,则发生了所谓“‘气’为身之充……其充不美,则心不得全”这样的变化,产生了主张要靠“专一”这种精气的集中来积极对付的变化。另外,小野分析,《内业》中“心气”的用语,显示了“心”和“气”的交错;还有,“心”不仅具有广泛性,还具有深入性的要素。而这种“心”深处之“心”,被称之为“意”。同一个“心”,成为具有广泛性又具有深入性之物,就变成具有和《心术上》以前的东西完全不同性格之物。《心术下》《内业》中使用的“意气”,或“气意”“心意”,可以说是显示了与“心”之“气”交错的“意”的深层状况的窗口。所以,在小野泽精一看来,从《心术上》开始,到《心术下》《内业》变化中的所见情况,可以看到:作为人的认识,或行动的主体方面,不仅有“心”,而且还提出了“体”,也就是“心”的内涵,不仅具有广泛性,还企图朝中间深入的内层发展。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小野说:《心术下》和《心术上》的根本不同之处,不在于认为是由“神”或是“道”这些他律的规范来决定人的形成和生存方式,而在于企图通过在身体中充实自然之“气”,由自律的集中力来把握外物和世界。到了《内业》,在人的形成和行动中的“气”的主导性,更鲜明地彻底化了。经过了体验到身和“气”的阶段,“心”在意义上,有着广度和深度的伸缩,无论在作为主体的身和形方面,还是在作为对象的神、道和“气”方面,都产生了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生命力的“气”的渗透性,它不仅涉及人之身,而且进入了包括所有物的广阔范围;另一方面,在“气”中高度升华的“精”,带着比神、道更多的新鲜性被独立地提了出来。
小野泽精一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典籍资料,通过广采前人成果,探讨了“气”逐步成为一个哲学概念的思辨过程。当然,在将《管子》中的“气”和《孟子》中的“气”做比较时,他还提出这样的观点:“《孟子》也好,《管子》也好,都认为‘气’是充实身体之物,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而在‘气’和志,或者和心所占的比重上,《孟子》虽也重视‘气’,但认为‘志’最为优先;与此相反,《心术下》《内业》,虽也重视心,但认为‘气’更为优先。二者可以看到这样的差异。同样是围绕‘气’和心,如果加以比较,还可以看出,在同一个山东半岛(即齐国和鲁国之中),也存在着泰山南面邹地的孟轲偏重于心,即精神方面;泰山北面齐地的《管子》则偏重于‘气’即身体方面的倾向。”对他的结论,有的学者并不认同,比如刘长林提出:《管子》诚然非常重视身体,然而正是《管子·心术上》强调:“心之在体,君之位也。”故与身相比,更凸显其对心的重视。从《心术》《白心》《内业》之篇名亦可见,其所论气,均从属于心。如果将《管子》四篇与《孟子》相比,只能说四篇对“气”之概念的论述较之《孟子》更为详尽,但在心与气的关系上,二者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从认识和实践的角度说,“气”与心相联系,心能够主使“气”,修心是关键,故心优先于“气”。《管子》四篇正是这样做的[4]896。
关于对《管子》四篇中这个问题的关注,还有室谷邦行的《〈管子〉中的“气”》①《北大史学》第18号,(北海道大学史学会),1978年。转引自谷中信一编《日本·中国:〈管子〉研究论文、文献总目索引》,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96页。,文章主要探讨的是《管子》中的“气”“道”的概念,以及“气”和“道”的关系,其详细内容不再赘述。
三、《管子》四篇中的“养生说”研究
从体悟“道”,到依照虚静之法加强心之修养,从而实现与宇宙合一,达到“养生”的愿望,对于《管子》四篇中的“养生观”探讨比较深入的是鬼丸纪的《〈管子〉四篇中的“养生说”》②《日本中国学会报》,1983年。转引同上条,第100页。,文章重点通过《管子》四篇中的早期道家思想与“养生”形成学说之前的原始状态的关系而展开探讨。
首先在“道”的体悟与养生这一部分,鬼丸纪认为在《管子》四篇中,“养生说”是以“虚静”说来体现的。鬼丸纪援引了《心术上》的文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虚静之道,本是自然界的法则。它规定着自然现象的发生。人若遵循自然之道,便能规定人事现象。人在最初形成这一认识时,是把自然法则导入人事,是把人与自然的合一作为一种理想。人若遵循自然之道,在人世间便可遂心如意,同时也便形成了能够“化育万物”的心理。体悟了自然界的理法,便与自然界成为一体,这样一来,人力便波及到自然现象中了。鬼丸纪指出,这即是《心术上》中的“养心说”。
接着,鬼丸纪又考察了《心术下》和《内业》中所论及的“气”的概念,以及“气”与“心”的关系问题。他说,从这两篇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意”存在于“心”之深奥处,是先于“言”和“思”活动的,也就是说“意”是人进行思维以前的一种精神活动,而“气”也是人进行思维以前的精神活动状态,具有这种性质的“气”在《孟子》和《庄子》中同样可以看到,但又有不同。根据鬼丸的观点,此两篇文章中并没有明确将“气”与“心”区别开来,但把“气”作为一种存在于心底的意识,在《管子》之前的文献中并没有见到,所以他认为这是人们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心术上》论述由舍弃人知、人为,而体悟自然界法则,从而达至理想状态,而《心术下》在对“心”做了深刻考察的基础上,论述了“气”的作用,“气”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存在于人之心底的,因此,养心说逐渐为养气所取代。养心说应该是养生说本来的形式,随着“气”这一概念的形成,养气说成了养生说的核心。
在第三部分中,鬼丸纪指出,《心术下》和《内业》篇中的“气”具有两重特性:一、它存在于人的内心,是超越人知的;二、它的生成万物的能量遍流宇宙全体。为了搞明白为什么《管子》把“心”之修养与化育万物相结合?为什么“气”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特性?作者把《管子》四篇对“人”的认识做了一番考察。《内业》篇云:“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鬼丸认为,这里解释了人即由“气”而生成,“精气”造就了人,人与宇宙是密不可分的,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随着以万物的主宰者为中心的自然观被新的价值观所取代,人们对人生的关心加强了,“养生”成为此时一个重要问题为人们所思考。《管子》四篇中出现的“气”的思想,抑制了有神论的自然观,构建了观念上的新的价值体系。
最后,鬼丸先对《内业》篇中提出的“和乃生”的生命观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的生命是禀自然界之“精气”和“形气”而成,因而“和”乃人之产生的根本条件。“和”一旦遭到破坏,人便会有喜怒之情,于是出现了一种作为养生方法的“虚静说”。而《管子》四篇中的“养生说”正是用“虚静”法养“气”,与自然合一,便能体悟“道”。这就是养生的终极目的。他强调,理想中的君主,便是以注重养“气”来正确主宰万物的,其行为也会对自然之顺调产生一定的影响。
他指出,《管子》四篇中提出的观点,后来成为道家“养生说”的主流,而“和”的生命观对《老子》《庄子》《孟子》的养生说也有很大影响。
四、关于《管子》四篇的成立年代
很多学者对现行的《管子》四篇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们根据各篇目的特征,关注了很多诸如“道”“气”“心”“精”“和”等词汇,探讨这些词汇背后的概念和蕴含的思想史的意义,从而得出对《管子》四篇的时间排列的思考,而很多的论证也在这样的时间序列上得以展开。我们在此呈现一些学者在其论文中对《管子》四篇的成文年代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赤塚忠在他的《道家思想的原始形态》中谈到:《心术上》的“原经”中用了道家思想的主要概念如道、物、真人、明等,尤其是显示了由虚静达至神明智的否定和飞越的哲学论理,而且这些概念和论理,通过作者和《老子》《庄子》篇章中的思想做比较,它们都是素朴的,可以看出它们的某些原始形态。所以他认为“原经”大概成书于公元前四到五世纪之交。
在对《心术下》的考察中,赤塚忠认为,下篇承继了“原经”的系统,而且,《心术下》是以新概念的提出而展开的,提出了“气”的概念,心的能动作用以及“养生”的概念。这种“养生说”,在《白心》篇和《内业》篇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心术下》篇大概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叶。接下来,赤塚忠又分析了《心术下》篇与《内业》篇的关系。通过对文本的分析,他指出,《内业》篇的写作年代不仅晚于《心术下》篇,也晚于《心术上》篇和《白心》篇,《内业》篇是对其他三篇内容的综述。
在分析《白心》篇时,赤塚认为此篇承接的是《心术上》篇,但同时又提出了新主张。而且《白心》篇还谈到了“和”与“义”的关系。这种思想与《墨子·天志下》的“天欲义而恶其不义也”,同属具有墨家思想特征的主张,作者认为此篇受墨家思想的影响,应该成书于公元前三到四世纪之交。
鬼丸纪的观点同赤塚忠有相似之处,他并没有论证《管子》四篇的大致时间,但内容的顺序和赤塚基本一样。他的排列是:《心术上》篇最早,《心术下》篇次之,而《内业》篇则较晚,《白心》篇的写作时间同其他三篇联系起来比较困难。
金谷治在他的《管子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他不赞成刘节、郭沫若两人将《管子》四篇作为整体来看的观点,他认为其证据不足。他承认《心术》上下篇和《内业》篇三篇无论从资料的前后关系,还是从内容上看都有一定的关联,但《白心》篇却与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很小,应该将它们分开来看。金谷治推定《心术上》是作于战国中期或者末期,《心术下》《内业》《白心》作于战国末期。
町田三郎在考虑《管子》四篇的时间编成过程时,他根据金谷治的观点,认为《心术》上篇的经与解的关系,与汉初老子文献派对待《老子》的态度是相适应的。据此,他认为《心术》上篇出自老子文献派之手,甚至进一步认为其余三篇也都一样。《管子》四篇无论其中的哪一篇,基本上都在秦汉时期与老庄派有些重合,而成书时间上他也比较赞成金谷治的观点。
五、《管子》四篇的其他问题研究
在《管子》四篇的研究者中,町田三郎也是很重要的一位日本学者。町田三郎(1932—),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文学博士。他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先秦两汉思想研究领域有着极高的学术造诣。他不但着眼于《管子》文本的整体研究,也关注《管子》四篇的思想,他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管子〉四篇》①《文化》,第25卷1号,又载于《秦汉思想史研究》,1961年。转引自谷中信一编《日本·中国:〈管子〉研究论文、文献总目索引》,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88页。和《再论〈管子〉四篇》②《东北大学教研部纪要》第4号,1966年。转引同上条,第90页。。在这两篇论文中,他的关注点在于《管子》四篇与《管子》的关系,而在《再论〈管子〉四篇》中,他指出,通过将四篇与《老子》《庄子》比较,可以看出《管子》四篇的思想是不成熟的,是朴素的,其中包含着道儒法及其他鬼神养生论的折衷主义态度,即四篇这样的存在方式,实际上就是内含有四篇的《管子》全书的普遍特性。在这样的构架下,四篇并不是偶然混入《管子》之中的,毕竟它是以《管子》的土壤为自身养分而生成的思想。在町田看来,贯穿《管子》全书的思想也是折衷主义的,并不局限于《管子》四篇。这是他个人的独特观点。这个观点发端于他的《论〈管子〉四篇》,其中他提出了一个“中”的观念,他认为这是《管子》四篇的实践规范,尤其是在《白心》这篇中论述了“中”这一概念;在《再论〈管子〉四篇》中,他说,《白心》篇从道的思想分离开,逐渐向创造另外的规范“中”的方向前进,从这点上也表明了《白心》篇的思想是最晚熟的。
对于町田这样的研究方法,原宗子给了这样的评价:“他的研究方式,面对的研究对象正因为是‘杂乱之书’——《管子》,因而显得更有意义。对他而言,《管子》是有独特性的,是包含各类思想逐渐膨胀生成的道家,所谓《管子》的独特性,是说在与道家、儒家、法家等的比较当中,可使其逐渐显现出来。”[1]11町田明确指出了《管子》四篇与道家的关系,但他也指出,从《管子》四篇里可以看出,对形而上的世界的关注已经在淡化,转而对于形而下的日常实践规范的探究,而这也是《管子》全书的方向。
石田秀实在1985年发表了《关于〈管子〉四篇与〈荀子〉正名篇中的“语言”问题》,是从古人思维方式的角度来分析比较两篇文章的关系。日本学者佐藤将之在评论这篇文章时说,石田认为,《管子》四篇提倡“虚心”而完全排斥所有知识、判断的标准,是一种特别的心理状态,也就是“气”的充分扩张的状态。在这种构架下,由自己的“身体动作”来掌握对象,以因循“不言之言”。相形之下,荀子提倡“虚——而静”的“大清明”,这其实是荀子将《管子》四篇的“虚心”用在日常认知的过程中而成的一种境界,但若如此,“大清明”境界系指“完全空白”的状态,所以无法产生对象世界的名字。因此,在荀子的知识论中有“类”概念的范畴。但如此又会碰到问题,即“类”的范畴既然是普遍的,何以会产生不同语言和“奇辞”等“异常”情况。石田认为,荀子提出“约”的概念来说明普遍的“类”范畴是产出不同语言的理由。整体而言,石田对中国古代的认识论,与认知过程及语言之间关系的分析,提供了《管子》(乃齐学)与荀子哲学一条不同的发展脉络[5]82。
1990年,幸本千寻发表了《〈管子〉的心和“神”——以〈心术〉上、下和〈内业〉篇为中心》,他从《管子》四篇中的三篇入手,关注“心论”的特征,也在探讨心与“道”“神”“气”和“精”的关系。幸本说,不可否认,《管子》四篇作为《管子》里面传授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而被广泛印证、论述,无论哪一篇都是关于心的修养的文章,但是,在对待心的机能作用上,其实道家是持否定态度的,而儒家却给予了充分重视,所以他认为,在道家思想中,“神”应是取代“心”的一种存在,所以他对《管子》中这个“心”和“神”的思考是,《管子》四篇中所重视的“心”,其实是经过儒家孟荀思想而得到的提升和完善,而道家把这种“心”和其重视的“神”相结合加以采用,并将这种思想意识下的心的概念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加入到“心”原有的涵义中,并用道家思想来修正“心”。而到了《内业》篇中,首次出现了将“道”“神”“气”“精”相结合的说法。他说,这些篇目所蕴含的思想是当时的时代思想,不仅仅是一家思想的阐述,吸收利用诸家的思想来阐述自家学说的杂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但它也非诸家主张的拼凑,而是具有一定的立场和方向性的。通过《管子》四篇,使得我们希望探寻《管子》这本书在道家立场下如何实现其现实目的,这些思想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人,经历怎样的过程而形成的,因此对《管子》各篇的形成、思想倾向和意义也是作者今后关注的重点。
综上,我们对日本学者关于《管子》四篇的研究从几个方面做了一个梳理,重点也是放在把日本学者的观点归纳介绍给国内读者,而不是通过批判其观点来凸显笔者本人的观点。希望本文可以为国内外管子学研究专家提供一些日本《管子》四篇研究的相关信息,为后续更加系统地研究和专项研究打下基础。
[1]原宗子.管子研究的现状与课题[G].流通经济大学论集,1984.
[2]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赵守正.管子注译[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4]刘长林.中国象科学观:易、道、医(下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佐藤将之.二十世纪日本学界荀子研究之回顾[M]//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B226.1
A
1002-3828(2017)04-0120-07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7.04.19
2017-06-23
本文是2016年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第一批重点项目“管子通论”之“《管子》海外研究与传播”的阶段性成果。
杨纪荣(1973—),女,山东巨野人,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讲师,主要方向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夏晓辉(1972—),男,陕西杨凌人,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方向是日语教学与日本历史研究。
张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