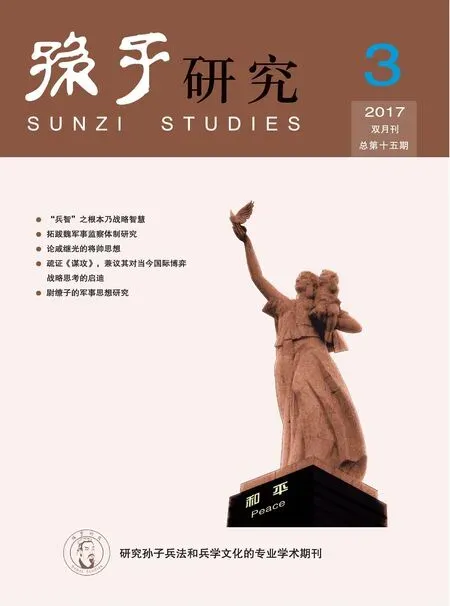我心中的先进党员形象
2017-01-27李治亭
李治亭
我心中的先进党员形象
李治亭
我是1940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4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一个只上过4年小学的农村孩子,成长为一名解放军军政委,都是党哺育的结果。我虽然已经离休多年,但始终不忘记自己是个老党员、老同志,永远珍爱自己的荣誉,保持政治本色。
回忆起我熟悉的一些老领导、老战友、老功臣、老英雄,尽管职务不同,但他们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却是相同的,这就是战争年代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滴水反映出太阳的七色光彩,一种“观念”、一种行为都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操守信仰。这些战争年代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人立身处世的一面明镜。做人民的公仆,人民将永远记住他;做人民的儿子,人民将永远怀念他。共产党员就要以他们为学习的榜样,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认认真真做事,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将军列兵李耀文
李耀文同志,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我军具有崇高威望、德才出众的老将军。我与他相识是在抗日战争中的1944年,他任鲁中军区第4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我是鲁中军区《前卫报》记者,采访过他。后来他任鲁中军区第23师政委,我作为记者又采访过他。他任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第26军政委、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时,我在报社工作。60多年结下了深厚友谊。
我永远不会忘记1958年9月,他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时,我当时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十分了解他下连当兵一个月的情况,写过报道。
1958年济南军区党代表大会上,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同志传达了毛主席提出的全体干部每年参加体力劳动1个月和军官每年下连队当兵1个月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军区党委响应。党代表大会一结束,李耀文同志就随同司令员杨得志上将去了连队。
李耀文同志下连队当兵的动人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脱下了将军服,换上了士兵装,身背绿被包,佩戴列兵衔,来到徐州某团6连当兵。
为了避免特殊照顾,李耀文改名叫李耀,战士都亲切地喊他“老李”。从团部来到连队那天,他谢绝了军、师领导陪同,自己背着背包,徒步来到连队。6连住的是老式营房,全连100多人同住一个大宿舍,睡的是双层木板床,他被安排在下铺。排长为了让他休息得好些,夜间站岗总是把他排在头班或末班。他坚决不同意,要求按顺序排班,经常半夜起来放哨。
清晨,起床号一响,他便翻身起床,快步到门外站队。一天是5千米长跑,他跑步不减速,一直坚持到终点。跑步回来,不顾满头大汗,整理内务,清扫卫生,擦玻璃,刷痰盂。劳动中,和战士一起挖土、抬土、拉土。在连队与战士同吃一锅饭,同吃一样菜。一天午饭,他发现饭桌上多了一盘辣椒炒肉丝,便找到司务长,耐心说明下连当兵不能搞特殊的道理,然后把菜倒在大菜盆里,这件事深深感动了连队官兵。
6连是全训分队,训练课程很紧。在训练场上,他身背冲锋枪,腰挎手榴弹,不怕风吹日晒,摸、爬、滚、打,不甘落后。战士们竖着大拇指夸“老李是合格的战士”。当兵一个月,他四次冲锋枪实弹射击,弹无虚发,四次优秀,全连也取得满堂红的好成绩。
国庆节连队举办文娱晚会,李耀文同志拉着胡琴来了一段优美的独奏,战士们听得十分入迷,叫好声不断。
一个月列兵生活,他被评为“五好”战士。在欢送将军离开连队那天,战士眼含泪花,拉着将军的手,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李耀文同志动情地说:“同志们留步吧!我们相处时间虽短,友情很深,人走心在。”将军当普通一兵的风采,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1960年,在广州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李耀文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在一个休息室里,一位领导同志指着李耀文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与杨得志同志一起下连当兵的李耀文同志。”毛主席微笑着与他握手,然后问起下连当兵的情况。李耀文汇报说:“一个月当兵生活,与士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打掉了官气、暮气、骄气、娇气、阔气,消除了官兵之间隔阂,密切了官兵关系,保持了普通一兵本色。”听了介绍,毛主席高兴地称赞:将军当兵不简单哩!好啊!这是军队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好做法,是个发展……
永不褪色何志远
我与何志远同志相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任第26军政委,我是师宣传科长;他任山东省军区政委、济南军区顾问,我是济南军区前卫报社社长,多次采访报道过他。1980年我任报社社长时,亲自主持了《前卫报》刊出《将军之位战士本色》专题通讯,并撰写了向他学习的评论文章。每一次与他接触,都受到感染,受到教育。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艰苦奋斗是人民军队的本色,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所在。一个人在生活上越讲究,就越会感到不满足,就越会忘掉群众的疾苦。”
何志远同志是一位1955年授少将军衔的将军,从普通农民到党的高级干部,地位变了,自觉做人民公仆的思想没有变,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没有变。
“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何志远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生前家中使用的桌椅板凳等家具,还是20年前管理部门配发的。一张引人注意的圆桌,是用几根木条钉成的,已很陈旧。一个发了黄的旧藤椅,上面捆了些旧棉絮,罩了一床几十年前公家发的黄毯子,他在时一直当沙发用。我在济南军区任报社社长时,有年春节去给他拜年,一坐下去吱吱作响,便说:“何政委,你该换一个沙发了!”他笑呵呵地说:“我舍不得啊!坐着怪有感情的。”有一年春节前,管理处统一做了一批沙发,给何志远政委家送去两个,他婉言谢绝,并说:“先给别的领导同志,我的沙发还行。”可是管理处考虑到节日期间到他家看望的人比较多,就再三劝说暂留几天,过了正月十五再商量处理。何志远政委想到这个“商量处理”的话中有话,笑了笑说:“好!”管理处同志以为这次说动了老政委,沙发留下了,满心喜悦。谁知农历正月十六机关的人刚上班,他一个电话打到管理处:“已过了正月十五啦,沙发怎么还不抬走?”管理处处长为难地说:“政委,沙发暂时先放在你家用着吧,以后再说。”没等说完话,何政委插话了:“克己奉公是革命人的本分。那不行。你要不来抬,我就要派人送去了。”无可奈何,管理处只好派人去他家把沙发抬走了。
何志远同志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是党给的,只能当人民公仆,不能当官老爷。他对自己、对部队、对身边工作人员、对家庭成员,都是这样严格要求的。有一次何志远政委突然发烧38度,想吃点橘子。公务员小马跑了几家商店都没有买到,很为难、很焦急,便到管理处诉说政委身体不好,开了封介绍信,找果品公司的领导买了5斤橘子。高兴地拿回来,送到何志远同志面前,并亲手剥了一个给他吃。他忙问:“几次没买到,这次是怎么买到的?”一听是用介绍信特殊供应,便严肃地说:“小马,可不能这么办事啊!商店里有就买,没有就算,打着我的牌子去找人家,群众会有意见。”他就这件事,对身边工作人员、家里的人约法三章:一,不准打着他的牌子去买群众买不到的东西;二,不准用他的名义办私事;三,不准去要额外照顾。
何志远同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不断告诫自己,绝对不能利用职权谋私利、搞特殊,由人民公仆变成官老爷。几十年来,他不仅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而且时时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做脱离群众的事。
奇袭白虎团英雄杨育才
杨育才同志是陕西省勉县人,1949年入伍,195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入伍后不久即奉命入朝作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荣立三等功3次、二等功1次、特等功1次,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一级国旗勋章”。回国后,杨育才光荣地出席了全军第二次英雄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接见。
杨育才离休前是济南军区第68军一名副师长,离休后他在济南干休所安家。我不止一次地到住处看望、采访他。1997年月底,军区组织11位英雄进京参加国庆节活动,其中就有杨育才同志。他几次到青岛看望当海军的女儿,我们都相聚。他的英雄事迹令我难以忘怀。
1981年离休后,杨育才仍然关心部队建设,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先后担任30多个单位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校外辅导员、政治顾问、名誉校长等。十几年来,杨育才先后做报告800多场次,听众达28万余人。杨育才曾被济南军区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三次被评为先进离休干部。1998年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杨育才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北京,当人们走进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战争”陈列大厅时,首先会发现,在那些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战利品中,有一面用白色丝线绣着的“虎头旗”。虎头两侧还绣着两个大字:“优胜”。这就是美李军在朝鲜吹嘘炫耀的所谓“王牌部队”伪首都师第一团——“白虎团”的团旗。如今,这面虎头旗上“优胜”二字的标榜,已成了对当年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伪军的绝妙讽刺。
1953年6月,当朝鲜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准备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竟公然破坏遣俘协议,制造借口,扣留我方战俘2万余人,并叫嚣继续“北进”,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为了加深敌人内部矛盾,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配合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决定立即组织夏季战役的第三次进攻——金城战役。在战役发起的7月13日夜里,时任副排长的杨育才带领一个12人的“化装奇袭班”深入敌后,于14日2时直插二青洞附近,出其不意,一举歼灭了白虎团团部,给我正面攻击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给大部队穿插开辟了道路。这场战斗后,杨育才成了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奇袭白虎团”的故事也传遍了天下。
他既是一名有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又是一个心底无私的人。1981年,杨育才从副师长的位置上光荣离休,仍然保持着英雄无私的本色。
杨育才有五个子女,他无论在位时还是离休后,都没有利用手中权力和战斗英雄的特殊身份给子女们谋过一丝便利。大女儿杨军15岁那年“上山下乡”,两年后在农村入伍,护校毕业后分配到了蚌埠某医院,后来又随部队调动到青岛,至今仍在卫生科当护士。二女儿杨华、儿子杨波和三女儿杨红当兵退伍时,他没考虑给孩子安排个理想的工作。如今儿女们单位效益都不好,儿子前年就下了岗。小女儿军校毕业时,完全有理由留在父母身边,可他反而做工作让女儿服从分配,结果分到了淄博某部测绘大队。子女们没跟英雄父亲沾过半点光,有时不免埋怨几句。杨育才总是说:“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再向组织伸手,觉得心里有愧啊!”
1999年4月25日,中国老龄委组织了全国百名英模进京观光团,杨育才是其中之一。
4月28日,他参观了中南海毛主席故居。4月29日上午,安排参观毛主席纪念堂。28日那天晚上,杨育才发起了高烧,陪同来京的大女儿杨军怕父亲撑不住,就劝他别去参观了。可杨育才说什么也不肯,他说:“别的活动我可以不去,看毛主席纪念堂我一定得去!”从踏上台阶那一刻起,杨育才就激动得全身颤抖。他来到毛主席遗体前,深深鞠了三躬。抬起头时,已经泪流满面。杨育才深情地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一个旧中国变成了一个新中国。我有今天,中国人民有今天,绝不能忘了他的恩情。我想念他啊!”
从纪念堂回来后,杨育才的病情陡然加重,当天下午就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5月23日,他辞世了。但他在战斗中那种无所畏惧的大无畏精神,他那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中国“保尔”朱彦夫
朱彦夫,1933年出生在沂蒙山区沂源县张家泉村,从小家贫如洗,一天学没上过。1947年参军,打了上百次仗,立了三次功,负了十多处伤;淮海战役伤了腿,在朝鲜战场上的一次战斗中受重伤,动手术后全身成了“肉轱辘”。他身残不失志,顽强生活,从1996年至1999年四年时间里,他嘴臂并用,绑笔、抱笔配合,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了《极限人生》《男儿无悔》近60万字的自传体小说。他是用血肉和生命写的书。人们称他是中国的“保尔”。
迟浩田上将曾先后三次看望他,并称赞他是一个真正革命战士、一个真正共产党员、一个真正中国人形象。1985年迟浩田任济南军区政委不久,就前往看望朱彦夫。1987年参加孟良崮战役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时,迟浩田再次去看望朱彦夫,鼓励他把自己的事迹写成书,教育后人。后来,迟浩田还亲笔为朱彦夫的《极限人生》题写了书名,为《男儿无悔》写了序。2003年10月15日,迟浩田又看望了朱彦夫,祝福他健康长寿,全家幸福。
1997年7月,朱彦夫的事迹受到了俄罗斯《真理报》驻北京特约记者安·克鲁申斯基的关注,安·克鲁申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文章,评价和介绍了朱彦夫的价值观和生平事迹。朱彦夫写了致安·克鲁申斯基的信,书面回答了安·克鲁申斯基的提问。
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是志愿军第26军77师231团的一名班长。我当时是军《战旗报》总编辑,曾报道过他的事迹。一次他所在连队奉命坚守长津湖以西的250高地,激战7天7夜,全连几乎全部阵亡,朱彦夫头部和四肢都负了重伤。昏迷中,饥渴难当的他,竟将自己被打出眼眶挂在脸上的左眼球吞进了肚里!他被送回国内抢救,整整昏迷了93天,大小手术进行了47次,四肢全部被截掉。
1957年,重新站立起来的朱彦夫,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他当村支书25年,工分不记、报酬不要,只靠国家发的几十元津贴过活。他什么照顾也不要,对乡里乡亲却照顾得很周到。有的老人生活困难,他牵肠挂肚送些钱物;见老人的房子漏雨,就用自家的麦秸,请人修好。老人见朱彦夫全家吃的是瓜干煎饼,房顶也露着天,禁不住落泪:“他大叔,您这是舍了自己顾别人啊!”
2000年4月27日,我乘车去他的住地沂源县南麻看望询问他。2003年7月27日,是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的日子,我又专程代表迟浩田副主席去朱彦夫住地山东沂源南麻看望了他。我请他谈谈人生价值,他激动地说:“人生价值在于贡献。我靠的是对党的坚强信念。只要对党的信念不变,精神不垮,就没有过不去的险关。奋斗着,就是幸福。”铮铮誓言感人至深。
迟浩田上将在朱彦夫著的《男儿无悔》一书序言中写道:
我们这些从战争中走来的人,曾目睹和亲历战争的惨烈与牺牲的悲壮。有多少可亲可爱、朝夕相处的战友,英勇地倒在沙场,消逝于烽火硝烟中。朱彦夫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他向人生的种种磨难,包括困苦、挫折、病痛、彷徨、绝望甚至是死亡宣战,向生命极限发出一次次冲击,不仅创造了生命的辉煌,而且获得了超越生命意义的新生,实现了生命的再造,表现了一个在党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特有的生命力。他把生命的能量定格在最壮美的极限深处了。
这是对他,一个共产党员最公正的评价。
(责任编辑:周淑萍)
Images of the Advanced CPC Members in My Heart
Li Zhiting
李治亭,撰文时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社长、总编辑,后任青岛警备区政治委员。1987年3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