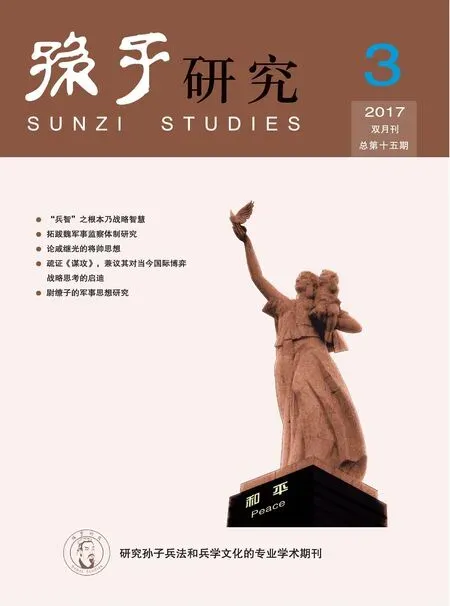拓跋魏军事监察体制研究
2017-01-27刘军
刘 军
拓跋魏军事监察体制研究
刘 军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承袭汉魏晋制度,结合自身特点,创设了行之有效的军事监察体制,具体包括监军行台、督军使者和各类副将。朝廷甚重督察要员的选任,通常以皇家姻戚、近信侍臣和宪台官员充当耳目,又特别注意人事关系的回避原则,确保监察活动的正常开展。督察要员不只局限于监视,还更多参与指挥决策和作战行动,职能全面深入。北魏军事监察体制顺应皇权专制发展的趋势,渐趋完备合理,不仅捍卫家国天下,还极大丰富了中古兵学文化与制度文明。
拓跋魏 军事监察 监军 集权专制 兵学文化
军事监察是对军队系统的日常勤务和作战活动进行督责,从而确保国家严密管控军队的制度,它是军事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构成军事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历代兵家在强调运筹帷幄的同时,还格外重视督军机制的有效实施。在古人看来,能否驾驭军队才是克敌制胜、拱卫家国的关键,并且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摸索出宝贵经验,它融汇传统兵学的精粹,相关成果值得后人梳理借鉴。分裂动荡、战乱频仍的六朝时期(220~589年)是兵学突飞猛进的阶段,特别是盘踞北方的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386~534年)走在时代的前列,其军事监察体制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不仅维持政权的长治久安,也为后世树立了足资模仿的样板,具有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意义。正缘于此,北魏的统治形势与内乱不息、手足相残的两晋、南朝形成鲜明反差,并为日后北朝征服江左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这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但仍有继续研究拓展的必要。笔者的问题意识和基本线索源自《魏书》卷七六《卢同传》的记载,孝明帝时,尚书左丞卢同为杜绝冒领军功的现象,上表曰:“请自今在军阅簿之日,行台、军司、监军、都督各明立文按,处处记之。”①[北齐]魏收:《魏书》卷七六《卢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3页。可见,降至北魏后期,行台、军司、监军等督军大员在排位序列上已凌驾统兵都督之上,表明监察权力向指挥领域的体制性渗透。本文便围绕行台、军司、监军,以及与军司属性类似的副将联合构建的军事监察平台及其职权运作展开论述。
一、行台对征镇诸军的监控
行台是中古国家宰相机关尚书省派驻地方的临时性办事机构,全权代表中央镇抚地方。行台制度始于魏晋,《通典》卷二二《职官四·行台省》:“行台省,魏晋有之。昔魏末晋文帝讨诸葛诞,散骑常侍裴秀、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钟会等以行台从。至晋永嘉四年,东海王越帅众许昌,以行台自随是也。”①[唐]杜佑:《通典》卷二二《职官四·行台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11页。北魏建国伊始便承袭魏晋旧制,设行台镇戍刚纳入版图的河北地区。史载: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邺。……帝虑还后山东有变,乃置行台于中山,诏左丞相、守尚书令、卫王仪镇中山。”②[北齐]魏收:《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1页。至北魏后期,行台制度渐趋稳固成熟,其中使者行台和统军监军行台具备军事监察功能③关于北魏行台的类型和职能,参见牟发松:《六镇起义前的北魏行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1991年。,需要详细说明。
北魏使者行台亦谓“台使”④台使之称始于东晋、南朝,参见牟发松:《魏晋南朝的行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10辑,1990年。,平素专司督察方镇统帅。史载,幽州刺史张赦提放纵妻子受贿,台使李真香“出使幽州,采访牧守政绩。真香验案其罪,赦提惧死欲逃”⑤[北齐]魏收:《魏书》卷八九《酷吏·张赦提传》,第1922页。。又冠军将军、岐州刺史元谧“暴虐下人。肃宗初,台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驿逻无兵,摄帅检核。队主高保愿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谧闻而大怒,鞭保愿等五人各二百”⑥[北齐]魏收:《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赵郡王干附谧传》,第543页。。元谧怒笞部下,正因为其向台使举报自己役使兵丁、破坏防务的罪行。紧急事态下,台使则负责督战,随时奏报军情。《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深传》:“深为侍中、右卫将军、定州刺史。时中山太守赵叔隆、别驾崔融讨贼失利,台使刘审考核,未讫,会贼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审驰驿还京,云深擅相放纵。”⑦[北齐]魏收:《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深传》,第431页。不久,元深被征还朝,褫夺兵权。以上三例足证台使巡查力度之强,其对将领的威慑力可见一斑。
北魏末叶,为讨伐四方叛乱,频繁设置督军行台。为确保充分发挥效能,朝廷合理编制组织人事关系。因大批皇室宗亲领兵带队,行台必由异姓臣僚担任,以防宗室势力独大,利用血亲纽带营私舞弊。具体事例详见下表:
当然,文献中也有特例。《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深传》载,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北道大都督元深领兵讨伐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叛乱,随军行台竟是同宗元纂,二人还曾联名“表求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赉,息其乱心”①[北齐]魏收:《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深传》,第431页。。这岂不违背朝廷规制?实际上,行台元纂监督的对象原本是汉臣李崇。案《魏书》卷九《肃宗纪》,早在正光四年(523年),“诏骠骑大将军、尚书令李崇,中军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元纂率骑十万讨蠕蠕”②[北齐]魏收:《魏书》卷九《肃宗纪》,第234页。。另据《周书》卷一五《于谨传》称元纂为“大行台仆射”③[唐]令狐德棻:《周书》卷一五《于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44页。。可知元纂此时以尚书右仆射衔领督军行台。次年,李崇出任北讨大都督,继续搭档元纂征讨破六韩拔陵,怎奈遭部将元渊(即元深)“表崇长史祖莹诈增功级,盗没军资。崇坐免官爵,征还,以后事付渊”④[北齐]魏收:《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1474页。。元渊于是取而代之,“专总戎政”⑤[北齐]魏收:《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深传》,第431页。,因前线事态紧急,才没有调换行台人选,元纂赖以留任。所以说,宗室与异姓互相牵制乃北魏行台监军的常态。
行台监军制度对将领的约束作用显而易见。兹取三条例证:其一,《魏书》卷七七《辛雄传》:“时诸方贼盛,而南寇侵境,山蛮作逆,肃宗欲亲讨,以荆州为先,诏雄为行台左丞,与前将军临淮王彧东趣叶城,别将裴衍西通鸦路。衍稽留未进,彧师已次汝滨。北沟求救,彧以处分道别,不欲应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众已集,蛮左唐突,扰乱近畿,梁汝之间,民不安业,若不时扑灭,更为深害。王秉麾阃外,唯利是从,见可而进,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专裁。所谓臣率义而行,不待命者也。’彧恐后有得失之责,要雄符下。雄以驾将亲伐,蛮夷必怀震动,乘彼离心,无往不破,遂符彧军,令速赴击。贼闻之,果自走散。”⑥[北齐]魏收:《魏书》卷七七《辛雄传》,第1694页。表明行台有权干预军事部署,督促主将积极行动。其二,《魏书》卷八二《常景传》:“杜洛周反于燕州,仍以景兼尚书为行台,与幽州都督、平北将军元谭以御之。……腹背受敌,谭遂大败,诸军夜散。诏以景所部别将李琚为都督,代谭征下口。”⑦[北齐]魏收:《魏书》卷八二《常景传》,第1804页。说明行台可相机行事,随时接掌军事指挥权。其三,《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北海王详附颢传》:“葛荣南进,稍逼邺城。武泰初,以颢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以御荣。颢至汲郡,属尔朱荣入洛,推奉庄帝,诏授颢太傅,开府、侍中、刺史、王并如故。颢以葛荣南侵,尔朱纵害,遂盘桓顾望,图自安之策。先是,颢启其舅范遵为殷州刺史,遵以葛荣充逼,未得行。颢令遵权停于邺。颢既怀异谋,乃遣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为己表里之援。相州行台甄密先受朝旨,委其守邺。知颢异图,恐遵为变,遂相率废遵,还推李神摄理州事,然后遣军候颢逆顺之势。颢以事意不谐,遂与子冠受率左右奔于萧衍。”⑧[北齐]魏收:《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北海王详传附颢传》,第564页。主将图谋不轨,行台未雨绸缪、暗中防范,化解危机于无形。总之,督军行台对稳定局势厥功至伟。
二、监军使者对征镇诸军的控制
监军使者,起源甚早。《通典》卷二九《职官一一·监军》追溯至春秋末齐景公差遣宠臣庄贾监视司马穰苴。①[唐]杜佑:《通典》卷二九《职官一一·监军》,第804页。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指出:“君主委付军权予将军,为了解控制情况,防止将军滥用权力乃至造反,君主有必要派出亲信为监军,以监察将军,使其正确执行君主之命令,并可把军中、前线之事务随时向君主报告;故监军之出现应与将军之出现同时,且不必到将军成为正式官衔才出现,有将军之事实即当有监军”②廖伯源:《汉代监军制度试释》,《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台北: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8页。。这说明两个道理:监军是君主集权专制的产物,监军与专业性的军事指挥权伴随始终。北魏建国,皇权主义的大幕徐徐拉开,监军配合王朝武装的升级扩张正式出台。最早的记录是后燕濮阳太守郦绍,“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授兖州监军”③[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二《郦范传》,第949页。。稍晚的有明元帝时,猎郎安原“出监云中军事”④[北齐]魏收:《魏书》卷三○《安同附安原传》,第714页。。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监军系统不断膨胀,原本作为军务帮办和参议的“军司”也纳入其中。⑤刘军:《北魏军司考论》,《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我们汇总各类监军的情况,一并归纳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控制军队甚严,若无监军,绝不贸然动兵。史载,宣武帝景明初(500至501年),署理扬州刺史元英上疏力陈“取乱侮亡”之道,建议趁南朝萧宝卷、萧衍君臣火并之机,“乞躬率步骑三万,直指沔阴,据襄阳之城,断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鱼肉。我居上流,威震遐迩,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断绝。又命扬徐二州,声言俱举,缘江焚毁,靡使所遗”。结果却“事寝不报”,没了下文。面对稍纵即逝的战机,元英只得退而求其次,把战略层面的总体规划降格为东线某个要点上的战役企图,即直扑交通枢纽义阳三关,为日后大举南征建立稳固的前进基地。⑥[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附英传》,第497页。[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齐纪一○》系此事于和帝中兴元年,即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的十一月,当年五月则有咸阳王元禧谋逆被诛之事,曰:“帝以禧无故而反,由是益疏忌宗室。”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503、4488页。此事标志宣武朝彻底扭转重用宗室的方略,从此宗室(尤其是服内近属)外出征镇备受掣肘,参见拙作《论北魏宣武帝宗室政策的变轨》,《内蒙古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元英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感知到宣武帝的疑忌,主动要求“请遣军司为之节度,世宗遣直寝羊灵引为军司。……寻诏英使持节、假镇南将军、都督征义阳诸军事,率众南讨”⑦[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附英传》,第497~498页。。必须强调的是,元英军中绝非一位军司,还有邓羡和薛凤子。⑧[北齐]魏收:《魏书》卷二四《邓渊附邓羡传》,第637页;卷四二《薛辩附薛凤子传》,第944页。日后,元英征剿冀州京兆王元愉反叛,挥师与萧梁会战郢州,宣武帝又遣军司薛怀吉和卢同督战。⑨[北齐]魏收:《魏书》卷六一《薛安都附薛怀吉传》,第1357页;卷七六《卢同传》,第1681页。可见,即便条件成熟,但无监军不出兵,且一军中派驻数位军司实行多重管制,显见皇帝的真实意图。
各类监军的选任同样大有名堂,其来源主要有三:一是禁卫武官,前引羊灵引本为皇帝的贴身扈从——直寝。薛怀吉的履历,“自奉朝请,历直后寝,领太官令”①[北齐]魏收:《魏书》卷六一《薛安都附薛怀吉传》,第1357页。。直寝是武卫将军麾下的直卫诸职之一,属“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的比视官,通常由皇帝亲宠的正式朝官兼任。②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90页。接替元英担任扬州刺史的任城王元澄请求攻打钟离,督军的钦差范绍本为羽林监。③[北齐]魏收:《魏书》卷七九《范绍传》,第1755页。又元澄出镇扬州之际,“启(张)普惠以羽林监领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寻加威远将军”④[北齐]魏收:《魏书》卷七八《张普惠传》,第1729页。。张普惠曾为元澄安西将军幕府旧部,元澄实则是按照朝廷的既定原则启请监军,既可顺利开展工作,又能消除皇帝的猜忌。二是中书、门下、集书省侍从文官。史载,中书侍郎贾思伯,“及世宗即位,以侍从之勤,转辅国将军。任城王澄之围钟离也,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⑤[北齐]魏收:《魏书》卷七二《贾思伯传》,第1613页。。中书官员典掌草拟诏诰、出纳王命,与皇权关系密切。门下官员监军见《魏书》五八《杨播传附杨昱传》:“贼围豳州,诏昱兼侍中,持节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颢,仍随军监察。豳州围解。雍州蜀贼张映龙、姜神达知州内空虚,谋欲攻掩,刺史元脩义惧而为请援。……诏以昱受旨催督,而颢军稽缓,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军。”⑥[北齐]魏收:《魏书》卷五八《杨播附杨昱传》,第1293页。同书卷七七《高崇附高恭之传》载尔朱荣盛赞高恭之:“臣本北征蠕蠕,高黄门与臣作监军,临事能决,实可任用。”⑦[北齐]魏收:《魏书》卷七七《高崇附高恭之传》,第1716页。侍中、给事黄门侍郎乃门下省的正、副长官,司职咨议顾问、拾遗补缺,是皇帝的近信侍臣。集书省官员监军见《魏书》卷六一《毕众敬附毕闻慰传》:“以本军除散骑常侍、东道行台,寻为都督、安乐王鉴军司。”⑧[北齐]魏收:《魏书》卷六一《毕众敬附毕闻慰传》,第1364页。同书卷七七《羊深传》:“正光末,北地人车金雀等帅羌胡反叛,高平贼宿勤明达寇豳夏诸州。北海王颢为都督、行台讨之,以深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行台左丞、军司,仍领郎中。”⑨[北齐]魏收:《魏书》卷七七《羊深传》,第1703页。散骑常侍和通直散骑常侍皆近侍显职,非亲宠之臣勿居。三是监察御史,御史主纠举非违,因职权便利,自汉代起便多任监军,故史书频见“督军御史”之名号。⑩廖伯源:《汉代监军制度试释》,《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第70页。北魏沿袭汉制,《魏书》卷八二《李琰之传》:“孝庄初,太尉元天穆北讨葛荣,以琰之兼御史中尉,为北道军司。”⑪魏收:《魏书》卷八二《李琰之传》,第1797页。北魏倾举国之兵征剿葛荣,故以御史台最高长官督战,以示皇帝的高度重视。正常情况下监军多为各类侍御史。或为侍御史,前引元英征义阳军司邓羡曾任侍御史⑫魏收:《魏书》卷二四《邓渊附邓羡传》,第637页。,毕祖彦“以侍御史为元法僧监军”⑬魏收:《魏书》卷六一《毕众敬附毕祖彦传》,第1365页。。或为治书侍御史,同为元英征义阳军司的薛凤子为治书侍御史⑭魏收:《魏书》卷四二《薛辩附薛凤子传》,第944页。。《魏书》卷四一《源贺附源子恭传》:“领治书侍御史。秦益氐反,诏子恭持节为都督、河间王琛军司以讨之。”①[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一《源贺附源子恭传》,第934~935页。同书卷六一《毕众敬附毕祖朽传》载,治书侍御史毕祖朽,“延昌末,安南王志出讨荆沔,以祖朽为志军司”②[北齐]魏收:《魏书》卷六一《毕众敬附毕祖朽传》,第1362页。。或为殿中侍御史,同书卷七九《鹿悆传》:“庄帝为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御史,监临淮王彧军。”③[北齐]魏收:《魏书》卷七九《鹿悆传》,第1762页。北魏差遣心腹近臣和执宪要员督军,无疑是皇帝牢牢掌控兵权之举措。
北魏使者督军,军使有权调查、奏报军情,便于皇帝及时了解。《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附英传》:“萧衍遣将军寇肥梁,诏英使持节、加散骑常侍,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道诸军事,率众十万讨之,所在皆以便宜从事。……遣步兵校尉、领中书舍人王云指取机要”;元英围攻钟离,“遣主书曹道往观军势,使还,一一具闻。”④[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传附英传》,第499~501页。同时协调前线事务,确保有令必行。《魏书》卷五七《崔挺附崔孝芬传》:“孝昌初,萧衍遣将裴邃等寇淮南。诏行台郦道元、都督河间王琛讨之,停师城父,累月不进。敕孝芬持节资齐库刀,催令赴接,贼退而还。”⑤[北齐]魏收:《魏书》卷五七《崔挺附崔孝芬传》,第1266~1267页。同书卷七七《辛雄传》:“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萧衍遣萧综来据彭城。时遣大都督、安丰王延明督临淮王彧讨之,盘桓不进。乃诏雄副太常少卿元诲为使,给齐库刀,持节、乘驿催军,有违即令斩决。”⑥[北齐]魏收:《魏书》卷七七《辛雄传》,第1694页。这是北魏监军的基本职权,它在皇帝和军队之间搭建了直接沟通的桥梁,增强了皇帝对军事的掌控能力。
必须强调的是,北魏监军使者不只局限于旁观式的监督,更多是以军务帮办的身份全面、深入地参与决策运筹和作战行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加强对局势的掌控。首先,监军可为统帅出谋划策,使之忠实贯彻朝廷的战略方针。《魏书》卷七九《范绍传》:“扬州刺史、任城王澄请征钟离,敕绍诣寿春,共量进止。澄曰:‘须兵十万,往还百日,涡阳、钟离、广陵、庐江,欲数道俱进,但粮仗军资,须朝廷速遣。’绍曰:‘计十万之众,往还百日,须粮百日。顷秋以向末,方欲征召,兵仗可集,恐粮难至。有兵无粮,何以克敌?愿王善思,为社稷深虑。’澄沉思良久曰:‘实如卿言。’使还,具以状闻。”⑦[北齐]魏收:《魏书》卷七九《范绍传》,第1755~1756页。可见,贵为宗王的元澄在钦差面前丝毫不敢专擅,机密事宜均向其通报,由此上达天听。关键时刻,监军摆明态度,足以决定主帅的立场向北。《魏书》卷六六《崔亮附崔光韶传》:“(崔光韶)为东道军司。及元颢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风靡。而刺史、广陵王欣集文武以议所从。欣曰:‘北海、长乐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独抗言曰:‘元颢受制梁国,称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资仇敌,贼臣乱子,旷代少俦,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齿,等荷朝眷,未敢仰从。’长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张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征士张僧皓咸云:‘军司议是。’欣乃斩颢使。”⑧[北齐]魏收:《魏书》卷六六《崔亮附崔光韶传》,第1482~1483页。军使跻身指挥团队,操纵了军队的“大脑”,能够约束各级将佐的言行。
其次,监军可统领兵马,独当一面。《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附嵩传》载,北魏与萧梁鏖战江淮,“衍征虏将军赵草屯于黄口,(扬州刺史)嵩遣军司赵炽等往讨之”①[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附嵩传》,第487页。。同书卷六一《薛安都附薛怀吉传》:“萧衍遣将寇陷郢州之三关,诏英南讨,怀吉仍为军司。以义阳危急,令怀吉驰驿先赴。时豫州城民白早生杀刺史,以悬瓠入萧衍,衍将齐苟仁率众守城,于是自悬瓠以南至于安陆,惟义阳一城而已。怀吉与郢州刺史娄悦督厉将士,且守且战,卒全义阳,与英讨复三关诸戍”②[北齐]魏收:《魏书》卷六一《薛安都附薛怀吉传》,第1358页。。又同书卷七二《贾思伯传》:“任城王澄之围钟离也,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及澄失利,思伯为后殿。澄以思伯儒者,谓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谓虚谈,今于军司见之矣。’”③[北齐]魏收:《魏书》卷七二《贾思伯传》,第1613页。监军领兵带队,既可实时把握战斗过程,又能激励军心士气,是深入控制军队的有效手段。特别是,监军可与前线官佐建立直接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主将的分权和牵制。④[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一《源贺附源延伯传》:“南秦民吴富反叛,诏以河间王琛为都督,延伯叔父子恭为军司。延伯为统军,随子恭西讨,战必先锋。子恭见其年幼,常诃制之而不能禁。”第931页。这反映的不只是叔侄间的亲情,还说明军司有权越过主帅径直问责部众。
再次,监军可以持节,享有最高军事裁判权。前引元英征义阳军司薛凤子,监元颢西北道军事杨昱、羊深,元澄扬州军司贾思伯,元琛秦益讨伐军军司源子恭等皆持节。⑤[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二《薛辩附薛凤子传》,第944页;卷五八《杨播附杨昱传》,第1293页;卷七七《羊深传》,第1703页;卷七二《贾思伯传》,第1613页;卷四一《源贺附源子恭传》,第935页。节符是皇帝赋予全权的信物凭证,持有者如朕亲临,可先斩后奏、便宜行事。其等级、权限见《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⑥[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9页。监军持节,酌情惩治抗命者,震慑力十足,乃提升监察成效的硬性保证。需要注意的是,监军多为次一级的“持节”,最高档次的“使持节”非常罕见。这是因为,征镇主将多加“使持节”,为充分彰显其统帅权威,避免监军越俎代庖,同时也是将其权力限制在军事领域,防止专擅独断,故降级授予。
三、副将对主将的监控
陶新华先生研究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征镇主将的副贰——副将或副军,类似军司担负督军之责。⑦陶新华:《魏晋南朝的军师、军司、军副——军府职官辨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4期;《北朝的军事监察官——监军、军司》,《殷都学刊》2005年第1期。这是个重要启示,引导笔者思考北魏副将的选任和职权机制。实际上,北魏军队数次大规模哗变都是在副将的弹压下被化解,需要找寻其中的制度根源。
北魏副将是由皇帝亲自挑选和任命的。《魏书》卷四三《严稜附严雅玉传》:“真君中,诏雅玉副长安镇将元兰率众一万,迎汉川附化之民,入自斜谷,至甘亭。”⑧[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三《严稜附严雅玉传》,第959页。因其职责重大,故在组织人事上需特别考虑。充任副将者主要有姻戚。史载,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年),东平王道符举兵长安,持异见被杀者就有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真。⑨[北齐]魏收:《魏书》卷六《显祖纪》,第127页。万氏祖出契丹酋豪,与拓跋部累联姻,一门频出驸马,万振尚高阳长公主,万安国尚河南公主。①[北齐]魏收:《魏书》卷三四《万安国传》,第804页。万古真与之同侪,必定忠于皇室,因而遇害。再如安东将军、兖州刺史李崇,“(孝文帝)车驾南征,骠骑大将军、咸阳王禧都督左翼诸军事,诏崇以本官副焉”。李崇之父李诞,乃文成元皇后的次兄,与皇室有姑侄关系。②[北齐]魏收:《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1465~1466页。或以近信侍臣副军,史载,太武帝委任清河大族崔徽为乐安王范副将,与之俱镇长安,崔徽此前历中书侍郎、秘书监,堪称皇帝的文胆。③[北齐]魏收:《魏书》卷二四《崔玄伯附崔徽传》,第624页。《魏书》卷四二《薛辩附薛胤传》:“(太和)十七年,高祖南讨,诏赵郡王干、司空穆亮为西道都将。时干年少,未涉军旅。高祖乃除胤假节、假平南将军,为干副军。”薛胤弱冠释褐中散,外放后以内侍履历还朝供职,深得孝文帝的信赖。④[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二《薛辩附薛胤传》,第943页。又同书卷四七《卢玄附卢渊传》:“(孝文帝)车驾南伐,赵郡王干督关右诸军事,诏加渊使持节、安南将军为副。”卢渊历秘书令、监、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侍从要职,还曾与孝文帝密议立后之事,亲近程度可想而知。⑤[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七《卢玄附卢渊传》,第1047~1049页。北魏皇帝以姻戚、近侍副军,督战的用意不言自明。
为提升副将的督军职权,朝廷为其加挂诸多职衔:一是持节,前引西道副将薛胤“假节”,关右副将卢渊“使持节”。⑥[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二《薛辩附薛胤传》,第943页;卷四七《卢玄附卢渊传》,第1049页。前文已述,持节代表军事裁判权,否则无以震慑属下。二是加集书省散官,前引长安镇副将崔徽加散骑常侍。⑦[北齐]魏收:《魏书》卷二四《崔玄伯附崔徽传》,第624页。散骑常侍统领集书省,《通典》卷二一《职官三·侍中》:“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旧为显职,与侍中通官。……后魏、北齐皆为集书省,掌讽议左右,从容献纳,领诸散骑常侍、侍郎及谏议大夫、给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书之右,其资叙为第三清。”⑧[唐]杜佑:《通典》卷二一《职官三·侍中》,第552~553页。加此职即拥有入直禁中、专折奏事的特权,为副将汇报军情创造了便利条件。三是加将军军号,起到调节职级的作用。前引李崇为安东将军,崔徽为平西将军,薛胤假平南将军,卢渊为安南将军。⑨[北齐]魏收:《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1466页;卷二四《崔玄伯附崔徽传》,第624页;卷四二《薛辩附薛胤传》,第943页;卷四七《卢玄附卢渊传》,第1049页。需要说明的是,副将所加军号俱为五品以上的重号将军,享有开幕府、设僚佐、统外军的资格,无疑增强了干预军队的权力。四是兼领王国属官,北魏承袭西晋惯例,广行宗王出镇⑩刘军:《北魏宗室外镇述论》,《兰州学刊》2009年第4期。,王国官佐通常随之赴任,皇帝以其兼任副将,可在辅助训导之余收监视之效。史载,乐安王范副将崔徽同时“行乐安王傅”⑪魏收:《魏书》卷二四《崔玄伯附崔徽传》,第624页。。以上各类加官并非单独使用,而是多重组合搭配,使副将职权多样化,无形中对统帅形成强大的制衡力。
如此精心安排下,北魏副将对军事指挥层的支配力渐趋巩固。一是决策调度权。史载,咸阳王禧左翼副将李崇统筹全局,“徐州降人郭陆聚党作逆,人多应之,骚扰南北。崇遣高平人卜翼州诈称犯罪,逃亡归陆。陆纳之,以为谋主。数月,冀州斩陆送之,贼徒溃散”①[北齐]魏收:《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1466页。。二是方面统兵权。如前所述,副将加军号,领兵带队自在情理之中。关右副将卢渊,“勒众七万将出子午。寻以萧赜死,停师。是时泾州羌叛,残破城邑,渊以步骑六千众号三万,徐行而进。未经三旬,贼众逃散,降者数万口,唯枭首恶,余悉不问”②[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七《卢玄附卢渊传》,第1049页。。在此情况下,外镇宗王若年幼无知,权力就会被副将架空,更便于皇帝遥控。无怪卢渊名为副贰,实则“制命关右”。不过,副将督军的事例主要集中在平城时代(386至494年),而在洛阳时代(495至534年)近乎绝迹,这估计与行台、监军制度全面启动,且日趋高效,副将督军的职能随之式微有关。
结语
北魏王朝在积极吸纳汉族军制基础上,结合自身丰富的斗争实践,摸索创设了集监军行台、督军使者、副将三位一体,周密细致、成熟稳固的军事监察体制。从根本上讲,这套制度的成型与皇权专制的发展是完全同步的。由上述研究可知,这套制度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各级督察官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与军队始终保持平行利益关系,这种系统外开放式对立监察明显优于系统内封闭式循环监察,从而规避人情世故的无形干扰,保证监察工作的客观公正性。其次,巧妙安排督察官员的人事关系,皇帝尽遣姻戚、心腹近臣或职业监察官,确保对军队的严密控制,严格人事回避制度,杜绝通同作弊的出现。再次,通过加官、兼领等方式完善督察官员的职能角色,同时将其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探寻平衡监察主客体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复次,推动监察权与指挥决策和作战行动的有机融合,实现向监督对象内部的深度渗透,以加强对军队的监控力度。总之,北魏从制度框架到组织人事,构建全方位、多视角的监察平台,不仅维护了拓跋帝国的统治秩序,也为中古兵学文化和制度文明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于北魏军事监察体制实际效能的评估,还可将其同隔江对峙的南朝政权比对获知。江左宗王出镇极其普遍,南朝君主多遣寒人出身的心腹爪牙充任诸王典签(又称签帅),签帅位卑权重,负责照顾诸王的饮食起居,代替长官批阅公文,于是加强典签控制诸王的权力,成为中央控制方镇军队的主要措施③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3页。。即便如此,也未能防止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发生。北朝虽有典签,但主要出现在北齐和北周,北魏罕见其事迹④高敏:《北朝典签制度试探》,《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北魏典签的记载仅一见,《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天赐三年)置散骑郎、猎郎、诸省令史、省事、典签等。”第2974页。疑典签之制空有诏令,并未真正实施。,此乃南北制度差异之一。相比南朝典签的简陋粗糙,北魏督军体系更加完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它避免了南朝过分苛暴的极端化倾向,在维护地方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又给予将领充分施展的空间。因此,当南朝阋墙之争不断时,北魏的将官军佐却能在制度允许的宽松环境下大有作为,不能不说这是北魏在军制层面的创举和贡献。
(责任编辑:仝晰纲)
Research of the Military Surveillance System of the Tabgatch Wei
Liu Jun
The Northern Wei regime founded by the Tabgatch Xianbei tribesmen inherited the governmental system of the Han, Wei, and Jin dynastie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wn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it established the effective military surveillance system comprised of the Military Inspector Office, Military Governor and various kinds of deputy generals. The imperial cour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the important officers responsible for the inspection affairs. Usually, the relatives of the imperial families, the trusted ministers and the governmental officers were selected as the informants. The imperial court also paid attention to the abstention principle of human relationships to ensure that the surveillance actions could be regularly launched. The work of the important surveillance officers was not limited to inspection.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anding and decision-making as well as the warring action. The military surveillance system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followed the development of imperial autocracy. With an improved system, it not only defended the state, but also greatly enriched the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 and governmental system civilization.
K239.21
A
2095-9176(2017)03-0033-010
2017-03-08
刘军,历史学博士,现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专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行国体制研究”(编号14D031)内容。
Kew Words:Tabgatch Wei; Military Surveillance; Inspector in the Army; Centralization of State Power; Military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