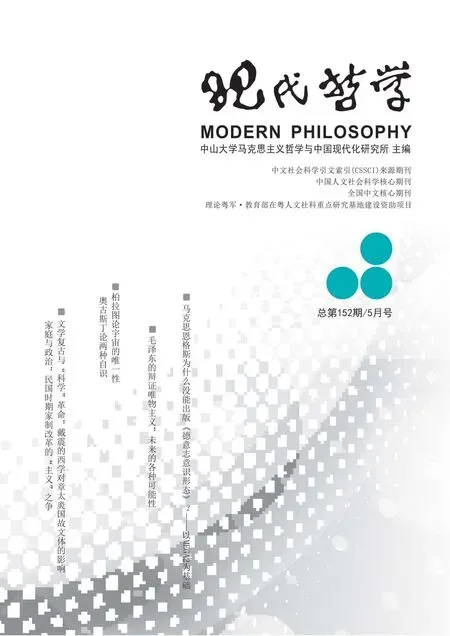启蒙与宗教
——胡适与福泽谕吉*
2017-01-27中岛隆博
[日]中岛隆博
启蒙与宗教
——胡适与福泽谕吉*
[日]中岛隆博
当竹内好倡导“作为方法的亚洲”时,他显示了一种跨-普世性的构想,即普世性不是由西方所赋予的普世性,东方也参与其中,双方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追求更完善的普世性。本文延续竹内的问题意识,通过比较日本和中国来思考启蒙与宗教的问题,分析的人物是分别代表日本和中国之现代启蒙的福泽谕吉和胡适。胡适的启蒙是一种“浅显”的启蒙,它拒绝个体精神深层这一形而上学装置,这缘于胡适是标榜反黑格尔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继承者。福泽谕吉的启蒙也不是西方现代启蒙的复制,而是东亚具有的另一种不同启蒙的可能性,即不诉诸精神层面的实用主义的“浅显”的启蒙。如果不是像福泽那样视儒教为启蒙之敌,而是与西方现代文明一起批判儒教,揭示其可能性的条件,那么日本现代启蒙的形态应能大大改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胡适推动的中国现代启蒙。在今天的东亚思考启蒙,我们必须追问如何批判儒教和整个西方现代启蒙,为此,胡适和福泽谕吉应是必须被超越的人物。
启蒙;宗教;现代性;普世性;儒教
在我国,谈论“启蒙”就是谈论福泽谕吉,这么说并不为过。
——丸山真男*[日]丸山真男:《福泽的“实学”转向:福泽谕吉的哲学研究序论》,[日]丸山真男、松泽弘阳编:《福泽谕吉的哲学》,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第34页。
引 言
当竹内好倡导“作为方法的亚洲”(1961年)时,曾这样阐述普世性的含义:
为了更广泛地实现西欧优秀的文化价值,我们应该再度用东洋文化来涵括西洋,也就是从我们这一方反过来变革西洋本身,通过这一文化的反击,或者说价值上的反击,来创造出普世性。以东洋的力量来变革西洋,是为了提高西洋创造的普世性价值,这成为我们今天东西方相对的问题点。这既是政治上的问题,同时也是文化上的问题。日本也必须具备这样的构想。*[日]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竹内好全集》第5卷,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第114—115页。
这里的普世显示了一种跨-普世性(trans-universality)的构想,即普世性不是由西方所赋予的普世性,东方也参与其中,双方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追求更完善的普世性。
彼时竹内心目中的具体人物是约翰·杜威。竹内强调,杜威看到五四运动时说:“日本表面上看起来先进,但却是脆弱的,不知何时会崩溃。中国的现代化是非常内发型的,即缘于自身的要求而产生出来,所以是坚固的。”*[日]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前揭书,第100页。而且竹内声称:“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必须将日本和中国进一步加以比较。”*[日]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前揭书,第100页。
在此,我将延续竹内的问题意识,通过比较日本和中国,来思考启蒙与宗教的问题。而我想分析的人物,是分别代表日本和中国之现代启蒙的福泽谕吉和胡适。
一、启蒙与“自主的个体”
今天思考启蒙有什么意义呢?时常有人提到,尽管启蒙思想是普遍的现象,但启蒙精神却是18世纪欧洲固有的运动,比如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Todorov)声言:
启蒙思想是普世的,即使我们并不能总是和到处观察到它:这正是我们不得不首先注意的东西。这不仅涉及到以启蒙思想为前提的做法,而且也涉及到一种理论觉悟。我们在印度公元前3世纪之后给皇帝的告诫或在皇帝颁布的法令中就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我们在8世纪到10世纪伊斯兰教的“自由思想家”那里,或在中国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宋朝儒学复兴时期,或在公元17世纪和18世纪初黑非洲反奴隶制运动中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中略)
这各式各样的发展证明启蒙思想的普遍性,根本不是欧洲独有的特权。然而,这种运动确实是在18世纪的欧洲加速发展和巩固起来,在那里形成了随后在所有大陆传播开去的思想轮廓:首先在北美,然后在欧洲本土、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我们不会忽略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在欧洲而非别处,比如中国?我们并不想解决这个难题(历史的变动是一些无限复杂的现象,有着多重甚至矛盾的原因),但我们会指出存在于欧洲而别处没有的特征:这就是政治自主、人民自主和个体自主。此处,这个自主的个体在社会内部而非外部找到一个位置(正如这可能就是印度的“弃绝者”、伊斯兰教土地上神秘主义者和中国僧人的情况)。欧洲启蒙运动的特性,就是为个体、民主这些的联合出现作出铺垫。*ツヴェタン·トドロフ:《啓蒙の精神 明日への遺産》,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8年,第111—114页。[法]茨维坦·托多洛夫:《启蒙的精神一份给明天的遗产》,马利红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2年,第141—145页。
此处作为欧洲启蒙主义的特性提出的是“自主的个体”这一概念,被视为现代启蒙的特征,这种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在考察东亚的现代启蒙时也反复出现。比如,下文将谈到的福泽谕吉提倡“独立自尊”,而其后“自主的个体”在日本如何强迫性地发挥作用,已无须赘言。在中国,胡适也在其“健全的个人主义”上再三强调“特立独行”。*胡适:《介绍我的思想》(1930年),欧阳哲生编:《胡适全集》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63页。
那么,今天重新讨论“自主的个体”就是思考启蒙吗?诚然,今天我们仍旧生活在欧洲现代的启蒙精神之中,但是欧洲现代启蒙精神不能简缩为“自主的个体”这一理念。我们需要通过将欧洲启蒙精神历史化并进一步加以解构,创造出能够批判“自主的个体”这一陈词滥调的新启蒙。因为在“自主的个体”这一理念中纠缠着一种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通过认定某一特定的个体或集团没有达到自主而迫使其服从。这在东亚的启蒙中尤为明显。面对近代欧洲,19世纪和20世纪的东亚在被迫意识到自己尚未完全自主的同时,又在自己内部区分出更加自主的部分和更加不自主的部分,并意图使后者服从于前者。准此,则今天在东亚探讨启蒙,就必须对这种权力关系保持警惕。
二、启蒙、宗教、儒教
关于启蒙,康德依然是绕不过去的思想家,因为康德把“自主的个体”作为启蒙的出口。在《何谓启蒙》的开篇伊始,康德如是说: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カント:《啓蒙とは何か》,东京:岩波书店,1950年,第7页;[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
康德设想的启蒙后的成熟状态,就是人自由地“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状态*カント:《啓蒙とは何か》,第10页;[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第24页。;反之,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不去思考,而让他人代替自己思考的安逸状态。但是,康德用“不成熟”一词来表达的启蒙的对立面是什么呢?那就是宗教。
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カント:《啓蒙とは何か》,第18页;[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第29页。
为什么是宗教?康德说:宗教中的“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カント:《啓蒙とは何か》,第18页;[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第29页。。那么,对宗教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康德说: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充分自由、甚至于有责任,把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カント:《啓蒙とは何か》,第12页;[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第25页。
这是康德所谓“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典型例子。亦即是说,如果以前的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カント:《啓蒙とは何か》,第10页;[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第24页。,那么启蒙后的神甫则说“任意争辩,但是必须信仰!”
无疑,这样将理性引入宗教的某些部分的做法,形成了欧洲近代的世俗化过程。而且,正如约翰·波考克(J.G.A.Pocock)在《野蛮与宗教》中指出的,其背后是与中国思想的剧烈碰撞。也就是说,在无神却能够构成世界这一点上,中国相对于基督教欧洲而言,已经表现出脱离宗教的成熟状态*波考克提及碑文与美文学院的成员兼主管尼古拉·弗雷列(Nicolas Fréret),论述了那个时代欧洲的教养érudition 因为与中国尤其是儒教相遇而发生的变化(J.G.A.Pocock,Barbarianism and Religion, pp.152-168)。比如他说:“对于皮埃尔·白伊鲁提出的无神论的社会如何能够成为道德的社会这一问题,弗雷列说,至少对于某些儒教徒而言,那些遵循道德律的仪礼并将之付诸实践的有德之士发现了同时建构道德和物质性存在的‘理’。有德之士由此而得以凝缩、纯化和完成,甚至可以达到不死。在其显而易见的死(其本身也许是幻想)后,这些人仍然作为有德之士而受到人们的景仰。”(Ibid, p.167)。
堀池信夫有关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论述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前面已经提到,狄德罗的哲学立场不同于龙华民(Nicolò Longobardi),在1753年撰写《中国哲学》时,狄德罗就已经从理神论转向自然宗教式的观念,其自然宗教的内涵几乎接近无神论。而且他在龙华民传达的中国哲学中看到了他所抱持的理念得以实现的一种形态。中国哲学中没有如基督教中的神那种超越性的唯一存在,但社会秩序井然。中国证明,即使没有神,也可以实现有秩序的世界。狄德罗构想无神之世界的启蒙立场因之得以强化,而不会出现相反的影响。*[日]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家》下,东京:明治书院,2002年,第497页。
由此可知,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未必是欧洲内生的运动。托多洛夫认为,正是因为与中国而且是单一支配的中国相比,欧洲所具有“多样性”,才使启蒙精神能够在欧洲得以发展*[法]茨维坦·托多罗夫:《启蒙的精神留给明天的遗产》,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8年,第114—121页。。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中国这一外部,而且是无神的启蒙之楷模的中国,那么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不可能出现的*关于中国这一楷模,托多罗夫也没有忘记,中国的儒教教育对18世纪欧洲哲学影响巨大。参前揭书,第113页。。
三、理性的不安
倘若如此,现代欧洲启蒙精神岂不是通过抹去中国这一使之成为可能的条件,而扮装成普遍性的样子吗?然而,“理性的不安”始终挥之不去。雅克·德里达说:
理性(逻各斯或者ratio)首先是地中海的产物吗?它已抵达了雅典和罗马的良港并停留到它在海岸边的时间的结束吗?它从不起锚或漂流吗?它决不以决定性的方式或关键的方式很快地切断与它的出生地、地理和谱系的联系吗?*ジャック·デリダ:《ならず者たち》,东京:みすず书房,2009年,第227—228页;[法]德里达:《无赖》,汪堂家、李之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
德里达在这里并未言及中国,但是对德里达而言,理性不是植根于某一特定的大地,而是在世界的海洋中航行,中国并没有事先被排除在外。附带指出,借用米歇尔·福柯的说法,德里达在此处对理性进行了批判。因为福柯解读康德的《何谓启蒙》时说:“所谓‘批判’,可以说就是在启蒙中变得成熟的‘理性’的航海日记。”*[法]米歇尔·福柯:《何谓启蒙》,《福柯精选6 实际政治、统治》,东京:筑摩书房,2006年,第373页。但是理性的航程充满危险,不断面临触礁和登陆的危机*ジャック·デリダ:《ならず者たち》,第231—232页;[法]德里达:《无赖》,汪堂家、李之喆译,第163页。,那么如何才能“拯救理性的荣誉”呢?德里达求助于翻译:
翻译承担了理性的一切命运,亦即未来的世界普遍性。*ジャック·デリダ:《ならず者たち》,第227页;[法]德里达:《无赖》,汪堂家、李之喆译,第160页。
为了拯救理性的荣誉,我们需要知道如何翻译。例如翻译“合理的”这个词。知道如何在多种语言中尊重“理性的(rationnel)”与“合理的”〔raisonnable〕之间的细微差别而又超越尊重(saluer)一词的拉丁性。*ジャック·デリダ:《ならず者たち》,第302页;[法]德里达:《无赖》,汪堂家、李之喆译,第214页。
理性吁求翻译,通过翻译成其他语言而挽救它的荣誉。这不仅是说reason、raison、Vernunft是拉丁语ratio或希腊语logos的翻译,亦是说这些词也与其他的谱系,比如拉丁语的intellectus或希腊语的nous的翻译,甚至与“理性”或者汉语的“理”相关联。引导启蒙的理性,就这样通过翻译,面对自身的复数性。而且即使中国的名字被隐去,中国对于这一理性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胡适的启蒙与宗教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现代的启蒙。中国现代启蒙的代表人物胡适(1891—1962)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在中国复制欧洲现代的启蒙。既然如此,胡适就应该从启蒙的立场出发,对宗教采取严厉的态度。实际上,胡适对中国宗教的态度确实如此。胡适的自传云:
这座小圣庙,因为我母亲的加意保存,到我二十七岁从外国回家时,还不曾损坏。但我的宗教虔诚却早已摧毁破坏了。我在十一二岁时便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第1集,第59—60页。
胡适自称十一二岁时就已经是无神论者了。胡适举出的原因是,早早见背的作为儒者的父亲的影响,以及在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读到的儒者范缜神灭论的影响*胡适:《四十自述》,前揭书,第57—62页。。亦即是说,使胡适的自我启蒙成为可能的条件中,包括作为启蒙话语的儒教。
那么,声称“我们的思想经过解放之后,就不再虔诚地拜神佛了”*胡适:《四十自述》,前揭书,第62页。的无神论者胡适,是如何具体地批判宗教的呢?根据赵娜整理的“胡适的宗教思想论”,胡适认为在中国可以称为宗教的是佛教和道教,他批评二教“欺人”“有害无益”*胡适:《〈老残游记〉序》(1925年),《胡适全集》第3卷,第583页;胡适:《胡适口述自传》(1950年代录音),《胡适文集》第1集,第416页。。作为来自启蒙旗手的宗教批判,这自然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胡适对封建体制化的儒教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众所周知,吴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烈批判儒教,胡适对此表示了由衷的支持,盛赞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胡适:《〈吴虞文录〉序》(1921年),《胡适全集》第1卷,第763页。。在这一赞誉之前,胡适写道:
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胡适:《〈吴虞文录〉序》(1921年),前揭书,第763页。
显然,年轻的胡适与吴虞以及陈独秀都对儒教抱持着批判的态度。但是,既然儒教是使胡适的启蒙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那么他对儒教的批判与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自然有所不同,因为胡适通过对基督教的比附而又重新肯定了儒教。
五、儒教的重新肯定与“浅显”启蒙
胡适将儒教作为宗教重新加以肯定的著作是《说儒》。这篇论文将儒教解释为被周朝征服的殷朝的宗教,并将之与犹太教相比较,认为老子是守护传统儒教的儒者,而把孔子界定为与耶稣基督一样,是改革的弥赛亚*胡适:《说儒》(1934年),《胡适全集》第4卷,第42、56、82页。。
那么,作为“弥赛亚”的孔子是如何改革宗教的呢?胡适云:
“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就是把整个人类看作自己的责任。耶稣在山上,看见民众纷纷到来,他很感动,说道:“收成是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马太福音》第9章第37节〕曾子说的“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正是同样的感慨。
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就是孔子的新儒教。*胡适:《说儒》(1934年),前揭书,第62—63页。
这就都是超过那柔顺的儒风,建立那刚毅威严,特立独行〔《礼记·儒行》〕的新儒行了*胡适:《说儒》(1934年),前揭书,第73页。。
此处昭示的是基于个体的自主与平等,而对全人类承担责任的新儒教。这正是欧洲现代的“新宗教”,它通过实现“社会化”,扩大对他者的想象力和同情心,并作为“新道德”呈现出来。
如此一来,胡适把孔子的“新儒教”诠释为启蒙后的“新宗教”,于是儒教不再是“打倒孔家店”的对象了。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中,以“并不要打倒孔家店”为题,强调自己决非反儒*胡适:《胡适口述自传》(1950年代录音),《胡适文集》第1集,第418页。。但是,这是否可以说启蒙的旗手胡适被儒教收编了呢?
从上述的情况看,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诚然胡适的启蒙本来就没有彻底批判基督教,反而拥护宗教的社会化形式,亦即道德。在此意义上,不得不说胡适的启蒙原本就是不彻底的。这也是东亚启蒙的陷阱,因为既然以欧洲的现代为榜样,那么东亚的启蒙就必须是以欧洲现代启蒙为条件。尽管如此,胡适重新界定儒教,在无意之中恢复了使欧洲现代启蒙成为可能的(被遮蔽了的)儒教这一条件,这也可以说,胡适的启蒙是以不同的方式对欧洲现代启蒙的重复。
那么,胡适的启蒙与欧洲现代启蒙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那就是胡适的启蒙是一种“浅显”的启蒙,它拒绝个体精神深层这一形而上学装置。这缘于胡适是标榜反黑格尔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继承者。实用主义祛除了深邃渺远的神这一终极目的(telos),力求平直地说明这一世界的应有状态。这一学术方式贯穿于胡适的启蒙之中:
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这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二十五年来,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民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第1集,第80页。。
这就是主张“浅显”的胡适。但是,这是东亚的现代具有的、另一种别样的启蒙的可能性,即不诉诸精神深度的实用主义的启蒙形态。
当然,儒教能否像胡适希望的那样,作为道德化、社会化的“新宗教”而发挥作用,谁也无法保证。因为与胡适主张的相反,儒教独自探究精神深层并将之道德化的同时,也为实践的层面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是从东亚的角度倡导能够批判欧洲现代的新启蒙。那么,重新回顾胡适之启蒙的意义,对批判性地超越欧洲现代而言,便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六、福泽谕吉与儒教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日本现代的启蒙。据丸山真男之见,日本启蒙的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因为福泽成功地复制了西方现代的启蒙。比如对于本文开头言及的托多罗夫所谓的“自主的个体”或者康德意义上的成熟,福泽这样说:
况且贫富强弱并非天定,而决定于人的努力与否。今天的愚人可以在明天变成智者,从前富强之国可以在现在沦于贫弱,古今这种例子是不少的。如果我们日本人从此立志求学,充实力量,先谋个人的独立,再求一国的富强,则西洋人的势力又何足惧?只须与讲理者建交,对不讲理者则驱除之。这就是个人独立和一国独立的道理。*[日]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第32—33页;[日]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9页。
所谓独立,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例如自己能够辨明事理,处置得宜,就是不依赖他人智慧的独立;又如能够靠自己身心的操劳维持个人生活者,就是不依赖他人钱财的独立。*[日]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ゝめ》,第33页;[日]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第19—20页。
所谓“对不讲理者则驱除之”,表明福泽彻底地排斥被认为是不理性的事物,这一点意味深长。
那么,对于福泽的启蒙而言,敌人是什么呢?在康德那里,敌人是基督教,而福泽选出的与基督教相类似的,则是儒教。让我们看看《福泽谕吉自传》中的叙述:
我明明通晓经史之义,偏装作不知,我往往不客气地攻击汉学者的弱点,可说是个叛教者。站在汉学的立场,我是个旁门左道。
我之所以将汉学视为敌人,那是因为我深信,在今日开国之际,若是陈腐的汉学占据了少年的脑了,则日本无法进入西方文明之国的行列。因此,我要尽最大的力量拯救他们,将他们引导至我所信仰的原则。我的态度是,全日本的汉学者尽管攻击我,由我一个人来抵挡他们。*[日]福沢諭吉:《福翁自伝》,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第208页;[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杨永良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年,第246页。
福泽的启蒙是面对年轻人进行教育,使受汉学毒害的年轻人脱离未成熟状态,接受西方文明,成长为独立的成年。丸山真男这样评述福泽的启蒙以儒教为敌的态度:
从幕末到明治初期最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通过其“洋学”,一方面把欧洲的市民文明移植并普及于日本,作为建设新日本的材料,另一方面又要打破深深扎根于国民思想中的封建意识。而当他竭尽全力做这两件事时,他认为挡在他面前的最强韧的障碍,就是儒教思想。*[日]丸山真男:《福泽谕吉的儒教批判》(1942年),[日]丸山真男:《福泽谕吉的哲学外六篇》,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第7页。
为何是儒教呢?如果要原封不动地复制西方现代的启蒙,不是应该针对渗透在日本人生活之中的宗教,即神道和佛教吗?福泽认可的日本宗教也是神道和佛教,而非儒教。那么究竟为什么要以儒教为敌呢?
七、福泽谕吉之启蒙的结构
在此需要明确一下福泽对宗教的态度。福泽是在西方现代意义上理解宗教的,亦即精神信仰。在日本,这种意义上的宗教只有佛教,然而佛教已被政治吸收,毫无势力可言。福泽描述为:“日本全国根本就没有宗教。”*[日]福沢諭吉:《文明論之概略》,第223—226页;[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982年,164—167页。那么掌握日本人心灵的是儒教吗?但是正如丸山真男指出的,日本并未广泛接受儒教*[日]丸山真男:《福泽谕吉的儒教批判》(1942年),前揭书,第7页。。那么何以福泽要将儒教定为启蒙之敌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虑以下两点:一是福泽之启蒙的独特结构,二是福泽之启蒙的政治意义。
首先看第一点。读福泽的自传,感觉福泽自己从未被启蒙,因为福泽被描绘成从少年时代就已经不需要启蒙的成年。其中没有被启蒙的历史,找不到精神纠结的故事。佐伯彰一说福泽没有“精神自我”:
福泽真是精力充沛而又挥洒自如的写手,他一本又一本地写出大量著作,愉快之极,几乎是天生的笔杆子,但是他从来没有为自我表达的问题而烦恼。他与那种欲将喷涌而出或者等不到沉淀下来的机会而始终剧烈躁动的精神自我毫不相干。*[日]佐伯彰一:《日本人的自传》,东京:讲谈社,1974年,第95页。
取而代之的是对身体的过度凝视和用“可笑”一词所象征的距离感*[日]福沢諭吉:《福翁自伝》,第64、311—313、302—303页。。考虑到福泽跟随绪方洪庵学医的经历,他对身体的执着或许可说是理所当然的。但他只是滔滔不绝地讨论身体如何摄生,而“精神自我”却几乎从未出现。如果要举出福泽的“精神自我”,那就是对自己的行为保持距离、并且觉得很“可笑”的那个自我。
显然,福泽的启蒙具有实用主义的功能性和嬉戏的特征,用以对抗精神的深刻性。丸山真男所揭示的福泽哲学正是这一点:
如果要寻找最接近福泽之思维方式的西方哲学,那首先就是实用主义。他主张所有认识都由实践目标(“议论的主体”)所规定,宣称“不是物可贵,而是它的作用可贵”,认为事物的价值并非是内在于事物的特性,而始终是根据事物对具体环境的功能来决定事物的价值,这样的观点不正是实用主义吗?*[日]丸山真男:《福泽谕吉的哲学》(1947年),[日]丸山真男:《福泽谕吉的哲学外六篇》,第82页。
我们看到,福泽的主要命题都是根据条件而得出的认识,亦即应该加上括弧来理解的。由此可知,他思考的特质就是不断变换的视角。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生即游戏这一命题是他所加的最大的括弧。*[日]丸山真男:《福泽谕吉的哲学》(1947年),前揭书,第112页。
在这一点上,福泽的启蒙不是西方现代启蒙的复制,而是东亚具有的另一种不同的启蒙的可能性,即不诉诸精神层面的实用主义的“浅显”的启蒙。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福泽和胡适的启蒙结构大致相同。
职是之故,福泽必须以儒教为启蒙之敌。因为儒教对精神深层有着独特的探讨,并将之道德化的同时,也为实践层面奠定了基础。换言之,儒教拥有的启蒙力量如果在近代日本得以发挥的话,那么福泽所期望的欧洲启蒙的“浅显”之处就很可能被抹消掉。
八、排除儒教的政治意义
福泽视儒教为启蒙之敌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福泽的启蒙具有政治意义,即通过排除儒教而排除中国乃至东亚。《福泽谕吉自传》中表现出对中国难以掩饰的轻蔑:
纵观今日中国的情势,我认为只要满清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就无法迈向文明开化的大道。换言之,必须彻底推翻这个老朽的政府,重新建立新的国家,人心才能焕然一新。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将满清政府推翻之后,中国是否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么成功,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满清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或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日]福沢諭吉:《福翁自伝》,第262—263页;[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杨永良译,第308页。
在福泽看来,当时中国和朝鲜在政治上的腐朽完全是由儒教造成的。要脱离儒教达到“文化开化”,就应该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楷模。
丸山真男将福泽的态度概括如下:
对攘夷主义乃至排外主义的思潮,谕吉都始终如一地坚持抗争,而对于朝鲜及支那的外交问题,他却始终都是最强硬的推进论者。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表面上看来矛盾的态度能够在他内心形成一个统一的志向,正是反儒教意识起到连接的作用。(中略)
谕吉曾经在《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中对过去的日本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批判被原封不动地复制到支那身上。对于朝鲜的改革,他也认为“朝鲜的改革就是排除支那儒教的弊风,不断推进文明开化”,因而激励“改革的当局者下定决心坚持不懈,改革不仅是为了彼我两国,也是为了履行天职,推广世界共通的文明主义”。对于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他始终代表着舆论中最强硬的一方,主张攻到北京,决不罢兵,宣称“这次战争说是中日两国之争,实际上是文明对野蛮、光明对黑暗的战争,其胜负如何,关系到推进文明的气运”。可以说,甲午战争以最明确的形式证明了谕吉的独立自主与国权主义之结合是以反儒教主义为媒介的。*[日]丸山真男:《福泽谕吉的哲学》(1947年),前揭书,第30—33页。
丸山尖锐地揭示出,福泽的“反儒教主义”态度直接扩展到中国与朝鲜的政治改革乃至甲午战争。换言之,福泽的启蒙的政治意义就在于,通过以儒教为敌,从一开始就把整个东亚都纳入范围,而不仅仅是日本,因而福泽的启蒙原本不外乎就是“脱亚”。
结 语
正如丸山真男所说,福泽就是日本现代启蒙的化身。如果是这样,那么引导这一启蒙的理性最终通过暴力登上了中国和韩国的海岸。然而,这一理性不也可以开启不同的航程吗?因为其中包含着与欧洲现代不同的启蒙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像福泽那样视儒教为启蒙之敌,而是与西方现代文明一起批判儒教,揭示其可能性的条件,那么日本现代启蒙的形态应该能够大大改观。而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胡适推动的中国现代启蒙。
在今天的东亚思考启蒙,我们必须追问如何批判儒教和整个西方现代启蒙,为此,福泽谕吉应该是一个必须被超越的人物。
(责任编辑 杨海文)
B261
A
1000-7660(2017)03-0124-08
中岛隆博,(东京 113-8654)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西学东渐与广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三大建设”专项资助
*本文是2016年12月6日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所做演讲“启蒙与宗教:胡适与福泽谕吉”的基础上撰写的。
译者简介:乔志航 ,北京人,文学博士, (东京 113-8657)日本东京大学兼职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