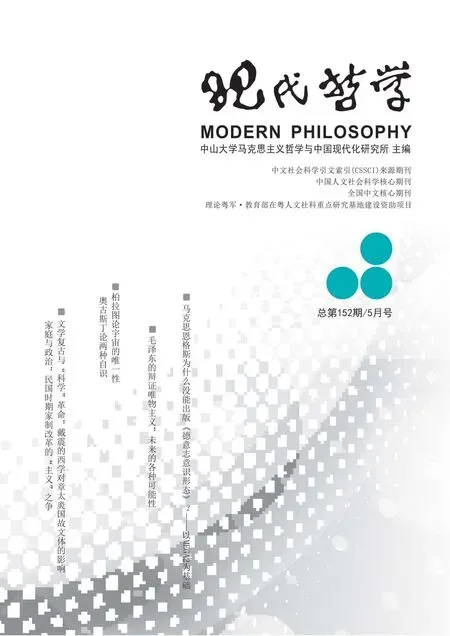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中的马克思
2017-08-01杨栋
杨 栋
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中的马克思
杨 栋
“海德格尔与马克思”这一论题的深入离不开对一些基础问题的解答。作为这样一个基础问题,马克思本人在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中扮演何种角色,值得深入探讨。基于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手稿”,从其思想道路的发展出发,结合具体文本来分析马克思在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中扮演的角色,不但有助于厘清马克思在海德格尔思想发展中的作用,明确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相关评判的出场背景,更有助于把握对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哲学关联进行研究的基础、可能性和前进的方向。
马克思;海德格尔;存在历史手稿;存在历史思想

以上两个特征的效果历史规定着今时今日我们在“海德格尔与马克思”这一论题下开展研究的基本处境,对这种处境的自觉乃是我们从事相关研究的出发点。这种自觉激发笔者在此提出并试图探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本人在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或者说“海德格尔的马克思”是怎样的?
海德格尔全集的持续出版,使我们较之前人更有机会通过文本洞悉海德格尔思想的全貌。本文试图基于这种洞悉对“海德格尔的马克思”进行探察:首先,笔者将论述海德格尔“存在历史手稿”的价值,以及这些手稿所展现的内容对厘定海德格尔思想道路全貌的作用及相应成果;其次,基于相应成果,从思想和文本两个角度分析“海德格尔的马克思”;最后,得出相应的结论和启示。
一、“存在历史手稿”与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
近三十年中出版面世的最为重要的海德格尔全集文本是第65卷《哲学论稿(从事发而来)》(BeiträgezurPhilosophie(VomEreignis))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随后几卷手稿。海德格尔晚年的私人助手、海德格尔全集的主要编辑出版者弗里德里希-维尔海姆·冯·海尔曼(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将这一文本群称之为“存在历史手稿”,包含全集第65、66、67、69、70、71、72卷。*目前只有第72卷《开端之径》(Die Stege des Anfangs)尚未出版。虽然这一提法并不能涵括相关时期(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后期)海德格尔所有的重要文本*例如,这些文本还应该包含:同时期的其他手稿,如全集第73、74卷等;同时期的讲课稿,如全集第45卷;以及相关的研讨班课程记录,如第85卷等。,但基本给出了这一时期最为核心的文本。一方面,通过这些文本,海德格尔“转向”期的思想,即历来因缺乏直接文本证据而最富有争议的思想部分,得以展现给研究者;另一方面,出于这些文本纷繁复杂的手稿特征,使得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对于其价值和作用产生争论,乃至对这一时期海德格尔思想本身的价值和作用产生争论。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近三十年来海德格尔思想研究最基本的理论背景。首先,这种背景本身时常凸显为新的研究主题,如历史(Geschichte)概念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位置、语言(Sprache)主题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出场方式、以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运作方式(Verfahrensweise)或曰方法(Methode)等。其次,这种背景提供的更为宽广的视域促使研究者回顾、检讨过往的一些研究,如海德格尔思想“转向”(Kehre)之实质是什么、存在问题(Seinsfrage)在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中的位置等。最后,这种背景为再后来出版的文本所引发的讨论提供最基本的理论背景。例如,自2015年开始出版的“黑皮本”(Schwarze Hefte)所引发的新一轮关于海德格尔政治立场的探讨,其理论根基正是“存在历史手稿”所展现的海德格尔同时期的哲学思想。
总体来说,“存在历史手稿”展现出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思想(seinsgeschichtliches Denken)。就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发展而论,这种思想形态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首先,在思想的核心问题上,“承上”是指承袭和发展了《存在与时间》提出的存在问题。这表现在海德格尔进一步将存在问题表述为哲学的基本问题(Grundfrage),区别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Leitfrage)。主导问题将存在作为存在者进行追问、或者追问存在者之存在,从本质上是对存在者的追问(die Frage nach dem Seienden),进一步而言就是对存在者之存在者状态(Seiendheit)即在场状态(Anwesenheit)的追问。而基本问题追问的是存在本身(Sein als solches),并不追问存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问题具有主导问题和基本问题的双重属性,因而是一个过渡问题。这种双重属性可以从对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分析中得以说明。《存在与时间》中,存在问题的被问者(Gefragtes)虽然是存在,但被问询者(Befragtes)是作为此在(Dasein)的存在者,即个体的人,而通过分析此在的生存现象所展现的,即存在问题的被问得者(Erfragtes),是存在的意义(Sinn von Sein)。由此可以看出,《存在与时间》中的作为存在意义问题的存在问题,虽然朝向了存在本身,却不得不通过问询人类这一存在者的存在实现。较之于此,存在历史思想对于存在问题的处理更为彻底。被问者虽然依然保持为存在,但被问询者是此之在或曰此-在(Da-sein),指的是存在本身与人发生交互关联的那一个区域,存在在此区域开显自身,因而此之在根本不同于此在,不是从存在方面对人这种存在者的命名,所以存在历史思想的直接研究对象就不是作为存在者的人,而是存在向人自我显示(sich zeigen)的那个领域。诚然,人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努力进入其中,但其并非天然地占据这个位置,相应地,这时存在问题的被问得者就不是通过人之存在而展开的存在的意义,而是存在本身的展开,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的真理(die Wahrheit des Seins)。
其次,“承上”是指存在历史思想将历史本身或曰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提升为思想的根本视域。由此表现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发展中的视域转换。虽然时间概念在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中出场较早*参见M. Heidegger, “Der Zeitbegriff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16)”, in Frühe Schriften, GA 1, Frankfurt a. M. 1978, S. 413-433.,但直至1923年,时间都未成为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视域,同时期实际作为视域发挥作用的是作为“生命理解之工具论”(Organon des Lebensverstehens)*M. Heidegger,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1919/20), GA 58, Frankfurt a. M. 1993, S. 256.或“过程”(Prozess)的存在者层次上的(ontisch)历史。海德格尔在1924年写作《存在与时间》的初稿《时间概念》时,才触及这种存在者层次上的历史的生存论-存在论(existenzial-ontologisch)意义,将之表述为人类此在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参见M. Heidegger, Der Begriff der Zeit, GA 64, Frankfurt a. M. 2004, S. 132f.基于此,在同样作于1924年的同名报告《时间概念》*参见M. Heidegger, “Der Begriff der Zeit (Vortrag 1924)”, in GA 64, Frankfurt a. M. 2004, S. 105-125.中,海德格尔明确提出朝向时间的发问,并指出唯有通过对人类此在的观察方能得出相关的答案。他说:“此在始终以一种他可能的时间存在[Zeitlichsein]的方式存在。此在是时间,[因为]时间是时间性的[zeitlich]。此在不是时间,而是时间性[Zeitlichkeit]。”*Ibid., S. 123.进一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明确指出:“时间必须被明确为所有存在理解和一切存在解释的视域,且被予以真实地把握。为了明确这点,需要从作为理解存在着的此在之存在的时间性出发,源始地展示作为存在理解之视域的时间。”*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192006, S. 17. 中译文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三联出版社,1987年,第23页。在此语境中,历史被把握为奠基于此在之时间性上的存在者层次的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与此相对,在“存在历史手稿”的语境中,“历史在此并不[被]把握为一个与他者并立的存在者领域,而是唯独着眼于存在[Seyn]自身的本现[Wesung]”*M.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A 65, Frankfurt a. M. 32003, S. 32. 中译文参见[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6页。。作为“如此存在(Was-sein)和如何存在(Wie-sein)之更为源始的统一”*M. Heidegger, Grundfragen der Philosophie. Ausgewählte “Probleme” der “Logik”, GA 45, Frankfurt a. M. 21992, S. 202.的存在之本现被海德格尔称之为事发(Ereignis)。因而就有“事发是源始的历史本身,由此或可表明,存在的本质现身[Wesen]在此一般被作‘历史地’把握”*GA 65, S. 32. 参见中文版第37页。。如此这般被把握的历史,即存在历史,自此成为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视域。
最后,相当程度上,“承上”是指存在历史思想在方法上承袭了海德格尔早年(1919年)的现象学“突破”*参见T. Kisiel, “Das Kriegsnotsemester 1919: Heideggers Durchbruch zur hermeneutischen Phänomenologie”, in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99), 1992.。概言之,这表现在将研究对象把握为自我显示着的现象,对这种现象作内容(Gehalt)、关联(Bezug)和实行(Vollzug)意义上的结构分析,并分析相应的经验方式。*参见M.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GA 60, Frankfurt a. M. 1995, S. 63. 中文本参见[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孙周兴编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2页。这种方法特征在1924年的作为《存在与时间》初稿的《时间概念》中有着明显的表现。具体到“存在历史手稿”中的方法进路,思想的对象依然是作为自我显示着的现象的存在。这一现象的基本内容是真理,是事发性的(ereignishaft)。依据存在自身发生(sich ereignen)的方式不同,真理显示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可以是开端(Anfang)、历史、此之在等。关联于真理的基本方式是思想(Denken),它区别于传统,不将真理作对象性地(vergegenständlich)把握,而是对真理作顺应着的占用(fügende Verfügung),这种占用也是对通向真理之路的开辟和占用,这种道路是尝试性的、歧路丛生的,因而是复数的,即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林中路(Holzwege)。这种思想正是狭义上的“存在历史思想”。与之相对,广义上的“存在历史思想”则是对存在问题作存在历史式回答的道说活动(Sagen),存在真理现象的实行意义便通过这种活动得以实现。简言之,通过道说活动,存在真理被带入语言。这种语言的基本形式是词语(Wort)和道说(Sage),前者不同于传统哲学意义上作为范畴的纯粹概念,后者则不同于作为命题的陈述。在道说中实现的是这样一种关于存在之真理的经验:存在作为语言现象自我发送出来。由此,语言主题在存在历史思想的完成形式中出场。
正是在语言主题上,存在历史思想表现出在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上最显著的“启后”特征。1947年面世的重要文本《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以下简称《书信》)展现出一种具有不同风格和主题的海德格尔思想,这主要是指与前期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思想的不同,这种不同同时突出表现在海德格尔对语言主题的论述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66页。,这个著名的论断被广为引用和讨论。显而易见的是,在《存在与时间》中语言论题处于一个相当次要的位置,而此时语言却跃升为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主题之一。由于“存在历史手稿”在海德格尔生前并未出版,所以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早期的海德格尔思想其时并不被绝大多数研究者了解,所以《书信》在思想上的出场背景被遮蔽了,因而其所反映出的差异被放大,从而促成了研究者论域中所谓的海德格尔的“转向问题”;进一步,由于语言论题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的“突兀”,造成研究者们将转向问题与语言问题深度勾连在一起*约翰·塞利斯(John Sallis)的相关论述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语言是转向的恰当位置”“语言和转向互属”。参见J. Sallis, “Language and reversal”, in Macam, Chr. (Hrsg.), Martin Heidegger,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ume Ⅲ: Language, London 1992, pp.190-211.。实际上,通过对“存在历史手稿”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从思想形态上而论的海德格尔的“转向”,正是从作为此在分析学的生存论现象学,向作为此之在分析学的存在历史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语言论题的出场并不突兀,而是存在历史思想对存在本身之探索的初步成果。这一成果经由《书信》强化,在20世纪50年代得以更进一步的深化*相关探讨的结集参见[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海德格尔从而将开辟并占用通向存在之真理道路的存在历史思想的根本任务表达为“将作为语言(道说)的语言(语言本质现身)带向语言(有声表达的词语)”*M. Heidegger, “Der Weg zur Sprache”, in Unterwegs zur Sprache, GA 12, Frankfurt a. M. 1985, S. 250. 中文本参见[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第262页。。除了语言,晚年海德格尔在技术、科学等主题上的思考也源于“存在历史手稿”*主要参见GA 65, S. 126ff. 中文本参见[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第133页以下。;但从存在历史思想的基本理路来看,语言概念的出场在方法和主题上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存在历史思想与“海德格尔的马克思”
从“存在历史手稿”出发,分析存在历史思想在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上承前启后的位置,对于厘清“海德格尔的马克思”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首先,在文本中,20世纪30年代以前,即存在历史地运思之前,马克思或任何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成为海德格尔的研讨对象*虽有论者试图从物化(Verdinglichung)、历史等概念出发探索此一时期海德格尔——主要是《存在与时间》中的思想——与卢卡奇思想的关系,但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海德格尔文本中没有直接谈及卢卡奇,另一方面二者的联系可能间接建立于与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主要是埃米尔·拉斯克(Emil Lask)——的关联上。关于“海德格尔和卢卡奇”这一论题的代表性研究,参见L.Goldmann, Lukács und Heidegger, Darmstadt 1975.(法文原版参见L. Goldmann, Lukacs et Heidegger, Paris 1973)。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稍早可能在于海德格尔的成长背景、求学环境和致思动机都和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无关,稍晚可能在于纳粹德国对马克思思想的明令禁止。其次,20世纪30年代后,海德格尔直接谈及马克思处,其运思基础都可回归到“存在历史手稿”中的相关思索。关于这些文本上的依据,埃克斯罗斯指出:“海德格尔并未提供给我们一条诠释马克思的基本线索。他从未如深入研究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和尼采那样深入地研究过马克思。然而在海德格尔的思想尝试中,马克思却绝未缺席。通过试图把握现代技术——甚至行星技术——的本质,通过试图阐明机器时代以及核子时代的根源,通过试图思想着质询无家可归状态[Heimatlosigkeit]和无根状态的世界命运[Weltschicksal],海德格尔使人感到,马克思处于这些尝试的背景中。”*K. Axelos, Einführung in ein künftiges Denken. über Marx und Heidegger, Tübingen 1966, S. 8.事实上,对于马克思的这种背景作用,海德格尔也有所透露。在1931年弗莱堡大学夏季学期的讲座课中,谈到《存在与时间》的哲学努力时,海德格尔说:“……在某本称为《存在与时间》的书中的谈到与用具打交道的活动[Umgehen]时;[这]并非为了修正马克思或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国民经济学,也非源自一种粗陋的对世界的理解。”*M. Heidegger, Aristoteles, Metaphysik Θ 1-3, Vom Wesen und Wirklichkeit der Kraft, Gesamtausgabe Bd. 33, Frankfurt a. M. 21992, S. 137.a然而,马克思在海德格尔处具体发挥何种作用,则需要进一步结合相关文本进行讨论。
就笔者所见,虽然海德格尔在写于1936-1938年的第一部存在历史手稿《哲学论稿》中就谈到了马克思主义*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第19节“哲学(关于问题:我们是谁?)”(第一部分“前瞻”)中写到:“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形式,它本质上既与犹太教毫无干系,根本上也与俄罗斯毫无干系;如果说在某个地方还潜伏着一种未展开的唯灵论,那就在俄罗斯民族身上;布尔什维主义原本是西方的,是欧洲的可能性:群众的升起、工业、技术、基督教的枯萎;但只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理性之主宰地位只不过是基督教的一个后果,而基督教根本上是有着犹太教起源的(参看尼采关于道德的奴隶起义的思想),那么,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就是犹太教的;然而这样一来,甚至基督教根本上也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还有,由此而来,何种决断成为必然的?”([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第59及下页。),但首次公开基于存在历史思想的语境谈及马克思本人,则是在写于1946、出版于1947年的《书信》中。在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从他的存在历史观出发,对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他所理解的“人道主义”(Humanismus)——和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讨论。关于马克思,海德格尔首先指出,他从社会角度对人本质的规定*参见[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第374页。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都是非历史的*参见[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第376页。,它们同过往的人道主义享有相同的前提:“homo humanus[人道的人]的humanitas[人性、人道]都是从一种已经固定了的对自然、历史、世界根据的解释的角度被规定的,也就是说,是从一种已经固定了的对存在者整体的解释的角度被规定的。”*[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第376页。也就是说,过往的人道主义和形而上学互为根据。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和尼采虽然都完成了对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但总体上还都属于传统形而上学历史的一部分,而形而上学的历史作为存在真理本身显现的实有过程,是历史的事实。*参见[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第396页。就此而论,在海德格尔眼里,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终结阶段的一个代表人物,马克思本质上依然是形而上学的。
形而上学的历史后效是导致了现代人类的无家可归状态。着眼于此,关联于马克思,海德格尔又指出:“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一种世界命运。因此就有必要存在历史地思考这种天命[Geschick]。马克思在一种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出发认作人类之异化[Entfremdung]的东西,与其根源一起开始于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这种无家可归状态——它出自存在的天命而在形而上学之形态中被带来——通过形而上学得以巩固,同时被形而上学作为无家可归状态遮盖起来。正因为马克思经验到了异化,亦即伸入到了历史的一种根本维度[Dimension],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对历史的见解就胜过了其他历史学。但是因为无论胡塞尔还是萨特,就我目前所看到的,都未认识到存在中历史之物的根本性,所以不论是现象学还是存在主义都未进入那样一个维度,在此维度中,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有成效的对话才变得可能。”*M. Heidegger, “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 (1946)”, in Wegmarken, GA 9, Frankfurt a. M. 1976, S. 339f. 中译文参见[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第400及下页。海德格尔在此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自己的无家可归状态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异化概念之所思与无家可归状态之所指一致,都朝向对根本性的历史维度,即存在中历史之物的根本性之维的自觉。这一维度就是存在作为历史本身自我发送(sich schicken)的维度。这种存在的发送(Schickung)本身就是所谓的天命。所谓的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从存在的天命来说,就是处于西方思想第一开端(der erste Anfang)至终结之内的人类此在的命运(Schicksal)。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这一开端开始于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柏拉图等人,终结于黑格尔、尼采;此一阶段的人类此在的基本处境是,要么意识到了存在本身和存在者的基本差异却没有思考这种差异,要么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总之,都是将存在思为存在者,继之对存在者整体予以固定的解释。这种生存处境被海德格尔称为存在被遗忘状态(Seinsvergessenheit),是相应的人类此在之“存在于世界之中”(In-der-Welt-sein)的基本规定;从被交道的存在者角度来说,存在被遗忘状态使之处于一种存在被离弃状态(Seinsverlassenheit)。因而人类此在的存在被遗忘状态与存在者的存在被遗忘状态互为表里。这样一种状态使得人类处于此之在之外,也就是说,没有达乎在此之在中的持立状态(Inständigkeit),亦即没有以绽出之生存(Ek-sistenz)的方式存活。这种绽出之生存被认为是存在历史意义上的人的真正本质,就此来说,能够经验到作为语言现象自我显示着的存在,在语言世界中塑造自我,就是在家状态。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说“存在在思想中达乎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第366页。;反之,则是“无家可归”。也就是说,人可以是其本质而存在,也可以不是其本质而存在;是其本质而存在为“在家”,不是其本质而存在为“无家可归”。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恰恰思及了人不是其本质而存在的状态,就此而论,海德格尔将马克思视为思想上的先行者,给予其积极的评价。
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从其思想基底上虽然是形而上学的——显然是翻转了的,但是在具体观念处却又突破了形而上学的桎梏,体现了对存在历史真理一定程度上的自觉。于是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既有批判又有阐扬。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角色十分类似于尼采等人:一方面,被归为西方思想第一开端的历史即形而上学的历史,成为海德格尔批判和超克的对象;另一方面,在一些具体的观念上,被海德格尔引为朝向西方思想另一开端(der andere Anfang)的思想上的先驱。
然而上述第一种形象显然发挥着主要作用,这通过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进一步引用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在1957年弗莱堡所作的演讲《思想的原则》(GrundsätzedesDenkens)中,谈及马克思的劳动(Arbeit)概念时指出:“……‘劳动’这词在此并非指单纯的活动和功效。这个词说得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劳动概念,而劳动被思为辩证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现实物之生成展开并完成其现实性。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不在绝对的自我把握的精神中,而是在生产自我及其生活资料的人类中识得了现实性的本质,这种做法虽然使马克思和黑格尔处于极度的对立,然而通过这种对立,马克思依然处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因为生命[Leben]和现实性的支配[Walten der Wirklichkeit]各处表现为作为辩证法亦即作为思想的劳动过程——只要那种生产中本来发生生产作用的部分是思想的话,所以思想就能被把握和实现为纯理论-形而上学的思想,或者科学-技术的思想,或者这两种形态的混合和扭曲。每种生产在自身中业已是反思(Re-flexion),是思想了。”*M. Heidegger, “Grundsätze des Denkens”, in 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GA 11, Frankfurt a. M. 2006, S. 139f.这里包含了海德格尔两方面的想法。
其一,进一步延续《书信》的思想,将关于人的基本看法与其形而上学基础联系在一起,来解释马克思的形而上学属性。关于这一点,海德格尔随后在1969年9月7日于法国莱托(Le Thor)举行的研讨班中进一步指出,将人的本质置于社会性的生产关系中,在实践中看待生产,将实践视为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理论又将生产概念塑造为人类通过其自身的生产,这就表明马克思有一种十分确切的关于人的理论观念,而这种观念也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从而为黑格尔哲学所包含,于是海德格尔强调说“没有黑格尔,马克思就不能改变世界”*参见M. Heidegger, “Seminar in Le Thor 1969”, in Seminare, GA 15, Frankfrut a. M. 1986, S. 353.。虽然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使存在先于意识,但马克思将存在经验为生产过程,这一想法的来源是黑格尔将生命视为过程,也就是说“生产的实践概念[der praktische Begriff der Produktion]只能基于一种源自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M. Heidegger, “Seminar in Le Thor 1969”, S.353.。
其二,延续《书信》的思路,通过将生产、劳动等本质上归为作为最基础意义上行动(Handeln)的思想*参见[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第366及下页。,来理解马克思的相关概念。这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思想”,正是存在历史意义上的人与存在本身的关联及实行方式(Bezugs-und Vollzugsweise)。从这种观念出发,海德格尔随后在作于1961年的演讲《康德的存在论题》中引用并解释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论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interpretiert]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verändern]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一方面,海德格尔在此暗示出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对于康德“存在论题”(These über das Sein)意义的理解不究竟,从而提出了哲学不应只解释世界而需要改变世界的要求。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的相关努力对于哲学改变世界是意义深远的。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指出,改变世界的要求以及改变世界的活动本身都要以一种思想的改变(Veränderung des Denkens)为前提。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提出哲学改变世界的要求本身就隐含了他较之以前的哲学已经有了一种思想上的改变。*参见[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第523及下页。这种思想的改变,依据海德格尔的看法,也就是经验存在的方式的改变。
这两个方面的合题依然是存在历史视域下人与存在本身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从人的角度讲,这种关系作为经验存在的方式,可分别作关联(思想活动)和实行意义(道说活动)上的把握。因而,一方面,存在历史思想认为最基本的人与存在关系的改变乃是思想关联层面的。据此,海德格尔在1969年9月17日接受德国电视二台记者理夏德·维塞尔(Richard Wisser)采访时,又一次就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提纲明确指出:“在引用并遵循这句话时人们忽略了一点,改变世界以世界观念[Weltvorstellung]的改变为前提,并且,要获得一种世界观念,人们就必须充分地解释世界。这就是说:马克思在谈他的‘改变’时,他依据了一种完全确定的解释世界的方式,由此可见,这句话是缺少根基的。它唤醒了一种印象,好像马克思说了坚决反对哲学的话,事实上,它的后半部分恰恰有以哲学为前提的要求,虽然他没有明说。”*《理夏德·维塞尔对海德格尔的采访》,载[德]贡特·奈斯克等编著:《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陈春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页。
另一方面,存在历史思想虽然以人、人本身生存方式的改变为出发点,但却以顺从存在的真理为标的。据此,海德格尔在1973年9月弗莱堡泽林根(Zähringen)住所的讨论班上*参见M. Heidegger, “Seminar in Zähringen 1973”, in GA 15, S. 387.又一次回顾了他在《书信》中对萨特观点——“严格来讲,我们在一个其上只有人的平面上”*参见[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第393页。——的批评,并同时认定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根据与之类似,正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虽然这个引文出处的语境是政治的,但海德格尔随后指出,他对这一论断的解读是形而上学的。这就是说,海德格尔认为:其一,马克思延续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翻转,即把人而非绝对者(das Absolute)作为知识的实事(Sache),从而得出“人[应当]是人的最高本质”*同上。;其二,随着马克思将人本身推向极致,造成了“存在之为存在一点也不(nihil)为人所存在”这种与存在无干的状态,正是海德格尔所理解的虚无主义的本质,从而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到达了虚无主义(Nihilismus)的极致。*参见M. Heidegger, “Seminar in Zähringen 1973”,in GA15, S. 393.
三、结论与启示
无疑我们可以争论海德格尔是否恰当地理解了马克思,但不可否认的是海德格尔晚年对马克思的论断是惊人的*这表现在海德格尔的论断与我们当代的一些理论尝试——比如在哲学上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来批判虚无主义在历史问题上的变种——有着根本的矛盾。。然而,从其二战后谈论马克思的历程来看却是一以贯之的。这就使得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论断成为其本人思想道路上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从存在历史思想的背景出发,海德格尔的论断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虽然在人与存在的互相关联中考察存在显现的方式和人的本质,但却始终强调存在本身的支配地位,并将这种支配地位推向了极致。概言之,虽然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某些具体思想主题有所褒扬,但却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完型依然是形而上学的。同时,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终结意义上来看,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即海德格尔所认为的存在被遗忘状态的极致。由此,马克思就成为海德格尔存在历史思想的哲学上的、而非政治上的辨证(Auseinandersetzung)对象。参照海德格尔对待西方历史上其他重要思想家的态度来看,一方面马克思在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上扮演的这种角色不能被单纯界定为积极或消极,另一方面由于海德格尔从未给与马克思以专题的讨论或系统的诠释,使得我们不得不认定马克思对于海德格尔本人思想的重要性既不及同时代的尼采,又不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史上的其他大家。
笔者认为,以上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有着如下启示。首先,不能枉顾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评判,武断地从海德格尔出发来诠释马克思,或者进一步发展出一个“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其次,启发我们在哲学研究上,要将马克思放在西方思想的历史发展背景中,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得出一个既不拔高又不贬低的客观结论,从而有利于我们将之与当代现实做恰当的结合。最后,对于“海德格尔与马克思”这一论题的进一步开展而言,可就如下论题作进一步的思考:沟通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必要性及目的究竟何在;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可在何种层面——方法、视域、抑或论题等——上进行沟通;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理解是否恰当;是否存在从马克思出发解读海德格尔的可能性,等等。
(责任编辑 巳 未)
B516.54
A
1000-7660(2017)03-0030-08
杨 栋,陕西乾县人,德国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西安 710049)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讲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西安交通大学新教师科研支持计划;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7M6B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