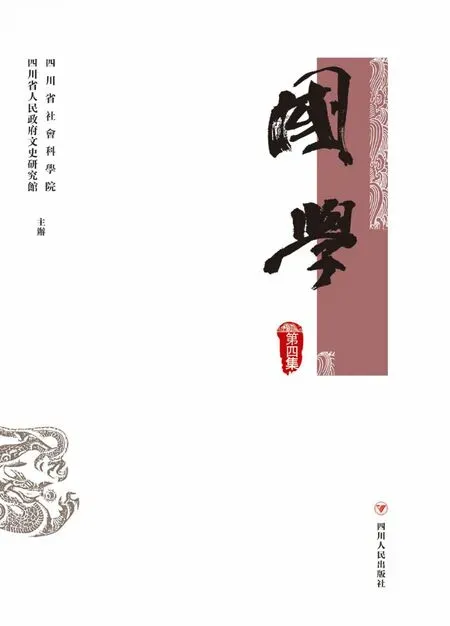研習宋史:我的自主選擇
2017-01-26張邦煒
20世紀60年代初,我開始研習宋史時,專攻宋史的學者屈指可數,宋史領域有待開墾的荒地多,值得探究的問題多,理當修訂的成見多。今非昔比,鳥槍换炮。宋史學界隊伍壯大,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大幅度提昇。近年來,每當拜讀優秀青壯學人所贈大著,“一代新人勝舊人”之感油然而生,不禁想到這首打油詩:“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後浪風光能幾時,轉眼還不是一樣。”我有一幅“自畫像”:“思維方式——止步於80年代之初;知識層面——停滯於21世紀之前。”這絶非“賈雨村言”。本人即便有一星半點成績,已是宋史研究處於薄弱階段的往事,而且還有待糾謬,豈敢張揚。因友人一再盛情相約,終於勉爲其難,寫下這篇自述。鑒於何玉紅、刁培俊兩位教授已有訪談録[注]何玉紅、刁培俊:《兩宋歷史的多角度探討——訪張邦煒教授》,《歷史教學問題》2007年第6期。刊佈,本文儘量减少重複。
一、“我的事情我做主”
常聽學生説,他學歷史出於偶然或無奈,甚至抱怨歷史捉弄人,走錯了房間。我則不然,學歷史實乃平生志趣之所在,是我獨立自主作出的選擇。
我對歷史的濃厚興趣是50年代中期在成都十二中(今改爲川大附中)讀高中時養成的。時值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時,李政道、楊振寧榮獲諾貝爾獎之初,黨中央響亮提出:“向科學進軍。”這五個字入耳入腦入心。實不相瞞,我當年心中的榜樣是中科院長郭沫若。我對未來的嚮往是:像郭老那樣,研究歷史,做無黨派人士。[注]後來纔知道,郭老早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後,就加入中國共産黨。我崇拜郭老,與正處於青春躁動期關係極大。我和不少同學一樣,喜歡他的詩篇《天狗》:“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何等氣概!喜歡他的劇本《屈原》:“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長江,我思念那東海,那浩浩蕩蕩的無邊無際的波瀾呀!那浩浩蕩蕩的無邊無際的偉大的力呀!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樂,是詩!”相當震撼!郭老在我心中威望下降,始於其詩集《百花齊放》面世之時。其時人們議論紛紛:“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相傳連郭老本人也説:“老郭不算老,詩多好的少。”然而我酷好歷史之心始終不變,曾將史可法的對聯“鬥酒縱觀廿一史,爐香静對十三經”作爲座右銘,懸挂於陋室。[注]如果要準確些,應改爲:“鬥酒縱觀兩宋史,爐香静對一屋書。”我曾請有“巴蜀才女”之稱的鄉賢黄穉荃前輩書寫這14個字,以備懸挂。誰知她老人家寫的竟是:“文發春華,學徴秋實;才橫東箭,器重南金。”愧不敢當,只能珍藏。
1957年高中畢業時,我一心報考歷史系。没想到居然遭到歷史知識相當豐富的父親一再勸阻。他認爲歷史只能作爲愛好,不能作爲職業,建議我報考物理系。一定要學文科,就報經濟系。他説,物理學、經濟學比較實用,更能直接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今天看來,父親很務實,他的主張不無道理。然而當時父親的阻攔適得其反,我的逆反心理飆昇。正好《語文》課剛學過李白的《夢遊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我竟然將較爲開明的父親視爲“家庭權貴”,心想:你青年時代投身於“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戰鬥,我今天要向你的封建家長制開火,揚言:“我的事情我做主。”當時高考可填報十二個志願,我一口氣填了十二個歷史系,抱定非歷史系不讀的决心。
我大哥1946年考大學,接連考取中央大學、北平大學、重慶大學三大名校,三選一,選擇上北大。父親高興地讓他坐飛機,上北平。這次我會考取什麽大學呢?録取通知書是星期天全家在人民公園喝茶娱樂時收到的,我被録取到蘭州大學歷史系。這個結果遭到父親當衆嘲笑:邦煒考起了個第八志願。我臉紅了一陣,心想:好學校有差學生,差學校有好學生,關鍵不在於學校,而在於自己。父親的嘲笑鞭策着我日後加倍努力學習。我表示要向列寧那樣,不知疲倦地讀書,每天學習十二小時。從那時起,我即養成“開夜車”的習慣,是個“夜貓子”。大學階段,我的歷史專業課成績在班上始終名列前茅。
父親是30年代先後在北平、東京上大學的,對後來崛起的蘭州大學不大瞭解。其實蘭大不算差,用現在的高校分類來説,畢竟是個“211”“985”大學。不過當時理科强、文科弱。江隆基校長後來曾説,蘭大文科有水準的教師就是個趙儷生。[注]這句話不一定很準確,蘭大文科有水準的教師還有楊伯峻先生等。只是楊先生到蘭大遲,走得早,時間短。其實趙先生也是1957年纔從山東大學調來的。爲解决學生普遍關心的師資問題,校方大量臨時聘請名校名師任教。我們班大一的考古學通論是北大閻文儒、吕遵諤老師上的,中、外兩門通史由中山大學丘陶常、梁作幹老師講授。當時蘭大文科主要靠中大支援。大二安排的課程中有中大容庚、商承祚先生講古文字學,劉節先生講中國史學史。後因容、商、劉三大家受到學術批判而未果。1959年,校方因噎廢食,乾脆採取果斷措施,取消文科,蘭大歷史系一度合併到西北師院,改稱甘肅師大,現稱西北師大。“三反以後不管錢,反右以後不發言。”同學們對這個决定雖然不滿,只能聽從。我的本科以至研究生階段的學業是在甘肅師大完成的。平心而論,當時西北師院歷史系的師資力量强於蘭大歷史系,西北師院抗戰時期曾稱西北聯大師範學院,因其前身是北平師大,文科藏書比蘭大要豐富些。如果不圖虚名而務實效,這也不失爲一項可取的舉措。
“我的事情我做主。”我還“自主”地作出了以下三大選擇,這些都深深地影響着我這一生。
其一:自告奮勇當白旗。從1957到1958年,蘭州大學的反右派鬥爭、拔白旗運動搞得轟轟烈烈。繼陳時偉副校長夫婦等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後,校黨委劉海聲書記又拔了林迪生校長的白旗。師生中右派、白旗的數量都不少。當時的口號是:“插紅旗寸土不讓,拔白旗一個不留。”拔白旗運動與向党交心、紅專辯論交叉進行。班上開會討論:誰是白旗?我傻乎乎地(在今天看來)站起來交代自己的只專不紅思想,並自報白旗。我的錯誤是晚上熄燈後還在盥洗間讀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陳夢家的《殷虚卜辭綜述》,早上不起床參加體育達標活動,拖全班後腿。起初認爲白旗只是思想認識問題,不是一頂政治帽子,算不了啥。當學校在大喇叭裏通知,白旗同右派一起到工地參加勞動,纔感到問題之嚴重。好在《紅旗》雜志1959年初發表評論《不要亂戴白旗帽子》,據説是傳達黨中央的新精神。總書記鄧小平指示:“拔白旗不要亂拔。”中宣部長陸定一發話:“紅旗可以插,白旗、灰旗不要拔。”於是拔白旗運動匆匆結束,我的白旗帽子自行作廢。1960年底,黨中央糾正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的“左”傾錯誤。受到降職處理的劉海聲副書記專程到師大向我們這些“白旗”賠禮道歉,態度相當誠懇。蘭大黨委爲鄭重起見,出於好意,决定正式平反,於是這段經歷被記入檔案。其實際後果是人事幹部此後不時提起我十七八歲時留下的這個“歷史污點”。
其二:出於愛好學宋史。1961年,我本科畢業後,留校做中國古代史研究生。我這個“揭帽白旗”居然留校,與當時的形勢有關。學校正貫徹《高教六十條》,整頓教學秩序,强調以教學爲中心,以教師爲主導。我這個專業課成績好的學生理所當然地留校了。究竟研習哪個斷代?教研室主任金寶祥先生是唐史專家,他徵求我的意見。受何兹全、梁作乾等先生的魏晉封建論和侯外廬、胡如雷等先生的唐宋變革論影響,我認爲魏晉與兩宋的歷史向着相反方向發展,時代特徵很鮮明,但揭示欠充分,後者尤其薄弱。我不願跟唐史專家學唐史,而選擇學宋史。金先生可能有些失望,但他很開明,認爲興趣是學習的第一推動力,表示尊重我的志趣。金先生説,《續資治通鑑長編》很難找,學校圖書館有一部浙江書局本。《宋會要輯稿》前些年剛影印批量發行,利用得很不夠。你不要浮皮潦草,而要認真仔細地研讀這兩大部書。當時書籍少,讀書用書的人更少。學校圖書館允許我將館藏綫裝書借回寢室細讀。單就這點來説,條件比今天好。我十分感激金先生,是他讓我做自己想做的事。2014年,金先生百歲冥壽,我既撰文紀念:《一位特行獨立的思想型史家》,又瞻仰其出生地——浙江蕭山臨浦鎮臨江書舍,還到蘭州他老人家墓前祭拜。
其三:心血來潮進西藏。研究生畢業前要填工作分配志願表,表上有工作性質與工作地區兩欄。填表前,學校動員畢業生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組織我們到蘭州劇場看話劇。“一生交給黨安排”,“黨指向哪裏就奔向哪裏”,“祖國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志願”,話劇深深地打動了易於激動的我。填表時,我按照話劇裏的語言,在工作性質一欄填上五個字:“爲人民服務”,在工作地區一欄填了三個字:“全中國”。恰逢西藏方面向教育部要文科研究生,有關領導看中這張志願表:西藏很艱苦,正需要這樣的同志!於是我進藏了,分配到西藏人民廣播電臺任編輯。[注]可參看拙稿:《西行萬里到拉薩》,載西藏人民廣播電臺編《走向輝煌》,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當時組織上只講進藏,不講出藏,没有“援藏”這個詞,口號是:“長期建藏,邊疆爲家。”譚二號(譚冠三政委)又加了八個字:“死在西藏,埋在西藏。”藏族群衆將“文革”前進藏幹部稱爲“永久牌”,“文革”後進藏人員稱爲“飛鴿牌”。我這個“永久牌”雖然没有“埋在西藏”,但在西藏待的時間不短。陳樂素老先生是宋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後來他批評我:你在西藏時間那樣長,十分難得。你不學藏文,不搞藏學,不研究藏傳佛教,仍然搞宋史,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失誤。陳老的批評很中肯,然而我研習宋史的興趣實在太大。我進藏時的行李是八個小紙箱,裏面裝着心愛的數百册書籍,幾乎全部與宋史有關。它們騎過西藏高原上的毛驢,坐過雅魯藏布江裏的牛皮船,還乘着汽車翻越了昆侖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米拉山、色齊拉山等一座座高山,始終陪伴着我。在當時的西藏,《長編》《會要》這類書籍根本無法找到,研究宋史的基本條件不具備。工餘之暇,除讀史書外,也讀些“閒書”。至今仍不時回憶起當年的情境:在喜馬拉雅山區、羊卓雍湖邊,坐在酥油燈下,烤着牛糞火,夜讀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雨果的《悲慘世界》。
實話實説,我的長期建藏思想並不牢固,總想有朝一日,回到內地,繼續研習宋史。對於我進西藏,改行做新聞工作,師友們當面對我没説啥,心裏很惋惜,認爲用人不當。“文革”一結束,金先生就試圖調我回學校。研究生期間結識的老友朱瑞熙後來分配到中科院近代史所工作,他曾爲將我調往北京而活動。當時的西藏只能進,不能出,內地是不能向西藏要人的。趙先生對他的研究生葛金芳等説:“蘭州從前有兩個優秀史學青年,可惜一個跳黄河,一個遠走西藏了。”要求他們的學位論文達到我們畢業論文的程度。其實他們後來居上,論文更上一層樓。“跳黄河”的是指我的研究生同學余用心,他的畢業論文受到明史兩大家誇獎。鄭天挺先生的評語是“足以成一家之言”,王毓銓先生説“研究生而有這樣的成就是罕見的”。令人痛惜的是,用心在“文革”中失蹤。
1980年,我在西藏工作十五年之後,終於夢想成真,得以返回故鄉,到四川師範學院(今四川師大)歷史系任教。人過中年,學業荒疏。值得慶幸的是,80年代前期,我獲得兩次再學習的機會。一次是1982年春天,經朱瑞熙推薦,到上海師大,在程應鏐先生主持下,參與編審《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與徐規先生等前輩學者在一起緊張地工作,深受教益。另一次是1983年上半年,經友人賈大泉介紹,與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酈家駒先生認識,由酈先生提供方便,到歷史所訪問,得到陳智超、王曾瑜、吴泰等朋輩先進的關照,獲益良多。當時處於業務人員青黄不接的時期,不少單位都缺人。離京返川時,酈先生勸我不要走,就留在歷史所,調動問題由他負責解决,我十分感激。但很不現實,不僅本單位不會放我,而且一家四口的北京户口絶無解决的可能。我曾想就近在成都换個以研究爲主的單位,恰逢曾棗莊、劉琳二位主持川大古籍所,正着手編撰《全宋文》,需要學宋史的。事情正在進行中,柯昌基等同仁提醒我:古籍整理非你我所長。我纔恍然大悟:我的老師無論金寶祥還是趙儷生都是理論派。金先生要求學生“做有思想的歷史研究”,“從史書中讀出哲學的意境”。趙先生常説:“要考辨,更要思辨。”與師承關係有關,受經歷、地域等因素局限,古典文獻學之類正是我的短板。於是此事作罷。普通師範院校教學任務重,研習宋史只能在教學之餘。但畢竟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還有幾位一心向學的友人在一起談學問。友人們後來皆學有所成,有的大名鼎鼎,恕我略去他們的姓名,以免有“拉大旗作虎皮”,“我的朋友胡適之”之嫌。友人遠走高飛,而我始終在四川師範學院任教,直到退休。以教師爲職業,站在課堂上,面對一張張年輕的笑臉,自有其樂趣。
二、“商榷派”有什麽不好
如今人們常説“問題意識”,只怕並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讀研究生時,我就從刊物上知道,研究學問無非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决問題,難點在於發現問題,如能提出真問題,問題已解决一大半。“吾愛吾師,吾猶愛真理。”對老師、對前輩乃至權威的既有結論不應輕信,凡事都要多問幾個爲什麽。於是身上揣個小本本,抓住一瞬間,將驀然想到、稍縱即逝的各種問題及時記録下來,以備日後思考。與今天不同,當時不以著述多少論高低。金先生要求我們多讀書、多思考、多積累,少寫作。他説:“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多必濫!”但我手癢癢,總想寫。寫得並不多,已被嘲笑爲“多産作者”。所寫習作有兩篇被採用,《試論宋代的官田》刊載於本校學報,《宋代客户的身份問題》[注]載《光明日報》1965年8月11日《史學》版,發表時題目改爲《宋代存在著大量的自由佃農嗎——與束世澂先生商榷》。由《光明日報·史學》登載。畢業論文《北宋租佃關係的發展及其影響》[注]《西北師大學報》1980年第3、4期連載,人大複印資料《中國古代史》1980年第3期、1981年第2期連續全文轉載。雖然當時未公開發表,但學校將它鉛印成册,不僅呈送評審人北大鄧廣銘、南開楊志玖教授,而且寄給各高校中古史教研室,廣泛徵求意見。華東師大束世澂、中大何竹淇、武大李涵等不少前輩學者主動寄回評語。據説當時還健在的蒙文通老先生也看過,並叫人寫評語。因此《影響》一文在宋史學界小圈子內有一定影響,朱瑞熙在《史學月刊》1965年第6期發表的論文中引用了這篇未刊稿。至於中科院歷史所孫毓棠先生的意見很具體,仔細到措詞遣句,是《歷史研究》編輯部轉給我的,叫我參照孫先生的意見修改後寄回發表。我正在酒泉縣東洞公社搞“四清”運動,没時間修改,而《歷史研究》已於1966年初停刊。此文遲至1980年纔公開發表,其實是篇舊作。在今天看來,《官田》等文問題不少,很稚嫩。如《官田》一文的參考文獻只有《文獻通考》《宋史·食貨志》《宋會要輯稿·食貨》三種常見史料,但都是我認真讀過的。引用的恩格斯論述:“支配農民的租賦就遠比支配他們的人身重要很多”,是我從《德國古代的歷史和語言》一書中讀到的,只怕還是第一次被引用。不轉引、不拼凑,對初學者來説應當是個優點。
當時我二十剛出頭,血氣方剛,是個“易膽大”。《官田》等文均屬於商討性文章,商榷的對象主要是雲南大學李埏先生的《〈水滸傳〉中所反映的莊園和矛盾》以及束世澂老先生的《論漢宋間佃農的身份》。李先生在《矛盾》一文認爲宋代是個無處無莊園的“莊園世界”,莊園是在經濟上與外界無交往的“絶緣體”,並將宋代的莊園定性爲農奴制。我的老師陳守忠先生在講課時對李先生的觀點大加贊賞,我則認爲很值得商討。我在《官田》等文中提出了一些與當時主流認識不同的論點。其一,宋代的主要土地經營形態不是莊園制而是租佃制。宋代的官莊已難以爲繼,或出賣或出租,陸續被租佃制所取代。其二,宋代農民的主體既不是農奴,也不是自由佃農,而是租佃農民。佃農退佃“自由”的爭得、私家佃農而負擔國家賦役、超經濟强制權力的削弱等等,一概表明宋代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是人身依附關係趨於弱化。其三,宋代還殘存着少量莊園,但大多並非與外界隔絶的“絶緣體”。宋代農村商品經濟相當活躍。我的《官田》一文是1962年底發表的,第二年冬天在《歷史研究》上讀到鄧廣銘老先生的《唐宋莊園制度質疑》。我在贊同之餘,也有一點想法:唐代莊園與宋代莊園只怕不完全是一回事。鄧老此文以及山東大學華山先生的一論、再論宋代客户身份兩文在學界影響較大,此後宋代莊園制、“絶緣體”一類的説法不再流行。
從具體到抽象,從抽象到具體,往復於兩者之間。我還從具體史實中抽象出兩個簡明扼要、或許有些新意的看法。一個叫:宋代“賦重役輕”。從兵役大體消逝、廂軍分擔夫役、夫役雇法施行三個方面加以論證,認爲這是宋代賦役制度的一大變革。數十年後,包偉民教授在《宋代財政史研究述評》一文中對這一歸納給予積極評價。另一個更爲重要的觀點是:宋代“弱而不貧”。長期以來,人們將宋史視爲一部窩囊史。一説到宋代,就是四個字:“積貧積弱。”對於這一成見,我大不以爲然,有兩句打油:“人云宋史本痛史,我謂宋史亦壯篇。”我在《影響》一文“引言”中以人口增長、耕地擴大、産量提高等量化數字爲依據,認爲:“在我國中世紀史上,有宋一代放射出來的光彩足以同漢、唐兩朝前後相輝映、相互爭妍麗。”這些數字後來被《在歷史的表像背後》《興盛與危機》等著述徵引。這些推算得來的數字是不準確的。當時我就説:“只是些近似值。從絶對意義上講,並不可靠。就相對意義而言,所展示的趨勢是可信的。”宋代“弱而不貧”的觀點,我始終堅持。後來在《瞻前顧後看宋代》[注]載《河北學刊》2006年第5期,《新華文摘》2007年第1期、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07年第1期全文轉載。一文中又將宋代的歷史地位概括爲“兩大超越”:“橫比當時世界各國,超越世界各國,處於領先地位;縱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繼漢朝、唐朝之後的又一座新高峰。”
八九十年代,在研討會上,多次聽到一位前輩學者嘲笑“商榷派”。我心想:鄙人不就是個“商榷派”麽?跟着又想:“商榷派”有什麽不好?理性的學術商榷與粗暴的學術批判有實質性的不同。當年提倡學術的戰鬥性,學術批判多,我們這些懵懂小青年參與了不少。幾天前,在中知網上偶然看到一篇史清的《駁馮定同志的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熄滅論》,使用粗暴語言,給馮老扣上“修正主義”帽子,不免臉紅,深感惶愧。所謂“史清”就是我們幾位研究生同學的集體署名,是當年批判馮老的《平凡的真理》時寫的。戚本禹《評〈李秀成自述〉》發表後,我們還跟着瞎起哄,寫了一篇《李秀成是怎樣走上叛徒道路的》,批判羅爾綱等老先生。其實,就連這位前輩學者本人也既學術批判他人又受學術批判。這個教訓是很深刻的。學術批判不可取,學術商討不可少。真理未必一定越辯越明,然而正常的學術商討確乎是推進學術繁榮的助力,嚴肅的學術批評勝過廉價的相互吹捧何止千百萬倍。我的《官田》等文未必很理性,但大體還在正常的學術商榷範圍之內。《身份問題》一文的末尾原本有句與當時的四清運動相聯繫的話,陳守忠老師叫我删掉,説兩者絲毫不相干。好在這次我聽了師長的話,不然又多一個歷史污點。對於學術商討,李埏先生寬宏大度。80年代初,我拜會李先生。他告訴我,讀到你們學校寄來的《影響》一文,他立即給學校寫信:這樣的學生應當受到表揚。李先生的長者風範,令我敬佩不已。向李先生學習,我歡迎别人批評。後來北大李立博士從方法論的角度批評包括我在內的不少同行,我多次在公開場合高興地講到此事。宋史學界有個敢於批評的“監督崗”真好,有利於提高探討品質、端正學術風氣。可惜李立畢業不久就改行。
三、讓“唐宋變革論”豐滿些
我曾以“較爲頑固的唐宋變革論者”自稱。研究生時,幾篇習作無非是從土地制度、賦役制度的角度探討唐宋變革。這一探討因遠走西藏而中斷,後來斷而相續,且越發自覺,並有所拓展。之所以如此“頑固”,與日本學者宫崎市定特别是錢穆老先生不無關係。1963年,讀到商務印書館剛翻譯出版的《宫崎市定論文選集》。雖然我並不認同宫崎將宋代豔稱爲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認爲東方的文藝復興早於西方的文藝復興幾百年,並引發了西方的文藝復興,也不贊同宫崎將由唐入宋定性爲從中世到近世的轉化,但他的有關論述大大加固了我從前業已初步形成的唐宋變革論。受時代局限,錢穆等老一輩歷史學家的著述,我青年時代讀得很少。遲至1983年在歷史所時,才讀到錢老的《理學與藝術》一文。錢老視宋代社會爲“純粹的平民社會”,我覺得不甚確當。但他説:“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就宋代而言,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給我莫大啟發。闡釋唐宋變革論,僅着眼於農民起義口號的變化、人身依附關係的减輕、土地私有制的深化,未免太乾癟。要讓唐宋變革論豐滿起來,必須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
主攻方向雖然明確,但畢竟是重起爐灶,應當從何入手,一時拿不定主意。先寫些調適性文章,偶有所感,即興而作,無中心,很零亂。如因官員及其家屬經商等問題開始凸現,寫下《宋代官吏經濟違法問題考察》[注]載《社會科學研究》1986年第1期,《新華文摘》1986年第5期全文轉載。《宋代禁止官吏經商始於何時》[注]載《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4期。《宋代官吏經商問題剖析》。因高薪養廉之説蠭起,寫下《宋代“省官益俸”的構想及其實踐》[注]載《四川師大學報》1987年第1期,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1987年第2期全文轉載。《宋神宗的重禄法》,認爲“益俸”必須以“省官”爲前提,“重禄”應當與“重罰”並舉。因當時正着手建立各種回避制度,寫下《宋代避親避籍制度述評》。[注]載《四川師大學報》1986年第1期,人大復印資料《宋遼金元史》1986年第2期全文轉載。此文有“取巧”之嫌,趙甌北《陔余叢考》書中就有《避親避籍》一條[注]趙甌北《廿二史劄記》、錢辛楣《廿二史考異》、王西莊《十七史商榷》合稱清代三大史學名著,是從前治史者案頭必備之書。其實,趙氏《陔余叢考》一書重在考辨風俗、名物流變,其參考價值不亞於《劄記》,我不時查閲。此外,如錢氏《十駕齋養新録》等都值得重視。。我確實從中轉引了一些史料,但主要依據當時没有標點本、只有綫裝本的《慶元條法事類》,是《叢考》不曾引用的。“文章合爲時而著”,《官吏經濟違法問題考察》或因“趨時”而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其學術性則相當差。范文瀾先生曾告誡我們,借古説今宜審慎。這類文章容易陷入“古今不分,漫談時政”的泥淖,是不宜多寫的。還是應當回歸唐宋變革這一關鍵性强且頗具牽動力的重大論題。
“老虎吃天,從何下手。”在拿不定主意的鬱悶之中,忽然想到南宋史家鄭樵《通志·氏族略》裏的一段話:“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閲。”這段名言研究者人人皆知,但似乎誰也没有加以深究,於是豁然開竅。到四川師大任教不久,我首論“取士不問家世”,再論“婚姻不問閥閲”。
斷代史研究應前後貫通,力爭做到“斷中有通”。然而説者容易做則難。因我的導師金先生主治唐史,我對唐代雖無研究,還算略知一二。有位前輩學者斷定,唐代“科舉制是最主要的做官途徑”,唐代“絶大部分都是科舉出身而致位宰相的”,唐代科舉制“替庶族取得政治地位大開了方便之門”。我在《略論唐代科舉制度的不成熟性》一文中,依據史實對這三個重要結論逐一提出異議,認爲這“是把北宋纔發生的事情提前到唐代”。唐代科舉取士“采名譽”“重素望”,“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榜出率皆權豪子弟”。新瓶裝舊酒,極而言之,科舉其名,薦舉其實。難怪唐人説:“文章世上爭開路,閥閲山東拄破天。”並進而指出,唐代死的抓住活的,新的生長着的官僚政治與舊的衰落着的門閥政治激烈較量,幾乎勢均力敵。《不成熟性》是爲《試論北宋“取士不問家世”》[注]載《四川師大學報》1982年第2期,人大複印資料《中國古代史》1982年第11期全文轉載。作鋪墊。《不問家世》一文對包括糊名等措施在內的北宋前期科舉改革作了概述,認爲宋代大體確立了“取士不問家世”“一切考諸試篇”的原則。宋人説:“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這一原則的確立堪稱我國古代選士制度史上的一大變革。至此,魏晉隋唐“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的時代告終,典型的官僚政治形成。進而指出,北宋的官僚政治不僅與“公門有公,卿門有卿”的魏晉門閥政治,以及“粗人以戰鬥取富貴”的五代武夫政治大異其趣,而且與隋唐的半門閥半官僚政治明顯不同。宋代政治亦可稱爲士大夫政治。隋唐政權是門閥士族等級與庶族地主階層的聯合政府,而兩宋王朝則是由科舉出身的讀書人所組成的士大夫階層當權。用宋朝人的話來説,即是:“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門閥士族等級具有排他性、世襲性,即所謂“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而士大夫階層則具有開放性、非世襲性,即所謂“驟得富貴”,“其家不傳”。從門閥政治到官僚政治,不失爲一大歷史性進步。學校制度與科舉制度相關聯。我與朱瑞熙合著《宋代國子學向太學的演變》一文,論述國子學即貴胄子弟專門學校轉化爲太學即士庶子弟混合學校的過程,旨在從學校制度演進的角度闡述唐宋變革。此文初稿的題目是《論宋代國子學的太學化》,完稿後寄請瑞熙斧正。他認爲“化”字不甚妥帖,改了標題,並有所增補,於是兩人共同署名。《宋代文化的相對普及》一文[注]載北大古文獻所、川大古籍所編:《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則揭示科舉、學校制度的變革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人尊孔孟,家家誦詩書”的新局面。陸放翁詩云:“力穡輸公上,藏書教子孫。”宋代這類耕讀家庭相當普遍。至於“人人”“家家”云云,係當時人的文學語言,未免言過其實。
關於宋代婚姻,起初只寫了三篇文章,都圍繞唐宋變革這個中心,具有明顯的連續性。第一篇《試論宋代“婚姻不問閥閲”》[注]載《歷史研究》1985年第6期,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1986年第2期全文轉載。,從“士庶婚姻浸成風俗”、後妃“不欲選於貴戚”、宗室婚姻“不限閥閲”三個方面予以闡述,藉以證明從前士庶不婚的陳規大體被打破。蘇東坡詠歎:“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户嫁崔盧。”陸放翁歌詠:“寒士邀同學,單門與議婚。”“不問閥閲”又問什麽?我的回答是:“不問閥閲”而“貴人物”。所謂“人物”即“賢才”,説穿了,是進士。王安石詩云:“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緑衣郎。”“緑衣郎”是新科進士的代稱,詩句形象地描述當時盛行的榜下擇婿風氣。第二篇《宋代的“榜下擇婿”之風》[注]載《未定稿》1987年第4期。對此有所闡釋,認爲這一風氣的形成表明社會心理由“尚姓”即“崇尚閥閲”轉向“尚官”即“崇尚官爵”,意味着歷史的車輪邁過嚴格的門閥政治時期,進入典型的官僚政治階段。與前代相比,宋代是更爲標準的郞才女貌時代。在當時,所謂郞才女貌,其實質是郞官女貌。“從一定意義上説,榜下擇婿無非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達到新的門當户對的一種特殊手段。”二程子説:“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據此,人們長期以來普遍認爲:唐時禮教束縛不嚴,宋人貞節觀念頗重。第三篇《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注]載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第3集,臺灣稻香出版社1993年版。對上述傳統説法提出異議,指出:宋代婦女再嫁者仍然較多,法律在原則上允許婦女再嫁,輿論並不籠統譴責婦女改嫁,二程子這句“名言”對宋代社會的實際影響並不大。進而認爲:宋代不是貞節觀念驟然增長、婦女地位急轉直下的時期;理學是宋代的官方哲學和主要統治思想一説並不確切;理學興起於兩宋,適應時代需要,體現時代精神,自有其歷史的正當性,其流弊主要在明清。人們通常認同:“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會進步與否的天然尺度。”本文的撰寫意圖在於説明由唐入宋並非意味着傳統社會從發展到停滯。
有關婚姻問題的史料相當零散,80年代没有電子檢索版,搜集史料很費功夫。宋人所撰類書幫了我不少忙。如“榜下擇婿”一詞,我首先是從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科舉門》裏讀到的。然後再查《宋史》列傳、墓誌銘等傳記資料,這類現象相當普遍。有關宋人筆記對典型事例有繪聲繪色的描述。而“未第不娶”這一“家訓”或“志向”以及“晚娶甚善”“壯年不嫁”之類則出自《事類備要》前集《婚禮門》。唐、宋兩代的改嫁婦女究竟孰多孰少?舉例論證法説服力太差,應當有個較爲具體一些的數量性概念。别無他法,只得採用抽樣考察法。《太平廣記》與《夷堅志》是兩種性質相近的小説集,分别反映唐、宋社會的實情。我將兩種書中所載再嫁、三嫁婦女一一查出,列爲表格,得出的結論是:宋代改嫁婦女不比唐代少,南宋改嫁婦女甚至多於北宋。總之,在當時的條件下,史料根本無法網羅殆盡,只能力爭做到説明問題而已。
上述三篇文章發表後,一家出版社約我寫本書,暫名爲《兩宋婚姻》。於是我將探討範圍擴展到族際婚、中表婚、異輩婚、收繼婚以及進士賣婚、宗室賣婚、商賈買婚、“婚嫁失時”即大男大女等問題。這本書只有14萬字,最後定名爲《婚姻與社會·宋代》,因故改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首先撰文推薦這本小書的是同門師弟魏明孔研究員,他將此書稱爲“一幅多彩的宋代社會生活圖”。好友趙葆寓編審隨後以“開拓宋史研究的新領域”[注]載《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5期。爲題,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書評。臺灣學者黄寬重研究員在《新史學》上也有書評[注]載《新史學》第5卷第1期,1991年3月。。師弟李華瑞教授後來回顧道:“20世紀末以前,討論問題直接與唐宋變革論聯繫並加以肯定的學術論著,大致只有張邦煒先生的《婚姻與社會·宋代》。”[注]李華瑞:《“唐宋變革論”對國內宋史研究的影響》,《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1期。這些評議出自“關係户”之口,不一定很客觀。當時物流不暢,這本書成都賣不掉,外地買不到。時任北大歷史系總支書記的鄭必俊老師到鄧廣銘先生家中借來複印。鄧老開玩笑説:你的書在北大,讀的是複印本。可能是書評影響所致,臺灣宋史座談會召集人宋晞先生在港、臺兩地無法買到此書,輾轉通過其學生、香港梁天錫教授同我取得聯繫。我立即以拙著相贈,從此與宋先生相識。他早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師從張蔭麟、陳樂素二老,後來曾任中國文化大學校長,1995年邀請我到臺北參加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經過一段時間的探討,我對唐宋變革論形成了一些總體性的初步認識:唐宋之際確實發生了一場具有劃階段意義的變革。它不是一種社會制度代替另一種社會制度,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社會革命。它不是以突變的形式出現,而是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漸進性長過程,大致開始於中唐前後,基本完成於北宋前期,可以北宋的建立爲路標。它不是下降型轉化,而是上昇型運動,並不意味着中國傳統社會從發展到停滯,相反標誌着宋代進入了傳統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新階段。對於這場變革的程度和意義既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它與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變革很難相提並論。《兩宋時期的社會流動》一文[注]載《四川師大學報》1989年第2期,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1989年第5期全文轉載。又有所補充:“傳統社會是個封閉式的凝固態社會,猶如一潭死水,人們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以至職業一概具有非運動性。宋代與前代相比,呈現出較爲明顯的社會流動傾向。”並將其表現歸納爲三個方面:“政治上:‘賤不必不貴’”;“經濟上:‘貧不必不富’”;“職業上:‘士多出於商’”。認爲:社會流動傾向“不僅使人們的門第觀念相對淡化,而且給宋代社會帶來某些生氣。”後來唐宋變革研究有走向泛化的跡象,臺灣學者柳立言研究員及時指出:所謂變革“不是一般的轉變,而是一些巨變,這些巨變有一個特色,就是它們對政治、社會和經濟等造成‘根本的改變’。”我深表贊同,“唐宋變革是個筐,一切變化往裏裝”的偏向應當避免。如果將唐宋變革論抬高到指導思想的高度,勢必掉入另一類以論帶史的窠臼。
四、“被牽着鼻子走”
舉一反三,由此及彼。八九十年代,唐宋變革研究領域新的學術增長點爲數不少,可開掘的論題較多。我在《婚姻》一書的《結語》中列舉了一些:“諸如學校方面的‘廣開來學之路’、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學術方面的從漢學到宋學、文學方面的從‘雅’到‘俗’、書法方面的從碑書爲主到帖書爲主、繪畫方面的從宗教畫、政治畫爲主到山水畫、花鳥畫爲主等等。”然而我未能朝着這個可持續性强的方向繼續前進,後來只是應李華瑞之邀,寫了篇述評性文字《唐宋變革論與宋代社會史研究》以及《唐宋變革論的首倡者及其他》[注]載《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1期。。有學生問我:爲什麽未能繼續?我説了句玩笑話:“被别人牽着鼻子走了。”[注]這類事情較多,如佐竹靖彦、李裕民兩位教授約我寫《中國大陸近十年來的宋史研究》,載日本《中國史學》創刊卷,1991年10月。我從事學術探討,自來是個“小生産者”,有一條原則是一般不與他人合作,以免因署名等問題扯皮,出了問題,互相推諉。然而這條原則在80年代後期被打破。
1987年,從南開開會返回成都,路過北京,王曾瑜約我同戴静華、朱瑞熙兩位一道撰寫《遼宋金西夏社會生活史》。[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版,2005年再版。酈家駒先生在座,他很贊成。專案是曾瑜從歷史所領來的,按照慣例,主編非曾瑜莫屬。但他表示不設主編,四人共同署名,以年齡爲序,他一定排在最後。時下物欲橫流,曾瑜看薄名利。話説到這個份上,除應允外,無話可説。後因戴静華先生過早去世,曾瑜邀請吴天墀先生的兩大弟子劉複生、蔡崇榜教授參與,署名原則不變。按照曾瑜的安排,我承擔婚姻、婦女、生育、養老、喪葬等章節。因而寫下《遼宋西夏金時期少數民族的婚姻制度與習俗》[注]載《社會科學研究》1998年第6期,人大復印資料《宋遼金元史》1999年第1期全文轉載。等描述性文字,算是正式着手之前的“熱身”。本來這個項目正好與唐宋變革論相結合,但不能“一切變化往裏裝”。何况曾瑜不大贊成唐宋變革論,既然合作,在一本書裏就要保持基本觀點的大體一致。在進行這一項目時,我雖然也探究了一些問題,如避回煞、燒紙錢、看風水、做道場等喪葬習俗,以及宋代盛行火葬的原因等。通常認爲,宋代火葬盛行是佛教傳入中國的結果。其實是有問題的:佛教從漢代傳入,到唐代後期已達九百年之久,爲什麽火葬者屈指可數?在我看來,火葬習俗形成於五代十國時期,關鍵在於“五季禮廢樂壞”,包括死者以“入土爲安”在內的不少傳統觀念動揺。加之適逢戰亂,生者尚且苟延殘喘,死者後事只能從簡,火葬在變亂中悄然成爲風俗。火葬是契丹、党項、烏蠻、末些蠻的原始葬俗,而吐蕃受党項影響,女真受契丹、漢族的共同影響,轉而實行火葬。由於各民族之間喪葬習俗的相互交流,無論漢族還是少數民族,火葬者越來越多。於是宋遼西夏金時期成爲我國歷史上火葬最爲盛行的時期。然而這些探討大體都不着眼於唐宋變革。
我與黄寬重先生1989年冬天相識於重慶釣魚城研討會上,他認爲我提交研討會的論文《宋代的公主》品質不錯,帶回臺灣發表。上世紀90年代中,寬重與柳立言先生邀請陶晉生、馬伯良、佐竹靖彦等十二位中外宋史學者共同探討“宋代家族與社會”。我在被邀請者之中,可能與我曾經爲《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撰寫“封建家庭制度”條目有關,是酈家駒先生要我寫的。我將封建家庭制度的發展過程歸納爲習慣規範、以禮代法、以禮入法三個階段,將其特點概括爲尊長卑幼、夫主妻從、嫡貴庶賤、親親疏疏,認爲這一制度“突出父權,旨在强化皇權”;“維繫家庭,旨在加固根基”。“皇帝大家長,家庭小朝廷。”我兒時在傳統大家庭裏生活過,多少有些實感,特别對尊長卑幼這一點,體會較深。與今天的“小皇帝”們不同,我在祖父面前,没有坐的資格,只能畢恭畢敬地站立,小小年紀就領教過“家法”的滋味:“楠竹筍子煎坐墩肉”(家鄉俗語對“打屁股”的戲稱)。我習慣於中觀研究,多採用舉例式的論證方法。這種方法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寬重這次要求採用個案研究的方法,對我來説是一次新方法的訓練和嘗試。説真話,我對這一研究方法很不習慣。於是依樣畫葫盧,按照寬重《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的模式,寫下《宋代鹽泉蘇氏剖析》[注]載《新史學》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宋元時期的仁壽——崇仁虞氏家族研究》[注]載中研院史語所編《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98年6月印行。兩文。但我不願止步於對蘇氏、虞氏家族作一般性描述,總想寫出其特色,如將蘇氏、虞氏分别定性爲政治型名門、學術型名門,並作了一些論證。參與宋代家族個案研究,我有兩條體會。一條是宋代家族研究從前往往以累世聚居於一地、財産爲家族所共有的“義門”爲重點,其實宋代家族的主要形態不是共財同炊,而是别籍異財。另一條是任何方法都既有其長又有其短,應揚其長而避其短。記得前人曾説,漢學其特色爲考證,其流弊爲煩瑣,宋學其特色爲玄想,其流弊爲空疏。如果能入於漢學,出於宋學或入於宋學,出於漢學,固然很好,但只怕魚與熊掌很難兼得。宋代家族個案研究後來出現千篇一律的公式化傾向,任何家族的演進歷程無非是崛起—興盛—衰敗三部曲,探究其原因不外乎從家産、教育、仕進、婚姻、交遊等方面着手。個案研究的流弊顯現出來,寬重對此有所批評[注]可參看拙稿:《黄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讀後》,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與方法相比,態度更重要。“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堅守,“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潜沉,尤其要緊。
因我曾發表《再嫁》《公主》以及《宋真宗劉皇后其人其事》等文,被誤認爲婦女史探討者,柳田節子、伊沛霞、鮑家麟、劉静貞乃至高彦頤等研究女性史的女性學者視我爲同行。鄧小南教授與我1996年一道到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訪問,於是熟悉起來。她一度致力於性别史研究,約我參與,因而寫下少量有關文章。中國古代婦女史研究從前從反對男尊女卑、提倡尊重女權的美好意願出發,將婦女史視爲“一部婦女被摧殘的歷史”,其正確性很難置疑。進而引申爲古代婦女“無知識、無職業、無意志、無人格”,只怕就過猶不及,適得其反了。我在《兩宋婦女的歷史貢獻》一文中,不贊成古代婦女的全部生活無非是圍着鍋臺轉、生兒育女,認爲:兩宋時期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婦女的歷史貢獻是多方面的,包括參與政治、發展經濟、繁榮文化、主持家政等等。上世紀90年代以後,性學書籍在社會上廣爲流行。有關書籍往往拿歷史説事,把唐代渲染爲性自由奔放階段,將宋代斥責爲性禁錮最爲嚴厲的時期,並認爲古代性學鼎盛於隋唐,阻滯於兩宋。我在《兩宋時期的性問題》一文[注]載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編《唐宋女性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8月版。中認爲:相當開放的敦煌性文化並不代表唐代全國各地的整體狀况。如僅以某一特定地域而論,宋代嶺南某些地方盛行的“卷伴”“聽氣”“飛駝”“多妻”等習俗表明,其性生活的開放程度與唐代敦煌地區不相上下。從總體狀態上説,唐、宋兩代均處於性壓狀態,並無實質性的不同,只有程度上的差異。同時指出:宋代理學家的主流性觀念既非縱欲,也非禁欲,而是節欲。他們的節欲主張無可厚非。南宋養生學家李鵬飛提出的“欲不可絶”“欲不可早”“欲不可縱”“欲不可强”等原則相當精闢,在中國性學發展史上應當佔有一席之地。小南後來似乎與婦女史告别,我問她原因何在,她的回答大致是:海外傳入的新觀點太多,跟不上。小南尚且如此感嘆,至於我更無跟進的可能。上述涉及婦女方面的文章,後來大多收入人民出版社2003年印行的個人論文集《宋代婚姻家族史論》。劉複生教授囑其弟子韋兵博士撰寫書評,題爲《從婚姻家族看唐宋之變》。[注]韋兵:《從婚姻家族看唐宋之變》,載《中國圖書評論》2006年第2期。
五、轉向王朝史
或許與“將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趕下舞臺”的號召有關,我對王朝史素來無興趣。之所以轉向王朝史,是被好友趙葆寓“牽着鼻子走”。葆寓出身北大,爲人耿介,好學深思。我80年代初與他相識,一見如故。1987年,歷史所周遠廉、宋家鈺兩位川籍歷史學者張羅編寫多卷本《中國封建王朝興亡史》,兩宋卷由葆寓承擔。葆寓要我寫北宋,他寫南宋,我二話没説,慨然應允。誰知葆寓一病不起,只得由我一人獨自承擔。我懷着緬懷好友的心情,花了幾年功夫,將兩宋歷史發展的歷程較爲認真地梳理了一遍。此書對有宋一朝的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以及關鍵性制度和國策都有概述和評介,可能因此而被小南列爲北大歷史系本科生學習宋史的參考書之一,一些大學歷史系也跟着如此。因爲是集體著作,完稿時間一開始就約定。爲了如約按期完成,梳理重大事件只能依靠以事件爲中心的紀事本末體史書。當時《長編紀事本末》一類的書籍較難找,篇幅又大,我主要參考《宋史紀事本末》。《本末》不具有原始性,可作爲入門書,是不能作爲基本史料予以引用的。但它畢竟將重大事件從頭到尾,集中記叙,爲我編寫王朝史提供了方便。至於如何評議這些事件,《本末》中華書局1955年版每卷之後所附“張溥論正”,多少給了我一些啟示,並參讀王船山《宋論》。至於吕中《宋大事記講義》之類,當時很難找到。多卷本《王朝興亡史》出版後獲中國圖書獎。但以兩宋卷而論,至多只能體現80年代的研究水準,在今天看來,相當“小兒科”,有待釐正深化細化的問題很多。進入新世紀以後,鄧小南發表《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再出發”》等文。在小南的引領和感召下,她的弟子們和研究團隊取得了令人囑目的成就。至於整個宋史學界,有關著述比比皆是,其中有份量者不少。兩宋王朝史到了應該改寫、重寫的時候。
我那本王朝史是概要性的,惟其如此,充實擴展的餘地較大,因而此後臨時要趕寫一篇什麽文章,雖不能説信手拈來,但確實比較容易。諸如《韓侂胄平議》《宋孝宗簡論》《吴曦叛宋原因何在》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均可視爲兩宋王朝史的副産品。然而其主要副産品當推一本書和一篇論文。
一本書是《宋代皇親與政治》[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書名可改爲《兩宋內朝研究》,和《婚姻與社會·宋代》一樣,是以論文爲基礎擴充而成。我先前著有《論宋代“無內亂”》[注]載《四川師大學報》1988年第1期,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1988年第2期全文轉載。《宋代對宗室的防範》[注]載《首都師大學報》1988年第1期,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1988年第3期全文轉載。《宋朝的“待外戚之法”》[注]載鄧廣銘、漆俠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北宋宦官問題辨析》[注]載鄧廣銘、漆俠主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1993年第3期全文轉載。《兩宋無內朝論》[注]載《河北學刊》1994年第1期,人大複印資料《中國古代史》(二)1994年第3期全文轉載。等文。宋代的政治制度可以分爲外朝即官僚系統與內朝即皇親系統兩大體系。前者可謂熱門話題,研究者們雲集於此,後者則“門前冷落鞍馬稀”。內朝具有兩大基本特徵,一是由皇帝的親屬或親信組成,二是淩駕於以宰相爲首的外朝之上。與外朝相比,內朝更能體現傳統政治“家天下”統治的屬性。宋人説:“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宋代最高統治者汲取這一歷史教訓,對皇親國戚乃至家奴的權勢都作了較爲嚴格的制度性限制。這本小書分爲宗室、後妃、外戚、宦官四個部分,分别揭示宋代宗室任職受限、後妃較少插手朝政、外戚基本不預政、兩宋大體無閹禍四個歷史現象,從而得出了宋代大體無內朝、基本無內亂兩大結論。宋代皇親國戚之間雖有權力之爭,但不曾激化到兵戎相見的程度,最高權力的轉移總的來説比較平穩。宋人炫耀:“本朝超越古今”,“百年無內亂”。宋代大體無內朝意味着基本無內亂,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內部較爲安定的社會環境作爲一個重要因素,促成了宋代社會經濟的騰飛和文化的高漲。本書出版後,讓我感動的是年事已高、健康堪憂的馮漢鏞先生獎掖後學,生前主動寫下《〈宋代皇親與政治〉書後》,予以推薦。事前事後均未告知,是别人看到後告訴我的。師弟、西北師大胡小鵬教授以及河南大學苗書梅、北京師大游彪教授也分别在刊物上撰文評介[注]遊彪:《〈宋代皇親與政治〉評介》,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4年第10期。。游彪早年在四川師大歷史系念本科,出於師生情誼,難免言不由衷。
一篇論文是《論宋代的皇權與相權》[注]載《四川師大學報》1994年第2期,人大複印資料《中國古代史》(二)1994年第6期全文轉載。。宋代皇權與相權的關係,自1942年錢穆老先生《論宋代相權》一文問世以來,學界一概認同錢老的皇權加强、相權削弱論。80年代中期,王瑞來教授反其道而行之,針鋒相對提出相權加强、皇權削弱説。在撰寫兩宋王朝史的過程中,我結合史實思考這個問題,得出第三種結論,寫下《論宋代的皇權與相權》一文。此文指出:兩種此强彼弱的觀點看似截然相反,其實其出發點驚人的一致,都立足於皇權與相權的絶對對立,只怕有“在絶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恩格斯語)之嫌。皇權與相權並非兩種平行的權力,作爲最高行政權的相權從屬並服務於作爲最高統治權的皇權,兩者相互依存。宋代在通常情况下,皇權和相權都有所加强。皇權的强化表現在皇帝的地位相當穩固,没有誰能夠同他分庭抗禮,因而宋代被稱爲“看不見篡奪的時代”。相權的强化表現在以宰相爲首的外朝能夠比較有效地防止皇帝濫用權力,作爲皇帝分割外朝權力工具的內朝大體上不存在。何以如此,應從宋代當權的士大夫階層的特質中去尋求。與從前的門閥士族相比,由科舉出身的讀書人所組成的宋代士大夫階層個體力量雖小,群體力量卻大,因而在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能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一個問題居然有三種答案,引起有關學者關注。趙儷生老師的高足、我的師弟葛金芳教授來信表示贊同,信中有“讀後徹夜難眠,茅塞頓開”等相當誇張的語言,並囑其弟子桂始馨博士予以評介,認爲此文“突破了皇權與相權此强彼弱、簡單對立的舊框架,將二者作爲一個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來考察”。
我們那套多卷本《王朝興亡史》的出版經過若干年的周折,最終由人民出版社張秀平編審推薦給廣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秀平是我蘭大歷史系的先後同學,她於90年代中期,約我寫一本有關宋徽宗及其大臣們的書。我起初遲疑,最終接受。遲疑的原因是梁啓超、魯迅都强調,歷史不應當是帝王將相的家譜。因而吉林文史出版社曾約我寫一本宋朝帝王傳,我托故婉謝。而最終接受則出自友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花了不少時間,探究徽、欽兩朝。但只有點滴體會,始終未能形成系統性的新見,於是慚愧地交了白卷。這些點滴體會陸續寫成7篇文章,主要探討兩個問題。一個是:徽宗初政爲什麽受到好評?徽宗即位之初,人們寄予厚望。黄山谷詩云:“從此滂沱遍枯槁,愛民天子似仁宗。”後來博得贊譽,王船山説:“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觀。”其原因之一是徽宗即位具有極大的偶然性,並無深厚根基,不得不謹慎行事,推行平衡新、舊兩黨的建中之政。《宋徽宗角色錯位的來由》《關於建中之政》兩文對此有所揭示。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徽宗初年“內外皆有異意之人”,他更不敢膽大妄爲。據《宋徽宗初年的政爭》一文[注]載《西北師大學報》2004年第1期,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04年第2期全文轉載。考察,其反對者上層有蔡王、章惇集團,中下層有趙諗及其同黨。另一個是:北宋爲什麽亡國?並非落後挨打,實因腐敗亡國。如北宋晚期士大夫階層集體墮落。關鍵在於最高統治集團極度腐敗,以致民怨鼎沸,民變連綿。《北宋亡國的緣由》一文指出,徽宗唱的不是老調子,而是唱着“新”調子,但依然無法逃出亡國的命運。北宋晚期之所以腐敗,《北宋亡國與權力膨脹》一文[注]載《天府新論》2000年第1期,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00年第3期全文轉載。認爲,是由於北宋開國以來所形成的隨意性較大、具有脆弱性的權力制約體系,到徽宗時全面崩潰,皇權以及內朝、外朝的權力一概惡性膨脹。“靖康岌岌,外猘內訌。”至於靖康內訌,雖然次要,也不失爲一個導致北宋亡國的一個具體原因。大難臨頭、國破家亡之際,徽宗、欽宗居然反目,父子勾心鬥角,欽宗甚至將其父親徽宗變相軟禁。對此,《靖康內訌剖析》一文[注]載《四川師大學報》2001年第3期,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01年第3期全文轉載。有較爲詳盡的考察。這些文章大多收入人民出版社2005年印行的《宋代政治文化史論》。我手中無“資源”,兩本個人論文集的出版主要靠當時本單位負責人楊天宏教授奔波。[注]我無科研經費,連複印資料也是用他的經費。此書出版後,路育松編審在《書品》2006年第2期《書苑擷英》欄目中予以推薦。著有歷史小説《柔福帝姬》的米蘭女士以《撥開春秋筆法的迷霧》爲題,以本報書評人的身份,在《南方都市報》發表書評。[注]米蘭:《撥開春秋筆法的迷霧》,載《南方都市報》2005年12月5日。她曾在《網易·讀書頻道》工作,約我開個專欄,暫名“兩宋逸聞”。我畢竟比較古板,又不願意貼近現實,其結果只能是點擊率太低,因而作罷。我與這位女士始終未曾謀面,至今不知其真名實姓。
六、休息之外動點腦筋
從前有句豪言壯語:“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座。”或許與當年教師退休制度不完善有關,是“英雄時代”的産物。如今屬於“凡人時代”,只怕人人都應當退休。我是2008年68歲那年退休的。同仁們退休後,有的金盆洗手,有的退而不休。而我從自己的健康狀况、學術積累等實際情况出發,處於兩者之間。據説不動腦筋要癡呆。李華瑞在首都師大歷史學院替我找了點力所能及的事做,於是休息之外,動點腦筋。幾年來,因無工作之累,寫些緬懷一類的文章,如《令人懷念的“三嚴”史家》[注]載張世林編《想念鄧廣銘》,新世紀出版社2012年。《川內開花川外紅》[注]載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吴天墀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置身功利外,心在學問中》[注]載鄧小南等主編《大節落落,高文炳炳——劉浦江教授紀念文集》,中華書局2015年。《爲人沉穩,待人寬厚》《宋學的眼光,漢學的功力》等等。除此而外,姑且可稱爲學術論文的寫了十來篇,大多刊載本校學報。[注]人過中年以後我一般不投稿,要投也往往就近投請《四川師大學報》刊登。1980年以來在本校學報發表論文二十六篇,查手機“壹學者”可知,其中十三篇人大複印資料全文轉載。而人大複印資料全文轉載我的論文總共不過二十五篇。據手機“中知網”統計,我在《歷史研究》上發表的《試論宋代“婚姻不問閥閲”》被引用十五次,而在《四川師大學報》發表的《論宋代的皇權和相權》《論北宋晚期的士風》《兩宋時期的社會流動》《兩宋火葬何以蔚然成風》《兩宋時期的喪葬陋俗》則分别被引用五十三、四十二、二十四、二十一、十六次。《不問閥閲》一文引用量較小,原因或許是有關研究者徑直引用《婚姻與社會·宋代》一書。附此一筆,試圖説明當前實行的期刊分等制不一定合理。對此,人們議論多多,這裏只是增添一個實例而已。可能是因爲挂名編委吧,其中七篇被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全文轉載。人大報刊資料中心近年創辦《歷史學文摘》,號稱“我國首家歷史類文摘學術期刊”,從七篇中又選登了五篇。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昇。老來似乎返樸歸真,又同青年時代一樣,有一股不輕信、不盲從的勁頭,所寫文章大多具有商榷性。不同的是,理性隨着閲歷的增多而增長,認爲應當盡力做到不趨時、不迎合、不走極端、不殺偏鋒。雖然寫了若干商榷性文章,但絶不使用傷害性語言,並不具有戰鬥性。
上世紀80年代以後,我寫的商榷文章比重明顯减少,自有其緣故。80年代前期,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漆俠先生在鄭州舉行的宋史研討會上提出“西不如東”説,將川峽四路一概劃入西部落後地區。漆先生徵詢我的意見,我説:宋代四川既有足以同兩浙路媲美的成都府路,也有同廣南西路一樣落後的夔州路。後來與賈大泉合著《宋代四川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一文[注]載孫毓棠等主編《平準學刊》第2輯,中國商業出版社1987年版。,由我執筆,史料主要靠大泉提供。大泉年長於我,比我“成熟”。他告誡我:自説自話,不要商榷。因而誰也看不出這是一篇商榷文章。唯獨漆先生敏感,他採納我們的意見,在其著作中補充了一句:“宋代西部地區,除成都府路、漢中盆地以及梓州路遂寧等河谷地(即所謂的“壩子”)而外。”[注]漆俠:《宋代經濟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頁。另一件是我那篇《略論唐代科舉制度的不成熟性》提交在成都召開的唐史研討會,指名道姓,坦誠商榷。消息傳來,老先生雖然無所謂,但其弟子們頗爲不滿。文章後來被胡如雷先生選入《唐史論文集》,我將老先生的姓名删掉,只針對觀點。當年我至多只是個“中生代”,寫商榷文章,不能不有所顧忌。如今已是退休老者,無功利可言,顧忌少了。
宋朝從前備受貶損,而今博得贊美,有學者甚至認爲:“宋朝達到中國文明的頂峰。”並相應地提出宋代農民歡樂説、宋代婦女幸福説、宋代官場廉潔説、宋代士大夫人格高尚説,盛贊宋朝統治者實行君相互制制、黨派互監制,推行高薪養廉、保障言論自由等政策。這些説法只怕相當偏頗,人們難免會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何來頂峰?一家一姓坐天下的趙宋王朝真的好上天了麽?“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謬誤。”連我這個較早反對宋朝積貧積弱説,認爲宋朝實現了“兩個超越”的老年人也坐不住了,起而寫下《不必美化趙宋王朝——宋代頂峰論獻疑》一文[注]《四川師大學報》2011年第6期,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12年第2期全文轉載,《歷史學文摘》2012年第2期摘登。,依據基本史實對上述種種説法一一提出異議。“大宋”一詞,我少年時代曾聽説,是在看川戲時。《五台會兄》楊五郎唱:“大宋朝有一個火山王。”《三盡忠》文天祥道白:“老天爺,你莫非要滅大宋!”北宋統一規模有限,南宋只是半壁河山,將宋朝稱爲“大宋”,分明是不確切的。“橫看成嶺側成峰”,歷史是多面的,認識是多元的,爭議還會繼續。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朱瑞熙、王曾瑜、葛金芳、虞雲國等不少同道對此文持肯定態度,何忠禮、許懷林兩位教授還以不同形式予以再傳播。而今“厓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以後無華夏”之説流傳很廣,甚至認爲“元朝根本不是中國的一個朝代”。究其根源,在於孫中山的“兩次亡國”論。爲此,我在《應當怎樣看待宋元易代》一文中,扼要剖析了孫中山從漢民族主義者轉化爲中華民族主義者的過程,認爲:“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後發展變化較大。孫中山是中華文明從未中斷論的首倡者之一,他較早採用‘中華民族’新概念,力主‘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譚其驤先生説得好:不應當“以宋朝人自居”。我們作爲現代的中國人,固然是宋朝人的後代,但遼朝人、西夏人、金朝人、大理人、吐蕃人、元朝人都是我們的祖先。我們不能僅僅站在宋朝人的立場上看待歷史問題。“厓山之後無中國”的感嘆並未完整準確地表達宋朝遺民的憤懣心理,有替腐朽的晚宋王朝唱挽歌之嫌。長期以來,人們對元代文化誤解較多。元代“漢文化不受尊崇”,便是一大誤解。元代社會有退有進,中華文明在元代又有新的發展和進步。明朝取代元朝後立即着手官修《元史》以及傳統的“二十四史”之説都是對元朝係中國歷史上的正統王朝的認定。
關於宋代的士大夫和富民,均有兩種絶對對立的觀點。對於前者,持“君子論”者有之,將宋代盛贊爲“君子時代”,頌揚“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是中國歷史上最高傲、最有骨氣的一群知識分子”。持“糞土論”者亦有之,斷言宋代士大夫大多數“是卑鄙齷齪之徒,更有巨惡大憝之輩”,將士大夫從總體上痛斥爲“群小”,比喻爲“糞土”。對於後者,持“中堅論”者有之,將富民認定爲“社會中堅力量”。持“豪橫論”者亦有之,將富民一概斥責爲“奸富”,一言以蔽之,爲富不仁。我個人認爲,兩種觀點各走極端,都具有片面性,於是寫下《君子歟糞土歟——關於宋代士大夫問題的一些再思考》[注]載《人文雜誌》2013年第7期,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13年第5期全文轉載,《歷史學文摘》2013年第4期摘登。《宋代富民問題斷想》[注]載《四川師大學報》2012年第4期,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12年第6期全文轉載,《歷史學文摘》2012年第4期摘登。兩文。翦伯贊先生半個世紀以前就告誡我們:“不要見封建就反,見地主就罵。”今天我們能“見士大夫就反,見富民就罵”嗎?反之亦然,也不能“見士大夫就贊,見富民就捧”吧。我特别不贊成將以土地擁有者爲主的宋代富民稱爲主要納税人一説,當時的田賦分明是地租的分割,是地租中的一小部分。不應當把勞苦大衆排除在外,片面地將富民視爲社會的中堅力量。至於《昏君乎明君乎——孟昶形象問題的史源學思考》一文,並非商榷性文章,旨在剖析後蜀後主孟昶兩種不同形象的形成背景及演變路徑,並探究其原因,以揭示蜀地民衆對北宋朝廷從對立到認同的歷史過程。
《重文輕武:趙宋王朝的潜規則》一文[注]載《四川師大學報》2015年第1期,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15年第2期全文轉載,《歷史學文摘》2015年第2期摘登。開篇就説:“開拓新領域與深化舊論題是推進學術研究的兩翼,前者固然尤其重要,後者似乎也不可或缺。舊論題往往在本學科領域具有繞不過、避不開的關鍵性,且其中不無某些值得再探究的新問題。”相比之下,我比較看重舊論題,這或許是出於無力開拓新領域的老年人的偏見。但我在這一舊論題中試圖寫出一些新意,如文武並重是趙宋王朝半真半假的真宣言,重文輕武則是其心照不宣的潜意識,以及文臣、武官兩大群體既非一概勢如水火,也非各自鐵板一塊之類。是否達到預期目標,只能由讀者去評判。《讓民衆充滿獲得感——王安石的鄞縣施政與熙甯變法之異同》一文除力求“舊中有新”而外,也多少表達了一點對社會現實的有限關懷。《戰時狀態與南宋社會述略》一文[注]載《西北師大學報》2014年第1期,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14年第2期全文轉載,《歷史學文摘》2014年第2期摘登。此文依據2013年8月19日在河北大學的講稿整理而成。這次講演《光明日報》2013年9月9日第5版《光明論壇》欄目曾以《戰時狀態:南宋歷史的大局》爲題,用整版篇幅摘要刊出。兩篇文章因來源相同,不免有某些重合之處。本想提出一個新論題:戰時狀態是認知南宋歷史的一把鑰匙。認爲:從總體上説,兩宋社會經歷了從和平環境到戰時狀態的演變。與大局的變换相適應,兩宋的時代主題也經歷了從變法圖强到救亡圖存的轉化。長期處於戰時狀態或准戰時狀態這一南宋歷史的大局,制約並牽動着南宋社會的諸多(不是一切)方面。並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舉例式地作了一些粗略考察。文章發表後,纔偶然在網上發現黄寬重似乎有篇論文,題爲《絶境求生——南宋政治文化的蜕變》。我當面詢問寬重,他説前些年在人民大學只是講講而已,並未形成文字。內容是否雷同,没有細問。
拉拉雜雜,寫得已經不少,最後再説一件事。我的《兩宋史散論》電子版是四川師大電子出版社爲獲上級批准於2009年趕緊製作的,無版權頁。因趕得太急,其中錯字相當多。北京師大特聘教授葛金芳師弟是個感情色彩極濃的性情中人。他來信説:“此書並不‘散’,而是有主綫貫穿的,此綫即‘唐宋變革論’。兄在宋史研究中所抓皆大問題、關鍵問題。經濟如租佃代莊園,政治如‘尚姓’到‘尚官’,社會如‘婚姻不問閥閲’和‘榜下擇婿’,文化如國子學向太學的轉變及文化普及,軍事如‘樞密院——三衙——都部署’體系等,皆抓住大關節、大趨勢。可見‘眼光’與‘功夫’兩者同等重要,功夫中有眼光,眼光又統率功夫。”大概是我退休不久,第二天又是我的七十歲生日,師弟要給我這個不成功人士一點安慰,信中過分的話不少。他還説:“‘二十五字真言’,既不失傳統,又與時俱進,既是吾兄爲人之寫照,又是後學應學之榜樣。”所謂“二十五字真言”是怎麽一回事呢?上世紀末,河南大學劉坤太教授因開辦中國宋史研究網站,來信問我的齋名和自語。我的回答是:“我這個人糊裏糊塗過日子,没有什麽齋名。我對歷史現象乃至社會現實一概看不真切,一切恍恍惚惚,如果一定要取個齋名,姑且名之曰:‘恍惚齋’。至於自語,暫且寫下二十五個字:‘遇事灑脱些,做事認真些,待人坦誠些,性情開朗些,生活瀟灑些。’”就此打住,不再囉嗦。一句話:此生還算幸運,多數時間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自娱自樂,樂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