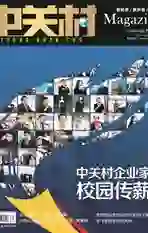廖理纯:胸怀生态,墨者无悔
2017-01-19明星
明星

廖理纯说,他立志要做一名墨者。他要和众多志愿者们一起呼唤志愿精神,唤醒国人心中的无私和善良,为国家搭建一座大义、相爱、和合的桥梁。
人最难面对的是名和利,最难看懂的是生和死。
2016年4月,育林治沙公益人物、走进崇高先遣团团长廖理纯站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堂上,面对数百位莘莘学子,袒露自己的心声。“既然人生的长度有限,那就让它的宽度延长。让我们用无私无畏去战胜自私自利,重视信仰,追随英雄,让自己人生无憾的同时,为后代保留出生存的空间。”
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像墨者那样,奉献自己,护佑后人,让人性散发出更耀眼的光辉。
悟
“我小的时候,不知道生命是有尽头的,认为自己可以永远快乐地活着。”廖理纯对作者说。
1965年,他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生,母亲毕业于清华大学,父亲在国防部五院从事导弹研究工作。“根红苗正”,加上老师、父母的谆谆教导,他从清华附中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之后,他没有选择像父亲那样,在航空航天领域里翱翔,而是在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在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创业事迹感召下,进入联想,从一名基层员工做起,凭借自己的努力,24岁就已升任为联想集团广州分公司经理,成为当时柳传志“门下三杰”。
直到1993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我国正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创业的热潮在全国空前高涨。廖理纯从零开始,创办北京晨拓联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十几年的时间里,廖理纯和他的团队一路开拓进取,从最初仅有3名员工、年营业额300万元的情形,发展到后来员工百余人、年最高营业额6亿元的局面,销售渠道遍布全国。
少年时代的简单快乐,青年时代的英姿勃发,让廖理纯不知“愁”为何滋味,也不明“生死”为何物。
但是,几次直面生死的经历后,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换位思考人生。
2002年5月7日,廖理纯一位多年不见的好友到北京出差,期间与他小聚,当晚乘飞机赶回大连。就在第二天,一个噩耗传入廖理纯的耳朵,昨晚飞回大连的航班失事,朋友也不幸罹难。“前一天还与我推杯换盏、生龙活虎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至今,他还为好友的离去感到惋惜。
如果说这次遭遇让他感知到生命的脆弱,那另一件事的发生却让他彻底认清人都是要死的,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现实。
廖理纯似乎还没从“大连空难”中缓过神来,他从前的一位同窗,平时身体没什么毛病的一个人,因为突然的疼痛就医,第二天便死在了医院里。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他的同学还没步入不惑之年,就已年华逝去,纵使高官厚禄也无可奈何!同学父母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委托廖理纯替他们在火葬场捡的骨灰。
至今,他还对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进焚化炉前,还是身形完整的一个人,出来之后,就剩下累累白骨……”廖理纯捡起同学的腿骨、胸骨、脑骨中的一部分,递给火葬场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将骨头放进一个小麻布袋中用手一搓,骨头瞬间变成了粉末。廖理纯看着那皑皑的骨灰,神情恍惚,愣在原地,痛苦地说不出一句话。
“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啊?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很快也会这样?”从火葬场回来后,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他要好好琢磨一下应该怎么生怎么死的问题。
他是认认真真地想了很多,甚至想起外公在世时对他说的话。
那年外公80岁,身体瘫痪,只得常年卧床,随时有可能离开人世。有一天,外公突然指着桌上的台历对他说,“理纯,台历是不是每过一天撕下一张,撕下一张一天就过去了?”他回答:“是呀。”外公沉默良久后,感慨道:“唉!人的一生至多也就三万多张台历,当三万多张台历全撕完后,生命也就结束了。”
在那个年代,像外公活到八九十岁的年纪,很多人羡慕得很,都要对他说上一句“长寿是福啊!”但在外公眼里,这样活着很痛苦。这位老人的一生经历了中国从统一到割据、再从割据到统一,并不断完善壮大的过程。在临走的前几年里,老人一点都不快乐,他认为“大丈夫莫若战场马革裹尸还”。他很彷徨,也很害怕,怕的是再过十年,除了亲人以外不会再有人记得他了。
为了纾解外公的愁闷,廖理纯一有空儿就去找老人聊天。他清楚记得,老人最爱讲古今义士的光荣事迹,荆轲、文天祥、谭嗣同、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这些英雄都是老人敬重的榜样。他们将大义置于首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讲到激动之时,外公还会大声地吟诵,“云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在爷孙俩你一言我一语中,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外公笑了,那个缠绕在他心里的结,终于解开了。他说,人生不过是一个交棒和接棒的过程,把自己毕生的心得留给后人,让他们从中受益,得到启发,少走弯路。这不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吗?
当时廖理纯还年轻,不能完全体会其中的含义。直到身边同龄人的离开,关于生与死这个严肃的课题,再一次撞击他的心房,让他全身战栗。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不知死,又焉知生?就如美国文豪马克·吐温所言,“了解死亡的人会更加坦荡与诚实。”
为了领悟生死的意义,廖理纯甚至参佛问道,与很多人探讨生与死的问题,并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一本书,为书取名为《何以无所畏惧》,2005年面向全国出版发行。
书中万语千言,道出了他对生死的顿悟。
他感慨生命就像一朵鲜花一样,花开无常,花落无常。他说,历史长河中,人的一生只是昙花一现,精神将使人类摒弃自私与狭隘,变得崇高而伟大,赋予人性光荣和骄傲的光环。人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也应该知晓精神的力量。既然人生无常、时光飞逝,我们就一定要珍惜好每一天,即使是朝生暮死也要实现生命的意义。
为了时刻警醒自己,廖理纯制作了一个特殊的台历,以倒计时牌的方式,提示着他剩余的生命。“按照中国人平均年龄76岁来计算,我还剩8700多张台历。”他以这样的方法勉励自己,每一张台历都要珍惜,每一天都不能浪费。
他说,金钱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生与死的机会。这两个机会,他都得把握好!
于是,他从创富的神话中走出来,真实地拷问自己的内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大义”、“公利”的种子在他心中发酵,他开始专注绿化环保公益事业,针对中国人的精神的问题,“对症下药”,著书立说,并乐此不彼。
行只有知晓生命之有限,才会重新规划人生的台历。
“人的一生有好多事可以做,挣钱只是其中的一件。如果致力于环保公益,他人生的台历会更加精彩!”廖理纯说。
每到春季,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地区都会遭遇沙尘暴天气。起风之时,仿如沙海咆哮,天气昏暗,甚至伸手不见五指。沙海吞噬了整个城市,带给人们极度的恐慌。据气象部门统计,2000至2012年,沙尘暴每年光顾北京的平均次数是12.4次。
“如同上帝在玩一个匪夷所思的游戏:他把中国西北部和中亚地区沙漠和戈壁表面的沙尘抓起来往东南方向抛去,任凭沙尘落下的地方渐渐堆积起一块高地。”(2002年《自然》杂志)更严重的是,沙尘会阻塞交通,埋没河道,侵袭农田。
为了治理沙尘暴,专家倡议用植树的方法来防风固沙。于是,大批的志愿者赶去沙漠里植树。廖理纯也在其中。
2004年,他参加了由中国社科院和国际志愿者共同组织的恩格贝绿化活动。那是他第一次去恩格贝植树,也是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恩格贝,地处中国八大沙漠之一—内蒙古库布齐沙漠中段,距包头市60公里。近万名国际志愿者参与进来。至今,国际志愿者们种下400万棵高大的乔木,恩格贝的环境和气候全然改变,并成为国家4A级景区。
这次植树经历刺激到了廖理纯。“国际志愿者来一天干一天的活,工作极其标准化,现场不留一片垃圾,中国人边干活边聊天,树坑挖得大小不一。”他的话语带着淡淡的苦涩,“一个人一天能挖70多个坑,那么大捆的树苗,”他用手比划着,“在沙地上能走1000米。”然后,摇摇头,“中国人没几个行的。”
两相对比,廖理纯自惭形愧。“在中国的土地上,国际志愿者用20多年时间,在库布其沙漠中植出恩格贝这个绿洲。国际志愿者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人应该做得比他们更好才是。”
于是,从2005年起,廖理纯开始号召和带领志愿者奔赴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植树封沙。2006年,他辞去晨拓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只保留董事长一职,全力投身于生态保护的事业之中。
为了固沙防尘,廖理纯曾用了3年时间奔赴全国各地考察,他去过漠河,也进过西藏,并一路扶贫助学。他跑到林科院去请教专家,到恩格贝与志愿者交流心得,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终于,在2011年,他带领志愿者在浑善达克沙地的南沿建立了第一个绿化基地。2013年,在河北省张北县的盐碱地上建立了第二个绿化基地。
从2011年开始,每年的4月初至11月中旬,每周至少一次,廖理纯带领志愿者像迁徙的鸿雁,唱着《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开始了春去冬回的绿色长征。五年以来,已经有218批、超过8000多人次的志愿者奔赴两个基地绿化植树。基地里种植了杨树、榆树、樟子松、云杉、油松和落叶松,现已培育出130万株树苗,每年新增绿化面积上千亩,为北京构筑起绿色的长城。
建立基地、培育苗圃、支付志愿者食宿的费用,都是廖理纯自掏腰包,迄今为止已花费了一千七百多万元。但他只是坦然一笑,“钱不是短板,种树的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平时一顿吃一碗面条就够了。”
著
或许是中关村知名企业家的缘故,从他决定“荒废主业”、自掏腰包去植树开始,批判的声浪便从四面八方朝廖理纯涌来。
“你干这事儿,天天累死累活的,不赚钱,还要倒贴,图的什么呀?”甚至有人当着他的面,说他是神经病。换作以前,听别人这么说,他会气得不行。现在不气了,他会一笑了之,“他们没那个境界”。
“在中国,做企业的人很多,但关注环境、改善环境的人很少。如果经济发展了,生态环境却一团糟,就违背了我们发展的初衷。我们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也要有人站出来甘当奉献者。”廖理纯神情严肃地说。
善意的误会,是容易纠正的。无知的嘲讽,也是可以谅解的。批判一个环保人士,多少总应该知道一些生态的知识。否则,说出了糊涂话就会贻笑大方。
一位朋友曾善意地劝他,“理纯,不要去沙漠种树了,沙漠也是很美丽的,不要去破坏沙漠好不好?”听了这话,他很震惊,“沙漠是自然界被破坏到极致的产物。沙漠没有什么所谓的美丽,而是何等的艰险!”
诸如此类,他听到的荒诞的生态观还有很多,认为沙漠中没有水的说法,认为荒漠中种不活树的方法,认为地球表面的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说法,认为去草原种树是破坏草原的说法,认为大树都是抽水机、会抽干地下水的说法,种不活树埋怨老天不下雨的说法,认为种植灌木优于种植乔木的说法,认为要通过砍树来增大风速吹走北京雾霾的说法……
这些说法令人瞠目结舌,啼笑皆非,却也让他欲哭无泪。
于是,他决定不再沉默,他要去调查,去论证,他要向世人证明,他走的路是通往前方的,植树是保护生态的正确的做法。让谬误在真理的阳光下消失殆尽吧!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廖理纯虚心请教环保专家,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总结基地植树经验,亲赴荒漠地区调研,终于在2015年完成了《对抗荒漠化》白皮书。他印刷了成千上万本,赠送给每位参与植树的志愿者。
在白皮书的前言部分,清晰地写着这样一段话:据统计,全球土地荒漠化面积达3592万平方公里,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9%。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目前我国荒漠化还在不断扩展蔓延,沙逼人退,速度惊人,造成大面积的可利用土地退化或沙化,危及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土地荒漠化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经济贫困,已成为中国当今面临的最大环境威胁。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否则后代将失去生存的依托。”廖理纯说。
为何要选择植树?还是恩格贝带给他的灵感。上世纪8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以南的恩格贝地区还是一片沙海,经过一批批志愿者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几百万棵高大的乔木在这里扎根和生长,沙地变成绿洲,成为国家4A级景区。
恩格贝的变化给廖理纯带来了莫大的信心。
他接着论证,荒漠化地区变成绿洲,离不开一个元素,那就是水。除了地表水以外,降水是补充当地水源的重要组成,它是云和当地水汽共同合作的结果,即空中的湿润空气和地面水蒸气的配合。
而每棵树都是巨大的蒸发器,它们就像一台台抽水机一样,将地表的水分送上天空,之后这些在天空中的水分又变为雨水浇灌大地。廖理纯坚持认为,相对地球内部巨大的水量来说,种树不但不会带来地下水的减少,而且会有利于地球海平面的保持。
在廖理纯的两个绿化基地里,有130多万株乔木在茁壮地成长着。他已开始畅想,或许几年、十几年后,当地将是一片郁郁葱葱、虫鸣鸟叫的景象。
他的理想又何止这些!他说他非常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推动每位公民一生为国家种活100棵树。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中,中国13亿人,按照乔木25棵每亩的密度,中国将不会再有荒漠化土地。
“如果此生能够将这个目标向前推动一点点,就是死而无憾。”
言
2016年初冬的午后,作者与30余位志愿者从北京出发,乘坐走进崇高第215次“航班”,一路“飞行”,目的地是海拔1400米的内蒙古高原张北县馒头营乡。航班是一辆蓝色大巴的别称,五年以来,它承载了近8000人往返于北京和浑善达克、张北三地。
在这趟航班中,廖理纯是当仁不让的机长,同时也是司机和讲解员。他的伙伴侯东风、车亮,以及先遣团成员王展和王若涵分别充当了解说员和领航员的角色。而此次参与植树的人,年龄纵跨50后至90后,不仅有党政机关干部、企业高管,还有高校大学生。一路上,在机组成员的鼓舞下,志愿者们大声唱着《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心中是满满的正能量。
四个小时后,天已擦黑,一行人到达张北基地。几乎一丁点时间都没有耽搁,所有的志愿者被分成6个小组,在廖理纯的带领下,依次进入已种好的乔木林中,为小树修建多余的枝丫。经过一晚上养精蓄锐,第二天一早,我们又整理行装,来到基地,正式开始植树工作。两个多小时里,志愿者们从搬运苗木营养杯,到挖坑、除草,再到为苗木填土、浇水、施肥,一桩桩一件件干得有声有色。身为带头人的廖理纯则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工作有力,指导有方。
很多人说,廖理纯这个人很特别。他不仅关心沙漠里树要怎么种才能活,更关注中国人的精神和情怀。
有细心人为他算过一笔账:每位志愿者吃喝住行的一应开销,相当于雇佣当地农民的3-5倍,而劳动量却不足当地农民的1/4 。他却坦言,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每名志愿者都能在短短两天的体验过程中升华为“种子”,由此带动更多人加入到植树的队伍中来。在廖理纯眼中,志愿者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志愿精神的接力人,更是正能量的传递者。
为了发扬民族精神,廖理纯攻读了北师大西方哲学史博士学位,除了研究经济,他还广泛涉猎历史学、教育学、农学、医学、兵法等。
他俨然是一名布道者,趁着往返基地的途中,给志愿者讲述三皇五帝、逐鹿中原、汉唐盛世、抗日战争等历史中涌现出来的无私无畏的大义精神。他说道德之中,和为贵,贵族就是勇于为国家奉献的人。
他尤其尊崇墨子之道,并坚持认为志愿精神就是墨子提倡的“大义”之体现。
先贤有云,“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三者诚为人类最高理想,为吾国之精神。”“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
廖理纯说,墨子是重“义”贵“义”的。墨子为了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社会公义,一生之中往来于诸侯之间,奔走于公卿之门,不计得失,不惜生死,丝毫不为利禄所动。
“天下之害”的根源正是在于原本同根生的人们彼此之间的“不相爱”,人们只爱自己,不爱他人,为了自身的私利,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而对于天下之公利,可谓更是毫不顾及,正是缺乏了人们之间原本存在的爱,才导致了社会中的种种乱象。
他倡导人们,一定要做对整体利益有帮助的行为,尽管这样的行为会对自己的个人利益带来损失,甚至会有自我的牺牲,这样的行为就是“义”。他大声疾呼,在国家内部,人们彼此应该互敬互爱,互相帮助。
在墨子的“理想国”中,国家中的每一位也都是这个大家整体的一部分,是这个大家的主人,下级服从上级,上级爱护下级。在这个“理想国”中,尽管暂时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贤者,但身在各个领导岗位的人都应该是不计个人得失的贤者,从而带动并监督整个社会中的人们都在为国家做出努力。
廖理纯说,他立志要做一名墨者。他要和众多志愿者们一起呼唤志愿精神,唤醒国人心中的无私和善良,为国家搭建一座大义、相爱、和合的桥梁,从而推动国家早日达到“大同”的太平盛世。
采访手记:
汉代哲学家王充曾说,“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即德才兼优,德优才大,方能做大事成大事,方能授益于众造福于众。
廖理纯在事业正值黄金期激流勇退,“弃商从树”,不计私利,全身心投入环保事业;同时,他在植树之余,著书立说,不断地审视中国人的精神疾患,倡导人们秉持大义无私的志愿精神为国家做贡献。是为德者!是为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