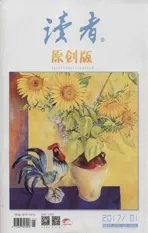守山与探山的人
2017-01-17文|尼佬
文 | 尼 佬
守山与探山的人
文 | 尼 佬

“喜欢裸泳的人太少了,可惜我们去裸泳的路线就是没法重合。”
我的一个朋友看了我在新疆恰布其海游泳的照片后,忍不住对我说。是啊,我总是在巴山、天山或是喜马拉雅山冰冷的湖里炫耀一番,他则永远在地中海和南中国海的小岛上跳来跳去。虽然我们都喜欢和水亲密接触,可是对于要在水上看到怎样的风景,永远都有不同的需求。
旅行作为一种探险求知方式的年代,已经过去太久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即使再艰苦的行程,旅行都无可避免地成为消费主义的一分子。我们对旅行的要求,远远比“豆花是咸还是甜”的问题要复杂,它可能更类似于我们采取什么方式让自己提神或兴奋,是绿茶?红茶?普洱茶?丝袜奶茶?意大利浓缩咖啡?美式咖啡?卡布奇诺?伏特加?甚至不是食物或饮料,而是一曲大卫·鲍威或者凤凰传奇。这样鸡毛蒜皮而又如此严重,你怎么可能让我们绑在一起呢?
我倒是说过,如果一个人平常生活中不喜欢麻烦别人,也不喜欢别人超出工作职责和关系限度来麻烦自己,然后又对自己处理陌生环境有自信,那么,独自出行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
享受孤独没有性别差异,我所知道的那些胡乱跑的姑娘,大多是一个人上路。当她们去一些治安曾经出现不靖的地方,通常会扯一些善意的谎言给家人,譬如去的明明是萨拉热窝,却说成布达佩斯,或者说有两个朋友同行。扯这样的谎的前提是—她们是非常熟练的“老鸟”,懂得应付旅途中所有的突发事件,并对保护自己和亲人留有余地。
只是,尽管人生而孤独是恒定的,但需要陪伴大概也是永远的人性吧。独行和同行的比例,就是你对孤独和陪伴比例的自我调适。
只有一种出行属于不能分开的例外—徒步。
探山
2009年夏天我去贡嘎山,当地人的破摩托车把我送上海拔4600米的子梅垭口。那天在下雨,雾气蒙蒙,别说雪山了,20米外的路都看不见。我自己走路下山,翻过垭口,下了大约300米,走出雾气,贡嘎山突然又冒了出来,可惜仍然云雾环绕,只看到点点雪线。
走到山谷里的子梅村已经下午三点了,村民很热情,听说我想当天就去贡嘎寺有点儿惊讶,但还是给我指了路。我遇见村支书贡布,他有点儿得意地给了我一个“幽灵”手机号码,事实上,中国移动在当地计划开通的时间是2010年开春。
问路后我继续前行,想去有守庙的苦行僧的贡嘎寺歇息,第二天看日出金山。走到莫溪沟,小桥上,突然出现一只小鹿,纯白,眼睛明亮,如精灵般地隔着莫溪沟看着我。
我满心欢喜,觉得好像掉进了像是《魔戒》那样的电影里,天使出现了。
白鹿忽然就不见了。我呆了呆,过河。事后证明,它好像不是一个吉兆。
三点半开始进山,五点半还不见翻越的迹象,我意识到我走岔道了,立即决定返回,然而基本不见驿路通道,只好摸索,下到莫溪沟,水边依然没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攀岩六次,过河七次,心里叹气:“这行为多像驴友啊(我一向认为自己只是背包客,不是户外爱好者)!”
七点开始下雨,我开始担心背包里的电脑和相机(嗯,我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找回村落这点能力我还比较自信),滑坡草甸,枯树独桥,基本让我全身湿透。
八点十五,终于发现了贡嘎寺到子梅村的驿道,却都是上坡,我打着雨伞慢慢走,藏獒的叫声不时传来。八点四十分,终于进了子梅村唯一挂牌的民宿。
这是村支书贡布的二弟和三弟的家,还供养着他们的爷爷。80多岁的爷爷的汉语出乎意料要好过孙子。那一夜我们自然谈笑言欢,我还第一次喝到了电动酥油茶机打出的酥油茶。贡布坚决否认他给我指的路错误,他们一般在岔路口都有藏文佛语标志,那我只好承认自己没有佛缘。
在他们的吓唬下(说康定和石棉边界有劫匪),第二天一早,贡布用摩托车送我赶到下子梅村,追赶上一群广州来的驴友,他们从康定旁边的榆林出发,到这儿已经五天了。
这之后,我没有再试图冒险独自进第一次去的森林。
守山的人
自然是难以被蔑视的。而那些在今天仍然与自然亲密相处、守住山脉的人类,更是我们探索人地关系最难得的瑰宝。
在横断山脉的西缘,碧罗雪山的中段,也有一个像子梅村一样与雪山依偎的村庄,叫茨中村。这里居住的也是藏族人,不同的是,他们是极少数有着天主教信仰的藏族人。我的向导红星如此热爱山林,甚至在山林中造了一座无人居住的木屋。
那天清晨,我们从茨中的澜沧江畔出发进山,一路垂直上升1400米,到达海拔3300米左右的拉扎牧场宿营,全程约26公里。如此巨大的高差,使我们气喘吁吁,落在向导和赶马人的后面。然而峭壁青松,清流激湍,湛蓝天空下,光线如影子一样打过重重雪松,让人抬不起眼,无力看江尽。中间路过一棵极高的大树,树中央有神龛,供奉的却是耶稣,木刻的十字架在悄无声息的丛林中,像是森林的护身符。
两小时后,可通农用车的大道结束,自此开始腐物掩盖的森林之路。冰冷溪水旁,常有巨木倒下,只能惋惜地抚摸一下那数不清的年轮。在穿过两个无人牧场后,下午三点半,我们终于抵达今夜宿营的牧场,几近力竭。红星亲手搭建起来的驿站静静地立在河谷里,红红黄黄的树影铺天盖地,就此住下再好不过。
我得说,这座木屋比我想象中的美多了。孤零零立于天地间,那日乌云蔽日,木屋像拯救洪荒的方舟。
听红星的朋友说,搭建这个木屋客栈,红星的父亲是反对的。红星倒是执着,在一帮喜爱碧罗雪山的本地和外地朋友帮忙集资下,人马搬运了半年,终于在这深山处建好了这座小屋。在我们之前,大约已有十队人享用了这小屋。红星的愿望,又变成了储一点儿钱,买两匹又好又听话的马,带客人的行囊上山。
木屋自然是没有电的。向导和马夫迅速地从山谷中搬来了柴火,烧起了温暖的火塘。没有人离得开火塘,也离不开由马从山下驮上来的酒,红星甚至还在这里留了青稞酒。葡萄酒喝光了喝青稞酒,总归是无夜无尽。跟我们搭伙的美国男孩背了吉他进山,唱起他父辈的爱国歌曲This land is your land,这样的老派,在这个牧人渐渐消失的深山,让人有点儿恍惚。
夏天早已过去,但我们还是遭遇一点儿季风的余韵,白日的一点点雨,换来傍晚森林上的半边云,夜里繁星寂寥。酒兴过后,胡乱找了片草地躺下,身体紧贴着潮湿冰冷的地球表面,看着星星和沉沉的云,和城市异曲同工的疏离感,尽在眼底。
第二天得从海拔3300米的牧场垂直向上1000米到达海拔4300米的垭口,再下到海拔3400米的峡谷地带,也堪称一次伟大的拉练,仍然是26公里。下午两点多,终于抵达此次徒步最高的垭口,于海拔4300米的垭口处,直面碧罗雪山海拔4500米的最高顶。美国男孩兴奋地吼了一声,向导翻了个白眼,告诉我们说会引来雨水。
雨果然就来了,垂直1000米的下坡路上云雾缭绕,原本清晰的峡谷牧场变得无比遥远。然而这场雨也给我们在第三天登顶海拔3900米的垭口时带来了奇观:一夜之间,山那边,我们曾经路过的顶峰已经有了积雪。往西看,则是连绵如云的高黎贡山,怒江在看不到的深山底层奔流。
没想到,精彩还在下山处。红星拿出一壶10斤重的红酒,说带我去见一位“台湾爷爷”。我们俩走岔道,滑溜溜穿过无数不能称为路的路,踩着荆棘和野草,最终到了一间有着绝佳高黎贡山风景的木屋,叩门进去,主人家正准备午餐,招呼我们就座。
这便是碧罗雪山的传奇人物阿赛。他是山下的白汉洛村人,今年已经80岁。他在台湾生活多年,1988年返回,在碧罗雪山各个牧场放牧迁徙,随着季节高高低低地居住,雪季有时候会回花莲。谈到太平洋边的花莲,他笑:“天天都吃鱼。”那天他的餐桌上也有鱼,是孙辈从怒江边徒步送上来的。
到了告别出门时我才意识到,藏地的居民是几乎不吃鱼的。这碧罗雪山两边的藏族人,有着坚定的文化认同,却已经在三江的流淌陪伴下,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拖着已经半残的双腿,我们继续下山到河谷的迪麻洛,沿着水流前行15公里,怒江奔腾的声音已遥遥传来。探山将近尾声,而守山的人,永远与山河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