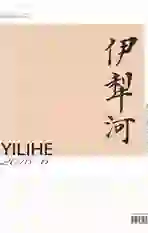槐香时节
2017-01-16田俊娥
田俊娥
雪还在零零星星的落下来,仿佛梨树园里飘着的点点梨花雨。灰濛濛的槐树林像蒙着一层紫纱,再配上静寂的幽谷,俨然一幅水墨画。几只绿眼睛水鸟黑塔似的蹲伏在秃枝桠上。汤勺形的大社场上端有几户人家,孙五家就住在离社场最近的那一个院落里。此刻,孙五家的堂屋里坐满了人,大家叽叽喳喳地讨论着为孙家迎亲的事。孙五的父亲孙金戴着一顶破旧的黑毡帽,坐在炉壁旁不停地翻动着一双粗糙的大手,仿佛在烤炙两段五爪的篓勾,人声间歇片刻,孙金从头上摘下破毡帽,粗声说道:“依我说女娃娘家就一个老大儿,一个弟弟,彩礼四万六不算少,搁着我娶孙五他妈那阵子,也就千儿八百的。我寻思着……”
媒人蔡安是婉春的姐夫,他打断了孙金的话:“他姨夫,咱们都是自己人,有话说到面面上,人家娃娃也俊着哩,就是她娘走得早,爹和弟弟没个人照应,饭拾掇不到世上,所以才拖这么久。”
有个本房的叔辈插问道:“他蔡姨夫,雨红她娘是怎么走法唻?”
“哎哎呀,说来话长哩,说是跟野汉子跑了,这一跑就是十来年。跟一个秦川来的赊鸭贩子走的,走时,小丫头子才七岁,儿子玉郎也不过五岁嘛。好狠心呀!”媒人啧啧,直摇头。
“那么,后来就再没了音讯?”旁边人问道。
“音讯倒是有,”蔡媒人摸摸短胡茬儿,饶有兴趣地接下去,“那年个,雨红娘实在熬不住了,想两个孩子呀,俗话说‘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没有不想的道理。可雨红她爹银斗子是个要面子的人,坚决不接受这个女人,抡起钁头把她赶出了家门,一直追到上竹林,才眼泪汪汪地回来,雨红那会儿十岁,领着小弟弟寻了十里路,也没见着她娘,后来也就断了音讯了。”
孙金起身往炉膛里添了几块木柴,走到门道里,招呼院子里正在给一只奶山羊喂草料的老婆婉春:“快晌午了罢,赶紧给他蔡姨夫们弄些饭吃。”
婉春从面缸里舀出几碗面和成柔软的面团,擀了几把子细细的长面条;她像一只臃肿的大肥猫,在锅台前缓慢移动着,她向来做事慢,是出了名儿的柔性子。她把泡好的菠菜干捞出来,剩下半盆绿绿的翡翠色的菠菜水,静置在桌面上,上面漂浮着几根枯黄的草屑,仿佛凝固了的碧玉肉冻子。乡下人一年四季很少能吃上几回新鲜蔬菜,除了夏天去集市买几颗洋葱和西红柿当宝贝似地拎回来,其余季节都吃野苜蓿、地软之类的野菜,偶尔也买几斤菠菜回来穿在细绳上晾干了备着冬天做长面吃。
蔡安一连吃了三大瓷碗长面,抹了抹冒汗的脑门,长吁了一口气,抻了抻鸡肠子似的脖子,看了看窗外,说:“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二十里路,远着呢。”
孙金放下碗筷,再三劝蔡安多吃一点,蔡安说什么也不吃了,于是人们都起身送蔡安出门。婉春拎着一个黑皮包赶出来,胖脸上堆满了笑容,说:“这几个油馒头和包子请他姨夫带回去给姐姐尝尝,别嫌少。”
蔡安笑着说:“哪里的话,真是劳你费心,雨红和孙五的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再去说叨说叨,没准儿能赶在年前迎进门,来年抱个大孙子。”
大家都笑着送走了蔡媒人。
迎亲的队伍像摆长蛇阵似地在平坦的乡间道路上移动着,橘红色阳光照耀在车窗玻璃上,熠熠生辉,像跳动着的星光。打头的车子缓缓移动着,大红色被面横绑在车头上,两朵娇艳的大红花扎在车翼两侧,彩带随风一飘一扬的。乡下时兴一种习俗,谁家迎亲开“牛头牌”汽车,可算是排场极了。婚姻大事一生只有一次,孙金也狠了狠心,租了一辆“牛头牌”汽车,又租了几辆普通汽车载迎亲的人以及新娘家的亲戚。
太阳已经斜到了半山腰,通红的西边天际有几只雀鸟疾驰而过。这一座古老而萧条的村庄坐落在一个湾臂里,仿佛一只蚕匍匐在一片桑叶上,因为村庄所处地方是一块平整的椭圆形状,活像一片树叶;村庄的东边是一条宽而深的河,与其说是河,不如说成坝,因为是蓄水用的,因淹死了一个放羊娃,坝被拆除了,现在变成了干涸的河床。只长一些水草之类的,草丛子里流着涓涓的细流。河底一棵柳树下有两眼泉,每逢旱季,村上的人会到泉里挑水吃。这条河分为上河坡和下河坡,呈“v”字型,像一条盘虬的长蛇,一直延伸下去,河上游是几眼泉和一片小树林;黑压压一片,尤其在夏天,风涌动着树冠,像巫婆在施法似的摇摆不定,据说那里长满了齐腰高的苜蓿草,但很少有人进去过。对于人们来说,那是一片神秘的不可随意进入的领地。
太阳像一团即将燃尽的火焰,在做最后的挣扎,想把最后的光明留给人间。“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一群脖子上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排着一条长队,边唱着“下学歌”边沿着河对岸一条平坦如砥的黄土路前进着,队伍的首末两端各跟着一个队长,他们大多是六年级的学生,专门负责整队和下达散队号令。当队伍抵达了河坡口时,队首的队长下达了命令:“家住在附近的同学们可以散队了,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其余的同学重新整队,跟上,不许乱。”
芦珠和班里一个瘦小的女孩子假装鞋被踩掉了,故意落在队伍最后面,芦珠用胳膊捅了捅望着河对岸发愣的同伴,神秘兮兮地说:“哎,我大爹家的大哥今天迎亲,我们从下河坡走,这样快些,我好想看看新娘子的样子呦。”芦珠生得倒很俊秀。一张薄薄的白净的瓜子脸上嵌着一双圆石子般的大眼睛,泛着紫黑色的光,像刚从水里捞上来的,呈有螺旋形的花纹,四周覆盖着一圈乌黑而浓密的长睫毛,看着灵活可人。一管细嫩直挺的鼻子不偏不倚地生在脸的正中间,尖尖的下巴上方一张薄唇,嘴角微扬,说话时调皮又爽朗,活像一头养在山间的麋鹿。还不曾涉想到人世的复杂与离奇。
那个女孩子把眼睛瞪得奇大,由于眼白多,活像两个白色的五子棋上点了两滴黑墨水,许久,才吃吃地说:“我怕哩,听我爷爷说,这河里有鬼哩,下河坡也有狼,我们还是……”
芦珠胸脯微微起伏着,略带恼火地说:“别听你爷爷瞎说,你到底去不去,这条路多近,一翻过河坡底就到大社场了,我大爹家就在河坡底上端,我们一起去看新娘子好不好?”芦珠近乎央求道。
那小女孩仍固执地摇摇头,甩开两只羊角辫,头也不回地边跑边颤声回答道:“我要去追前面的队伍,兴许还能追上,你还是跟我们走上河坡吧。”风吹着道路两旁的芦苇呜呜作响,仿佛哀怨的箫鸣声。芦珠望着远去的背影,失望地叹了口气,望了望落日的余晖,在一片灰蒙中快速向下河坡跑去。她一边跑一边回想起以前听过的鬼故事,吓出一身冷汗。还好,她终于看到了大社场旁苜蓿地里的几株核桃树,紧绷的神经像上紧了的发条被人突然间拧松了似的,瞬间松懈下来。此时,黄昏染红了落日,透过稀疏的树枝,洒下斑驳的影子。她趴倒在苜蓿地上,揪了一棵嫩苜蓿芽儿,丢进嘴里,慢慢地咀嚼了一会儿,又吐出来,拍拍身上的泥土,欢快地向家奔去。路过大妈家门口,她伸出糖瓜似的脑袋向门道里望了望,院子里人像蚂蚁似的热潮着,忙忙碌碌的,靠堂屋的廊檐下摆了十几桌酒席,搭起塑料顶棚,还拉着长长的细电绳子,末端吊着一个50瓦的白炽灯,投下一片橘黄色的灯光。客人们个个喝得面红耳赤,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红红绿绿的荤菜,还有细细的胡萝卜粉丝儿……
“啊六六,满上呵……”几个络腮胡子的人在划拳,喝声震天,地上铺了一层鲜艳的鞭炮碎屑,棚壁上和门楣上贴满了大红“喜”字,几个圆溜溜脑袋的小孩子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芦珠心想,咦,怎么不见新娘子啊,这时,婉春从厨房里出来了。今天,她身上穿了一件天蓝色碎花上衣,青黑色毛底料裤子,头发梳得油光光的,用一根皮绳束着,像燕子尾巴似的朝天翘着。一看到芦珠,笑容便立刻僵在她那茄子似的胖脸上,在寒气和灯光的衬托下,泛着紫光,她龇了龇那颗镶铁的耙齿一样的门牙,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想转身进去。走了没几步,她一转身看见芦珠还没有走,就走过来,在芦珠脑袋上按了一下,扬了扬了手,赶鸡似地说:“去,回家找你奶奶去。”婉春呵斥道。这时,孙金端着一碟酱花生往堂屋里走,见到这情形便走过来略带恼火地对了婉春说:“要煮饺子了,还不回厨房看看去。”说完便转身进去把两扇红漆铁门虚掩上了。芦珠双目如熄灭了的火焰,顿时黯淡下来了,她的脸刹那间变得通红,像烤熟的红薯发着热。她低着头走回了家。
在门道里一头撞到了奶奶怀里,奶奶微笑着用她的两只瘦而粗糙的大手捧着芦珠的头急切地问道:“芦珠,你怎么现在才回来,这么晚了,你放学不赶快回家,跑哪儿去了?”
芦珠把头扭向一边,呕了一口气,恹恹地说:“上我大妈家去了,本来想看一眼新娘子,没想到被我大妈赶回来了。”
奶奶用大手摩挲着芦珠黑亮亮的头发,安慰道:“别伤心了,先吃饭,吃完饭,我领你去好不好?”
芦珠点了点头。
一道象牙色的光从窗户里透进来,奶奶低垂着双眸,把两扇笨重的木窗关上,捻开了灯。她的脸皱缩成一个核桃,看着熟睡的芦珠,呆坐了半晌。
2
春天到了,太阳暖烘烘的,残雪多半已化去了,高突的山丘像小面包似的连绵不绝地排列着,漫山遍野的桃树舒展了枝条,吐出焦红色碎蕾。远处的山峰一显黛青色,被一层薄薄的烟雾笼罩着,田野里冒着热腾腾的蒸汽,在太阳的烘烤下袅袅升腾。一个老农扶着一把铁犁,“噢唷噢唷”地赶着一头黄牛,在田间划出一道道匀称规整的沟壑,像一架弯弯的彩虹桥。再加上蒸汽的陪衬,仿佛古画里的仙人耕作图。
芦珠的爷爷一大清早就去耕田了。这座独门小院里静悄悄的,几只鹊鸟张着一对对琥珀色的圆眼,静谧地端坐在梨树枝头,安详地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芦珠醒了,掀开被头一骨碌爬起来,揉了揉朦胧的睡眼,跳下炕去,穿上鞋,跑去厨房里找奶奶。
厨房里烟雾弥漫,奶奶正在蒸一锅糜面馒头,黄黄的馍馍出锅了,芦珠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头扎下去,又抽出来,闪动着灵活的大眼睛,说:“奶奶,熟了,没粘筷子。”
“好孩子,你睡醒了没?”奶奶抚摸着芦珠光滑的发丝问。
“睡醒了。”芦珠说。
“那有一桩差事需要你去办。”
“什么事?”
“去给田里耕地的爷爷送饷午饭。”
“哦。”
一切都装备好了,装了满满一竹篮子干粮,四角各放一玻璃杯泡好的浓茶。“爷爷就爱就着茶吃饷午饭。”芦珠嘻笑着从奶奶臂弯里接过篮子,兔子似的一蹦一跳地上路了。
蜿蜒曲折的小路如羊肠般错综复杂,芦珠紧握编织篮一路欣赏着道路旁的原野。小路两边,镶着茂盛的野草,狗尾草簌簌地摇曳着栗色的毛茸茸穗子,乌紫的寒鸦花像个俊俏的小媳妇似的,在微风中把尖细的喙伸得老长。偶尔,有一两只藕荷色的短尾兔在草丛中出没,惊起几只觅花的蝴蝶。
太阳渐渐升高了,牵牛花伏在路沿上,张着粉紫的小喇叭;路边有几株长枝条的柳树,抽出了柔白的絮,带着蜜糖似的味儿,蛱蝶在微风中飞来飞去,像绿叶的恋人。芦珠左手挎着篮子,右手拿着一把从田野里采来的野花,爬上了一段小坡,望见一个老人正扶着犁头,佝偻着背,活像一只龙虾。他吃力地扬起灵蛇般的鞭子,“哦嘘”“哦嘘”地赶着一头黄牛耕地。后面紧跟着两个女人,一颠一颠地撒着白色的颗粒物。
芦珠见他们还不来,于是将篮子放在一块凹地上,防止它滚落。她伸手从旁边的袋子里抓起一把颗粒物,仔细观察着,陷入了无限的遐想。哇,这白色颗粒物像极了秦川货郎担子里摆着的豆豆糖。不过,那豆豆糖五颜六色的,嚼在嘴里有一股子冰凉的汽水味儿,极甜。想着想着,她抓起一粒欲往嘴里塞。
“哎呀,你在做什么?”一个身材微胖的中年女人吼道。她乱蓬蓬的头发仿佛一个老鸹窝。她摘下扣在蓬发上的草帽,在阳光下不耐烦地撩起上嘴唇,露出黑炭似的龋齿的门牙,呆滞的目光四下里扫视着,下嘴唇似滚水烫过一般向外翻着。由于先天性弱视,父母给她取名“亮子”,希望眼睛能明亮些。二十四岁时嫁给芦珠的哑巴二叔,芦珠的父亲排行老三,加上芦珠共有五个孩子。芦珠是第三个孩子,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七八年前都随父母去了省外,一直没有回来。芦珠一岁半时,她母亲又产下了一个妹妹,她便跟奶奶生活在一起,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着。
“二妈,你看这东西像不像豆豆糖?”芦珠抓了一把化肥侧着头问道。
“那是化肥,小笨猪。”亮子龇着獠牙喝道。
这时,芦珠的爷爷和大婶婉春也从田埂上走了过来。
老人双腿软得像装了弹簧似的,颤悠颤悠地朝篮子这边走来,站定了。蓝卡叽破褂子衣裾上沾满了泥土,脸痛苦地抽搐着,粗大的毛孔里渗出密密的汗珠子,身体歪斜着,像泡酥的瓦片一样会顷刻间破碎。他欠身脱下一只破布鞋,垫在屁股底下,摘下土黦黦的一顶草帽,露出了极短的头发,似刚收割过的庄稼茬儿,高低不齐,灰白而失去了生机。松懈的脸皮上堆着皱纹,眼窝深陷,两鬓染上了白霜,在一张橘皮脸的下方,留着一撮山羊胡子。他静坐片刻,伸手从篮子里揪起一个金黄的糜面馍,喝着茶吃嚼起来。
在他们吃饷午饭的当儿,芦珠在一旁静静地玩着沙土。不一会儿,他们吃完了,婉春和亮子还坐在原地休息,老人并不闲着,起身去犁铧前撕扯着缠绕在上面的一团团如铜丝般的草根。亮子便转动着两只像凝固了的羊油似的白眼珠,低声对芦珠说:“芦珠,你想不想吃胡萝卜呀?”
“想。”芦珠天真地回答道。
“去田埂下面那块长条地去,那里种了一大片胡萝卜,还有红芯子的水萝卜。”亮子怂恿道。
“那人家找上来怎么办?”芦珠畏惧道。
“胆小鬼,你不会跑啊,跑到我这里来就安全了。”亮子仍鼓励道。
芦珠还是犹豫不决,亮子用肘子捅了捅婉春,使了一个眼色。于是,婉春故意笑吟吟地讽刺说:“芦珠,你这么胆小,难怪你妈不要你了,连个萝卜都不敢拔。”
芦珠最怕人家说自己是没人管的孩子,于是连忙说:“我去。”便站起来,浑身有些颤抖地朝萝卜地走去,像白天出穴游走的鼠子。
一片绿茵茵的萝卜地呈现在眼前,鸟羽般的叶子铺满一地。鸡爪状的叶子沿着一根轴梗生长着,四散开来,罩住了地面。芦珠四下里张望了一下,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攥住一个萝卜,用力拔了出来,接着又拔了几个婴儿脚拇指头那么粗的胡萝卜,慌忙跑了出来。婉春和亮子一人拧了一个胡萝卜,在衣襟上蹭了蹭,咔嚓咔嚓地吃起来。
这时,不远处走来一个身影,婉春低声对亮子说:“人来了,快走!”
只留下芦珠瞪大了眼睛坐着,那黑影像一阵黑风似的旋来,一步步朝她逼近,仿佛一只恶狼要活吞了兔子似的瑟缩着的芦珠。芦珠慌忙站起来用爷爷的破布衫盖住那几只胡萝卜。她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恐惧,心脏像一个充足了气的气球,轻轻一碰就会爆炸。她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朝爷爷那边走去。
“站住。”那个黑色的巨影朝她吼道。
芦珠红着脸,低头站着。
那个黑脸女人猛地掀开衫子,露出了几只黄黄的瘦小的胡萝卜,那胡萝卜也像害羞似的蹙缩着,似乎比芦珠还要紧张。那黑脸女人本来就黑的脸愈发地黑了,像半截扭曲了的黑树皮,狰狞地笑着,像拎小鸡似的一把将芦珠提起来,芦珠像一片挂在腊月树梢上的枯叶,浑身发抖。爷爷急忙赶了过来,黑脸女人指着地上的几只胡萝卜,张着一张血盆大口谩骂起来,不堪的言语像冰水般灌进了老人的耳朵,老人浑身瑟抖着,脸色铁青,抄起手中的鞭子,劈头盖脸地朝芦珠瘦小的身体上抽去。哭声夹杂着叫骂声,嚷成一片,嘈杂极了。女人尖厉的叫骂声像刀刃一样割着空气和阳光,传出好远,回荡在田野上空,像拉电锯般尖锐刺耳。
3
五月时节,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下河坡一片片枝干粗壮的槐树茁壮地生长着,枝头挂满了雪白的槐花。芦珠穿一件白色碎花小衫,一只手提着笸箩,一只手捏着奶奶给捏的“泥瓦呜”,可以横在嘴上吹出曲子的,追着小伙伴们欢快地跑下河坡去。因为每年这个时节人们都会采槐花,掐苜蓿芽儿,蒸香甜的槐花糕吃,已经有许多身着花衣裳的妇女在那里忙碌了。当然,孩子们也不情愿寂寞,照例跟了去。
孩子们互相嬉戏追逐着,像一群活泼可爱的嬉闹的小鸭子,在草地上踱来踱去的。一串串银铃般爽朗的笑声回荡在瓦蓝瓦蓝的河坡上空,他们的头顶是槐树庞大的树冠,团团簇簇的槐花盛开着,如雪一般洁白。几只圆肚子细腰的黄蜂伏在槐花上,针尖似的尾巴一颠一颠的,吮吸着蜜汁。整个河坡闷香扑鼻,浓郁芳香的气味令人窒息。树林的沟壑处流出涓涓的细流,地上铺了一层形状圆圆的半卷的槐叶,在露水长时间的浸润下散发着腐朽的味道,高处的岩层中不断有水珠渗出,滴落在落叶上,发出窸窸窣窣清脆的响声,仿佛音乐般动听。野苜蓿摇曳着美丽的身姿,犹如一位绝代佳人。
这时,一只灰腾腾的野兔从身旁闪电般跃过,孩子们惊呼起来,群起而逐之。不一会儿,野兔跑上向阳的一个斜坡洞穴里躲了起来,任凭孩子们如何投掷石子,甚至是放开喇叭似的喉咙大喊大叫,如春雷般震彻河谷,它就是匿藏着不出来。
“算了吧,兔子不会出来了。”芦珠略带失望地说。
“为什么呀?干嘛那么肯定?”一个小伙伴不解地问道。
“因为它一定是被妈妈保护起来了。”芦珠诚恳地答道。
“呦,自己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还说兔子。”一个调皮的男孩子讥讽道。
“你胡说什么?我爸爸妈妈会回来的。”芦珠争辩道。
那个男孩子又说:“你是槐花林里捡来的,我奶奶告诉我的。还说,也不知道哪个没德性的骚女人生完了孩子扔下就跑了。”
“你再说一遍,你这不要脸的小混蛋。”芦珠气紫了脸,说着,扑上去,用两只小手死死钳住男孩子的脖子,那男孩子挣扎着,双手抓住了芦珠的衣领,用力一扯,露珠抓着的手松开了,那个男孩子就势推了她一把,芦珠向后一个趔趄,皮球似地从斜坡上滚落下去,躺在河沟里一动不动了。孩子们尖叫着跑下河坡去,有几个跑回去叫人。瘦小的芦珠静静地躺在那里,像火化过的纸人,只剩下黑色的灰烬组成的影子留在那里随风颤动着,仿佛风一吹就会化为灰烬消失。她黑石子般的眼睛渐渐褪去了光泽,像一团将要燃尽的火焰,慢慢黯淡下去,眼珠子木然不动地盯着天空,脸颊上被荆棘划破了几道口子,沁出了鲜血,发暗的嘴唇微微抖动着。
芦珠在众人的尖叫声和呼唤声中,微微转动了一下眼珠子,一个稍大一点的女孩子在芦珠的胳膊上轻轻地摇动着,带着哭腔说:“芦珠,你快醒醒呀。”
芦珠的脸色变得像白垩石的土壤般惨白,两股鲜红的血液从鼻孔中汩汩流出,染红了白色碎花衣襟。远处一只水鸟惊起,芦花摇曳着灰白的穗子,一阵冷风吹过,发出呜呜的声音,仿佛地狱般阴森。
奶奶赶到时,芦珠已被人们抬到了大社场的草垛后面。芦珠睡在一堆麦草上,用一团青藤草从头到脚覆盖着。顿时,老人像一滩消融的蜡似的瘫在地上昏厥了过去……
芦珠被安葬在槐花林中。
第二年,又是一个槐花飘香的季节。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妇人左手拄着一根竹竿,右手提着一个小笸箩,嘴里念叨着:“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的姑娘都来了,就剩我芦珠没有来……”她步履蹒跚地行走在下河坡河畔的小道上。
一阵风吹过,槐林如绿浪般翻涌着,发出“哗啦啦”的闷响声,吞噬了老妇人忧伤的哀吟声。
卧蚕县有个四月八庙会,每年四月八日要举行为期半个月的祭祀活动,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年轻妇女祈求神灵赐个男孩子的。这个习俗沿袭了多少年无从知晓,反正是很久很久了。祭祀除了摆供奉香案,献奉果,收香火钱,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外,最隆重的要数唱十四天的迎神戏。
四月初,全庄人开始为迎神的事做准备了。孙金爹是四月八庙会里的会长,专门负责请戏团和安排戏子们的食宿问题。天麻糊亮,孙金爹肩上搭了一条长褡裢,手里拎着一个布口袋,挨家挨户地收面收钱。钱数不限,白面最少一碗,也有人给两碗的。一连收了两天,总共收了满满两大袋白面,一大沓红红绿绿的钞票,眼下戏子们的伙食问题解决了,可住宿问题仍没有着落。
一天,一个须发皆白,长衫飘飘的老人来到孙金爹的小院子里,寒暄一阵后,道长说:“老兄啊,有一件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孙金爹一向为人旷达,便扬头答道:“有什么事你尽管讲出来,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会全力帮助的。”
道长捻了捻花白胡子,把两只铜铃般的双目眯成一条缝,低声说道:“戏团里有个快要临盆的女戏子,不必上台表演,我想给她找个住处,你看——”老道长顿了顿,呷了一口浓茶,接着说:“寺院里肯定住不成,生产就在这几天里头,血腥之气必会冲犯天神,这要是天神降罪下来,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想请你务必想个办法,把这个女戏子安顿下来,要快啊!”
说完,老道长便扬长而去,孙金爹望着茶杯里冒出的热气发呆。孙金娘苦着脸怏怏地坐在炕沿上,慢吞吞地说:“依我看,村子里头一定没有愿意收留这女戏子的。我娘先前给我讲过一个大姑娘回娘家生孩子的事,说是被血气冲晦了祖上,栽了满院的菊花,三年过后,才镇住了这邪气!”
孙金爹眉头挽成鸡蛋那么大,没好气地说:“道长发了话,不照办,还能怎么整!”
孙金娘是个菩萨心肠,又信奉神,于是便说:“实在不行,就让住咱家吧。”
孙金爹粗声吼道:“那怎么成,万一生孩子怎么办?”
孙金娘宽慰地说:“先住下来,等快要生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不然,那就送到槐林里去,那儿密不透风的,也没什么人。生完了,大社场有间破门房,让娘俩先住在里头,我会照应好的。”
“就这么办吧。”孙金爹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
七天后,那个女戏子在槐树林中产下了一个女婴。槐树林生长得十分茂密,进去宛若迷宫。生下孩子后,孙金娘一手抱着裹在棉被里的孩子,一手搀扶着极度虚弱的女戏子,一步一步缓慢地朝槐树林外走去。槐树林里异常闷热,一串串银子般的马蹄形槐花挂在枝头,还有一种中间紫红四周雪白的槐花更如水晶珠似的悬在枝头。林子里香气弥漫,仿佛浸泡在香水缸中一样。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一眼望去,可以看到大社场边缘的几株老胡桃树了,在四月的阳光里宛若几只歪脖子野鸡站立着。玫瑰色阳光透过密密的树枝照射下来,斑斑驳驳的树影在潮湿的空地上跳跃。窄窄的道路两旁长满了翠绿的芦苇,芦苇狭长的叶片上挂满了水珠,在阳光的照耀下,仿佛一串串珍珠似的。突然,女戏子扶着一株槐树坐下来。白的、紫的槐花落了一地,踩上去吱吱作响,仿佛铺了一层蚕丝绒被似的。孙金妈把孩子放在芦苇棵下,一滴露珠从叶子上窸窣滚落下来,滴在了女婴红皱的脸颊上,女婴立刻打了一个冷颤,哼哼了一声,又安静地躺着。
孙金妈走过去,蹲在女戏子身旁,掏出一只手帕,替女戏子揩去额头上沁出的密密的冷汗,关切地说道:“姑娘,你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到家了。”
女戏子艰难地抬起头,脸惨白得犹如一张白纸,几绺乱发被汗黏贴在脸庞上,嘴唇上像挂着一层霜,眼睛像两口枯井似的空洞着。半晌,她才缓缓地说:“大娘,我恐怕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请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孩子……”她又喘了几口气,说:“孩子——”突然,她的喉头像卡住了鱼刺似的,干咳一声,头歪向了左肩,斜倚在槐树干上一动不动。
孙金妈包裹好孩子抱回了家,想起芦花上的水珠滴在女婴脸上,便取名叫“芦珠”。三儿子孙福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两岁,小女儿一岁。经过商议,决定把芦珠给三儿子做三女儿。当然,孙福媳妇后来又生下了一个女儿,第四胎终于是个男孩儿。后来,孙福带着妻子儿女去了外省,再也没有回来过。芦珠由奶奶拉扯大,并送去学堂读书。秋天,他们一起去槐树林扫树叶儿,捉珍珠眼的绿蜻蜓……芦珠像一头欢快的小鹿,东蹦西跳,采了一大把狗曲花儿,要奶奶给编成一只花环戴在头上。
如今,槐花林依旧是那个槐花林,芦梗棒像往年一样结了红通通的蒲棒,俨然一枝枝小蜡烛,风一吹,雪白而轻盈的芦花飞舞着;不同的是,槐林小道的尽头,多了一座小土丘,孤零零的伫立着。一个目光呆滞、憔悴不堪的老妇人在坟堆前烧一堆黄色的纸钱儿,几缕轻烟垂直上升,直冲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