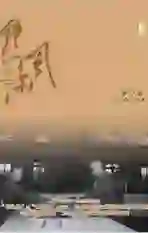王芸生:起伏跌宕的报海生涯
2017-01-16徐廷华
徐廷华
王芸生原名德鹏。“芸生”这个名字是他1928年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王芸生说:“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于是便保留了这个名字。
贫苦发奋的少年
王芸生,1901年出生在天津一个贫苦人家,为了“改换门楣”,父母决定不再让王芸生像他两个哥哥那样碌碌无为,家里省吃俭用,供他上了4年私塾。后来,实在供不起他读书,13岁的王芸生到一家茶叶店去当学徒。白天来来去去给客人送茶,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读一些杂七杂八的古典小说。
一天,有个卖报的想用一份《天津白话午报》换一包茶叶末,掌柜的答应了。于是王芸生每天都能看到这张白话报。茶叶店陈掌柜和管账先生都很信任他,把每天赚的钱点清包好,叫王芸生送到银号。送钱的路上有个报栏,贴的是天津《益世报》。王芸生最爱看副刊上的小文章,看到喜爱处,就从怀里掏出一把修脚刀,把文章挖下来,日积月累收集了不少。时间一久,他发现这些文章有规律可循,感到自己也能写,于是萌生了给《益世报》投稿的念头。当时正值徐世昌当总统,段祺瑞做国务总理,报纸副刊上几乎天天都有讽刺他们的文章。王芸生深受触动,写了平生第一篇稿子寄给《益世报》,题目是《新新年致旧新年书》,署名“倦飞”。文章借旧去新来,讽劝徐世昌、段祺瑞不要恋栈,该下台了。三天后,此文居然在副刊“益智粽”上登了出来。
那时王芸生已经在茶叶店苦熬了三个年头,满师后每月可得三元钱的薪金。但充满幻想与激情的他,又重新燃起了上南开中学的愿望。他辞去了茶叶店的工作,投靠到已出嫁的大姐家。大姐每月花50个铜子给他订了一份《益世报》,一连几月,他足不出户守着报纸,每天写一篇甚至几篇稿子,天天都在投稿,竟没有一篇投中。大姐只得又托人介绍他到一家小布店里继续当学徒。苦难的学徒生活又开始了。夜晚,等到掌柜、老板娘都睡着了,他才悄悄地在炕桌上摆一只空肥皂箱子,点燃积攒起来的蜡烛头,浏览一些书籍。他常说:“这微弱的烛光是我在漫长黑夜中的一颗启明星,它给了我知识、希望和光明。”
王芸生从报刊上既读到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也读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文章,并开始接触到外文。当他下定决心要学英文时,正巧上海《申报》登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招生的广告,他开始念函授英文,凭着刻苦劲儿,在不长时间里就能阅读一些英文书报。后来他就试着去给人家做翻译,渐渐的有了些收入,不过他的兴趣还是在办报纸上,机遇终于圆了他的梦。
博古引他入报界
1926年,王芸生从天津来到上海,在上海他结识了办报的博古(秦邦宪),当时他们住在一个亭子间里,博古文章写得好,且有革命激情。在博古介绍下,王芸生加入了共产党,并和几个共产党人一起办起《亦是》、《猛进》等周刊,还担任《和平日报》的编辑工作。用他的话说:“那一年的生活,大体说来,是轰轰烈烈的,终日所接触的都是热血蓬勃的人物,夜间则睡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1927年春节前因老母病重,王芸生回到天津,为《华北新闻》写社论。
当北伐军打进南京时,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派出军舰炮轰南京,引起程潜率领的第六军官兵奋起反抗。针对这一事件,王芸生在《华北新闻》的社论中声援第六军将士的正义行动。而《大公报》则发表文章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与人如是,社会和平矣;国与国如是,世界和平矣……”第二天,即4月2日,《华北新闻》又发表了由王芸生执笔的社论《中国国民革命之根本观》,对《大公报》这篇社论进行反驳。文章写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对侵略者无所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净尽!”《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没有回应,但向人打听《华北新闻》社论的作者为谁,得知后,便传话王芸生,希望会晤。此次见面,却成就了两位终生师友的初晤。
1928年5月,王芸生出任《商报》总编辑。但因与老板在观点上有严重分歧,不得不辞职。他给《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写了求职信,张季鸾接信后,亲自登门接王芸生到《大公报》。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就与《大公报》连在一起了。
报人襟怀爱国情
1929年8月22日,王芸生正式进入《大公报》,他发现《大公报》不偏不倚的办报理念跟自己的理想不谋而合。
王芸生在《大公报》最初负责编地方新闻版,孔昭恺在《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回忆:“他(指王芸生)编的地方版颇不一般,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多所抨击,并以标题出之,标题有评论色彩,他常在这类标题下加个惊叹号,以加重语气,有时随写随念叨着说:‘给它来个棒槌!……当时河南当局对《大公报》地方新闻版最恼火,大概挨了王芸生的不少棒槌。”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张季鸾派王芸生协助汪松年编中日关系史料,后汪因年老、才力不及,推举他来主编。于是从1931年9月到1934年4月,王芸生往来于平津之间,奔走于各大图书馆,广泛搜集材料,走访历史界和外交界前辈,晚上伏案写作,常常通宵达旦。他每天写出一段,即在《大公报》上连载,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读来铿然有声。连载三年,受到广泛欢迎,许多学者和外交家把珍藏的材料寄给他。这便是后来结集出版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也因了这本书声名鹊起,擢升为编辑部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
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王芸生和张季鸾故地重聚,这让王感慨万千,此时的他“已不是一个一般的报人,而是身兼报人和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全国有影响的报人。“那时的朋友们,到现在已死的死,散的散,都为一个大时代尽过他们的责任了;屈指数来,也有不少的人们业已显达。我对于显达的人们毫不羡慕,而对于被时代巨浪吞噬了的朋友们,每一念及,辄不免心头滚烫,暗暗的落泪。”他把自己五年来写的三十几篇文章汇编成《芸生文存》第一卷,由上海大公报馆出版发行。第二年,他又在炮火硝烟中编了《芸生文存》第二卷(取名《由统一到抗战》)。
《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迁到重庆后,张季鸾的肺病日益严重,编务逐渐交给王芸生处理。张季鸾常对人说:“王芸生文章好,人品好,编辑业务交给他完全可以放心。”甫到重庆,王芸生收到国民政府聘他为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聘书。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打来电话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军委会还送来相当数目的薪水。王芸生立刻把聘书和薪水一起退了回去,张季鸾闻之,赞扬王芸生是执行《大公报》“四不”方针(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模范。王芸生自己也曾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
上世纪40年代有人这样评价王芸生:“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这也正是《大公报》的办报理念之所系。其实,给予《大公报》最高评价的恰恰是毛泽东。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泽东当场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
“反右”中躲过一劫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王芸生坚持“我有封建思想,决不出卖朋友”。当时全国三家仅存的党外报纸中,《文汇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徐铸成、储安平都已先后中箭落马,王芸生也在劫难逃。这些都是当时定下来的。是毛泽东的一句话,改变了王芸生的命运。
毛泽东说:“光明日报、文汇报的主编都打成右派了,大公报的王芸生就放他一马吧。”主席说这番话的时候,王芸生正在新闻协会做检查,忽然开来一辆轿车,把他接走,说是有要事相商。弄得王芸生一头雾水,心想能有什么要事呢?没想到轿车直接将他送回家,什么话也没说。
不把王芸生打成“右派”,是另有深意。作为一张不偏不倚的民间报纸,《大公报》的影响非常大。而要树立无产阶级的新闻观,就要把具有中间色彩的《大公报》批倒。谁来批?党内的人来批不合适,力度上也不够。最合适的人莫过于王芸生了。如果给王芸生戴上“右派”帽子,再由他批判《大公报》就会打折扣了。
就这样,在“反右”期间,王芸生没再过问《大公报》的编务工作,而静下心来对《大公报》的历史和各时期的言论作了一次系统的清理。他对《大公报》猛泼污水,大扣帽子,横加指责。现在看来有点过分自贬,不够客观,但还是为后人研究《大公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资料。
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黯然逝世。离世前他悔恨自己参加了那场对《大公报》的“围剿”,尤其涉及对前任总编张季鸾的评价。他痛苦地说:“对季鸾,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他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大公报实际上是由我来盖棺定论,把他埋葬了。”
这个在生命尽头认定自己留下“白卷”的人,曾用他手里那支“仰扶轮”之笔,影响过中国整整一个时代。(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