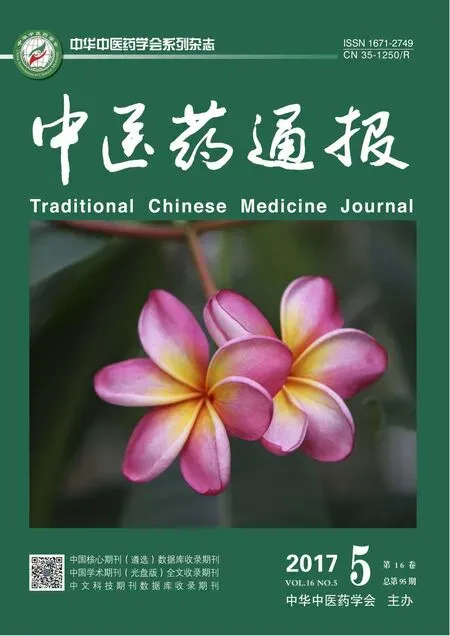仰观医圣张仲景成长之路
——华佗对张仲景的启示
2017-01-14曹东义张相鹏张培红王红霞
● 曹东义 张相鹏 张培红 王红霞
仰观医圣张仲景成长之路
——华佗对张仲景的启示
● 曹东义1*张相鹏2张培红1王红霞1
中医发展 张仲景 华佗
张仲景与华佗,都是东汉末年的医学家,两个人一个擅长辨证论治,一个外科手术空前绝后。按说华佗外科手术做得好,内科水平也很高,他对于后世的影响应该在张仲景之上。但是,尽管在《后汉书》《三国志》之中都有华佗的传记,其对于后世的影响却远不如张仲景,这有很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华佗“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文化水平高,有太尉、郡守等高官举荐,有曹操重视,但是,他不做官,也不愿做御医,只希望当一个民间医生,却被当作罪犯杀害了。华佗临死的时候,“出书一卷”,真诚地告诉狱卒说:“此可以活人!”但狱卒怕受牵连因而不敢接受。珍宝“白给不要”的遭遇,严重地伤害了华佗的自尊心,他只好把“可以活人”的宝书“索火烧之”,一把火烧了。
张仲景不论是做太守,还是做县令,尽管政绩不明显,没有被史书记载,但是他“坐堂行医”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今被人称颂。
1 华佗的不幸遭遇,让张仲景有所顾忌
现有的资料没有说张仲景与华佗互相认识,但是,他们都生活在东汉末年,是汉献帝时期的著名医学家。二人互相比较,华佗的年龄与被害的确切时间无从可知,但是可以通过曹操爱子曹冲(公元196~208年)的夭折得到佐证。曹冲八岁称象,因病死于非命。曹操捶胸顿足地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而《三国志》说华佗“年且百岁”还有壮年的容貌。因此,华佗在此前不久遇害,是可以断定的,也可以由此推断华佗要比张仲景大很多。
根据《伤寒杂病论·自序》,张仲景说“建安纪元(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也就是在公元205年左右他才开始写这部不朽的著作,从一般名医需要具备的文化素质、医学素养和写书的年龄来推测,那时的张仲景大约50多岁[1]。此时应为华佗声名远播的时候,张仲景对华佗的事迹和遭遇,不会不有所耳闻。这对于张仲景来说,应该是很有刺激性的新闻。这个事件一定在张仲景脑海中引发了深刻的反思,对其以后的行医道路不能不产生巨大警戒。
张仲景年幼生活的时期,即是汉灵帝让蔡邕等人刊刻“熹平石经”,提倡“鸿都门学”的时代。因此,他满腹经纶、饱读诗书、医道精湛;却也处于“卖官鬻爵”“党锢之祸”不断的“举世昏迷,莫能觉悟”时期。此后,社会动乱又爆发了旷日持久、战争残酷的“黄巾军起义”,以及疫病的大面积流行。这些都让年轻的张仲景奋起读书,著书立说,苍生大医,救助百姓。然而,时局的动荡不安又不能不让张仲景谨小慎微。
2 张仲景写作《伤寒杂病论》的时代背景
汉灵帝公元168年登基,此时张仲景大约18岁;黄巾起义爆发的公元184年,张仲景34岁。他不仅和大多数民众一样,一起经历战乱岁月,政治上也有痛苦印痕,或许这场动乱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
青壮年时期的张仲景,有自己心目之中的英雄——名医扁鹊,也有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步入中老年之后,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猛烈地抨击当时社会上的读书人。他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2]
他对“当今居世之士”的激烈批评,必然是根据此前读书人的情况以及自己的阅历、素养而提出来的,不可能是空发议论。而“当今居世之士”对待人生、对待医学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又和几十年的社会动荡有关。
张仲景时代的社会动荡,突出地表现在黄巾军起义的爆发,它是一系列社会矛盾逐渐积累而形成的。
自《山海经》中出现道家追求健康长寿的“神仙思想”萌芽以来,道家思想在战国秦汉时期广为流行。直到西汉中期以后,由于汉朝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才逐渐在政治上不被官方重视。为了生存,其黄老之学与神仙术相互融合起来,由宫廷士大夫走向民间老百姓,道教也就在这时应运而生。
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道教的创始人张陵(张道陵)以老子《道德经》为蓝本,作《老子想尔注》引道入教,成立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他在鹤鸣山自称是受太上老君之命,创立天师道,自封为天师,俗称五斗米教。该教的宗旨由为帝王服务改为替普通百姓“降妖除魔、治病祛灾”,为后期道教组织发展壮大奠定了群众基础。随着教徒的增多,其孙张鲁也在巴蜀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影响深远,长达20多年。后来,天师道被统治者称为“米贼”。
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张鲁被曹操降服之后,拜为镇南将军,天师道得以保存,后来逐渐向北方传播,成了北魏的国教。此时北方的张角(今河北省平乡人)也是依托黄老之学,创立了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为根本教法。起初,张角的活动似乎仍属普通的宗教活动,以符水咒说为民治病,发展徒众。经过不断传播,蓄积力量,十余年间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大方三十六,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
到汉灵帝熹平年间(公元172-177年),随着汉王朝内部宦官集团和外戚士人等政治斗争的加剧,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疾病灾害重生,民众思想混乱,社会各种矛盾复杂尖锐。此时,太平道已不再简单地为百姓看病。终于在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历史著名的黄巾军起义,正式拉开了农民起义的战争。黄巾军后来被统治者蔑称为“黄贼”。
这种乱世的景象和环境,与道教首领们利用中医传教的机会谋求“改天换地,另立王朝”有很大关系。
这就是张仲景著作《伤寒杂病论》的时代背景。了解这一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时张仲景的所思所想。是什么影响了医圣张仲景的思想?是什么启迪了医圣的学术思想?
3 张仲景“避道家之称”,事出有因
东汉末年,战争连年不断,瘟疫大面积流行。农民领袖张陵、张鲁、张角、张宝、张胜等人先后借助传道拉拢老百姓纷纷建立政权。张姓在历史上是大家大姓,当时的张姓道教人才辈出,极具影响力。事实上,当时的道教首领们也确实在为老百姓看病解除痛苦,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规定,比如说专门设立治病的场所,还有专门救济百姓住宿吃饭的地方,在为广大患者提供救助方面做了一定的贡献。然而,天师道、太平道却在为大众救济治病的同时,发展壮大自己道教势力范围,以试图号令、影响、左右天下的政治,这就引起了统治王朝的注意和打压。
大灾之后、大兵之后,常有大疫,这是历史的常识与规律。社会的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量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备受瘟疫疾病的折磨。《伤寒杂病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写作的。张仲景在序中说:“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即公元205年之前),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处在历史潮头的张家人,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出现大批死亡和逃亡,张仲景由于其姓氏是否受到“株连九族”式的拖累?张仲景出生在一个宗族素多,向余二百的大家族,必然心里有所顾虑。
南朝梁时名医陶弘景曾充分肯定了《汤液经》与《伤寒论》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其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介绍到张仲景写作《伤寒杂病论》的情况时说:“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3]
陶弘景说《汤液经》所记载的阳旦、阴旦、青龙、白虎、朱鸟、玄武“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4]
对于被陶弘景奉为这样神圣的方剂,大多数人都会崇拜万分。然而,张仲景以其“六合正精”的方剂做为自己撰写伟大著作的基础原材料,却为避道家的称号,重新组合,换药改名,加减变化,这其中既有医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也有其重要的政治背景。
4 “坐堂行医”实在是被逼无奈
“坐堂行医”是医圣张仲景的伟大创举,影响了中医几千年的诊疗模式。现在,探讨这一古代的行医方式,还有重要价值。但是,医圣“坐堂行医”究竟是怎样独创的,它背后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政治、文化和张仲景写作《伤寒杂病论》的背景来思考。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这样写道:“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闕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张仲景批判当时的医生只会趋炎附势、追求浮华、不学习经典、只按各自家传的知识不求改变、不探求疾病的根本,而是敷衍了事、马马虎虎便出方药、号脉只是应付了事不知所云、只所谓窥管而已。这样的医生看病,岂能视死别生?针对张仲景生活的那个年代的医疗环境,医圣给予了最严厉的批评。
那么在医圣的心目中,怎样才是一名合格的医生呢?张仲景在序中这样说:“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至哉”。张仲景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但是作为高明的医生,医圣不想有华佗那样的遭遇而招来杀身之祸。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由于历史原因,道教的传教活动是被政府打压的。如果在家看病,容易集聚大量的患者,有传道的重大嫌疑。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清楚是看病还是在传教。
所以,张仲景作为当时的长沙太守,坐堂是他的本分与职责,其借坐堂之职为老百姓看病服务,治疗再多的患者,都可以避免“借行医之名,行传道之实”的嫌疑。因此,我们可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大胆的设想,“坐堂行医”首先是张仲景无可奈何的一种“避嫌”选择。这个推断,可以探求“坐堂行医”的历史渊源与来龙去脉;也可以探求张仲景写作《伤寒杂病论》的“独特”方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
5 张仲景愤世嫉俗,大胆创制经典
张仲景是一个善于继承的人,也是一个大胆改革、善于创新的医学家。
他继承了《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理论,也继承了《难经》“伤寒有五”的学说,还学习和借鉴了伊尹《汤液经》的方药,并且都进行了改造、升级换代,创立了不同于前人的六经辨证,也推出了不同于《汤液经》的“经方体系”。
张仲景借鉴了医经家的理论,整理了经方家的经验,才有了如此大的贡献。
“尊师重道”曾经是汉儒的光荣传统,“师法”“家法”都很严格,很难出现拆了《汤液经》、改造《素问》六经、编制《伤寒论》的事情。但是,东汉末年“太学经师”,解释经典走向了烦琐哲学的异端。一句话的解释可以达到几万言,“皓首穷经”也学不了多少真东西。
东汉末年,鸿都门学重视辞赋、文艺,受到汉灵帝政府重用,严重地冲击了太学的经典传承,也给了张仲景突破藩篱的精神力量。他对前人流传下来的医学典籍,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
首先,在著作的编排上,《汤液经》用脏腑辨证论百病;用“六合正精”系列方药,治疗外感热病和天行。如其五脏辨证体系,有小补心汤、大补心汤;小泻心汤、大泻心汤。也有小补肺汤、大补肺汤;小泻肺汤、大泻肺汤。还有补肝、泻肝;补肾、泻肾;补脾、泻脾的方剂,并且都是有大有小,对仗整齐,体系完整。
《伤寒杂病论》的编写体例则与《汤液经》不同。后者五脏辨证百病在前,诊治热病天行的“六合正精”四神方在后。张仲景如果按照《汤液经》的体例写一部新书,应该叫《百病热病学》,而不是《伤寒杂病论》。
《汉书·艺文志》记载的经方,以及《素问》《灵枢》论述百病,都重视脏腑辨证。《金匮要略》虽然也重视脏腑,但是在形式上远没有《辅行诀》所收载的五脏补方、泻方各分大小那样规整,一般也不用脏腑命名方剂。
张仲景为了突出伤寒病的诊治,把百病统称为“杂病”。可见伤寒病的“独尊地位”的确立,是张仲景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家训”。此前的《素问》《灵枢》,只有用“热病”命名的章节,没有用伤寒命名的专篇。
张仲景之后,伤寒学家、伤寒著作逐渐涌现,“热病”“天行”很快就成了“绝学”,没有人去专门研究,也没见有人撰写专著。
这是中医历史上,诊治模式的重大转化。此后,明清温病学家的崛起,也是“模式转化”的结果。
6 改传经理论,尊古不泥经
《素问·热论》对于“伤于寒”的热病,按照每一日传一个经的模式分类临床证候。认为发病日期具有“决定作用”: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日期与证候的对应关系,非常严格,固定不变。并且提出“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
验之临床,“日传一经”,并与“三日前后分汗泄”联在一起叙述,其缺陷十分突出。是遵从经典,将错就错?还是大胆改革?
张仲景吸收《素问·热论》学说之精华,按六经分篇述其证治,同时又不拘泥“日传一经”,处处以证候为据,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治疗思想。如:“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
《伤寒论》之中,论述伤寒的病程,经常见到“二三日”“四五日”“五六日”“十余日”等不确定的日期描述。这种“或然”之词,完全基于临床实际情况,也是对于“日传一经”的明确否定。
当然,张仲景治疗伤寒病的丰富方法,也绝对不是汗法、泄法可以概括的。
7 变革“六合正精”,提倡“随证治之”
按照衣之镖先生的研究,阴旦汤、阳旦汤有一个共同的药物组成即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四味药,可以叫“混元汤”。它加桂枝为小阳旦,加黄芩则成小阴旦;再加人参,就成为“大方”。[6]这是一个规律性很强的原则。
张仲景在《伤寒论》之中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些原则,而是“另起炉灶”,根据病情提倡“观其脉证,随证治之”。
以热病天行为例,医圣仲景不只是注重发热这一临床表现,而是对发热的程度和伴随症状都做了非常精确细致的辨别,同时制定了各自的治疗方法。比如,发热伴恶寒的麻黄汤证;发热恶寒伴汗出,或有鼻鸣干呕的桂枝汤证;发热伴素有咳喘,又患外感表证的桂枝汤加厚朴杏子汤证;发热伴外感表证兼内有水饮的小青龙汤证;发热恶寒伴内有燥热的大青龙汤证。这就充分体现了张仲景辨证论治的理念。
张仲景的《伤寒论》也可以称为临床上救误的代表作。因为当疾病在表证的时候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治疗,表证未去可能又损伤正气,会出现各种临床的变证、坏病。比如,表证伤阳的桂枝加附子汤证;表证身痛的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证;表证心悸的桂枝加蜀漆龙骨牡蛎汤证;表证欲作奔豚的桂枝加桂汤等证。这同样体现了“观其脉症,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思想。
这样一来,既摆脱了《素问·热论》的“日传一经”束缚,也不受《汤液经》的“六合正精”限制,而是根据“辨证论治”的实际需要,产生出一系列的“经方”。每一个“经方”都是不同病机的概括,而不是膜拜“神明之剂”,不敢越雷池一步。
《伤寒论》是集治病八法于一身、理法方药于一体的完整体系。张仲景对于每一个治疗大法的应用都很细致,包括适应证、禁忌症以及方药的煎服法和注意事项。例如,针对下法的使用,根据不同的病机特点,就有三承气汤、抵挡汤、大小陷胸汤的不同。
所以,仲景治疗伤寒的法则、方药是如此的严密、精确,被后世称为经方;张仲景也被称为医圣!一部《伤寒杂病论》决不只是汗、泄二法或者汗、吐、下三法的几个简单方药所能概括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了。
仲景六经辨证体系是中医经典理论之一,从古至今始终指导着中医临床各科的实践。其内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
王叔和作为有幸整理《伤寒杂病论》的第一人,他在《脉经》之中把张仲景的著作精华吸收进来,并且是按照“可”“不可”汗、吐、下等治法进行分类,但仍不能完全揭示张仲景六经辨证的突出贡献。
王叔和、孙思邈所说的“伤寒热病”,强调了伤寒学家对于热病学术的继承,却没有揭示从热病到伤寒的“诊治模式转化”,也难以预见日后的温病学创新。
仲景六经辨证的学术特长,是在宋代之后才被认识的。由于缺乏《辅行诀》这样的学术著作提供线索,所以,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过程里,人们对于张仲景的困惑,以及他的贡献,知之不多,研究不够。
他的学术承接前代,其著作经过晋唐时期长达千年的传承,到宋代之后引起医学名家们的重视,引发了金元医学争鸣,启迪了明清的温病学,一直影响了几千年,到现在日本仍然把他的方药作为国家药典许可的“免检”药品,畅销全球。
[1]张茂云.伤寒杂病论成书年代及仲景生平年代考[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2014,12(4):19-20.
[2]姜建国.伤寒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6.
[3]张大昌,钱超尘.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114.
[4]衣之镖,衣玉品,赵怀舟.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23.
[5]曹东义,张仲景坐堂行医或为避嫌[N].中国中医药报,2017-2-22(8).
[6]衣之镖,赵怀舟,衣玉品.辅行决五脏用药法要—校注讲疏[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226.
曹东义,男,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著有《中医外感热病学史》等多部著作。
1.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050031);2.河北中医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05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