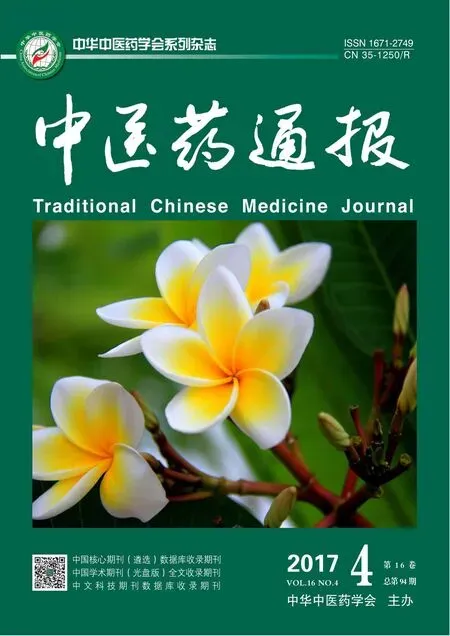学习经典 倡导多脏调燮
2017-01-14王行宽
● 王行宽 石 好
学习经典倡导多脏调燮
● 王行宽*石 好
多脏调燮 隔脏治疗 胃脘痛 癃闭
多脏调燮是中医诊治疾病的特色之一,它充分体现了中医的整体学说及脏腑相关学说的正确性和临床实用价值。
1 多脏调燮的含义
“多脏调燮”是指某一脏腑病变后,在治疗时绝不能仅仅囿于该既病之脏腑,而是应根据脏腑相生、相克的规律,当先防治有可能传变的脏腑,或兼治合并病变的脏腑。五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一脏有病,可以影响他脏;已病之脏腑,也可能是其他脏腑所殃及。故治病时必须有全局观念,当先防治未病之脏腑,或同时兼治他脏之病变,避免顾此失彼,此病甫缓,他病复剧。在多脏调燮的过程中,还能体现中医隔脏治疗的特色。隔脏治疗法,即某一脏腑病变后,不一定直接治疗该脏腑,可以根据脏腑相生、相克的关系,治疗其它相关的脏腑,而达到治疗该病变脏腑的目的,可以隔一脏、隔二脏,乃至隔三脏治疗,此为中医独特的治疗方法。《难经·七十七难》曰:“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仲景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亦言:“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笔者在学习经典著作的同时,结合自己多年的临证体验,认为肝病当先实脾的理论,还不能仅仅囿于未病先防之说,须知实脾法即是治肝病的主法之一,所谓“扶土抑木”“崇土实木”。肝脏有病,直接治肝,此为常规治法,但也可以不必直接治肝,通过调理或健补脾胃而达到治肝病的目的。《素问·脏气法时论》谓:“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难经·十四难》云:“损其肝者,缓其中。”可见其早有明训。故肝病实脾开创了中医隔脏治疗法之先例。不仅如此,实脾即培土还能生金,金气旺盛,宣肃有常,则自能克木,使木气条达,此又寓隔二脏治疗之意。隔二脏治疗的范例,还可以从“左金丸”的组方得以启迪。左金丸本为治疗肝火犯胃,胃中灼热、泛酸、吐酸而设。然方中并无直接清泄肝火之药,而是根据“实则泻其子”,木生火,肝生心,心为肝之子,故用黄连清泄心火。“子能令母虚”,从而间接使肝火得以清泄。用吴茱萸入肝,取“火郁发之”,不仅引药归经,更有加强清火之效,此为隔一脏治疗。心火既清,不仅肝火可泄,而且心火清又不能克肺金,则肺金旺又能克制肝木,岂非隔二脏治疗?由此可见,中医之治法极为丰富多彩,用不同的治法,皆可达到同一治疗目的,正所谓殊途同归。所以“辨证论治”,着重强调一个“论”字,“论”有讨论、研究、探讨之意,若用“施治”则差之谬矣!
2 多脏调燮的渊源
“江自岷山出,其源可滥觞”,“多脏调燮”的学术思想实创始于张仲景。仲景在《金匮要略》中不仅引用了《难经·七十七难》肝病实脾之文,还在《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中提出“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由此可见其倡导多脏调燮之端倪。
“肾气丸”本为治疗下消肾阳虚证而设。肾虚阳气衰微,既不能蒸腾津液以上润,又不能化气以摄水,故症见“饮一斗,小便一斗”之下消。肾气丸由八味药物组成:干地黄、山药、山茱萸、泽泻、丹皮、茯苓、桂枝、炮附子。其方虽名为温补肾阳之剂,其实温补肾阳者仅桂、附二味。其它六味,即六味地黄丸却为补益肾阴的代表方剂。因阴阳互根,阳生阴长,阳气既虚,则阴焉有不虚之理,故必兼阴虚之象。故医术高明者皆知:欲补其阳者,必从阴中而求,方能达到阴平阳秘,否则阳气虽一时获补,而温阳之剂易耗气伤阴,则阴气愈伤,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六味地黄丸的组方亦与此理相契合,欲补其阴,必从阳中求阴,故用山茱萸温涩之品,冀阳生阴长,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以“中”为主的特点。《三字经》曰:“中不偏,庸不易。”故“中”有“尚中”“中和”“中庸”之意。中医学认为人体保持“中和”,即“阴平阳秘”,才不会生病;若阴阳失衡,则疾病随之而生。故中医有“持中守一而医百病”之美誉。
更令人深思的是仲景在肾气丸的组方构思中亦考虑到了肾与脾、肝之间至为密切的关系,体现出治未病的理念。肾阳虚则火不暖土,势必会导致脾土虚弱;肾阴虚则水不涵木,又易萌生肝阴失济。故分别遣用山药、山茱萸以健脾、补肝,笔者将其称之“一级预防”。尤其称道的是还远虑到若脾虚失健则势必生湿,故选茯苓与山药相伍,不仅加强健脾之力,且兼有渗湿之功;肝为将军之官,体阴用阳,山茱萸虽能补肝,然其性温涩,恐有伤肝阴之虞,故用丹皮清热、凉血以制之;肾主水,为水脏,肾虚则水饮不化,易致潴留而成水肿,故用泽泻与干地黄相配利水湿而不伤阴,笔者又将此称之谓“二级预防”。由此可见仲景诊病思维及处方构思极为缜密:阴中求阳、阳中求阴;治肾为主,兼顾脾、肝,多脏调燮;补不忘泻、温不忘清,务在平调,冀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3 多脏调燮运用举隅
3.1疏肝和胃、佐金制木法治胃痛胃痛又名“胃脘痛”。胃脘痛有时与心脏病的症状相似。如噫气常为胃病之主症,然《素问·宣明五气》中又说“五气为病,心为噫”,故胃病与心脏病有时易于混淆。连一代名医朱丹溪亦云:“心痛即胃脘痛。”(《丹溪心法·心脾痛》)胃痛的病机关键为胃气不和。引起胃气不和的因素一般有寒、热、虚、实之分,其间又有兼夹食滞、痰凝、血瘀之异。医者据其临床症状分析,辨证论治多无谬误。然胃痛其病位虽在于胃,而涉及的脏腑绝非仅仅囿于胃腑,其中与脾、肝、肺三脏关系最为密切。脾与胃共主运化,均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气宜升则健”,“胃气宜降则和”,胃气不和必然罹患及脾;脾虚中州失健亦易致胃纳、腐熟失常。故临床脾胃病多主张并治,昔贤陈士铎称之谓“双治法”,即“双治者,一经有疾,单治一经不足,而双治二经,始能奏效,故曰双治。……如人胃吐不可单治胃而兼治脾”(《石室秘录·双治法》)。
笔者习用自拟经验方“柴百连苏饮”(由柴胡、百合、黄连、苏叶、吴茱萸、白蔻仁等组成)加减治疗各类胃病,每见良效。方中用白蔻仁者即寓胃病治脾之意,同时方中也体现出胃与肝、肺的密切关系。
首先,胃与肝密切相关。《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痛”。《素问·至真要大论》亦言:“厥阴司天,风淫所胜,民病当心而痛。”皆启示胃痛与肝木偏旺,横逆犯胃有关。肝属木,为刚脏,主疏泄,喜条达,能舒通气机。“木疏土则脾滞以行”(何梦瑶《医碥·五脏生克论》),故有利于脾胃的运化。《血证论》亦曰:“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而水谷乃化。”胃属土,主受纳,以通降为和。若肝气郁结,疏泄失司,横逆犯胃,则胃气阻遏,有失和降,故症见胃脘胀痛;木郁化酸,故胃病常伴泛酸、吐酸。历代诸贤中最先阐述肝与胃关系至密者当推张仲景。如《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治》中“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一文指明厥阴肝病可犯胃脾,引起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呕吐等症。后世医家认识到肝与胃关系密切者并不少见,如《杂病源流犀烛·胃痛篇》云:“胃痛,邪干胃脘病也……唯肝气相乘尤甚,以木性暴且正克也”,言明肝木犯土克胃乃正常的相克关系。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明确提出“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肝木必侮胃土”“肝木肆横,胃土必伤”等理论,指明胃病其病虽在于胃,而其咎实责之于肝木的道理。其倡导“两和肝胃”“凡醒胃必制肝”“安胃和肝”“抑木畅中”“治肝可以安胃”等特色治法,甚获后世医者所赞誉并借鉴。故笔者提出“治胃不疏肝木,非其治也”。“柴百连苏饮”中用柴胡为君药,疏肝解郁,条达肝气,其意即在于不使肝气横逆犯胃,则胃气自可安宁和降。
再者,胃与肺密切相关。《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气膹郁皆属于肺。”《素问·灵兰秘典论》谓:“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金克木,土生金,故肺金气机失调,宣肃失司,一则克木制肝不力;一则子病及母,子盗母气,致使肝、肺皆病,气机郁滞。对此病机,王孟英在《温热经纬》中的论述最为精辟:“肝气逆则诸气皆逆;治节不行则一身之气皆滞”。欲安宁胃气,平抑肝木,必须宣肃肺金,肺金旺盛,治节复司,则自能行经于人身之左位,起制木之能,即“佐金制木”之谓。“柴百连苏饮”中用苏叶与百合相伍,辛润结合、宣降并用,“苏叶以通肺胃……以肺胃之气非苏叶不能通也”(《温热经纬·薛生白湿热病篇》),故能宣肃肺金,金气旺则自能制木。黄连与吴茱萸同用,即“左金丸”。此即遵“实则泻其子”之训,肝火旺不直接泻肝,而清泄心火,子能令母虚;心火既清,不克肺金,肺金治节复司,则又司制木之职。
3.2宣肺化气、疏肝健脾法治癃闭癃闭是以小便量少,排尿困难,甚则小便闭塞不通为主症的一种病证。其中小便不畅,点滴而短少,病势较缓者称为癃;小便闭塞,点滴不通,病势较急者称为闭。“癃闭”之名,首见于《素问·五常政大论》:“其病癃闭,邪伤肾也。”《素问·宣明五气》曰:“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指明了发生癃闭的病机为膀胱气化不利;膀胱气化失约则发生遗尿。《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焉。”膀胱位居最下,三焦水液所归,故州都之官者,水液汇聚之处也。水液之所以能流入及排出于膀胱,全赖于膀胱气化功能是否正常。若气化不利,则发生癃闭;不约则发生遗尿。“肾司二便”,膀胱的气化功能主宰于肾,肾气旺盛,气化有力,则膀胱开阖功能正常。然膀胱的气化功能又不完全取决于肾,尚与肺、肝、脾密切相关。“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肺主气,为水之高源。若肺气膹郁,治节失司,则如王孟英所谓:“治节不行,则一身之气皆滞”。故肾与膀胱的气机亦无不例外发生郁滞,难以化气行水,则小便发生癃闭。朱丹溪曰:“通小便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窍开而下窍之水出焉。”故宣通肺气,使治节复司,三焦决渎有权,则小便自能汩汩而排出。“以提其气,气升则水自降下,盖气承载其水也”(《丹溪心法·小便不通》),此即“提壶揭盖法”之运用。笔者习用百合、苏叶、杏仁、桔梗、炙麻黄、葶苈子等药,宣降并用,以开启上源。其中以苏叶最为称道,“苏叶以通肺胃……以肺胃之气非苏叶不能通也”(《薛生白湿热病篇》)。除此之外,笔者习用桂枝,其辛温,能入肺与膀胱,宣通阳气,蒸化三焦以行水。
肝主疏泄,然肝之疏泄功能,绝不能仅仅理解为对情志而言。其它如人身之血液、津液、唾液、涕泪、尿液、大便、男子之精液以及女子之经、带、胎、产等分泌、排泄正常与否,亦均与肝之疏泄密切相关。“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素问·刺禁论》)人身之气机,合乎天地自然。肺气从右而降;肝气由左而升。左升右降,肝与肺构建了人身一条极为重要的气机升降之轴,以保证人身气机的通畅。“肝气逆则诸气皆逆”,更何况足厥阴肝经上行扺少腹,绕阴器,故泌尿、生殖方面的疾患大多与肝的疏泄功能相关。笔者在诊治癃闭时常选用柴胡、当归、白芍、枳壳、香附、郁金、玫瑰花、合欢花等疏肝之药,尤倡导用全瓜蒌。清·王学权在《重庆堂随笔》中谓:“栝蒌实,润燥开结,荡热涤痰,夫人皆知之,而不知其舒肝郁、润肝燥、平肝逆、缓肝急之功有独擅也。”亦常选用石韦,《别录》言其“止烦下气,通膀胱满,补五虚、安五脏、去恶风、益精气”,诚不失为治病及养生保健之良药。
运用益气健脾法,其意有四:一为增补气化之源;二为土克水,健脾以祛其水湿;三为培土以生肺金;四为若肝虚则祟土以实肝木,肝实则扶土以抑木亢。可谓一举四得。
综上所述,笔者治癃闭倡导以宣肺化气、疏肝健脾法多脏调燮的学术观点。下面列举医案1则以说明之。
多脏调燮癃闭案刘某,女性,58岁。2012年6月10日初诊:小便量少,点滴而下,排尿困难,伴双下肢水肿3月余。小便极少而无胀痛之不适,卧床时尿量稍增多,活动时则明显减少,多种关于肾脏的检查均无异常。舌淡红,苔薄黄,脉细弦。中医诊断:癃闭。辨证:肝郁气滞,肺气失宣,膀胱气化不利。拟疏泄肝木、宣通肺气、化气利水。方药:柴胡10g,枳壳10g,白芍10g,百合15g,苏叶8g,桔梗10g,杏仁10g,炙麻黄5g,炒葶苈10g,全瓜蒌15g,桂枝10g,白术10g,茯苓10g,党参10g,泽泻10g,石韦10g,甘草3g。8剂。
2012年6月18日复诊:夜尿明显增多,翌晨下肢水肿已不著,白昼尿量及小便次数亦近于正常。方药已弋获病机,效不更方,拟原方15剂。
3个月后因其它疾病就诊,诉原患病证己愈。
王行宽,男,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第二、三、四、五批传承老师及全国名老中医药传承工作室传承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首届名中医。对内科疑难杂症及急危重症最为擅长,对心脏疾病及胃肠疾病研究经验丰富。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