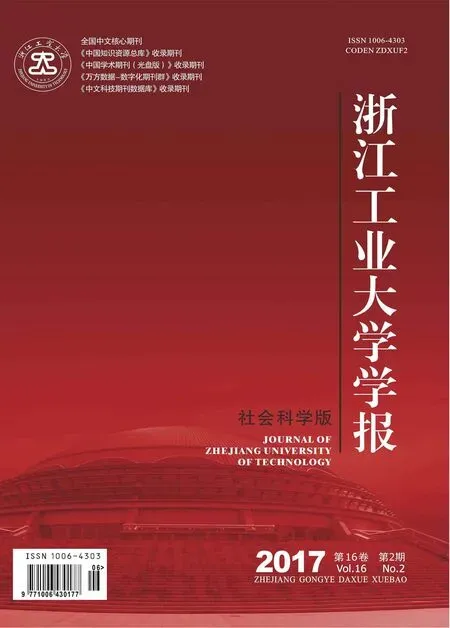转型期的乡土惶惑:论《秦腔》
2017-01-12张晓玥唐碧波
张晓玥,唐碧波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转型期的乡土惶惑:论《秦腔》
张晓玥,唐碧波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贾平凹的乡土书写始终聚焦于转型期的社会历史复杂性,并在时代精神和社会情绪的纵深透视的同时,细腻地呈现了自我的独特心灵体验。《秦腔》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乡的巨大变革为历史背景,聚焦“乡土—家园”的文学母题,以难以弥合的“家”的分裂,构成了传统乡土社会终将消逝的历史隐喻;并将自我的情感与理智的深刻矛盾贯穿其中,小说因此具有了作家的自我精神图谱意味。小说形式上注重对民间传统艺术资源的汲取,具有以情带事、事中含情的叙情性特征。乡土不再是诗意的精神故园,是《秦腔》关于中国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再发现的留白。
贾平凹;《秦腔》;乡土文学精神
在贾平凹数十年的创作中,乡土关怀贯穿始终。对他来说,乡土具有多重的意义,是自己的故乡,是由家而国的“乡土中国”,也是关于心灵家园的精神期待和情感体验。贾平凹的乡土书写始终聚焦于转型期的社会复杂性,并在时代精神和社会情绪的透视中呈现了自我的独特心灵体验。2005年出版的《秦腔》,无论在贾平凹的创作道路还是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史中,都是一部值得深入探讨的作品,由此也可以引发出关于中国乡土文学精神走向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一、乡土探寻的轨迹
80年代之初,贾平凹以商州系列小说令文坛瞩目。他笔下的陕南山地生活,空灵、古朴、悠远,充满人情人性之美,又不乏神秘气息。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很快就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冲击。《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小月前本》等,开始探索农村经济改革所引发的乡土伦理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家发现,传统乡土社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裂变,甚至逐渐解体。一方面怀着深深的眷恋,抱有浓浓的乡土乌托邦情怀,一方面又发现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新变,这就形成了贾平凹看取乡土世界时的复杂目光——意欲超离却被乡土的根性所牵扯,试图退守到自我的精神慰藉中,却又在历史理性的驱动下不由自主地展开自我怀疑。这种矛盾重重的心灵状态,充分地呈现于1988年的长篇《浮躁》。“全中国最浮躁不安的河”——州河,是改革初期的时代情绪与社会精神状态的隐喻。躁动不安,又充满生气,这是州河的状态,又是小说主人公金狗的性格特征,同时也映现出作家的矛盾心态:“惶惑中的欣慰,迷惘中的希望”[1]。80年代的贾平凹,始终处于精神家园的寻找和重构的过程中,他心存犹疑,同时又努力守护着自己的期待和信心。这种期待和信心,首先源自他的乡土乌托邦情怀,他近乎固执地赋予传统乡土的人性、人情以美好的品格;另一方面,这又是贾平凹的历史理性使然,除旧布新的时代令他对社会历史的进步性发展抱有信心。这一时期,贾平凹的不少小说被视为是“改革文学”的重要环节,正是因为他的艺术主调与时代主潮的应和。不过,由于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动的复杂性,也由于作家精神阅历的丰富和思想认识的深入,贾平凹的乡土乌托邦理想和历史理性很快发生了动摇。他发现,养育和滋养了他的乡土,绝不仅仅是田园牧歌的世界;他倍感亲切的乡风民情中,其实也留有根深蒂固的人性粗鄙,甚至丑陋;而历史的河流不可逆地向前奔涌,却也不可避免地裹挟着泥沙乃至污秽。于是,他的乡土视野中,惶惑与怀疑越来越多,越来越浓重。
沿着这样创作轨迹,90年代的《废都》,显然不是横空出世之作,而是作家的情感体验与思想认识的必然产物。这时,贾平凹的个人生活也陷入前所未有的磨难,他经历了“久病、亲亡、家破、谣言、官司等诸多不幸,他渐悟过去的商州神话几乎都是虚幻”[2]。《废都》的视点远离了乡土,转向城市和现代知识者。不过,这与“商州世界”之间,却彼此构成了一种双向的互文。从“商州”看“废都”,可以发现作家十余年来“寻乡”漂泊行旅中持续怀疑与不断失落,最终累积酵化为了的世纪末的都市颓废和知识者沉沦;从“废都”反观“商州”,则可以认识到,原来幻美的“商州”,不过是一个都市异乡人寻求情感故园时的错位了的精神对接。《废都》是贾平凹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界碑。他在后记中说,这是安妥他的灵魂的一本书;其实,这只是一种自我抚慰的表白,小说所呈现的,其实是他的无法安妥的灵魂。90年代后期,贾平凹又陆续创作了的长篇小说《土门》《白夜》和《高老庄》,依然的心灵痛楚的持续浇灌。这些作品中,城市景观愈发凸显,城与乡的对立乃至对撞也愈来愈鲜明。“白夜”本就是一个悖论的意象,明与暗,梦与醒,混乱颠倒,混沌一体。作为城市外来者的夜郎和颜铭,进入的正是一个时空颠倒错乱的“白夜”,一个污秽横流、荒芜颓圮的“废都”,因此不可避免地遭遇肉体的磨难和精神的创伤。“土门”也是一个隐喻。门是两个空间,即城与乡的临界处——“仁厚村”就处在城乡结合地带。门本应是牢固的,而“土门”却显然是不堪一击的,现代城市对田园乡村的侵袭是难以抗拒的。贾平凹眷恋着乡村,同情着乡土,甚至信仰着传统乡土的美好道德,他把笔下作为“仁厚”化身的老村长取名为“成义”。但这位村长在变革着的社会中,已经不合时宜,村民不再信任他,“仁厚”也罢,“成义”也罢,不过是莫大的讽刺。《高老庄》书写了高子路教授携娇妻西夏回乡的旅程。透过西夏的眼睛,乡村的落后、愚昧乃至污秽被呈现;高子路也因为这次回乡,陷入了与西夏以及前妻菊娃的微妙复杂纠葛,这是今与昔的情感两难,也是取舍于乡村与城市时的文化困境。
从商州到废都,再到仁厚村和高老庄,贾平凹小说构成了一条乡土探询的精神之路——起于乡土理想,又逐渐走向怀疑和瓦解。他的乡土探询不是单向的,而是始终在现代城市的参照中展开。贾平凹曾说:“慰藉这颗灵魂以安宁的,在其漫长的二十年里,是门前屋后那重重叠叠的山石,和山石之上的圆圆的明月。这是我那时读得有滋有味的两本书……山石和明月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在我舞文弄墨挤在文学这个小道上后,它们又左右着我的创作”[3]。贾平凹的乡土情感无疑是真诚且执着的。他的回顾充满着恬适的气息和诗化的意味。不过,恬适往往属于记忆。隽永空灵的记忆遭遇现实时,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种种犹疑、惶惑,甚至令人焦灼的痛楚。文学的世界中,乡土作为精神家园的隐喻,几近成为了中国古往今来的一种具有原型意味的文学想象结构,乡土情怀常常包涵着“家”的期待和诉求。在有的作家那里,“家”成为一种意识,一种具有终极色彩的意义符码。但贾平凹并非如此,“家”在他的乡土书写中,是一种矛盾性的情感记忆和情感期待,是一个复杂的甚至是悖论性的情意综;其中包含着历史理性意味的意识成分,深刻联系着中国当代的社会历史转型,但情感性更为浓重,感性的成分非常饱满,理性的诉求却相对模糊。作家诉诸于此时,意义的关切也许不是自觉的,繁复甚至纷乱的自我心灵状态的表达却不由自主。
二、乡土与家
《秦腔》(2005)是继《废都》之后,贾平凹创作道路上又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贾平凹说:“以前写商州,是概念化的故乡,《秦腔》写我自己的村子,家族内部的事情……夏家基本上是我的家族,堂哥、堂嫂、堂妹,都是原型,不敢轻易动笔,等于是在揭家务事”[4]。家事映射国事,棣花街是新世纪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这是一部写近20年农村变化的长篇小说,主要是写乡下一些事情,写现在农村为什么大量的农民离开,写农民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这样一个事情”[5]。在不可逆转的时代变革潮流中透视与自己的身心息息相联的乡土,贾平凹延续着他的乡土书写的一贯视角。这可谓是作家新世纪的精神回乡,故人与故地的故事,带来了小说情感心理蕴涵的格外繁密与复杂。
清风街的生活千头万绪,流淌着“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作家建构了一个转型期的乡村人物谱系,用以支撑“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这首先是亲缘关系的族谱,并将转型期的政治和文化的复杂性隐含其间。作家取义儒家“四德”,将老一代夏氏四兄弟分别取名为天仁、天义、天礼和天智,赋予他们传统道德和价值的寄托。夏天义是卸任的村支书,他以淤地造田为自己的理想抱负,他的事业曾经风生水起,一度“成了清风街的毛泽东”,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代言人;夏天智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曾经做过小学校长,晚年醉心于秦腔脸谱的绘画,代表着传统的乡土文化。新任村支书是夏天义的侄子君亭,他试图大展宏图,建设集贸市场,城镇化、商业化的变革将彻底打破传统农村的社会经济形态。不过,村长秦安却是夏天义的继承者,他坚持以农业为本。夏天智的长子叫夏风,一位在城里已经小有名气的记者,秦腔在他眼里不过是“下里巴人”的游戏,不值一提。不过,夏风的妻子白雪确是当地的秦腔名角,丈夫眼中土里土气的乡土艺术,是她的挚爱。这显然是矛盾重重的新一代。夏氏的年青一代,已经是叛离传统的一代;而守护承继的那一方,却是外姓人。双方在角逐,但结果却是秦安斗不过君亭,秦腔正在不可逆转地持续衰落着。作家给予年轻一代命名颇富深意。君亭谐音“君停”,这或许是作家代表传统一脉而发出劝诫和希求。然而,在滚滚而来的城镇化(城市化)的浪潮,终究是素朴的乡土情感所难以抵挡的。一切终将逝去,一切都无法挽留。棣花街作为三秦大地上小小的一域,注定无法安然其外——“秦安”不可求,扑面而来的是“秦不安”。有人觉得秦腔土里土气,有人却视之为“阳春白雪”——“白雪”与“夏风”将如何相容?夏天智的幼子叫夏雨,一个游手好闲的乡村小混混。风雨欲来,传统的风习、价值、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注定要飘摇于世了。白雪和夏风的家庭自然不和睦,夏风不仅读不懂,甚至也无意其读懂白雪的心。变革时代中的夏氏家族,老辈的兄弟们依旧情重和睦,但到了年轻一代,每个家庭都危机重重,鸡飞狗跳。而那些外姓人家,媾和、偷情之事更是时常发生。这是一个轰轰烈烈、除旧布新的乡村,这又是一个分崩离析、礼崩乐坏的乡村。礼义仁智,难以代传。从血缘家庭的内部开始,传统在瓦解,在断裂,在破败,这如同细胞分裂一般快速地扩张,断在根子上,颓势不可挡。
面对乡土,中国现代作家有启蒙理性立场的批判,也常诉诸个体情感性的追忆,更多是两者的结合,而缺乏的却是一种更高审美意义上的超越性审视。审美超越需要以知识理性和历史认知为思想前提,同时也更需要人类性意义的心灵体悟能力。由于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以及宗法人伦的文化积淀,长期以来,中国作家习惯于在乡土中寻觅和寄托家园情结。持续的历史转型进程中,很多作家经历了由乡入城生活变迁,难免怀有客子之感的生存体验,在文化身份与情感认同之间陷入矛盾。他们身在城市,却在城里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因此以乡愁的情感为内核,以忆乡的心理为支撑,以归乡的叙事为框架,从城市异乡人的姿态和立场出发构建乡土乌托邦的精神净土,往往成为他们的乡土书写的显著形态。《秦腔》之前,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多少具有着“乡土神话”色彩,而《废都》《白夜》等,又有着鲜明的“城市噩梦”意味。这些,都没有超越这样的情感维度和精神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中审视,《秦腔》就显出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它标志着贾平凹的乡土—家园情结的终结,因此成为了他个人创作道路上一座新的里程碑。传统乡土的消逝不可逆转,以小说叙事中无法弥合的家的分裂结构,隐喻关于当代中国的历史认知,是《秦腔》最重要的思想艺术探索,这也构成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乡土—家园”母题的新的纵深透视和表达。“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6]。鲁迅在1935年写下的这段话,围绕“侨寓”处境和“乡愁”心境展开,在揭示当时的乡土派作家追觅精神家园的创作特点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他们内向型的自我写作,指出了这种实际是难以开拓读者的心胸和视界的。《秦腔》不同于过去的乡土小说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作家敏锐感受到,在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乡土—家园”的精神神话其实只是虚幻的自我想象。认识到这一点,无疑带给他一巨大的情感创伤,但他还是以“家的分裂”来瓦解了这一神话。贾平凹在《秦腔》后记写道,这部小说是“为了忘却的记忆”“为故乡竖起一块碑子”。这是他一次纪念碑式的写作,纪念的同时,也是标明了诀别的姿态。但他眷恋乡土的情感却是挥之不去的,因此他的写作自然也就“充满了矛盾和痛苦”。
三、疯癫与叙情
按照通常的艺术观念,小说总是被视为是一种叙事的艺术。不过,《秦腔》的独特艺术风貌,却难以用叙事这个词来涵盖。小说试图以一种节制自我和隐藏主观意识的方式展开叙述,但叙述的过程又处处含情。《秦腔》煌煌40余万言,所呈现的是清风街的各种庸常琐事,各式人事短长,这是一部由日常细节的铺叙构成的小说。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说,清风街的故事并非是“茄子一行豇豆一行”那样清晰可见的,而是“老是黏糊到一起的”,这就好比用长竹竿打核桃,“明明已经打净了,可换个地方一看,树梢怎么还有一颗?再去打了,再换个地方,又有一颗。核桃是永远打不净的。”贾平凹所聚焦的,其实不是各种故事,而是事中之情。换言之,与其说作家在叙事,不如说他在叙情,通过鸡零狗碎的铺展寄托一种复杂的自我情感状态。他眼看着曾经情牵的乡土在时代的变革中开始面目全非,亲近的变得遥远,熟悉的变得陌生,于是既爱又恨,恨又不忍,恨中于是生怜,怜而伤情,进而悲罢作别,却别亦难舍。他由衷地对老一代的天义、天智抱有敬意,那样的诚挚,却又无可奈何地哀叹他们已经“不合时宜”;至于君亭、夏风,他是批评的,但不苛严,有一点嫌恶之感,却又抱着理解;秦安是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对象,但作家也明秦安即便争了也是争不来什么的;至于白雪,就像她的美好的名字一样,想要小心翼翼的捧在手心里,但却又无奈地目击她的注定要融化的命数。小说展现了一个家长里短的世界,诸如夏天智画脸谱、夏天义吃凉粉、秦安赌博君亭报警、夏风白雪夫妻怄气、乡村戏团的演出风波等等,作家的既真又浓的复杂情感,就渗透流淌在其间。
《秦腔》出版以来,批评界多从叙事的角度展开评析。其实,这与其说是一部具有叙事独特的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叙情性的小说。以情带事,寄情于事,是《秦腔》的显著的叙述特色。叙情是我国民歌、民谣的常见艺术手法,这在江南吴歌的长篇叙事诗中表现得尤为显著。陕北民歌相对来说体制较短小,但也常常以因事生情的铺叙为主。用叙事和抒情的二元思维来阐释《秦腔》,难免有些捉襟见肘。叙情作为叙述方式,一方面表现出了地道的“土气息、泥滋味”[7],一方面又是作家探索自我心灵的痛楚与矛盾状态的路径所在。引生和夏风是与白雪发生着情感纠葛的两个男性,也透露出作家自我的两个不同的侧面。疯子引生忠实地追随着夏天义,他深深地爱着白雪,甚至在“伤害”了白雪后自断生殖器。这一行为怪异,多少带有些超现实意味的角色,显然被作家赋予了特定的象征意义。引生对白雪的爱,隐喻着对传统乡土生活和文化的超功利的爱,不过,在转型甚至断裂的当下乡土生活中,这是不合时宜的,于是只能以疯癫的状态存在。引生既是故事中的角色,同时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他又常常超离于故事之外,这正是作家试图表达和纾解的矛盾重重的自我心灵状态:深爱乡土,深爱乡土传统中的美好、纯洁与质朴,但这些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发生着难以挽回的异变。所以他只能把引生塑造成一个疯子,疯是爱得深、爱得不顾一切的特殊表现。但是,他的所爱正在消逝,无可挽留的消逝着,那么,施爱者的如何能够不疯呢?疯固然是变态,但变态有时又是常态的一种极端形式。引生的对立一方是夏风。他在乡村长大,后来进了城成为文化人,却因此看不起农村了。通过一些村民的视角,小说有分寸地批评着夏风,但却也抱着一定程度的理解。他是家乡人的骄傲啊!毕竟如今的家乡落后了,留存着那么多的愚昧,藏着许多见不得光的污秽。夏风其实也是一个矛盾的构成,出身于农村,却是城市的知识者身份,这不免让人联系到作家的自我。夏风和引生的矛盾对立,或许正是作家心灵世界的不同侧面。这是经受着分裂之痛的心灵,理智引导他从乡村走向城市,但根性的情感却丝丝缕缕、缠缠绕绕,剪不断,理还乱。这是贾平凹的心灵复调,纷乱如麻又痛苦不堪。小说正是作家一幅身心分裂、情理对峙的自我精神图谱。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在这里,“作家把自我劈成几份,分配到他的小说的一些角色中去”[8]。
小说《白夜》中穿插了许多目连戏内容,意欲表现城市外来者的异化主题,营造人神鬼杂糅的神秘氛围。对此,贾平凹说:“在近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目连戏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即阴间阳间不分,历史现实不分,演员观众不分,场内场外不分,成为人民群众节日庆典。祭神求雨、驱魔消灾、婚丧嫁娶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9]。目连戏,正是《秦腔》艺术构思和表现重要艺术资源之一。引生时而疯,时而醒,疯语疯言,经常灵魂出壳,亮出诡谲谶语,他兼有叙述者与故事角色的双重身份,通过在故事里跳进跳出的方式实现双向的功能。这同目连戏内外交合的舞台结构,以及观演合一的演剧方式,其实是异曲同工的,而且也与作家面对故土的异变时若即若离,却始终无法超离的心态彼此呼应。这进而构成了小说看似混杂交错的氛围,这种氛围又与乡村的日常泼烦生活状态彼此形成互文关系。如果将小说的世界理解为一个生活的舞台,那么其间上演的则是一出具有鲜明目连风格的大戏。贾平凹不仅是这场戏的导演,他甚至时常急切地意欲带上面具,粉墨登场。小说也引用了不少秦腔的唱段,多为悲腔、苦腔,是为了烘托小说的韵调和氛围,其阅读效果可能因读者的接受而又差异,关键则在于读者对秦腔艺术本身的了解。这如同《秦腔》以及作者的其他很多小说一样,多呈现鲜明的陕西口语风格,其中的味道可能只有陕西人才能体味得最真切——拆开“秦腔”二字,“秦”即秦地陕西,“腔”则是当地人常说的腔口。从贾平凹给人物命名时的隐喻象征来分析,小说的题名其实也暗示着他对语言风格的自觉追求。
四、表现与发现
有评论者认为,贾平凹通过“半痴不傻、半疯不癫、神神道道的叙述者引生”来表现 “朴素的情感”,“显得太突兀”,因此“朴素的情感也不免变形了”[10]。这其实误读了《秦腔》的艺术探索。作为一部铺叙“生活流”细节的小说,《秦腔》的艺术不是再现型的,而是以再现为方式的表现型的作品。作家以叙情为目的展开叙事,所叙之情感其实并非是“朴素”的。它是“哀伤、悲悼、惶恐、冲突、分裂、纠缠”的,这样的情感状态,需要一种变形扭曲、疯癫中透着清醒的口吻来承载。贾平凹强调,为了还原乡村生活的真实,他采用了“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对此,评论界基本持有肯定和认同。而用非常态的方式,表达自我情感和心理的复杂状态,其实也是出于同样的艺术思维。接受小说的特色化的叙述方式,却拒绝这种叙述方式的主体(叙述者),这在立论的逻辑上不免有自相矛盾之嫌。究其原因,这源自再现与表现的二元分立的认识思维。从文学的最高精神的角度看,再现总是有限的,再现也通常是意向性的,所谓客观地反映,结果也总难免是主观表现的另一种呈现。文学世界作为心灵世界,作家自我心灵的滤取是文学进入现实的本质方式。
与《秦腔》再现方式的表现性相联系,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文学的心灵发现的问题。表现复杂的或纯净的心灵,是文学,这是心灵史的书写或者是心灵横断面的透析;发现人们所忽略或尚未充分感知的心灵,也是文学。心灵的发现,是对既定现实以及既有存在的超越。发现总是具有时间性的,任何发现都不可能具有永恒的发现性,发现也具有心灵史的意义——未来时态的心灵史的意义。表现与发现之间并无必然的高下之别,也不能截然分开。但既然人是时间中的存在,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只拥有有限的时间,那么就有理由要求人的文学提供给人能够超越有限物质生命的新的心灵发现。在心灵表现中抵达心灵发现,具有最高意义的审美价值。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史上,鲁迅发现了国民性的劣根及其文化土壤,沈从文发现了自然人性疗救现代文明病的意义,孙犁则试图发现了战争背景下人性的诗意。用今天的眼光看,《秦腔》的发现是,在当下社会语境中,乡土不再是一个具有精神家园意义的神话。这是一种否定性的发现。
《秦腔》呈现出一种对位型的艺术思维,即追求表现方式与表现内容在风格、情调上的呼应——以一地鸡毛的细节来还原凡庸日常的生活,以扭曲分裂的形象来表现情理对峙的自我心灵。这是贾平凹持续在探索的一种的艺术方式和小说观念。他曾在《高老庄》后记中说:“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这源于我对小说观念的改变。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什么,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张扬我的意象”[11]。这种贴地而行的艺术自觉,其实也不免令人有匮乏之嫌,匮乏于超越生活本身、超越自我困境的精神洞见力。面对生活的复杂以及自我的困境,作家陷入得很深,却未能有所超离,因此也就使《秦腔》的心灵发现,止步于一个否定性的命题。否定当然并非无价值,否定隐含着新的创造的可能。有人称台湾作家白先勇为“最后的贵族”。关于乡土和农民,他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中国落后,农民占了最大多数,他们没有机器,要很辛苦才种出东西来,真是‘粒粒皆辛苦’。他们的劳苦,知识分子尊敬。但换个环境,在美国,农民只有百分之五,工作一点也不辛苦,样样都有机器,在美国我就看不出农民崇高在什么地方。美国的工人,一点也不苦,往往有几部汽车。农民、工人劳苦本身不足以决定文学内容的丰富或贫乏”[12]。这里并没有高高在上的贵族心态,白先勇其实只是通过一个历史事实——超越国界的世界性眼光中的历史事实——去探问文学的最高价值。由此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关于乡土或农村文学,“中国意识”与“世界意识”之间,“中国情感”与“人类情感”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从人类性看取中国性时,后者的精神高度和历史深度究竟在哪里?这种高度和深度,从美学的角度具有怎样的意义?在行进中的中国社会变革与历史转型过程中,乡土作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重要精神资源,将得到怎样的再发掘?这是值得深思的命题。乡土不再是诗意的精神故园,“为了忘却的记忆”其实难以忘却的,留住它,是踏上新路的起点。这是《秦腔》关于中国新世纪乡土文学之再发现的留白。
[1] 李星.混沌世界中的信念和艺术秩序——《浮躁》论片[J].小说评论,1987(6):29-34.
[2] 李自国.论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家园意识[J].当代文坛,2000(6):24-27.
[3] 贾平凹.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C]//雷达.贾平凹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4.
[4] 贾平凹,郜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J].上海文学,2005(7):58-61.
[5] 张英.贾平凹:回到商州[N].南方周末,2004-5-13(13).
[6]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M]//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5.
[7]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C]//吴平,邱明一.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303.
[8] 杰克·斯佩克特.艺术与精神分析——论弗洛伊德的美学[M].高建平,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116.
[9] 贾平凹.白夜:后记[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387.
[10] 刘志荣.缓慢的流水与惶恐的挽歌——关于贾平凹的《秦腔》[J].文学评论,2006(2):146-151.
[11] 贾平凹.高老庄:后记[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415.
[12] 白先勇.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M]//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235-236.
(责任编辑:薛 蓉)
Confusion about the rural society in transition: study on Qin Qiang
ZHANG Xiaoyue, TANG Bibo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Jia Pingwa’s unique creative feature lies in his represent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self within the historical and emotional complexities of a transitional society.QinQiangmetaphorically blends the irreversible elapse of tradition into an irreconcilable fragmented structure of family, and in some degree achieves the new profound perspective of the literature motif called “native soil—home”. This expressionistic novel, which shows a division of the physical self and the psychological self as well as the mental self and the sentimental self, fully represents the psychological pattern of the novelist himself. Stylistically, as a sentimental narration, it derives a lot from the traditional artistic resources, and shows its best when the affection is combined with the narration.
Jia Pingwa;QinQiang;the spirit of rural literature
2017-03-28
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NDJC181YB)
张晓玥(1976—),男,辽宁沈阳人,教授,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影视研究;唐碧波(1992—),女,浙江奉化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
A
1006-4303(2017)02-02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