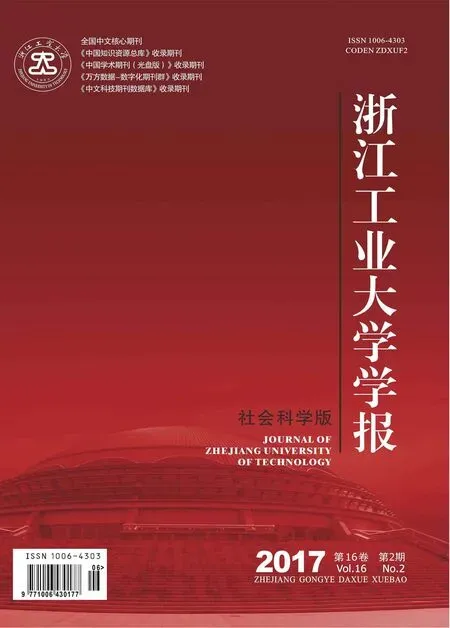非公有制财产刑事法律保护的缺陷及其完善
——以职务犯罪为视角
2017-01-12张兆松周淑婉
张兆松,周淑婉
(浙江工业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310023)
非公有制财产刑事法律保护的缺陷及其完善
——以职务犯罪为视角
张兆松,周淑婉
(浙江工业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310023)
加强对非公有制财产刑事法律保护是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的重点之一。现行刑法规定的职务犯罪,在罪名设立、犯罪构成、定罪标准、刑罚处罚等方面,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歧视非公有制财产保护的现象。由于刑事立法的缺陷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刑事司法中的“平等保护”难以实现。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不符合我国《宪法》和《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立法机关应尽快将加强对非公有制财产的刑法保护纳入立法修正计划。
非公财产;职务犯罪;缺陷;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
2004年《宪法》修正案专门将“平等保护公私财产”条款规定在国家根本大法中,旨在明确和强化对非公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十八届四中全会2014年10月23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指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十二届四次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1]。为了贯彻落实宪法原则和中央四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先后出台司法文件对非公有财产的法律保护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12月17日出台《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16年2月19日出台《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但由于刑事立法的缺陷,刑事司法在保护非公有制财产方面始终步履维艰。
为了加强产权保护,加快推进“平等保护”原则的实现,中共中央、国务院2016年11月4日颁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坚持平等保护。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意见》还首次特别要求:“加大对非公有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为了进一步落实《意见》精神,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11月28日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17年1月6日出台《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在上述司法文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强调:“坚持平等保护。坚持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对各类产权主体的诉讼地位和法律适用一视同仁,确保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注重对非公有制产权的平等保护。”最高人民检察院强调:“坚持平等保护原则,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的财产权,确保各类产权主体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平等、法律适用和法律责任平等、法律保护和法律服务平等。”
为了实现平等保护原则,“在刑事司法方面,应平等对待侵犯不同所有制公司、企业权益的刑事案件,不能因为是非公有制公司、企业而采取差别待遇”[2]。但是,立法规定是司法适用的前提,我国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刑事司法的根据是刑法的具体规定。如果没有刑事立法上的平等,就不可能有刑事司法上的平等。但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滞后于宪法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3]。有学者认为,“未来中国的刑法立法从技术层面需要考虑进行相当规模的犯罪化”[4]。笔者认为,这在非公财产刑事法律保护方面尤为必要。本文旨在通过对现行职务犯罪的分析,揭示现行刑法对非公财产保护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供立法机关在修改刑法时参考和借鉴。
二、非公有制财产刑事法律保护的缺陷
(一)非公单位职务犯罪罪名缺失
1.性质相同的危害行为,刑法仅保护国有资产。“97刑法”在第8章“贪污贿赂罪”中设专条规定“私分国有资产罪”(第396条)。本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国有单位中的国有资产,将私分非公有财产的行为排除在刑法打击的范围之外。所以,实践中对一些非公单位的工作人员,集体私分单位财产的行为就无法得到刑法的制裁,严重侵犯了财产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2.某些渎职犯罪主体仅限于国有单位工作人员。“97刑法”中,国有公司、企业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为了保护我国市场主体的管理秩序,“97刑法”专门在第3章第3节规定了“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并在第165条、166条、167条、168条分别规定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等5个罪名。这些犯罪主体必须是“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或者“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非公单位工作人员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为亲友非法牟利,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失职或滥用职权行为,不管行为多恶劣,后果多严重,都不构成犯罪。
(二)非公单位定罪标准低于公有单位
目前,“两高”司法解释往往对单位犯罪和自然人(个人)犯罪规定不同的定罪标准。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0年5月7日《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规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定罪起点数额是:个人行贿1万元,单位行贿20万元。单位定罪数额标准是个人定罪数额标准的20倍。而司法实践中长期将非公单位排斥在单位犯罪主体中。这就意味着非公单位行贿1万元即构成犯罪,而国有单位行贿20万元才构成犯罪。“97刑法”第30条明文规定单位犯罪主体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按照当然解释的原则,“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当然应包括非公单位。但落后的司法理念和传统的司法惯例,非公单位一直视为自然人犯罪主体。这一现状直到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出台《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单位犯罪解释》)之后才有所改变。根据《单位犯罪解释》规定,刑法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这一司法解释虽然有所进步,改变了以往司法实践中一概将非公单位犯罪视为自然人犯罪的做法,但它仍没有把平等原则贯彻到底。因为《单位犯罪解释》规定,独资、私营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只有具备“法人资格”,才算刑法中的“单位”,而对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则毋须“法人资格”的限制,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会议纪要》和指导案例,司法实践中还把公有制单位的内设机构也视为单位犯罪主体。这明显背离刑法平等原则,加重非公单位的刑事负担。
(三)非公单位职务犯罪要求高
1.非公单位职务犯罪构成苛严。(1)根据刑法第163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要求必须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不论是“收受型”的受贿和“索取型”的受贿,都要求同时“为他人谋取利益”,否则不构成犯罪。而刑法第385条所规定的受贿罪则区分“收受型”的受贿罪和“索取型”的受贿罪,对“索取型”的受贿罪不要求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不仅如此,“两高”2016年4月18日《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第13条第2款还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出了推定性规定,即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司法推定性规定,有利于降低检察机关指控受贿犯罪的难度,而这一司法解释仅适用于受贿罪。(2)贿赂犯罪对象过于狭窄。我国贿赂的对象,刑法仅限定为“财物”。为了适应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两高”《解释》第12条对“财物”作了扩张性解释,即“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这一规定是符合时代和廉政要求的。但这一合理的司法解释也仅适用于刑法第8章所规定的受贿罪,而不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2.非公单位职务犯罪定罪数额过高。根据原司法解释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是5千元,职务侵占罪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是5千元至1万元。但“两高”《解释》在大幅度提高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的同时,还大幅度提高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即将这两个罪名的定罪起点数额提高到了6万元。这不仅是国家工作人员贪贿犯罪数额的2倍,而且使非公职务犯罪与普通侵财犯罪(盗窃、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更加悬殊(是盗窃罪的20~60倍,是诈骗罪的6~20倍)。
(四)非公单位人员职务犯罪刑罚过轻
1.主刑偏轻。1997年我国修订《刑法典》时,立法机关将传统的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加以分解,将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从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置罪名和法定刑。前者适用非公单位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后者适用公有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两者重要区别之一是法定刑不同。非公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挪用资金罪的法定最高刑分别是15年和10年有期徒刑;而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的法定最高刑分别是死刑和无期徒刑。对非公单位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处罚偏轻,表明现行立法歧视对非公财产的保护,也严重影响对非公领域腐败犯罪的打击。
2.附加刑缺失。《刑法修正案(九)》的一大亮点之一就是对贪贿犯罪普遍增设罚金刑。经修正后,《刑法》第8章所列的各个罪名,绝大部分都已增加了罚金刑的适用*包括贪污罪、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但对非公单位的犯罪,《刑法修正案(九)》除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164条)”增设了罚金刑外,其他非公单位的职务犯罪,《刑法修正案(九)》没有作出任何修改规定。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均没有规定罚金刑,其中挪用资金罪没有规定任何财产刑。
(五)“二元”管辖体制严重影响刑事诉讼
根据现行立法,国家工作人员贪贿犯罪由检察机关立案管辖,非国家工作人员贪贿犯罪由公安机关管辖,这种“二元”管辖体制带来诸多问题,表现在:
1.管辖冲突,影响对职务犯罪的查处。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我国传统的国有企业已越来越少,绝大多数已改制成为国有控股、参股企业,而这类企业中哪些人可以构成贪污、受贿罪,哪些人只能构成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往往争议很大。尤其是立案之初,事实尚待查明,定性问题难以明了。面对此状,“二元”管辖体制带来的问题是:案件好办、阻力小、干扰少的案件,公、检争管辖;而案件难办、阻力大、干扰多、关系网厚的案件,公、检不管辖,互相推诿。这直接影响对腐败犯罪案件的及时查办,造成群众举报难、告状难。特别是一些基层检察机关面临贪贿案件查处数量的考核,为了完成办案数,就把一些明显属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贿犯罪,按贪污罪、受贿罪立案侦查,以规避职能管辖的冲突。
2.管辖冲突,引发执法难题。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被检察机关管辖了或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被公安机关管辖了,管辖主体错误如何救济?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在职务犯罪的侦查中,管辖主体错误不影响侦查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5];第二种观点认为,管辖错误是重要的程序违法,先前的侦查行为应当无效,合法的侦查机关应当重新立案侦查[6]。由于理论上有争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12月22日专门作出《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改变定性后可否直接提起公诉问题的批复》。根据该《批复》精神,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或者“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且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管辖。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直接起诉。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92条仍沿袭了上述规定。应该说上述司法解释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也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但由于我国检察机关不享有完整的侦查管辖权,该解释的法理依据并不充分,实践中仍有争议。
三、完善非公有制财产刑事法律保护的思考
坚持平等依法保护,“根本上是要完善法律体系和制度安排,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各种不合理规定,消除隐性壁垒,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7]。鉴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对现行的职务犯罪规定从以下方面作出修改。
(一)进一步扩大非公人员职务犯罪范围
1.增设、修改罪名。为了扩大对非公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在刑法第3章第3节规定的“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作出如下修改:(1)增设私分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资产罪。(2)将刑法第169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修改为“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资产罪”。
2.扩大非公单位职务犯罪主体。即将现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等5个罪名的犯罪主体,由原来的国有单位(国有公司、企业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扩大到所有单位的工作人员,从而把非公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腐败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二)将非公单位明确纳入单位犯罪主体
鉴于当前对单位犯罪主体理解的不一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对《刑法》第30条所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含义作出立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刑法》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包括非公单位。在立法解释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对单位犯罪的司法解释作出修改:刑法第30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从而使公有单位和非公单位犯罪适用同样的法律条件。
(三)降低非公单位职务犯罪要求
1.放宽非公单位的犯罪构成要件。(1)取消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受贿犯罪侵犯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和不可收买性,特殊主体(不论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只要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了他人贿赂,就构成刑事犯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刑法要求受贿罪必须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2)扩大贿赂的范围。世界上一些廉洁国家都将贿赂范围规定得非常宽泛,如新西兰1961《犯罪法》第99条规定:“贿赂是指任何金钱、有值对价、职务、工作或者任何利益,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的”;新加坡《预防腐败法》第2条规定,“贿赂”包含任何提供、许诺或者约定报酬的行为。我国刑法学界对贿赂的范围有“财物说”“物质性利益说”和“利益说”三种观点[8]。笔者认为,贿赂犯罪的本质属性、社会危害性和当前贿赂的现状及国际公约的规定等,都要求立法机关必须对贿赂的范围,由“财物”“财产性利益”扩大到各种利益。在立法机关对贿赂范围作出修改之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的贿赂的认定可以参照“两高”《解释》的规定。
2.降低非公单位定罪量刑数额标准。“两高”《解释》大幅度提高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不仅偏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和刑法原则,而且违背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导致大量非公单位的职务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加剧我国职务犯罪的蔓延,实不可取。再说,“调高贪污贿赂犯罪数额标准短期内并不能解决刑事司法实践难题,长期看更无益于提升惩治腐败犯罪效益”[9]。笔者认为,应当大幅度地降低非公单位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目前,至少要降至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一样,才谈得上“公私平等”。
(四)修订非公单位职务犯罪的刑罚
1.提高非公单位犯罪的自由刑。现行非公单位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刑罚偏轻,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如笔者近期代理的被告人林斌职务侵占案,林原系宁波富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总经理,他在2015年6月至2015年9月期间,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侵占的公司货款1亿余元人民币用于炒股、赌博等,案发后仅追回几百万元,导致公司破产倒闭,危害十分严重,而根据刑法规定,林最多只能判处10~15年的有期徒刑,这显然不利于惩治犯罪。所以,应将现行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的刑罚,由有期徒刑15年提高到无期徒刑;挪用资金罪的刑罚由有期徒刑10年提高到有期徒刑15年。这样的刑罚设置,一方面可以与盗窃、诈骗等普通侵财犯罪的刑罚保持一致性,另一方面又相对低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贿犯罪,以示对国家工作人员贪贿犯罪从严。
2.增设非公单位犯罪的罚金刑。《刑法修正案(九)》对国家工作人员贪贿犯罪普遍增设了罚金刑,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贿犯罪则没有增设罚金刑,这仅用立法疏漏是难以解释的。这表明立法机关重视的还是公有制单位的职务犯罪。对贪贿犯罪分子适用罚金刑是对其犯罪动机的反制。《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的司法实践证明,罚金刑对贪利型的贪贿犯罪具有较好的刑罚规制效果。所以,要进一步扩大罚金刑对职务犯罪的适用,特别是对非公单位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适用。要通过刑法的再修订,实现罚金刑对所有职务犯罪的全覆盖。
(五)统一职务犯罪职能管辖
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划归公安机关管辖后,一直存在打击力度不够的问题。如2010至2014年5年间,浙江宁波市检察机关办理受贿案件528人,而公安机关同期移送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仅49人;浙江衢州市检察机关办理受贿案件174件182人,而公安机关同期移送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仅24件32人。有的公安机关连续几年没有办理一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这充分证明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由不同机关管辖的做法,不利于保护非公财产和对非公单位职务犯罪的打击。笔者建议统一职务犯罪立案管辖权。如香港反贪机构廉政公署(ICAC),“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有效遏制了政府内集团式贪腐之后,私营机构已成为廉署重要的工作对象。最近5年,在香港廉署每年收到的近3000宗贪腐举报中,有至少6成举报针对私营机构”[10]。目前,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已步入试点阶段,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及所辖县、市、市辖区将设立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职权[11]。随着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腐败犯罪侦查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将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统一行使。笔者建议,届时应将非公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统一划归监察机关行使。
平等保护的背后是特权和歧视。“立法要真正引领改革、保障改革,让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平稳推进,就必须根据改革的要求,对涉及到产权的法律法规进行及时的立改废”[12]。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存在着较严重的重公有制财产保护、轻非公财产保护的现象,存在明显的对非公有财产的歧视。刑事立法缺失的背后凸现的是立法理念的滞后,只有立法机关真正树立平等保护的立法理念,才能制定出一部体现平等保护的刑法典,而只有实现立法平等,司法平等才能落地生根。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应根据宪法和中央《意见》精神,把如何加强对非公财产的刑法保护纳入立法视野,着力推动刑法典的修改。在未来刑法修订中,把非公有制财产保护放在应有的位置,从而真正使平等保护原则在刑事领域得到实现。
[1]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6-03-05(1).
[2] 时延安.非公经济刑法保护应遵循三项原则[N].检察日报,2017-03-11(3).
[3] 赵丽,王曼宁.“加大非公有财产刑法保护”背后有何深意[N].法制日报,2016-12-07(5).
[4] 周光权.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J].法学研究,2016(4):23-40.
[5] 游伟.商业贿赂犯罪的侦查管辖与证据效力[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5):129-131.
[6] 王俊民,潘建安.刑事案件职能管辖冲突及其解决[J].法学,2007(2):154-157.
[7] 杨维汉.公私财产保护须一视同仁[N].新华每日电讯,2016-11-28(1).
[8] 周光权.刑法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77.
[9] 谢杰.贪污贿赂犯罪治理的制度优化与规则补充——基于对最新司法解释的法律与经济双面向反思[J].政治与法律,2016(3):30-42.
[10] 冯学知.香港廉署反贪防腐不问公私[N].人民日报,2016-12-22(20).
[11] 姜洁.中办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N].人民日报,2016-11-08(3).
[12] 秦平.产权改革最终考验的是法治[N].法制日报,2017-03-07(1).
(责任编辑:薛 蓉)
On the defects and perfection of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of non-public prop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ty crime
ZHANG Zhaosong,ZHOU Shuwan
(College of Law,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China)
How to strengthen the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of non-public property is one of the key points of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in China. In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there is a seriou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protection of non-public propert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uty crim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duty crime, the standard of conviction, punishment and other aspects.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rime,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equal protection in criminal justice. The existence of this phenomenon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criminal law in China. Therefore, China’s legislature should put the protection of the non-public property of criminal law into the legislative amendment plan as soon as possible.
non-public property; duty crime; defect; perfect
2017-03-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FX078)
张兆松(1962—),男,浙江金华人,教授,硕士,从事职务犯罪、检察学研究;周淑婉(1996—),女,浙江金华人,从事刑法学研究。
D914
A
1006-4303(2017)02-02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