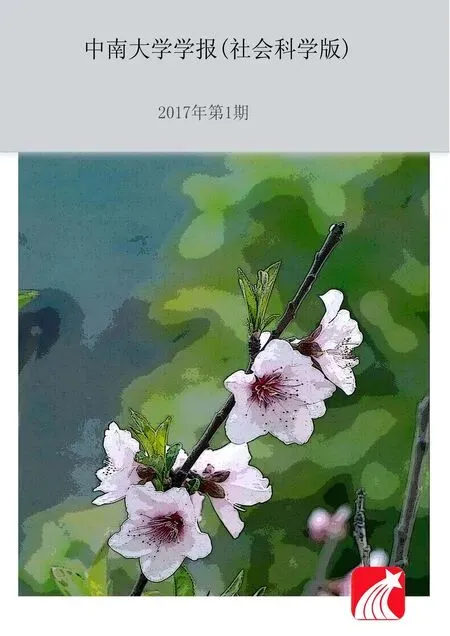俄罗斯治理变革策略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17-01-12孔令秋
孔令秋
(哈尔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俄罗斯治理变革策略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孔令秋
(哈尔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全盘西化”的社会转型虽然打破了苏联“全能型国家”的禁锢,并初步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多元共治的格局,但畸形的国家治理和低效的“民间治理”使俄罗斯转轨出现了政治上的纷争与动荡、市场经济中的丛林生态以及社会的分裂与混乱,陷入了严重的秩序危机。普京在叶利钦改革所构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基础上,将更多的俄罗斯元素注入到治理变革当中,努力打造国家治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同时加强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建设,以此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双强均衡”,逐渐探索出一条自主化发展的“俄罗斯治理之路”。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俄罗斯在坚持“强国家”的前提下,不断增强社会的自治能力,并拓展社会的自治空间,构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回应机制。俄罗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策略以及治理变革路径的演变对处于社会深度转型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民间治理;法治秩序
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由国家启动、以西方为样本的治理变革历经一系列失败、挫折与阵痛后,终于走上了一条自主化发展的“俄罗斯治理之路”。从现状看,俄罗斯已经摆脱了20世纪末的秩序困境,依靠走自主化和自我发展的治理之路实现了秩序的重建。基于“东方专制主义”历史传统以及转型期现实困境的相似性,俄罗斯治理变革策略的演变对当代中国治理路径与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叶利钦时期非政府组织的崛起与治理失衡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俄国)建立了国家主义色彩极其浓重的苏维埃政权,“全能型国家”和“总体性社会”使苏联的集权程度不断增强直至失控,最终走上了解体的不归之路。俄罗斯独立后,“全盘西化”的转型战略使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离,催生了社会自主自治的强烈愿望,非政府组织的瞬间崛起与发展,为治理秩序的生成提供了主体准备,但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失衡却使俄罗斯陷入了严重的秩序风险。
(一) 叶利钦时期的激进变革与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取“全盘西化”的变革战略,对苏联模式予以全盘否定,试图在短期内构建西方式的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为此,叶利钦进行了理想的制度设计:在政治方面,废除苏联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实行多党制,并且确立了权力相互制约的三权分立制度;在经济方面,实行私有化,全面推进市场经济;在社会方面,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以建立公民社会。叶利钦以激进变革的方式推进这些理想设计,并以实际行动对苏联时期所形成的传统体制予以彻底颠覆,可以说“叶利钦时期的转型主要是解决制度变迁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问题”[1]。
仿照西方架构所进行的全面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使俄罗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格局得以形成。叶利钦建立的有限政府使国家权力迅速从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依赖于“全能型国家”的“总体性社会”当中抽离出去,并造成了社会的权力真空,从而使社会产生了急切的自治需求与压力。为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叶利钦放任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非政府组织的生成与发展,使其活跃于俄罗斯联邦境内,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93年俄罗斯独立之初,非政府组织数量约为8 500个,1997年已经达到160 000个,到了2000年则达到了近275 000个。①这些非政府组织基于维护相关集团的利益和实现社会公益的需要,开始在“民间治理”中崭露头角。至此,俄罗斯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格局初步形成。
(二) 对非政府组织角色的理想期待
为了推动社会自治,俄罗斯颁布多部法律对非政府组织予以合法化确认,1993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确定了结社自由原则,而后又颁布了《俄罗斯联邦社会联合组织法》《俄罗斯联邦非营利组织法》和《俄罗斯联邦慈善法》等,这些法律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合法的框架,因而极大地促进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大量崛起是在借鉴西方的治理格局的基础上,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为前提的,俄罗斯希望通过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增强民间治理能力,并对非政府组织角色赋予了理想的期待:一是希望通过非政府组织有效分解国家权力并推动有限政府的建立。苏联时期的“全能型国家”及其集权体制使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陷入了困境中。基于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需要,俄罗斯希图通过非政府组织对国家权力的分解,推动有限政府的建立,进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格局的形成。二是希望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增强社会自治能力。俄罗斯在治理变革当中,大幅度收缩国家权力的运行范围,让非政府组织来填补国家权力的运行真空,接替国家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进而使社会的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三是通过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增强政治合法性。在苏联“全能型国家”的管制下,社会缺乏活力,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机制不完善,公民的参与意识不高,导致国家建构的法律制度缺乏运行的社会基础,从而影响到政治的合法性。而非政府组织则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表达利益诉求,从而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三) 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失衡
叶利钦改革时期,俄罗斯的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虽然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西方化的制度形式与本土国情内在的深层张力,使模仿西方所建立起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畸形发展。在自由主义主导下所建立的有限政府因权威性和有效性的丧失而演变成“弱政府”,对国家与社会的控制严重乏力;采取“休克疗法”进行“社会财产大分割”所建立起的市场经济却演变成了“寡头经济”;转型中所出现的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被寡头精英或西方政治势力所俘获,在“民间治理”中表现出明显的治理能力不足。“在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进程中,当公民社会被精英集团、寡头政治剥夺、肢解得支离破碎之时,公民社会就会被既得利益集团和寡头阶层进一步利用,作为他们上演街头政治,并借此俘获国家政策,甚至是与国家公开对抗的舞台。”[2]国家治理的畸形与“民间治理”的低效导致俄罗斯陷入了严重的秩序危机当中。改革的仓促性与不成熟性,使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陷入困顿之中,“1999年,俄罗斯的GDP比1991年下降56%,工业产值下降60%,农业产值下降50%。经济陷入瘫痪,通货膨胀严重,因卢布贬值导致民众直接损失了4 600亿卢布储蓄,物价上涨51倍,而名义工资仅提高11倍,1999年失业率高达15.2%。”[3]
二、普京时期的治理能力塑造与秩序重建
普京继任俄罗斯总统后,通过调整治理理念,以构建“强国家”和“强社会”为目标,一方面增强国家的权威性和国家权力运行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采取引导、扶持和规制等方式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民间治理”能力的培育,逐渐形成了“国家建构—社会回应”的治理模式,并以此为框架进行俄罗斯治理秩序的重建。
(一) 治理理念的调整与治理体系的重组
普京继任总统后,通过调整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弱政府−弱社会”治理格局,转向“强国家−强社会”的治理结构指向。普京认为统一的“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动员经济社会力量并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必要元素,它“是团结俄罗斯社会、复兴俄罗斯的精神良方”[4]。因此,普京以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团结的“俄罗斯思想”作为强国家与强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以力求为俄罗斯所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构建。首先,普京通过树立宪法权威,整顿宪法秩序,加强了以“可控性”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建设,构建强有力的“垂直权力体系”以及推动“有效的经济”等方式实现“强国家”的建设,改变“弱政府”的治理乏力与被动局面。其次,以“可控性民主”为基础,推动非政府组织的有序发展,打造理性的“社会回应”,以此来推动“强社会”的构建。在非政府组织发展策略上,普京改变了叶利钦时期放任发展的态度,通过立法对非政府组织(含“不受欢迎的组织”②),尤其是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外国代理人进行法律规制,以创建新的非政府组织和唤醒国家与民族意识等方式对功能异化的非政府组织予以抗击,以此来增强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功能。
在“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治理理念下,普京致力于国家与社会互动机制的建构。其一,2001年,在国家的推动下,俄罗斯非政府组织与总统和政府高层共同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公民论坛”,标志着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互动交流的平台正式建立。其二,2006年,俄罗斯成立了社会院③,各社会团体代表可以通过社会院的协商机制商讨国家重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其三,俄罗斯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协商民主体制,使其成为重要的立法参与主体,在立法过程中,邀请相关的非政府组织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④。通过以上机制和平台,俄罗斯实现了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互动博弈。
(二)“民间治理”进程中的转型秩序重建
通过治理理念的调整和国家与社会互动机制的建立,普京时期的“民间治理”在俄罗斯转型秩序重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非政府组织承载的多元民主诉求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以及治理秩序生成创造了条件。“民主社会的理想模式是一个有向心力的社会,而现实却是一个离心的社会,即不是只有一个权力中心 (卢梭所设想的‘公意’),而是有很多的权力中心。”[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多元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俄罗斯公民权利诉求的不断增长,使社会产生了利益表达机制的内在需求。具有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承载了多元的民主诉求。俄罗斯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初步实现了对权力的多中心分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多元民主诉求的整合,从而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以及治理秩序的生成创造了条件。通过普京时代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搭建,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国家的公共决策当中,从而使公共政策具有了民意基础而具有了正当性与合法性。
其次,“民间治理”实现了对纵向权力的分解与对横向权利的平衡。俄罗斯独立后,“全能型国家”体制被迅速打破,国家权力迅速抽离社会空间,而作为“民间治理”重要主体的非政府组织则对这部分权力进行了纵向的分解,既分享了苏联时期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同时,又以社会自治空间限定了国家权力的运行界域,构筑了防止权力侵犯权利的堤坝。而且,非政府组织通过自治规则与非正式规范,培养成员之间的互惠、合作以及信任等公民精神,并通过理性博弈规则实现了社会成员之间横向权利的平衡。
再次,“民间治理”实现了公民精神塑造并推动了公民的理性民主参与。在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与国家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臣民或人民身份导致了俄罗斯公民精神的缺失,在俄罗斯历史上“为权利而斗争”的非理性行动比比皆是。而非政府组织则能够通过价值观的整合与利益的平衡,培养公民的理性宽容与妥协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并以谈判、协商等方式理性地参与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俄罗斯的各种非政府组织以社会院、公民论坛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以及参与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就是公民理性民主参与的重要体现。
最后,“民间治理”推动了价值共识、制度认同与自律秩序的生成。价值共识指的是“不同价值主体之间通过相互沟通而就某种价值或某类价值及其合理性达到的一致意见”[5]。俄罗斯转型初期,市场经济所催发的多元利益基础上所形成的多元价值观,因缺乏有效的整合而使俄罗斯陷入“思想观念的价值撕裂”之中。这种多元价值观下的价值撕裂,造就了“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6]普京时期,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能力明显增强,一方面,非政府组织通过对公民精神的塑造和对多元价值观的整合而形成价值共识,推动共同遵守的非正式规范的形成;另一方面,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非政府组织在立法的过程中,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通过理性协商促进共识的形成,进而产生体现多元利益的正式法律制度。因此,无论是非正式规范还是正式的法律制度,均因为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形成而增强了公民对制度的认同感,进而推动了自律秩序的生成。
三、转型俄罗斯的秩序追求与治理变革的发展趋向
普京执政后努力打造国家治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加强了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建设,以此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双强均衡”,治理秩序也逐渐走向正轨。俄罗斯的转型之路和不同阶段秩序构建的成效表明,俄罗斯的治理变革之路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过程,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最终走上了自主化发展道路。同时,俄罗斯的“民间治理”也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强”均衡、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的耦合秩序以及“东方专制主义”路径依赖等特殊的路径与走向。在当下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在各个领域已崭露头角,发挥了一定的权力分解与权利平衡的作用。虽然近来俄罗斯基于国家利益在因克里米亚问题和叙利亚问题上与西方发生激烈冲突,为防范国内“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成为“颜色革命”的工具,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打压措施,客观上使“民间治理”出现一定程度的停滞,但这并不必然导致俄罗斯治理变革的发展趋向的改变。
(一) 俄罗斯治理进程中的自主性秩序追求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格局以及“民间治理”的秩序生发机制是在西方的语境下产生的,俄罗斯仿效西方所进行的秩序变革和对法治之路的探求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西方的经验逻辑与俄罗斯“本土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与张力。西方的“民间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长期博弈的背景下产生的,以非政府组织为重要参与主体的“民间治理”“是公众表达利益和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体现了社会管理对民主、法治以及社会公正等价值的追求”,[7]“民间治理”在形成之初就具有自发性。而俄罗斯的“民间治理”则是为了实现西方的民主法治而由国家推动形成的,具有人为构建性并体现出了对国家较强的依赖性,“民间治理”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策与法律导向。叶利钦时期以西方为样本所进行的社会结构转型为俄罗斯走自主化道路确定了基本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但由于缺乏对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本土国情的关注而陷入治理误区。普京时期则在叶利钦改革框架的基础上,将更多的俄罗斯元素注入到治理变革当中,寻求西方经验与俄罗斯“本土性”的结合点,进行自主化道路的探索与尝试。
首先,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强均衡”来推动治理秩序的形成是俄罗斯治理之路的主要特征。俄罗斯特殊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决定了俄罗斯完全走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强国家”在俄罗斯治理秩序生成中必须承担主导性角色,而“强社会”则能为俄罗斯治理秩序的生成提供社会根基。其次,俄罗斯初步形成了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的耦合秩序。俄罗斯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框架的确立以及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互动回应共同推动了俄罗斯建构秩序与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再次,俄罗斯的“民间治理”具有明显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路径依赖。在俄罗斯的“民间治理”中,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是影响俄罗斯“民间治理”不可忽视的传统因素,并使俄罗斯的“民间治理”具有浓厚的“东方专制主义”特质。最后,根据俄罗斯的传统与现实国情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俄罗斯与西方的秩序观会由冲突逐渐走向融合,在治理的过程中,俄罗斯仍然会坚持强国家取向,同时,“民间治理”的功能会不断提高,“民间治理”的空间也会不断拓展,并在俄罗斯的秩序重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 大国治理中的强国家取向
俄罗斯是一个历史传统悠久、幅员辽阔的大国,在大国治理中,必须考量到历史传统、现实国情、民族性格以及复杂的国际秩序格局。“俄罗斯改革的经验表明:绝不可以轻视各地区形成的民族文明、各地区形成的经济关系以及精神特性。”[8]叶利钦时期,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希望在俄罗斯快速的实现自由和民主,结果是有限政府演变为“弱政府”,使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并陷入秩序危机。美国学者福山认为“国家建构也许比治理更重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也许比自组织治理更重要”[9],普京的治理策略调整验证了福山观点的正确性。2000年,普京以铁腕人物的形象出任俄罗斯总统,“在对叶利钦时期的混乱无序进行了系统整治之后,俄罗斯政治从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可控”[10],在强国家的理念下,俄罗斯逐步摆脱了秩序困境。在多元治理中,国家一直属于重要的、起主导作用的治理主体。“2012 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彰显了重塑世界一流强国的雄心,使强国意识和威权主义继续得到加强”[11],“可控性民主”仍然是普京在国家治理中必须坚持的理念。“可控不只是控制国内的政治秩序,还包括不允许西方的染指,同时,也是对国内意欲倚仗西方势力伺机而动的反对派提出警告,进一步压缩反对派的活动空间。”[10]俄罗斯的现实国情、国家主义传统、东方专制主义的路径依赖以及民族性格决定了俄罗斯在大国治理中强国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在大国治理中,强国家的取向必然还要保留。首先,俄罗斯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以及威权政治在历史中的影响是俄罗斯在治理中无法抹去的痕迹,这种传统必然要嵌入到俄罗斯当代以及将来的治理模式中。其次,俄罗斯的公民社会还不成熟,大量的非政府组织能否对治理秩序的生成产生积极的作用,还取决于国家的合理调控和引导,强国家是塑造俄罗斯强社会的必要条件。再次,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颜色革命”的威胁,俄罗斯必须保持“强国家”的威力,以使国家安全不受侵犯,如因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问题俄罗斯与西方发生了对抗,西方以经济制裁和制造事端等外部手段进行施压,并试图通过“颜色革命”在内部瓦解普京政权,而普京则以强硬的、甚至不惜武力威胁的手段还击西方的挑衅。总之,在将来的很长时间内,俄罗斯的强国家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双强”均衡仍然是俄罗斯治理之路的典型特征。
(三)“民间治理”功能的增强与空间拓展
普京担任总统后,继续在叶利钦建立的西方框架下进行改革。普京一再强调,俄罗斯不会将强有力的和有效的国家与极权主义混为一谈,俄罗斯不会回到帝国极权的老路上去,因为帝国治理形式不会长久,是错误的。[12]强国家需要有强社会作为支撑,因此,普京对分散国家权力和实现多元治理是积极倡导的。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在社会服务、社会整合以及参与国家治理中已经和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普京政府也一直在积极探索国家与非政府组织进行交流对话以及合作的机制与平台。普京时期,俄罗斯的“民间治理”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很不成熟,俄罗斯的公民精神和理性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因此,在当下的俄罗斯,赋予不成熟的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以更多的使命,“民间治理”违背其初衷而走向其反面的风险极大。因此,普京的“可控的民间治理”是符合俄罗斯的现实国情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阶段的。
对于俄罗斯国家来说,与非政府组织确立伙伴关系,实现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互动博弈是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思潮下的必然选择,也是俄罗斯走上民主法治国家之路的必然选择。因此,俄罗斯不会毫无限度的遏制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在不威胁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俄罗斯政府会不断推动非政府组织“民间治理”能力的增强,并积极探索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方案。从另一角度来看,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有其自身成长的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政府组织的理性化参与能力会不断增强,其对权力的纵向分解和对权利的横向平衡能力也必然会不断提高。尽管近年来,俄罗斯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防范国内“颜色革命”的发生,以法律手段对西方“颜色革命”的工具——非政府组织进行国家管控⑤,但是这些非政府组织并非俄罗斯的主流,因此,在国家推动与社会自发生长的双重合力下,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功能会不断提升,其“民间治理”的空间也会不断拓展,并在俄罗斯的法治秩序构建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四、中国与俄罗斯:“法治中国”建设的反思与借鉴
中国以改革开放的方式放弃了“苏联模式”,开启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并转向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法治建设之路。“国家主义”的法治建构路径虽然取得了诸多的成就,但由于社会动力的不足,导致“国家主义”法治建设遭遇难以逾越的瓶颈——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法治秩序并未如期而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理念纳入到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策略之中,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战略构想。面对改革深水区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通过“民间治理”与国家治理双向互动来推动法治秩序的生成就成为当下中国的必然选择。
中国与俄罗斯具有类似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及秩序建构逻辑,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是以皇帝(沙皇)的绝对权威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统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侵吞和同化了社会。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僵化单线性发展,造成了东方社会的超稳定性和发展的停滞性。”[13]而且,中国与俄罗斯原来都同属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处于社会转型期,历史基因的同质性和转型起点的相同性决定了当代中国借鉴俄罗斯治理秩序的路径与策略的可能性。当然,俄罗斯的国情与当代中国的国情具有很多的差异性,这也决定了中国对俄罗斯治理与法治推进方式借鉴的限度,即不能简单的照抄照搬。
首先,在道路选择上,必须在“法治中国”框架下确定治理法治化之路。从俄罗斯治理变革的路径来看,叶利钦时期忽视传统和照搬西方治理框架的路径选择最终使俄罗斯陷入严重的秩序危机,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克洛茨沃格曾经慨叹到:“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现在,我建议中国同志继续‘以俄为师’,只是我们这次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14]而普京关注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变革则使俄罗斯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治理格局。因此,纵观俄罗斯的治理变革与法治秩序构建历程及俄罗斯“民间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当代中国必须走“自主化”发展的“法治中国”之路,一是要借鉴西方经验,坚持法治的底线原则。通过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互动合作,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对权利的合理保护,促进公平正义的法治秩序的实现。二是正视传统,从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俄罗斯改革初期对传统的忽视是俄罗斯陷入转型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重视历史传统,将传统文化的精髓注入到当代中国的法律精神与法律体系之中。三是关注现实,重视法治的中国特性。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治理秩序必须建立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体的民意表达机制,同时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
其次,在治理模式上,当代中国必须确定“国家主导与社会参与”的治理模式。叶利钦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失衡发展以及普京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平衡为当代中国的治理模式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确立“国家主导与社会参与”的治理模式,坚持国家在改革发展与法治建设中的主导性地位,增强国家的权威并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通过“强国家”增强当代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并保证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稳定的社会秩序,防止改革陷入失控的风险。同时,必须调动社会在治理中的参与潜力,扩展社会治理空间,培育公民精神,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提高“民间治理”能力,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协商民主制度等民主参与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回应。
再次,在具体策略上,必须建立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双重秩序生发机制。俄罗斯治理变革策略的演变及其后果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建立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双重秩序生发机制是当代中国实现治理法治化的基本策略。法治秩序的构建是在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以及权利与权利的互动平衡中实现的,因此,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中实现建构秩序与自生自发秩序的耦合。一方面,通过树立宪法权威、实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以及进行顶层设计等举措来增强国家在治理中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通过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增强正式法律制度的运行实效。另一方面,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功能,通过非正式规范实现社会自治以及实现社会整合。在构建“强国家”与“强社会”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同步推进与互塑回应,即以“民间治理”促动国家治理权威性的提升,同时以国家治理推进“民间治理”有效性的增强,最终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重秩序生发机制来实现当代中国的法治秩序。
注释:
① 由于当时俄罗斯对非政府组织没有官方统一数据,本处所采用的为外国学者统计数据。Press Conference With a Group of Experts Regarding the Results of Social Research on Democracy in Russia”, Federal News Service,www.fednews.ru. 2003 (также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о в. Johnson’s Russia List, no. 7399, 4.11.2003)
② 2015年5月,俄罗斯立法机关通过了“不受欢迎的组织”法,将“威胁俄宪法制度基本原则、国防能力或国家安全”的外国或国际非政府组织认定为“不受欢迎的组织”,“不受欢迎的组织”在俄境内开展活动将受到处罚。
③ 俄罗斯联邦社会院(俄文为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社会院的活动旨在协调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之间的利益,社会院的具体任务就是采取听证会、圆桌会议和现场会话等形式对被认为是国家和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对俄罗斯联邦所制定的重大经济、政治与社会政策以及相关的法律文件进行论证。由于社会院并非权力机关,社会院的决议以总结、建议和呼吁的形式出现,具有协商的性质。
④ 笔者在俄罗斯做访问学者期间,对俄罗斯中小企业协会阿穆尔州地区的负责人别洛鲍洛多夫进行访谈中了解到,俄罗斯中小企业协会是在总统办公厅的建议下成立的,该协会经常参与涉及中小企业利益的法律草案的讨论,并提出相关意见。例如,2010年,俄罗斯中小企业协会针对国家杜马增加征收中小企业社会保险的法案提出异议后,该法案得到了及时的修改。
⑤ 如在2015年5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不受欢迎的组织法》(закон о «нежела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对那些对俄罗斯宪法制度基本原则、国防能力和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国际或者外国非政府组织予以认定为不受欢迎的组织,并予以禁在俄设立分支机构、金融管制、罚款乃至刑事处罚等手段严厉打击。2015年7月,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认定的首个“不受欢迎组织”为美国民主基金会(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фонд в поддержку демократии из США),11月又将“索罗斯基金会”等定性为“不受欢迎的组织”。
[1] 陆南泉. 20 年来俄罗斯国家转型进程分析[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2(1): 51−57.
[2] 张慧君. 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180.
[3] 于祖尧. 休克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访问俄罗斯见闻[J]. 电器工业, 2001(2): 4−10.
[4] 诺贝托·博比奥. 民主的未来[J]. 国外理论动态, 2013(12): 100−110.
[5] 汪信砚. 普世价值·价值认同·价值共识——当前我国价值论研究的三个重要概念辨析[J]. 学术研究, 2009(11): 5−10.
[6] 俄罗斯总统官方网站.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DB/OL].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2113 2, 2015−05−15.
[7] 孙晓莉. 西方国家政府社会治理的理念及其启示[J]. 社会科学研究, 2005(2): 7−11.
[8] А.О.博罗诺耶夫. 中俄改革的特点与公民社会的形成问题[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5(1): 58−62.
[9] 郁建兴. 治理与国家建构的张力[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8(1): 86−93.
[10] 徐向梅. 普京新政下的俄罗斯依然是可控民主[J]. 国外理论动态, 2013(3): 89−93.
[11] 王秋文. 俄罗斯转型政治文化的基本态势与价值取向[J]. 国外理论动态, 2014(4): 85−89.
[12] 陆南泉. 转型中的俄罗斯[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27−128.
[13] 马长山. 西欧的“独特性”“东方专制主义”与近代法治[J]. 求是学科, 2001(2): 63−67.
[14] 吴易风. 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J].财政研究, 1996(2): 53−60.
Evolution of Russian reform strategy in governance and its revelation to China
KONG Lingqiu
(School of Marxism, Harbin College, Harbin 150086, China)
In Yeltsin era, Russian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broke its fetters as a “universal state,” and a multiple and mutual-governing pattern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was established. However, the malformed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neffective civil governance plunged transforming Russia into political strife and turmoil, law of the jungle i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division and chaos in the society. Russia was thrown into serious order crisis. In Putin era, on the basis of Yeltsin’s reform framework, fuses more Russian elements into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reform, exerts efforts to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trengthens interactive mechanisms of state and society, so as to seek the point of integration of experience of West and Russia and to attempt to explore the road of self-reliance.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 Russia sticks to the “strong country,” increases social autonomy ability, expands the autonomy space of society, and constructs the response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Russia’s strategy of adjusting the relationship of state and society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ance pat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to China who is now in the depth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Russia; NGO; civil governance; order of rule of law
D521
A
1672-3104(2017)01−0117−07
[编辑: 颜关明]
2016−02−21;
2016−05−09
孔令秋(1973−),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法学博士,哈尔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法政治学,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