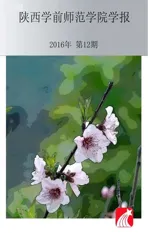生存困境与发展必要:绥远基础教育及对内蒙古扫盲运动的影响
2017-01-10陶继波崔思朋
陶继波,崔思朋
(1.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70;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生存困境与发展必要:绥远基础教育及对内蒙古扫盲运动的影响
陶继波,崔思朋
(1.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70;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绥远省是民国时塞北四省之一,1914年袁世凯当政时将其从山西分出,并与兴和道组建为绥远特别区,1928年建立绥远省,至1954年并入今日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自治区)。近代绥远地区,尤其日本侵略后,处境危机四伏,加之当时本地封建势力和统治阶层的疯狂掠夺,使当地社会民众生存举步维艰,这也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教育事业凋零破碎,基础教育举步艰难、教育工作者受到迫害。千里草原上的文盲和半文盲的比重高达90%以上,高于全国80%的平均线。近代绥远基础教育事业发展艰难及对文盲的出现的影响极为深切。新中国成立后,自治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的开展都需要人民的参与,扫盲运动的开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扫盲运动;内蒙古;社会混乱;影响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12.018
扫盲运动是新中国成了以后的一项重要教育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使命。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翻身成为国家主人。政治上的翻身也必然要求思想文化上的解放,在旧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无权、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接受文化教育和享受文化的权利。而新中国的成立后,文化普及即是其施政的理念使然,也是保障人民群众根本权益的必然举措。然而面对当时举国上下有80%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的情况,一场旨在扫除人民群众中文盲,对人民群众进行文化教育的工作势在必行。就内蒙古地区而言,新中国成立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东、西部分别存在着日伪控制下的伪满洲与伪蒙疆傀儡政权统治。其亲帝反人民的倾向,对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尤其是奴化教育、分化教育等带有侵略和奴化性质教育政策的推行,对于基础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这又势必导致文盲的大量存在。而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建设都亟待扫盲运动的开展,这也是导致扫盲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必然因素。
一、关于近代绥远基础教育与内蒙古扫盲运动的前人研究梳理
对于近代绥远地区基础教育发展与内蒙古地区扫盲运动的前人中,已有学界前辈对涉及此类教育的档案资料进行梳理,然而系统的研究尚付阙如。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直接涉及此问题的研究多体现于论著的部分篇章,以及一些研究论文与学术论文中。
(一)史料整理与专著研究方面
直接涉及绥远基础教育与内蒙古扫盲运动的有:中央教科所编的《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年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
直接涉及绥远基础教育与内蒙古扫盲运动的有:日本学者浅井加叶子的《当代中国扫盲考察》(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余博与谢国东的《中国扫盲教育》(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秦政奇的《内蒙古教育年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牛敬忠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欧阳璋的《成人教育大事记(1949—1986)》(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马云的《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内蒙古教育志》编委会的《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第1辑、第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绥远通志馆编《绥远通志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编《扫除文盲文献汇编(1949-1996)》(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论著,所谓直接涉及,也并非是就绥远地区基础教育与内蒙古地区扫盲运动进行研究,而是在论著的部分篇章与内容中有所涉猎。通过以上所叙述的关于此问题研究的相关论著,可以发现,其中直接相关的研究论著仍属欠缺,多数研究仍徘徊于资料的汇编或是将其当作研究背景加以介绍。
间接涉及绥远基础教育与内蒙古扫盲运动的有:文斐的《我所知道的伪蒙疆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乌拉西林的《内蒙古图书馆事业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乌兰图克主编的《内蒙古民族教育概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王雷的《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王向远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王野平主编的《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王铎主编的《当代内蒙古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王铎主编的《团结建设中的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承礼主编的《中国东北沦陷区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孙景磐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赛航、金海编的《民国内蒙古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任其怿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齐红深的《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齐红深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内蒙古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金海的《日本在内蒙古殖民统治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主编的《内蒙古通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等论著。间接涉及的各论著中,多是就中国范围内的基础教育或扫盲运动、以及有关绥远、内蒙古地区教育及与教育相关的问题研究中对基础教育及扫盲运动有所涉及,故而将其作为间接涉及方面成果进行梳理。
(二)学位与学术论文方面
直接涉及绥远地区基础教育与内蒙古地区扫盲运动的文章有:李云霞的《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扫盲运动研究(1949—1965)》(内蒙古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文章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为范围,就建国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扫盲运动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崔娜的《从文盲到识字的人:1949—1959年内蒙古地区扫盲运动研究》(内蒙古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文章依托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对建国后的内蒙古地区扫盲运动进行了整理,并以宏观的视角,对少数民族地区扫盲运动开展的特殊性和价值进行了论述。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农牧民教育处《内蒙古自治区扫盲工作概述》(《农村成人教育》1994年第Z1期)。此数篇文章是直接涉及内蒙古地区扫盲运动的研究论著,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经验。牛敬忠的《绥远地区教育近代化初论》(《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马寒梅的《傅作义与绥远经济文教事业的发展(1931-1937)》(《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等文章。
间接涉及绥远地区基础教育与内蒙古地区扫盲运动的文章有:所谓间接涉及,即是在文章中对扫盲运动及绥远地区基础教育有所涉猎,但并未深入研究。与内蒙古地区扫盲运动间接相关的多是体现在对于这一时期内蒙古地区成人教育、社会教育及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包括:任其怿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动(1931年—1945年)》(内蒙古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斯钦巴图的《东蒙古殖民地社会与文化的变动(1931-1945)》(内蒙古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阴瑞芬的《民国时期绥远地区师范教育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闫海霞的《民国时期绥远社会教育初探》(内蒙古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武志华的《民国政府蒙旗教育政策及相关措施》(内蒙古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杨红的《我国少数民族扫盲教育现状与发展研究》(《成人教育》2007年第1期)等文章。与绥远地区基础教育研究相关间接相关的文章还有张建军的《抗战初期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始末》(《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12期);张建军的《伪蒙疆时期蒙古学校教科书编辑与使用情况浅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余子侠的《日伪统治下伪蒙疆政权的留日教育及教育交往》(《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徐志民的《近代日本政府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政策探微》(《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徐志民的《抗战时期日本对蒙疆地区留日学生政策述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徐志民的《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1937-1945)》(《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王海峰的《抗日战争时期绥远省政府对边疆教育的推进》,(《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2期);汪丞与余子侠的《论伪蒙疆政权的留日教育活动及其特点(1937-1945)》(《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任其怿的《日伪时期内蒙古西部的日本语教育》(《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等文章。
可以看出,以上对于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中,一个明显的问题,便是基础教育与扫盲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基础教育是人民群众识字的最基本、也是初期的环境,而对近代及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地区教育问题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这一问题,这也即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和所想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二、民国时期绥远省基础教育发展概况
初等教育是教育之基础,一般国民如不能接受最低限度教育,则政治建设、物质建设或教育本身的要求都难以实现。政治建设而言,凡党义之宣传自治之训练,国家观念之养成,民族意识之培植,均将有不可克服的障碍。物质建设而言,一切科学知识,乃至最简单之卫生常识均无法使一般国民了解,一切建设也都无法操作。[1]200初等教育是基础性教育,文盲的出现也多是由于其未能接受基础教育而导致。故本文也就基础教育对于文盲出现的影响入手,将近代民国时绥远地区基础教育做一介绍。绥远省的近代教育起始于清末,但受师资不足、经费短缺等影响,虽当局做过一些努力,但整体而言,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学生人数都难以与内地省份相比。民国初年的绥远省教育发展停滞,绥远省失学儿童人数达18万人。[2]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也对绥远省的教育颁行了规定。包括学费、学生数量、开展重点区域图书馆等。[3]682最早的一所省立小学成立于民国十二年(1923)。其建立也是“民国十一年十一月时,绥远旅京学会在绥演剧得一千余元捐款倡立,翌年二月,即正是成立,名曰绥远平民学校”。[4]413在此之后,又相继成立了第二小学、第三小学等数所省立初等学校。
傅作义执政时对绥远省基础教育的重视:第一,教育经费方面:加大对教育投入,1932年教育费用计划投入27048193元,其中只省财政厅所拨款目达19401678元,其余则由地方配给。[5]62也制定了教育经费款目的相关规定,包括《绥远省教育厅管理教育款产办法》和《绥远省各县局管理教育款产办法》等,明确指出教育经费专用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得挪用,并且所统征税款中附加的教育经费不得减少,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第二,对于教育从业者的重视:包括为省立小学教师增加工资,月薪30元(约值1400斤面粉);高新聘任教师,从吉林省邀请女教师等。[6]第三,对于学生的重视:对儿童入学教育极其重视,调查适龄儿童情况,规定其入学学习。并制定《调查学龄儿童纲要》规定各县、地区及时调查儿童情况,督促其入学接受教育。[7]此外,还采取奖学金激励制度,激励更多的人考入高等学府。第四,学校建设方面:举办民众学校用以对社会民众的文化教育,举办职业学校培养各业的专业人才。[6]傅作义的教育政策对绥远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教育取得了较大进步。然而受到当时社会混乱、外国势力影响等影响,学习人数相比于总人口而言所占比重仍旧很小。
抗日战争爆发前,绥远省基础教育发展概况如下:(见表1-3)

表1 1933年绥远省省立各小学信息统计表

表2 绥远省时期各县小学调查表
抗日战争前,绥远省学校教育已初具规模。抗日战争中,绥远省文化教育机构多随绥包的失陷而解体。只有绥西的五原、临河、安北、东胜等县局有几所小学。但这些学校也难以满足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教育的需求。
全面抗战爆发后绥远省教育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出现了许多高校及文化机构西迁。国民政府也将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战略大后方,对于战略后方也开展了文教工作,推进边疆民族教育的方针, 增设了边疆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等。这也即边疆教育,国民党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了《推进边疆教育方案》,方案中也提出了实行边疆教育的方针。“绥包”沦陷,教育便移到西部进行教育复兴活动。但受当时社会环境动乱影响,虽取得了一些成绩,却未能实现教育的大发展。1940年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巩固边疆和加强边疆民众的爱国意识,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大对边疆教育的支持,在蒙藏教育司扩充人员,开设两科执掌蒙藏教育。第一科负责边疆各种教育事业,各边疆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及经费和师资配备等;第二科负责边疆教育法案、图书教材等的编译、研究和出版事项。[8]19国民政府时期,其教育目标在于培养边疆民族的国家意识,灌输三民思想。注重建设心理上的国防,共抵外辱,并非是为启发民智而进行。

表3 绥远省各乡级小学(包括高级与初级)统计表
三、绥远基础教育发展困境及文盲出现原因
基础教育是针对适龄学童而开展的基础教育,是民国以来,人民群众识字的最基本手段。而近代绥远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极为艰难,这也是导致文盲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很有必要对于绥远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困境及文盲出现的原因进行论析。
(一)日本侵略对基础教育发展及文盲出现的影响
日本侵略期间,对于自治区社会知识分子的迫害极为严重,肆意抓捕知识分子、任意枉杀,致使社会大众对知识望而却步。知识分子被迫害也使传播文化的人数骤减,对于教育的影响不可小视。日本控制满蒙期间,制造了相当数量迫害知识分子的惨案,尤其是城市,知识分子是首要打击对象。据彭谦回忆:“1940年和1943年,日寇在厚和市进行了两次大逮捕,先后被捕有五六百人之多,109人遭杀害,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员,罪名是‘救日救国会’成员”。[9]84此外,当时反动亲日势力也投入其中,当时宪兵队、特务队等民族败类也捏造各种罪名,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彭谦介绍:“敌人用酷刑逼着被捕的人乱咬,凡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甚至朋友关系也都成为了被捕的对象。逼供、刑讯的结果像滚雪球一样,扣捕面逐日扩大,所有牢房都注满了人。”[9]85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也相当残酷,当时“永平商行(书店)的李秉政(中国大学毕业),敌人认为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宪兵队给住单间,敌人用各种办法折磨他,让他夜不能休息的写材料,用思想折磨法,企图获得‘思想不良’的证据”。[9]89当时知识分子的命运悲惨,因知识而获罪,饱受折磨。教师被捕入狱,受到各种非人迫害,让人不敢问津此职业,学校没有了教员也就无所谓学生,知识的传播中断了。对于非教员行业知识分子的迫害,也影响了人们的求知欲,不敢向知识靠近。
(二)伪蒙疆政府统治对基础教育发展及文盲出现的影响
伪蒙疆自治政府施教理念和内容背离了教育的本真含义,这对文盲大量出现也有影响。最高学府“蒙疆学院”办学宗旨是“日蒙亲善,民族和谐”、“善邻友好,发扬东亚道义精神,培养实用人才”。实质是企图通过教育推行“欲无其人之国,须先无其文化”的反动政策,专门培养忠于日寇的奴才。[10]81人员安排上也多由日本人任职,虽有少数中国人也精通日语,经过专门培训。讲授内容也与中国文化无关,“精神训练、武道训练、精神讲话、军事训练、作业训练、人文科学、神道及皇道”等。也讲一些地理和历史,但也与中国无关。毕业生连中国有多大,祖国的山河资源都不知。历史课上,只讲日本如何帮助朝鲜和满洲建国,不讲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10]82造成了对中国文化冷视,出现目不识丁的文盲群体。蒙疆学院的学生一部分是日本调来,另一部分是“伪蒙疆”各机关选送。毕业后一部分送往日本留学外,大部分回到原机关加薪任职,成为“伪蒙疆”政府的骨干。[10]82知识分子没有起到知识传播中介的作用,或为高官厚禄而自甘为当时的反动政府服务,或受日本文化影响,出国学习,受此影响社会风气也日益偏离了我国文化。此外,德王兴办教育也以军事教育为主。博彦们都回忆:“德王认识到巩固自己统治,必须有忠于自己的军队和军事干部。一上台便着手整顿军队,创办军官学校。考虑到占领区蒙古青年没有完全接受日本奴化教育,怕引起麻烦。因此,主张先办幼年学校,有毕业生再创办军官学校,使蒙古族青年彻底奴化”。[11]83统治当局及外来因素影响下的教育叛离了中国文化,以日语为媒介,教导的奴化思想和反中国的文化,对人身心的危害极大。其教育的军事化也是出于政治目的,没有关乎到民众们的文化教育。
(三)生活贫困对基础教育发展及文盲出现的影响
对外方面,受到以日本为首的列强国家的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对内方面,受到统治当局和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封建社会贵族等上层社会的压榨。因此,当时社会民众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普遍贫困,生活条件低下。经济侵略下,肆意倾销商品、侵占市场、掠夺资源、资本输出、控制铁路交通等,破坏社会秩序,物价猛增,财富被搜刮殆尽,贫困和家庭破产时有发生。没有相应的经济条件又何谈有机会识字!除经济掠夺外,烧杀抢夺也是一种方式。在固阳县,“七·七事变”后,十月间,日军侵略该地,当时部队“每天早晨奔往农村,见人先打一顿下话再说,要上大烟吸大烟,还让妇女给他们烧烟泡。有肥猪就开枪打死送城里,见到羊群赶回杀几只肥的孝敬上司。到处要大烟,吃饭是炖肉、油饼或者米饭;喂马料是顺墙角倒下一堆,吃不进去为止。为勒索意一晚七餐,也调戏妇女”。[12]154民国后,“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各种摊派,加剧了人民的负担”。[13]98—99日本全面侵华后,通过“借地养民”而设荒务局,进行垦荒种田,加大税收的名目。1938年,各种地方税目多达38种。强迫牧民“出荷”农牧产品。[13]161
(四)社会秩序混乱对基础教育发展及文盲出现的影响
社会秩序混乱,战争频发,土匪和兵匪横行无忌,缺乏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这一角度来讲,也是造成近代自治区文盲大量存在的外部因素。近代自治区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在于外国势力的入侵与本地区反动势力的分裂活动影响,而土匪与兵匪则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并对社会进一步动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影响。土匪、兵匪及战乱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是极大的。固阳县“民国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间,大股的土匪分布在全县,多达上万,常年盘踞,糟害人民,破坏农业生产。加上当时灾害的频发,十室九空”。[14]6民国成立后,自治区的土匪活动仍猖獗无度。仍以固阳县为例,“1926-1927年固阳县匪患猖獗,造成了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的局面。不论大股或小股土匪进村首先是人吃、马喂,人离肉面不进口,就宰牛杀羊。马喂的是莜麦捆子,吃一半糟蹋一半。影响之下,出现的卖儿鬻女、妻离子散,死亡不计其数”。[15]234当时自治区西部地区土匪活动猖獗,匪盗猖獗活动不仅破坏正常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而且还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危害。[16]人们生命财产受威胁,又何谈从事受教育。战争的频仍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更甚,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日本入侵之后对内镇压和对外反抗斗争。论及战争,当时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日本帝国主义为使冯、蒋火拼,收渔人之利,派飞机在长城内外侦查“抗日同盟军”的行动。当时国内各派系之间纷争,国外势力介入其中,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严重破坏了自治区社会秩序。
(五)人们主观排斥情绪对基础教育发展及文盲出现的影响
人们缺乏对知识的需求。人失去了对知识或者识字的愿望是旁人无法左右的。当时日寇在自治区的反动势力残酷剥削镇压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小学的教员,势必会导致民众对知识望而却步,有知识会给自己带来不幸,甚至是家破人亡。人们缺乏学习和认字的欲望,也就是说从人的主观能动性角度来分析,人们没有此方面的要求。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学习知识很难给人们带来好运,当时的社会状况也决定了知识的命运,社会民众学习知识的实际作用难以预测,尤其是日本侵略和本国一些反动势力对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以及日本推行奴化教育,加之当时日本对自治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严密控制。加上当时日、伪蒙疆政府的长期统治,这也就造成了当时人们对文化知识的冷漠,以致出现建国后文盲大批存在。中西部地区,人口稀少且分散居住,各地区之间相对闭塞,缺乏往来,交通不便,人们往往居于一隅。各居住地之间相对独立,交通不便也使得人们很难外出,世代在居住地生存,文字很少用到,因不与外界过多往来,所以文字交流也微乎甚微。
四、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扫盲运动开展之必要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是先于新中国而成立的,其成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便着力开展扫除文盲的工作,这也是有其必然性的,综合分析,可包括如下几方面原因:
(一)经济恢复与发展急需扫盲运动开展
首先,人作为劳动力,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教育担负着劳动力再生产的任务,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没有被劳动者掌握前,是一种潜在的劳动力。只有当它被劳动者掌握并运用于生产,才由潜在的形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7]438通过扫盲运动,使人民能够发挥自己的主人翁与自我主体意识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与自治区经济发展。乌兰夫也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治区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各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也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特别是工农牧业的生产,举办各种学校,只有经济和文化发展了,才可能培养出各种建设人才,后来它又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17]152
其次,扫盲运动是自治区成立后经济恢复发展的需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只有人民大众识了字,掌握了文化知识才能进一步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智慧,促进国家经济的良性发展”。[18]日本侵略后,以“借地养民”为幌子,又提出“出荷”,强行霸占农牧民的农产品和牲畜,严重阻碍了农牧业的发展。
再次,扫盲运动的开展也是自治区工商业发展的需求。随着“蒙禁”政策的松弛和逐渐废除,加上农业区扩大带来的农业定居人口增加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商业贸易活动的增加,直接导致原有的商业城镇的发展和新商业城镇成批出现”。[19]35如“归化城毛纺工艺局(1905年胡孚宸创办)、喀喇沁右旗的综合工厂(扎萨克贡桑诺尔布创办)、蒙古实业公司(蒙古王公创办)等”。[19]40—41虽然这些近代企业规模不大,经营效果并不十分显著,却为自治区带来了经济活力。但好景不长,日本侵略后,阻碍近代企业的发展。“1947年,全区仅687家工业企业,其中有8个粮食加工厂,8个发电厂和1个半机械化的毛织厂。当时工业总产值5300多万元。仅占工业总产值9.6%。至于商业,一些中小企城镇已有一定发展。但总体上还是落后,特别是在农村、牧区”。[13]45
(二)政治建设急需扫盲运动开展
扫盲运动的开展是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并应以领导历次革命政治运动的精神来领导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运动。[21]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内蒙古自治区的干部多是战争岁月洗礼下的革命志士,受时代影响,存在相当数量的文盲干部,对其进行文盲扫除也是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且“从工农兵劳动人民及工农干部中扫除文盲是我国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20]不仅如此,通过扫盲工作,能够更好地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指示与思想,让民众们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党和国家的性质,积极拥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激昂的民族自豪感,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人们积极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浪潮。“扫除文盲提高了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正是高度发挥劳动人民责任心与创造性的基本条件之一。这是因为劳动人民要在生产活动中充分发挥责任心与创造性,就促使他们渴望文化和教育。扫盲恰恰谈的就是为了满足他们在文化上的最低需求。当前无论在工业和农业中,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对于提高生产和改进产品质量都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情。发掘潜在的能力,不仅从现有的工厂设备、土壤改造方面,而且要从人的方面,在劳动人民翻身做主的条件下,掌握了文化与技术的劳动人民,人们的创造性是无穷无尽的。结合以上所述,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工农兵劳动人民及其干部中扫除文盲,是国家实行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21]当时章叶频副厅长指出:“扫盲运动要密切结合生产和中心工作,为政治服务。学习内容要为政治服务。授课内容的其中一项便是政治课,由党团支部书记结合时事政策和中心工作讲解。学习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会议文件。这也大大的提高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22]
(三)教育建设需要扫盲运动的开展
1913年,教育部便对社会教育做出规定,主张扩充图书馆、建设博物馆、美术馆等。并提倡文艺音乐演出和公众体育等活动,制作通俗教育用具与图书资料等。[23](P.997~998)教育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融入新的时代气息。对于教育的近代化,“教育近代化是指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建立新式学堂,培养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思想人才的过程既是相对于封建教育而言,也是针对传统社会中教育职能主要是由家庭承担这一现象而言”。[24]193社会教育在近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虽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个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彻底的实现翻身。对于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早在战国时代的荀子就曾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可见,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故而对民众进行社会教育是极其重要的。“社会教育范围至广,效用至宏,举凡一国普通士庶之性情、道德、智能,皆受熏育陶熔于此,而国家所以谋社会程度之增进,庶民智力之扩张,本固邦宁之上理者,亦即以此为之机括”。[25]101—102新中国成立后独立愿望得以实现,中国历史主题转换为建设家园、追求富强。社会教育中驱除奴化影响,消灭奴隶意识等历史任务又摆在面前。旧文化教育制度已不能适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新的教育呼之欲出。
(四)人民群众主观需求需要扫盲运动的开展
不识字,也就失去了为自己建设和发展的技能,这也是促使人渴望知识,渴望开展和实现扫除文盲工作的动机。识字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正常有序进行,也激发了人们学习的欲望。不识字已严重干扰了日常生活,如发生在当时哲里木盟中旗保安屯的王张氏身上的一件事。“王张氏由于不识字,将五万元的一张票子当成了五千元给花掉了,这件事大大教育了她决心上冬学学习文化的欲望,结果她在冬学中学会了四百个字”。[26]在阿荣旗三道沟努图克向阳峪嘎查第五组村民随文有身上也发生了一件因不识字而导致较大的损失的事情,据载:“随文有本人是旗劳模,以前对文化认识不足,政府干部到该嘎查进行土地复评工作,检查地照时,他错把劳模奖状带到会场,之后又返回家中寻找。第二次到会场时,干部已经走了,又自行追去,耽误了一天生产。[27]不识字对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极为深远。
扫盲工作是一场群众性的工作,之所以在自治区成立之后掀起了扫盲运动的一个又一个高潮,而在此之前的民国和清政府时期没有出现,也是由于群众的参与程度不同而导致的。自治区成立之后开展的扫盲工作是一场群众性的文化革命活动。提及其群众性和文化革命性,可以从以下几点论说:第一,所谓“群众性”是指扫盲工作不只是一个文化教育工作,而是一个关系着每个人的文化革命运动,扫除一个文盲就增加了一份革命力量。第二,扫盲工作和各部门都有关系,文盲不扫除,政府、团体的各项工作都会受阻,因此扫盲工作就成为各方面的共同任务。第三,扫除文盲是群众自己的事情,和每一个群众密切相关。不识字的人要学习,认识字的人要人学习。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投入到扫盲运动中。最后,扫除文盲必须成为群众自觉自愿。[28]
(五)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需要扫盲运动的开展
从文化继承与发扬的角度言之,需要不断开拓人民群众学习的主观欲望以保障文化的传承。自治区史文化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历史时期,许多口耳相传的文化或民俗因缺失文字记述而被遗失,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失最为严重。自治区成立后,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电视和网络日益进入人们视线,人们更多的时间用在看电视或网络上,社会生活中,没有了以往在街头巷尾谈天说地的场景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冷淡。那些口耳相传的民俗、文化、经典也日益淡出人们视线。那些凭借口耳相传下来的文化因没有文字记载与传承载体任其自由发展,无法延续。而边疆民族地方往往是汉文化断层带,这些地区多是多种文化交汇之地,且有部分地区也是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之区。[29]因此,边疆地区的文化保护和发展就更有其特殊性。民族地区的诸多文化中,尤其是民俗文化因没有文字记载而消失是最为严重。没有文字记述。然没有文字记载,文化始终难以传承,这也是导致现代社会以来许多文化和文明失去其原有的价值,其作用日益经济化、商业化的重要原因所在。鉴于此,开展扫除文盲的工作,让广大民众们识字十分必要。新时代以来,虽实现了对文盲的扫除工作,使人民群众实现了对知识文化的了解与学习,然而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也需要人发挥主观性作用。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继承和发扬文化教育工作,通过教育手段、网络媒体的宣传等实现文化的传承。[30]
[1] 申晓云等主编.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 闫海霞.民国时期绥远社会教育初探[D].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G].
[4] 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第一辑下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
[5] 绥远教育公报,卷三,第11期[M].内蒙古图书馆馆藏本,1933.
[6] 马寒梅.傅作义与绥远经济文教事业的发展(1931—1937)[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8(1).
[7]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本厅学校教育科拟计第二期中心工作,档案号:419—1—3.
[8] 曹树勋.边疆教育新论[M].上海:正中书局,1954.
[9] 彭谦.伪蒙疆时期日寇对大同知识界的残酷迫害,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A].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10] 徐志明.蒙疆学院略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A].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11] 博彦们都.伪蒙疆的军事幼年学校,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A].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12] 日伪时期伪蒙古军在固阳县的暴行,谷阳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A].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1987.
[13]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
[14] 李雨春.固阳县建国前后的农业生产状况,固阳文史资料(第四辑)[A].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1987.
[15] 民国年间固阳县匪患片断,固阳县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A].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1987.
[16] 崔思朋,李夕璨,贺向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内蒙古西部土匪猖獗活动的原因分析——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见闻为线索[J].党史文苑,2015(4).
[17] 乌兰夫.乌兰夫文选(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1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9]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
[20]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关于扫除文盲工作文献选载(一九五二年九月——一九五六年三月)[J].党的文献,2012(5).
[21]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胡昭衡在第一次扫盲委员会议上的讲话,档案号:302—1—198.
[22]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章叶频副厅长在东、西部地区扫盲、业余教育现场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档案号:302—1—231.
[23]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4] 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25] 通俗教育研究会.通俗教育研究会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A].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6]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哲里木盟一九四九年冬学工作总结,档案号:302-01-168.
[27] 上冬学去,争取文化上翻身[N].内蒙古日报,1952-01-22(第3版).
[28]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关于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问题,档案号:302—1—24.
[29] 周琼.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观[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30] 陶继波,崔思朋,夏琳.斯文·赫定日记里的内蒙古民俗文化——兼论开展民俗文化教育的必要性与途径[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7).
[学术编辑 黄彦震]
[责任编辑 李兆平]
Survival plight and the necessary of Development: the primary education of suiyuan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ce to the Literacy education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TAOJi-bo,CUISi-peng
(InnerMongoliaUniversityAssociateProfessorofHistoryandTourismCultureInstituteHohhot010070,China;GraduateSchoolof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FangshanDistrict102488,China)
suiyuan is one of the four provinces in saibei. It was divided from shanxi province in 1914,and combine with xinghedao as suiyuan especialy zero. Set up suiyuan provience in 1928. until 1954, become a part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n modern times, suiyuan prvince was occupated by japan, in this region, there are so many feudal forces,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s life were very hardship.it is also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areer, most people haven’t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In this region, there were more than 90% people couldn’t read and write. So,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ment the education, the first difficult is solve people’s learning how to read and write. On the other hand, the economic and education, etc.there are also need to solve people’s education.
Literacy movement; suiyuan province; the society; influence
2016-04-28;
2016-05-12
陶继波,男,内蒙古巴彦淖尔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史、内蒙古地区史;崔思朋,男,黑龙江五常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历史·民族研究
G529
A
2095-770X(2016)12-007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