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我的兴趣是研究芸芸众生
2017-01-07徐琳玲付端凌
徐琳玲++付端凌
“如果我可以假设明朝能够延续下去,那么中国和欧洲各自的历史就会非常不同。我不知道那会是更好还是更糟,但至少,中国会在17到18世纪继续与外部世界保持接触”
在北大燕京学堂的学术论坛上,卜正民就中国历史上“大国”、“帝国”、“强国”的定义及其政治内涵,与中国学者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等我慢慢变老以后,就不去在意自己是不是态度友好这回事了。”他顽皮地一笑,用恰到好处的幽默感赢得了现场一片掌声,也试图给已经有点火药味的气氛浇上一瓢友好的温水。
空气依然紧绷。挨着他坐的一位年长的教授反唇相讥:“不要以为像你这么挑剔和苛刻,就能证明你的观点一定是对的。”
坐在酒店休息区的沙发上,当我们重提他触犯“众怒”的言论的初衷,这位知名的加拿大籍汉学家眼里闪着光。他直率地把某些主流观点斥为“彻底的谎言”。“我得承认,中国人看待自己历史的一些老调,有时确实让我感到annoying(恼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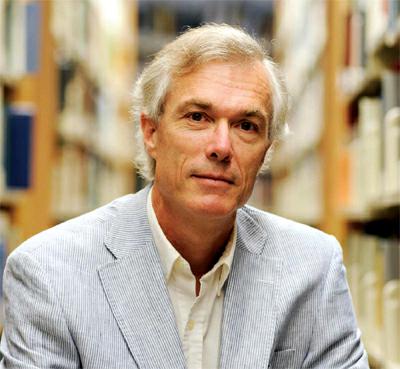
抛出这句犀利评论时,他仪态优雅地侧身靠着沙发,修长的身形,一头微卷的银发,举手投足之间尽显绅士风度。在某网站的学术讨论版上,曾有好事者把他列入海外“最帅汉学家”榜前三,说他是一个“苗条版的施瓦辛格”,仅次于酷似老牌007男星肖恩·康纳利的明星学者史景迁。
马不停蹄的研讨、讲座和访谈,让“苗条版的施瓦辛格”看上去很疲惫。然而一听到“好问题”,他的棕色眸子又立即亮了起来,瞬间恢复敏锐与活力。说到心领神会处,他把手掌重重拍在膝盖上,洋溢着兴奋。
“我想立刻上床睡觉去。”采访终于结束,他竭力抑制住一个哈欠——第二天还有一场大型讲座等着他。
“来北京,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逛书店”
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卜正民顾不上倒时差,就去逛了位于成府路蓝旗营的万圣书店,把明史架子上的书和新出版的古籍全部扫荡了一遍。在论坛讨论的间隙,他又见缝插针,杀到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在中华书局的书店里一直待到中午,让会议组委会差点找不到他的行踪。
“扛回来满满一大箱子书。”说起新收罗来的宝贝,他一脸心满意足。“来北京,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逛书店。”
在北京各大学术书店的显眼位置上,他也看到了熟悉的面孔。2016年年底,由他主编、五位海外知名汉学家共同完成的《哈佛中国史》在中国出版。这套六卷本的通史涵盖了秦汉至清朝的“帝制中国”时代,赢得了由学术界权威人士参评的诸多大奖。
卜正民本人撰写了元明卷——《挣扎的帝国》。以“龙见”这样富有神话色彩的意象,这位擅长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从生态环境和气候变迁的角度,切入了元、明长达四百年的王朝历史,展现了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生态、家族生活、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元、明与世界的贸易、文化、信仰的交流和往来。
“历史一半是必然的,一半是偶然的。”卜正民并不相信有所谓的“历史必然性”。
四十多年前,把这位名叫蒂姆斯·布鲁克的加拿大青年学生吸引至这个东方古老帝国的神秘过往的,正是一时被激发的好奇心、一连串相遇的人与事,以及地缘政治作用下的种种契机。
大学假期一次欧洲旅行的偶遇,让专修英语文学的布鲁克对东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到学校后,他选修了“中国佛教”课程,那是多伦多大学当时唯一提供的与佛教有关的课程。他遇到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老师。
“他从不写板书,一进教室就随意坐下,然后开始滔滔不绝。”跟着口吐莲花的宗教学老师,布鲁克修完“中国佛教思想”,接着又修了“中国道家思想”。
为了搞清那些听起来云里雾里的佛、道名词,他又学起了中文。中文老师为他取了一个简洁响亮的中文名——卜正民。
上世纪70年代初,冷战的铁幕政治发生深刻转变。在各自寻求突破的可能性中,中美两国高层开始接触,一些民间的文化、教育交流通道由此打开。这给了学中文两年的卜正民一个进入“红色中国”的机会。
在文革后期的北京和上海,他以交流生的身份留学两年。在复旦大学,他跟着李庆甲教授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吃食堂里的白菜和土豆,和班上的工农兵学员成为好友。
回到西方世界后,他在哈佛、剑桥一路追寻他的兴趣,师从孔飞力、李约瑟,走上了中国历史研究之路。
回顾自己的人生故事,卜正民时常提到“幸运”二字。“我从没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过规划,也没设想过要有怎样的事业。那不是吸引我的事,真正吸引我的是思考有趣的问题。”
他常常提到90年代初和著名学者朱维铮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散步。途中,他吐露了身为外国人做中国史学研究的困惑。听完后,朱维铮把中国比喻为一间只有窗户的房间,自己是屋里的人,卜正民是屋外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屋里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
在《哈佛中国史》中文版总序中,这位“局外人”写下给中国读者的一段特殊心曲:
“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每一卷都有各自独立的声音”
人物周刊:在《哈佛中国史》的元明卷里,你对忽必烈、朱元璋两位王朝开创者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帝王,直至20世纪。你的依据是什么?
我之所以给他们这么高的评价,是我意识到忽必列、朱元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忽必烈入侵中国后,他把蒙古族的风俗、传统带到了中原,特别是关于国家、皇权政治,以及他如何确保汉人对他的忠诚。这引发了很大的后果,包括皇权继承制、中断科举制度等等,这些给中国人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的制度。但是,他是个强人,建立起一套新的帝国行政体系。
当朱元璋14世纪崛起、夺取天下时,他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忽必烈,尽管他声称他把中国人从蒙古人那里解放出来了,他也确实做到了。但是他对如何统治一个帝国的想法,很大程度上还是受蒙元的影响,譬如帝国该如何运转,禁城该如何,这些都是来自蒙元。所以,我在书里把元和明结合在一起写。
明朝并非和元朝是一刀两断的决裂,而是从元中产生、孕育的。朱元璋声称他把蒙古人赶出中国,但明和元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从蒙古人那里继承了很多元朝惯例。朱元璋决定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坐拥绝对的权力。他建立起一套杂糅蒙元和宋朝体制两方面传统的新体系,一套强大的政治独裁体制。这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未必都是好的,但这套体制被他之后的中国皇帝们继承下去。只是,那些中国皇帝恐怕没有像他这样有影响力了,大概只有清朝的康熙可以类比一下。
我并不想在书里花太多篇幅来讲述政治史。要记住,这本书本意是写给外国人看。所以,我着重关注几个最关键的皇帝,忽必烈、朱元璋和万历。至于其他的皇帝,他们是谁,娶的皇后和后妃是谁,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他们的施政纲领,我都一笔带过。
除了政治史,我想更多地讲述当时社会、文化这些领域发生的故事。
人物周刊: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把《哈佛中国史》和《剑桥中国史》放在一起作比较。你也参与撰写过《剑桥中国史》。作为主编和参与者,你会怎么比较这两套通史?
《剑桥中国史》的目标读者是研究生,而且不同章节由不同的学者合作完成;《哈佛中国史》是写给本科生和有兴趣了解中国历史的一般读者。
中国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这必定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但我想让《哈佛史》比《剑桥史》更简短一些,而且我想让哈佛史的每一卷有它自己独立的声音。由负责撰写的学者从各自研究、思考的角度来讲述他那一部分的故事。这样的好处是让学者有自由度去选取不同朝代的特点,但可能会让读者不容易形成逻辑一致的整体印象。
我们不需要再编写一套《剑桥中国史》,已有的《剑桥中国史》已经够好了。我自己也参与编写了其中一章,基于非常详细的研究。我们想写一套面向本科生和一般读者的通史,而不是研究生和学者。
这并不是我自己的主动意图。是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向我提议编写一套有关中国史的书。我和她见面第一次谈论这件事大概是90年代后期,当时他们出版了我的一本书。她说想要一套研究很深入的中国通史,既不是《剑桥中国史》那样的,也不是只有一种声音的那种有深度的作品。她问我可否组织编写,我说我来试试。
其实,我本人并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我的任务是找到专长于某个年代的学者,并且他要能够跟上该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因为我很希望这套书吸纳最新的东西,而不是还在重复十年前、几十年前的内容和观点。我希望他不但能把最新研究发现融入进来,还能从一个有意思的角度来阐述他的研究。期间,我联系了一些学者,有的说抱歉我达不到你的要求,有的说自己学术积累还不够。最后,我找到了另外四位学者一起完成这套书。
我只给合作者提了非常笼统、简单的要求:不能只是政治史,但要给读者提供一个基本的政治背景,要涉及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问题,以及他自己认为最有趣、最值得去探讨的一些问题。我尽量确保参与的学者能有足够的自由度来撰写他的那一部分。
我定下秦汉为这套通史的第一部分。然后,我和负责写这一部分的陆威仪讨论了他要写的内容。他最先完成其中几个章节,这为后面几卷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模式。我们彼此合作密切,并不要求大家都一致,但都要求把该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发现融入进来,同时要让它可以被一般读者理解和接受。
总的来说,《哈佛中国史》是面向本科生的、半学术风格的。
明的崩溃和“道德气象学”
人物周刊:在元明卷,你从气候和生态环境入手,不但意指皇朝的外部生存环境,还糅进了中国政治文化里特有的“道德气象学”。这种把政治运势和气候变化对比联系起来的方式,令我们耳目一新。你当初是如何构想这样一个角度的?
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晚明的历史。明亡于1655年,传统的叙述认为:明朝的崩溃是因为权力独裁、党争、伦理道德沦丧、商业化对农业社会经济的打击,类似这样的故事已经被人讲述了一遍又一遍。
然而,当我读到越来越多关于明朝时期的资料,我看到了当时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天灾频繁。从1630到1640的崇祯年间,气温平均比正常年份下降二到三度,帝国境内出现了普遍的干旱、蝗灾等等。在我看来,那正是明朝溃败的主要原因。生态环境的压力最终压垮了一个努力挣扎求生存的帝国。
我发现,元、明所处的时期正是气候史上的小冰河期。它始于13世纪,当时蒙古人正从北方入侵中原,气温到1640年代降至最低点,那正是明朝灭亡时期。
在这段历史时期,帝国境内的人们对气候变化都很敏感,因为一旦发生天灾,他们不得不去应对。人们通常也会试图解释天气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糟,这就是所谓的“道德气象学”。
生活在21世纪的人当然不会用“道德气象学”来解释天灾人祸,我们用火山喷发、太阳黑子、地壳运动这些科学方法来解释气候变化的原因。当时中国人解释灾害,基本是用道德逻辑。如果当朝皇帝做了无德之事,随后发生天灾,就会被解释为老天对皇帝的惩罚。
所以,我的最后结论是:来看一看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思考、理解气候变化的,我把气候变迁作为一种方式来解释明朝的那些动荡和危机。
人物周刊:用气候变迁来解释元、明王朝的崩溃,会不会有以偏概全的嫌疑?毕竟这是一套集体完成的通史,并非一部可供个人自由发挥的学术作品。
哦哦哦,(心急状)我只在我书写的部分引用了气候变迁的分析方法。你看,这个研究角度是非常新的。写这一卷时,正好是我对气象史非常感兴趣的阶段。当时,其他的合作者已经完成了他们所负责的各卷,我只在我自己写的这一卷里采用了这个角度。
你是否认为我写的这一卷太机械了?气候肯定是一个无法忽略的重要因素。明朝的崩溃当然不只是因为气候变化,仅仅生态环境本身解释不了任何东西。然而,当你试图去解释明朝为什么崩溃,如果不把气候考虑进去,肯定是不完整的。明朝的崩溃,气候异变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这就是我如此写作的意图和逻辑。
“徐光启是明朝最有见识的精英”
人物周刊:在你的书写中,明后期的官员徐光启被当作一个关键人物,他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的交往,他皈依天主教,他学习、翻译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等知识,他向朝廷提出引进西方技术来造火炮。这是出于把中国史放入世界史的范畴来审视的意图吗?
我着重写了徐光启,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值得关注的人物。我之前研读过有关他的史料。在回应外部世界上,他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是佼佼者:他皈依了天主教,和耶稣会传教士成为朋友,并和日本、澳门都有来往接触。他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去接触更为广阔的世界,对帝国以外的世界没有心存恐惧。
其实,他最最关心的是北方边境防御女真族入侵,就是后来入关的满族。他意识到明朝必须增强自身的军事能力。他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学到了包括几何学在内的知识。制造火炮火器需要运用几何学的运算,他发现从欧洲人那里可以学到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他有很实用主义的关怀。
他非常愿意通过异教的资源来学习这些专业知识。他不排斥基督教,他也不害怕欧洲人,心态非常开放。
可以说,徐光启是明朝行政体系里最聪明最有见识的精英之一。
人物周刊:元明卷专门拿出一个章节叙述明朝士人和普通百姓的信仰和精神状态。除了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高层士大夫,还有儒家思想的反叛者李贽。明后期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忽然集中地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探索世界和宇宙的意愿?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一个人对信仰的思考,是受许许多多因素共同决定的。16世纪末期,中国传统的儒家信仰出现过一次危机。学者王阳明倡导心学,他把知的根基更换为更主观的标准,也就是,所谓的“真实”不一定就是你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你的主观理解成为“真实”。
当时的一些儒家学者感觉到了信仰危机,他们认为儒家思想的根基受到了威胁。有许多读书人开始亲近佛教,他们对佛教思想很感兴趣,试图用佛教思想来补充、丰富儒家思想,把释、儒进行哲学上的融合。
徐光启对佛教很反感,他不认为佛教是一种合乎常识和理智的哲学。他后来选择天主教,因为他认为基督教教义更符合科学和逻辑。他倡导“补儒易佛”,以此作为对儒家信仰的补充。
这场思想危机集中爆发于1590年代,当时对已有儒家思想的不满和怀疑开始出现。一些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寻找别的思想资源,一部分人亲近佛教,极少数人选择基督教。
那是一段因缘际会的特殊时期。所以我会说,耶稣会传教士在1590年来到中国是很幸运的。如果他们是1550年代来中国,可能就做不了什么。他们来得正是时候。(拍掌)
人物周刊:明朝中后期,中国人和西方在贸易、文化、科技交流上的频繁与从容,和中国人19世纪面对列强挑战的那种惊愕与痛苦,形成鲜明对比。在你看来,明清对外的开放和封闭,和它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确实如此。但是,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满清入关、征服中国后,很大程度上关闭了和外部世界接触的大门。他们允许耶稣会士在中国停留,但把他们带进皇宫。事实上,康熙身边就有一群来自欧洲的学者,他们教他几何学、天文学。他学习了大量的西方知识,但是只限于皇宫里他自己学。所以,这些知识并没有机会进入社会,得到应用。
而在明朝,皇宫和皇帝们对这些外国人怀有戒心,万历皇帝就拒绝接见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所以,这些传教士进入了中国社会,他们带来的新知识在文人、学者的圈子里传播开了。
历史学家从来不做假设,我们只说历史发生了什么。但是,如果我可以假设明朝能够延续下去,那么中国和欧洲各自的历史就会非常不同。我不知道那会是更好还是更糟,但至少,中国会在17到18世纪继续与外部世界保持接触。
历史事实是清朝的皇帝们查禁、迫害传教士,中国变得非常封闭孤立,士人对外面的世界也变得抱有敌意。同样糟糕的是,耶稣会本身在欧洲也遭到来自天主教会的打压。中国和欧洲由此断绝了交流和交通,彼此怀有敌意,直到19世纪。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
“地方志帮我搞明白县一级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人物周刊:中国是一个修史传统很深的国度,一是有大量官修和民间的史料存在,一是几千年来正史都打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烙印。作为一名身在局外的研究者,你如何收集、选取研究资料?
目前,有关元明的大部分史料已经出版,所以我不太需要特地跑到中国来研究元明史。当然,新史料肯定还会不断被发现。大部分所谓的官修正史,如元、明史,都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它首要目的是为了论证后一个王朝崛起的正当合法性,和前一个王朝灭亡的必然性。所以,它是一种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文本。
但是,所有的史料都是有价值的信息。我会在某种程度上参考正史,更大部分参考当时的文人笔记和地方志。因为我发现:正史的最大问题是它所记载的都是发生在京城、权力高层的人与事,离普罗大众的真实生活非常遥远。而地方志能反映当时县一级的社会生活面貌。我非常喜欢地方志,它能帮我搞明白县一级的人是如何生活的。笔记更文学化,文人们会每天写下他的经历。
地方志、地方文人写的笔记,被我视作最重要的两种史料。我不太关注记录思想、哲学这一类的文本,更关注那些能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文本。
人物周刊:李约瑟、孔飞力是你的合作者和研究生导师。在中国史研究上,他们给你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在哈佛读博时,曾在李约瑟手下作过一年的研究项目。那段经历让我不只关注科技史,也关注起史学本身——就是如何组织起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李约瑟的卓越成就在于他肯定了中国有科学传统。在他之前,对中国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是儒教的,是不讲科学的。所以他挑战了之前西方汉学界的主流观点,提出了一种理解中国历史的新方法。
和李约瑟的合作,让我对中国历史如何被书写、编撰发生浓厚兴趣,以及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理解它。
孔飞力是我在哈佛读博时期的指导老师。他的研究堪称杰出。他对中国社会的人际网络,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在不同条件下的行为有非常深的理解。我想我对中国地方社会的兴趣,部分是受他影响。他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史学者。社会史研究是我这一代学者引入汉学里的,我的前一代还没有真正应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当你复原当时的社会关系,会看清楚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
在中国史研究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中国本土的历史家傅衣凌。他曾任教于厦门大学,在1950年代写了很出色的社会经济史著作,虽然那时还不叫社会史。他全力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基于地方史料做了很出色的研究。在当时,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想法。
我在1978年见过他一面。我们会面,聊了几个小时。他已经六七十岁了,而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研究生。我当时所知甚少,浪费了他许多时间。但他对我非常友好。我非常佩服他,认为他是文革前中国最好的明史学者。他是很谦和很安静的一个人,非常非常的老实。我很幸运见到了他。
“没有所谓的历史必然性”
人物周刊:能否谈谈你个人的史学观?
我个人的史学观非常有弹性,并不只依据某一个特定的理论。我尽量去理解——我认为,大多数人在他们的生活里是无力的,你会遭遇各种处境,你无法把控你的环境,有来自政府的管控,还有来自社会、来自家庭的压力。我的兴趣是研究芸芸众生感到无力时,他们是如何面对处境的。
所以,我会去追寻当时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经验,而不关注那些伟人伟业。譬如,我会去研究明朝的气候变迁,我也有兴趣关注权力关系,看它是如何发挥影响的,人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如何生存下去的。我所指的,不只是农民如何设法活下去,还有官员们,因为当时政治气候严峻,他们也背负着许多压力。
人物周刊:史学家总试图解释历史的起因和进程。你个人如何看待历史事件的因与果呢?
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有起因,困难在于确认到底哪些因素最关键。另一个挑战是“偶然性”,我不想说偶然,或许说“巧合”更合适。一个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另一个事件的发生。所以在历史上,没有所谓的“压倒一切的历史动力”。虽然确实存在着会导致事件发生的趋势,但是还存在着许多偶发的、并发的因素。譬如塞尔维亚发生的一起枪杀事件,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所以,你必须承认你无法解释所有事情的起因。当某个事件发生,你倒推回去,会想可能是这个因素导致事件的发生。这么做的时候,你可以教育自己:世界究竟是如何变得糟糕。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并不太平,一些小型战争在某些地区发生,譬如叙利亚局势就处于失控状态。一个小事件也许就会引发大危机。2001纽约双子塔的撞击事件,就是一桩异常事件,没有人预料它会发生。它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外交、军事政策。如果“9·11”没有发生,世界目前的局面会完全不同。但是,如果有其他事发生,国际关系的发展或许也会很不同。
所以,没有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当事件发生,你试图理解事件造成的影响。但是你必须接受:这中间不一定有必然的因果逻辑。
卜正民(Timothy Brook)
生于1951年,加拿大人。哈佛大学博士,现任英属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2015-2016年度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主编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代表作《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凯觎权力:佛教与晚期明士绅社会的形成》、《维梅尔的帽子》、《杀千刀》。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