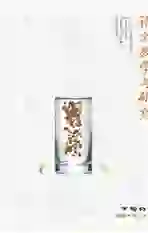山行
2017-01-05黄逸凡
黄逸凡
老僧提溜着一串色如琥珀的星月念珠,一身皂色海青,从山脚下向着山上一步步行走。
初夏的阳光微煦,洒在山林间,万物都闪着金光。清凉明快的溪水中,漂游着几群绿豆大小的蝌蚪。流水并不湍急,它们顺着流向游到弯道,随即溯洄到原处的河石间嬉戏。数日前它们还是一簇簇漂浮于水中的卵,如今它们已经能够自由自在游弋水中。一只白肚突眼的青蛙匍匐在岸边,碧绿的皮肤像穿了迷彩,和岩上的青苔混为一体。要不是眼睛时不时地灵动转溜,是难以被发现的。
老僧见此情景,微笑着默诵佛号,两三步便轻快地踩着光滑的河石越过了溪流,继续行走在小路上。
大雨是时有的。在午后匆匆地来,撒几番泼,又匆匆地去了。昨日里的合欢花便遭受了洗礼。原本合欢花开得极好。黛青的花托上抽发出浅红色棉絮一样的细线,丝丝分明,密织成一朵绢红娇媚的绒团。眼前,粉红的丝线脱离了萼,散落在地上,层层密铺,在方硬的青石路上成了一张花毯。
不久后就会有小沙弥跑到这里,将地上的绒绒落英拾起。回到寺里洗净、筛选、烘干,制成花茶或药材,封存起来。合欢安气凝神,服用后有百般裨益,就是不能使人增岁月、长合欢。老僧小心翼翼绕过地上花的残骸,手中念珠拨转了几圈,口中念念有词。
山愈行愈高了,周围的树林也随着行走的深入变得茂密、高大起来,路也泥泞、坎坷、曲折,越发难行。泥点有的爬上了老僧脚下的布鞋,有的跃上了老僧海青的下摆。
嘎嘎。
不知哪里传来鸟雀的啼声。循声向一株楠木上望去,是一只乌鸦停栖在巢边。它的尖喙上叼着一只不住挣扎着的蚱蜢,却没有将这美味吞下肚。它急躁地四处张望,又在巢中拨弄着什么。它开始不安地跳动起来,翅膀也一直快频率地抖动着。这略带诡异的一幕,老僧活了数十年,也未曾见过。这时,巢因这乌鸦的跳动,剧烈一震,一道黑影从巢中跌下,发出嚓的枝叶破碎声。走近一看,却是另一只乌鸦,已死去多时了。它双眼微张,本应尖利的喙有些发秃,无力地张开,柔软的细舌撇向一侧;羽毛枯萎,颜色杂乱不均;小腿呈不健康的土灰色,尖爪已经被磨得圆滑。树上的活鸦因巢的颠簸,一个趔趄,从癫狂中惊醒过来。它直直立着一动不动,如庄严的卫士。叼着的蚱蜢不知脱逃到哪里去了。“卫士”喉咙深处突然发出呜呜声。如歌剧厅里黑色燕尾服卷裹着的深沉咏叹调。
阿弥陀佛。老僧向天长诵一句佛号,给死鸦念了几篇往生咒,才稍稍心安,继续行走。
说来这山高路长,老僧紧赶慢赶,也行了整个下午。眼见得高山顶近了,太阳从林间探出脸,挂在西边。老僧有些累了,步履间带着一丝拖沓、冗赘。脸是红扑扑的,不知是急行所致,还是夕阳洒下的红光映在他的脸上。
一只大雁出现在老僧头顶,朝着太阳的方向飞着。它飞得极高,在远空成为一个孤零零的黑点。一路来,它不知经过多少颠簸磨难,没有伙伴的指引,找不到家,找不到北国,它便飞向太阳。
看那孤雁渐行渐远,融化在无边无际的红光中,老僧肃然。
菩提娑婆诃。眼前视野开阔起来。夕阳在身后树林打上如血的光辉,来时的路也映得殷红。老僧脸上仍然一副肃穆模样,脚步已然止住了。前方已无路,他不需要再继续行走,他此时面朝红阳,立身山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