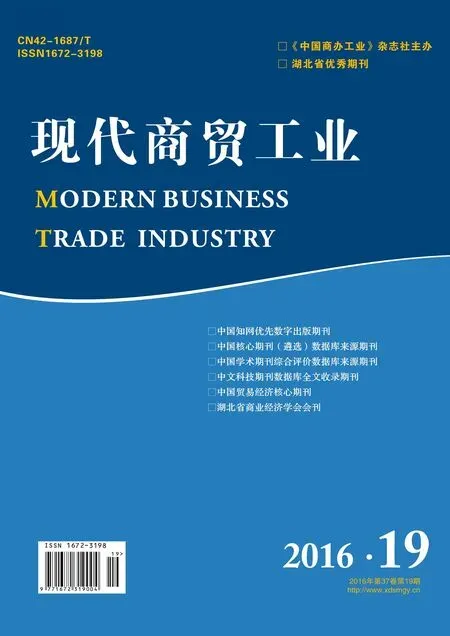守望乡土的精神感知
2016-12-30杜乐
杜 乐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生死百年》是闵良先生的第一部长篇文学作品,由黄河出版社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读罢此书,心中涌起的是阵阵对于历史发展进程中平凡人生活艰辛的五味杂陈。轻拂封面,隐形暗纹的乳白色似乎象征着中华民族质感而又丰厚的历史发展。几片看似无意飘零的落叶好似那沧桑的变迁。因为来到宁夏读书,因为对于文学执着的爱好,一部《生死百年》让我感受到的了宁夏作家在现今这个浮躁且追名逐利的社会下,仍旧保持一份乡土情结的可贵。作者闵良先生以平实的叙事方式记录了一个四川名叫举人湾的山村百年变迁中,家族间的生死情仇,深刻地折射出在近百年的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人生存的苦难,艰辛以及对于人性本身的关注与呵护。
回望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不论是鲁迅,王鲁彦,沈从文,汪曾祺到新时期高晓声,贾平凹,陈忠实,还是福克纳,马克·吐温,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都不约而同地将文学眼光与思考聚焦在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养育着自己的热土。乡土文学,以其承载着审视历史发展与关照人性幽微的担当,产生了极富丰沛的思想内涵与引起思索的优秀作品。这一部《生死百年》也正是这以创作路径的感染下,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回顾与讲述了百年变迁中,家族所走过的爱恨情仇,冲突与抗争。笔墨间饱含着“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情结。
小说中,作者以其平实,质朴的语言记录下载历史发展的车轮下,一代代中国人真实且艰辛地生存状态,更多地迫使这群以土地为根本生产资料的中国人接受新生且变幻莫测的时代变迁。作者在行文中,以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写起,饮食男女最能反映人类生活境况。哥哥与“我”的抢食,“我和哥哥经常为争论对方是否真的处于饥饿状态而大打出手”,但却也可以因为“吃”,“我们”竟也能“忘记了过去的不愉快,彼此原谅了对方,我们就像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妻,进进出出都拉着手。即使晚上睡觉,我们也越过原来横在中间的父母相拥而眠。当然,大人们并不知道我们这样要好源于共同的利益。”甚至就连年迈的“奶奶”也很“健吃”。这样“上有健吃而不能做营生的奶奶,下有待哺的孩子,我的父母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天奔忙着。”“饥饿”是人类最根本的生理需求,作者将几代人对于食物的渴望描绘得淋漓尽致,也从最基本的生存层面真实折射出时代发展中,不变的是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用写实的手法,完成回望故土的文学化方式。用饱蘸深情的笔触感受那个时代人性的幽微与生活的艰辛,进而深刻思索百年历史变迁中,中国人生存的艰辛与苦难。“吃竹笋虫的填肚,与饥饿的人试图剥瓜子解围的处境居然出奇一致,面前一大堆瓜子,哪怕手脚并用,肚子也永远难饱。”多年后“我小心翼翼地捧着巴掌大的细瓷饭碗,里面慢慢盛着一碗亮晶晶的白米饭,没有红薯,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来没想过吃干饭不需要红薯。”在小说文本前后的比照之下,作者记述了乡土社会的生活体验,真实地反映出时代变化,民族生存的深刻主题。因为在历史对生命的严酷考验下无非两种结果,一是死亡,一是活着。历史在冥冥中注定了一些人的命运,无论你如何挣扎你都不能逃脱,在历史面前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卑微的弱者,无意识的消亡者。小说中如此描写比比皆是,中国人在生存的艰难面前总是出人意料的可以活下来。一个苦难民族在历尽沧桑之后,背负着沉甸甸时代变迁的印记。
与此同时,一个民族或地域文化最为核心的便是乡土风俗的描写。中国自古就有酿酒,品酒悠久的“酒文化”。诗文中就有曹操“何以解愁,唯有杜康”的人生感慨。“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军旅豪迈,还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女子忧思。因此,作者在小说中,不惜用大段的文字描述四川不同于别处的“酒文化”,小说中书写有关“酒文化”就显得很有乡土特色。因为“我和母亲如此痛恨父亲并非空穴来风,我亲眼见过的就有好几场,那些烧酒在他们面前跟白开水差不多,正因为如此,多年后我才理解‘川人好酒’的真实含义。”就连“门市部里硕大无朋的酒罐与厂房里散发着香味的酒槽一起构成镇上最明显的标记。”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凡乡土作家都会以乡土风俗的记述作为其显著特点。汪曾祺启蒙笔下高邮地区风俗画小说,鲁迅笔下绍兴老家的“咸亨酒店”,“社戏”的回忆等等,都是将乡土中国中最能凸显其地域本色的典型风俗大加描写。在风俗习惯中,审视自我,深挖中国人伴随时代变迁的心理变化,进而对人本身的生存进行深刻关照。这沉静而又不哗众取宠的写作方式,在时下喧哗与骚动的时代中,显得质朴而又富于人文关怀厚度。作者用沉痛而又伤感的笔尖,叙写历史沧桑变化当中,生命坚韧的可贵,也同时体现出作者以一种无意识的写作方式表现出对乡土的眷恋与深情,表现出与五四那一代启蒙文学家对于人性,生存境况的深切关照的一致。无论是祥林嫂,九斤老太,闰土等的人物塑造,亦是对“三味书屋”,“社戏”等的典型环境的书写,鲁迅笔下构建的是绍兴老家的乡土生存变迁。而小说中,作者主要用四代人的生活变化,爱恨交织完成对乡土生活的书写,从而深刻挖掘民族心理,讲述内心深处生命与历史变化的抗争。
在仔细且饶有兴致的阅读小说过程中,作者有意识地塑造了“和尚”这一人物意象,象征着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数次出现的“和尚”总是以一种远离政治,远离社会发展,远离纷扰的世事纠缠的姿态“点化”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最简单却又深刻地生活哲理。这好似庄周“逍遥游”般思想的高度,将人的思考调整到远离尘嚣的境界来审视宇宙万物和世界的纷争,但却也有孔子积极入世的向上精神。在作者的笔下,不动声色地完成中国几千年深厚儒道的耦合。小说中,作者在叙述“文革”中两位和尚在口蜜腹剑大献谄媚之后,将完全不明事理,破坏道德生活秩序的“绿军装”带上了“不归路”,天龙寺最后的和尚,似乎象征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中,舍生取义的侠者风范,渴求人类失落的文明与道德。另一方面,也好似浮华背后作者新中国保留了一份美好且纯美的净土,是对人性的呵护与关照,也是对世间生灵的怜悯。
立体且真实的塑造“和尚”这一道德意象中,作者将人生简单却又常常忽略的哲理蕴含其中。小说文本中,这样描写,“和尚向他摊开右手。闵正千不解地问,什么?和尚说病呀,把病都拿来我才能给你治呀。闵正千下意识地再身上抓了抓,然后双手停在半空中,和尚哈哈大笑说,连病都拿不出来,我怎么给你治呀?施主你没病。说罢,和尚起身就走,还念叨万物不垢不净,不生不灭,烦恼由心,病痛由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得不感慨,作者独特的文学构思,从而深刻却又具体的加深了小说文本的文化历史厚度。作者深厚的文化素养与其文本所呈现出的小说意蕴无疑更加呈现出作为乡土作家根深蒂固地对于沉甸甸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敬仰与乡土生活的眷恋。这也区别于时下夺人眼球但又空洞乏味的流行文学作品形成了鲜明地对照,进而突显出作者对于文学的坚守与其清醒的认识。
作为典型乡土小说作品,我还窥探到作者在用一种直白的叙事方式,用看似简单的文学书写形式,呈现出生命的强韧。作者在叙写时代变迁中,以符合典型时代大众文化叙写时代特征。费翔“故乡的云”,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非诚勿扰”中宝马女的哭泣等等都显示作者在观照乡土的同时,与关注时代发展相同步的社会发展的时代性。纵览小说文本,作者笔下百年变迁的描述中,虽没有《白鹿原》般大开大合,不似《红高粱》般热血沸腾,但却记述的是质朴浓郁乡土家族的变迁,真实却又感动人心。
[1] 闵良.生死百年[M].银川:阳光出版社,2011.
[2]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