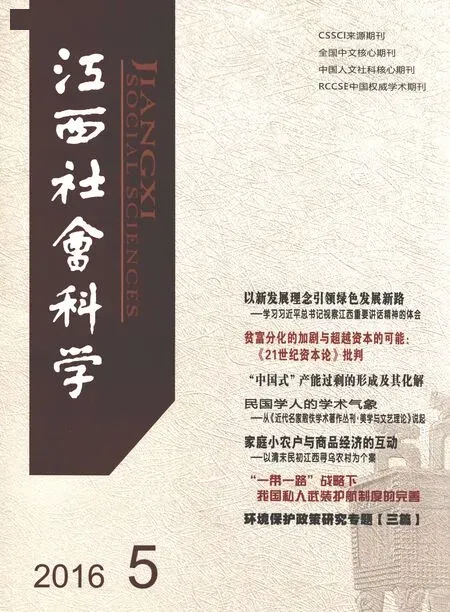家庭小农户与商品经济的互动
——以清末民初江西寻乌农村为个案
2016-12-19邹雄飞
■温 锐 邹雄飞 陈 涛
家庭小农户与商品经济的互动
——以清末民初江西寻乌农村为个案
■温 锐 邹雄飞 陈 涛
长期以来,传统中国农村的家庭小农户经济“被静止”为阻碍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然而,解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等史料,清末民初寻乌农村的家庭小农户,借助遍布于城乡的墟镇与商道,将自己的农业生产,多元兼业与打工经商,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于市场与商品交换平台,农民的身影在市场网络中则是随处可见。因此可以说,家庭小农户经济与当时水平的商品市场实已融为一体,可谓是“须臾难离”。
传统中国农村;家庭小农户;商品经济;清末民初寻乌
温 锐,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邹雄飞,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陈 涛,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江西南昌 330013)
随着中国农村改革实践和学界对于家庭小农户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入,将“家庭小农户经济”称为是阻碍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的传统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学者们进一步阐述了舒尔茨“理性小农”的观点:中国传统的家庭小农户经济具有“类似资本主义”的特点[1](P1),也可以成为新生产方式的“孕育母体”,兼具自发的“竞争、适应、转化功能”和“动态开放本质”[2](P3);家庭农场式的经营具有“效率最高、单产最多、技术吸收最快”等优点[3];在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进程中,家庭小农户经济实是市场经济网络中的一个个“网眼”,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驱力”与“活水源头”。[4](P368-369)
本文基于毛泽东1930年所作的著名《寻乌调查》及其他史料,以位处中国东南腹地赣闽粤三省交界的清末民初江西寻乌农村为研究个案,立足于遍布于城乡的墟镇与商道这组商品交换平台,从家庭小农户的农业生产、兼业打工经商、日常生活和市场网络中的农民身影等视角,全方位展示清末民初寻乌家庭小农户与市场经济的多向互动,并以此为典型个案,进一步佐证将家庭小农户经济“静止”为“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深陷的学术误区。
一、农业生产与市场的密切联系
尽管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特别强调,清末民初寻乌的农业生产总体处于传统农业社会阶段,但作为受到近代商品经济不断冲击的地区,与传统商品经济共生共存的寻乌农村家庭小农户经济从农业生产基本要素的配置,到土地租佃地租率的竞争博弈,再到农产品的流通,都无一不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土地、资金、劳动力、劳动工具等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源。在农业生产实践当中,家庭小农户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配置自己的生产要素。从史料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寻乌家庭小农户对于上述生产要素的配置即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的,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土地要素流转通过市场实现优化配置。在清末民初的寻乌农村,作为农业生产基础性要素的土地之佃、典、卖,都体现了市场化配置的特点。例如,在寻乌全部农村土地中,公共土地占40%,占全部农村人口总数不足8%的地富阶层占有土地的30%,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仅有30%左右的土地。[5](P105)这也使得当年寻乌地权占有严重不均,许多农民都缺乏赖以维生的土地所有权。然而,在地富阶层受近代商品经济刺激而普遍逐利工商经济大潮的情形之下,全部公共土地、绝大多数的地富占有土地,以及部分中农自耕农因距离家中较远或耕作不便而出租或佃入的土地,都是通过当时边区较为盛行的土地租佃制度及其市场化运作进行的,也促使土地与家庭小农户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优化组合,从而既为缺地少地的农民维生提供了重要条件,也实现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农地生产效率的提升。[6]再如,在寻乌农村,以土地典当(包括“过手典”和“不过手典”)和“卖绝”为主要形式的地权流转,也是在市场规范下并借助于市场交换来完成的。而随着市场供求、土地肥沃程度上下浮动的田地典卖价格,则进一步凸显了土地资源市场化流转配置的特点:典当坑田每石租为15元,塅田20元到25元;售价坑田每石租17元到20元,塅田每石租30元到40元。[5](P143-144)
农业生产的人工投入依靠市场调剂。众所周知,在不增加土地面积和提升农业科技投入的情况之下,投入更多的人工和“精耕细作”,就是传统家庭小农户普遍用来提升农业单产的主要方法。同时,农业生产的周期长、季节性强和劳动强度大等特点,也决定了农业生产需要通过市场机制调剂其人工投入。具体看清末民初的寻乌农村:家中或多或少带耕了“十几二十石谷(田)”的大中地主,农忙时节通常需要雇请一个长工帮忙,具备“万户”身家且人丁单薄者则要雇请两个长工才足以应对基本的农业生产所需[5](P124);除了大中地主要雇请长工、短工帮忙之外,“新发户子”(小地主中的一种)在农忙时期,也多需要雇请零工或雇工帮忙;即便终日劳作于农田的一般农民,出于“追赶农时”等需要,也可能有着雇请人工(部分是相互“换工”劳作[7](P412))帮忙的需要。上述农业生产中相应人工的投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助的性质,但其既是在市场交换原则规范和影响下进行相应人工补充或置换的,也与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紧密相连,特别是地富阶层雇请长工、短工、零工等帮忙,都是要“出工钱的”[5](P143),更是集中体现了其与市场的紧密联系。
牛力、种子和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需借助于市场调配。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对于当时占全部农村人口70%之多的贫苦农民生产资料状况的扫描,实际上就揭示出了短缺时代寻乌农民各类农业生产资料普遍缺乏的现实:贫民中的境况最好者(半自耕农),土地也“不够使用”;贫农中人口的最多者(占贫民总数60%的佃农),虽无自己的土地,但大多数有自己的牛,部分家庭甚至有两到三头牛;佃农中的穷困者,同样无土地,但犁耙等生产工具“多窳败”,本钱很少,牛则是几家共养一头或是替地主饲养,自己仅能“定得一爪子”;至于贫民中的最穷困潦倒者,则是无地、无本钱、无牛力、有犁无耙,甚至借米借盐都是常有之事。[5](P132-133)在如是情形下,为了保障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开展,牛力、种子及其他农业生产必备工具,就需要借助于市场的借贷来调配。例如,在当时的寻乌农村,贫民“为了莳田”,到了农历三月要借稻谷做种子。再如,农忙时节,缺乏牛力者要向亲友或地富租借牛力来耕田;缺乏或生产工具“窳败”的农民,则还需要租借或购买相应生产工具从事农耕生产。[5](P133、P147)
(二)市场机制中的地租博弈
土地租佃的市场化运作及租佃双方在市场机制影响下的多元竞争博弈,使得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土地租佃的地租种类变化、地租比率的确定以及高低波动,都深深刻上了市场的烙印,也凸显了地租博弈与市场交换的密切联系。
1.地租的种类
与学者们对于整个赣南闽西农村地租调研的普遍结果相一致,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土地租佃的地租也基本是以实物地租为主,货币地租并不占主体地位。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当年寻乌农民所缴纳地租,实物地租(谷物)占80%,按谷物价格折钱交租的“货币地租”占20%。而从《寻乌调查》可见,当时寻乌农村土地租佃还存在一些名目的“附加租”。例如,地主将田批给佃农耕种,五年一批的单批每石租收“批头钱”一毛,十年一批的双批则收两毛或三毛;再如,当时佃农承租地主土地,要每一年或两年给地主送一只“田信鸡”,双桥区佃农每年还要请地主吃一顿“田东饭”。[5](P140-141)
2.地租比率的博弈
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土地租佃的地租比率,尽管被有的学者认定为在50%—56%之间[8](P150),但依据对于当年寻乌地租比率的重新估算,如果将在当时农民维生中具有关键作用的土地“副产”(番薯、芋头等杂粮)纳入土地总产量计算,“实际地租率”就只有33%—37%。[9]另据我们在寻乌的反复实地调研,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各地仅有肥田的地租比率在50%及以上,贫瘠之田、山田则因无人愿耕而只收20%甚至于更少的地租。[10]
定格于当时寻乌土地租佃双方的地租比率博弈场景,其一,虽然土地收获采用“见面分割”之法,原定双方各半,“名义地租率”为50%,但遇有“撮谷种”之情形,佃户会在双方分割前先撮出一部分补偿因留秧田而来的损失。此种情形之下的地租比率,即便只计算“正产”,也明显会低于50%。其二,分享土地收获采用“量租制”分成之法的,主佃双方原本约定分获正产的5.6与4.4,但出于佃户“穷困日多”的状况和彼此利益的休戚相关,双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多按5:5的比率分享正产。其三,尽管在“定额租制”下,主佃双方原已商定分成比例、租谷质量及“半荒无减”等,但在农业生产遭遇灾荒或歉收之际,双方最终多是“精冇照分”。[5](P136-142)这种情形下主佃双方权衡实际的地租博弈,地租比率即便按正产计算也不会超过50%。其四,在客家民系聚族生活的寻乌农村社区,那些当时宗族民众很可能“都有份儿”的社区“公田”是被出租土地的主体部分,本族人或村中邻里承租耕种该类“公田”,还通常能照普通地租比率享受到“一至二成”[11](P595)的优惠。上述情形的博弈,便使得当年寻乌全县原本呈4:6之势的“见面分割制”与“量租制”,最终还是正产的各得半壁江山,甚或要低于正产的50%以下。
3.市场变化导致地租比率高低波动
19世纪60年代潮汕地区的开埠,使得寻乌因扼守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及其商品经济腹地商贸孔道而商品经济日渐兴盛,获利“更为丰厚”的工商经济也不断刺激和吸引着社会各个阶层争相逐利其中。这样,承租“公田”与地富的土地求取生存发展保障就不再是农民维生的唯一首选方式,从而也使得土地租佃制度盛行下的当时寻乌农村土地租佃比率,因受到市场供求等机制的影响而一度呈下降态势。
进入民国之后的寻乌,因长期受到战乱等的影响而使传统商道被堵塞,这也使得民众的外向型生存发展选择受限,民众对土地的依赖性转强,从而也同样因市场供求状况转换而致使地租比率呈攀升之势。至苏区革命前夕,寻乌农村土地租佃的实际地租比率便由33%—37%上升为38.5%。[9]
(三)农产品流通依赖于市场交换
《寻乌调查》中对城乡市场上众多农产品的罗列,在说明当时寻乌城乡商业繁盛的同时,也突出体现了其流通与市场交换的紧密联系。
首先,寻乌的农村圩场与县城市场充斥着各类农产品。循着毛泽东当年调研时的视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在当年寻乌吉潭、牛斗光、留车、寻乌县城、澄江、石排下等六大重要市场,还是在岑峰、篁乡、三标等普通小圩场,大米都是其中主要售卖的农产品和商品之一,且毫无疑问地成为第一大生意;而柴火、猪肉、猪子、鸡鸭、竹木器、各类小菜、鱼、水果等农副业产品,都是“不小的生意”,也在当时寻乌城乡圩场生意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5](P94-96)
其次,农产品在寻乌城乡出口货物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表1可以看出,大米、茶叶等农产品不仅是当年寻乌最主要的对外出口货物,还主要是通过境内外市场来解决其流通问题的。例如,在农地收获物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大米,除了供应给城乡居民食用之外,便主要是销往福建武平和广东平远、梅县等缺粮的邻近区域;茶叶则80%以上销往广东兴宁,向梅县输出的不足20%;木头的出口,基本上都是本地木材商贩协助广东龙川商人收购,销往龙川市场。[5](P52-54)。

再次,在当时寻乌城乡进口及商道通过货物中,农产品也居主要地位。油、豆、米、鸡、牛、猪等主要农产品是当时通过寻乌商道,挑往寻乌各地市场或是广东梅县等地发卖的 “大宗”。以茶油的进口为例,寻乌进口的茶油主要来自于兴国等地,仅澄江圩每年进口的茶油价值即高达十五万元左右。而牛的买卖,除了给寻乌当地政府带来丰厚的抽税收益之外,还使得原本无牛的寻乌县城出现了“每月逢一”(即农历的初一、十一、二十一开市)的“牛岗”,从而既解决了农业生产对耕牛的需要和市场对肉牛的需求,也带来了寻乌年均至少132 800元的牛市生意。[5](P48-51)
概括上述内容,清末民初寻乌的农业生产,从要素的配置,到市场交换的地租博弈,再到农产品的流通,都处于市场交换和商品经济的裹挟之中,从而也为农民于无处不在的市场当中多元兼业与打工经商奠定了必要基础。
二、市场中的兼业及打工经商
清末民初的寻乌农村,因人地矛盾尖锐、地权分配不均,使得农民难以停留在土地等传统农业生产空间谋生;再加上近代潮汕地区开埠及商品经济勃兴的刺激,便使得家庭小农户在勤力农耕求取基本生存保障的同时,积极探索出了外向型工商兼业,努力打工经商的谋生路径,从而进一步拓展了自身的生产发展与生活空间,也不断加深着其与市场的紧密联系。
(一)兼业打工常态化
耙梳相关史料可见,在清末民初寻乌贫困小农所从事形态多样的兼业活动当中,奔忙于传统商道和圩场充当挑米、挑盐、挑豆、挑油、挑杂货等的脚夫苦力是农村青壮年强劳动力进行兼业的最普遍方式;一根扁担、两条绳索或两个箩筐即是他们谋生的重要工具。在水、陆运输多靠“活人的肩胛”的清末民初,农闲之际的贫苦农民纷纷受雇于各类雇主,从事挑运、搬运等工作,构成了当时奔忙于赣闽边省际商道“苦力”中的主体。因而,在当时的寻乌城乡纵横数百公里的繁忙省际商道上,与南来北往的货流、物流紧紧相随的,便多是兼业讨生活的贫苦农民们。他们绝大多数是出卖劳动力,帮助老板挑运商品(米、盐、油、豆、杂货,也包括活的牲畜)南来北往,或是做排夫、船工、搬运工等赚取脚力钱。
尽管确切的农民兼业数据无从统计,但从文献的相应记载中我们并不难窥测到清末民初寻乌农民兼业大军之浩荡。毛泽东便估算指出,仅是通过寻乌商道的挑脚夫数,自安远挑鸡鸭等至梅县发卖而途经寻乌商道的日均100人以上,从石城、瑞金挑米至梅县的日均300余人[5](P48-49);在寻乌罗塘至福建武平下坝之间,以及连通广东兴宁、平远与寻乌篁乡的商道上,兼业奔忙的各类脚夫苦力们更是 “如同蚂蚁牵线”[12](P2-7),不绝于途。而据我们对包括寻乌在内的赣闽边区的反复调研,受访的老人(出身农民家庭者)几乎都做过挑夫苦力,他们多同时兼营小额的油盐、米盐或是日用杂货等的贩卖小生意,仅少数人是专门替别人挑担的挑脚夫。
尽管贫困小农充当“挑夫苦力”奔忙于省际商道辛苦异常,甚至还有“性命之忧”[13](P94),但作为其发展外向型兼业及寻求生活补添的重要方式,如是选择既丰富了农民们的生产发展路径,也使得贫困小农的身影得以多元活跃于当年寻乌城乡的市场网络当中。
此外,在农忙时节和农闲之际,受雇于各类雇主的短工或零工从事的多种打工行为,都是一种市场交换的兼业,也是农民适应市场需求常态化兼业的重要体现。如贫民多在农忙时节帮助地主从事犁地、收割等工作,农闲季节则主要通过帮地主摘木梓(茶子),帮助地主富农做房屋、冬翻土地以及处理婚丧嫁娶等急情大事的方式打短工或零工,兼取家庭农业收获之外的收入以补家用。据调查,兼业等杂收占到了贫农家庭收入的1/3。[5](P170)
(二)家庭手工业的延续发展
由于毛泽东当年的调研对于寻乌城乡的商业状况格外关注,因而其《寻乌调查》文本对于寻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城乡商品市场的繁荣也有着较为全面的揭示。
其一,手工产品充斥寻乌城乡市场。例如,寻乌城的木器店便向城乡居民供应着多种生活用具。常见的有台、凳、椅、桌、床铺、脚盆、招牌等生活用具,以及学校使用的黑板、课桌椅等木器。再如,工农贫民要使用到的便板子、提桶、水桶、饭甑、菜板等也多是从“插花”圩期的圩场上购买。[5](P83-84)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年寻乌贫困小农向家庭手工业的拓展,在为其通过家庭手工业品带来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当年寻乌城乡市场商品的种类,满足了民众生产生活的多样化需求,从而有力地助推了当年寻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二,寻乌城乡手工业者人数众多、行业分布广泛。在寻乌城2700余人口中,手工业者(包含手工工人、手工业主和商店店员在内)便多达297人,比例高达11%。行业分布则是遍及缝纫店、黄烟店、酒店、伞店、爆竹店、理发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饰店、洋铁店、修钟表店、屠坊店等;而在农村地区,农事闲暇时的农民也能兼做各类手工产品 (各种圆木和竹器),如饭甑、锅盖、桶子、水勺、脚盆、尿盆、竹椅子、簸箕、米筛、竹篮子等,有些农民甚至还能做台、凳、椅、桌等技艺要求更高的手工品。[5](P99、P170)
其三,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与手工业品的更新。梳理《寻乌调查》及相关史料可见,在近代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寻乌传统家庭手工业及其产品除了部分破败之外,还展现出与时俱进、发展更新的一面。例如,裁缝店做衣服,1920年前一概采用手工制作,十年之后变为“用机器的13家,手工仅3家”;衣服的式样,则在短短的3年(1920—1923年)之内,就由兴“破胸、方角、大边的上海装”转为流行“七扣四袋身很长的广州装”了。再如,伞店制作洋布伞,木器店采用进步样范制作木器,“乃社会需要的”打洋铁店从无到有[5](P79-93),既说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也体现了家庭手工业及其产品在继承原有技艺和样式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更新与进步。
需要看到的是,作为城乡商品(市场)经济繁荣重要标志的手工业的发展,既与农民中的强劳动力兼做挑夫、苦力相辅相成合理利用了小农户家庭的剩余劳动力资源,也为他们实现多元兼业、打工经商,以及推动城乡商品经济的繁荣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而也将家庭小农户与商品市场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三)投身商海闯江湖
清末民初寻乌城乡商品经济的勃兴,有效刺激了市场对于各类商品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为家庭小农户从事贩卖小生意、投身商海奠定了必要基础,从而助其不断丰富多层次谋生致富的选择。
首先,走村串户“敲糖子卖”等,从事较低层次商业活动,为寻乌底层农民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便对当年寻乌农民以此种方式参与市场竞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具体例证,一是兴宁人罗义成,本是穷苦农民,早年就来到寻乌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并由此发财致富,最终累积了千元资本,在寻乌城稳稳当当做起了老板;另一是当时寻乌唯一“现存举人”——古鹿苹(雇农之子),小时候因家庭穷没饭吃,便时常提个小篮子走村串户卖小口(糖子、荸荠、咸萝卜等)以换取微薄收入。[5](P63、P163)
其次,依据市场需求兼营农副产品小生意,是清末民初寻乌城乡农民贴补家用及参与商品经济的重要表现之一。在当年遍布寻乌各地农村形态各异的圩场中,农民多会依据自身家庭劳动力状况,顺应市场需求变化灵活从事各类小生意:其一,农民将平日节省下来的米加工成各类“米果”,在逢年过节之际,尤其是“会景”(迎故事或打蘸,均为客家传统习俗)的时候,卖“板子”(即米果,有软板子、铁练板、铁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鱼子板、苎叶板、番薯板、印子板等多种)的农民便会来回穿梭于城乡市场之间;其二,有粮食剩余的农民,在农业生产青黄不接、米价高涨之际,将米挑至市场发卖以赚取高额季节性差价;其三,缺乏本钱做小买卖者,则主要是上山砍柴火、种植各类小菜(芥菜、芹菜、藠头、苦瓜等)或蓄养鸡鸭等挑至市场发卖;其四,寻乌各地按照农历“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开市的“插花”圩期,因“日日有圩、天天有市”而使得农民能够随时入市。《寻乌调查》所提及的潘登记、何祥盛、刘恒泰、范老四等水货摊子,“并没有开张门面的店”,而是一四七圩期在县城摆摊经营,三六九圩期赴吉潭设摊赶圩。[5](P77-95)此外,在寻乌各地农村社区,还活跃着众多半营生意半营农业的小店铺。如《吉潭镇志》便记载,清末民国时期,该镇人口密集的村庄有多达上十家这样的小店。这些小店主要面向本村民众,本钱仅需十余个银圆和一间小房子,主要售卖香纸、蜡烛、鞭炮、油盐糕点等,这样既可赚钱贴补家用,又方便了邻里。[14]
再次,强劳动力农民在兼业做苦力的同时,从事长途贩运兼营小生意,既丰富了其维生的手段,也助其投身商海。因自身资本的缺乏,当年赣闽边地区强劳动力农民兼业主要是出卖苦力替商家或店铺挑运货物,或是在石排下、澄江、寻乌城、罗塘等上下货物的地方搬运物资。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挑运辛劳后,他们或多或少累积了一定的“血汗钱”。当这些钱被兼业农民用来贩卖食盐、布匹和土特产等商品挑往寻乌城乡自行发卖时,便转化成了商业资本,既能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升值利润,也使得兼业农民进一步地与商品经济活动捆在了一起。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所特别提及的,水货杂货店店主张均益,最初即由做挑夫苦力累积资本,而后借助于五六年来不辞辛劳地帮寻乌城商人挑米、香菇等商品去梅县,转而自己贩卖一些布匹、咸鱼、盐以及杂货等商品回寻乌城发卖的方式进一步增殖资本,最后才在寻乌城开设起店铺经营水货、杂货生意。[5](P77)
最后,成为商家商户,专事工商业经营或以此维生。梳理《寻乌调查》及相关地方志史料可见,农民在累积或借贷到了一定资本之后,基于自身已经或即将脱离农业生产耕作的现实,他们多会在城乡市场或墟镇设摊开铺,成为商家商户,这既为他们的生产发展拓展了维生的空间,也在事实上成了当年寻乌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寻乌调查》文本所列举的杂货店主罗义成、药材店主王普泰、伙店店主刘步权,就是此方面的代表。[5](P63、P78)
此外,清末民初寻乌地富阶层的商业性质表现尤为突出。他们本身即是由农民力作致富或经营小商业致富上升而来,在实现自身经济社会状况上升流变之后,他们中有的坚守着以原有耕种土地求生存的传统维生选择,也有的加工米子发卖或放债给贫苦农民,还有的积极顺应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竞相逐利于“获利更为丰厚”的工商经济大潮。即便是当年已经成为寻乌全县最大地主的潘明徵,在发家之初,仅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区区80余石(20亩)谷田,与一般中农并无本质区别。[15]其能实现自身经济社会状况的巨变,便是在坚持力农致富的同时,顺应商品经济潮流,灵活借助于市场网络的延伸及其所提供的诸多发家致富机遇,广泛聚集社会财富,从而不断跻身农、工、商、学等行业,最终也得以成就传奇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贫困小农兼业及打工经商的初衷在于“添补”生活所需,但上述行为的发生和完成,不仅满足和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维生需求,也在事实上加深了其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等与市场的紧密联系,从而既使家庭小农户的生产发展处于市场经济的紧紧包裹之中,也因其向上发展而为现代城市的发展孕育了必要的工商资本。
三、日常生活与市场密不可分
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广大农民时常遭遇的“禾头根下毛饭吃”困境,以及近代商品经济勃兴刺激下其多元兼业及打工经商的外向型发展路径,造成农民日常生活所需对于商品市场的依赖日深。
(一)日常吃穿通过市场调剂
聚焦清末民初寻乌城乡大小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农民从市场上主要购买的盐、米、油、豆腐、衣饰品等消费品可见,不仅“远道而来”的各类洋货需靠市场供应,而且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品也主要靠市场调剂。
例如,寻乌本地不出产的食盐是农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也是当年寻乌城乡市场最重要的商品。因此,仅有2700余人的小小寻乌县城,却有着“汇通”、“新发昌”、“韩祥盛”、“周裕昌”和“万丰兴”等五家盐店。据毛泽东调查估算,这几家盐店生意做得多的可年收入大洋两万余元,少的也有六七千元的收入,五家卖盐生意合计年收入十万元左右。[5](P58)再如,尽管大米在清末民初寻乌对外出口农产品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米生意在寻乌城乡市场的“失宠”。《寻乌调查》便显示出,农业生产力水平较落后的时期,无地少地农民有限的农地收获在交租、还债之后,往往会面临“禾头根下毛饭吃”的困境。换言之,当年寻乌城乡人口众多的无地贫民,在多元兼业及打工经商等赚取生活来源之后,也需从市场上购买或借贷谷米,这也正是当年寻乌农民从业选择与别的地方不尽相同,以及大米成为市场主要商品之一的重要原因所在。
此外,当时寻乌农民通过市场购买各类衣饰物品,也体现了其日常生活与市场的紧密联系。寻乌城乡市场上品种齐全、色彩丰富的土布、竹布、竹纱、绸缎、呢绒、夏布等,是民众衣料的主要来源。产自杭州的绸缎中的华丝葛、纺绸等,更是受到了城乡妇女的青睐而变成了“每个女人都有”的头帕。[5](P62)
(二)贫困小农仰仗市场借贷
纵观清末民初寻乌农民的生活境况,前述诸多限制因素导致他们的生活时常遭遇困境,特别是进入民国之后赣闽粤边区的长期战乱使得农民艰难摸索出的外向型兼业道路被堵塞,许多贫民在遭遇灾荒、婚丧嫁娶等大事急情,甚至于应对最起码的日常生活所需,都不得不仰仗市场机制下的借贷来解决。
具体而言,一般年景,贫民承租地主土地所得农地收获尽管相对有限,还要受到地租、债务等的分割,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仍能有限度地满足贫民短时间内的基本生存需求。这样,贫民只有在农历三月要莳田之际,或是农历四五月青黄不接时节,抑或是过年过节,才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向公堂及地主富农借谷 (米)或借钱买谷(米);但在非正常年景,即农业生产遭遇灾荒,或是贫民家庭遭遇婚丧嫁娶等大事急情之时,贫民维生就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宗族公堂或地富阶层,通过市场机制寻求钱物等方面的借贷救助。至于盐、食油、谷(米)以及农业生产工具犁、耙等实物的借贷,不仅本身多是商品或依赖市场供给,而且其借贷利息的计算和偿还都是依据市场行情或利率进行的。
尽管上述借贷行为可能未必完全是由市场主导,但从其借贷的发生到完成,无不浸润着市场因素的影响,且其借贷利息的高低时刻受到市场的影响并随其变化而上下波动。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实已对农民的生活空间形成了无孔不入的态势,贫困小农需要仰仗市场借贷赖以维生。
(三)丰富生活依赖市场取得
在谈及清初寻乌民性、风俗之时,当地文献多记载:“(吾邑)人民向称淳朴,勤俭是其本能,耐劳实出天性。”[16](邑俗)“布袍蔬食,不艳华丽;士敦操,尚惜廉耻;民力稼穑,女勤纺绩,燕(宴)会婚丧俭约,有唐魏之风。”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寻乌文献却多称当地风俗“(近今)稍尚侈靡,嗤朴素”[17](卷二《风俗》)。具体到毛泽东所调研的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即便是境况一般的农民,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当时的寻乌城乡,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与富,一律头上和手上戴着金银等装饰物,即便是再穷的女子,也都头发上插着银簪子,戴着银耳环;“稍微有碗饭吃的女人”,则必定有手钏和戒指。如是风尚,也使得小小的寻乌县城却同时经营有七家首饰店。在社会用伞方面,凡属“后生家”和“嫩妇女子”,不论工农商学何种出身,差不多一概都撑洋伞,而不再喜欢原来用的纸伞了。[5](P92、P82)
考究上述寻乌社会风俗及农民生活变化之原因不难发现,19世纪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开埠,以及沿着寻乌城乡商道不断涌入的大量物美价廉的近代工业品充实了寻乌城乡商品市场,从而较大地丰富和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是其重要诱因。尽管当年寻乌农村的一般农民基本维生都显艰难,日常生活也仍承袭着俭朴的传统,但随着城乡市场商品的不断充裕,农民生活所需对于市场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其日常生活也正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而渐趋丰富多彩,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农民日常生活与商品市场的密不可分。
总之,与前述贫弱小农发展农业生产、兼业打工等与市场联系密切并无二致,清末民初寻乌家庭小农户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始终浸润着商品(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
四、家庭小农户:寻乌商品经济的“活水源头”
清末民初时期,包括寻乌在内的赣闽粤三边农村普遍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矛盾,深处山区的寻乌农户,更是无法仅靠土地产出维持生活。但从前文所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寻乌的家庭农户表现出了吃苦耐劳、勤俭自励、发家致富的优点,他们本身就具有市场基因;加上潮汕开埠后对农户经济意识的影响,使得寻乌的家庭农户在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与商品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推动了寻乌境内外商道及市场的构建。在当时,就寻乌内部市场联系而言,吉潭、牛斗光等几大重要市场,以及遍布寻乌城乡的24个主要农村圩场[18],将寻乌全境串联成了一张彼此相连的大网;就其与外界联系来看,位居重要商贸孔道地位的寻乌城乡在事实上勾连着赣闽粤三省的省际商贸,南下广东梅县、福建武平,北上筠门岭、瑞金等地的货物客流多需在寻乌境内中转或需要借助寻乌商道通过。正是在这纵横交错的传统商道和星罗棋布的墟镇所架构与串联起来的巨大境内外市场网络当中,出于求取最基本生存发展保障的本能需求,被视为亟待“阳光”与“雨露”滋润的“马铃薯”们[19](P693),正以此起彼伏的身影、前仆后继地为着美好幸福生活挥汗洒泪,从而在其身影活跃市场网络的同时,也有力助推了当年寻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前行。这也造就了《寻乌调查》中所展现的寻乌(尤其是县城、吉潭、澄江等地)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换言之,即家庭小农户是当时寻乌商品经济的“活水源头”。
清末民初寻乌农村的个案充分表明,家庭小农户经济不仅不会阻碍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本来就是商品经济的“活水源头”与创造者;同时,立足发财致富的家庭农户经济,其发展也须臾离不开商品经济。以墟镇与商道及其向外延伸的市场平台,家庭农户经济与商品经济形成多向互动,两者高度契合,融为一体。显然,将家庭小农户经济“静止为”阻碍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的传统观点,不仅错谬百出,而且也割断了家庭小农户与商品经济“须臾难离”的内在联系。
[1]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M].太原:山西高校出版社,1995.
[3]赵冈.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
[4]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温锐.清末民初赣闽粤边区土地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4).
[7]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寻乌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8]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9]杨丽琼,温锐,赖晨.苏区革命前后赣南闽西地租率再认识[J].古今农业,2009,(2).
[10]寻乌县立中学基金会管理委员会赁耕字契1—6号[A].民国档案全宗号1[Z].寻乌:寻乌档案馆,手抄本.
[11]杨彦杰.长汀县的宗族经济和民俗[M].香港:国际客家学会,1996.
[12]武平文史资料(第5辑)[M].武平:政协福建省武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1985,(5).
[13]Lillie Snowden Bousfield.Sun-Wu Stories.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32.
[14]吉潭镇志[Z].寻乌:寻乌县县志办,手抄本电子版.
[15]潘作体.一个文盲农民创业发富誉扬三省边区的传奇[Z].未刊稿电子版,1999.
[16]谢竹铭.寻邬乡土志[M].民国版(电子版).
[17](清)王衍曾,古有辉.长宁县志[M].1907,活字本(电子版).
[18]寻乌文史资料(第3辑)[M].寻乌:政协寻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2.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王立霞】
K207
A
1004-518X(2016)05-0123-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家庭农场发展机制优化研究”(13BJY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