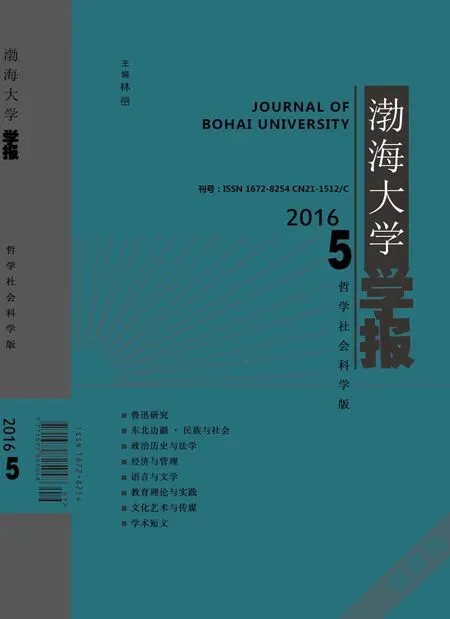从“理性主义”到“科学人本主义”
——关于当代教育观转变的哲学思考
2016-12-18侯金鹏陈晓英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侯金鹏 陈晓英(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从“理性主义”到“科学人本主义”
——关于当代教育观转变的哲学思考
侯金鹏陈晓英(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理性”与“人本”不仅是哲学领域中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两条主要路线。在理性主义哲学观和人本主义哲学观的影响下,这一概念势必会产生“理性主义”的教育观和“人本主义”的教育观。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目前的教育观是“理性主义”的。通过追问理性与人本在哲学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的相互关系,分析“理性主义”教育观和“人本主义”教育观各自的偏颇,进而指出当今教育观的转变应该从“理性主义”转向“科学的人本主义”。“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是理性主义教育观与人本主义教育观的辩证统一,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新思想。
理性;人本;教育观;理性主义;人本主义
在哲学视域中,“理性”与“人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潮流,总的来说,“理性”的潮流代表着一种逻辑能力和科学精神,它的追求是形而上的;“人本”的潮流代表着一种体验能力和创新精神,它所追求的实践是形而下的。
一、哲学视域中“理性”与“人本”关系的三种形态
在哲学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理性”与“人本”的相互关系也不同。根据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可以将“理性”与“人本”的关系概括为三种不同的形态:重“理性”而轻“人本”、重“人本”而轻“理性”、“理性”与“人本”的辩证统一。
(一)重“理性”而轻“人本”
重“理性”而轻“人本”,不仅是“理性”与“人本”关系的一种具体形态,而且也是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主要特征。可以说,从古希腊哲学产生一直到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重“理性”始终是每一个哲学家所追求的目标。而在盲目追随“理性”的同时,“人本”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当然,也有一些哲学家在追逐理性的潮流中看到了“人”的存在,比如古希腊时代的智者学派,其代表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了看待世界因人而异的相对主义的观点。他提出了著名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论断,第一次强调了人的重要性。在其后的苏格拉底也强调了“人”的存在。苏格拉底一生都在不断追问、探讨人世间的各种概念,与之前的元素论者追问世界本原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创始人笛卡尔和弗朗西斯培根,都被誉为是主体性时代觉醒的奠基人。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论断。从怀疑一切开始,最终导出“我”的存在,肯定了人本身的意义。弗朗西斯培根从知识论的方面肯定了人本身,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世纪以上帝为中心的形而上学体系。其后的大哲学家康德更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的认识能力的问题,提出了物自体和现象界的区分,调和了经验论和唯理论。
上述几个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了“人本”,但从本质上来看,他们又都是在肯定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基础上来探讨“人本”的。在他们那里,“人本”的思想尽管地位不同,但究其根本,仍都是在为理性服务的。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与当时崇尚诡辩的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当时的希腊奉行民主制,崇尚论辩技巧,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智者学派就是以诡辩而著称。因此不难看出,他所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支撑他的诡辩而服务的。诡辩仅仅是一种逻辑游戏,并没有切入到“人”本身。而苏格拉底可以说是古代与“人”最接近的哲学家,但是他所追求的“人”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形而下的人”,即虽然提出了人的“概念”,但没有切入到人的精神层面,没有去探讨人的生命力、思想力和创造力。因此,他的学生柏拉图随着他的思路创造了一个理念世界,也达到了古代唯理主义的巅峰。培根和笛卡尔两人都从不同的层面上看到了“人”,但他们所追求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他们眼中的“人”完全是为他们的知识观所服务的。康德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也不能说他就是重“人本”的。虽然他对于人的认识能力、人的情感等因素进行了探讨,但他依然认为人的很多能力是先天的,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进而没有注意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
从根本上来说,西方哲学发展到黑格尔之前,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都是找到一种科学的解释世界的方法,并认为这种科学一定是理性的,因此,他们并没有重视到“人”本身。无论是苏格拉底、奥古斯丁、笛卡尔、康德,还是黑格尔,他们都试图变成理性主义的大师,而没有去发现人的创造力、生命和精神。
(二)重“人本”而轻“理性”
重“人本”而轻“理性”,这是“理性”与“人本”关系的第二种形态,它也是近现代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潮流。这种“人本主义”在黑格尔之后曾一度占领了哲学的中心,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叔本华、廓尔凯郭尔、尼采、伯格森,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看到了生命的本质,看到了生命的创造力。叔本华将世界的本体归结为意志,现象界的所有事物都只是意志的不同表现。人类固然少不了理性,是理性使人类高于动物,但理性并不是万能的。“理性往往使我们失去知觉的敏感,理性的概念常常与具体事物脱节。即使在生活实践中,理性也不能很好地指导我们的行为。”[1]廓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更是强调了鲜活的人本身。对廓尔凯郭尔来说,生存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自觉的追求,追求作为自己命运的自我。这个自我既不是一个有生命的特殊的存在物,也不是唯心主义的那个形而上学的自我,而是一种可能性,是一个不能一劳永逸达到的目标,一个永远的任务,因此是一种持续的生成状态。作为西方非理性主义或“人本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尼采对于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变革作用。他提出了权力意志,人和超人的概念,并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他的所有这些批判都基于一个基本点,就是重塑生命的价值,肯定生命的伟大。尼采的变革在于他彻底变革了理性在以往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使人的生命正式回归到哲学的中心。其后的哲学家亨利伯格森,提出了生命的时间在于绵延,而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繁琐的数字。“当我们用语言或符号来表达生命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将它从变动不居的东西变为静止的东西,将它空间化。计算时间就是将时间空间化。传统哲学的‘规律’或‘必然性’的概念无法用于生命或绵延。这也意味着宇宙的每一瞬间都是创造,人的自由在存在论上得到了保证。”[1](67)
生命哲学的潮流一度占领了现代哲学的巅峰,它所崇尚的“人本主义”变革了人们理性主义的思想。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生命哲学家这里,“人本”固然获得了重生,同时他们也摒弃了理性,其结果必然导致重“人本”而轻“理性”。人本身的精神和创造力固然重要,但理性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尽管这种人本主义潮流很强大,很吸引人的眼球,但它完全忽视了理性的作用,所以必然是短暂的。
(三)“理性”与“人本”的辩证统一
在上文中,我们分别探讨了两种“理性”与“人本”的关系形态,“唯理性主义”重视理性的作用,但是它在抬高理性地位的同时放弃了人本身;而“唯人本主义”注意到了“人”的重要性,但却不加批判地反对理性,在强调“人本”的同时又忽视了理性的作用。因此,将二者融合起来,成为其后哲学家的主要努力方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很好地思考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唯物的,它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们认识这些客观规律需要通过人的理性。马克思在其哲学的认识论中又将理性认识理解为人类认识对象所要进行的第一次飞跃(人类的认识活动有两次飞跃,第一次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次是从理性认识上升到实践)。马克思是肯定理性的,但马克思也敏锐地发现了在他之前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机械性。之前的唯物都是片面的,都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2]可以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从人本主义的视角上融合了之前的理性主义,他看到了“理性”与“人本”的辩证统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他发展了创新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人本的视角上肯定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
“理性”与“人本”的辩证统一,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也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新趋势。在当今世界科学主义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形势下,强调科学观与人文观的融合、实证主义与人文文化的融合,这些相关思想层出不穷。“理性”与“人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而当下的教育观则更需要这种“理性”与“人本”的融合。
二、“理性”主义教育观和“人本”主义教育观的主要困境
哲学观是反映一个时代主流观点和核心思想的指向标,往往一个时代有什么样的主流哲学观,就会产生怎样的科学观、文学观、艺术观。当然,教育观也不例外。教育观既有属于自己的独有特征,同时也是众多观点相互融合的产物。我们在哲学的视域中探讨了“理性”与“人本”相互关系的三种不同形态,在前两种哲学观的指引下势必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教育观,即“理性主义教育观”和“人本主义教育观”,二者有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劣势。
(一)理性主义教育观及其缺陷
理性主义教育观是一种以实证教育为核心、以训练人的理性能力为目标,强调社会效用的教育观。它受“理性主义”的影响,重“理性”而轻“人文”,在教育的形式上强调逻辑思维能力和固定的学习模式,在教育的成果上追求实用性。在这种教育观指引下的教育模式能够很好地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提升学生的实用技术和技巧。在相对固定化的知识学习模式中,学生的学习能够更加专注,更有利于知识的扩充。但这种教育观的劣势也十分明显,正如理性主义哲学观轻视人文主义哲学观一样,这种理性主义教育观也轻视人文主义教育观。
其一,只注重以实证应试教育模式为主的思维能力训练,不注重培养学生的内在精神修养和创新品质,教育模式也往往是封闭式的教育。笔者认为,封闭式教育从整体上来讲弊大于利。教育的本质从哲学的角度来讲,是“使人成为人,继而成为某种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理解,即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教育不能脱离社会,教育的过程更不能脱离社会。封闭式的教学模式是教育脱离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教育模式将导致学生经过学习之后往往在理论上很扎实,但投身社会之后却连基本的生存能力都不具备。这种理论与实际的脱节,显然不是教育发展想要的结果。
其二,过于强调学生理性思维能力的训练,而忽视了学生人格品质的培养。众所周知,近年来已有多数违法案件的当事人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和博士生。他们虽然都是高学历,理论能力和科研能力都非常强,但他们的价值观和个人品质却是不道德的和自私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责任在学生个人;另一方面,责任在教育。如果教育能够培养很好的个人品质和修养,那么像这样的犯罪行为或许会减少很多。究其原因,是理性主义的教育观对于人文素养的忽视。
其三,理性主义教育观过于强调社会效用,导致出现功利主义的学习选择。理性主义教育观注重实际效用,在教育过程中往往过早地将知识专门化和专业化。“爱因斯坦批评的教育制度的‘过早专业化’和弗兰克批评的‘过于专门化的科学家的教育制度’,其根源还是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密切相关。因为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在实证主义那里,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因此,物理学当然只关注物理学的事实,化学只需关注化学的事实,等等。这样一来,不仅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而且各门学科下面的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也可能被切断。”[3]这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正是来源于理性主义的哲学观,专业领域内的过于专门化加强了学习过程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使得在教育领域里,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他们都只关注教育的工具价值、技术价值,而忽视了教育的人文价值。
(二)人本主义教育观及其缺陷
人本主义教育观是一种以人文素质教育为核心,以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和创造力为目标,强调人的精神修养的教育观。它受“人本主义”的影响,重“人文”而轻“理性”。在教育的形式上,人本主义教育观强调自由放任式的学习模式,不以应试为目的,专注于素质道德教育。这种教育模式充分尊重了人的自由,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让学习变得轻松,随心而行。由于不采用封闭式教学,学生能够充分接触社会,借此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但是,这种教育观也有其明显的弊端,即忽视了理性的作用。
其一,只注重学生精神品质的培养而不注重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导致了人的单向度片面发展。尽管人本主义强调“人”,但这个“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个非理性的片面的人。我们今天强调的“以人为本”,也不是以一个片面的非理性的人为本,所以,在这种狭隘的教育观下培养出来的人,一定是一个单向度的片面的人,一个缺乏科学素养的、过于情感化的、非理性的人。这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讲,必定是弊大于利。
其二,这种“人本主义”教育观不注重科学。在当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形势下,这种教育观必然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本主义教育观强调的是,只有非理性的生命体验、情感、意志、本能等,才是最真实的存在,是人的本质;而科学与理性只不过是人类意志的工具,并无实在的意义。这就是说,人本主义的教育观将认识与体验完全剥离开来,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同时,它以体验的世界为其根本,完全忽视了认识的世界,这必然导致人类认识思维的退步。
其三,这种“人本主义”教育观极度反对功利主义,导致其教育成果社会效用低下,使教育不能有效地为社会创造财富。人本主义教育观以人的情感、体验为基础,极度反对功利主义,这就导致了教育的实际社会效用低下,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在追求高效性人才的新时期,以这种教育观教育的学生往往很快被社会淘汰。
(三)理性主义教育与人本主义教育相分离的主要问题
通过分析理性主义教育观和人本主义教育观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可以看出,在教育观上,无论是“重理性、轻人文”,还是“重人文、轻理性”,都有其主要问题。如果将二者在教育实践中分离,不仅不利于教育观的科学转变,而且还会使教育本身丧失意义。
其一,理性主义教育与人本主义教育相分离,势必会导致“理性”与“人本”在思想体系上的进一步分离,最终导致双重层面的片面发展。教育观在根本上是以哲学观为基础的,如果理性主义的教育和人本主义教育在实际上相分离,则必然会导致相应的思想理论的分离,而思想体系上的分离最终会进一步导致实践上二者的分离。
其二,理性主义教育与人本主义教育相分离,会进一步导致教育与生活的脱轨。“教育乃生活之根本,如果将教育比作一棵大树,那么生活就是其埋在土里的树根,树的生长需要不断地从生活中汲取水分和养料,如果教育脱离了生活,就好比树身脱离了树根,树身本身失去了营养源,其必将成为一堆枯木残枝。”[4]可见,要想使教育回归生活,必须要将理性主义教育和人本主义教育很好地融合起来,只有让树和根相连,树才能变得枝繁叶茂。
三、从“理性主义教育观”到“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的转变
要想规避理性主义教育与人本主义教育相分离的问题,就要选择“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它是理性主义教育观和人本主义教育观的辩证统一,是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式教育观。
(一)“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的基本内涵
“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是集“理性主义教育观”和“人本主义教育观”为一体的新式教育观,在哲学体系上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辩证统一,在思想内涵上是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的辩证统一。“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不仅在理论上肯定了理性的重大作用,而且更主张以实践为基准,而实践的主体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既注重理性的科学精神、逻辑能力和指导作用,同时也重视人本的精神修养、道德品质和创造力。
“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是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这种教育观强调,在教育的同时,既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加强思考逻辑的严谨性和专注性,也注重培养学生在进行科研的过程中要秉承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注重自身的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这种教育观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个人身上的高度统一。
(二)向“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转向的必要性
目前,从整体上来讲,我国的教育观仍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教育观,依然是以应试教育为教育的目标。但是,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人本”的重要性,也正在从“理性主义教育观”向“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转向。
其一,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理性主义教育观”过早地将学生送进教室和课堂,又在大学阶段过早地进行专业化的分类,这种教育模式只能培养一批理论人才。而当今世界需要的是创新型人才,这是“理性主义教育观”难以做到的,所以,需要转变教育观,而“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无疑是我国教育转向的一条出路。“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是时代发展需要的一种新的教育观,它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其二,“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是“新事物”,它是由“理性主义教育观”和“人本主义教育观”孕育而成的,是对这两种教育观的综合与改进,因此,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是新时代应运而生的教育模式。
(三)向“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转向的主要路径
从“理性主义教育观”发展到“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其间需要经过两次转变,一是哲学观的理论转变,二是从知识教育到文化教育的实践转变。
首先,是哲学观的转变,即从原来单一的或是理性主义的、或是人本主义的哲学观,转变为将二者相互融合、辩证统一的哲学观。这种转变并不是随意的思想理论上的转变,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目前教育进程中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逐步进行哲学观的转向,再进一步到教育观的转向。
其次,是从知识教育到文化教育的实践转向。“说知识教育转向文化教育,并不是说知识教育不对,知识教育本身并没有错,它是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问题就在于目前的知识教育已经取代了文化教育,只见部分而不见整体,应试教育的问题也出在这里。这样就势必会导致知识与文化的分离、教书与育人的分离以及读书与做人的分离。”[5]所谓文化教育,从根本上说,它是这样一种教育:不再仅仅以知识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以知识为其主要内容,是包括知识在内的人的整个文化的教育。也就是说,让学生真正从旧的“知识的接受者”转变成新的“知识的创造者”,让教师真正从旧的“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文化的传授者”,让学生受益的不仅是知识的增长,更是文化的熏陶。
综上所述,我国教育观的转向应当从当前的“理性主义教育观”转向“科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即通过哲学观的转变带动教育观的转变,通过思想理论的转变带动教育实践的转变,使“理性主义教育”与“人本主义教育”有机地融合,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1]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
[2]庄友刚.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16.
[3]孟建伟.试析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分离的根源——从科学观与人文观的角度看[J].教育研究,2004(1):15-16.
[4]孟建伟.教育与生活——关于教育回归生活的哲学思考[J].教育研究,2012(3):13.
[5]孟建伟.从知识教育到文化教育——论教育观的转变[J].教育研究,2007(1):14.
(责任编辑陈佳琳)
G40-02
A
1672-8254(2016)05-0119-05
2016-04-03
侯金鹏(1992—),男,渤海大学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技术哲学研究;陈晓英(1964—),女,博士,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科技与社会研究。